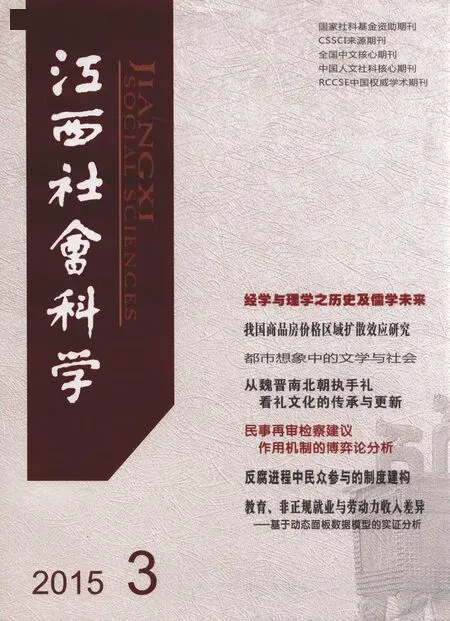“地方精英”视域下的宋代民间办学——以江右为例
邹锦良
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两宋教育发展亦有目共睹,官学历经“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以及“崇宁兴学”三次改革后臻于鼎盛,一方面学校数量大增,“州郡不置学校者鲜矣”[2](卷30),另一方面学生人数增多,“负担之夫,微乎其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子,尚日进一、二钱,令厥子入学”[3](卷12)。不唯如此,“日臻发达的书院教育、自成体系的宗室教育、特殊领域的经筵教育”使得两宋教育不仅领先于当时,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4]。在宋代崇文导向以及印刷术推广等因素影响下,民间办学活动获得发展良机。
在地方社会管理方面,宋代亦出现新趋势,如傅衣凌所说,基层社会的管理在宋以后大部分由民间组织承担。中国社会是一种多元结构的社会,从经济基础、社会控制的体系、司法系统到思想文化,都存在着“公”与“私”两大部分[5]。因此,伴随着宋代地方精英阶层的兴起,民间办学活动成为他们参与地方社会的重要途径。本文将通过梳理“地方精英”参与民间办学活动来关注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问题。
一、基础:“地方精英”之兴起
(一)从“乡三老”到“地方精英”
中国传统社会地域辽阔、民众分散,官僚制度难以顾及每个角落。因此,中央政权如何将效力贯穿于庞大疆域内的基层社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在传统中国的官方和民众之间,始终有一种社会机制在起着承上启下功能,或称之为“乡族势力”[6],或称之为“乡村社会中的民间权威”和“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7],或称之为“地方社会领袖”[8]等。事实上,夏商周时期便设置“三老五更”管理地方,《礼记·文王世子》载“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管子》一书中多次提到“三老、里有司、伍长”等乡里官员系统[9](P305),《墨子·号令》有“吏卒民无符节,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闾者失苛心(止),皆断”[10](P403)。延至秦汉,地方社会亦承袭三老制,“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皆秦制也”。“乡置有秩、三老、游徼……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11](卷12)可见,乡三老在基层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掌教化,为民众师”,而且“常就朝廷大事,地方政治特别是官吏的去留,当地的福利,作为民众的代表,领衔上书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往往都能得到当局的重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作用,并拥有很高的声望”。[8]魏晋亦承此制,“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乡佐、有秩主赋税,三老主教化,啬夫主争讼,游徼主奸非”[12](P1258)。同时还设立了“三长制”,“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13](P2855)。隋唐基层社会设置“乡里耆老”与“父老制度”,《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乡官》记:“大唐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他们掌握了在乡村中登记户口,统计田亩,催驱赋役、判理词讼等公权力[14]。
由唐入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中间阶层较之以往更为活跃。这个阶层在继承三老制基础上有了新变化。学者们对此关注甚多,对这一阶层的称谓殊异。有称之为“富民阶层”,认为“唐宋以来,富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对乡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乡村精英群体,推动乡村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长期保持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15]。有用“非政府势力”来概括宋代在基层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富贵之家等力量群体[16]。有称之为“乡村精英”,认为“两宋时期在乡村社会中有声望、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其架构在专制国家和普通民众之间,扮演着上下沟通的连接枢纽作用和社会控制作用的社会角色,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17]。有使用“民间强势势力”来概括宋代在一定地域空间内,具有某种资源优势而又非政府性的人或群体[18]。还有以“长者”来涵盖宋代基层力量,认为“宋代士族在基层社会的形象之一长者推动了地方公益活动的展开和地方的建设”[19]。“至宋,长者代替秦汉的父老成为民间权威的代表……宋朝长者在地方救济、公益事业、地方教化、乡村裁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对地方社会的支配权。”[7]美国学者较早关注这一阶层,并称之为“精英阶层”,他们认为:“到12世纪末,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南方地区,开始形成一种自存性的精英集团,他们掌握着基层社会主要的经济政治资源,已不如前代的精英阶层那么关心在全国政治中建功立业,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基层的安定与家族的进德延嗣。他们反对国家政权过多干涉基层事务,因此,从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精英阶层的雏型。”[20]应该说,美国学者所谓的“地方精英”阶层较为契合本文关注对象江右的地方社会发展情况,地方社会力量趋于多元化,他们有效地填补了国家行政和广大众民之间的“权力空隙”,在基层社会发挥主导作用,民间办学的兴起便是“地方精英”在地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显证。
(二)江右之经济文化基础
宋代江右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史载:“江南东西路,盖《禹贡》扬州之域,当牵牛须女之分,东限七闽,西略下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21](P2192)江右向宋政府上缴的漕运和赋税均位全国前列,“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22](P109-110)。
富庶的经济带动了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文化氛围之盛,嘉祐(1056—1063)中,吴孝宗作《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23](P682)因为强大的经济基础,宋代江右不仅州县官学高度普及,而且如书院等私学也蓬勃发展,因此,宋代江右的民间办学有着广泛的基础。
(三)江右之人才基础
宋代江右经济富庶,带动了文教发展,文教发展又促进人才涌现。史称“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24]。据统计,《宋史》列传中江西籍人物数量多达240人,宰相、副宰相级的显宦有25人。宋人罗大经对家乡人文之盛誉美道:“江西自欧阳子(修)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巩)、王介甫(安石),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朱文公(熹)谓江西文章如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皓皓不可尚已,至于诗,则山谷(黄庭坚)倡之,自成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25](P284)毋庸置疑,宋代江右人才兴盛是民间办学兴起的人才基础。
二、参与:“地方精英”与民间办学
在良好的地域经济与文化基础上,宋代江右民间办学十分兴盛,不仅在数量上领先于全国,而且在规模上也翘楚一时。地方精英中既有闲居地方的学者,又有暂无功名的士子,还有盘踞地方的家族等。他们通过在地方社会的特殊地位以及对地方公共资源的调配,积极参与民间办学。
(一)闲居地方之学者:从“明理修身”到“化民成俗”
宋代江右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使得闲居于此的学者数量颇多,民间办学活动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担当的重要方式。
北宋初年,洪州学者邓晏在家乡创办秀溪书院便是想在乡野中实现“修身”及“化育”之目标。邓晏以家学精于《易》创办“易南精舍”。太平兴国二年(977),江西安抚使王明“式新”洪州郡学,“下令访老成博达者充之,邑以邓先生名闻”,郡邑长吏、士人共举邓晏,邓晏执教两年成就斐然,“作人之效,月异而岁不同”,“当路迭勤奖荐,恳辞获命,乃谢事。诸生援之数四,志不回,愿执经从之西者众。而‘易南精舍’苦隘也,乃宗富者请广之,郡邑亦为资费”。在宗族、乡民的资助下,“易南精舍”扩建,“建大堂于后曰崇礼堂,中设孔子位,翼以颜、曾、思、孟,外困以门,周环以垣”,名曰“秀溪”。北宋著名文学家孔武仲有感于邓晏之民间办学活动,为秀溪书院作记云:“惟率以心,惟率以身,惟务和易,勤谨。夫勤谨则有功,和易则易从,以身以心则有典,则是以作人之效月异而岁不同。”[26](卷21)黄庭坚高祖黄中理在家乡双井创办了芝台书院,“广聚图籍达数万卷。诸子孙皆以文学知名……四方游学者常数十百人”,宋庠、宋祁兄弟亦曾挟策来游。至黄庭坚曾叔祖黄注,“乐以家资赈乡里,多聚书以招四方之士”。[27](卷14)
地方学者参与民间办学,首先是出于“明礼修身”之价值追求。信州刘允迪辞任德安知县后“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乡人之愿学者,亦许造焉”,其民间教育活动在当地影响深远。朱熹在评价其功绩时便说:“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则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所以自乐其身者,唯恐日之不足。虽廪有余粟,府有余钱,能毋为州里灾害则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刘侯者,身虽宠而官未登六品,家虽温而产未能千金,顾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则可谓贤远于人……古人之所谓学者,岂读书为文,以干禄利,而求温饱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国家而已矣。”[28](卷80)
同时,地方学者参与民间办学,与“继承道统”之追求亦密切相关。宋代儒生在重振儒学方面具有强烈使命感,从宋初理学先驱孙复、周敦颐、程颢、程颐到南宋理学大家杨时、朱熹、张、陆九渊等均热衷于办学,以传播和传承儒学。朱熹及其门生后人在江西办学、讲学门徒甚众,影响甚广。理学家饶鲁归居余干后专意于传播先贤之学,“四方聘讲无虚日,作月来馆以居学者,又作石洞书院”,先后“主白鹿、濂溪、建安、东湖、西涧、临汝诸书堂”[29](P2812),以此扩大理学影响。又如朱熹弟子陈文蔚曾在丰城龙山书院、宜春南轩书院、景德镇双溪书院以及白鹿洞书院讲学,传布理学思想[30](P231)。宋代“理学家每到一地,便热衷于建书院,聚生徒,著书立言,书院成为其学术创造与思想理论传播的基地。理学家也正是依托书院,其学术创造、思想论辩、理论传播活动得以顺利开展”[31](P180)。
此外,地方学者民间办学还出于一种“化民成俗”的社会担当。受传统儒家影响,经邦济世是读书人应有本质,发明先贤之道,化民成俗无疑是其中重要内容。对于笃信儒学、以之作为行动指南的学者而言,作育人才,教化民众,正是实现经世思想的必然要求。民间办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被赋予了社会教化的职责,社会教化是民间办学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功能[32](P359-377)。朱熹在修复白鹿洞书院时便指出:“境内寺观钟鼓相闻……而先王礼乐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阔,合军与县,仅有三所,然则复修此洞,盖未足为烦。”[33](P33)
(二)暂无功名之士子:从“自我实现”到“文化传承”
众所周知,在北宋,由于“江淮川广统一的完成,亟需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以及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等多种因素”[34],科举十分兴盛,录取名额较之唐代有大幅增加,读书人也随之大增。但科举辉煌的背后也产生了大量落第士子。暂无功名之士子包括积极应考科举和落第的士子,是宋代基层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在基层社会各种力量重构时期,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寻找立足点和领域,在基层社会公共空间中发展自己势力,确立本群体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35]。
宋代江右文教发达,暂无功名的读书人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优势,在民间办学中承担起优先职责。他们中有的办学首先是为了自我生活之需,宋代吉州安福县刘遇一边在地方教书,“授徒数十百人”,一边积极应考,虽累举不第,但一直都没有放弃。其子刘德礼“幼警敏”,也跟随父亲备考,亦屡举不中,念及“母老家贫复以授徒为生”。[24]乐平人马廷鸾考进士之前“甘贫力学,既冠,里人聘为童子师”[21](P12436)。
地方士子办学更多是出于文化传承之担当。永丰人黄惟直“自少以传习修洁为乡党所称,名卿达人争致以诲其子弟,既连蹇场屋,志弗克施”。于是他决定在家乡“举义塾,聚英材而教育之,以乐吾志”,他选择了“五山辐辏……宜为学者藏修之地”,“悉其力,建龙山书院……青衿来游,莫不竞劝”。[36](卷26)黄惟直无疑是希望通过“教书授徒”来实现文化传承。新昌人蔡羋亦如此,“力学不仕,筑义方书院”,为鼓励学子勤奋苦读,到该书院就读的学子只要“有志于学者俱廪给之”。[26](卷71)新淦人谢谔在中进士前在槐堂书院授徒,声名颇盛,来此求学者“北自九江,南暨五岭,西而三湘,东则二浙”,谢谔倾心施教,学子成绩突出,“或以学闻,或以行著,或以能称,或以文炳”。[21](卷131)毋庸置疑,门生学子自奋向学,从而将文化传承下去,这是办学士子十分乐意看到的。
(三)盘踞地方之家族:从“敦亲睦族”到“融入地方”
宋以后,家族制盛行,许多家族聚族而居,在地方上形成规模较大的社会基层组织,这些家族在维护地方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江右地方社会则出现“义族兴学”之特色。
江右家族热衷民间办学由来已久,可上溯到唐代桂岩书院,此为中国最早的聚徒讲学。曾任国子祭酒的幸南容为给本族子弟创造读书机会而创立桂岩书院,“日与诸弟课书其中,相勉以振”[26](卷120)。此后,鼎峙于江南的三所在当时享有颇高声誉的民间书院——江州陈氏东佳书院,南康洪氏雷塘书院,洪州胡氏华林书院——均是由义族所创。江州义门陈,聚族而居,达千人之众,室无私财,厨无异爨,陈衮“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26](卷120)。“建昌县民洪文抚,六世义居,室无异爨。就所居雷湖北创书院,舍来学者。太宗遣内侍裴愈赍御书赐其家。”[37](P867)洪州胡仲尧“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从学者数千人。岁时讨论讲习无绝,又以为学者常存神闲旷之地,游目清虚之境”[38](卷28)。
家族办学之初始目的为教育本族子弟,所谓“化行乡党民无讼,教得儿孙尽有才”。龙泉鲍氏捐己财助后学,建金斗学堂,“书堂之建,将聚乡族之子弟而教之”[39](卷14)。安福周奕彦建秀溪书院,“讲经有堂,诸生有舍,丛书其间,旁招良傅,以训其四子”[24](卷77)。旨在通过教育提高本族子弟文化素养,并希望他们通过读书入仕提振家声。贵溪高氏桐源书院记中便有:“高氏子孙读书于书院,当以古圣贤心学自勉,毋以词章之学自足。他日有自此而达于郡邑,上于国学,赫然名闻于四方,则书院不为徒设矣。”[40](卷9)由此而上,义族办学还兼有“敦亲睦族”之目的,所谓“学然后知礼义孝悌之教……一家为学则宗族和睦”[41](P7356)。江州陈衮家“合族同处,迨今千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26](卷120)。当然,家族办学在教育本族子弟同时,往往也会对乡里子弟乃至外地求学者开放,一方面营造出一种相互切磋交流的学习氛围,另一方面也借此扩大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以此融入地方社会。陈氏东佳书院、洪氏雷湖书院、胡氏华林书院均吸收外族子弟入学,使得三所家族书院均成为当地颇有实力的教育机构,家族势力无疑也随着扩大。也就是说,这些义族在倾力办学过程中,不仅扩大了家族声誉,而且使家族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之主导。故美国学者琳达·沃尔顿说:“建立一个向士人社会开放的书院,是一个家庭提高自身声望,表明其对地方精英身份诉求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投资,以财产来交换地位。”[42]
三、互动:“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
宋代江右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实现了良性互动,一方面,地方文化勃兴为地方精英发展提供了基础,江右亦成为培育和吸引“精英”的重要沃土。另一方面“地方精英”在逐步“获得社会声望和基层社会的某些主导权”[43]的同时,客观上也提升了地域学术文化水平,扩大地域文化影响,并推进地域文化普及。可以说,民间办学是实现二者互动的重要载体。
地方精英通过参与民间办学活动,并以此为依托进行学术活动,有力提升了地域学术水平。众所周知,宋代“学统四起”,学术呈现地域性和民间性特色。学者们身居地方总是努力寻求一个具有良好学术基础和传播条件的学术空间,文化浓厚之地便成为他们合宜的选择。宋代较为著名的地域学派中,如湖湘学就是由胡安国父子从开创湘潭碧泉开始,著书讲学,研治学问,此后张创城南书院,讲学于岳麓书院,使湖湘学“当时为最盛”[29](P1611)。闽学的发展与传承也是以民间办学为依托的,朱熹在福建及其周边地域创办数量众多的精舍和书院,并在此讲学和创作。在江右,朱熹也依托书院传播学术,他不仅修复白鹿洞书院,而且积极投身其他办学活动,尤其是通过在各个书院的讲学和会讲,在传播学术思想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江右学术水平。同时,宋代“江西之学”领军人物陆九渊以办学传播其学术主张,影响深远。淳熙十四年(1187),陆九渊建象山精舍,居山讲学,众多学者追随而至,先后求见请教学问的学者“愈数千人”,象山精舍遂成为学术传播的重要阵地。
此外,江右当时所兴起的诸多会讲,对于加深学术氛围和传承学术思想也裨益甚大。学术大师依托江右民间办学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会讲,使得江右学术高潮迭起,影响甚大。淳熙二年朱陆鹅湖会讲,长达数日,参与者除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四人外,还有著名学者刘清之、赵景明、赵景昭、朱泰卿等十余人。此次会讲给后世学术争鸣产生了深刻影响。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两人又在此进行了会讲,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话写出来,刻在石板上,编成《白鹿洞书堂讲义》长期保存。这些学术大师的会讲,不仅江右本地学子得以亲聆,还吸引了众多外地学子前来,杨万里所言:“士之自远而至者常数百千人,诵弦之锵,灯火之光,简编之香,达于邻曲。”[24](卷76)因此,江右也成为学术研究和传播的中心区域,有“北宋理学五子”之称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及李觏,南宋理学大家朱熹、陆九渊都曾在江右通过民间办学机构传布学术。“他们的加盟无疑提升了民间学校教育的质量和办学效益,他们的人格就是一种媒介,其足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一个教育传播的中心。”[44]
地方精英的积极参与还极大促进了地域文化普及与传播。民间办学兴起使一些偏远地域变得不再“蛮荒”,如“坐落在‘不文明’的内陆地区如赣州的书院,起着‘文明’使者的作用”[42]。一方面是通过他们的讲学活动,传播思想与文化,另一方面借助于民间办学的藏书推进地域文化普及。众所周知,藏书是衡量民间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大量的藏书必将弥补地域文化积累之不足,并促进地域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胡氏书堂“筑室百区,聚书千卷”,东佳学堂“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叶梦得在贵溪石林书院“聚古今图书数万卷”,朱熹在修复白鹿洞书院时积极筹书,“收藏应付学者看读”。学者们聚书首先是考虑就读学者之阅读,但同时也面向大众开放,如东佳学堂规定“不仅仅本族弟侄子孙阅读,而且在此学习的外来宾客,也享受同等待遇”[45]。因此,地方精英在地域文化普及方面影响甚大。
[1]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6,(2).
[2](明)彭大翼.山堂肆考[Z].四部丛刊本.
[3](宋)欧阳守道.巽斋文集[Z].四部丛刊本.
[4]姜锡东,魏彦红.近十年来宋代官学研究述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2).
[5]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3).
[6]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一个探索[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1).
[7]杜芝明,张文.长者与宋朝社会[J].云南社会科学,2011,(2).
[8]牟发松.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J].文史哲,2006,(6).
[9](清)戴望.管子校正[A].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0]罗炳良,胡喜云.墨子解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1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南朝)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谷更有.乡治方式的传统与变迁——唐宋乡村控制与社会转型系列研究之一[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15]林文勋,张锦鹏.乡村精英·土地产权·乡村动力——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启示[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4).
[16]王华艳,范立舟.南宋的非政府势力初探[J].浙江社会科学,2004,(1).
[17]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J].社会科学辑刊,2004,(2).
[18]廖寅.宋代两湖地区民间强势力量与地域秩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9]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J].新史学,1993,(4).
[20]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N].光明日报,2000-11-03.
[2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3](宋)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4](宋)杨万里.诚斋集[Z].四部丛刊本.
[25](宋)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清)谢旻.(雍正)江西通志[Z].四库全书本.
[27](宋)袁燮.羍斋集[Z].四库全书本.
[28](宋)朱熹.晦庵集[Z].四库全书本.
[29](明)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0]李国钧.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31]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2]肖永明,唐亚阳.书院与社会教化[A].中国书院[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33]毛德琦.中国历代书院志[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34]王瑞来.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J].国际社会科学,2009,(3).
[35]黄云鹤.宋代落第士人参与基层社会事务问题探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3,(8).
[36](宋)真德秀.西山文集[Z].四部丛刊本.
[3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8](宋)徐铉.骑省集[Z].四部丛刊本.
[39](宋)袁甫.蒙斋集[Z].四库全书本.
[40](宋)汪应辰.文定集[Z].四库全书本.
[41](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A].中国方志丛书[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42](美)琳达·沃尔顿.南宋书院的地理分布[J].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1).
[43]宋燕鹏.试论南宋士人参与地方公益的外在动因[A].宋史研究论丛[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
[44]张雪红.南宋教育重心的下移与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的新特征[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45]王河.南宋书院藏书考略[J].江西社会科学,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