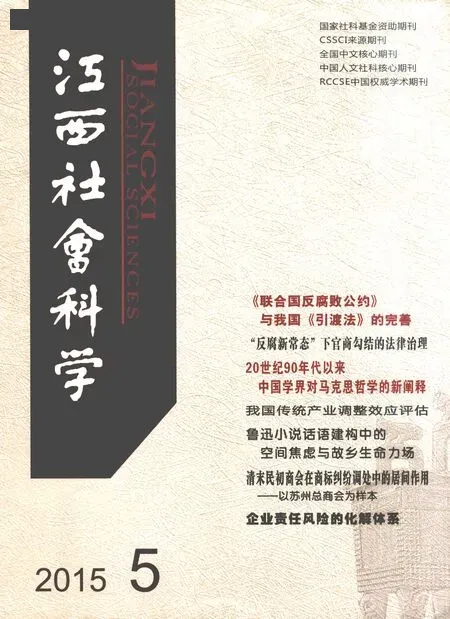濒危语言的逻辑辩证、社会学因素及其复兴路径
■卡米力江·阿不都克力木 阿尔斯兰·阿布都拉
据语言科学家统计,世界上现有语言6000余种,只有5%—10%的语言是安全语言,其余全部是 “濒危语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一次用“语言地图”的形式绘制了一个《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展现了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该组织发布的等级量表数据,目前全世界97%的人仅集中使用4%的语言,3%的人说着全球96%的语种,有3000多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只有10000人左右,其中大约有2500种语言濒临灭绝,538种语言面临极度灭绝危险,502种语言面临严重灭绝危险,632种有确切灭绝危险,607种存在灭绝可能。[1]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减少,预计在21世纪结束时,世界上将有95%的语言消亡或合并。令人欣慰的是,语言的濒危问题获得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等方面的广泛关注[2](P85)。语言濒危现象已成为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危机,是当代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因此,这一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对这些语言进行保护、抢救、记录已是刻不容缓。
一、全球化时代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濒危问题
近20年来世界濒危语言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也存在若干问题。主要有:第一,缺乏世界公认的语言信息数据;第二,对濒危语言研究的性质和目标认识不同;第三,对世界语言的名称没有规范化与标准化的对照;第四,对濒危语言的保存与保护缺乏统一的认识。国内外语言学界在全球语言的发展趋势研究领域上有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在不同语种的不同洲、国家和地区的衰退分析以及全球语言的相关数据等方面。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下,给予丰富多彩的文化以平等的表现舞台是全人类追求的目标,保护语言种类的多样性就是保护文化生态平衡。保持语言种类多样性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已经消亡或者开始衰退的语种上,怎样在最大程度上针对不同的濒危语言进行研究等[3]。“濒危语言”这一命题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之后,国际语言学界在近百年以来针对语言濒危现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语言学界达成了濒危语言保护、濒危语言问题制度化的共识,尤其是最近五六年濒危语言问题研究如雨后春笋,并且在该问题上取得初步的成效。“濒危语言”这一概念的提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弱势语言的消亡与对濒危语言问题的认识,有利于人们对语言演变规律与语言结构的认识。
美国建国以来,印第安人的土著语已经有150多种不复存在,尤奇语这一种“与世隔绝”的语言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说这种语言的人数由起初的数万人锐减到现在只有5个人。美国政府面对这一“与世隔绝”语言濒危的问题,正在以录音和录像的方式在儿童中间进行普及,试图通过语言的复兴缓解全球部分族群的濒危母语。美国政府的复兴尤奇语这一举措并非空想,历史经验表明,公元前70年,犹太人的都城被毁掉以后,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从此只能使用寄居国的语言,希伯来语(犹太人的土著语言)仅仅只在少数的英裔巴勒斯坦人与土耳其人中使用,但现在仅仅在以色列使用希伯来语的人数就超过700万。再譬如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语,这一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8个高龄老人使用,阿伊努语濒临灭绝,但后来这种语言经过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让当地的后人学习自己的语言,目前阿伊努语使用的人数正在慢慢增多。再例如新西兰的毛利语,政府实行了 “语言小巢”的计划以后,现在毛利语已成为抢救濒危语言的典范。语言的多样性犹如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虽然诸多土著语言正面临着全球化、工业化、互联网等的冲击,但是这种消亡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
语言作为一种沟通工具,也是一个信息贮藏库,承载着民族的兴衰。语言的消失伴随着非物质文化的消亡,特别是传统和口头(诗歌、传说、谚语和笑话)所组成的珍贵传承的消亡[4]。保护濒危语言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生物多样性”,语言的消失同样损害了人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平衡。当今平均每隔10到14天,就有一门濒危语言绝迹于世。时至今日,现代技术已使得常见语种的学习空前便捷:语言可以录音传播,也能迅速归档分类。通过游戏式的教学,云端数据库和形形色色App的应用,外语交互学习更是直达前所未有的便利程度。
因此,有前瞻性的探索者们纷纷将宝押在了科技的力量上,他们期待以科技来实现濒危语言的复苏乃至灭绝语言的复活。这些尝试正在结出硕果。(1)欧洲:挪威北部的萨米语被编入了可供下载的网络字典中;盖尔人的博客正不断分享着爱尔兰语的学习经验;马恩岛语的学习者们正在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来提升他们的熟练程度。(2)北美:纳瓦霍人开发了一套光盘自学课程;彻罗基语的学习者们建立了一个虚拟交流平台;加拿大马尼托巴湖的齐佩瓦人与美国温尼贝戈人正在使用iPhone应用扩大语言的影响力。(3)非洲:肯尼亚口语的数据库已于近日建立;马里以文字为载体,传播其著名神话传说的同时也致力于拯救其文字;某网校公司现特意为金丝雀岛口哨语开设了课程。(4)美洲中南部:巴西破天荒地为齐斯基语言编译了语言管理文档;萨尔瓦多为皮皮语编撰了一本会说话的字典;巴拉圭的阿切尔人自述录影带也在筹备制作中。(5)亚洲:中国为少数民族语言制作了许多在线绘画朗读故事书;Youtube上已经开设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语课程;印度地区多达780种未入库的语言现已全部入库并列表规划完成。(6)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因纽特语课程正式在因纽特官网上发布了。(7)中东:迦勒底人通过在线讲故事的方式将伊拉克语逐步发扬光大。(8)大洋洲: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语与太平洋的许多小岛语现都有了视频学习的站点。
上述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语言濒危的速度,但是对于全球6000多种语言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性了,许多国家先后设立专项基金或成立各种机构,在资金和政策制度支持的基础上,带动了许多的语言学家投入濒危语言的记录和研究之中,这一举措的发展与倡导为濒危语言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
二、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逻辑辩证
近年来,濒危语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语言的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层面。语言多样性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每一种语言的消亡都意味着人类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损失。语言保存着人类对文化创新和语言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部鲜活的民族史、文化史。流传在民间的故事、神话、谜语、诗歌、唱词、传说等精神财富,它们的延续与传承都需要依靠语言,这种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被取代的,并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加以传播,如藏族的《格萨尔》、彝族的《阿诗玛》、壮族的《百鸟衣》等等。乔姆斯基曾经指出:“任何一种语言代表着一种思维系统,语言是一切可思维对象的总和,体现着本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这种结构系统深藏在语言内部,每一种语言都体现着他的共性与独特属性。因此,人们担心语言多样性的丧失是否会导致人类思维方式单一化甚至退化[6](P58)。语言的失落将会是全人类的悲剧,一种语言消逝的背后,不仅仅意味着不同世界观的消亡,更重要的是沉积在语言当中与我们相关的自然、地理、生物、医药等各方面的积累消失。例如,世代以放养驯鹿为生的西伯利亚图法拉尔人,在其语汇中有不少描述驯鹿皮色、花纹、头部标记以及生活习性、个性等综合信息的语汇,这对研究野生动物的进化史来说弥足珍贵。从研究价值和保护的角度来看,记录和保存濒危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际语言生活。
语言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认识语言的构造、功能及其演变规律,土著语言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也面临着怎样认识濒危语言、如何展开对濒危语言结构特点的研究、如何确定濒危语言的标准等问题。影响语言濒危是社会因素综合的结果,目前“濒危语言”研究只处于起步阶段,由此决定了对语言濒危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在复杂的语言领域中,语言是否濒危、濒危的程度都没有客观的判断,当然,我们也不能从定义入手,将所有功能衰退的语言都列入濒危语言行列,濒危的语言到一定的程度后不见得就走向消亡,因此,如何界定濒危语言的标准尚未统一,但是对濒危语言进行记录是应对语言濒危问题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一项举措。就语言学本身来说,思维无法自我表达,需要借助语言来形成思想完成储存或者表达,深挖土著语言中蕴含的智慧与语言资源积累的丰富程度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点也衬托出对语言的记录与收集是解决语言濒危的基础。
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语言的多样性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7]如今人们都知道语言濒危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濒危语言走上语言复兴之路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人们时常误以为这只是那些濒危语言社区的问题。文化是语言的精神家园,弱势语言的消亡更多的是忧虑与精神家园的丧失。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濒危语言的深入田野调查,人们越发深刻地意识到语言濒危的影响已远远超出语言学领域,更多的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凝聚体,这些问题直接反映着社会和人文层面的问题,如怀旧与现代化、语言权利与伦理问题、记忆与忘却等。[8](P23)在社会交往中因民族文化习俗的不同而导致语言的不和谐现象,语言知识的匮乏、文化信仰的危机、和谐理念的含混都可能造成语言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往往会陷入尴尬的境地甚至触犯对方的禁忌,甚至引发不必要的冲突。语言濒危问题,轻则影响正常的交际与交流,重则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与矛盾。语言的濒危或者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淡化给社会带来的更多是精神与社会稳定的危害,而不是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单一语言更有利于交流。因此,应及时采取措施对策,保护世界语言的多样性。
三、语言人类学视野下语言濒危的社会学因素
濒危语言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语言学和语言本体状态等方面进行,更应关注社会历史条件和语言演变的内在驱动力。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一个民族千百年间积累的知识经验,记录着人类知识的一个侧面和局部,共同构成人类知识和财富的宝库,同时也是发展语言学的重要资源。据语言资料表明,语言资源能够成为揭开历史上谜团的钥匙。因此,对即将消亡的语言资料进行抢救性记录和保存,不仅是对语言学研究,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更能促进语言规范化、现代化和社会和谐化的共同发展。
语言濒危乃至消失的原因有两类,其中由于主动的语言转用造成的本族语消失是产生当代语言濒危现象的主要原因。其次,影响语言转用的还有人口比例、文化基础、经济优势等多种基本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对语言的使用是不可估量的,最终由取得优势的因素决定语言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带动了不少落后地区的发展,却也同时给各地居民的语言带来了一场“大浩劫”[9]。为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说小语种的青年人纷纷舍弃自己的母语,转向英语、汉语、德语、法语等更具世界影响力的大语种。这不得不说是全球化的一大副产物。使用者很容易把运用广泛的语言与机会相联系,而把使用范围小的语言与落后相联系,因此他们停止向自己的孩子讲使用范围小的语言。除非这种语言具有书面文字,否则一旦某代人不再把它传授给头脑具有最大程度可塑性的儿童,这种语言差不多就灭绝了。我们都知道,成年人学习一种语言是多么困难。因此,在一些相对闭塞或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他们的母语相对而言都保存较好,但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周边,语言消失或融合的速度远远大于相对闭塞的地区。地理特点对语言存续的整体规律有着重要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载体的小语种在互联网、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被边缘化、加快衰弱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背景下,语言的多样性遭到严重的破坏与“灭绝”。对现代观点而言,有书面文字的语言看上去正规并且“真实”,而仅在口头上使用的语言看起来将逐渐消失并且有些狭隘。除此之外,语言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决定了语言的态度,强势的语言往往更具有吸引力,不同的文化在相互交往接触的过程中导致思想观念、生活模式的改变或放弃,必然导致弱势语言因缺乏“经济价值”而无人问津。导致语言濒危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语言机制的内部矛盾,语言内部矛盾表现在语言作为纯工具与获得收益的工具,语言的工具性在社会发展中被不断放大,从而导致语言的文化认同以毁灭性的姿态呈现,于是在恶性循环中侵蚀着语言生态链。互联网的兴起让小语种处于被遗忘的弱势地位,与目前拥有6000种语言相比,到2115年地球上可能仅存留约600种语言。对此,美国语言学家David Harrison将这种情况称为 “三重灭绝威胁”——“物种和生态系统正在崩溃”“越来越多的小的、未书面化的语言正处灭绝的边缘或者消失的状态”“随着生态系统和物种的消亡,知识也会失传”。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界殖民战争,它已经多次导致了语言灭绝:本土使用者使用自己的语言,会遭到灭绝或惩罚。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毁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自然灾害、疾病、战争等灾难造成母语遗失的高达1000多种,这一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10](P178)澳大利亚人在受殖民之前,共有700多种语言,在白人入侵以后土著语大幅度减少,有95%已消失殆尽,如今只剩下不到50种。殖民运动对澳大利亚土著语言是一个极大的冲击,那些累积在岁月里的故事、神话、谜语、诗歌等都因语言的消失而被摧毁。澳大利亚土著语消失的主要原因是殖民入侵导致土著政治地位较为低下,他们致力于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放弃本族语,进而促使土著语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失去了紧迫的生存或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被迫性的主动选择也是造成语言濒危的一个重要因素。拉美国家约有4000多万印第安人,共有600多种印第安语言,但是不少拉美国家政府的政策要求必须学习西班牙语,并将西班牙语看作是文化的象征,这一举措导致250种土著语言濒临消失的危险。
本文通过细致分析濒危语言的社会学因素、消亡过程、深入挖掘濒危语言的认识价值,力求为保护世界濒危语言的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并从语言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上提出保护濒危语言的一系列措施,为今后制定语言政策及措施提供参考。
四、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复兴路径构建
世界的开放与交融加速了语言的濒危,各个国家和族群都面临传统语言文化的消亡与濒危。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使用群体,一种语言消亡意味着这个群体千百年对科学和艺术的沉淀也随之远去。为应对语言濒危带来物质与精神财富遗失的威胁,我们不仅不能放弃多种多样的地方语言,更需要语言专业人员、语言族群、政府组织和各国非政府的通力合作,充分发掘各种语言中蕴含的文化精华。因此,构建一套强有力的拯救与保障机制是复兴濒危语言的重要保障。
濒危语言问题涉及全世界,记录、保护和传承这种继承方式是我们重要的任务之一[11](P232)。学者们用极大的热情重视濒危语言,关注濒危语言,要像保护濒危动植物一样保护濒危语言。应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深入民族乡村进行调查研究,培养一支能在该领域一代代传承下去的队伍,建立濒危语言保护网站、论坛,并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通过交流经验、成果,为抢救和保护民族语言出谋划策,也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存在相似性,濒危语言的趋势只能延缓,无法阻止,因此,我们更需要联合多学科全方位、多手段、多层级、多视角的研究。除此之外,还需要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协同开展濒危语言保护工作,并设立相应专项经费(资金来源的渠道可以采取募捐、拨款等多种方式),保障专项课题组、有关专家或者领军人才等群体能顺利进行语言挽救工作,对濒危语言进行摸底调查,掌握一手资料。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工具,语言多样性是全社会共有的财富,因此,丢失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对社会文明的抛弃。开展濒危语言抢救工作应采取必要措施积极宣传本土语言和文化,政府有必要制定保护濒危语言和文字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媒体等平台加大社会对濒危语言保护意义的认识;应当以方言为抢救单位,将语言的抢救与口头文学、诗歌、传说等民俗内容的抢救结合起来[12]。抓紧时间记录调查研究弱势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陆续调查研究和刊布濒危语言资源,整理出其语音系统、语法系统,并出版濒危语言学专著和词典或者为弱势语言制订一套拼音字母,利用多媒体、录音和录像等现代化手段构建计算机词汇语音数据库,更多地保存土著语言中的文学作品声像资料。除此之外,应该提高土著语言的政治地位,可以将继承本族群的母语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建立濒危语言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少数民族聚居区、濒危语言保护示范区等,与此同时,还可以将濒危语言融入教育或者社会生活中,使民族语言的文化生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和保持。
开设濒危语言口语课程,这是保护濒危语言文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又是提高小语种政治地位与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高语言的使用活力。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并成为政府行为,应设立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的专项资金,纳入每年的经费预算中,专款专用。在母语学习方面,要在民族学校开设民族语言课,并将其纳入课时,编写和传统文化知识有机结合的教材,开发濒危语言文字教学和自学的教材、读物和全媒体产品,从而达到保护濒危语言的目的。国家通过教育的方式促使学生掌握世代相传的知识经验和现代知识,如此一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综合知识,而且又能有效地减缓母语濒危的速度。语言的功能是促进家庭内部和本族聚居地的生活交流,如果拥有强大的使用群体或者族群对本族母语拥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语言忠诚,那么这种母语怎么都不会消失。因此,本族的积极性与自觉意识能有效促进语言文化的传承与保存。
语言学学者在复兴或延续语言活力的过程中常常遇到一些因各种社会因素难以复兴的语种,针对这种情况应竭尽全力地对其采取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尽可能把该语言的故事、歌谣、诗史等口头文学通过文字、音标、意译等方式记录下来,最直接的是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录制少数民族语言音档,并建立语料库[13]。语料库是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有效的记录手段与研究的新方向,不仅能减轻语言学家在浩瀚档案翻译工作的工作量,而且记录的有声和形象资料能供语言学学者研究和复原参考。数字化文档的永久性保存,将会给语言多样性问题带来极大帮助。英国剑桥大学通过“世界口头文学保护项目”抢救一些濒危语言,主要是通过对迅速消失的歌曲、诗歌、传说等口头文学用音频、视频等现代手段予以存档,这种方式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1]Christopher Moseley.Encyclopedia of the World's Endangered Languages.Rutledge,2007.
[2]Julia Sallabank.Attitudes to Endangered Languages:Identitiesand Polic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3]赵阿平,郭孟秀,何学娟.濒危语言[J].当代语言学,2014,(4).
[4]韦茂繁,秦红增.语言、濒危与文化——语言学与人类学的对话[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5]王跃龙.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逻辑缺陷[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6]Peter K.Austin.One Thousand Languages:Living,Endangered,and Los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7]何丽.濒危语言保护与语言复兴[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8]Lenore A.Grenoble,LindsayJ.Whaley.Endangered Languages:Language Loss and Commun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9]王烈琴.语言濒危与语言维护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10]Evans,Nicholas.Dying Words: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What They Have to Tell Us.Wiley-Blackwell,2009.
[11]Peter K.Austin.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Cambridge Handbook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2]秦银国,郭秀娟.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的批判性探讨[J].贵州民族研究,2013,(4).
[13]田有兰.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理论与美国国家语言政策实践[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