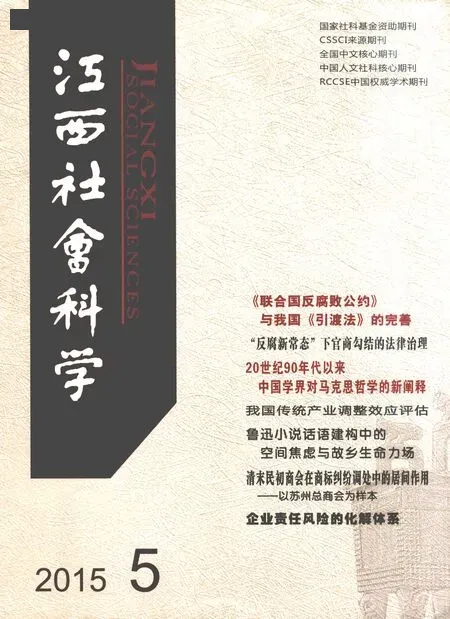民国社会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主动接纳
■朱季康 (美)孔祥德
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欧美起步,于晚清时期进入中国,至民国时期进入群体性传播阶段。民国政府、社团及学者群体对其展现出主动接纳姿态,在各个层面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进行吸收与消化,使之在较短时间内融入中国社会。在这个接纳的过程中,中国本土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框架也开始构建起来。
一、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主动者
(一)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迅速传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引导社会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
第一,在政策层面,通过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督促引导中央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重视与加强对近代学前教育事业的规划、管理与发展。
1928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部提出“全国儿童健康完全由国家负责保障”,规划实施“五大计划”,即“一、五十年内造成十万助产士;二、对助产士有适当的监察和管理;三、使国内遍设妇婴保健机关;四、推进关于儿童健康问题之研究;五、实施学校卫生,促进学龄儿童健康”[1]。这五大措施都与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密切相关。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确定以每年4月4日为中国儿童节。1935年,国民政府又确定该年8月1日起至次年7月31日为中国儿童年,“通饬全国切实实施行儿童幸福事项”[2]。其时,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长代表马宗荣等都发表了重要的演说。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和中华慈幼协会等主管机关或团体,也发表了重要的宣言。“儿童节”、“儿童年”的创设是一项创新,也是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重大举措。围绕“儿童节”、“儿童年”,民国政府组织了施行委员会,出台了《中国儿童年实施办法大纲》,督促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各项活动。《办法大纲》阐述儿童年的实施目的为“以唤起全国民众注意儿童教育,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及图谋儿童福利,以完成儿童之肉体、精神及社会的能力为目的”[2]。1935年8月10日,行政院训令(第04263号)全国“以儿童年开始,全国各机关学校及各社团应依照一切法令,尽力实施以谋儿童福利”[3]。同年,中央宣传委员会及内政部通令(警字第1134号)全国实行《报纸杂志出版儿童特刊或周刊办法》[4],规范儿童报刊的发展,客观上也引导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宣传。1935年11月26日,教育部再发通令,宣传儿童幸福事业。[5]
抗战时期,由于儿童保育在战争时期的特殊需要,国民政府也出台了系列战时儿童保育政策。抗战之初,卫生部就拟定了卫生建设五年计划,内含儿童保健工作,“为增设妇幼保健机构,训练儿童保健人才,力求工作普遍推广”[1]。1938年,教育部又下达《战区儿童教养团暂行办法》[6]。1943年3月20日,行政院核准备案《社会部奖惩育婴育幼事业暂行办法》。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目标也在抗战时期得以确立:“在实现善种善生善养善教善保,以培养健全儿童,造成优良国民,藉以增进民族活力。奠定建国基础。”[7]有关近代学前教育事业的各项政策和法令,在抗战胜利后开始出现制度化的趋势,并在1947年经国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把实施儿童福利政策列入了专条。
在中央政府的提倡下,各级地方政府也有所行动。如儿童年前夕,各省都通令所辖县市执行中央儿童年实施方案。如山西省政府通过公报形式发布第607号训令,江西省政府发布教三字第6415号训令等。各地方政府还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与措施。如1940年3月19日,安徽省政府公布 《安徽省立临时小学教养难童暂行办法》;1943年,广东省政府训令(阳社三济字第66522号):《令发广东省各县市局推行宗族抚养贫苦儿童办法》等。
这些政策措施由各级政府所推行,对近代学前教育相关思想被民国社会所接纳起到了导向作用。
第二,在实际操作层面,通过召开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参与国际合作、加强学术交流的方式,以及创办官方或有官方背景的学前教育机构,积极引进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同时摸索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本土化发展。
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夕,北洋政府就派员参加了相关的国际性会议。1925年8月,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在北京举办第一次国际大会,“规定保护儿童权利五条原则”[8]。时任与会代表、驻瑞士使馆二等秘书官兼国际劳工代表处处长的萧继荣还向政府做了专门报告。此后民国政府也多次举办各类相关会议。这些会议肯定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并鼓励在社会进行推广。第一次中国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会议发布宣言称:“现代的儿童是父母与国家共有的,同时是儿童自有的。”[9]这是典型的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所倡导的内容。民国政府还通过各种方式鼓励教育界进行国际交流,派出了数次大型的官方教育考察团,赴日本、欧美等国进行考察,近代学前教育事业也是其中主要的考察内容,相关考察报告也大多被公开发表,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创办官方及官方背景的近代学前教育机构方面,民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现实的压力,这些机构主要围绕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行政院就下令推广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响应。如1928年,安徽省政府教育厅训令(第342号)所辖各县:“务希于十七年度起,即饬所属实验小学或师范附属小学,尽先设立幼稚园;并于师范学校内,斟设幼稚师范科,以培养幼稚园师资。十八年度开始,更希设法在乡村师范学校内斟设乡村幼稚师范科,在乡村小学内斟设乡村幼稚园,以期幼稚教育,渐次推广。”[10]各公办学校也纷纷开始建设附属幼稚园,培训幼稚师资。如1930年,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开始设立幼稚师范科,其课程目标的设计中明显采用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理念。
除了幼稚园及幼稚师资培训机构,大量有关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机构相继创办。1935年8月,南京社会局局长陈剑如提出《扩充救济院、育婴所案》[11],建议政府加强对流浪婴幼儿的保护和对婴儿的公育措施。全国各地政府都设立了类似的机构。如广州之婴孩寄托所系广州社会局举办。这些机构的经费基本上是由政府所承担的。如1941年,江西省政府财民济字第06042号训令就强调了对各县儿童教养所及保育院经费的财政保证。1936年、1947年、1948年间,此类机构的数量呈直线增长。同时政府开始进行近代学前教育事业的创新示范工作。1936年秋,国民政府社会部开始筹办南京儿童福利实验区,并聘儿童福利专家熊芷女士主持,经一年多努力,陆续开办了三个儿童福利站和一个托儿所。这些儿童福利站都位于城市贫民区,如南京下关实验儿童福利站就是针对南京贫民区儿童保育的示范。而另一个福利站所在的合群新村,也是一个棚户区。这是民国政府在近代学前教育事业上的创造,也是民国社会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一个渠道。同年,根据《大公报》记者吴元坎等人的调查,上海市的托儿所、难童教养院、孤儿院、贫儿教养院、街童及乞丐收容所达到了54个[12],号为全国之冠。抗战前后,随着公医制度的不断发展,儿童保健事业也有新的进步。1946年,各级地方妇幼保健机构如妇婴保健院、妇婴保健所、产院、卫生事务所、卫生教育委员会等开始出现,专办产妇及儿童保健工作。从中可见政府的作用。
(二)相关社团是民国社会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重要推动力
民国时期,关注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各种社会团体数目庞大,性质繁杂,几乎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由于这些团体的特殊性质,特别是教育与慈善类的社会团体在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传播方面,作用巨大。如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女子生活部于1936年设立婴儿培养园。南京中央医院门诊部保健科于1948年附设儿童保健会,除正常的儿童保健工作外,为加强近代学前教育保育思想的传播,他们还组织了各类联谊活动以增进与家长的联系。“儿童保健会为了各家长的联络,更时常举行恳亲会。”[13]这种专业人士与家长联谊活动的开展,从民国社会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过程来看,其效果与意义不言而喻。这类组织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战后,都有新的增加。如抗战时期的1938年4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2月,成立了联合国难童救济中国区委员会。
这些社会教育团体通过举办演讲、演出、慈善及各类其他公益事业,在儿童的福利、保护等方面对社会民众进行理念的灌输与典型的示范,是政府政策措施的有力补充。
各种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医学、经济学、人口学的学者们是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国社会传播的始作俑者及忠诚的拥护者。思想是由个体而传染至群体的,能够使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理念成为国家意志而加以执行,是民国学者的功劳。
民国时期,不少学者出国留学或考察,尤其是教育学领域,在杜威等外国学者的影响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等国外院校成为中国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家的摇篮。陈鹤琴、张雪门等学者通过吸收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成为民国社会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学者们除了在教育领域积极尽责外,在社会领域,他们推动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传播的努力也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通过舆论的呼吁来推动社会的认识。以往学者研究近代学前教育家大多以几位名师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关注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民国学者群体数量庞大,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国的传播与发展并非某几个学前教育名师的专利。他们相对一致地认为民国社会需要近代学前教育思想。1920年,雁冰就说道:“我确信教养儿童是极难的事,却又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脉的事。”[14]1929年,陈际云呼吁:“我并盼望各省多设幼稚园及蒙养学校以教养儿童,并多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幼稚师范科去培养教育儿童的保姆。”[15]除了呼吁之外,亦有学者通过建立相关组织来推动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社会的传播。这些组织具有多种层次。1932年,杜从坡曾参与发起中国儿童公育院。1946年,南京母婴保健委员会成立,委员来自“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卫生当局,有医院院长、有大学校长和教授,有社会福利社的主持人”[16]等各个社会群体,学者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
二、抗战时期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时代内涵
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国社会的传播呈逐渐扩展的态势,但引发民国政府、社团及学者群体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全面接纳的时代原因则是抗战的爆发。其中,近代儿童公育与保育思想成为其时两个最具有时代内涵的热门领域而广受关注。
抗战全面爆发前,儿童公育、保育的讨论只限于教育界与学术界,20世纪20—30年代初,关于公育是否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还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辩。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公育与保育成为大后方政府与民众的统一认识。
近代公育思想进入民国社会有一个明显的接触—争论—接纳的过程。民国医学家夏德贞女士曾形容民国初期人们对儿童公育的感官认识:“托儿所这一名词,在中国是很陌生的;一般民众根本不知道。”[17]民国社会首先接触儿童公育并非战争的原因,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逐渐扩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与经济生存压力的增加,同时也因为传统大家庭的瓦解,导致儿童公育成为民国学者无法回避的话题。“普遍的设立托儿所,即是普遍的给予妇女参加生产,从事职业的机会,换句话说,托儿所的普遍设立,即是社会生产率一般的提高,社会生产率一般的提高,即是社会进步的加速。”[18]很多学者认为:“托儿所的事业在现代的中国看来似乎是一种必须的工作。”[19]这种观点因为与传统育儿理念格格不入,因而遭受抨击,但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反对意见很快便平息了。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从战时环境角度考察,近代公育与保育思想契合当时实际,符合当时中国民族与政府的最高利益,有助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业,因而国民思想迅速转变。“自抗战以后……到处有创办托儿所的呼声,有些地方由妇女团体相继创办起来;人们才慢慢认识托儿所的重要。”[17]“各地的有心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保育战时儿童的呼声,先后发起战时儿童保育运动。”[20]与抗战前相比,更多的民众投身现实的儿童公育与保育事业。
国民对近代公育、保育思想的接纳不仅限于大后方,沦陷区也同样有所进步。“上海沦陷后,有一批妇女工作者,留了下来,于是打破重重难关,分别把儿童工作做将起来。”[21]1944年,上海滩两个报社联合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募捐运动,将筹集到的100多万善款捐给了10个“有成绩”的儿童公育保育单位。这些组织的存在与功绩,也证明沦陷区的国人对儿童公育、保育思想的接纳与贯彻。
近代儿童公育、保育思想在抗战时期也超脱了原先的理想,有了新的内涵。为国家为民族保存血脉,为中华复兴的未来保存力量,是近代公育、保育思想鲜明的时代内涵。抗战时期托儿所等幼儿公育保育机构并不单纯地是为解救抗战时期家庭经济及职业妇女的困难,有学者就曾指出:“托儿所是国民教育的起点,托儿所是国民健康的基础,托儿所是抗战中增强抗建工作效率的柱石。”[17]为着这个理想,儿童的公育与保育工作就不仅是保护与福利这些内容,教育也是重要的方面。这就使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 “教”属性功能也得到了开发并有了时代内涵。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国家前途的角度考量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中“教”属性的价值。1933年,有学者呼吁:“近来我国政府与人民,虽然注意到国民体育问题,但对儿童保育事业,仍为一般人所忽视,殊为遗憾!”[22]1934年,中大实验学校小学部主任龚启昌也谈道:“诚然,近年来有志之士也已经注意到了民族复兴的工作。……却仍旧忽略了一件,基本中之基本的工作,就是儿童和青年的训练。”[23]1935年,更有杂志阐明:“儿童时代的行动和表现,是在与社会的整个文化,和民族紧相关联的。”[24]政府也对此有所触动。1935年,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曾说:“所以我们要求我们民族的生存,我们就该赶快将民族复兴起来,使中华民族做世界是那个最强有力的一个民族。”[25]而使民族强盛的根本方法就是教养好下一代。这种观念在受到抗战中中日国力对比的刺激后更加强烈。落后的传统育儿理念已被民国学者视为 “实在是我国以往的不幸民族萎弱的致命伤”[26]。时为行政院社会部长的谷正纲就提出:“儿童福利就是民族福利,这是我们近年创导儿童福利的口号。”[27]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更信儿童安全,为家庭,为国家,社会安全。”[28]这样的观点几成教育界共识,也为大多数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国人所接受。
三、民国社会主动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表现与效果评价
国民思想层面的群体性转变可以通过其行为的转变而观察出来。通过分析民国社会各类近代学前教育机构、协会的创办,相关文论的发表及中外交流的状况,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接纳的程度。
晚清开始进入中国的各类近代学前教育机构从起初的教会主导到政府主导,在民国时期有了数量与质量两方面的提升。抗战前,各地都创办了一定数量的近代幼儿保护机构,如1926年,上海市全市育婴机关收养(绝大部分为出生至三月左右)婴孩总数为2083人[29]。这个数字较晚清时期已大有增进。各地也创办了一定质量的幼稚园,如1930年,广东省全省幼稚园达到了20所左右,入园幼稚生约2000人[30]。这个数字也几乎为晚清全国总和。按照其经费标准合理推算,广东省每年在幼稚园事业上的政府经费投入就达3万元左右,也是晚清时期所没有过的力度。经过20余年的投入,至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时人叶冶钧评价中国各地“公私立幼稚园的设立,已有相当的成绩”[31]。抗战时期,以儿童公育、保育为主体的各类近代学前教育机构在大后方蓬勃兴起,数量多,影响大,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截至抗战结束的1945年,社会部直辖的儿童保育机关有19所,育婴4512名。一年后,育婴数字又增加到6696名。[32]而全国在社会部备案的儿童保育机构达到了1737所,江西、浙江、湖南、四川、陕西、福建都超过了百所。[32]在这个过程中,公育与保育的机构也不断细化,如儿童保健设施在抗战时期伴随着公医制度逐渐发展,“在各省市县乡都有卫生机构,负责推行这种儿童保健工作”[1]。1945年, 又增设地方妇幼保健机构,专门负责产妇与儿童保健工作,相关机构有妇婴保健院、妇婴保健所、产院、卫生事务所、卫生教育委员会等。
各类与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相关的协会组织也在民国时期有所发展,成为推动民国社会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生力军。抗战前,这些协会组织主要以民间教育与学术界自发创议设立居多数,也多以学术研究、慈善救济为主要活动。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政府也参与进来,组织倡导了一批具有官方身份的相关协会组织。如1934年成立的南京育婴事业指导委员会。又如次年成立的儿童年实施委员会等都具有官方身份,具有较强的行政推动力与指导力。抗战过程中,此类协会组织数量呈几何级增长,其活动也更加频繁与多样,对民国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1938年由宋美龄领头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是其中具有领导性质的组织,在后方各地都有其分支机构。其成立同日,还成立了由马超俊、谷正纲等发起的战时儿童救济协会。
根据笔者对近代学前教育文论出版的计量分析,民国时期,共出版了约500种主要涉及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编著,另有各类杂志发表2000余篇相关文论。从编著杂志的角度来看,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国时期的传播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同时,各类相关的学术交流也开始进行,其中有典型意义的,如1920年北洋政府派出欧美教育考察团,对欧美诸多国家的教育状况(包含学前教育)进行了系统考察,其考察团员的日记在国内广为刊登。中华慈幼协会会长裴美德博士为美国人,卸会长任后,曾在1937年于上海华懋饭店设宴招待各国侨沪妇女界领袖,“裴博士讲演中国之儿童幸福事业,并由中华慈幼协会干事丁秉南报告最近工作之发展情形”[33]。与会者为英国总领事夫人、商务参赞夫人、德国总领事夫人、意大利大使夫人、比利时总领事夫人、瑞典总领事夫人、瑞士总领事夫人、荷兰总领事夫人、葡萄牙总领事夫人、智利总领事夫人、江海关总税务司夫人、路透社社长夫人等20余人,足见盛况。
虽然民国社会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采取了接纳的态度,也作了很多的工作,有很多成就。但民国社会长期处于混乱的政治形势与战争环境中,加之传统旧思维的制约,对其接纳的现实效果评价不能过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于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现状的批评之声更加响亮。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状况确实令人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国社会的传播更加广泛与深入,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近代学前教育,对其现状进行反思与探讨。这个时期的批评寄托了一种希望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的全民愿望。
对虐婴的批评是其中的主流。1929年,日本学者西山荣久所作的《中国婴孩的民间杀害》一文对中国福建、江西、广东、浙江、安徽、云南、北京、扬子江以南地区虐杀婴孩的情况进行了描绘。现实的压迫与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理想相隔太远,很多国人深感焦虑。1930年,中华慈幼协会发布该年报纸所载虐杀婴孩数据:“儿童被弃二十一件,溺婴四十二件。”[34]陈碧云称:“我们可以说,中国大多数的儿童,现时正处于一种最危急的地狱生活之中!”[35]
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无法在中国贯彻的焦虑也是学者们批评的焦点。“河南有几百万个盛创造发明种子的器具——儿童,被工师选进园圃——学校的约有数万个;只是多半还在被固封着,没有发掘;或是已被发掘而没有植于适当的地方,或培以适当的方法,所以将来的发荣滋长开花结实,究竟能有几多,实在是没有多大把握。”[36]这是1929年河南省一个省的状况。“我国于近几年中,在几个大都市里,对于儿童教育的设施,时常改进,尚差强人意。其他城市,亦有较小规模之设施,但只供中产阶级儿童们所享,贫苦者和农村上的儿童,仍得不到一些好处!”[37]这是1935年中国大城市的状况。“我国因教费拮据关系,不能普遍推行幼稚教育,除掉大都市中说有少数装饰门面的幼稚园外,其余如乡村中,简直找不到幼稚园的踪迹。”[38]这是1937年中国农村的状况。
学者们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实际作为的效果也普遍持怀疑态度。有学者以为政府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与传播过程缺乏敏感性,行动缓慢。认为政府的很多相关政策只是具文,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即使对政府引以为傲的“儿童年”策划,学者们也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我们过细检讨她究竟有了多大的成绩,中国大多数的儿童是否已经得到了几多实惠时,不惟作者觉得有点汗颜,即令负有教育儿童责任的人,也未必能够给个具体答复。”[39]
抗战期间,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推广很快,但受战争影响,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在中国发展十分不平衡。“我国儿童运动的发现,到现在只不过十多个年头吧!除了那些文化发达的大都市比较晓得儿童的重要之外,其余大部分农村的儿童生活,简直仍旧和十多年前——未有儿童运动的时候——的生活一样。”[26]并且由于战火,中国幼儿的死亡率很高,这也是与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推广者主观意愿背道而驰的现实。根据中共的统计,1946年,全国儿童非正常死亡数为16 634名[40]。这个数据应该是不完整的。因为仅1947年11月,国民党上海市卫生局就宣布 “市内街头因冻饿而死及被丢弃的孩尸就达一千三百具”[40]。但也有例外,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学校、机关、工场、以及部队先后成立半托或全托的儿童保育机关,集中力量保卫孩子,给儿童较好的衣食,并提倡营养,注意卫生,实行严格的预防传染病的制度”[40]。
总体而论,民国社会对于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是呈欢迎的姿态的,在接纳的过程中,政府、相关社会团体与学者是主动者,妇女领袖及官僚群体中的部分个体贡献了特殊的力量。抗战时期,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中的保育、公育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国社会有了相当的基础,但近代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民国社会并不令人满意,受到时人的抨击。
[1]施正信.我国儿童保健政策与设施[J].儿童福利通讯,1948,(19).
[2]金石音.儿童年论母性[J].东方杂志,1935,(19).
[3]教养全国儿童事项[Z].内政公报,1935,(19).
[4]抄发报纸杂志出版儿童特刊或周刊办法[Z].广东省政府公报,1935,(303).
[5]宣传儿童幸福事业教部通令[J].公教学校,1935,(24).
[6]战区儿童教养团暂行办法[Z].湖北省政府公报,1938,(359).
[7]张鸿钧.我国儿童福利政策[J].儿童福利通讯,1948,(13).
[8]祁伯文.“儿童节”、“儿童年”与“儿童世纪”[J].陕西教育月刊,1935,(8).
[9]李寄尘.家庭教育与儿童福利[J].福建妇女,1946,(1-2).
[10]奉院令推广幼稚教育[J].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28,(19).
[11]扩充救济院育婴所案 [Z].南京市政府公报,1935,(156).
[12]上海儿童福利机关之概况(一)[J].儿童福利通讯,1947,(3).
[13]刘涵年.南京中央医院之儿童保健工作[J].儿童福利通讯,1948,(19).
[14]雁冰.评儿童公育问题——兼质恽杨二君[J].解放与改造,1920,(15).
[15]张涛.五岁以前的儿童教育[J].安徽教育,1929,(4).
[16]陈纪彝.南京母婴保健委员会工作概括[J].妇女新运,1948,(4).
[17]夏 德 贞.托 儿 所 在 中 国 的 需 要 [J].甘 肃 妇 女 ,1943,(3).
[18]叶楚生.怎样办托儿所[J].江西妇女,1940,(2).
[19]夏德贞.闲话托儿所[J].甘肃妇女,1944,(5).
[20]林 苑文.儿童保育在广东[J].东方杂志 ,1938,(11).
[21]一珠.上海沦陷后的儿童工作[J].现代妇女,1945,(3-4).
[22]汰生.儿童与社会[J].民众周刊,1933,(13).
[23]龚 启昌.复兴民族与儿童[J].时代公报 ,1934,(51).
[24]本刊与儿童[J].美术生活,1935,(6).
[25]吴铁城.儿童为民族强盛的基础[J].美术生活,1935,(6).
[26]黄龄.今后实施儿童教育的展望[J].社会特刊,1941,(1期教育号).
[27]谷正纲.儿童福利就是民族福利[J].社会工作通讯月刊,1945,(4).
[28]南京下关实验儿童福利站开幕记[J].儿童福利通讯,1947,(3).
[29]上海育婴事业统计[J].社会月刊,1929,(6).
[30] 粤幼稚园最近之调查 [J].中华教育界,1930,(9).
[31]叶冶钧.普遍推行幼稚教育与托儿所[J].小学教师,1937,(8).
[32]社会部直辖儿童保育机关保育儿童人数[J].社会福利统计,1946,(2).
[33]各国妇女界领袖协助儿童幸福[J].妇女月报,1937,(1).
[34]华君.目前中国的妇孺救济事业[J].妇女杂志,1930,(11).
[35]陈碧云.现代家庭制与儿童问题[J].东方杂志,1935,(17).
[36]文青.发刊河南儿童的旨趣[J].河南教育,1929,(16).
[37]林煦.农村儿童教育之普及问题[J].人言周刊,1935,(32).
[38]绍白.怎样推行乡村幼稚教育[J].小学教师,1937,(8).
[39]谭唯勇.谈谈农村儿童教育问题[J].江西省妇女生活,1936,(1).
[40]在发展中的儿童保育事业 [J].新中国妇女,19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