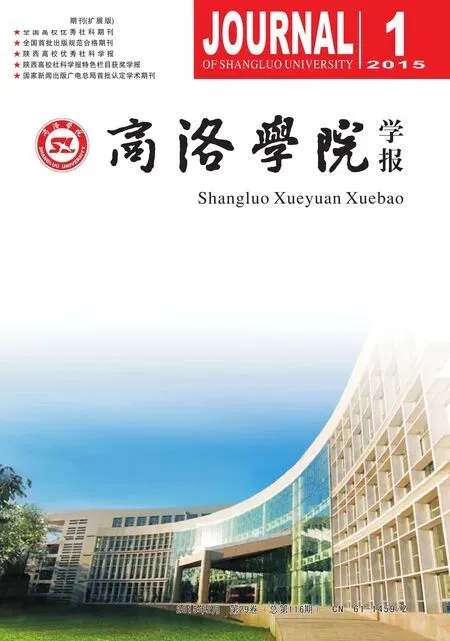小林正树电影美学分析
杨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4)
小林正树电影美学分析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4)
小林正树被称为“日本影坛四骑士”之一,其电影中有大量关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展示,最明显的是对武士制度及近代日本极权制度的反思批判,对民族元素的使用,对日本民间传说的展示。他对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展现并非浮于表面的“奇观化叙事”,而是采用仪式化构图和推镜头的运用,用电影语言来建构寓言化的叙事,他对个体命运的悲悯是建立在对更大的制度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小林正树;电影;美学
小林正树的电影中对日本传统文化、民族元素的银幕化展示较为明显,传统文化如能乐、武士道、日本民间传说等和电影媒介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并没有破坏电影时空的本体性,而是水乳相融。小林正树对日本文化的不断反思,个体生命被政治机器摧残的悲剧,可以说是贯穿他几部重要作品的一个母题。个体与体制的对抗一直是人们较为关注的一个人文命题,而小林正树的作品中,不论是指涉武士道的《夺命剑》《切腹》,还是矛头直指极权统治的《人间的条件》(1-6部),体制对个体生命的倾轧、个体对体制的反抗都那么真实克制,残酷动人。本文从文化母题、静态美学、对民族元素的使用三大方面,阐述对小林正树电影的美学理解。
一、文化母题:对传统文化、日本极权体制的反思——冷静的社会学家
(一)对武士制度的反思批判——孤独武士抗争制度的传奇悲歌
日本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自身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10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由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作为特权阶级的武士从小需要接受严格的文化、军事和自身品德培训,成年(元服)后效力于军事化的封建领主,成为职业军政府中的雇员;而失去工作的武士则被称为“浪人”。武士对于从中国传来的儒家文化中的礼义廉耻极为看重,尤其注重形式化的生活与精神仪式,如撰写和歌和茶道,当然还有至关重要的切腹[1]。江户时期是日本武家政治中最后的时期,也即日本三大幕府时代中最辉煌、最持久的德川幕府时代,聪明而且善于隐忍的德川家康在获得天下后,不但加强了对于各地封建领主(大名)的控制,还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庶民的生活,使得农民与町民(即所谓的城市人)生活各有所取、所需和所享,这也成为政治稳定的因素之一。但同时,大名权力的受限使得大批武士沦为浪人,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困浪人经常跑到诸候家要求切腹自杀,或真或假的切腹造成了很多悲剧。
《切腹》即是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极好透视。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浪人津云半四郎前去伊川家请求切腹,真正目的却是为不久前被要求残忍切腹而死的女婿正名——女婿出此下策只是为给病倒将死的妻儿筹钱治病。讲出真相的半四郎得到的却是伊川家的嘲讽,最终孤身奋战的半四郎身死无名,伊川家的威名却牢不可破。
如果将《切腹》与《七武士》(1954)做个比较,会发现同样是武士制度的一曲挽歌,二者的姿态却有许多不同。与黑泽明强调武士精神的理想主义相比,小林正树更像个冷静的社会学家,冷峻地道出社会的残酷与当权者人性的缺失。就民族气质和人性,尤其是个人在时代中的命运悲剧和渺小无力而言,《切腹》更具穿透力和沉痛感。无论是苍老的半四郎在众武士环伺下缓缓道出真相的凄凉感,还是抗争身死后真相被秘而不宣、摔碎的神像重又立起的荒诞无力感,都那样清晰而沉重,电影的指向性异常明确。除了武士道精神的命题有异外,二者的最终指向也存在根本差异。《七武士》着力在对大时代下悲壮武士精神的祭奠和悲挽,有一种时代洪流下的史诗感;而小林正树却像拿起一把手术刀在精细地剖析武士制度本身的痼疾,为个体被政治机器倾轧的悲剧做着深刻的社会分析。在小林正树的镜头下,我们看到的是更加血腥的残酷现实:当武士道仅仅成为一具空空的躯壳时,还剩下什么?当武士神圣的切腹行为已然成为一种讹诈手段,当昔日荣耀的武士被制度本身所迫又去利用制度的疏漏时,社会仅剩的就只有对权力的膜拜和对真相的漠视。这个双向悖论谑味十足,津云半四郎的“殉道”是向着这个武士道信仰已然崩塌的世界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
如果说《切腹》是一曲底层武士对权力机制的集中控诉和反抗悲歌的话,那么《夺命剑》就是身处权力机制之中的贵族武士的奋起狂呼。《夺命剑》的背景也是德川幕府时代,由于武士的婚姻自由都要受藩主支配,藩主将爱妾阿市以大不敬的罪名赶出藩邸,强令其下嫁给武士伊三郎的长子与五郎,伊三郎家本着服从之意被迫接受;可就在夫妻合意、相处日洽之后,由于阿市生养之子成为藩主继承人,为声名考虑,阿市被强令召回,伊三郎一家为了维护武士尊严与藩主军奋力一搏。与半四郎的命运一样,伊三郎一家的血肉之躯无法撼动武士制度的威权,伊三郎最终也不是死在武士刀的决斗中,而是和半四郎一样死在火枪之威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武士道精神的解构。
(二)对近代日本极权制度的批判——“人道主义的好人与极权主义的恶人”
在很多人看来,小林正树最大的贡献是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自觉反思,这个立场来自他1942年受征召入伍,在中国东北服役,战后曾困于冲绳战俘营的经历,他亲身体验了战争祸害,让他明白了战争给双方带来的苦痛。
他的《东京审判》是迄今为止最重要同题材电影,而他自始至终站在人性角度去探索战争责任的问题,是一种经历之后的自觉。该片是战后审判22个日本战犯的实录,小林把收藏在美国的纪录片重新选材、剪辑而成。上映后,对于导演在片中处理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上,香港和西方部分评论家均有所非议,香港的雷竞璇博士曾撰文指该片是“伪善的反战电影”[2]175。由于掌控材料的单薄,笔者对这部电影的看法与许多学者相似,即“站在日本立场上批判西方主导的国际霸权”。
相比《东京审判》的争议性,《人间的条件》三部曲(1959—1961)则被公认为反思性强、有反战意味的史诗。以二战日本侵华为题的电影有好几部,此部是最长的而且反战意味强,把日本低级士兵在军队的悲惨遭遇拍得最为透彻。电影的时代背景是1943年的满州,以心存人道主义理想的“悲剧英雄”人物梶在不同现实情境中的挫败串起三部曲。电影一、二部梶以人道改革方针对待中国劳工宣告失败,集中探讨了殖民者的良心问题;三、四部描述梶在军队中亲闻参战同胞的悲惨境遇,揭露了军营内军国主义的恶相;五、六部讲述已成北满州逃兵的梶,死在西伯利亚战场的经过,揭露了苏联斯大林极权体制下的种种荒诞景象。《人间的条件》改编自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的小说,作家本人曾经应征入伍在中国战场作战。小林正树导演的三部曲被公认为是在反思日中战争方面走得最远的电影作品,比起现实指涉,作者更为关心象征层面的人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梶的理想是:“把人当作人来对待。”然而,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人”,在权力统治的现实中是否存在“做人”的条件,这是影片提出的问题。
与我看过的其他几部日本反战电影《二十四只眼睛》《望乡》等相比,《人间的条件》的指涉显得更尖锐更本质也更广泛,它直接深入日本近代扩张本质和军国主义的实质。“《人间的条件》是一部复杂的电影,它从一种天然的人道主义视角系统地检视并最终谴责了20世纪的三大‘主义’——工业主义、军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种反思是通过其主人公、悲剧英雄梶实现的。”电影对殖民地人民如中国劳工的视角还是相对平视的[3],尽管大部分劳工的形象仍是懦弱、动物本性的。
小林正树的实验之作《化石》,改编自井上靖的小说,全片约3个半小时,是一部思考生死问题的实验作品,显得有些艰深晦涩,“但影片不断以刹那的画面,以至近乎超现实的人物安排,从单薄故事逐步引领观众到投入的层面。整体观之,在形象的具体与思维的抽象之间,平实巧妙,恰到好处。”[2]1801976年,美国影评人约翰·西蒙在一篇评论中非常推崇《化石》,他将《化石》与伯格曼的《第七封印》对比,认为此片没有伯格曼沉重的宗教意识,而是通过大量意义深远的细微观察,展示死亡而非有任何结论,这正是此片与西方电影的不同之处。个人则认为它确实展现了东方艺术家的生死观,有种与《活着》同样的味道。
二、“静态美学”——仪式化构图和推镜头的运用
从镜头语言来看小林正树的这几部代表作,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其一,仪式化的构图。小林正树利用日本传统建筑横平竖直、对称工整、屋内空旷、楼宇低而森严、门框众多的特点,构图时刻意强调一种仪式感、森严感。在人物的调度方面更是与建筑物的肃穆感配合,演员因剧情要求经常站成一排或围成一圈,形成一种环伺其间的威严感、仪式感。如《切腹》《夺命剑》中主人公被众人环绕其中形成孤军奋战的压迫感画面随处可见,《做人的条件》中梶在工厂、军营中与众人成对抗之势也经常用到。这和小津电影中房屋建筑尽量追求对称和谐的造型美感,以此衬托家庭人际关系的适意不同,小林正树的建筑空间造型是要传达威严、压迫感。
其二,画面的直接切入和匀速推镜头的使用。小林正树的镜头不是沟口健二那种流动的、首尾相连、彼此呼应的长卷式镜头,而是从一个画面直接切到另一画面,非常干净利落,这就使屏幕产生了某种静态的效果,每个画面都像舞台的一角,整体连接就有一种舞台化的庄重感。加之构图上的讲究,把电影的仪式化和映像的静态美表达到了极致,这和电影悲壮的气质非常相符。匀速推镜头也是两部武士片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色,镜头总是缓缓推到人物背后,形成一种戏剧张力。例如《切腹》之中,经常是镜头从坐在众武士之间、低沉地讲述故事的半四郎身后缓慢而匀速地推进,形成一种压迫感和探求真相的知觉。
其三,动作场面上的仪式化与极简风格,以及动作场面与环境的极佳融合。小林正树电影中的动作场面经常用动作上的留白来建构一种极简与静态的风格。具体说来就是选取动作中最激烈的动势瞬间来着力表现,而省略掉动作的过程。典型的例子如《切腹》中半四郎与三大高手及片尾与众家臣决斗的场面。与三大高手的过招选择在三个独具个性的场景:狭窄房舍过道间、神庙里和旷野中,第一场突出空间的纵深感和对手的急切,至于动作则完全省略;第二场给出神像的许多特写,使得近身角力更添紧张感,同时也省略了半四郎割下对手发髻的过程。半四郎和泽泻彦九郎决斗一段是全片着力表现的场景之一,枯草、乌云、大风、神邸这些环境角色全然加入场景形象的塑造和氛围的营造。二武士大开大阖的仪式化动作和枯草随风而动的动势相得益彰,乌云密布、天地无光的环境,更营造出一种不可言说的肃穆悲壮。草木含悲,风云变色,天地为之动容的意境绝没有因为黑白影像的缘故有任何失真,可以说这是中外影史中决斗场面极佳的案例。
三、民族元素的使用——内容与形式的水乳相成
小林正树的《怪谈》改编自日本文化研究者小泉八云1896年的志怪文学作品《怪谈》和《骨董》中的四则,对日本传统文化,尤其是音乐、绘画还有宗教以及民间传说的化用都堪称一绝。
首先,《黑发》《雪女》《无耳芳一》《茶杯中》这四个故事素材均来自日本民间传说,主要人物涉及农民、武士、僧人、知识分子等,皆是日本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故事虽然离奇,但都讲述的是日本民族性格的一面,传达的感情包括誓言与背叛、忠诚与悲悯等人性共通的情愫。与近年大陆的某些古装大片相比,同样取材于古代,小林正树则让人感悟到日本文化——即使是冰山下的一角,也贯通在整个文化的庞大脉络中;而我们的某些国产大片却是游离于传统的华丽假面,完全按照西方惯常的价值观念来构建一个传奇,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割体断魂”。所以,“电影民族化”在艺术上并不仅仅是运用民族元素,而是要渗透民族文化,传递民族信息。
其次,小林正树电影对民族元素的运用做到了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样式的有效嫁接,传统音乐如能乐,传统乐器尺八(日本竖笛),传统美术浮世绘都和现代电影形式有效合理地结合在一起。《怪谈》的拍摄工作是在摄影棚里完成的,但那种舞台式的效果倒很符合日本民间舞台艺术歌舞伎的特征,或者说是电影化的歌舞伎更恰当,影片的旁白形式更是歌舞伎的风格。像《雪女》中的暴雪景象和雪女变身贤淑女子出现在村庄中的画面美轮美奂,是表现主义的风格融合了日本传统绘画浮世绘的特征,极有日本民族性和电影表现力。《雪女》雪穹中浮现出的一双双眼睛,颇似《爱德华大夫》中爱德华大夫催眠梦中的景象。《黑发》中日本古居的空间处理在营造气氛、表情达意、塑造人物方面的作用都非常突出。电影开场就是一段破败古居的空镜,镜头从大门、门廊、花园缓缓推过去,继而出现画外音交代人物背景,一开始就用环境奠定了整个故事森然哀伤的基调;武士另娶得势之后,居所变得气派,也外化了武士攀附新妻家室的郁郁,用一个新妻在高处安睡的镜头将其跋扈傲慢的个性轻易地展现出来,对比武士之后在地处小憩的镜头,强弱之势立现。武士归家之后的空间则全是他心境的外化,物是人是的画面全出自他的幻梦,在他发现妻子已离世之后,环境马上变为破碎到不可住人的废屋,头脸皆白、面无人色的武士在废屋中逃窜,电影用了一个大仰拍镜头表现了他的无处可逃:蜷缩在屋角,门窗封闭,黑发向他袭来。若与沟口健二的《雨月物语》相比,会发现小林正树的调度更具空间的延展性和广阔感,无论是不断延伸的推镜头还是不同机位、角度的拍摄,都延展了空间,使得空旷衰败的空间更像是人物心境的外化,不仅渲染了气氛,传达了情绪,也在电影本体——电影空间上达到成效。
小林正树的《怪谈》告诉我们:不管运用什么民族形式,它一定要和电影故事本身具有主题契合性和美学共性。《怪谈》中大量运用了能乐,而能乐与《怪谈》整部电影无疑是具有主题契合性的。正如佐桥丰藤和彦所评说的:“这种主题契合性首先来自于来源的相近,能乐题材多来自日本古典文学和民间传说,包括神话、古代史、和汉传说、平安及镰仓时代的物语、和歌、乡间口头文学。两者同是以日本古代历史、文化、民俗为蓝本的再创作,使影片与能乐首先在时代感、题材内容、精神气质上就有了基于同源的契合。”其次是美学上的共性,日本戏剧具有鲜明的主情性:哀愁、感伤、余情的情绪表达占去多半;而以表现幽玄美为最高目标的能乐就是这种极端主情性歌舞剧的典型代表。“一般说来,能剧没有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戏剧冲突,作为恐怖类型片的《怪谈》,却鲜有恐怖血腥的画面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平稳淡定的叙述使影片展现了一种奇妙的均衡,是诉诸感官体验的神秘深邃、缥缈幽玄之美。”[4]
李道新曾对地理意义上的亚洲电影和文化意义上的亚洲电影做了定义区分。他强调,亚洲电影更具亚洲认同感和普世价值观,因而也更有精神包容性和市场竞争力,并提出在一个文化主体性价值日益模糊的时代里,如何在建构整体的亚洲电影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亚洲各国电影的真性情,并极力张扬其内蕴的传统的和本土的文化特质,都是亚洲电影必须面对的难题[5]。“可以说,《怪谈》与能乐理念的完美结合为传统戏剧内化于银幕影像、民族传统美学重生于当代大众艺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6]小林正树的这几部电影,的确为如何合理运用民族元素这一命题做出了可资学习的典范。总之,主旨上的文化反思母题、影像风格上的“静态美学”、以及电影化了的民族元素使用,构成了小林正树电影最显著的三个美学特征。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郑树森,舒明.日本电影十大[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3]杨祎.论电影《归来》的改编策略[J].商洛学院学报,2014,28(5):42-45.
[4]佐藤和彦.能乐N心理学[M].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97.
[5]李道新.从亚洲的电影到亚洲电影[J].文艺研究,2009 (3):77-86.
[6]王燕.惊恐并美丽着——试论日本影片怪谈中的能乐之魂[J].外语教育,2010,31(2):74-77,100.
(责任编辑:刘小燕)
The Aesthetic Analysis on Kobayashi Masaki's Movie
YANGYi
(Institution of Art,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24)
Obayashi Masaki is known as one of the"four knights in the Japanese Movie".His movie demonstrates tremendous Japa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he most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incudes:the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Japanese knight system and modern totalitarian system,the use of national elements,displaying the Japanese folklore.His demonstr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not based on the superficial"narration wonders",but adopts the ritualized construction and tracking shot,he uses the move language to construct the allegorical narrative,and his compassion for the fate of individual is based on criticism of a larger system.
Kobayashi Masaki;movie;aesthetic;analysis
J972.6
A
1674-0033(2015)01-0044-04
10.13440/j.slxy.1674-0033.2015.01.011
2014-12-13
杨祎,女,陕西商州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