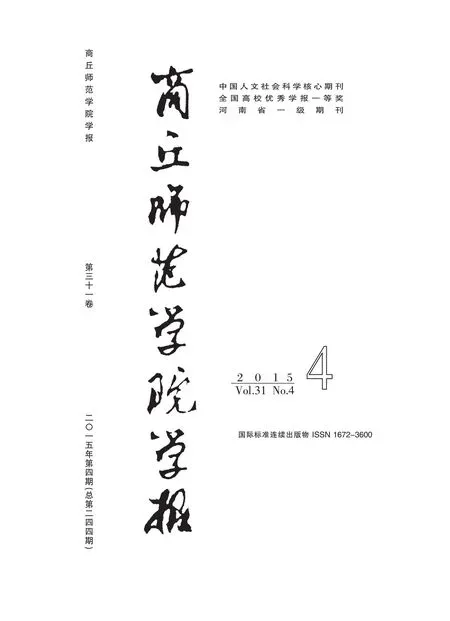对于“法律多元”与“地方性知识”理论的反思
张 世 明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对于“法律多元”与“地方性知识”理论的反思
张 世 明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千叶正士的《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被译成中文后,与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在中国彼此呼应,以至于关于地方性知识和法律多元的概念在学术论著中成为时髦的术语,形成话语的几何数级繁殖。因此,有必要对于学术界这种理论话语的偏颇进行反思,从法人类学角度揭示费肯杰教授的推参阐述方法的精髓所在,以期表达一种另类的声音而避免陷入井蛙之见。
法律多元;地方性知识;推参阐述方法
近些年,关于地方性知识和法律多元的概念在学术论著中成为时髦的术语,风靡一时,像藏密六字真言那样,被人们不时耳口相邮,形诸文字,仿佛具有点石成金的法力。法律多元理论在中国的时兴显然与日本法人类学者千叶正士(ちばまさじ,1919-2009)的著作《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Masaji Chiba,LegalPluralism:TowardaGeneralTheoryThroughJapaneseLegalCulture, Tokyo: Tokai University Press, 1989)有关。千叶正士的《法律多元》被译成中文后,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此书恰好又与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Clifford Geertz,LocalKnowledge:FurtherEssaysinInterpretiveAnthropology,Basic Books,1985)在中国彼此呼应,所以使爱好新思想的学人纷纷辗转敷陈,形成话语的几何数级繁殖。学术界的流行语往往令人们缺乏一种冷静的质疑能力。本文拟对学术界这种理论话语的偏颇进行反思,以期能够表达一种另类的声音,进而从法人类学的角度昭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一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将学问中使用的概念根据其基本性质区分为神学的定义和哲学的定义。日本法学家千叶正士在《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中将康德的这种区分加以这样的理解,即:前者可以被称为描述性定义(delineative definition),就像神学中的“神”一样,其性质是在学理思考开始之前作为先验真理而规定的前提性概念,随着思考的深入将其内容再进行演绎;而后者则可以被称为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像哲学中的“善”一样,其性质是作为首要问题先描述概念的外延,在此基础上,随着思考的进展,逐步深入到概念内涵的分析。描述性定义作为学术开始阶段时描述对象所使用的定义,其要件是在确定该对象的外延方面,判明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以及与其他学说的异同;而操作性定义则是随着分析的深入不断再构成的、作为根据事实阐明其内涵的工具概念,其要件是具有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并使用的客观性。千叶正士认为,因为科学的概念是工具概念(tool concept),所以其概念规定是操作性定义,这种理解作为世界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然前提,就相当于对康德所说的哲学的概念的再规定。“这意味着,最初,尽管概念的外延已得到描述,但内涵却仍不明确,通过学术研究的深入始得到阐明,最后终于构成为精密、准确的一般性概念。然而,因为这也还不是真正的最终定义,仍需继续研究或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说,结论性定义永远只是一种假定。科学的概念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操作性定义之上的。”[1]233一般来说,操作性定义是指根据可观察、可测量、可操作的特征来界定变量的含义,即从具体的行为、特征、指标上对变量的操作进行描述,将抽象的概念转换成可观测、可检验的项目。操作性定义是研究变量或有关概念与实际观察或活动之间的桥梁,将研究变量的抽象化形式转变为可观察、测量和操作的具体形式。因为概念的内涵和本质是无限的,所以在法学研究中,法律概念的定义往往都通过分解为若干构成要件的方式将其加以固定。与此相反,描述性定义常常包含着规范性的成分,因而也是一个规范性定义。
和费肯杰教授一样,千叶正士注重法律民族性的探讨,认为日本人最有特色的行为模式是“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他还概括出英国的绅士式的条理性、美国的法治(rule of law)至上、德国的日耳曼式的体系主义、法国的精神式的象征主义(esprit symbolism)、中国天道式的多元主义等本质主义特征。尽管从字面意义上讲西方法学是一回事,构成其对象的西方法又是另一回事,但它们在实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西方法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论证、保护和推进西方法,因此西方法是西方法学的产物。西方的法学家如果想真正面对法律与发展问题,就必须走出自己的体系,发展出一种跨文化的且内在于社会的法律多元的实证哲学。千叶正士认为,真正有资格理解一种独特的非西方文化的是本地的学者。他从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最初发展出包括官方法、非官方法和基本法(basic law)在内的“法律的三层结构”。这在本质上就是由自然法、官方法和习惯法三方面所构成的结构,但千叶正士却认为习惯法等术语模糊不清,所以弃之不用。后来,有人批评千叶正士把价值和观念纳入第三个层次的基本法中,而这不宜称之为“法”,颇滋疑义。为回应这种批评,千叶正士遂在1982年用“法律原理”(jural postulate)、1984年以来又用“法律原理”(legal postulate)替代了“基本法”,但定义均没有实质变化。这三个层次构成一个国家现行法律的整体结构。这三个层次的结合随社会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在现代社会中,官方法优越于非官方法,而在初民社会,情形正好相反。后来,千叶正士又进一步修正自己的概念框架,提出“法律的三重二分法”,即:官方法与非官方法、法律规则与法律原理、固有法与移植法。千叶正士采取操作性定义对法作出这样的界定:法是由无数权利义务和特殊的制度以及特有的价值理念的整体构成的一种组织性制度,由特定的社会组织创立并维持。
由于受到学术传播管道的限制,加之对于千叶正士“法律多元”思想的理解存在偏颇,中国学术界目前似乎一谈起法律人类学,就认为这是为法律多元提供理论资源的有力工具,将法律多元主义视为法律人类学取得自己地位的依据所在。但是,千叶正士书名的副标题就是“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其理论志趣并非仅仅局限于对于法律多元现象的描述,而是在于通过法人类学的研究创建一套普遍理论,即“多元法律的三重二分法”,认为任何国家的法结构都可以利用“三重二分法”加以观察和分析。在这种意义上,千叶正士的志趣实际上是以突破西方中心论法学的狭隘性和开拓一般法学理论为旨归。事实上,法人类学研究在德语法学国家首推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据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对于法人类学研究范围的界定可以看出,法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法律多元(Legal Pluralism)、土著民族法律(Rechte der indigenen Völker)、发展合作法律(Recht der Entwicklungskooperation)、跨文化冲突治理(Interkulturelles Konfliktmanagement)。可见,除集中于法律多元的研究以外,对于不同法律文化的冲突的消解、协调从而致力于全世界人类的和平发展,对于法人类学而言才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宏大课题。费肯杰教授的研究正是从法律多元的现实出发,通过法人类学研究为人类共同的合作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只是比千叶正士的研究走得更远,其推参阐述理论中的推参阐述Ⅳ是在千叶正士的考虑之外的。易言之,千叶正士的理论仅限于法律分析,而费肯杰的推参阐述理论最终落脚于经世,是世界治理的理论,是一个试图适用于跨文化的比较、比较法、发展援助、国际理解等的元理论尝试。
二
在中国法学界,有些中国法制史研究者费尽移山心力写成的中国法律史著作,之所以不被研究现代法的学者所接受,难入其法眼,除了接受者自身现代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之外,原因就在于这种研究本身存在严重问题。
其一,这种类型的研究都是如同冯友兰在其影响深远的《中国哲学史》开篇处所坦言的那样:“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2]1所谓“中国××学”、“中国××理论史”或“中西××学的比较研究”往往都只是将中国古代文献当作原始材料来切割拼凑,系从西方的“××学”视角对中国传统的理解,而使中国的历史、法律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活的灵魂①。正如达亚·克里希纳(Daya Krishna)在《比较哲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ComparativePhilosophy:WhatitisandWhatitOughttoBe)中所说的那样,属于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学者们“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去看待西方社会和文化,而是全盘接受西方学者们提出的标准,并竭力证明他们自己文化的各个领域中的成就,恰好与西方的那些成就相类似,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这些成就比西方所发现的差”[3]。因为在此以西学成为标准的逻辑中,中与西之间只存在“西”。这种所谓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根据西方早已确定的概念结构加以依附性实证研究,一开始就将那些尚在探求答案的问题从实际上根据被需要验证的理论予以事先解决了,阻碍了真正可以称为“比较的‘比较研究’”的出现。事实上,用任何一边为标准去重铸另一边肯定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既失去了自己的“原生态”特点,将自家思想元气摧折殆尽,而对方的真谛也难得其三昧,所以,这种援西释中的著作并没有在充分尊重中国传统法律的思想生命原则的前提下展开阐释工作,所以,自然在反对者看来是根本上牛头不对马嘴,颇形不伦不类的尴尬。中国现代法学自从清末修律以来,就面临全盘移植、袭取西方而仅足以作为蹩脚的学生的命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头踩空,而凡事只从半截做起,说话总依脚本而定,但源泉既已干涸,“鱼相与处于陆”[4]105,尚有多少回旋余地可言便不难预卜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张志扬感喟曰:“在中西两大壁垒的夹缝里寻找现实的立足点,即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乃是一个几近生存悖论式的难题。”②
其二,这样的法律史研究仍然偏重于载纪,而在富有生成建设意义的通则性理论方面缺乏作为,无法做到因而通之,调适而上遂于道,以致研究历史上的中国传统法律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就将法律视为“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体现乃至民族意识的一部分,认为真正的法学研究者的任务在于感受、理解这个民族精神在历史上生成、流变的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中,关于涉外民事和刑事司法的规定可以说是相当严格和缜密的。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新修订版第239条明确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0条也有同样的规定:“外国籍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的,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自诉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应当委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并依法取得执业证书的律师。”④不仅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需要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见该法第240条)。在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第16条又规定: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解释第306条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这种严格而缜密的规定尚多,兹不连牍繁引。研究现代中国程序法问题的法律人自然对这些规定极为谙悉,但却往往昧于其文本背后的纵深思想文化、意识乃至心态的支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规定中这种防闲綦严的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民族在近代经受百年屈辱历史之后的难以泯灭的心灵隐痛。如果把这些法律规定和清朝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涉外条约加以对勘,我们不难看出其防意如城的法律文本字里行间矫枉过正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冷峻的文字乃是近百年中国人拊心泣血之痛的结晶。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中国人曾经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1925年日本纱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而引发的五卅运动,就是其明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各种因缘辐辏,才给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外交努力带来了机会,中国人终得摆脱领事裁判权的沉重枷锁。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以后绝对不可能遗忘这段屈辱的历史,所以中国政府对于当年张之洞与马凯对话中所涉及的困扰中国近代历史的两个问题——基督教传教士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在不成文的操作策略中态度极其耐人寻味。领事裁判权问题在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的阴影不是轻易烟消云散的⑤。尤其对于法律研究而言,对于法律条文背后法意的参味宛如虽然主张即身成佛的藏密修炼步步均有证悟的参照依据一样,绝非泛滥成灾的自我感觉所能济事。目前,中国的许多法律学人没有从元思维层面入手通古今之变、从法律条文探究法律背后的精神实质,来源浅彀,汲而易竭,所以其鲁莽灭裂,固宜然矣。
清末在欧风美雨侵袭下,中国文化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观念到文字均与固有传统呈现出深刻的断裂。按照塞尔说法,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实在,不仅被用于描述事实,而且参与建构事实。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学概念引入后,这些通过翻译而被逐步建构起来的语言和观念又成为国人认知世界的框架结构。现代西方民法的制度和概念引入后,国人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民法问题争论不休,这其实关系到国人在现代化转型中因为断裂危机而发自内心的焦虑。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此话题。梅仲协是持肯定说的,谓:“我国春秋之世,礼与刑相对立。礼所规定之人事与亲属二事,周详备至,远非粗陋残酷之罗马十二表法所敢望其项背者。依余所信,礼为世界最古最完备之民事法规也。”[5]15但是梅仲协又认为,商鞅变法以后,礼与刑之间的分界泯灭了,中国古代民法都只是残留在律典的户婚、杂律中,“故中华旧法,以唐律为最完备。惜乎民刑合一,其民事部分,唯户婚、杂律中见其梗概耳”[5]16。最早持中国古代民法否定说者首推梁启超。梁启超非常沉痛地这样写道:“我国法律界最不幸者,私法部分全付阙如之一事也。”“我国法律之发达垂三千年,法典之文,万牛可汗,而关于私法之规定,殆绝无之。”“此所以法令虽如牛毛,而民法竟如麟角。”⑥王伯琦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发展,认为:由于民法所规范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不够发达,国家倾向以刑罚维持社会秩序。一些简单的社会关系则付与习惯加以调整,“观之唐律以至《大清律例》之内容,仍未脱政事法及刑事法之范围。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刑法等名词,原系来自西洋,如其意义在吾国未有变更,则谓吾国在清末以前,无民事法之可言,谅无大谬”[6]15。同时,他还针对肯定说加以辨析曰:“(历代律令)中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篇,虽亦含有个人与个人间应遵循之规范,但其所以制裁者,仍为刑罚。究其目的,仍在以政府之政治力量完成安定秩序之作用。其间之关系,仍为公权力与人民间之关系,仍属公法之范畴,与所谓民事法之趣旨,不可同日而语。如现行刑法有侵占、诈欺、背信、重利等罪之规定,其中无不含有民事上债权物权关系之规范在内,但其为刑事法而非民事法,固不待言也。”[6]15胡长清具有平衡性的观点似乎较为容易得到社会认同,即:“(《大清律例》)《户律》分列7目,共812条,虽散见杂出于《刑律》之中,然所谓户役、田宅、婚姻、钱债者,皆民法也。谓我国自古无形式的民法则可,谓无实质的民法则厚诬矣。”[7]16此一立论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形式民法(formal civil law),但有实质意义民法(civil law in substantial sense)。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讨论基本上是限定在成文法的范围内。肯定说以国家律典中存在与民事相关的条文为依据,甚而提出《户部则例》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单独的民事法规,或者礼是真正的民法。否定说则从一种本质精神上加以反对,认为应该整体地把握古代中国的规范系统,律典、礼制、令、例中的户婚、承继等条文固然与民事有关,但在当时都不是以一种对等的民事关系看待,而是一种治理与被治理的、今天的公法意义上的关系。中国古代律典的条文都是由罪名和刑罚结合而成,只能视为刑事法。在这种争论中,双方其实都是以现代法学中的法律关系作为划分标准。但是,现代法学中民事法律关系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且民事关系只是相对于“民法”存在并且外在于“民法”,依据民事关系只能说明民法与世界的某种联系,并不能说明“民法”这个事物的本质。民事关系与民法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联系,而只是一种充分关系。简言之,我们说民法必然规范民事关系,但却不能反过来说民事关系必然产生民法[8]。就此而言,将财产和人身法律关系作为民法“本质”并以此作为判定古代中国有无民法的根据的学说在逻辑上不可能说是适当的,并没有真正触及民法的本质属性;而反对说以意志自由、地位平等和权利本位等价值理念作为判断准则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这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不仅具有视野方面的局限性,而且以西方现代法律的理念绳墨中国古代法律这种释读框架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观色彩,存在时空误识的弊端。在比较法上,这种从法律理念把握问题的方法可以归纳入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方法的范围内。在西方比较法学家中,19世纪后期德国的一些法学家,如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和拉贝尔(Ernst Rabel)等都已倾向对比较法进行功能研究(functional approach)。茨威格特(Konrad Zweigert,1911-1996年 )与克茨(Hein Kötz)在《比较法总论》(EinführungindieRechtsvergleichungaufdemGebietedesPrivatrechts,Tübingen:Mohr Siebeck,3.Auflage,1996)一书就指出:“所有比较法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功能性’(Funktionalität)原则,由此产生所有其他方法学的规则——选择应该比较的法律,探讨的范围,和比较体系的构成等等。”[9]33功能比较法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比较法,它要从不同法律的差别中发现不同解决问题的手段。功能研究方法论者关注于对法律后面的实际状态的研究(Rechtstatsachenforschung),认为在法律上可比的只有那些实现相同功能的事物。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宝坻、淡新、巴县等一批清代州县档案和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的逐渐深入,法社会学意义的法的理解被导入,中国古代法的观察视野被再一次拓展。中国古代民法肯定说获得了新的资源,通过对这些底层社会的资料解读力图证明,即使在国家制定法层面无法肯定民法的存在,但至少存在调整民事关系的某种内在规则。这是一种扩充法律研究空间的功能性比较法路径的研究。然而,这种功能性比较在“中国的A是西方的B(简作中A是西B)”这种刘笑敢所称之为反向格义的言说方式下,又会面临生出许多假问题的危险,甚至导致削足适履。林安梧所举的筷子和叉子的例子就非常经典。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叉子。如果我们说“筷子和叉子都是餐具”,这是正确的,但按照这种反向格义方式,我们应该说“筷子是叉子”,而这显然非常荒谬[10]。正是这样,吉尔兹为了避免人类学中功能-结构学派的一些缺陷,标举阐释人类学的旗帜,提倡所谓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深度描写。
三
吉尔兹的理论固然不乏深刻的睿见,但其明显的片面性也是毋庸讳言的。吉尔兹的“深度描写”只是对赖尔分析的借用,是一种对思维的反映。他正是基于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对于“深度描写”的讨论,认为这给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不断探索和推理的研究途径,从而提出了“深度描写”的研究方法。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认为,事物看来更像是各奔东西而不是会齐聚拢,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可能越来越发音不和谐而可能使得任何有秩序的思想变得不可能,更远远谈不上将法律意识的各种形式转变成彼此通用的注解并相互深化。面对这个严肃的现实而不是在无力的一般化不真实的安慰这种糊涂认识中一厢情愿地把现实消解,我们有必要用科学的方式和其他的方式,获得很多很多的认识。在吉尔兹看来,着手建立一种普遍的法律理论是比着手建造一个永动机更为冒险的尝试,法律体制的相对主义者致力于“从其具体的文化附加条件中抽取纯粹的结构”[11]187,不啻是一种把金子变成铅的反常的炼金术。吉尔兹似乎对于现代国际法律原则和制度采取一种否认的态度,声称现代国际法的这些特征既不是世界法律观点目录中的最低共同标准,也不是作为所有法律观点基础的普遍性前提,而是投射到世界舞台上的我们自己法律的某些方面。
不少学者对吉尔兹深度描写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反对在理论的假设和证据之间进行僵硬的区分,并认为这存在着过于偏激的主观主义倾向,势必抹杀客观事实和主观解释之间所有的界线。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intheTwentiethCentury:FromScientificObjectivitytothePostmodernChallenge,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指出,在近来的文化史学中频频被人援引的吉尔兹研究方法,向批判的历史学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吉尔兹不仅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也不懂得什么历史学。他那篇《巴厘岛的斗鸡》的名文就是他研究方法的最高范例。观众们对斗鸡的反应就反映着一种被看作既是整合的又是稳定的并且形成一个整体的符号学体系的文化。吉尔兹并不观察发生在巴厘岛社会中社会过程架构之内的文化,也不考虑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因而尽管他号称目的是要避免体系化,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独一无二的表现上,然而他所借助的恰好是他所否定的宏观社会概念本身。而这就造成了方法论上的非理性主义。对符号的解释是经验所无法检验的。这种异域文化的‘意义’,就直接面对着这位人类学家。这就会防止引入主观偏见,而主观偏见则被认为既是对运用受理论指导的问题分析社会科学家们的工作进行渲染,也是对相信自己可以理解自己研究的主题的传统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进行渲染。但事实上,吉尔兹对文化的解释并没有任何控制机制。结果便是把人类学家的主观性或者说想象力,重新引入了他的题材之中”[12]128。华裔资深人类学家黄树民在其《林村的故事》等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中就这样批评道:吉尔兹带着哗众取宠的倾向,先把人类学定义为一种“解释性”的学科,随之又以批评所谓的人类“文化中立概念(cultural free conceptions)”或“场景独立概念(context-independent conception)”而对比较方法发起含沙射影的攻击。尽管他承认“相对论”是个定义未清的概念,不值得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加以捍卫,但却对由“反相对论”阵营酝酿出的“恐惧”相对论的种种苗头穷追痛打。任何在具体文化的禁制之外寻求意义,或对普通人性作理论概括的企图都被他打成嫌疑对象。按照吉尔兹的公式,全体人类学家都只能埋头于自己所研究的独特文化的蚕茧,并且满足于做庄子在濠梁之上所见到的河中之鱼,无论其乐与不乐[13]。
理查德·A.爱波斯坦(Richard Allen Epstein)在其论著中多次以英格兰法官布莱姆威尔男爵(George William Wilshere, 1st Baron Bramwell,1808-1892)当年审理过一个邻里侵权纠纷的案件(班福德诉特恩利)为例,这个案例的审理可以和吉尔兹关于“巴厘岛斗鸡”的深度描写相映成趣。在这个案例⑦中,一个当事人在自己的庄园烧砖,造成浓烟弥漫,邻居们苦不堪言,遂将其告上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像其他法官一样,布莱姆威尔男爵在面对具体家长里短的琐碎问题的同时,又不得不去思考涉及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基本原则,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损失和收益。在做一件事情时,如果平衡了所有这些损失和收益,并以此作为基础去追求每个人的福善,那么,这件事情的唯一目的就通向了社会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只要是既承受了所有的损失也享有了所有的收益,其在总体上依然是一个受益者”(The public consists of all the individuals in it,and a thing is only for the public benefit when it is productive of good to those individuals on the balance of loss and gain to all.So that if all the loss and all the gain were borne and received by one individual he,on the whole,would be a gainer)[14]102。理查德·A.爱波斯坦在《简约法律的力量》(Richard A.Epstein,SimpleRulesforaComplex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中译本序言中认为,尽管当时的批评者大多认为布莱姆威尔男爵是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但实际上,这里提出了一个普适性的基本原则。它是一个阐述社会利益意义何在的一般性原则,并不仅仅适用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和近代北美大陆的文化和传统,也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文化,自然也包括了今天中国的时代与文化。据此,理查德·A.爱波斯坦得出的结论就是:文化相对主义是没有说服力的。法律纠纷也许起源于并未吸引世界许多人注意力的、与地方性利益相关的具体事实,可是,解决法律纠纷的过程,论证这一解决过程的正当性,却依然迫使人们必须随之说明一些普遍原则,而这些基本原则,同时还必须经受理性的检验和时代的检验[15]2。理查德·A.爱波斯坦在此的分析对于我们反思吉尔兹关于“巴厘岛斗鸡”的深度描写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如果没有元层面的可沟通性,则对于“巴厘岛斗鸡”的深度描写也是不存在可能性的。与吉尔兹的理论相反,费肯杰教授的推参阐述理论恰恰旨在对存在于不同时间、地点和社会形态中的各种人类社会的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使得以经验为依据、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法律科学的确立成为可能,追求一种元本质上的“新自然法”(das neue Naturrecht)。
四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法律人类学家主要关注于法律通过实施制裁作为社会控制的面相,并将法律程序视为强制执行社会规则的手段。追随于马林诺夫斯基,法律人类学家普遍将争议解决机制认为是理性的。一个关键的辩论在此时出现在有关法律和人类学的方法之间,特别是对法律人类学家是否应该适用英美的法律范畴研究非西方社会的问题。这次辩论主要围绕两个当时的法律人类学的领导人物: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1911-1975年)和保罗·布汉南,尽管并非是仅仅限于这两个人。这被学术界称为“格卢克曼-布汉南之争”(the Bohannan-Gluckman controversy),双方均有精彩论文问世,并吸引众多学者参与讨论。格卢克曼主张使用加解释的普通法术语来描述原始法,以照顾英语读者的阅读需要。他曾在关于赞比亚巴罗册人(Barotse)司法活动研究的著作里,借用普通法上“通情达理之人”(reasonable man)这一术语。布汉南则强烈反对格卢克曼的做法,基于其对尼日利亚梯夫人(Tiv)原始法的研究,认为采用普适的法律范畴是了解和呈现异文化的障碍,法律是有关社会特定的一种文化组成部分,即使将另一个社会的法律概念翻译为英语词汇也是一种歪曲[16]。布汉南的名著《提甫族的正义与审判》将“民俗的体系”(folk system)和“分析的体系”(analysis system)加以区分:前者是土著们自行发展的概念体系,也是一个能够直接与之沟通和交流的人类学家所掌握的东西;后者则是科学家为了研究目的而发展的概念体系,它不属于任何“民俗体系”,是社会科学家的分析工具。布汉南主张应尽量使用当地的本土语汇,依照其音节拼成专有名词,虽然这些术语不容易被翻译成英文,但它们的含义可以在一个民族语境中加以解释。作为最早研究殖民非洲法院的学者,格卢克曼认为虽然洛齐规范(Lozi norms)是当地社会所独有,但洛齐司法推理所依据的“逻辑原则”却为一切法律制度所共有。布汉南将格卢克曼的结论痛斥为普适主义,强调梯夫人的法律概念,不是像英国体制所谓的law里面以法条来思考。格卢克曼认为布汉南的态度过于畏首畏尾,妨碍了卓有成效的比较分析。很明显,他们的辩论不是针对法律本身的性质,而是针对法律人类学的性质,提出了呈现、语言和文化比较问题。费肯杰教授指出,自从冯·沃伦霍芬(Cornelis van Vollenhoven,1874-1933)要求“从东方人视角审视东方事物”(to look on the Eastern things the Eastern way)以来,一些人类学家便认为,有必要完全从内部来审视法律秩序,用其自己的概念准绳对其加以衡量,从内部应用概念并且使用所研究法律的制度、分类以及体系精确地探究该法律,任何“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都应受到抵制。这些作者都是“非比较主义者”,他们主张每一种法律文化中有其自己的法律理念、现象及概念。用布汉南的话来说,这便是“民俗体系”学说,用德·约瑟林·德·荣的话来说,便是“其文化参与者的见解”(participants’ view of their culture)学说⑧。
近年来,法律人类学在中国也开始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阿图尔·考夫曼(Arthur Kaufmann)在梳理德国法理学发展的脉络时,就以费肯杰为代表的法律人类学作为超越长期以来自然法学和实在法学对立的一条新路径。现代社会科学纷纷从人类学汲取资源,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扩展研究的时空视域的趋势,因为现代理论毕竟是当下社会实践的产物,如同刀刃一样,直面现实时虽然犀利但缺乏厚度,所以各个学科遂纷纷上溯往昔,以历史学为奥援,使现实理论的刀刃具有厚重的刀背。事实上,历史学回溯的文化相对发达的历史时间跨度较之于以蒙昧简单文明为对象的人类学所延伸的时间还是短暂的一段,所以,现代理论→历史学→人类学其实是迤逦而上的。从西方社会学、东方学、人类学三者的研究领域来看,这其中一方面存在时间上溯的扩展,另一面也包含着空间上的开拓,即:从现代西方社会到具有悠久历史但在西方中心观笼罩下被视为不及西方发达的东方文明,再到西方人心目中未开化的其他文明。而在费肯杰看来,法学和人类学这种结合还存在将追求真与追求善、或者说事实科学与价值科学的两种学科方法相互结合。明乎此,我们不难理解现在国外法学界之所以青睐法人类学的原因。
就学科研究这一活动来说,恰如凯尔森所言:“认知法律的活动,只能是一种‘概念性的’ 法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离开概念进行构思。”[17]54但是,在一种思维模式中,法律的概念往往与其他概念相交织,都是由其他概念所定义的。这种法律的概念往往如同历史法学所说,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正如一滴水可以反映大海的光辉。对一种思维模式的法律概念的解读都是具有前见的,这种前见作为解读者的文化行李客观存在,很可能与被理解的法律概念如同电脑运行模板一样是不兼容的。所以,费肯杰教授的推参阐述理论并不强调所谓的“视域融和”,不要求理解者与被理解者放弃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思维模式,这在操作上可能是舍己从人或者强人从己,具有泯灭个性的危险和认识论的调和主义色彩。费肯杰教授将法律人类学中客位思考方法概括为“移用学说”(transposing theories)的理论,即将某人自己有关法律的概念和学说植入外国文明之中。他指出,在跨文化的沟通中,为该方法作“辩护”并不见得是出于传教者式的短浅目光,它甚至可能是掌握这一工具以得出能为“我们国内”的人所能想象到的结果的合理反映。如果展示依据地方自身的概念和体系理念运作的外国法律并且恰恰利用这些概念和体系理念对其进行解释时,每每会被读者误解。但无须赘言,对其他文化中法律问题的此类处理并不能令人满意。“移用学说”也不适宜进行比较,相当于中文中所谓穿凿附会。他们仅仅将某人使用其自己的“民俗概念”对其正在研究的其他“民族”中的发现予以分类所得出的观点进行比较,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比较。即使研究者的“民俗概念”被加上“引号”并加以放大以“适应”比较目的,也并不能完全确定“被比较者”以及第三者能够理解它们。然而,这是每项比较的最低要求。简而言之,概念的移用并不是概念的比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比附措施,其势必导致对他者思维模式中法律概念的强制性同化。尽管如此,移用某人自己的法律概念这一方法仍被广为遵循,具有其合理性。显而易见,移用者所依据以及应用于外国法律的法律理念会根据理解法律的一般可能性而有所不同。因此,某一法律概念的移用有三种主要方法:首先可能是一种自然法理念,即将某些法律定义视为一种能依据法律准则形塑现实的“现象”;其次可能是法律中赋予法律以纯粹性词语功能的一些社会资讯的学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唯名论者(nominalists)方式的概念;第三种方法可能源自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即试图将法律定义为现实的控制工具,并且遵从一种介于现实形塑自然法(wirklichkeitsgestaltendes Naturrecht)与法律形塑现实(rechtsgestaltender Wirklichkeit)之间的中间方式⑧。近代西方学者有一种情况,即:从西方的法律观念与状况出发,加以或多或少的修饰后,简单置诸其他民族及其法律之上。这种定义方法不仅把西方的法律视为法律的典型代表,而且将其推阐为法的全部。例如,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对法律的界定即是如此。他认为,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法律乃是国家通过外部强制手段而加以保护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对于法律和学说继受国而言,中国法学界有句广为流传的说法,声称大陆法律和法学抄台湾,台湾抄日本,日本抄德国。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反映了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梯度势差,但同时也说明了照抄照搬过程中本身存在调适工作,在层层转抄中其实就使外来的法律制度、概念和学说不服水土的排异性得以软化。事实上,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照抄照搬,而是如同费肯杰教授说所的“移用”。在费肯杰教授看来,这种移用理论的方法违反了每种思维模式都必须坚持其自身前提和结果的推参阐述I的原则,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进入推参阐述Ⅱ。费肯杰教授推参阐述Ⅱ层面的法律定义方式可以理解为将概念的思维模式纳入整体考量的体系间外部比较。
历史学界非常自然而然地将中西方互视作为超越此种对立的解决之道。这方面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必须对这种言易行难的所谓互视方法进行深层的反思。现在的学者动辄利用迦达默尔解释学中的“视阈的融合”这一术语作为上述互视比较的理据,这无疑把双向互诠问题看得太简单,有些太乐观了,本身是对迦达默尔理论的简单援引而缺乏自我的反思精神。因为如前所述,我们的知识行李是无法卸载的,丢掉视界就无法视见,即便我们一厢情愿力图使自己保持充分开放的视阈,但充其量至多是某些方面构成“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在交集之外的、俗话说我们与他人“对不上眼”的视阈却又总是在所多见。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者,恶能正之?”[18]41这里存在一个比较的困境,也恰恰说明了“客位”与“主位”研究方法论之争的一个悖论。按照费肯杰教授的说法,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
费肯杰教授是法学家,其五卷本《法律方法比较论》(Wolfgang Fikentscher,MethodendesRechtsindervergleichendenDarstellung,Tübingen: Mohr Siebeck,1975-1977)等又使其足以在法哲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较法和人类学的视野、在联合国立法的实践更令其具有从全人类的哲学高度思考不同文化之间求同存异问题。费肯杰教授推参阐述的目的就在于使不同体系之间的哲学比较、不同的思维模式之间的比较得以成为可能。费肯杰教授的理论表现出了这样一个倾向,即:对于非西方文化的认知,这不仅仅是坐标转移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衡量尺度改进的方法的元研究。费肯杰经常引述伏尔泰的这样一句名言:“尽管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希望能誓死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Ich bin nicht Ihrer Meinung,aber ich hoffe von mir,ich würde mein Leben für Ihr Recht einsetzen,sie zu äBern)。”⑨如果说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突破西方中心观寄希望于多学科的研讨班,那么费肯杰教授的推参阐述方法则是通过跨文化的国际研讨班,从而达致一种类似中国人所谓“和而不同”的境界。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做法。推参阐述Ⅲ层面的元研究尽管具有共识论的味道,与柯文历史真相符合论大相径庭,但反对认识论上的一切调和主义。所以,柯文表现出来的方法论训诫就是尽可能祛除研究者的历史承载,以期换位思考进入中国历史内部,而推参阐述方法则似乎没有这种如临大敌的高度紧张。尽管殷海光也将后设历史学(即元历史学,metahistory)的研究对象集矢于历史的“理论背景”(theoretical background),但他基于其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这一积极的理论目标设定,所以将消革(to eliminate)民族感情、政治中心观和价值评断等所谓历史学中认知以外的因子(extra-congitive factors)均作为其后设历史学的消极目标了,而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则将这些历史意识合法化彻底予以暴露。对于费肯杰教授而言,他将“客位”与“主位”研究方法论分别置于推参阐述Ⅰ和推参阐述Ⅱ两个层面,从而暂时化解了庄子在《齐物论》中就已经表示出来的比较的困境。然而,在推参阐述Ⅰ和推参阐述Ⅱ两个层面之后,费肯杰教授继续往前推进其思考,在推参阐述Ⅲ层面进行思维模式最低公分母的探讨,这是一种元研究。
注 释:
①现代中国人所使用的概念绝大部分都与西方文化相关,离开这些概念,基本上任何人都不可能进行思考。问题的关键仅在于中国学者的精神是否独立,所以绝不能以为使用了古文中未曾得见的概念就是西方中心观的反映。如果我们检视那些批评别人的学者的文章,就应该格外惜护所有严肃从事中西文化沟通的研究成果。有些人连古文都不通,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门外汉,又不认真研读批判对象的论著,总以为自己是一贯正确、伟大的学术警察。然而,读古书,当明古谊,居今世,不违今人。知贵真知,学贵实学,与其专以打无聊的口水仗为能事,不如用严格践履自己理念的笃实的学术产品给其他人打个样出来躬亲垂范,否则坐道、空谈不免有假道学的气息。洛克认为:“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当是抱着几分怀疑主张己见的(a rational man will hold his opinions with some measure of doubt)。”(参见Bertrand Russell ,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 2004,p.553。)唯我正确的强硬在某种程度上就从反面印证了自身不可救药的颟顸。在《樊山政书》中,樊增祥“批学律馆游令拯课卷”一文极为有趣,值得回味。樊增祥指出:“今之少年,稍猎洋书,辄拾报章余喙,生造字眼,取古今从不连属之字,阄合为文,实则西儒何曾有此?不过绎手陋妄,造作而成。而新进无知,以为文中着此等新语,即是识时务之俊杰。于是通场之中,人人如此,毕生所作,篇篇如此。不惟阅者生厌,作者自视,有何趣味乎?去年鄂闱,端中丞详加戒谕,如改良、起点、反影、特色之属,概不准阑入卷端。”从这道批文中可见,当时不仅连改良、起点、特色等我们今天的常用词被摒除于录取之卷,樊氏甚至对课卷中使用文明、野蛮等所谓不根字眼也严批痛斥,樊氏誓以天帚扫此垢污。该令在陕服官,谊当入境问禁,而竟贸贸为此,亦云不智。樊氏警告云,以后凡有沿用者必奋笔详参,决无宽贷。(见樊增祥:《樊山政书》卷六,那思陆、孙家红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1页。)中国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能倒退复辟进行语言文字的大清洗。拿西方中心观来开帽子工厂,对其他人肃反者在许多情况下恰恰是彻头彻尾以西方为教条,曾几何时对中国传统法律投畀一瞥?笔者在《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第二次全面修订版中所列举的新旧水火不相容的内讧造成中国现代大学诞生过程中历史联系被斩断的教训便堪资镜鉴。参见拙著《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②转引自吴兴明《比较的悖谬——谈汉语学术语境中的中西比较》,载于《求索》2007年第1期。
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见彭世忠主编:《民事诉讼法学》附录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1页。
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资料来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13/10/3687216,访问时间:2010年11月28日。
⑤正是这样,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8条和第309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外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本国人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受本国公民的委托,可以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但在诉讼中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涉外民事诉讼中,外国驻华使、领馆授权其本馆官员,在作为当事人的本国国民不在我国领域内的情况下,可以以外交代表身份为其本国国民在我国聘请中国律师或中国公民代理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3号,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89次会议通过)第325、326条规定: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领馆可以向该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不得采取强制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居住的外国人寄给中国律师或者中国公民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所在国外交部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中国与该国之间有互免认证协定的除外。请求与我国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的法院代为一定诉讼行为的,必须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同意。与我国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的法院请求我国法院代为一定诉讼行为的,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转达。
⑥参见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文集之十六第52-53页。前揭三条史料亦见于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5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页、第1311页、第1311-1312页。
⑦Bamford v.Turnley,122 Eng.Rep.27,32 -33 (Ex.1863)。
⑧参见费肯杰《推参阐述和法律的推参阐述性定义》,张世明、冯永明、孙喆、张頔译,见张世明、刘亚丛、王济东主编:《经济法基础文献会要》,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08页。
⑨这一名言的法语原文为:Je désapprouve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资料来源:http://www.citations-francaises.fr/Je-desapp, 访问时间:2010年11月28日。
[1]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M].强世功,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达亚·克里希纳.比较哲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J].国外社会科学,1989(3).
[4]张耿光.庄子全译·内篇·大宗师[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5]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6]王伯琦.民法总则[M].台北:“国立”编译馆,1963.
[7]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8]俞江.关于“古代中国有无民法”问题的再思考[J].现代法学,2001(6).
[9]Konrad Zweigert,HeinKötz.EinführungindieRechtsvergleichungaufdemGebietedesPrivatrechts[M].Tübingen:Mohr Siebeck,1996.
[10]邓曦泽.合法性、方法论、格义与言说方式之牵挂——从2005年5月香港会议谈起[EB/OL].http://www.studa.net/zhongguo/060409/09550865.html,2009-09-05.
[11]田成有.西儒论语:西方法律思想中的智慧[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2]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13]黄树民.比较方法的运用与滥用: 学科史述评[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14]Burn,William Laurence Burn.AgeofEquipoise[M].London: Taylor & Francis,1994.
[15]理查德·A.爱波斯坦.简约法律的力量:序言[M].刘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6]Sally Falk Moore.Certainties Undone: Fifty Turbulent Years of Legal Anthropology, 1949-1999[J].TheJournaloftheRoyalAnthropologicalInstitute,Vol.7,No.1 (2001).
[17]Kelsen.Juristischer Formalismus und reine Rechtslehre,58JuristischeWochenschrift( 1929)1724, cited fromTheJurisprudenceofInterests[M].trans.and ed.by M.Magdalena Schoch,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
[18]张耿光.庄子全译·内篇·齐物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李维乐】
The Reflection on the Theory of Local Knowledge and Legal Pluralism
ZHANG Shiming
(The Law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Since Masaji Chiba’s book,LegalPluralism:TowardaGeneralTheoryThroughJapaneseLegalCulture,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it echoes in China each other with Clifford Geertz’s book,LocalKnowledge:FurtherEssaysinInterpretiveAnthropology, which makes the concepts of local knowledge and legal pluralism become fashionable terminology in many academic works, the discourse thrive at astonishing rate.The present paper is to reflect on the bias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and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synepeische method put forward by Wolfgang Fikentsc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anthropology, in order to express another kind of sound and avoid tunnel vision.
legal pluralism;local knowledge;synepeische method
2015-01-11
张世明(1966—),男,四川内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经济法、中国法律史、边疆民族史研究。
D90
A
1672-3600(2015)04-009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