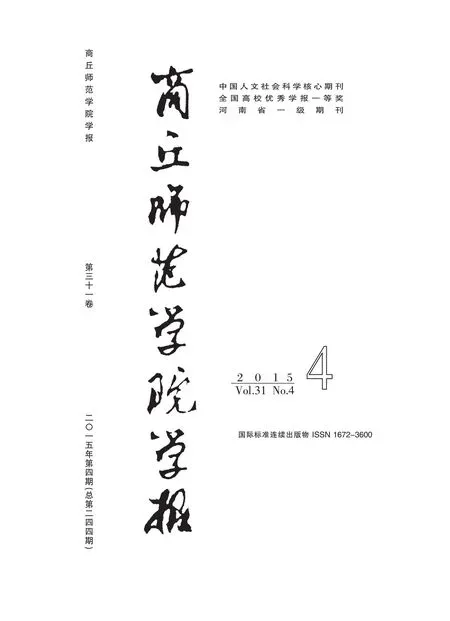人品文品交互辉映 学术育人相得益彰
——刘增杰等与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精神传统的拓展
刘 骥 鹏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人品文品交互辉映 学术育人相得益彰
——刘增杰等与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精神传统的拓展
刘 骥 鹏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增杰等新一代学人接过任访秋先生高擎的学术火炬,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范,从多方面拓展了任访秋先生开创的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精神传统。
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刘增杰;精神传统
在豫西抗战的炮火硝烟中,任访秋先生秉承“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的治学理念,在颇不宁静的书桌旁笃求宁静,孜孜矻矻、任劳任怨,克坚排难,开拓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片天地,并与他的同代学人一起逐渐构建起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精神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刘增杰、刘思谦等新一代学人接过任访秋先生高擎的学术火炬,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范,从多个方面拓展了任访秋先生开创的精神传统。
一
人性品格与学术品格交互辉映、相得益彰是刘增杰、刘思谦先生继承任访秋先生而又予以光大的一个显著特征。河南大学的区位劣势与其人文环境的和谐、人文学术的成就表明: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术研究,并不完全与物质条件的丰厚、城市环境的优越成正比。地处中原腹地的开封,不只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废都,而且也是一个被废弃的省会,且不说与东部发达的一线城市相比,即使与相邻的新兴省会——郑州相比,也显得相当落魄、寂寞与无奈。而在民国时期颇为辉煌的国立河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学科被拆并迁移到武汉、郑州、新乡,以之为基础崛起了多所新的大学。河南省会西迁之后,留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则遭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冷落,先后经历了河南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阶段。有意思的是,“大跃进”时期,即便全国各地一夜之间涌现出众多“大学”,而河南大学却依然被喧嚣的声浪所漠视。然而,正应了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无论遭遇怎样的命运,河南大学始终保持着落魄但不落后,寂寞却不沉沦,无奈却又能安身立命、自强不息的学术品格。她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操守,完全在于一大批学人对她的不离不弃,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有文学学科的任访秋先生、刘增杰先生和刘思谦先生。这批颇具古贤风范的学人在这个落寞的城市默默守候着这所寂寞的高校。尽管在查阅资料、发表文章、招收学生等诸多方面都颇为不利,然而他们却能拒绝繁华都市的诱惑,始终在此坚守着青灯自处的学术生涯,自然依靠的是他们人格的自信、强大与坚韧以及某种自甘落寞的奉献意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性品格,他们的学术品格才显得既如此淳朴厚重,又这样伟岸挺拔、卓尔不群,在学术界彰显出某种标杆性的意味。
作为河南大学中国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中的优秀代表,刘增杰、刘思谦属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步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多灾多难的第四代”[1],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背景,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生活烙印,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刘增杰和刘思谦先生,其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而青年时代则又是在政治运动中熬过来的。战乱、政治运动等不仅耗去了他们大量宝贵的时间,而且也对其人生与学术追求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大致说来,刘增杰先生更多地选择了对社会现实政治的顺应,但在敦厚、洒脱、柔和的外表下也不乏内在的清峻风骨,他“让岁月淡化掉苦涩与伤痛,更加投入地思想着,触摸着人生”[2]。在他看来,“文学研究的路实际上是一条自省的路。自我省察的程度往往直接决定着研究所可能达到的思想力度”[1]。他是把学术研究视为人生修炼的一种方式,并将修炼得来的人生感悟贯彻到学术研究和外在行为中,达到人品与学品的共同提升。
与刘增杰先生相比,刘思谦先生则更倾向于对社会环境的改变与抗争。在某种特殊的时期,她甚至呈现出某种激烈与莽撞。为此,她在特定范围内成为某种焦点人物,她也会因为自己的行为给身边人带来的尴尬而不安,因此也逐渐在人生策略上作出某些微调,比如她的由郑迁卞,就是不得已而作的人生调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刘思谦先生的这一被动迁徙,既是她本人的幸运,也是河南大学的幸运。因为她的到来,使河南大学文学院在80年代异常活跃的文学批评领域发出了自己亮丽的声音,并从另一角度继承了任先生等第一代学人延续下来的学术传统。她由此也和刘增杰先生一起,从两个互补的侧面,延续、拓展了任访秋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到了20世纪末,经过多年的耕耘,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终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俩与全国著名学者吴福辉先生携手,在王文金、关爱和、解志熙、沈文威等中青年学者的协助下,成功申报博士学位授权点,从而开拓出河南大学学术研究、学术育人的新境界。
二
学术研究淡定沉着、严谨求实、勇于创新是刘增杰、刘思谦先生努力拓展学术传统的又一方面。刘增杰、刘思谦先生从学术文献的发掘和学术理论的建构以及学术态度的持重与新锐、学术旨归的求实与求真等互补的侧面充实、丰富着任访秋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大致说来,刘增杰先生更注重文献建设,他对河南地域文学等作了大量的文集整理、校勘与阐释等方面的工作,其中,《师陀全集》为对师陀这位重要作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鲁迅与河南》对鲁迅与河南报刊、鲁迅与河南籍作家、鲁迅与河南风物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考释和梳理,“平实审慎,细大不捐”。在研究中,他常常遇到“某些史著在史料操作上所出现的讹误”,“特别是那些带有权威性的著作,失误往往显得格外刺眼”。他明确认识到,在世纪之交的学术研究中,“史料的薄弱,苍白,讹误,还有日益蔓延的趋势”,“史料编选的质量有日益下降的趋势。编选中的粗枝大叶、粗制滥造,大大降低了史料的可信度”[3]。因此极力呼吁“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4]。为了矫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浮躁之气,他与吴福辉先生等多位优秀学人一起倡导“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引起了全国业界同仁的热烈响应,并推动举办了多届这方面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科学化与严谨求实学风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秉承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刘增杰先生的文学史叙述、文艺思潮言说都显得格外谨慎、持重、精准。他坚持在求实的前提下有所创新,不苟言,不溢美,不隐恶,力求恢复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当然,他的这种慎重不唯与他经历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有关,还与他耕耘的学术领域密切相关。解放区文学是伴随着中共崛起而诞生的文学,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刘增杰先生最初涉足这一领域的时候,文艺界学术界乍暖还寒,政治权威对学术研究的宰制与干预依然触目惊心。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他勇敢地闯入了这片学术禁地,开始了开拓性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对包括解放区文学在内的左翼文学进行了颇有深度的阐释,为某些受批判的作家作品恢复了声誉,并初步还原了解放区文学的文学生态,颠覆了不少人对解放区文学的刻板印象。总之,他的持重不仅出自与意识形态的周旋,更是出自对学术的敬畏。事实上,他的持重并不影响大胆的学术创新,他早在90年代初就提出了“延安文艺新潮”的概念,首次对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等作家的杂文创作与文艺思想重新审视,并给予充分肯定,不唯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他的《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深入论述了近代以来14位颇具影响的作家、批评家的文学思想,通过对这些杰出人物与杰出作品的分析,把握住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波诡云谲的思潮变迁,见解精辟,新意迭出。
与刘增杰先生的学术态度相比,刘思谦先生更新锐、更具学术锋芒、而更着重于求真。这首先与刘思谦先生从事的当下文学批评有关。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浪潮最初是从文学界涌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创作潮流极大地冲击了保守僵化的极左思想,而关注、阐释、促动这一股股创作浪潮的文学批评则把情绪化、形象化的潮流上升为逻辑化、概念性的话语,从理论上为思想解放开辟新路。刘思谦先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她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在极“左”时代,她本人就常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甚至到了70年代末,她依然受到带有浓厚极左思想者的压制。在改革开放之初,蒋子龙的创作奏响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先声,其小说可以视为即将来临的国家全面工业化的报春鸟。自18世纪以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崛起,工业化是绕不过去的一条必经之路。然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却一波三折、命运多舛。洋务运动初步开辟出了近代工业的蜿蜒小路,却被迅速工业化的日本淹没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中。南京政府在东南沿海的工业化尝试尽管没有完全被列强的强势资本所挤垮,但吴荪甫的困境至少表明民族产业的脆弱与稚嫩;随后,日军的铁蹄更使这些脆弱的民族工业遭遇灭顶之祸。新中国依靠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建立起工业化的骨架,然而,政治运动的干扰、十年文革的埋汰,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企业因循、保守、弊端重重,严重落伍于世界新型工业化潮流。民族工业的现状召唤着一批工业弄潮儿引领中国的工业企业走出困境,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等人物形象就是新的时代对工业弄潮儿的呼唤。刘思谦教授敏锐地抓住这一批形象的典型特征,提炼出“开拓者”家族的命题,深化了文学界、企业界对这一新生群体的认识,将批评界对“改革文学”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刘思谦先生的命名与蒋子龙笔下的形象系列一起,激励着有志于产业报国的弄潮儿引领中国企业不断走向辉煌,其意义已经溢出了文学与学术的界域。初期除了对蒋子龙的批评之外,刘思谦先生还对一些影响大、读者关注度高的作家作品作出兼具阐释性与引领性的批评,如对张一弓的农村婚恋题材作品的解读,引出了当代中国妇女命运的问题。由此,她开始持续关注现当代女作家的生存与创作,将文学研究聚焦于妇女解放这一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带有焦点意味的课题,并与几位女性学者一起,构建其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骨架。在这其中,对丁玲在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中的摇摆与困惑作出了相当深刻、准确的阐释,颇为发人深省,不唯将当下的丁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还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命题,对左翼文学研究颇有启发意义。此外,她围绕着新时期十年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篇小说文体、十七年长篇小说经典化等问题,从多个角度进行当代文学的理论建构,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当代文学观。总之,刘思谦先生的批评实践与学术建树,在当代女性批评家中具有一定的标杆意义。
三
燃己度众、胼手胝足、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也是刘增杰、刘思谦先生拓展河南大学学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校园里的学者首先应该是一名称职的教师。在这一点上,以任访秋、刘增杰、刘思谦等为代表的河南大学文学院一批学者堪称为人师表的楷模。他们“带着教师职业的慈祥,和他的学生和同事之间,一直保持着看似平淡的真情”,他们对物质利益的淡泊、清静自处的操守、诲人不倦的耐心、自强不息的意志都足以泽被学界,垂范后人。
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历届研究生都深受这种学风的沐浴与滋润。一是授课内容丰富、学术含量高。刘增杰老师的文学文献课程,从新文学最初的期刊文献讲起,旁及新文学的学科化过程,其中对朱自清、李荷林、任访秋等先生拓荒性质的文学史著述与文学讲义,都作出富有启发意味的讲解,可谓春雨如油、润物无声;其育人态度之亲和、治学态度之严谨都给研究生们以深刻的感染。刘思谦老师的文学方法论课程,独辟蹊径,汲取古代书院教学方法的长处,在让学生细读指定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生与生、师与生之间相互辩难,从而深化了对各种研究方法优劣长短的理解与认识;事后,刘思谦老师和几位同学一起将给历届学生上课的讨论与作业编成了《文学研究方法论》一书,被多所高校采用为博士生的教材。二是诲人不倦,对学生的课后作业、论文习作批改不厌其细、不厌其烦。时下世人奉为金科玉律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的观念对这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毫无影响,他们往往搁下手中正在进行的科研任务,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学生的论文批改中,其修改的范围、幅度,有些几近重写。“红色经典重读”是刘思谦老师给2006级博士生们开设的一门专业课,课后每位学生提交了一篇论文习作,两周后,学生们拿到刘老师批改过的论文,都相当吃惊:从论点论据、作家作品、篇章结构到句子标点,她都作了仔细的修改和圈点。刘增杰老师对研究生论文从来也都是一字一句地审读,从观点材料、结构布局、遣词用字,都一一给以耐心的指导,其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每每令学生感激与赞叹。在教学中,刘增杰老师的扎实、严谨与认真,刘思谦老师的热情、细致与新颖,都给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三是将自身的经历与生命体验融入课堂之中,给学生以相当有益的人生启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两位老教师多有冲击,这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也给其生命平添了许多顿挫与波折。然而,他们并没有过多地停留在抱怨上面,而是以承受一切苦难的态度分析这些运动生成的深层原因以及运动中人性的种种表现,从而引出如何看待民族苦难、个人苦难的问题以及知识者如何在逆境中保持自我、保持奋进的问题,这种超然、豁达而又积极的人生态度给学生们的影响已经溢出了文学、学术之外,成为学生生命之旅中修身处世的智慧源泉。上述治学、尤其是处世育人特点,在关爱和、梁工、张云鹏、耿占春、孙先科、李伟昉、刘进才等该学科点教师们身上也都鲜明地体现出来。作为河南大学的一名学生,笔者深深感激这几位老师的教诲。笔者曾在拙作的后记中写下了这种内心感受:“如果说平生有什么幸运之事值得自己暗自庆幸,那就是我居然在虚度了多年光阴之后,还有幸步入这样一所人文积淀相当深厚的学校,跟随着这样一群纯粹的学人读书。他们的人格魅力书写着河南籍(吴福辉老师也常常自认为自己是半个河南人)知识分子的淳朴、厚道与持守。”
斗转星移、岁月更替,七十余年的光阴已逝,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形成了颇具气势的学术接力链条。刘增杰、刘思谦、王文金先生,后起的关爱和、解志熙、沈文威、孙先科,以及更年轻的刘进才、张先飞、刘涛、白春超、武新军、胡全章、孟庆澍等一代代学人,继承并拓展了任访秋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这其中,刘思谦对丁玲等现代女作家、孙先科对“十七年”某些重要作家作品的重新阐释都打破了某些已成定规的结论,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刘增杰、解志熙的史料整理,关爱和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上的近代文学研究都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他们力图以清代朴学传统矫正当下浮躁学风的努力,在“铁塔牌”的一届届博士毕业生身上也鲜明地体现出来。
刘增杰、刘思谦先生为代表的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团队,人品、文品交相辉映,学术、育人相得益彰。作为一个以学术立身的群体,中国古代的修身、立人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近乎完美的体现,做人与做学问的高度一致、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互相促进,使他们赢得了一届届学生和学界同仁发自内心的敬重。而随着一届届学子在全国高校的落地生根,河南大学的这些传统、这一学术群体的种种美德虽然润物无声,但必将发扬光大。
[1]刘增杰.路上——我的学术经历[J].东方论坛,2005(6).
[2]刘增杰.那一片火红的枫叶——访秋师杂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4).
[3]刘增杰.进展中的缺憾——略谈文学史建构中的史料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1).
[4]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3).
【责任编辑:郭德民】
2014-12-25
刘骥鹏(1963—),男,山东沂南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I206.6;I206.7
A
1672-3600(2015)04-008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