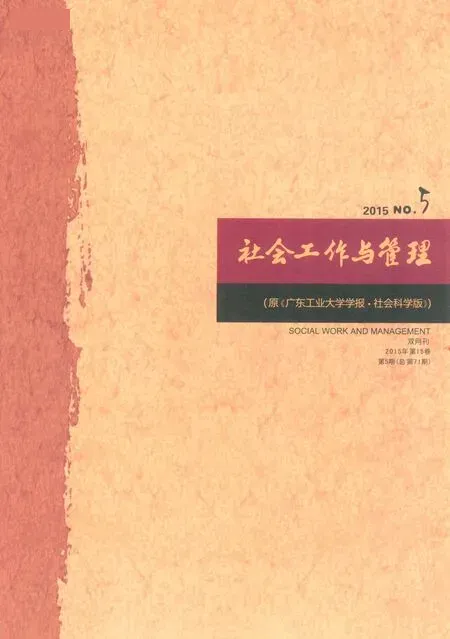论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的未来走向
屈振辉
(湖南女子学院教育与法学系,湖南长沙,410004)
我国社会工作近年来的发展亟待相应立法,这已成为我国社会工作界的共识。尽管某些省份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地方性立法尝试,但是全国性社会工作立法的进程依然非常缓慢。其成因固然与我国社会工作的不发达有关,但也与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理论研究的落后不无关系。“国内专业社会工作的实践尚无太多经验可以总结,关于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成果尚储备不充分,特别是社会工作立法方面的理论研究仅‘悄然拉开帷幕’。”[1]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因我国社会工作不发达,就误认为我国社会工作立法进程还可延缓,而应通过加快立法来促进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使我国社会工作立法早已时不我待。“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经验表明,专门的社会工作法律法规,可以极大地促进和规范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2]借鉴国外社会工作立法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及社会工作的发展,我国社会工作立法在未来将呈现出以下四方面走向。
一、社会工作立法是促进行业发展之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就处于转型期,社会发展尽管比较快,但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且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社会问题丛生,存在着各种显性和隐性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已经严重阻碍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如前所述,社会工作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也迫切需要运用社会工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当前我国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发展社会工作。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关照,利益分化过度失衡造成的裂痕需要弥合,社会信任和社会凝聚力需要重建……而发展以有效传送社会福利、建构和谐社会关系为己任的社会工作就成为一个重要选择。”[3]由此可见,发展社会工作对于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社会工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社会工作将成为我国今后重点发展的领域,社会工作立法因此也具有行业立法的意义。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行业发展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运用立法形式予以完善:其一,社会工作机构的管理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较之以往发展较快,特别是沿海地区社会工作机构如雨后春笋,其数量和从业人数在短期内呈现猛增之势。社会工作机构在我国还属于新型组织,现行立法也没有对其性质做出清晰的界定,且没出台法律法规,因此,无法进行较好的管理,某些机构违规从业和内部管理混乱的现象,已经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始显现。因此,我国必须加快社会工作立法的进程,以规范社会工作机构的组织和运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4]。这方面的社会工作立法可以借鉴《公司法》,借鉴其对组织构架和内部治理的规定。其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地位需要法律予以明确。职业在现代社会中是需要获得法律认可的,否则其职业者权益就将无法获得应有的保护。社会工作在我国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新职业,但有关社会工作职业的立法并未及时跟上。“社会工作是实践性工作,社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待遇与自我保护、社会工作的绩效评价等,需要从法律方面来规范。”[5]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职业立法尚处缺位状态,这也是造成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流失的要因,将使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成为无本之木。其三,法律应当明确政府在社会工作领域的职责。社会工作作为非生产、非营利性的社会事业,目前在我国较稳定的来源是政府购买服务。从目前全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政府购买服务较多的地方,社会工作就发达,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提供购买服务的,就落后。现代法不仅重在“治民”,更重在“治官”,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是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责。这项职责在计划经济年代由政府直接行使,换言之,即政府直接向民众提供社会服务;而在当今“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下,政府更多以间接方式向民众提供社会服务,例如,地方政府运用社会服务资金购买服务。但地方政府也有可能掌握着社会服务资金,而不将它们用于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这样不仅社会工作机构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民众也享受不到较高质量的社会工作服务。因此,对政府在社会工作领域的不积极作为,必须运用立法形式明确其职责,督促其作为。未来中国社会工作立法必须涵盖这三方面内容甚至对其专章规定,才能够起到促进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的作用。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总体并不理想,甚至并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行业,对此可通过立法形式推进其发展。依法治国是我国当代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通过立法促进社会工作行业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工作行业治理的法治化。加强立法是推进行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已为国内外许多行业发展所证明的事实。目前社会工作立法在西方国家已较为发达,美国、瑞典、奥地利及南非等国,都制定了有关社会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极大推动了这些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反观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相对较落后的现状,也与社会工作立法的缺位与疏漏有关。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行业迅速发展,但是相关的立法却严重滞后,甚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的瓶颈。[6]因此,应尽快制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立法,运用立法手段来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使之成为我国社会工作行业发展最重要的路径。我国社会工作立法应是促进社会工作行业发展之法。
二、社会工作法的基本法应当优先制定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制定社会工作相关立法,但是各国的社会工作立法模式却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围绕社会工作者为中心展开立法,例如,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和新斯科舍省的《社会工作者法》、菲律宾的《公共社会工作者法》、奥地利的《社会工作人员法》和日本的《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等;有些国家以社会工作职业为中心展开立法,例如,加拿大艾伯塔省的《社会工作职业法》、安大略省的《社会工作及社会服务工作法》、马耳他的《社会工作职业法》等;还有些国家并没有专门性的社会工作立法,而是将其作为其他社会立法当中的一部分,例如,韩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法》和瑞典的《社会服务法》中的相关条款。有学者将其称为社会工作立法的三大模式,即集中立法、分散立法和附属立法等模式。[1]基于对国外社会工作立法模式的上述划分,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工作立法应以社会工作职业为中心,即首先制定有关社会工作者法的法律法规。“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制定一部规范管理社会工作者的法律法规。”[7]“当前应该首先制定社会工作师法的专门法律。”[5]我国应将制定社会工作的基本法,即《社会工作法》置于立法最优先的位置。《社会工作者法》并不足以涵盖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中虽处于主体地位,但它并不能很好涵盖社会工作的全部内容。社会工作领域中某些亟待立法解决的问题,如社会工作机构管理和政府社会工作职责,就不适合在《社会工作者法》中进行规定。例如,社会工作机构在社会工作中也很重要,以《社会工作者法》为名的社会工作立法,就不适合将社会工作机构的内容涵盖其中。如果我国首先制定的是《社会工作者法》,那今后恐怕还要制定《社会工作机构法》,甚至要制定涉及社会工作其他方面的立法。这样的社会工作立法也就失去了其涵盖性,从而不符合立法应遵从的最大概括性原则。但通过制定《社会工作法》这样的基本法,则可以将社会工作的各方面内容涵盖其中,并且可起到统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作用。这个观点也是与有些学者不谋而合的。“应将制定一部属于集中立法模式的《社会工作法》作为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的最终目标。”[1]“我国社会工作立法应该以制定集中立法模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法》为最终目标。”[2]
有学者认为,我国未来“社会工作立法包括主体立法、事业立法和受助群体利益保护立法三个部分,”[7]其中前者基本上是有关社会工作者的规定;而中者和后者主要涉及我国社会工作各领域,但这些领域我国已有民政法规在进行调整。除非现有民政法规存在空白或已不合时宜,否则不宜用社会工作立法对其进行立改废,这样不仅徒增立法成本,且易导致法律冲突。还在事业立法和受助群体利益保护立法中将社会保障法的内容,如社会保险、救助、福利、优抚囊括其中,从而混淆了社会工作立法和社会保障立法。因此,这样的立法框架除前者外基本不可取。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工作立法先进经验,作为未来我国社会工作的基本法,《社会工作法》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章内容:总则(第一章)、社会工作者(第二章)、社会工作机构(第三章)、政府社会工作职责(第四章)、社会工作行业协会(第五章)、法律责任(第六章)、附则。总则部分主要阐明立法的目的和依据,以及其基本原则、效力和使用范围等问题;社会工作者部分主要规定社会工作者职业的法律地位及其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社会工作机构部分应明确社工机构的性质,并对社会工作机构的设立、运作及其终止,做出详尽规定,旨在规范社工机构行为;政府社会工作职责部分旨在明确政府职责;社会工作行业协会“从性质上说是作为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桥梁、对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利益维护的社会组织”,[8]必须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其地位和职责;法律责任部分主要是对违反本法行为进行制裁;附则部分是对本法相关问题的规定。这是我国社会工作立法应有的基本架构。[6]
三、尽快推动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出台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这也导致了各地社会工作发展有快有慢,通常沿海省份发展较快,内陆省份发展较慢。这导致了各地对社会工作立法的需求不同,通常沿海省份较为迫切,内陆省份不太在意。如前所述,立法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因我国目前还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立法,所以某些社会工作发展较快的省份或地市,例如,广东、北京、上海及深圳等地,都在寻求通过地方性立法形式加快其进程。这些地方性社会工作立法的呼声此起彼伏,也有力推动了全国性社会工作立法的进程。
我国社会工作立法应采取统一的立法模式,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法》。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的主要理由有三。第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这种立法模式。尽管加拿大和美国都有社会工作地方立法,各省(州)社会工作立法名称内容也各异,但这主要是因其尊崇英美法系的传统所致。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理应保持内部法制统一,社会工作立法不宜采用地方性立法的形式。第二,地方性立法的形式不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目前我国各地社会工作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如前所述,社会工作立法本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然而如果将这方面的立法权赋予各地的话,那么各地社会工作发展的差距也将被拉大,这也将导致各地的社会发展更加不平衡。“法律是寻求正义的科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公平正义和平等,如果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社会工作法律法规,不仅构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不平等,使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能得到保证。”[5]第三,各地纷纷立法也是对国家立法资源的浪费。“在现实生活中,一部立法可能耗时几年甚至十几年,或是造成大量立法资源的消耗,最终形成的却很可能是一部‘奢侈的法律’。制定‘良法’,需要我们在立法过程中注重立法成本的节约”。[9]社会工作立法就其本性而言应是“良法”,因此,就更需要注重立法成本的节约问题。时至今日,我国地方性社会工作立法仍处于规划阶段,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工作立法的难产。与其各地在社会工作立法上都搞各自为政,还不如集中全国这方面立法资源统一立法。因此,统一性社会工作立法在我国非常必要。“统一立法,立法权统一由中央行使,社会工作由一部统一的法典来加以规范是解决这种不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唯一方式。”[5]但我国社会工作立法应该是先制定基本法,还是如前所说的,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典”,在总体上还是持先制定基本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也有三个方面。第一,制定“统一的法典”模式的社会工作立法,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的立法成本,且时间漫长,因此,对我国而言只是美好理想而并不现实。而尽快制定《社会工作法》这样的基本法,则能够满足我国社会工作迅速发展的需要。第二,社会工作只是整个社会事务中的一个部分,对此不宜采用制定法典的形式进行调整。社会工作法就性质而言应纳入社会法典中,从而作为社会法典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奥地利社会工作立法就在《社会法典》中。制定社会法典较复杂,且耗时巨大,我国社会工作立法不能等待,必须先行。第三,在我国制定“统一的法典”社会工作立法,势必要涉及与对现行民政法规的立改废,这更是规模浩大且系统的复杂“工程”,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需要已是时不我待。综上所述,制定全国性的社会工作法基本法是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的当务之急。当然,广东、北京等社会工作较发达的省份,在社会工作立法方面进行的积极探索,也将为全国性社会工作立法提供许多借鉴。但后者更应考虑社会工作不发达地区的实际,而这也是全国性社会工作立法的要求。
四、路径上应专家参与与公众参与并重
专家参与与公众参与是现代立法两种路径,也是我国在社会工作立法时需要考虑的。前者是指在某个需调整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由对该领域具有专门知识、专门技能的人,参与调整这些领域的法律草案的制定过程;后者则是指全体民众都参与了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立法生成路径,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专家参与甚至是专家制定至少是草拟法案,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立法生成的主要路径。当然公众的参与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公众”主要指服务对象以及全社会成员。
在社会工作立法之中专家参与和公众参与,这两种路径不仅都有必要,而且还各有所长。专家参与不仅包括立法专家参与,还包括社会工作领域专家学者的参与;在后者中既包括理论专家也包括实践专家,即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和一线社会工作者。立法本身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法律工作,这意味着立法专家必然要参与到其过程中。在社会工作立法之中,专家参与有很多优势,它能保证立法的公正、正当、合法和科学,保证立法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规范性,从而保证该法的体系化及内部和谐、统一。[10]但社会工作毕竟是一种专业化的助人活动,具有自己独有的价值观、理论和工作手法。这是包括立法专家在内的很多普通人,甚至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都很难理解的。这时就需要社会工作专家、学者参与立法,从而保证立法在该领域中的专业性。社会工作立法就此而言具有两方面的专业性,即立法上的专业性和社会工作上的专业性,我国未来社会工作立法应注重这两者结合。与此同时,社会工作立法还应多吸纳社会工作者参与。他们具有较丰富的基层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在实际中遇到过很多具体的社会工作问题,也有着很多对这些问题智慧性的解决之道。这些都应当及时地吸纳到社会工作立法中,从而使立法更具有可操作性,且能解决问题。而我国目前很多地方性的社会工作立法调研,都是在当地社会工作者中进行和展开的,这就是社会工作立法之中的实践专家参与。[11-12]当然,如果只是专家参与立法甚至是专家立法,也存在着难以表达民众意愿等诸多弊端,因此,专家参与必须和公众参与密切相结合。“公民参与立法是保证立法民主的重要制度途径。”[13]事实上,社会工作立法并不像很多专门立法。后者往往局限在比较窄的专业性领域当中,从而远离人们的生活,而且人们也不常触及;而社会工作却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且社会越是发展,这种关系越是密切。广大社会公众是社会工作主要的服务对象,其对社会工作服务质量等问题具有发言权,因此,社会工作立法时必须要注重公众参与。
具体而言,未来我国在制定社会工作立法时,似乎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立法草案形成路径,即由立法部门召集立法和社会工作的专家,组织或者委托他们草拟立法的专家建议稿;然后由民政部门面向社会工作者征求意见,同时也由立法部门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从而形成对于立法草案修改的意见和建议。必要时,还可由民政部门组织在社会工作者中调研,从而形成社会工作立法的实践专家建议稿。在将两个专家建议稿合二为一的基础之上,再交由立法部门面向社会公众征求其意见。这样才能实现专家参与与公众参与的结合,也才能制定出科学专业和民主公正的立法。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社会建设正在逐步加快,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呼唤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使我国社会工作立法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谋划其未来的走向,这样才能为我国的社会工作立法铺平道路。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和积极努力之下,相信我国社会工作的法治化已不远。
[1]竺效,杨飞.境外社会工作立法模式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政治与法律,2008(10):140—146.
[2]袁光亮.我国社会工作立法思考[J].理论月刊,2011(7):139—142.
[3]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9(5):128—140.
[4]柳拯.关于社会工作行业组织发展的几点思考[J].中国社会工作,2011(20):8—10.
[5]方曙光.我国当前社会工作立法的探究[J].黑龙江史志,2009(2):135—136.
[6]屈振辉.论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的形成路径[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15(1):40—44.
[7]王云斌.社会工作立法框架建构研究[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2(8):26—30.
[8]彭善民.上海社会工作机构的生成轨迹与发展困境[J].社会科学,2010(2):54—61.
[9]刘少军.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2.
[10]布小林.立法质量研究[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106—107.
[11]谢泽宪.广东地区社会工作立法需求状况调查及立法路径建议[M]∥民政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社会工作文选(总第六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30—153.
[12]曲玉波,曾群.我国社会工作者的立法需求与路径选择——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地区综合的调查[M]∥卢汉龙,吴书松.时代性与社会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409—425.
[13]莫纪宏.论立法的技术路线——专家立法在立法公民参与中的作用[J].广东社会科学,2009(4):17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