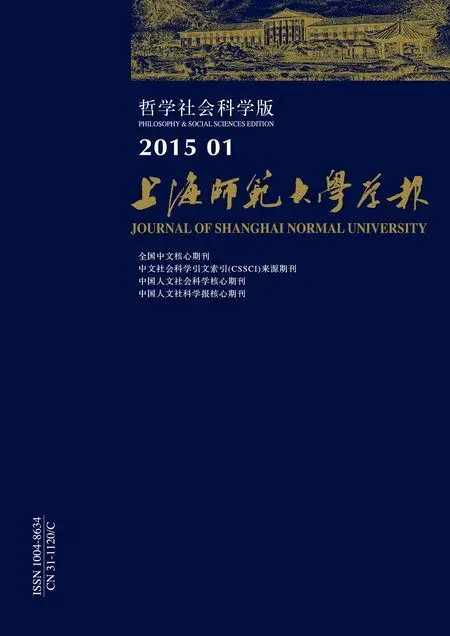国际劳工组织的悖论与承诺
[美]史蒂芬·L·威尔伯恩
(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 法学院,美国)
国际劳工组织一直致力于取得出色且受人瞩目的成就。为自由、平等、安全以及人格尊严领域中的正义且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提供更多的机遇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使命。①但是国际劳工组织和具有类似性质的组织却面临着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这些组织并非政府组织,因此它们没有直接的立法权力。很多时候,这些组织必须缓和与极具权势的经济力量的关系,甚至与他们发生正面对抗。在人口结构和工作环境极其复杂的环境下,劳工组织的工作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获得政府的协助。然而,这些政府部门常常在一个或多个领域中,存在着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比如,在制定完善的法规以及吸引资金方面。
本文援引了大量针对美国类似机构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国际劳工组织要解决的问题与自身的管理能力并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导致了一种严重的悖论。在侵犯劳工权益准则的重灾区,国际劳工标准要么没有市场、要么被束之高阁。国际劳工标准试图解决发展中的探底竞争问题(一种通过剥夺劳工、损费资源、破环环境来实现增长的做法),这将有助于缓解探底竞争现象。但同时,这些准则却使力争上游变得难以实现。国际劳工标准在与工人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领域可能最没有效力,比如在确保正义而有建设性的工作方面。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局限性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强。它还指出了该组织可能有能力解决的问题的类型。具体来说,国际劳工组织可能能够解决某些协调方面的问题,并在帮助促进国家内部的民主讨论和改变方面,起到了标杆的作用。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会介绍国际劳工组织的统治地位,并把它与统一法律委员会(ULC),②一个在美国具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组织进行比较。这两个组织在结构、职能和目标上大体相似。在美国,有大量针对在统一法律委员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机构的承诺及其局限性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将介绍这一研究的结果。第三部分将探讨这些研究中,国际劳工组织对美国国内类似组织的影响。
一、作为民间立法机构的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在许多方面是类似的。为了表达上的方便,我按照美国文献中的表述,将它们称为民间立法机构。“民间”,表明它们不是“真实”的立法机构,它们没有被赋予权力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立法机构”则表明,在重要的社会问题,它们依然是立法过程的参与者。正如所有便于表述的说法一样,这样的标签并不十分恰当。本节将描述和细化这些民间立法机构的类别,并将上述两个组织也纳入该范围内。
虽然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立法委员会功能类似于立法机关,但两者都不属于政府机关,也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因此,两者都扮演着在法律修订中给相关立法机关提出建议的建议者角色。这表明两者在立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相当的限制性。也就是说,它们的相关举措会受到针对其立法能力质疑的限制,它们的行动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劳的,除非别的合法立法机关采纳了它们的建议。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将对这些组织提出什么类型的规则产生很大影响。然而,这个因素不应该被过分强调。因为,从这两个组织方面来看,它们有一些相同的因素,使得上述限制因素不那么具有限制性。例如,这两个组织在工作方面从容不迫,从初步理念的提出,到最终成型的立法建议方案的确立,中间会有一个相当长的间隔期。这使得对提议通过可能性的预测变得十分困难。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约束。同样的,两个组织的理念和主要职能是制定可以颁布的法律条文。这方面的压力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远远大于质疑两者在制定条律能力上的局限会延缓甚至阻滞立法进程所带来的压力。③
尽管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在结构上有类似之处,但两者也存在着差异。我们先来看看两者的相似之处。首先,这两个组织在组织架构上大体是类似的。国际劳工组织的正式工作,由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劳工大会主理。每个成员国可派四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包括两个政府成员和来自工人和雇主群体的代表各一名。而在统一法律委员会中,每个州可以派出一个代表团。代表团在规模和内部构成等方面有一些不同,但代表通常由州长任命,各代表团通常由立法者和学者构成。④这里,两者有两个重要的相似点。其一是利益集团在两个组织代表团具有控制权的群体中,扮演着显著的角色。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工人和雇主都具有很明显的代表性;而统一法律委员会方面,州议员、学者和一些别的团体在这个过程中则发挥着显著的作用。⑤第二点是,两个机构的理事单位,不仅与基层的国家和州的政治进程紧密相关,而且同时又分别不承担直接且重大的政治责任。对于这两个组织来说,虽然最终监管机构的正式成员是政治任命的,但某种程度上因为没有法律授权,这两个机构都没能在区域政治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两个组织也都具备在制定议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领导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的领导机构在国际劳工大会的成员中产生,它负责制定会议议程,选举总干事,并负责该组织的计划和预算。统一法律委员会设置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来选举总干事,执行类似的功能,特别是议程设置功能。这些相似之处表明,这两个组织至少要分两个阶段来制定最后颁布的规定:(1)由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转发的提案;(2)通过会议或委员会本身的建议。
两个组织所采用的,考虑及采纳建议的程序也是类似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组织都要从两方面来审视通过法律的主题内容。对于国际劳工组织,这意味着在年会上要起草和讨论两份报告。对于统一法律委员会来说,这意味着每份立法草案都会在不少于两次的全委会年会上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讨论。这将有助于制定出经过精心策划和深思熟虑的立法案,但同时也意味着相对较长的延迟期,也为发挥组织内的政治动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另一个有趣的相似点是,两个组织提出的提案都分两种,这两种提案彼此之间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公约和建议书。公约是用于签约国颁布或批准的立法草案,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环节,使立法具有法律约束力。建议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是通过建议来指引政策、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工作。同样,统一法律委员会也制定统一的、模式化的条例。统一的条例之所以在草拟阶段严格保证统一性,是为了能够在州立法机关得到通过。另一方面,模式化的条例,运作上来说很像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书,“都是旨在作为立法程序的指引,国家可以引用或修改,以满足他们自身的需求和条件”。⑥我将在稍后讨论这个有趣的相似之处,但我将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在统一性的优势以及给定环境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需求之间保持困难的平衡这个问题上。
与其他类似组织的一些简单比较也突出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的相似性。美国法学会(ALI)是另一个在美国拥有影响力的民间立法机构,⑦它也针对现行法律拟定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建议草案,其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对各种不同领域法律提出有影响力的修订意见,如在合同、财产、侵权行为等方面。⑧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法学会与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存在着重大差异。由于美国法学会是一个自主发起的、终身会员制的组织,其成员与政治的相关性更弱,而且由组织本身选择自己的成员,而不是由政府官方任命成员。更重要的是,美国法学会制定的草案的功能和主要受众相比之前两者来说更具差异化。其制定的草案主要面向法官、律师、学者。修订建议,一般来说,主要针对的是法官和律师经常使用的法律条文,而不是对立法环节提出建议。这意味着,它不像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受到草案通过方面的限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修订议案质量不高,也很容易被法官和律师忽略。因此,美国法学会所面临的这种有效性限制,与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所面临的在通过方面的限制,在效力和本质上是大相径庭的。 同样,这个简短的回顾表明,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是颇为相似的,而且这种相似性强于两者中任何一者与美国法学会的相似性。
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的比较也印证了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大体相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是一个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立法机关重点协调和统一各国私法规则,特别是商业私法规则方面。⑨像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一样,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制定统一的私法规则并敦促各国采用。因此,它的立法实践也会受到通过限制。有趣的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也会制定类似劳工组织的建议书和统一法律委员会模式化法案的提案。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因为其制定的统一化的规定在提交会员国通过时遇到了困难。⑩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统一法律委员会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美国法学会的那些选择性的提案有更广泛的受众,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的选择性提案的受众仍然主要是立法机关,相比之下,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选择性提案的受众不仅是立法机关,同时也给其他组织或个人,如法官、仲裁员,还有在商业交易中涉及的各方。虽然这些更广泛的受众可能对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的提案感兴趣,但是两者提案的主要受众依然是立法机关,而不是这些群体。 更重要的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管理制度上与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有很大不同。 虽然设有一个由各成员国的政府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要决策权掌握在一个主事机构手中,但这些机构无论是从开会频率还是专业程度上来说都要强于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而且规模上也要小一些。因此,我们再一次证明了两者的相似度要比其中任何一者与美国法学会的相似度都要强。
国际劳工组织和统一法律委员会当然也有不同之处,以下的分析将会展现两者的一些不同之处。首先,国际劳工组织很明确地将利益群体纳入到它的组织结构中。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它是由“三方”构成的,也就是,公开从政府、工人和雇主内产生代表。相比之下,统一法律委员会没有明显与利益集团有联系的成员,恰恰相反,该组织呼吁会员暂且放下他们的个人和行业的利益,在工作时只考虑公众的利益。正如将在下文讨论到的,利益集团的动机可能影响这些民间立法机构出台什么样的提案。其次,国际劳工组织有一个更大的行政架构,这个行政架构内部还有一套更全面的问责体系。而统一法律委员会则有一个规模很小的行政人员系统,组织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委员自己做,这与制定统一而且规范的提案具有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国际劳工组织有一个规模更大的人员机构,更广泛的目标,以及更多元化的职责和责任体系。在除了制定公约和建议书外,国际劳工组织还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在其他事务中提高对劳动问题的认识,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并在劳工问题上拥有一套全面的数据。其职能的扩展对达成其作为民间立法机构的一些目标很有帮助。
二、美国关于民间立法机构的研究文献
在过去的15年里,美国学者已经对美国的这些民间立法机构的职能有了很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套有影响力的知识系统。这些研究试图弄明白并描述出这些组织是如何工作的,而不是研究其规范性,虽然它清楚地具有规范性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些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这个部分,我将介绍一些学者在此领域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第三部分中,我将思考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国际劳工组织。
首先,学者们从时间和原因两方面分析了这些民间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提案的模糊性或明确性。文献预测,民间的立法机构会产生模糊的提案,通常是因为其成员在制定提案时偏重的方面与立法人员希望偏重的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模糊性的规则往往赋予法庭更多自由裁量权,因为法庭与这些民间立法机构的成员在立法时的偏好,相比与政府立法成员来说更为相似。
然而,有时民间立法机构也提出具体的规则。相关文章表明,在两种情况下,这些组织才会制定具体的规则。要么是在当对相关政策有很多已经达成的协定,一时间可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实现协调时,要么就是当有一个是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能够取得这些民间立法机构内的政策辩论的胜利,并制定出具体的规则来维护胜利成果时。
在制定过程中出现探底竞争或者逐顶竞争现象的可能性时,学界也对这些民间立法机构提出过警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学界并没有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探底竞争现象,反而认为一个统一的法规要想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唯一的办法是接受底栖群体的规则。在所有其他情况下,都会出现反对者,而统一性的目标将会因此受到损害。统一的规则与底层群体的利益越有距离,就越有可能出现反对者。因此,这个过程包含倾向于肯定底层群体或迅速地向底层群体靠拢,而不是压制或阻止他们。同样,学界指出,如果逐顶竞争现象有可能发生,通过蒂布特排序或以其他方式,那么在利益顶层的压力下制定标准将会给机构的立法过程带来压力,也会使整个立法偏向于利益顶层的群体。
关于民间立法机构的研究文献也发现了一个与联邦制相关的观点。统一法律委员会是帮助起草并推动许多州的立法机关制定一个统一的法律的民间立法机构。实现统一性的另一种方式是由联邦立法机构制定法规。学界指出,民间立法机构和统一法律委员会的一个主要优点恰恰是它不太可能实现统一。联邦法律,顾名思义,将是统一的。而统一法律委员会所制定的法规,则可以根据州议会的不同情况进行修改。最“统一”的统一法律委员会所制定的法律不可能在没有经过州议会修改的情况下通过。相反,这些法规通常会加入地方的情况与特色。对于民间立法机构的研究文献还指出了民间立法与联邦政府立法途径对比时所突出的这种允许边际化改变的可能性。联邦立法途径意味着任何地方性的法规改变所带来的立法损失,都必须由地方政府承担。统一立法委员会的立法途径允许变化,以避免这些地方的损失。此外,边际变化的可能性,在维持统一性核心的同时,可以保留一些联邦制的好处,如政策创新、区域试验和区别性政策。
除了联邦和各州法律之间的比较,相关研究文献也比较民间立法机构与其他可能存在的民间立法团体。例如,在美国,统一的法律也可能会被外包给其他民间团体(如美国律师协会)、贸易团体和协会,或由个人(如通过权威的论文生产)。民间立法机构与其他可能的选择相比,主要的优点是它们促进汇集足够的资源来确保统一的法律颁布。对于其他群体来说,只有在任何个人或有关私人的方面利益团体可能获得足够的好处时,才会投入必要的资源,产生一个统一的法律。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统一法律委员会在其起草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可能会由于州议会对法案有自己的考虑而被否决。当利害关系方提出统一的法律时,否决的可能性较小。当利害关系方自己提出了相关的提案,这就对州立法机关在做政策选择时应该研究哪些领域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这些都不是我的结论,而是几位知名美国学者基于民间立法机构的仔细研究得出的结论。他们往往是积极的评估,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只是试图描述这些组织的运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目的不是规范。
三、关于作为民间立法机构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实例及其启示
这一部分将首先讨论上述预测是否适用于国际劳工组织。这是一个积极的评价。基于有限的核查,我的一般结论是,至少在一些美国文献指出的方面,国际劳工组织似乎充当了民间立法机构这个角色。然后,我将讨论这给国际劳工组织带来的可能的规范性启示。在一些重要方面,美国文献肯定国际劳工组织为完成自身使命而采取的方法。然而,分析表明,国际劳工组织面临着严重的限制和约束。
为了评估对于民间立法机构的预测是否适用于国际劳工组织,我核查了两个基本的有关童工的公约,《最低年龄公约》和《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这两个公约在各自的相对模糊或具体性上有很大的差异。《最低年龄公约》是非常模糊的、开放式的,甚至并未指出童工工作的最低年龄标准。相反,它允许各国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最低年龄标准。该公约还使各国能够排除某些类别的工作,并做出其他调整。《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则非常具体地指出了各项禁令(如禁止儿童奴役和卖淫),并为局部变化提供较小的空间。
这种差异与研究文献对于民间立法机构的主要预测吻合。文献预测,第一,当民间立法机构内部没有一个利益团体可以取得政策选择的绝对优势时,就会制定模糊的规则。鉴于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代表的分歧,以及成员国内部千差万别的童工状况,任何特定的利益集团控制最低年龄公约起草过程的话语权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文献研究,制定的法规将会是模糊的。相比之下,《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的具体性是有可能的,因为成员国在有限的实践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工人、雇主和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可能已经达成共识:有限种类的工作形式将严禁童工从事。《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比《最低年龄公约》更快被各国接受的事实恰好验证了这个假说。目前,只有12个国家还没有通过《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要知道它的出台不过只有10年。与出台超过30年的《最低年龄公约》相比,其通过率是后者的两倍。这与相关学者有关具体性的相关说法,即当有足够程度的共识时,即使没有组织内部的推动,具体性的统一性的立法也将同时出台是一致的。因此,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与美国文献对民间立法机构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
《最低年龄公约》似乎也与文献关于逐顶竞争和探底竞争现象的研究十分吻合。对于民间立法机构是否会迫于内部压力而促进逐顶竞争、设定刚好低于上限的标准,文献持怀疑态度。毫无疑问,《最低年龄公约》中关于最低年龄的设定远远低于最高值。例如,例外意味着,一些国家即使允许年仅12岁的儿童从事一定条件下的工作,即使部分童工完全处于条约的保护范围外,他们仍然是合法的。由此看来,正如文献预测的那样,公约不会有助于标准设置趋向最高值。
另一方面,文献预测民间立法机构可能协助或巩固探底竞争现象。有观点认为标准设置将会贴近最低值来推动实施,这将会导致默认低标准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确认过程会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公约”的制定环节也会有提出质疑的国家参与。从这一点看,劳工标准可以被设置为低于“公约”的最低水平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更接近底线。另一方面,“公约”的灵活性意味着国家可能将会实行相当低的标准。这可能意味着,正如学界预计,“公约”可能倾向于巩固低标准。持趋低标准策略的国家将批准“公约”,遵守尽可能低的标准,然后根据公约,为雇用可怜的低龄童工做法的指控进行抗辩。遵守公约标准的趋低性现象并不表明这些事正在发生,而是很有可能会发生。因此,这个预测并不明确支持关于趋高性的预测。
国际劳工组织似乎类似于美国文献中讨论的民间立法机构,这既是因为它们在结构上的类似,还因为,整体来看,它的一些做法证明了美国文献的预测。对于国际劳工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能力来说,这在规范意义上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分析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结构不适合实现统一的高劳工标准和社会保护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会从通过区分试图消除最糟糕的劳动条件和以提高劳动标准这两组概念开始。在第一组概念中,这一分析表明,国际劳工组织可能是一个不必要的或无效的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在大多数国家投入的努力是不必要的,因为根据假设,在大多数国家,低标准的劳动实践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使国际劳工组织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些国家也会自发地禁止。这些低标准的劳动实践只存在于缺乏民主体制和世界舆论监督的地区。对于这样的制度,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很可能是无效的。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国际劳工组织在实现改变方面的成功,很可能称为一种可以促进国家内部民主讨论的功能。但在这些制度下的这些问题,这些途径是不可用的。
该分析对于国际劳工组织在提高劳动标准以避免其发展为不人道境地的努力也没有持很乐观的态度。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像国际劳工组织这样的民间的立法机构是不太可能推动逐顶竞争标准的。此外,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可能会导致探底竞争现象,或者至少是巩固相对较低的标准。是否拥有足够的权力和对实现正义的、建设性的工作目标的追求存在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恶化。根本问题是,“权力”是一个分离的两极分化的词语,一个人可能拥有这种权力,也可能没有。而“正义的”和“有建设性”的工作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正义”和“有建设性”的工作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这涉及探底竞争问题,但又有所区别。当然可以说,在某一个点的工作低于可接受的“正义”水平,但(a)可能是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这是探底竞争问题),(b)可能没有反映国际劳工组织对正义或有建设性工作的更高期望。因此,“权力”往往与“正义”或“建设性”工作的这种更微妙的定义相冲突,至少使得后者所包含的丰富含义没有像应有的那样展现出来。
然而,尽管有这些显著的缺点,文献还是认为国际劳工组织在比通常理解的更为狭隘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劳工组织在解决由协调不当导致的低劳工标准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艾伦·海德教授一直通过他令人回味的猎鹿比喻来表明自己是这个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他拿雇佣童工问题来进行举例。猎鹿的故事内容是:如果猎人们合作,捕捉、共享雄鹿,那么每个猎人都会过得不错。但每一个人猎人也想设陷阱去捕获一只野兔,野兔虽小但更易捕捉。在游戏中的战略性难题是,只有所有猎人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获;但如果一个猎人背叛,随后每一个猎人都会因为无法捕获鹿而背叛,去设陷阱捕捉野兔。海德教授借鉴了这个著名的博弈论的例子来解释低童工标准。如果他们在时间1时禁止使用童工,而把他们送去上学,所有国家可以在时间2时处于较好的状况。但是,即使仅仅一个国家背叛而在时间1从童工身上获得了较小但较快的回报,那么所有国家都会背叛。像国际劳工组织这样的一个组织可能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可以让各国承诺在时间1遵守猎鹿策略(无童工),那么所有国家都会在时间2富裕起来。实验证据是明确的,在缺乏一些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多玩家猎鹿游戏几乎总是捕获了野兔,而不是鹿。因此,我们又一次确定,国际劳工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和富有成效的作用,如果它能够在这些情况下进行协调安排。
尽管指出了国际劳工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但这种协调性角色的逻辑支撑仅是相当有限的。首先,猎鹿理论的条件可能是相当罕见的。海德教授只明确提到了童工、强迫劳动、健康和安全标准。但我们尚不清楚,所有这些是否满足猎鹿理论的条件。例如,猎鹿理论要求,如果他们在时间1实施正确的战略,所有国家将在时间2受益。然而,如果所有国家在时间1时禁止童工,他们在时间2时是否会受益,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实证问题。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获益,那么这种模式下,该国家应该会在时间1背叛,这将导致其他国家的一并背叛,并导致整体的瓦解。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协调对普及禁止童工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相反,需要更多的努力,比如给这一类的国家承诺补贴,如果他们在时间1禁止童工,就可以确保在时间2时获取更高的回报。但这要求国际劳工组织不再仅仅是进行协调,而是实施一种更有难度的策略。
其次,即使说明了猎鹿博弈的条件,国际劳工组织是否可以承担协调的角色也未可知。其中的一个障碍在于,猎鹿博弈的试验工作表明,协调在较大群体内不太可能实现,即使是在重复协商的条件下。在一些没有机会参与反复磋商的国家,达成一致的劳工标准是一件更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际劳工组织是否有能力完成这类协调值得质疑。有关协调工作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工标准固有的模糊性。一方面称,国际劳工组织将协调在时间1的禁令,使之适用于所有年龄小于18岁的人。另一方面又说,正如《最低年龄公约》规定的,一些国家的某些情况下,禁止年龄小于18岁的人参加工作,但有时年仅15岁的人可以工作,甚至是14岁或12岁。《最低年龄公约》中的区别是有充分依据的,但这使得协调任务变得更加困难。相反,因为协调更加困难,倒戈的可能性也就更大。这导致野兔比鹿更加可能被捕获。
然而,这些问题和局限性,不应掩盖其给劳工组织带来的新的机会。猎鹿比喻表示,有些情况下,协调可以完成,并产生真正的实惠。当然这个任务是困难的,但国际劳工组织独特的优势,可以发挥这种协调作用。因此,它具有独特的优势,使国家和他们的工人获得这些实惠。另一方面,如果国际劳工组织无法完成协调工作,利益也就无法实现。
民间立法机构的研究还提出另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国际劳工组织不应该去追求统一的标准和国际化的共识,而是可以在发展高标准的、有利于成员国内部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讨论和实现建设性变化的基准测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这个角色为国际劳工组织设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提出了对高劳工标准的发展要求。它认为高劳工标准,主要依赖于国内层面的发展、生产力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大有不同。这种角色的设定,会动摇国际上的探底竞争或逐顶竞争的观点,而主要依赖于国家内部条件来确定劳动标准的水平和方向。它认为,国家间关于高劳工标准和优良的劳动实践的比较信息将会影响并促进国家内部劳工状况的改观。另一方面,尽管这些概念中很多似乎与国际劳工组织强调统一性和国际化共识不同,国际劳工组织也发挥了很多切合国际框架的作用,这样做是十分恰当的。它汇集了有关劳工状况和劳动实践方面的丰富数据,提供技术援助,并提供良好的劳动习惯的培训和指导。尽管国际劳工组织似乎执行这种类型的功能方面结构完善(在许多方面也一样),它提出了促进公约和建议书的发展的不同途径。但是标准不应该是追求广泛的认同而最终变得模糊且水平较低,标准的设定应该更有雄心。它们可能是更具体、水平较高,而且可以通过国家内部的民主进程予以调整的一种准则。
协助内部民主变革朝着更高的劳工标准发展,这样的功能才是文献希望民间的立法机构所发挥的。这一文章表明,一个民间立法机构的功能可能是集中资源,来支撑标准的制定。在这里,国际劳工组织可以担任这个角色。此外,文章指出,民间立法机构优势之一是,它允许非一致性,这十分具有讽刺意味。民间立法机构不是像联邦或者国际立法途径那样,对每个个体施行相同的规则,它允许调整和灵活性。在此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将提供劳动标准,但他们可以通过内部的民主进程调整,以适应当地的条件。
国际劳工组织这种类型的角色,与它现在的功能相比较来说,既变得更加宽泛,同时也相对地收紧了。首先,它的职能窄化了,很明显,因为它不再渴望制定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另一方面,它的职能也更广泛了,因为它有利于发展更高的劳工标准和更多样化的方法来促进它们的提案得到通过。
(余武姮 译,刘 诚 校)
注释:
①Quotation is from the “About the ILO” p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website,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_the_ILO/lang——en/index.htm (last visited, April 15, 2010).
②Although known informally as the Uniform Law Commission,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is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
③Alan Schwartz & Robert E. Scot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e Legislatures, 14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595, 608-09 (1995).
④The author is one of Nebraska’s commissioners on the Uniform Law Commission.
⑤Even when not implicitly represented by delegates, interest groups are explicitly invited and welcomed into the rule drafting process of every ULC project.
⑥From the ULC website, http://www.nccusl.org/update/DesktopDefault.aspx?tabindex=0&tabid=11 (last visited on April 15, 2010).
⑦Information on the ALI can be found on its website, http://www.ali.org (last visited April 15, 2010).
⑧The ALI also produces statutes to recommend to state legislatures, usuall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LC. This comparison, however, focuses on its main products, the restatements.
⑨Information on UNIDROIT can be found at its website, http://www.unidroit.org (last visited April 15, 2010).
⑩In addition to uniform laws, UNIDROIT produces model law, statements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legal guides. UNIDROIT admits that these other products are necessary because of enactability problems: “The low priority which tends to be accorded by Government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Conventions and the time it therefore tends to take for them to enter into force have led to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alternative forms of unification in areas where a binding instrument is not felt to be essential.” See UNIDROIT web page, at http://www.unidroit.org/dynasite.cfm?dsmid=103284 (last visited April 15,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