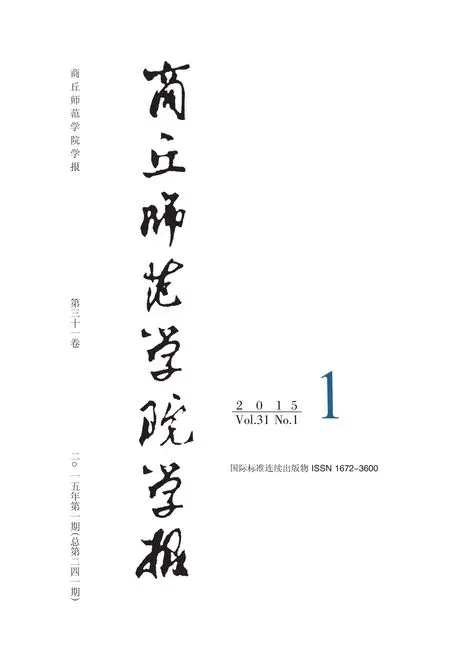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析评
李 明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60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析评
李 明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60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历经演化直至拉克劳与墨菲那里才基本成型。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它泛指一切用后现代主义思想、精神或概念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指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该思想基本内容是反经济决定论、反阶级还原论、反历史决定论、主张革命主体多元论、主张“激进与多元民主”。探索与批判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多元论;激进民主
一、后马克思主义演化史及其概念解读
据考证,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裔的哲学家波兰尼在其著作《个人知识》中最先提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但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范畴最初被人重视起来是缘于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的出版。在该部著作中,贝尔提出了著名的“双套图示说”:《资本论》第一卷图示和《资本论》第三卷图示。《资本论》第一卷图示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而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论》第三卷图示则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形式变化、产业经理、白领的涌现、利润的社会化等趋势。贝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是按照马克思的第二套图示演化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的对话”[1]73。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基本意思是指,由于社会关系复杂化、阶级的多元化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使古典马克思主义以社会整体的方式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革命模式成为不可能,社会的变革转向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良。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的科拉柯夫斯基、米奇尼克,法国阿兰·图雷纳,美国的琼·柯亨、鲍尔斯和金蒂斯等人对后马克思主义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真正使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深受普遍关注的社会思潮则是1985年拉克劳与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的出版,同时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也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演化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在拉克劳与墨菲那里,他们明显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视角、思维方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此之后,造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并用的情况,同时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也因此变得庞大而复杂,并引起了众多的学术纷争。这场争论是具有国际性的,詹姆逊、麦克莱伦、西姆等国外著名理论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提出了“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划界问题,影响较大,但难以形成共识。
后马克思主义最独特的地方“在于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武器来捍卫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价值”[2] 258。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产物。但需要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是不确切的,因为拉克劳与墨菲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不确定的概念,有时是指“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有时是指“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时是指“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有时是指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那么与后现代主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哪种呢?其实并没有特指,这就造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存在模糊性,只能大致将其界定为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糅合起来而形成的一场客观存在、影响广泛的西方社会思潮,但就其影响广度和深度来说则更多的体现在政治学领域内。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更多的应属于西方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已在我国学术界,尤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加强该思潮的研究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大体上将拉克劳和墨菲、德里达、詹姆逊、波德里亚、齐泽克等人的有关思想作为典型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了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其中,拉克劳与墨菲代表了“正宗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德里达是从后结构主义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逊是作为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批评者而滑入到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去的代表者;波德里亚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到后马克思主义的;齐泽克则是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坚定的游击战士”,思想飘忽不定而又始终渗透着浓烈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味道”。
二、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纵览
鉴于拉克劳和墨菲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我们很有必要单独透析一下他们所共同阐发的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理清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是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的基础上所建构出来的“激进、民主、多元”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构建一方面融合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理论,甚至含有胡塞尔的现象学,另一方面运用所融合的多种理论工具和学术话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及其思想进行重新阐释。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在传统的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体现在五个方面:1.阶级争斗和历史决定论;2.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3.资本主义危机和必然灭亡;4.革命的和批判的辩证法观点;5.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3]188-189。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拉克劳和墨菲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批判。
第一,批判经济决定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种“唯经济主义”基础上的理论,他们要拒斥的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那种“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的“还原论”观点。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经济决定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4]83。他们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经济决定论”的“不合时宜”性。他们指出,“经济决定论”所主张的经济是一个社会基础性的结构概念,政治、文化等依附其上,尤其是政治并没有什么独立性,总是围绕经济进行运转。但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经济无法决定政治,政治空间完全可以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拉克劳与墨菲严重割裂了政治与经济的必然联系,使政治悬空在经济之上,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
第二,批判历史决定论。拉克劳和墨菲采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把社会分解成不同的话语,并认为社会是受话语支配的。在他们看来,社会是由话语体系所组成的实体,它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它是偶然性的聚合地,而非是受历史必然性制约的场所,与社会密切相关的历史只是任意排列、随机出现、偶然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堆积。能将社会或历史的偶然性聚集、贯彻起来的只能依靠“话语的逻辑”。换句话说,历史呈现的只是语境,支配历史的也只是语境,而语境本身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因此,历史发展只能受制于偶然性,如果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也不可能脱离语境而存在,说到底,它依然还是遵循着偶然性的逻辑。拉克劳与墨菲明显夸大了历史语境的作用,否定历史发展存在客观的规律。
第三,批判阶级还原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是一种阶级还原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集中表现为把一切政治关系归结为阶级的经济利益关系。对阶级还原论的解构,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本质主义进行“颠覆”。他们认为经济范畴,特别是剥削关系与统治关系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例如,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中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等于工人阶级在政治要就一定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工人阶级其实在政治上已经被资产阶级所同化了,因而“工人阶级作为‘变化的历史力量’的观念已不再有效了”[5]76。这种观念本质上就否认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
第四,主张革命主体多元论。既然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受到质疑,那么资本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革命性的主体呢?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当今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身份,所有的社会身份都是随机建构的,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因而在政治主张和革命立场上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事实上……把政治主体构想为不同于阶级并比阶级更加宽泛,通过社会主义力量必得考虑,也能够接合的多种多样民主矛盾,这些政治主体得以不断地被构建起来。”[6]58所以,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主体不是单一的和固定的,而应该是多变的、多元的。
第五,主张“激进与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策略。由于革命主体是多元的,他们用一个含义模糊的“人民同盟”概念取代了“工人阶级”的概念,并将其视之为激进民主的主体,但人民同盟“不是由阶级关系构成的,也不是由任何决定性的社会关系构成,而是由话语构成的”[4]83。某时、某地“话语”诉求一致者就可能形成某种“同盟”,当某种“话语”消失后相应的“同盟”也就不存在,但新的“话语”可能再次联结新的“同盟”。因此,社会主义的革命动因并不源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社会解放的推动力是由自由、激进、民主的“话语”实践而构成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政治实践都不存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话语”就是基础,“话语”就是旗帜,“话语”就是方向,“话语”就是一切。这是十足的“话语本质主义”。其实,何种“话语”背后都有物质的动因和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拉克劳和墨菲显然是漠视的。
三、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的批判性反思
首先,虽然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抓住了历史上某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实际的“硬伤”,但以强调具体历史语境为借口而否认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发展规律性的 “假历史辩证法”,也使得其理论走向了相对主义而无法自拔。这便注定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犯了所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通病: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
其次,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从后现代主义观点出发,错误地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定为是近代哲学思维上的“本质主义”、“还原主义”的产物,其理论实质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其实,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并非是拉克劳和墨菲的独创,特别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是历时已久的,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经济决定论,而其他的所谓的反阶级还原论、反历史决定论、主张革命多元主体论看似新颖,实质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拉克劳和墨菲主要的作用是运用一套后现代话语将上述观点在后现代语境下系统化了,正是这种系统化,“拉克劳和墨菲系统误读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2]261,并在“系统误读”下“严肃”地论证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当然这种目标的设定,我们也只能将其看做一种“话语”而已。
再次,拉克劳与墨菲特别关注革命主体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社会主义革命主体问题是一个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界存在众多争议、异常复杂的问题。不仅是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要重新界定工人阶级的性质及其政治能力。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沙夫、西班牙左派社会学家特扎诺什、俄罗斯学者萨马尔斯卡娅等众多左翼人士也都认为单一工人阶级无法独立承担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工人阶级必须要善于和其他新兴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反战运动、反恐怖运动等结成战略同盟。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值得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注与研究。但他们否定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歪曲工人阶级的性质,将工人阶级降到一般的社会运动团体地位的思想是必须要加以批判的。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脱离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是无法成功的,即使实现所谓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也只是徒有虚名而不具备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最后,既要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上的错误性,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精神。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彼得拉斯指出,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撤退,后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的时尚立场,后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笔者认为,彼得拉斯的观点也许不适合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但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来说却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拉克劳和墨菲并不认同这种批判,他们面对西方传统左派的种种批评与质疑,始终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无须认错”的,特别是拉克劳在其另一本代表作《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对种种对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观念进行了系统性的回应,并一直都坚信自己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此,笔者暂且撇开他们理论本身的功过是非不谈,就他们从时代的发展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出发来认真地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精神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结论存在错误,但总比我们今天的某些闭门造车式、以正统自居的假大空“话语”所给予我们的启发要多一些。最起码作为一个以非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氛围下的知识分子能把探讨“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事”真正地来做,能把《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认真的研读,就值得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分子很好地进行自我反思。正如张一兵教授在提出文本学研究时所担心的那样:我们是否有资格去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7]1。我们今天也要反思,我们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分子是否完全具备了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资格?在当前中国语境下,笔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能够扮演一种激进批判力量的角色。因为,当代中国“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8]3。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多元革命主体的联盟和接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成我们抵抗当前权贵资本的一种重要的话语力量。当然,这种转化工作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寄希望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将包括后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多种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都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中,丰富自己的理论资源,拓展自己的理论空间和学术话语途径。不过,我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是必须的,这不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因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更因为在各类旧话语不断翻新、新话语层出不穷的话语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在不断接纳与批判他者中掌握理论上的话语权。
[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4][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英]拉克劳.阶级“战争”及其之后[M]//周凡,李蕙斌.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6][英]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里[M]//周凡,李蕙斌.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7]张一兵.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丛书总序[M]//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8]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M].北京:三联书店,2007.
【责任编辑:李安胜】
On the Post Marxism of Laclau and Mouffe
LI Ming
(Marxism School,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230601;Philosophy School,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The concept of post Marxism formed in the period of Laclau and Mouffe after evolution.The generalized post Marxism,which formed in western society of the 1980s,refers to the social thoughts which we employ in understanding Marxism by means of postmodern thought,spirit and concept.The narrow-sense post Marxism refers to the post Marxist thought of Laclau and Mouffe.This thought advocates the pluralism of revolution subject,and redical and plural democracy rather than economic determinism,historical determinism and class reductionism.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meaning to explore and criticize the post Marxism represented by Laclau and Mouffe at present.
post Marxism;determinism;reductionism;pluralism;radical democracy
2014-11-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编号:13BZX010);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编号:2012SQW010ZD)。
李明(1974-),男,安徽巢湖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A8;B1
A
1672-3600(2015)01-005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