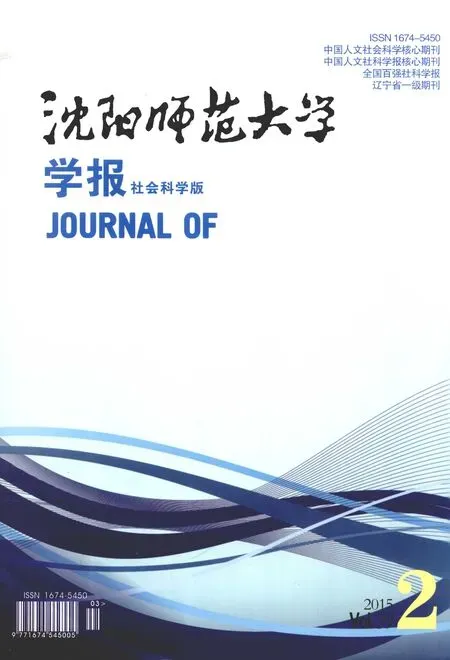《文心雕龙》中的小说理论因子
马骁英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文学与语言学】
《文心雕龙》中的小说理论因子
马骁英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由于刘勰独特的小说地位论和小说观,《文心雕龙》没有为小说文体设置专篇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兼备众体的文论名著中没有涉及小说理论。《文心雕龙》中存在着大量的小说理论因子,它们散见于《正纬》、《辨骚》、《谐隐》、《诸子》、《封禅》、《夸饰》等各篇章之中,虽如吉光片羽、零珠碎玑,但却弥足珍贵,具有非凡的理论深度和不容忽视的肇源意义。《文心雕龙》中的小说理论因子,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尚“奇”的艺术追求、贵“虚”的艺术旨趣、“会俗”的艺术价值取向。
《文心雕龙》刘勰;小说理论因子;小说理论发展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成就空前的文学理论名著诞生的时代背景。《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的所有文体,并且对每种文体都进行了高水平的理论阐释和理论总结。然而,通观《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的二十篇篇目,不难发现,《文心雕龙》似乎百密一疏地遗漏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种文体——小说。《文心雕龙》在其宏大的体系结构中,竟没有为小说保留一席之地,没有为小说这种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文体设置专篇专论。
通过对《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的梳理与细读,我们发现,事实上,《文心雕龙》并未完全忽略小说文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文体的蓬勃发展、繁荣兴盛,使得小说创作的艺术精神、艺术手法,自觉不自觉地、不可避免地浸润并渗透入了当时其他各种文体的写作之中,使各种文体都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小说创作的某些艺术手法,浸染了小说创作的斑斓的艺术色彩。同时,小说文体本身起源的“杂史、杂传、杂记”形态,与其他各种文体具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血缘关系,小说文体的雏形已经初具了兼备众体的某些特征,小说文体的雏形与其他各种文体已经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浑融局面。因此,《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对其他各种文体的论述与阐释,无可避免地、自觉不自觉地会论及蕴含在其他各种文体中的小说创作的艺术范畴、艺术手法和艺术精神,这些对其他各种文体中小说因素、小说特征、小说色彩的论述散见于《文心雕龙》二十篇文体论之中,构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小说理论因子的群落,它们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的最早痕迹,对这些吉光片羽、零玑碎璧的小说理论因子进行梳理和阐释,对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衍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尚“奇”的艺术追求
尚“奇”,追求“奇”的艺术效果、艺术情节、艺术形象、艺术表达方式,是小说文体的重要特征和鲜明特色。《文心雕龙》中蕴含着大量的关于尚“奇”的小说理论因子,对各种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的“奇”的特征进行了精要而透彻的论述。
《文心雕龙》指出,在众多文体之中,谶纬文体明显而突出地具有着尚“奇”的总体特征。我们通过详细体味《文心雕龙》对谶纬文体的论述,不难发现,谶纬文体的这种“奇”的显著特征,是谶纬文体中所蕴含的小说性因素所造成的。《文心雕龙·正纬》云:“经正纬奇”[1]30,指出,相比于儒家经书的严肃雅正,本应与儒经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谶纬文体却明显具有奇诡怪异的特征,与儒家经书风格之正形成尖锐对立,抵触背迕。后世学者认为,谶纬文体的这种奇诡怪异的总体特征,甚至达到了“颠倒舛谬”的近于“妖妄”的严重地步,《隋书·经籍志·六艺纬类序》云:“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孔安国、毛公、贾逵,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2]这些儒家经学视角之下的“妖妄”“颠倒舛谬”,实际上都是谶纬文体所包蕴的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性因素所造成的传奇性的故事性的令人惊心骇耳的艺术效果。刘勰在论述这种艺术效果时,运用了“鸟鸣似语,虫叶成字”[1]30这两个在谶纬文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典故作为例证,来说明谶纬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所带来的“奇”的文体特征。《左传·襄公三十年》:“鸟鸣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3]《汉书·五行志》:“董仲舒以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节三十余年,又忧伤国家之患祸,积阴生阳,故火生灾也。”[4]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嘻,悲恨之声。宋有灾异,鸟先感之,作声如言嘻嘻也。”[5]《汉书·五行志》:“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昭帝崩,无子,征昌邑王嗣位,狂乱失道。霍光废之,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帝本名病已。”[4]正是这些阴阳、灾异、符命等等在中国古代长期泛滥、风行的文化基因,使谶纬文体的内容具有了强烈的传奇性和故事性,促成了谶纬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的萌发、疯长,而这些小说性因素的奇诡怪异、“乖道谬典”[1]31的总体特征也成为了谶纬文体的文体特征。那么,谶纬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通过乖离正道、窜乱经典而实现的“奇”的文体风格、文体特征,是否有利于谶纬文体的翼辅配合儒家经典的政治功利性的文体功能的达成呢?《文心雕龙·正纬》云:“白鱼赤乌之符,黄金(一作银)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1]31《文心雕龙》又运用两则例证,加以分析,给出了新颖、完满、透彻、全面而有说服力的答案。《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6]《尚书中候·洛师谋》:“太子发,以纣有三仁附,即位,不称王,渡于孟津,中流受文命,待天谋,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赤文有字,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7]399《礼斗威仪》:“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黄银见,紫玉见于深山。”[7]517《文心雕龙》指出,这些本意在于翼辅、配合、解说、诠释《书经》《礼经》等儒家经典的谶纬文体中包含着大量的以奇诡怪异为特征的小说性因素,这些小说性因素利用乖谬荒悖的符命、兆应、征验、祥瑞、灾异,来实现动人心魄、惊人耳目的传播效果,这种以“奇”为尚的特征和效果,实质上无益于谶纬文体的诠释解说儒家经典的本意的达成,无助于谶纬文体的翼辅配合儒家经典的原初政治功利性的文体功能的实现,然而,谶纬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所造成的这种以“奇”为尚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传播效果,却在无意之间,给谶纬文体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历史性的重要意义,这就是超脱于政治功利性之外的纯艺术层面的文学性,尚“奇”的小说性因素让谶纬文体具有了内容丰富、生动曲折、奇异瑰伟、娓娓动听的故事情节和富丽、丰赡、润泽的语言辞采,使谶纬文体呈现出“纵横有义,反覆成章”[8]的艺术风貌,谶纬文体中的尚“奇”的小说性因素虽然无裨益于该文体政治功利性功能的达成,但是却赋予了该文体超脱出暂时政治功利意义之上的恒久的文学艺术意义和文化影响,谶纬文体中的尚“奇”的小说性因素以其奇妙的构思和表达方式,为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养料和不绝的艺术灵感,沾溉之泽,至为广远,例如,刘勰所引为例证的谶纬文体中的“白鱼赤乌”“黄金紫玉”之典,便被后世历代诗文、小说所广泛、频繁地征引、化用,保持着恒久的文化生命力,成为了鲜明的文化符号,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文心雕龙》进一步指出,尚“奇”的小说性因素也广泛存在于骚体文学作品之中。《文心雕龙》通过分析骚体文学中的小说性因素,点明骚体文学作品中小说性因素的尚“奇”的艺术风貌在实现手段、表现方式和艺术特色上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诡异”。以诡至异,以异至奇;因诡而异,因异而奇。通过虚假诡戾来造就不同于、迥异于传统旧说的新异之说,以达成“奇”的效果。《文心雕龙·辨骚》云:“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女,诡异之辞也。”[1]4《6离骚》中隐含的小说性因素,驱遣虚假诡戾、颠覆曲折之思,改造、幻化了传统旧有的神话传说定式,赋予旧有神话形象以新的功能,赋予旧有神话内容以新的情节,赋予旧有神话故事以新的意义,打破了旧有神话传说的模式与界限,沟通、融汇了多重神话的意义空间,创造、构建了多元神话的形象世界,以迥异于传统旧说的超凡的标新立异之辞,实现了“奇”的艺术效果。《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9]王逸注:“驾八龙者,言己德如龙,可制御八方;载云旗者,言己德如云雨,能润施万物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王逸注:“丰隆,云师,一曰雷师。宓妃,神女也。”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宓妃,伏羲氏女,为洛水神也。”《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王逸注:“有,国名,谓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配圣帝,生贤子,以喻贞贤也。鸩,一名运日,羽有毒可杀人,以喻谗佞贼害人也。言我使鸩鸟为媒,以求简狄,鸩性谗贼,不可信用,还诈告我,言不好也。”《离骚》中的小说性因素,绝不满足于仅仅原封不动地引用旧有神话传说,而是一反旧有神话传说的固定形态,大胆地改造、糅合、演绎、重构旧有神话传说,给旧有神话传说注入新的血液和精魂。《离骚》中所云的驾驭八龙而载云旗,委托云神丰隆乘彩云去向洛水女神宓妃求婚,凭借鸩鸟去有国向美女简狄说媒,就是上述的通过改造旧说、标新立异来达到“奇”的艺术效果的典型例证。第二方面是“谲怪”。以谲至怪,以怪至奇;因谲而怪,因怪而奇。通过欺诈谲诳的艺术手段来实现怪诞、荒诞的艺术面貌,进而达成“奇”的艺术效果。《文心雕龙·辨骚》云:“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骚体文学中隐含的小说性因素,运用谲诈欺诳的手段,将神话传说中最荒唐不经的成分突显出来,并使其荒唐的程度进一步深化,造成最大程度的荒诞、怪诞的艺术面貌,以实现“奇”的艺术效果。《天问》云:“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王逸注:“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故东南倾。”《天问》云:“羿焉日?乌焉解羽?”王逸注:“《淮南子》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宋玉《招魂》云:“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王逸注:“言有丈夫,一身九头,强梁多力,从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宋玉《招魂》云:“土伯九约,三目虎首,其身若牛些。”王逸注:“土伯,后土之侯伯也。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状如牛也。”骚体文学中的小说性因素,极谲诳欺诈之能事,使用最怪诞、荒诞的形象、情节来惊心骇耳、摄人心魄,撞折天柱、断绝地维、使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共工,射落九个太阳的夷羿,顶着九颗头颅的拔树力士,长着三只眼睛的土地之神,都是这些怪诞、荒诞形象的典型代表,这些荒诞、怪诞的形象,成功地创造了“奇”的艺术效果,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为后世小说创作所广泛征引、化用。
《文心雕龙》中的小说理论因子,有力地论证了各文体中隐含的小说性因素具有着“诡言遁辞,兼包神怪”的尚“奇”艺术追求,众多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通过诡谲怪异的手段来避正用奇、避直用曲,吸纳、囊括了大量的神怪性元素,实现了以“奇”动人的良好的艺术效果。
二、贵“虚”的艺术旨趣
虚构,是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是小说作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小说文体区别于其他纪实性文体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文心雕龙》中的小说理论因子,对众多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的虚构的艺术手段和贵“虚”的艺术旨趣,进行了精彩而深入的论述。
《文心雕龙·正纬》指出,谶纬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极善于运用虚构的艺术手段,具有“虚伪浮假,僻谬诡诞”的艺术特色。斯波六郎《文心雕龙札记》云:“‘浮假’者,无根据之意也。”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云:“浮假,谓其虚而不实也。”斯波六郎《文心雕龙札记》云:“‘僻谬’,意为不合于经典之伪语。”谶纬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以虚构手段,创造了虚妄伪薄、无中生有、浮虚不实、乖僻悖谬、离经叛道、诡诈荒诞的多重艺术模式,达到了以虚至幻、以幻惊人的艺术效果。历代学者对谶纬文体中小说性因素的贵“虚”的艺术旨趣,多有论述。《后汉书·桓谭传》记载了桓谭的观点,他认为,谶纬文体多通过虚构,造作“奇怪虚诞之事”,谶纬文体的作者基于“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的普遍心理规律,而乐于汪洋恣肆地以虚构创制“异闻”,以收惊听之效。《后汉书·张衡传》记载了张衡的观点,他认为,谶纬文体凭借虚构,“附以妖言”,率皆“虚妄而非圣人之法”。张衡也分析了谶纬文体以“虚”为贵的内在心理规律层面的原因,指出谶纬文体之虚构“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荀悦《申鉴·俗嫌》言简意赅地指明了谶纬文体贵“虚”旨趣的四大表象:“虚言,浮术,华名,伪事”,认为虚构手段贯穿于谶纬文体所涉及的言、行、名、实各个层面之中。刘师培《谶纬论》认为,贵“虚”的艺术旨趣,使谶纬文体“说邻荒谬,语类矫诬”,虚构的艺术手段,使谶纬文体“立说诚妄诞不经”。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认为,贵“虚”的艺术旨趣、虚构的艺术手段,使谶纬文体成为了“不可信”的“浮伪之所”。
《文心雕龙·辨骚》借助班固的观点,指明大量的变幻神奇、光怪陆离的虚构的艺术手段成就了骚体文学中的小说性因素。《文心雕龙·辨骚》云:“班固以为……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班固《离骚序》云:“多称昆仑悬圃,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经义所载。”骚体文学中充斥漫衍的类似“昆仑悬圃”的虚无缥缈的完全不合于儒家经传义理的虚构成分,构成了骚体文学中的小说性因素,并使其具有了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离骚》云:“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又云:“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王逸注:“悬圃,神山也,在昆仑之上。”《天问》云:“昆仑悬圃,其尻安在?”朱熹注:“昆仑悬圃,高广之度,诸怪妄说,不可信耳。”骚体文学中小说性因素的贵“虚”旨趣,或由实而生虚,或从无而生有,变幻不拘,手段多样,例如,《离骚》中“昆仑悬圃”之说,即是由昆仑之实象虚构出悬圃之虚象,带给读者充满无限遐想的艺术空间。
《文心雕龙·辨骚》进一步指出,骚体文学实际上是非小说性因素与小说性因素的混合体,是实与虚的混合体。骚体文学中的非小说性因素,即实的成分,是通过“典诰”风格的艺术形式来实现的。骚体文学中的小说性因素,即虚的成分,是通过“夸诞”风格的艺术形式来实现的。非小说性因素与小说性因素,实与虚,在骚体文学中,既统一,又对立,使骚体文学呈现出“典诰则如彼,夸诞则如此”的复杂的艺术面貌。小说性因素是贵“虚”的艺术旨趣、虚构的艺术手段通过“夸诞”的艺术形式来实现的,这是《文心雕龙》的小说理论因子中的重要观点。为了充分论述作为贵“虚”艺术旨趣的重要凭藉和支柱的“夸诞”的艺术形式,《文心雕龙》专设《夸饰》一篇,予以详细阐释。《文心雕龙·夸饰》云“: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相如凭风,诡滥逾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娈彼洛神,既非魍魉,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文心雕龙》在这里广泛引用《诗经·大雅·崧高》《诗经·卫风·河广》《诗经·大雅·假乐》《诗经·大雅·云汉》《尚书·尧典》、伪古文尚书《武成》、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羽猎赋》、张衡《羽猎赋》中的典型例证,论证出小说性因素的贵“虚”的艺术旨趣是依靠“虚用滥形”“诡滥逾甚”的“夸诞”方式实现的,虚构的艺术手段通过夸张、矫饰的“夸诞”途径完成了对小说性因素的构建,贵“虚”的艺术旨趣经由“夸诞”发展出尚“奇”的艺术效果,实现了由“虚”而“奇”的艺术转换。
《文心雕龙·诸子》指出,诸子文体中蕴含着大量的小说性因素,这些小说性因素运用虚构的艺术手段,使自己体现出超越方圆、不合规矩的舛谬驳杂、乖离杂乱的“各以其知舛驰,即为怪迂析辩诡辞”的“驳”特征。《文心雕龙·诸子》又进一步使用具体实例,论证了小说性因素的虚构手段所带给诸子文体的“驳”特征。“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驳之类也。”《文心雕龙》认为,这些广泛存在于诸子文体中的具有显著“驳”特征的小说性因素,实为贵“虚”的艺术旨趣与虚构的艺术手段的完美结晶。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云:“‘汤之问棘’,‘棘’,《列子》作‘革’,‘革’、‘棘’古音同。”《列子·汤问》:“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江浦之间生麽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子羽方昼拭眦,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觯俞、师旷方夜耳,首而听之,弗闻其声。唯黄帝与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斋三月,心死形废,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返。”《列子·汤问》:“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列子·汤问》:“夏革曰:‘渤海之东,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四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淮南子·天文》:“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在《文心雕龙》看来,如此众多地存在于诸子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所带给我们的令人神迷目眩的艺术世界,实在要归功于这些小说性因素的贵“虚”的艺术旨趣和虚构的艺术手段。尽管这种务“虚”的旨趣和手段,在思想意义上被《论衡·对作》斥为“浮妄虚伪,没夺正是”,但是,在纯艺术层面上,诸子文体中小说性因素的贵“虚”艺术旨趣和虚构艺术手段,绝对是高超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完美体现。《文心雕龙》更为深入地指出,诸子文体中小说性因素的贵“虚”艺术旨趣与虚构艺术手段,在总体面貌上,具有着“混同虚诞”的四大特征。范文澜注《文心雕龙》的《诸子》篇原文间双行夹批校语云:“‘混同虚诞’,‘同’一作‘洞’,铃木云:‘诸本作洞。’”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云:“‘混洞虚诞’,四字平列,而各明一义。‘混’谓其杂,‘洞’谓其空,‘虚’谓其不实,‘诞’谓其不经。”《文心雕龙》告诉我们,诸子文体中小说性因素的贵“虚”艺术旨趣与虚构艺术手段,凭借舛谬驳杂、由无生有、虚幻离奇、荒诞恣肆的四大特征,依靠超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极具心灵感染力的宏大艺术空间。
三、“会俗”的艺术价值取向
在《文心雕龙》的小说理论因子之中,有一个组成部分值得特别关注。这就是,对各个文体中小说性因素的区别于庙堂文学典雅之风的通俗风格的格外强调。《文心雕龙》指出,与庙堂文学一味追求雅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在艺术价值取向方面,更为贴近社会大众,更为迎合最广大受众的接受心理,更为主动地满足广大民众的审美需求,更为注重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的语言风格和有趣的艺术细节。各个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从而具有了积极适应广大民众接受品味的“会俗”的艺术价值取向。
《文心雕龙·谐隐》指出,诙谐文学与小说文体,在地位、语言风格、主要受众定位、艺术价值取向方面,是完全相同的,“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而且,在《文心雕龙》所根基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诙谐文学中,有一个组成部分本身就是用小说文体写成的,这就是俳优小说。南朝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云:“曹植初得邯郸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正由于小说文体与诙谐文学具有着如此巨大的共性和浓厚的亲缘关系,所以,小说文体和诙谐文学之间存在着共有的艺术价值取向和一致的文体风格。小说文体,在艺术价值取向和文体风格方面,与诙谐文学保持一致,追求“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小说文体和诙谐文学一样,致力于自身能够被最大多数的受众所理解、接受、喜爱,追求自身语言文辞的浅显浅近、通俗平易,努力迎合世俗的趣味,适合大众的口味,符合民间的品味,通过这些手段,小说文体展现出了与诙谐文学共通的“会俗”的艺术价值取向。
《文心雕龙》进一步广泛关注了各个文体中小说性因素的“会俗”的艺术价值取向,对它们切合受众审美心理、满足民间审美需求的艺术价值取向做出了精当的阐释。谶纬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文辞浅俗”,多“雷同之俗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以浅近平易包裹神秘内核,俘虏民间受众心理,从而在民间信仰中占据一席之地,扩大了自身影响,强化了传播效果,获得了广大受众的迷信和盲从。诸子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采用“缀以街谈”的方式,将最浅白通俗的直接来源于民间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吸纳入自身之中,以最大化地增强自身对民间受众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史传文学中的小说性因素,基于“俗皆爱奇,莫顾实理”的广大受众的普遍猎奇心理,将大量的传奇性、故事性因素和充满巧合、虚幻、神异、怪诞等惊人之语的野记传闻都吸纳入自身之中,以充分迎合广大受众在阅读史传文学时的爱奇、猎奇心理,体现出力求满足民间审美欲求的“会俗”的艺术价值取向。
结语
《文心雕龙》中的小说理论因子,散见于其《正纬》《辨骚》《谐隐》《诸子》《封禅》《夸饰》等各篇之中,虽非系统的专篇专论,但其理论高度、阐释深度、覆盖广度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超凡水平。这种高水平的理论成就,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厚灏瀚的时代文化背景作为其生长土壤的。《文心雕龙》的高水平的小说理论因子所诞生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杰作,它们是《文心雕龙》的小说理论因子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理论成就的坚实的作品基础和深层的文化根源。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志人小说有:三国魏代邯郸淳《笑林》、西晋郭颁《魏晋世语》、东晋裴启《语林》、东晋郭澄之《郭子》、东晋袁宏《名士传》、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东晋孙盛《杂语》、南朝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南朝刘宋虞通之《妒记》、南朝萧梁刘孝标《俗说》、南朝萧梁沈约《俗说》、南朝萧梁殷芸《小说》、南朝萧梁谢绰《宋拾遗》、南朝萧梁裴子野《类林》。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志怪小说有:三国魏文帝曹丕《列异传》、西晋王浮《神异记》、西晋陆蔚(或陆夏)《异林》、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晋郭璞《玄中记》、东晋干宝《搜神记》、东晋葛洪《神仙传》、东晋王嘉《拾遗记》、东晋孔约《志怪》、东晋戴祚《甄异传》、南朝刘宋托名陶潜《搜神后记》、南朝刘宋刘义庆《幽明录》和《宣验记》、南朝刘宋刘敬叔《异苑》、南朝刘宋傅亮《应验记》、南朝刘宋东阳无疑《齐谐记》、南朝萧齐祖冲之《述异记》、南朝萧齐萧子良《冥验记》、南朝萧梁任昉《述异记》、南朝萧梁吴均《续齐谐记》、南朝萧梁王琰《冥祥记》。在如此浩瀚而厚重的作品基础的支撑、托举之上,在如此丰富的文献素材的滋养之中,《文心雕龙》的小说理论因子,吸饱了充足的养分,破土萌芽,拔节抽穗,乘时而起,应运而生,有的放矢,言之有物,零珠碎玑,流光溢彩。
[1]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03.
[3]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126.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15.
[5]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20.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1.
[7]安居香山等辑.纬书集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399.
[9]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36.
【责任编辑杨抱朴】
I206.2
A
1674-5450(2015)02-0108-05
2014-11-03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K505600418)
马骁英,男,辽宁海城人,辽宁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以王嘉《拾遗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