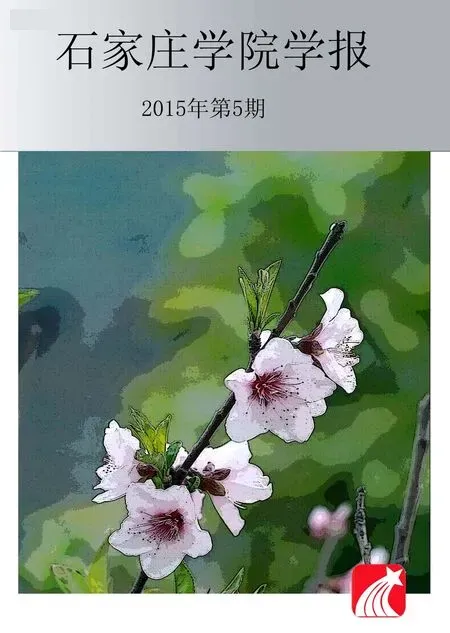唐宋之变:禅宗与9-11世纪的中国画论
——兼论禅宗和古典中国美学的关系
李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唐宋之变:禅宗与9-11世纪的中国画论
——兼论禅宗和古典中国美学的关系
李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古典中国画论在9-11世纪发生了一种奇特的变易:禅宗的观念一定程度上成为作者观念的来源,却表征为与之相异的话语模式,具体表现为道教、经典儒学、北宋理学三种不同的言说途径。通过这些路径,禅宗得到了两方面展开:一是其哲学维度被进一步确证,二是其本身以渗透时代显学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古典中国美学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格调。
唐宋;禅宗;画论;中国美学
在古典中国的语境中,“禅宗”意味着一种来源广泛且具有共享性质的实践活动。它包括观念和行为,其中观念的部分占据我们对“禅”的大部分印象。然而,一个早已被注意的问题是,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禅宗都未曾以无可争辩的官方宗教身份展开自身,却依然不断被各种人所热衷。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作为观念的禅宗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面孔,以便在更广泛的人群中流传。
而要完成这一推测,我们便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禅宗本身与其他学术传统的异质性:如果一种本来带有异域宗教性质的理论模式坚持要介入源流深远的本土思想史,它将依赖什么立足?或者说,它凭借什么进入古典中国的主导话语体系。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作出这样的解释:禅宗的历史不只构成着禅宗发展的空间,它也可以从“禅”本身的性质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在中古之后的中国,它很难说是一种宗教或单纯的救世之道,而是成为对世界阐释的途径,表现为一种哲学。这样,禅宗便不再也不必要从世俗历史的角度切入思想领域,它的主题保持着与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士大夫①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年)对士大夫阶层作出了如下界定:“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始终接受或多或少的标准化了的传统文化教育,以获取(并不必然导向)从事仕宦生涯的资格。因而我们将把‘士大夫’(gentry)和‘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二词基本上作为同义术语来使用,二者唯一的区别是:‘知识分子’包括有教养的僧人,而根据定义专指那些在官僚统治机构供职或被授职的‘士大夫’自然不包括他们在内。”(详见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偏爱的一致性;于是,在中古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纯粹意义上的“禅”不再被大部分人所拥有,人们只拥有在与社会普遍要求基本一致的话语系统中,根据自己意旨,对来源于禅宗的原材料作出不同角度的表达方式。这一点在艺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禅宗色彩笼罩下,批评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假设与带有主流性质的议题交互作用,终于形成看似驳杂却最终整一的意识场域。以艺术批评为主要表征形式之一,古典中国美学在唐之后的发展中,也鲜明地体现着这方面特色:观点借以表达的语言表现着主流意见的差异,而内在的问题和肌理,则相当程度上统一地发端于禅的观念。因此,我们的研究将从画论这一重要的艺术批评形式入手,将视角扩展至唐宋之交的9-11世纪,以便发现禅宗观念究竟如何在不断变革的知识界主导规范中生存,并发挥着它对时代显学的潜在影响。
一、唐宋之交的社会观念与禅宗
面对观念历史时,一种必要的做法是:论及禅宗本身的变易之前,先将社会政治的背景从中剥离出来,之后在讨论中逐渐发现这些因素如何在禅宗的演进中得到了选择性的回避或回应。
就整个社会观念领域而言,9-11世纪的300年所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内藤湖南(1866-1934年)在著名的“唐宋变革说”中阐释了这一点:在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学术文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莫不如此”[1]11-18。内藤本人推荐的是一种从社会阶层入手的方法,这种路径得到后世众多研究者的进一步应用。包弼德(Peter Bol)在《唐宋变迁重探》中,将内藤语境中的阶层凝聚到“士”的单一群体,以之为视角探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变易和扩展。①包弼德认为:“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在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详见包弼德《唐宋变迁重探》,出自《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但“唐宋变革说”及其后继者忽略了某些带有连续性而非变革性的方面。所谓“疑古”“自由表现”及士阶层的创造力迸射,不仅与文人的感悟和修持有关,也是他们事业一直以来不可或缺的部分。当我们看到教导的愿望在士人内在精神中的地位时便会了解,为什么在唐宋变革的几个世纪里,禅宗作为一种观念,被他们运用在不同情境中,产生了基本面貌的变易。
一般的观点认为,禅宗的真正开启者是慧能(638-713年)。②神秀(606-706年)所代表的北宗禅并不具有纯大乘的性质,故慧能所代表的南宗禅被习惯性地看作“禅宗”的代名词。忽滑谷快天认为:“达磨之特色禅门之宗风,从西天渡来沙门多以传翻梵经为业。达磨之东来不译出一偈,此彼与他之异一;毫不尽力讲授,只管以心要为教,此其二;不大小双演,纯弘大乘,此其三;斥有为已功德,独唱真乘,此其四;简明直截,蓦诲安心,此其五。达磨以后此等特色由其门徒益益加以发挥,遂至形成所称禅门特殊之宗风。欲知达摩之宗风,先要注意此等五种之特色。”(详见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宗思想史》,朱谦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这并不代表在慧能之先,禅宗无所源头;相反,如同慧能自己所承认的,《金刚经》对中国禅的观念特别是对南宗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从主题来看,《金刚经》的表达十分明确:“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2]74世间一切事物都虚幻不实、无有自性,即“空”。平时人们所看到的一切形相,都不是真切形相,事物的“实相”乃是“无相”;由于这一点,对于现实世界真实样态的探究以及对已有的权威标准的迷恋,都将毫无意义。这些前提所指向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要求人的“破执”:即使从事布施,也不能住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而行,有住即是住相,是取诸自性的执见,这种执见对诸法会产生虚妄分别,为境所转而不能自在解脱。若不住相,就不为六尘所动,心才能达到清净状态。可以看到,《金刚经》所指出的是新的超验式的本体论说方式,而这种论说以否定本体的存在为前提;它阐释“空”的义理,认为万法不常,而这和传统中国思维中对参与社会政治秩序的热衷相悖:如果秩序的存在本身便是虚空,则对它的执着也便成为荒谬之举。在这一方向上,《金刚经》为之后的禅宗观念提供了“不执”的方法要求,将“破执”作为开示的主题。
禅宗前史中的另一部经典《维摩诘经》则提供了内求的方法。“唯心净土”是其主要的教义。《维摩诘经》明确提出“心净则佛土净”,将此发大乘心后之当下一念心作为本净真心的开显,同时将“心”与净土思想相连属,讲十方世界有无量净土,将最终理想之境转而作为动力之发端,强调不依赖于形而上假定的自主创造,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严净;同时,不仅要求个人的、可以被体察和辨识的觉悟,还要凭借大悲心使众生都得解脱,“着眼于众生的共同分业力,致力于众生所居世界(依报)的改造”[3]151。如此,本经便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为不思议解脱的张本,确立了心净则行净,行净则众生净,众生净则佛土净的逻辑进路。如此,则“不执”驱逐了令人烦恼的俗世纷争,“内求”在“不执”的要求下,进一步指出明确的行动方向。它们共同构成了开示中的自我肯定主题,并以此弥补了之前的理性历史所带来的自我的缺席感、空虚感,以及由此而来的信心危机,故而会被知识分子所普遍喜爱;另一方面,它带有“宗”的性质,包含着现实的行为充满生机的律动,提供着“开示”本身所需的对真实环境的适应性,这种弹性方便了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并在具体的情境中以不同的程度与王朝理想建立关联。而此灵活性,在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处,既不可能见到,也不可能被期盼。因此,在接下来的具体分析中,我们便会看到,禅的观念究竟如何随着古典知识分子的处境变易,而以不同的哲学形式表现;此外,它也同样提供着哲学本身的问题,影响着问题的“开示”中所呈现的基调。
二、《记画》:南宗禅的道教面孔
唐代的文人中,有两位被认为相当深刻地介入了禅宗的发展史:王维(701-761年)和白居易(772-846年)。①汤用彤先生在谈到社会风气对白居易佛教信仰的影响时说:“(唐代)文人学士如王维、白居易、梁肃等真正奉佛且深切体佛者,为数盖少。此诸君子之信佛,原因殊多,其要盖不外与当时之社会风气亦有关系也。”(详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页。)前者生活在公元8世纪的前中期,彼时他的朝代处于稳定的上升阶段,而未见出显明的、走向另一种时代风格的端倪,禅观念也相对稳定地向着北宗禅和南宗禅共同的方向发展;后者则主要活动于9世纪前期的中唐社会,旧秩序已经受到了存亡威胁,王朝开始显出衰落,一度受到推崇的北宗所求“方便”难以为更多人所信服,“禅”的观念也逐渐偏于南宗。孙昌武、肖伟韬等学者对白居易的研究也向我们证实,这位主要以诗歌著称的作者已经在思想上开始偏向南宗禅。②见孙昌武《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182页;肖伟韬《白居易从法凝所学为南宗禅考论》,载《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93-197页。而站在另一方面的“北宗禅”观点,代表性学者有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82页)、陈引驰(《隋唐佛教与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3-94页)、张弘(《白居易与佛禅》,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等。但从时代特征和白居易本人经历来看,显然其观点更偏向南宗禅。所以,在白居易的禅思世界中,首先应当注意到的是北宗之外强烈的南禅色彩。
观,以心中眼,观心外相,从何而有?从何而丧?观之又观则辨真妄。
觉,惟真常在,为妄所蒙,真妄苟辨,觉生其中。不离妄有而得真空。
定,真若不灭,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为禅定乃脱生死
慧,专之以定,定犹有系。济之以慧,慧则无滞。如珠在盘盘定珠慧。[4]885
尽管题为“渐”以至被许多学者认为属于提倡渐悟的北宗,但整篇偈文的观念体系依赖于南宗。一般认为,白居易所受影响有《金刚经》的成分,《金刚经》则是南宗禅发源的根基。在《钱虢州以三堂绝句见寄因以本韵和之》中,白居易承认自己对这一经典深为钟爱:“同事空王岁月深,相思远寄定中吟。遥知清净中和化,只用金刚三昧经。”[4]392又自注:“予早岁与钱君同习读《金刚三昧经》。”[4]392而其他诗歌中更显著地表明南宗禅在白居易思想中的地位:“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4]125“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檀经说佛心。”③“檀经”即南宗禅经典《六祖坛经》。选自白居易《味道》。全诗如下:“叩齿晨兴秋院静,焚香冥坐晚窗深。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檀经说佛心。此日尽知前境妄,多生曾被外尘侵。自嫌习性犹残处,爱咏闲诗好听琴。”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在成文于9世纪初的《八渐偈》中,南宗禅的思想已经被作者自觉地运用,并推崇为某种评价人生态度的标准。借此考察成文于同一时期的《记画》,就很容易发现与《八渐偈》中相通的成分: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之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和役灵于其间焉。时予在长安中居甚闲,闻甚熟,乃请观于张,张为予尽出之……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余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4]937
在这篇相对简短的文字中,白居易对南宗禅的热衷至少在两个主题上得到了表现。其一是绘画作品所由而出的源头。“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心”成为作品的发端,是它借以形象化地呈现于外的基础;它被创作者所拥有,“不知自然而然”地提供着作品的“英华”与“律度”,使作者的技艺以无法觉察、无法言说的方式流露,却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这种“心”,与其说是北宗的“看心、看净”的“心”,不如说是南宗“直入净心”的“净心”,它被作者所体验和运用的方式,与南宗“以心传心,当令自悟”的悟入方式深相契合:作者本身具有根据主体意志重新构建世界样态的力量,只不过他并非现实地作用于世界,而是将新的世界以绘画的方式呈现于外。这样,在白居易发现,自己不得不对作品说些什么的时候,他转向了另一个主题:评画的标准。此处,他仍然谨慎地运用了与开篇相似的语言:“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不常”意示着并不存在固定的评价标准,“但觉”则证明了作者对接下来所要进行的评价充满了不自信与犹疑。深受南宗禅影响的作者深刻地明白“不执”的妙处所在,而一切断言性的议论都将是一种“执”;所以,他最后表示出谦逊的让步,以便将“无常”的观念延续下去,而将“常”与“执”的非法运用拱手让给可能会到来的、不理智的观画者。至此,南禅的观念被我们贯彻于《记画》的文本中,作为一种与其作者经历相契的解释路径。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发现在文本中,尽管时常流露出佛禅的意味,却似乎又在回避它;作者在书写中不仅并未使用南禅惯用的语言,甚至用另一种与之大为不同的话语系统来“遮蔽”佛禅思想。“天”“神”“灵”“全”等来自于道教的说法贯穿整个文本,且不断重复,加深着读者的印象;那么,它们究竟缘何出现?作者本人是著名的佛禅爱好者,为何要隐蔽形象,而表示对另一种观念体系的热衷?
当我们回溯之前的讨论便会发现,在白居易的时代,道教与佛教的纠葛,较之佛禅内部的观念迁流显得重要得多。事实上,武则天的时代之后,佛禅在官方的视野中,再未获得过更加荣耀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道教地位的上升。玄宗即位后,很快将武则天列佛于道前的顺序颠倒过来,支持道教进行两大革新①巴雷特(Timothy Hugh Barrett)在《唐朝道教研究——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中指出,在玄宗朝,“首先,是对皇室祖先老子的制度性祭祀,以此来强调皇室家族的神圣起源及其将被神灵永远护佑。其次,就是将教育和科考制度建立在道教而非儒家经典之上,这大概是想选拔出来的官吏能与唐皇志趣相投,不会因为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而不时地与君王针锋相对。起于开元晚期,在天宝年间一直持续的这两大革新被不断修改,并认为它们同等重要”。“此后唯一重要的变化主要与玄宗对其圣祖日益增加的热情有关,而较少关系到制度改革的深化。天宝十三载,‘道举’停习《道德经》,而加《周易》,这表明了对《道德经》的尊崇有增无减……因此,在天宝四载下诏将《道德经》列为诸经之首,在众书目中有着最为尊崇的地位,远远高于别的学派的普通经典。”(引自《盛唐时期的道教与政治》,曾维嘉译,《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26-32页。)最重要的一点是,玄宗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建议并没有因安史之乱而简单地消失,保持着强有力的惯性,影响着之后的社会观念和知识界主流。,使之成为盛唐审美主流,并且保持它旺盛的生命力,贯穿了整个中唐乃至晚唐。由此可以发现,在白居易成文于中唐的作品中,禅观念的“移置”是一件并不奇怪的事:“开示”的愿望,要求文人选择最便于教导他人的言说方式,以使自己的观念在扩展、延续之中获得长足的生命力。由是,南宗禅被包藏于道教的面孔下,凭借主流信仰的传播,使自己渗透入另一种学说的发展史。
三、《笔法记》:“摹仿”儒家
到了五代,古典山水画开始进入它的全盛时代,画论也随之转移话题。在荆浩(活动于五代后唐)的作品和理论中,关于山水的叙述获得了它独立的意义,成为具有自己内在逻辑的绘画主题;并且,由于支撑这种叙述的特定的历史观念,在更具有思辨性质的表达方式中变得鲜明,被这些观念所规约的、理论家的个人意趣,就更加要求通过与历史建立良好的沟通,而使自己得到更充分的表现。因此,在荆浩的代表作《笔法记》中,我们看到一个与白居易不同,然而同样充满了禅趣的作者: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禅性的偏爱和来自儒家正统的教育,形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层次;然而,它却未涉及到何者为附属的、后起的,而是以一种更加奇特的方式呈现,也就是禅对儒的“摹仿”。
北宋刘道醇(活动于1057年前后)《五代名画补遗》中记载了荆浩的主要经历:
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业儒,博通经史,善属文。偶五季多故,遂退藏不仕,乃隐于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尝画山水树石以自适。时邺都青莲寺沙门大愚尝乞画于浩,寄诗以达其意曰:“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笔踪。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树下留盘石,天边纵远峰。近岩幽湿处,惟藉墨烟浓。”后浩亦画《山水图》以贻大愚。仍以诗答之曰:“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到水平。禅房时一展,兼称苦空情。”[5]342
在这段记述中,荆浩被描述为一个尝以儒学为业、却终于在五代动乱中走向“退藏不仕”的隐者。隐居期间,长期被压抑的“自适”愿望得到了满足:他热衷于与佛门的来往,将山水作为闲情之偶寄,他的诗具有一种白描的空澹情调。没有关于作者生活的想象,就没有他的观念,也没有被这些观念所阐发的深层意味;因而,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便是将这些已被内化的生活,从他某些去除了感情色彩的观念表达中重新召出,并发现它究竟如何被一种与之异质的社会要求所容纳,以及如何通过并不属于它自身的话语来得到尽量确切的表达。
明年春,来于石鼓岩间,遇一叟,因问,具以其来所由而答之。叟曰:“子知笔法乎?”曰:“叟,仪形野人也,岂知笔法耶?”叟曰:“子岂知吾所怀耶?”闻而惭骇。叟曰:“少年好学,终可成也。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曰:“画者华也,但贵似得真,岂此挠矣。”叟曰:“不然。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6]256
《笔法记》以故事的方式搭建起论说的框架。徐复观(1903-1982年)认为,故事的结构“可能受《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受书于黄石老人故事的影响”[7]176,史迁的儒者笔墨显而易见;因而,他的风格被同受儒学教育的荆浩所引用,也成为可以理解的选择。荆浩的论述紧紧围绕着三个观念进行:“华”“实”“真”。前两者的对峙,很容易令读者想起儒家传统中几乎是核心性的问题:“文”与“质”。“文”是事物锲入现实的渠道,是事物的内在与真实的世界相接触时自然而然的反应方式,它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魅力所在;“质”则是事物得以获得其存在的源头,是其内在的精神,它将事物从对于外饰的“文”的虚幻迷恋中拯救出来,帮助它回到自身原初的规定。这两方面的对峙与互通,对于认识活动而言,是一项重要的启示:事物存在于世间,并不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供他者观看或利用的“模型”,它的存在除了使自己成为某些特性类别的标示甚或榜样的同时,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自己生命力和本质属性的具体存在物的这一事实,也是有意义的。正如我们永远不可能圆满地理解他人一样,如果仅仅把认知停留于事物对人所表现出的表层的“美”,我们便永远不能掌握关于它的“美”最深刻的问题,即它的存在之所由。所以,当荆浩把“华”与“实”的并立作为对画的要求时,他实际上承认着古老的儒家观念——“文”与“质”的统一。“华”与“实”的关系,在与文质进行类比的意义上能够得到同样相对性的阐发。①徐复观简要地阐述了这种相对存在的意义:“首先他(荆浩)提出华与实的观念。华即是美,艺术得以成立的第一条件,便是华;所以荆浩并不否定华。但华有使华得以成立的‘实’,此即是物的神,物的情性。此情性形成物的生命感,即是表现而为物的气。气即生气,生命感。荆浩在此处要求由物之华而进入于物之实,以得到华与实的统一。”(详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但“华”与“实”的相对存在,并不是静止于彼此间已被固定下来的关系,它们仍要将这种关系向前推展,发展出新的、能动的第三者,也就是“真”。“真”在艺术史上,曾经是普遍性的要求;它提供了一种评价艺术好坏的标准,却并不满足于这一职责,而希望得到来自更广泛程度的认可,成为判断事物存在合理与否的依据。在荆浩看来,“真”乃是“气”贯通于“象”的结果,是“活态”的别种说法:它提供着使人扩展到超离个体的普遍自然的可能性。
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曰,何以为似?何以为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谢曰:故知书画者名贤之所学也。耕生知其非本,玩笔取与,终无可成。[6]257
“真”生成于关系的扩展:“华”与“实”不再占据论说中的主要位置,而代之以“气”和“象”的运动。“象”被徐复观解释为“无气之形”[7]176,被认为是空虚的、有待被填充的事物形式,“气”则恰好弥补了它的缺失,以“遗”这种充盈并驻留的方式,使自己与“象”合成为一个圆满的整体,而共同具有了“真”的特性。在荆浩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鲜明的方向:“真”在开始便被以提问的方式确定为讨论的题目,并且,讨论中对不同对象间各种关系不厌其烦的叙述被这个题目赋予了整一性,为同一个原始命题服务。于是,可以发现,无论是“华”与“实”,还是“气”与“象”,它们不过是处于未萌状态的“真”的形成要素,“真”作为未来的可能性包藏于它们之中,盼望着在作者的步步引领中,让它的确实性得以在读者心中逐步证实。
但这种话题转向,对一些读者特别是深受儒学教导的读者而言,并不是完全自然的。尽管在文本的逻辑中,“华”“实”“气”“象”等概念有着一以贯之的顺承关系,却越来越具有越出礼教讨论之外的趋势;终于,落脚点被规定为“真”,而“真”无论对五代之前的儒学者,还是对饱阅“经史”的荆浩本人,都绝非一个寻常的儒家色彩的主题。事实上,在古典中国的言说中,首先使用“真”的是道家,而中唐以后,则是佛教各宗(特别是禅宗)以此为贯通事理的线索性话题。“真如”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观念,被禅宗(包括广义的佛教)认为是所要认识的最高义谛,即事物、世界、人心最本来的样态:
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坏。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2]89
在《坛经》中,“真如”被认为起自“自性”,来源于个体本身,同时又反过来规定着个体的属性,使之以“真”作为存在之合理性的依据:一旦“真如”消失,眼、耳、色、声便丧失了本应有的节制,成为了“坏”。这样,“真如”一方面成为人之应然具有的本质,另一方面,也在随念拓展中获得了更广大的意义,成为事物本质的代言。在这一方向上,“真如”与“诸法无常”构成了禅宗观念的两极:外在事相总是缺乏统一的稳定性,缺少成为合法性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于某些外在的辅助(“因缘”)才能够为人所捕捉,成为意识的和意志的对象,它所予人的感性印象是无法排解的虚无;“真如”弥合了这一点,它承认生命总具有自身的根源,而这根源又是异处相通的,并不是一片纷乱。世界由此有了不朽的确定性,它缓解了“诸法”变幻所带给人的无力感,贯穿起人自身的过去和未来,也塑造着无瑕的自然,将理想的面目还予它。荆浩对“真”的强调,显然源发于此心。山水画以求真为本,并不在于外在观察的真实程度,而在于画家本人用心体度,悟到物象的本原,从而使主观意兴与大化妙用联合成为一体,将作者自我生命、作品生命和表现对象的生命,以同一的渠道表现出来。这样,我们便发现,“真”借以表达的形式终于让步于它的实际内容,之前充满了儒家色彩的关于华与实的讨论,终究被落实于背后难以遮蔽的来自禅宗的“真”。禅的观念尽力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儒家规范性要求周围的空白;它对这一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从而形成理学的先声。
四、《图画见闻志》:“心印”与理学
如果注意到内藤湖南在提及唐宋变革时所不自觉流露的兴奋态度,便会发现这一变革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文人获得了自我表达的更大自由,而这一点在许多具有西学背景的哲学研究者看来,关乎自我的开显。在先秦至唐的儒学思想中,并不容易找到将自我作为战胜一切的力量的表达;而在佛教,特别是唐及五代的禅宗观念中,它却被不加限制地发展了,并在北宋王朝建立后不久,得到来自政权内部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和利用。①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北宋理学奠基者们对禅宗的态度并不友善。他们之所以征引、发挥某些禅宗理念(特别是其广阔的宇宙观念和一系列行为指导),更多地为了反过来与佛禅相抗衡。张载(1020-1078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曾有出人佛老的经历,但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读,他最终认识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终于归宗儒学。基于对佛学的了解,他对于佛教流传对儒学的危害有极深的体认。他指出,“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最终形成了“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驱”的局面,已到了危及儒学生存的地步。要改变这种状况,非“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正蒙·太和篇》)汲取佛禅中的有利因素,而反用以对抗佛老、传承圣学。这样,禅宗再次显示出它独特的渗透性:它被援引入新生的理学话语中,在新的知识框架内获得了另一种存在方式。
一般而言,北宋理学对于“自我”的看法,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人性。尽管论说的出发点各有不同,北宋理学家仍普遍地承认个体自我在生理性之外具有某种“善”,并且“善”的程度并非命定,能够通过人的行为来改变。这成为自我得以提升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境界。它关乎自我精神的有效扩展,并以“圣人”的必然目的来规划这种扩展的程度。在这里,“圣”的成就主要来自“心”的提升。受“心”的观念的启发,主要活动于北宋神宗熙宁时的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阐发了新的概念“心印”,用来代表“人心”与“想成形迹”的契合。②在郭若虚的时代,周敦颐(1017-1073年)、邵雍(1021-1077年)、张载(1020-1077年)、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关于理学的建构都有论述,这些人有的还出任皇帝的侍讲,如程颐。郭若虚尚仁宗弟东平郡王赵元弼之女,为严格意义上的“外戚”,因当对以上学者至少有所耳闻,并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故杨氏不能授其师,轮扁不能传其子,系乎得自天机,出于灵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矧乎书画发之于情思,契之于绡楮,则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诸贵贱祸福,书画岂逃乎气韵高卑。夫画,犹书也。杨子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6]304
“心”在郭若虚的议论中,被认为是非情境性的、人的定义性特质:它标示着人之品性、情思的源头,是未分割的整体,也是在表现于外时,他者所能领略到的唯一的“自我”。尽管它自身并不包含某种结构,却天然地与外部相关联,能够将想成之形迹复又纳入自身,加以印证和体味;同时,“心”也是能动的,可以自发地流出或高或卑的“气韵”,这“气韵”便是绘画作品背后的作者自我性最直接的体现。可以看到,郭若虚的“心”无论就其源头性还是能动性而言,都具有理学的色彩,因而理应归于这一学术背景之下;然而,当我们回溯早期儒学时,“心”较之其他概念,显得并非那么突出,甚至在相距宋代不远的唐代,韩愈(768-824年)和李翱(772-841年)的道统论,依然延续着“性”“欲”一类的表达模式,“心”的意义尚未得到有力的铺陈,它的力量也没有被全面地反思和诠释。那么,这一概念究竟主要取自哪里,就变成了关乎理学源泉的重要问题。
当我们将目光回溯至佛学,会发现传统儒家所未能深入探索的问题在禅宗处得到了提示。“心”在禅宗观念中,是一个相当常见的主题:禅宗前史的经典《金刚经》将“自性清净心”作为成佛在心性方面的要求;中土禅宗第三祖僧璨在《信心铭》中,几近通篇讲“心”,从“心若不异”出发讲“万法一如”,以为不随言教、无证无碍的自然修行观念作论证;《坛经》则更直接地提出自性清净、直了顿悟的心性论,将人的本真自我与“万法”所源之本体同一化。在《坛经》中,“自心”成为六祖慧能论说的开端。相对于西方习惯翻译为“mind”并指称“会分类的思维、判断和感情的活动”[8]175的“心”,它更重要的特征在于“自”,即完全的自我性。它仅仅属于拥有者——“众生”本人,带有拥有者自己独特的个性,无法被他者所取代,因而它也是拥有者确证自我存在、完成自我本性的唯一有效渠道。同时,它也总是与人的特殊的、不断展开的情境相联系,并不存于个人之外,故不能归结为抽象的实体。这样,自我性和具体性便共同构成了“心”得以被“我”识得的基础,使“还得本心”成为人在日常行为中能够努力而成的目标。
由于“自我”已经被认为是“心”最重要的规定性,“识心”也即“识我”,即回到自我的本来状态。慧能将本然之心看作“清净”“虚空”之心:“清净”即是无垢,意指未被烦恼污染的心;“虚空”则具有更广泛的指向,表征着“心”的至为广大:
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记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2]151-152
自心能够含容万法,也即是说,万法不离自心,都依托、建基于自我本心,而与心所具有的本体性力量来看,“万法”便显示出它的弱质性,故而说“万法皆空”。《坛经》非常明确地反对心外本体的存在,将本体绝对置于内心,通过对心加以独特规定来实现本体的超越化:
这也正是“顿悟成佛”在心性论方面的根据。它深刻地影响了理学,构成了功夫论的重要内容。因此,在郭若虚的论述中,“心”的主题自然地与“顿”的悟性说相互关联:
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6]307
“默契神会”是一个瞬间的过程,这一过程对参与它的双方而言,都是畅通无阻的;没有障碍将它们隔开,两者自然具有相通的潜能,并在刹那间际会、拥抱,成为深层次意义上的一个整体。在这里,两方面都消失于最终的“契”和“会”中,形成新的统一形式,并成就着作品的气象与境界。
[1][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M]//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
[2]陈秋平.金刚经·心经·坛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王新水.《维摩诘经》思想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6.
[4]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山水门第二[M/CD].文渊阁四库全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6]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世襄未完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周亚红)
Zen Buddhism and Chinese Classical Painterly Criticism from the Ninth to Eleventh Century
LI X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 particular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in classical Chinese painterly criticism from the ninth to eleventh century.Zen Buddhism,as an origin of critics opinions,performed as another dialogue formula which was distinct from Zen itself.This can be revealed by three dialogue systems:Taoism,classical Confucianism and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Through those approaches,Zen Buddhism expanded itself in two ways:its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was restated,and it influenced fundamental ques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Chinese aesthetics,permeating into those ideological mainstreams of certain periods.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Zen Buddhism;Chinese classical painterly criticism;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B83-06;B946.5
:A
:1673-1972(2015)05-0104-07
2015-07-08
李想(1990-),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