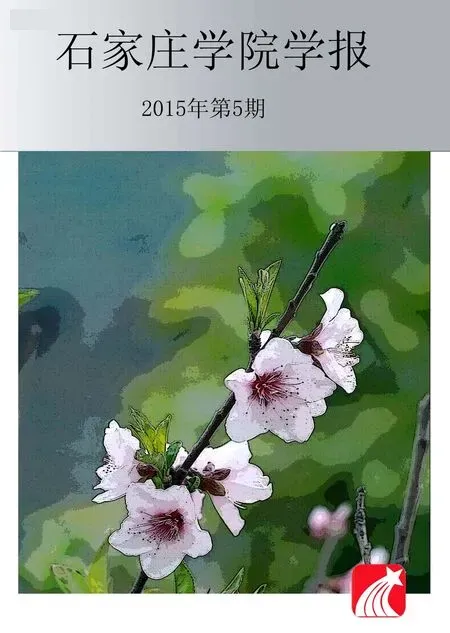摘下额头的青枝绿叶
——论灰娃的诗
张立群,郝瑞琳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摘下额头的青枝绿叶
——论灰娃的诗
张立群,郝瑞琳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灰娃的诗歌创作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以诗歌疗救自己的精神疾病,进而呈现出一个独特的诗歌世界。她的诗在确证主体的过程中,在主题、语词、叙述和形式上都有独到之处。解读灰娃的诗可以使人们重新认识诗人、写作等命题。
灰娃;自我疗救;主体;诗歌史
灰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作,到90年代末期出版诗集《山鬼故家》,其诗歌创作逐渐为诗坛所熟知。这不仅是一个写作过程,还是一个文学史现象。虽然其作品不多,但读后却能给人以独特的感受甚至惊异。灰娃带给我们的是何为诗人、何为写作等近乎本质化的课题,需要我们以特殊的方式予以回应和解读。
一、自我疗救史
按照文学史已有的概括方式,灰娃最初写作的阶段可以称之为“地下写作”。但结合灰娃的生活道路,并反复阅读灰娃的诗,却发现这种概括与实际有很大的“出入”:除了灰娃本人认为自己的创作与“地下文学”“不可能有关连”[1]248之外,她具体的写作方式也决定了与“地下文学”的不同。灰娃,原名理召,1927年生于陕西临潼。1939年到延安,就学于“儿童艺术学园”。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工作。文革之前,罹患精神分裂症,这一病症在文革开始后的六年内加重。1972年,处于恐惧、不解、愤恨、绝望、悲凉等处境的灰娃开始以“不由自主顺手随便在什么纸上,一句、两句、半句、一段、一个词、一个字”[1]240的方式写诗,逐渐对自己的疾病形成特殊的“疗救”。写于文革期间的诗,是灰娃写作的起点,也是灰娃诗歌最具价值的部分。它不仅确立了后来灰娃写作的基本方向,也使灰娃成为当代诗歌史上一位十分独特的女诗人。
将灵魂的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疾病转化为艺术创作的现象,在中外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并不少见。这一点,就深层心理学的观点也能说得通:将“焦虑”转化为艺术生产的过程进而形成艺术品,符合“焦虑的转移”和“超越快乐原则”;缓释“焦虑”后,艺术创造者的心灵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平静,并由此生成个性独特的艺术家直至天才。灰娃的“自我疗救史”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上述的“普遍逻辑”,但更为值得关注的却是其通过写作见证时代的“特殊性”。灰娃12岁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既有延安及战争年代革命者不平凡的经历,又有特定年代成长者与亲历者坦诚、无私、单纯、理想的情怀。她后来在回忆中谈到自己从延安移居到北京的不适感、苦恼都与此有关。之后,在历次思想文化运动中,她总是受到批判,恐惧、害怕使其患上精神分裂症。[2]123-144她是在情绪极度痛苦、倍受煎熬的背景下开始写作的,她的精神分裂也是在写作中获得了治愈——
我是无意中走到诗的森林、诗的园子里来的,事先并没有做一名诗人的愿望。是诗神先从我心里显现,心中起了节奏和旋律,于是不知不觉地和着那音乐律动……
我体会,诗是主动的,我乃被动者。是诗从心中催促我把它表述出来,写出的文字是我心灵的载体。这感受是幸福的、奇妙的、迷人的,是我在这人世间的最高的享受……
人生和世事馈赠我以诗。它让我的心摆脱了现实对我的折磨,超越于平庸繁琐的日常。[2]190通过诗歌,灰娃找到了心灵的安静之所、实现了自我疗救。灰娃的“疗救史”再现了诗歌的魅力,诗歌在治疗心灵创伤的同时,解除了时代现实和政治文化强加给个体的精神枷锁。在作品获得“自在自为的独立性”乃至“文革诗歌史”[3]价值的同时,灰娃本人也因此成为以诗歌获得生命救赎的诗人典型。
二、主体的确证
“自我疗救”阶段的灰娃在写作上首先呈现出一个处于围困状态中的“自我”。“她”以怀疑、恐惧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不时显露出一位歧路彷徨者的不安、惶惑但又不失清醒、自思、决绝的心灵状态:“我再不担心与你们/遭遇陷身那/无法捉摸也猜不透的战阵/我算是解脱了//再不能折磨我/令你们得到些许快乐/我虽然带着往日的创痛/可现在你们还怎么启动。”(《我额头青枝绿叶……》)①文中所引的灰娃的诗均出自《灰娃的诗》,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不再一一标注。身处精神分裂状态下的诗人自然感到周边危机四伏,而造成这一意识的根源却是现实语境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完全屈从是无法写出真正的诗歌的。只有在觉醒中抗争,才能在自我启蒙中挣脱心灵的围困、实现灵魂的救赎,灰娃的诗因此与现实语境之间形成了紧张、对峙的状态。
“哦觉醒的灵魂/我们满头乌丝/月亮银光吻过/太阳也洒过金辉/今夜它已被秋霜冬雪染尽/我们还是不厌弃泥土岩石/而渴求浮名黄金//从未奔赴盛宴/只以酩酊沉醉奉献/用热烈坚定的脚步踏碎/日久年深的忧愁/在牺牲的血泊中痛彻震颤/心/却欣然”(《路》)。对于灰娃回应外界的压力和心灵的焦虑时依靠的精神资源,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上援引的诗篇中看到:记忆、经历还有身上业已凝结成的顽强品格。可以说,在从精神围困走向自我超越的途中,灰娃能够凭借的只有这些。在这些诗行中,有当年曾经亲历过的出征前的“誓师大会”时振臂高呼时“必胜的信念”,有“战歌飞扬”,有“赤子的心与泪”(《路》)……像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灰娃的诗再现了岁月在其身上磨砺出的“坚硬的部分”。她以回想往昔质朴、火热的场景来摆脱梦魇的困扰,以灵魂重燃的方式“医治大地/累累伤痕”——
当他们回想如火如荼的往昔
是怎样
评说我们?
——《路》
是其确证自己的有效方式之一。
为了抵达“主体确证”的“彼岸”,灰娃显然要经历那种“穿过废墟穿过深渊”的过程。她不止一次在诗中诉说死亡的体验,及至留下长长的“墓铭”:“我眼睛已永远紧锁再也不为人世流露/深邃如梦浓荫婆娑”(《墓铭》)。然而,炼狱般的体验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强大且全新的“自我”,预示着一次凤凰浴火、涅槃重生。“我们可否再次点起/金色烛火/众琴铿锵”;“生命弦正要调好/去航越/瀚海冰峰”(《穿过废墟穿过深渊》)。穿过废墟、穿过深渊之后,灰娃看到了新的景象——
终于我望见远处一抹光
拂去玩额上的冰凌
我被这音乐光亮救起
彻底剥夺了你们的快意
——《我额头青枝绿叶……》
如果联系灰娃自言在诗歌创作时,是因为在“某个时候,心里有种旋律、节奏显现,不知不觉日益频繁在心里盘桓,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事,这音乐总挥之不去,音乐执意占据心灵,控制心灵。隐约中有异样感觉,这时,受此音乐催促,以文字释出,呈示为人们称之为诗的这种形式”[1]249,那么,将此处的“音乐”理解为诗歌似乎并不过分。以诗歌的光亮拯救自己,反衬出诗歌在灰娃“主体确证”中的重大意义。尽管结合灰娃的人生轨迹与创作轨迹可知:此刻的“主体的确证”在灰娃那里不是结果,只是一个过程。灰娃通过追忆走向未来,她所要摆脱的只是这一刻的“梦魇”。不过,即便如此,灰娃也塑造出了自己,她的诗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三、“死亡”与“土地”
“死亡”是灰娃“自我疗救”阶段的重要主题。她曾多次花费大量笔墨书写“死亡”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比如“墓园”“废墟”“亡灵”等:“当我们告别人间依稀长叹/可还有什么值得顾盼/为何总不肯闭合双眼/它是那样纯洁无辜永无希求/当我们长眠在荒墟墓园/坟头松枝荫蔽一丛素静百合/抚慰寂寞含冤的心愿”(《路》);“从峭壁迸溅散发野草泥土气息/带着魔法力量,我发誓//走入黄泉定以热血祭奠如火的亡魂/来生我只跟鬼怪结缘//……我已走完最后一程/美丽的九重天在头上闪耀”(《墓铭》)。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死亡”作为特殊的表意材料隐含着作者对非理性的关注。“死亡”反复出现且面相不尽相同,使作品充满了神秘的气息、灰暗的格调。“死亡”主题呈现着创作主体的生命预约,一方面易于使作品弥漫绝望、颓废的味道,但另一方面则潜藏着冲破生命低谷、向死而生的契机。就灰娃而言,她笔下的“死亡”显然属于后者。“‘废墟’‘死亡’既是存在的困惑,悲苦与煎熬的现世现实,也是因之而思绪飘忽幻灵幻美的去所。对现世现实恐惧、绝望而心有不服,意犹不甘,无奈之中思维任意飘往现实以外的幻觉所在。不由得人也飘回艰难的、如火如荼的岁月,以及种种又辛酸又温馨、浸透深情深意的往时往日。”[1]255带着对现世现实的质疑与困惑,灰娃笔下的“死亡”具有如下特征:在追忆温馨往昔时拒绝了令人痛苦的事实,因而使这类诗篇常常存有冲突对立的结构;“死亡”与生命的原初状态和来世的呼唤紧密相连,具有辩证的彻悟和理想关怀。
如果生命之旅可以被比喻成“一段路”,那么,在《路》中的“地上,为梦想缠绕又被抛却/地下,我们的喟叹透过泥土”,也大致能够建立“死亡”与“土地”的联系。“死亡”使生命归于大地,这使得灰娃后来的许多作品,如《乡村墓地》《土地下面长眠着》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到内在的演进逻辑。但是,如果着眼于“土地”意象本身,灰娃的诗作显然还包含着更为广阔的“主题”。组诗《野土九章》再现故乡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民俗节庆,通篇以“人人都说自己故土好/可我的故乡真真叫人心放不下”为线索。从“大地的恩情”到“大地的母亲”,再到“天下黄河”,灰娃从故土的具体细节出发,渐次地将土地扩展至“祖国”“东方”及至“整个世界”。她笔下的“土地”有着浑厚的历史感,同时也有着深广的忧患意识。“大地啊,山河/哪个年代我们祖先凿了第一口水井/什么岁月我们祖先搭起第一所房屋/我们打过多少仗织了多少布/经过多少回的天灾祸患/我们祖祖辈辈为你洒下多少血和汗/我们编了多少动人心弦的故事和诗篇/我们在黑夜里透视出你哭泣的面容/我们魂梦萦绕你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形影……”在灰娃带有寻根意识的叙述中,我们能够读到她对大地、故园的无限深情。她纯洁、质朴的表达方式使其总能“讲述你富饶而苦旱的原委遭遇/春去秋来夜夜在你头上守望你”式的故事(《故土》),总能自觉不自觉地提到母亲形象以及大自然美丽的风光,再者就是无边而孤独的大地(《大地从没有这样孤独》)和我渴望“谛听到大地的心”(《我怎样再听一次》)……这些形象、场景当然可以进一步地探讨,但无论怎样,它们都离不开“土地”这一基本的主题。
四、语词、叙述及其他
灰娃十分欣赏当代诗人昌耀的诗,她说:“昌耀语言硬朗,诗思奇崛,意象铿锵,气质高华,深沉,极富内在美。”[1]253其实,灰娃所肯定的昌耀的诗歌语言风格又何尝不暗合她自己的创作!阅读灰娃的诗,常常为其新颖的遣词造句所“触碰”——
流星曳去了但听
远梦回响
浪花溅泼
沉淀了一味咸涩
——《路》
寻找偃息的旗
我踏遍岩石和遗忘
——《沿着云我到处谛听》
在第一首诗中,动词“曳”单独出现,显然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新奇的感受;浪花的“咸涩”显然用动词散发搭配更符合习惯,但灰娃却使用了“沉淀”,从而拉伸了“浪花溅泼”和“咸涩”的时空内涵;在第二首诗中,具体名词“岩石”和抽象名词“遗忘”并列,共同作“踏遍”的宾语,不仅打破了常规的搭配方式,还给人以出人意料的阅读效果。改变习惯的构词形式,充分利用汉语本身的多义性、模糊性和词性的灵活转换,灰娃赋予了所咏之物新的表意空间,自然也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对词语的创新性使用,自然会影响诗歌语境的营造,同时也拓展了诗歌的叙述方式和想象力。以《山鬼故家》为例,这首记述1987年春陪画家张仃到湘西武陵源天子山写生而为楚地自然风光所折服、惊叹的作品,便以非凡的想象力和表现手法,既写出了景观的神奇、莫测,又写出了游历者“灵魂的激情忘我倾注”。在诗中,灰娃始终把握雄奇、灵魂历险的主旨,将深沉浑厚、纵横奇崛的氛围书写发挥到极致——
辉煌苍凉天地鬼神的遗址
石堆铿锵幽灵飞翔
藤条纠缠荆棘怒生
这儿住着潮湿的山气
白云流浪
蓝雾出没升腾
谁的领地谁的故家
赤豹山鬼
诡谲多情不为人知
——《山鬼故家》
而其颇具匠心的诗行排列、语出《楚辞》的典故,又为本已神秘、玄幻的“山鬼故家”平添了几分绮丽多姿。阅读这些诗句,可以领略灰娃既继承古典诗歌传统同时又善于变化的能力。她总是通过心灵的酿造实现写作的陌生化,她的诗歌对阳刚之美的追求和她作为女诗人的心性结合在一起,最终使其超越了性别、年代的限制,“抵达了诗歌美学最深层的底蕴”,从而“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1]8。
除上述提到的内容之外,灰娃在具体写作中偏爱浓墨重彩,其中尤以深沉、肃穆的“蓝色”为最。“蓝色幽冥的忧郁”“蓝色气层”“琴音冰蓝冰蓝的”,还有“宝石蓝”“月蓝”“雪青”等,“蓝色”是天空和海洋的颜色,可以给诗歌镀上一层冷色调,并使其诗作在拥有“一幅庞大剪影/静立天幕”(《暮》)之外貌的同时,具有坚硬、深邃的内在质地。
关于灰娃的创作,当然还有许多内容可以探讨,比如她许多“无题”诗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关系,又比如她在精神分裂状态下的写作与神秘主义、意识流甚或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等。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赘述。相对于文革的历史,灰娃有一首名为《只有一只鸟儿还在唱》,可作为她回应时代的心声;而相对于她全部的创作史,她有一首《无题》诗可作为绝佳的回答——
没有谁
敢
擦拭我的眼泪
它那印痕
也
灼热烫人
——《无题》
岁月的创痛使灰娃的诗有着抹不去的痕迹,它清晰可见、历久弥新,昭示着自由、坚强、不屈的诗魂!
[1]灰娃.灰娃的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2]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阿羊.暗夜歌者——评灰娃的诗[J].诗探索,1999,(3):149-158.
(责任编辑 周亚红)
Taking Off the Greenery on the Forehead:Studies on Huiwa’s Poems
ZHANG Li-qun,HAO Rui-lin
(School of Art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036,China)
Huiwa’s poem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try.Her poems,healing own mental illness,present a unique world of poetry.In the process of confirmed subject,her poems show a unique feature in the theme,diction,narrative and form.Interpretation of Huiwa’s poems can make people reacquaint poets,writing and so on.
Huiwa;self-treatment;subject;poetry history
I207.25
:A
:1673-1972(2015)05-0046-04
2015-07-26
2015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专项项目“当代诗人心态史论”(ZJ2015028)
张立群(1973-),男,辽宁沈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