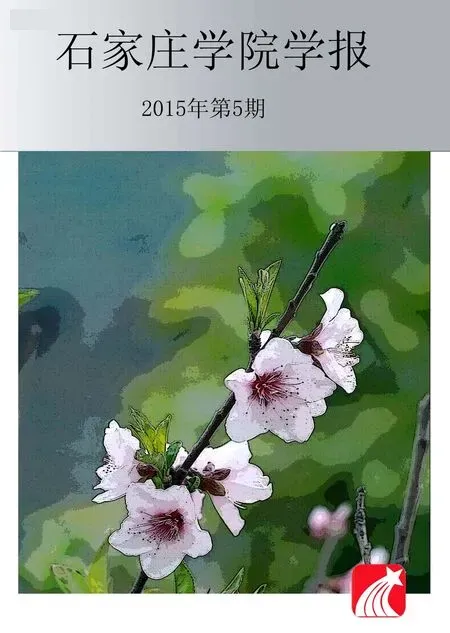何其芳对“追忆”之抒情方式的再发现
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
何其芳对“追忆”之抒情方式的再发现
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
何其芳在回望古典诗传统、重新阐释古典诗词时重新发现了“追忆”之抒情方式的魅力,是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而与此同时,他将这种抒情方式用于自己的诗歌建设中,追忆过去的爱情和青春,采用“化古”手法和对话体展开“追忆”,形成了他对新诗自身创作经验的发现,促进了新诗建设。
何其芳;追忆;抒情方式;再发现
何其芳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携带自己身处1930年代的眼光、诗歌素养、诗歌问题与诗歌经验重新阐释古典诗传统,重新发现了“追忆”的抒情方式,是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此同时,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追忆”爱情和青春,操持化古和对话的抒情策略进行“追忆”,亦是以自己的诗歌实践对传统的一种再发现。
一、“追忆”的再发现
何其芳自幼涵泳于古典诗词中,因而他受泽于古典诗词颇深,亦对之情感笃厚:
我是特别感谢我国古代的那些诗人的。如果我过去的那样两本分行写的东西里面,并不完全是一些枯燥无味的文字,某些部分还有一点诗的味道,一点流动在字里行间的抒情的气氛,那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这些古代的作者给我的教育的结果。尽管我过去写的绝大多数都是自由诗,很像受外来的影响更深更多,然而在某些抒写和歌咏的特点上,仍然是可以看得出我们的民族诗歌的血统的。[1]119
何其芳认为自己诗里抒情的气氛是“古代的作者给我的教育的结果”,并且肯定自己的诗歌“抒写和歌咏的特点上”带着民族诗歌的血统,这是何其芳对古典诗传统中抒情传统的重新认同。抒情传统是中国诗学的主脉,一直以来,不少学者把历代诗歌分为“诗言志”和“诗缘情”两派,他们认为前者主张表达“志”,“志”即封建意识规范和道统,所言之志为统治阶级之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抒情范畴;而与之相对的是自我抒情诗则以“诗缘情”的创作理论为依据。事实上,“志”尽管包含有封建统治阶级的“道”,但也包含有人之情,都归属于抒情传统这一中国诗学主脉。从《诗大序》的“诗言志”到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楚辞·惜颂》),从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再到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情动而言形,理发而辞现”,都是以抒情为本体的抒情传统占据诗学主流,正如金克木所认为的:“中国旧诗与西洋旧诗的显著的不同便在一偏于抒情而一偏于叙事。”“中国旧诗向来就以抒情为主是大致不差的话。”[2]针对1930年代的诗坛,金克木指出“新起的诗有三个内容方面的主流:一是智的,一是情的,一是感觉的”[2],可见,虽然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讲究逃避感情,退隐主观抒情成分,但“情的”依然是三个主流内容之一。何其芳与戴望舒一样注重抒写个人记忆与幻想,但他的抒情诗与郭沫若、湖畔派等诗人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抒情不同,他诗中的“抒情的气氛”主要来自对古典诗传统中抒情传统的重新认同。何其芳承认自己的诗歌创作是“抒情的写作”[3],他认为自己1930年代的诗都是为了“抒写自己个人的幻想、感觉与情感”[4]234。然而,何其芳的独特并非停滞于对抒情传统中“抒情的气氛”、抒写和歌咏的特点的继承,并非与奉抒情为“诗的本质”与“专职”[5]215的郭沫若一样沉溺于直接宣泄情感,而是对抒情传统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
何其芳曾借用李煜的一句词概括他早期那些诗的内容:“留连光景惜朱颜”[6],显然是把“留连光景惜朱颜”作为自己诗歌与李煜词的相通处予以认同。“留连光景惜朱颜”出自《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全诗如下:
阮郎归呈郑王十二弟
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落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春睡觉(有的版本为“佩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
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阑。[7]10047
这篇词作注家颇多,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俞陛云在《唐五代两宋选释》中的阐释是比较符合这首词的本义的:
词为十二弟郑王作。开宝四年,令郑王从善入朝,太祖拘留之,后主疏请放归,不允,每凭高北望,泣下沾襟。此词春暮怀人,倚阑极目,黯然有鸰原之思。煜虽孱主,亦性情中人也。[8]129
俞氏点出了此词的主旨:“春暮怀人,倚阑极目,黯然有鸰原之思。”此词表面上刻画了一个黄昏时倚栏怀人的“思妇”形象,实际上是李煜托借“思妇”形象表达自己的“鸰原之思”。所谓“鸰原之思”,典故出自《诗·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脊令,即鹡鸰,原本是水鸟,后来生活在高原,失去其所习惯的生活环境后,常以鸣叫来寻觅同类。后来常被用作当兄弟遇有急难时须相互援手的比喻义,“鸰原”则用以指代兄弟友爱。这首词的词牌注明是“呈郑王十二弟”,即李煜写给其弟郑王从善,传达的是李煜对其弟郑王从善的“鸰原”之思。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宋灭南汉,南唐局势愈加紧张,后主为缓形势,派弟弟郑王从善到宋朝朝贡,不料被宋太祖拘留。李煜曾于开宝七年(974年)秋上表宋太祖,恳求宋太祖放其弟从善归国,遭到拒绝,从此他常登高北望,思念其弟,动情处常禁不住涕泪沾襟,甚至谢绝歌舞酒乐。这一年李煜曾作《却登高文》直抒其“鸰原之思”,《阮郎归》这首词与《却登高文》作于同一时间,亦是抒发“鸰原之思”。“留连光景惜朱颜”中的“朱颜”与《虞美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中的“朱颜”一样,代指美貌的青年男子。此诗是诗人写给郑王的,而郑王当时并不在眼前,兄弟在大宋被扣留,既然是抒发鸰原之思,那么留连的光景并非指自己眼前的光景,而指兄弟在时的美好光景,所惜的“朱颜”也不是要爱护好自己的青春容颜,而是感慨兄弟的容颜可能已发生了变化,青春已被白白耗费在囹圄之中。诗人由眼前的光景追忆起郑王在身边的兄弟情谊与兄弟在时互助互协的情景,而今“无人整翠寰”,暗喻无人帮自己治理江山。诗人在黄昏时独自倚栏,追忆起兄弟的朱颜、青春和兄弟在时的美好光景,因此此词其实是“追忆”之作。需要注意的是,何其芳单独拈出此句以概括其自己之诗的内容时,进入其视野的是“亡国之君的词句”,然而事实上,李煜创作此词时并未亡国,因此何其芳以此词句作为其诗内容之概括时的意识领域已超越了此词创作的具体时间与背景,而将之视为亡国之君的词句,他所类比的是李煜之亡失国家与自己亡失青春,他认为自己虽然没有一个国家,却因为亡失了青春,而觉得自己亡失的青春与李煜亡失的国度有相通性。因此李煜的“留连光景惜朱颜”在何其芳那里已经获得新的解释,不再停留于追忆兄弟情谊的“鸰原之思”,而是对亡失的国家的追悔与慨叹,在他眼里,此正与他对青春的追悔与慨叹是相通的。只有从这种层面上去解释,何其芳诗歌的内容才真正与李煜的诗句存在相通之处。何其芳不是就诗句论诗句,而是从李煜的生命整体与诗歌全貌上去理解“留连光景惜朱颜”,已经完全跳出了这首诗产生的背景与原意。何其芳在借用时并未详细考证此词产生的具体语境,甚至因此发生“误读”①这里指的是此词句创作时李煜并未亡国,而何其芳却认为其为“亡国之君的词句”,显然是“误读”。,因此,这句词在何其芳的视阈中成为对南唐大好河山的光景的追忆和对时不我待、容颜易改的慨叹。何其芳从整体上理解李煜的悲剧生命,认为他留连于过去的美好光景,慨叹容颜易老,是对亡去的国家的追忆,何其芳借以抒发对亡失的青春的追忆,是对此句诗中“追忆”的抒情方式的认同,他以他个人的眼光重新阐释了这句词,发现了“追忆”这种抒情元素。宇文所安认为“追忆”是古典文学中往事重现的重要呈现方式②参见宇文所安《追忆》,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何其芳早在1930年代便发现了中国古典诗词中这种特殊的抒情方式,并用之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使其诗形成了独特的“抒情的气氛”,构成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
二、何其芳的“追忆”
何其芳以“留连光景惜朱颜”概括自己早年的诗,显然肯定了其早期诗中“追忆”的抒情方式。何其芳以李煜之亡失国家与自己之亡失青春相类比,对于何其芳来说,他所亡失的“国家”是过去的青春和青春时期的爱情,因此他的诗都在追忆过去,正如尘无曾发觉的:“无论他写的是什么,结果总是使我们怀念着过去或则向往着过去。”[9]对爱情的追忆和对青春的追忆成为何其芳追忆的主要内容。
(一)对爱情的追忆
1930年何其芳由于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而遭清华大学开除,在进入北大前的半年多时间里他遭遇了一阵“奇异的风”的吹拂。他当时所居住的“夔府会馆”为过去在京做事的四川人所捐款筹建,专供四川上京求学的学生居住,其时何其芳的堂表姐杨应瑞也借住于此,比何其芳大三岁而漂亮多情的杨应瑞热烈地追求何其芳,两人陷入热恋之中,但却遭到何其芳父亲的强行拆散,由此何其芳便陷入“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怀念与追想中,常沉醉于对那段未熟而酸涩、甜蜜而忧伤的爱情的回忆中。[10]20对此,何其芳曾回忆道:“直到一个夏天,一个郁热的多雨的季节带着一阵奇异的风抚摩我,摇撼我,摧折我,最后给我留下一片又凄清又艳丽的秋光,我才像一块经过了磨琢的璞玉发出它自己的光辉,在我自己的心灵里听到了自然流露的真纯的音籁。”[3]他把那时所遭遇的“奇异的风”的抚摩和摇撼称为“不幸的爱情”,可见其心底的深深遗憾。于是,《预言》中的爱情诗都成为对这桩已然飘逝的爱情记忆的追念与回想。何其芳通过对过去的爱情记忆的追忆表达他“几乎绝望地期待爱情”[6]的渴望。《预言》一诗抒写了诗人对已经逝去的爱情的追忆与回想: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呵,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
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
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
诗一开头在想象情境中回忆了爱情到来时刻内心的激动,诗人捕捉住“心跳”日子来临时的细节“足音”进行描写,展现了诗人对象征爱情的“年轻的神”到来前的等待与到来后的欣喜。接下来诗人对“年轻的神”到来的情景展开想象,想象中混合着曾经的爱情记忆,“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爱情的女主角杨应瑞来自与何其芳同样的故乡四川,因此诗人塑造的“年轻的神”象征的爱情来自南方显然是揉入了杨应瑞的影子;“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明显地流露着对昔日爱情记忆中曾闪现过的温暖的追忆;“再给你,再给你手的温存”的“再”寄托了诗人对爱情的渴望,也流露了诗人对过往爱情记忆的回想;年轻的神匆匆地“无语而来”又“无语而去”,象征了年幼时那段爱情来去匆匆,无果而终。整首诗在想象中展开追忆,在追忆中混合想象,触发点是“追忆”,终点亦是“追忆”,通过追忆曾经的爱情记忆展现诗人爱情心理的觉醒与对爱情的渴望。
《罗衫》更是一首凄美绝伦的爱情诗,充满了爱情逝去后的幽怨、缠绵与痛苦,难怪《汉园集》中原题为《罗衫怨》,收入《预言》时才改为《罗衫》。诗人借助“罗衫”的属性与用途展开对爱情的追忆与回想。“罗衫”是一种薄如蝉翼的绸衫,夏季过后便被主人收入箱底,不再与主人朝夕相伴,古代常借用来象征爱情的变故。何其芳重新启用了“罗衫”的隐喻意义,以此展开对过往爱情的追忆,诗人化身为“罗衫”,在“罗衫”的自诉与倾吐中引入了恋爱细节与场景的回忆,如嬉游时双桨打起荷香、欢乐时流泪、慵困时把口脂留在袖间、当女主人合眼时偷偷映到胸前的月下锦葵花的影子等,都是当初甜蜜爱情的系列细节。诗人在今昔对比中呈现爱情逝去后遭到冷遇的失落与痛楚,但诗人并不绝望,“我将忘记快来的是冰与雪的冬天,/永远不信你甜蜜的声音是欺骗”。诗人在追忆中传达了对未来爱情的期盼与渴望。《休洗红》通过衣服因被洗而褪色的物理常识,诗人摇身而变为洗衣服的少女,在洗衣过程中追忆逝去的爱情,“春的踪迹,欢笑的影子,/在罗衣的变色里无声偷逝”呈现了过去爱情的甜蜜幸福,也呈现了爱情的脆弱易逝,因此诗人幽怨地叹息失去爱情的怅惘,“能从这金碧里拾起什么呢?”“粉红的梦不一样浅褪吗?”“我的影子照得打寒噤了。”《赠人》在对过往爱情的追忆如“我害着更温柔的怀念病/自从你遗下明珠似的声音,/触惊到我忧郁的思想”之后,得出了“无希望的爱恋是温柔的”的结论。这是一种发自诗人内心深处的对过往爱情记忆的追念与痛楚。《雨天》中“是谁窃去了我十九岁的骄傲的心,/而又毫无顾念的遗弃?”是诗人对失去的爱情的伤感追问,诗人的追悔与怀念之情隐现于诗行间。《祝福》写出了对昔日恋人的“怀念”;《月下》通过书写对一位少女的思念,在追忆中抒发了绝望的爱。对于何其芳的爱情主题艾青曾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我们该记得何其芳有过“刻骨的相思”,“恋中的季候”,谁家少女的裙裾之一角的飘动会撩乱他可怜的心。总之,他有太深而又太嫩的爱。不消说他是属于我们旧传说里的所谓“情种”一样的人物。[11]
艾青认为何其芳“把糖果式的爱情看为生活的最高意义的基调”,在他的游戏规则不顺利的时候便嫌恶使他痛苦的实生活,陷入虚幻的白日梦和在幻觉中维持多余的生命。艾青显然否定了何其芳的爱情抒写,孙玉石则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何其芳的这些爱情诗,已经是基于个人的苦乐悲喜而又超越于苦乐悲喜,基于真实与理想而又超越于真实与理想,曾有过热恋而又超越于热恋生活层面。净化后的情感变得更冷静,更透明,从而进入了一种生命体验的美丽的‘艺术的爱情’。”[12]确实,何其芳的爱情诗跳出了以往的抒情模式,以“追忆”过往的爱情往事为基点展开对过去爱情的怀念与对未来爱情的渴望,这种“追忆”的抒情方式下展开的爱情已经过岁月沉淀,因而超越了个人的苦乐悲喜,超越了真实与理想,超越了个人感情得失的层面,具有更加感染人而持久的艺术价值。
(二)对青春的追忆
“留连光景惜朱颜”成为何其芳对自己过去的概括,他指出:“把这些杂乱的东西放在一起并且重读一遍后,我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愁。因为我想起了那些昔日。”“对于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我是惋惜,追悼,还是冷冷的判断呢?我无法辨别我的情感,我感到那不是值得夸耀的好梦,这些杂乱的东西就是我徘徊的足印。”[13]诗成了“昔日”和“消逝的岁月”的载体,成为过去的见证,因此何其芳在诗中通过“追忆”展开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展开对时间的感知。他说:“我那时唯一可以骄矜的是青春。”“留连光景惜朱颜。那是一位亡国之君的词句。虽然我的手里没有一个国家,我也亡失了我的青春。亡失了我的青春,剩下的就是一些残留在白纸上的过去的情感的足印,一些杂乱的诗文。”[6]他把自己亡失的青春与李煜亡失的国家进行类比,青春就是他的国度,诗文成为他追忆青春的残片。
对于《燕泥集》的命名,何其芳自我疑问:“《燕泥集》?难道是我自己那些情感的灰烬的墓碑吗?”他认为:“我现在仿佛就是一只燕子,我说不清我飞翔的方向,但早已忘却了我昔日苦心经营的残留在空梁上的泥巢。是的,我早已忘却了,一直到现在放它在我面前让我凄凉地凭吊着过去的足迹,让我重又咀嚼着那些过去的情感,那些忧郁的黄昏,和那些夜晚。”[13]何其芳作为一个“留连光景的人”,一直试图寻找他“失掉了的金钥匙”[14],这个“金钥匙”便是他唯一可以骄矜的青春。
何其芳反复称自己是“一个留连光景的人”,而他又常拿李煜亡失的国度比喻自己亡失的青春。显然所留连的光景是过去已逝的光景,所谓的“留连”其实是一种追忆,这种对过去光景的“追忆”成为何其芳主要的抒情方式。而在何其芳的记忆里,青春年华全是寂寞的岁月,“少年哀乐过于人”[15]的他唯一可以骄矜的青春在寂寞中消耗过去,因此诗中大多是对已然逝去的青春年华的追忆,过去岁月里的寂寞成为“追忆”的基调,诗人在追忆过去光景中抒情,追忆青春岁月里的寂寞。
何其芳的青春记忆是寂寞的,何其芳在寂寞中追忆青春,又在诗的文字中追忆寂寞的青春,“寂寞”成为何其芳抒情体系的主脉。这种情绪来自何其芳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何其芳自幼便“不是在常态的环境里长起来的”[6],童年的记忆里只有“冰冷的石头;小的窗户;寂寞的悠长的岁月”“那缺乏人声与温暖的宽大的宅子使那些日子显得十分悠长,悠长”[16]93,因此他的成长一开始就“营养不良”、“发育不健全”,及至后来他进到县城的新式中学的“新世界”中,看到的依然是“照样的阴暗、湫隘、荒凉”,他“感到的仍是寂寞”“越是感到人的不可亲近”[17]。而1930年他来到北平后,“文化古城”和“政治边城”的生活环境延续了他的寂寞:
那时我在一个北方大城中。我居住的地方是破旧的会馆,冷僻的古庙,和小公寓,然而我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每一个夜晚我寂寞得与死接近,每一个早晨却又依然感到露珠一样的新鲜和生的欢欣。[6]
寂寞的无可逃脱让他感到被人世遗弃的悲哀与孤独,因此他“写着一些短短的诗和散文,我希望和我同样寂寞的孩子也能从它们得到一点快乐和抚慰”,他感叹,“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味、那种境界和那些东西了”[18]。何其芳特别多愁善感,对寂寞有着刻骨铭心的深切感受。1930年5月19日他在给吴天墀的信里写道,一些朋友来本来很热闹,但游玩回来忆起远方的吴天墀和埋骨地下的杜深甫,心感热闹的光景难延续长久,却芳华易逝,于是便想哭,“自己的愁自己受”;1931年8月20日他在信中写道:“寂寞是当然的,而且是可爱的。”[19]102何其芳还曾回想起他的一次“可哀的心理经验”:
在过来一个旧历的新年后,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带着欢欣和一件小礼物去拜访一位朋友,洋车拉着我在冷落的铺满白雪的长街上,我突然感到一种酸辛一种不可抵御的寂寞。[6]
诗人在新旧交替的旧历新年时,看到旧的一年过去,一年的青春又消逝而突然感到寂寞和酸辛。1933年何其芳在《柏林》一诗中写下的最著名的两行诗句无疑是寂寞情绪最浓烈的精神投影:
从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20]24
对于这两句诗里所表达的内涵,诗人认为:“那仿佛是我的情感的界石,从它我带着零落的盛夏的记忆走入了一个荒凉的季节。……我叹息我丧失了许多可珍贵的东西。”[3]“寂寞”是何其芳情感的主核,现实世界中的寂寞让他沉醉于“倾听着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捕捉着一些在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于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这种寂寞中的工作成为他的癖好,他由此“开始了抒情的写作”[3]。因此,在1930年代何其芳的早期诗作中,处处可见“寂寞”的影子,处处可感受到“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3],如代表作《预言》中,“叹息”“温郁”“沉郁”“空寥”“夜”“无语”,《脚步》中“甜蜜的凄动”“无言的荒郊”“互递的叹息”“树上的萧萧”“低抑之脚步”“曲折的阑干”,《秋天(一)》中“郁郁的梦魂”“可怜的心”“叹息的目光”“深山的寂默”“透明的忧愁”“更深的绸缪”“暗暗的憔悴”等都透射出抒情主人公寂寞的内心世界。另外,其他诗中出现频率颇高的“忧郁”“寂寥”“寂寞”“幽怨”“寒冷”“隐遁”“僵死”“衰草”“月”等词语无不是诗人寂寞情绪的文字投影,以至何其芳自己读着所写下的那些诗行都“感到一种寂寞的快乐”13]。
青春的易逝,是何其芳追忆青春的主因。何其芳“追忆”的世界是一个“画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喜欢用花、水、月华、琴音等意象,这些都是极易凋谢或消逝的意象,正是何其芳追忆过往青春的意象投射,如《莺莺》《我埋一个梦》《我不曾》中的桃花,《罗衫》中的锦葵花,《圆月夜》中的睡莲和无声的落花,《梦后》中最易凋谢的黄花,《昔年》中的红海棠,《爱情》中的石榴花,《细语》中的白茶花等,都喻示了青春年华的凋零易逝;“水”意象则常分解为“雨”“露”等,如《暮雨》《雨天》《想起》等诗中“雨”意阑珊,《花环》《爱情》《墙》《慨叹》《圆月夜》等诗则满缀“露”珠;《月下》《圆月夜》《梦后》《扇》《罗衫》《祝福》等诗洒满月华,《脚步》《祝福》《秋天》等诗里琴音缭绕,这些意象都如镜中花、水中月、梦中人般似乎触手可及却又遥不可及,甚至无迹可寻,转瞬即逝,诗人通过这些意象传达了他对青春和过去时光的追忆之情。
三、追忆的策略
何其芳不是君王,却将自己过往的青春与爱情搭建成一个已亡失的自我“王国”,而“追忆”则成为重返这一“王国”的独特路径,那么,何其芳如何通过“追忆”而重返他的自我“王国”?细究内里,他主要通过“化古”创设古典情境,营造“过去”的氛围,采用对话体的追忆策略尤其是追问方式,步步深入地返回过去,从而建构起自己独特的“追忆”话语方式。
(一)“化古”
何其芳喜欢借用古典情境展开自己对过往青春与爱情的“追忆”,如化用古典诗词中的意象、语句、典故,将古典诗词中已有的情境与自己的诗歌情绪、感觉、幻想叠合,从而创设自己独特的诗歌情境,营造“追忆”的感伤、怀旧气息,增加追忆的厚度、深度与重量。
“化古”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自幼为古典诗歌迷醉的何其芳尤善此道,主要方法有三,一则重新激活古典意象,如“罗衫”,本是一个古典词汇,古代的陶渊明、李白、王维、晏几道等诗人笔下常出现这一意象,以“罗衫”的脱换象征男女关系的不稳定不可靠,暗蕴思念、盼望、关切、依恋、欢爱、伤逝等丰富内涵,但这一词汇现今已基本停止使用,何其芳却在《罗衫》一诗中重新启用这一意象及其内涵,以“罗衫”象征已成为过往陈迹的爱情,借用其与女主人的关系隐喻已逝的爱情,从而追忆曾经的过去;《休洗红》中也启用了“罗衣”意象,藉以追忆消逝的爱情;《扇》中的“扇”“绢面”,《关山月》中的“渔阳”“鸳瓦”,《休洗红》中的“砧声”“板桥”“白霜”“杵”,《古城》中的“塞外”“衰草”“胡沙”“危阑”“废圮的城堞”,《夜景(二)》中“马蹄声”“剥落的朱门”“衰落的门庭”等都是充满古典韵味的意象,何其芳都重新启用而作为追忆过去的载体,将往事引入更深远的过去时空情境中,更富有怀旧、追忆之韵。二则化用古代诗句,增加了追忆厚度,如《古城》中“悲这是故国遂欲走了,/又停留,想眼前有一座高楼,/在危阑上凭倚……/坠下地了/黄色的槐花,伤感的泪”化用了“楼高莫近危阑倚”(欧阳修《踏莎行》)、“感时花溅泪”(杜甫《春望》),“望不见落日里黄河的船帆,/望不见海上的三神山……”化用了“天长落日远”(李白《登新平楼》)、“忽闻海上有仙山”“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白居易《长恨歌》),都借古怀过去,援古抒发对过去的追忆之情,更增加了“过去时空”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寂寞的砧声散满寒塘,/澄清的碧波如被捣而轻颤。/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能从这金碧里拾起什么呢?”(《休洗红》)、“扇上的楼阁如水中倒影,/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叹华年流过绢面”(《扇》)等诗句都仿佛古典诗歌的现代“翻译”,杂糅了各家诗句,化合无痕,充满古典情韵而与“现在”更拉远了距离,延伸了“追忆”的时空感。三则启用典故,何其芳或拟用汉代乐府或唐代新乐府之题而入诗,如《关山月》《休洗红》《箜篌引》等,或借用历史传说或典故故事而衍生诗意,如《古城》中对《枕中记》《邯郸记》等故事原型的化用,《莺莺》中对崔护《题都城南庄》、孟棨《本事记》故事原型的衍变提用,《扇》中对“嫦娥奔月”的故事原型的启用,都是根据历史传说、典故激活新的联想,从而将自己的过往青春与爱情覆盖上历史、典故的厚蕴,使“追忆”超越了个人一己之情、事,其厚度、深度、重量均非直接抒情、宣泄之作可比。
(二)对话体
由于何其芳的诗大多是在追忆过往的爱情和青春记忆,因此,诗人在诗中总是虚设了一个倾诉的对象“你”,诗人以“你”为倾诉对象展开“追忆”,絮絮诉说,娓娓道来,仿佛要把过去的记忆都一一倾泻给对方。诗人在虚拟的对话中完成情感的表达,这种对话体常以自问自答或疑问句式的心灵对话模式形象生动、层层深入地传达着自我情绪,是我国古代汉赋“主客对话、抑客伸主”的传统艺术范式的重新启用。何其芳对这种疑问式的对话模式的运用很多,据任洪国统计,《预言》的35首诗中便有21首运用了明显的疑问手法[21],可见何其芳对疑问手法的运用娴熟程度。他在诗中处处运用疑问手法,这些疑问并非真正疑问难题或迷惑,也并不需要疑问的化解与解答,而只是内心世界宣泄和展现的途径,这种手法增强了诗歌的情感氛围。《欢乐》一诗显然是典型,全诗一问到底,几乎每一句诗都是疑问句式:
告诉我,欢乐是什么颜色?
像白鸽的羽翅?鹦鹉的红嘴?
欢乐是什么声音?像一声芦笛?
还是从簌簌的松声到潺潺的流水?
是不是可握住的,如温情的手?
可看见的,如亮着爱怜的眼光?。
会不会使心灵微微地颤抖,
或者静静地流泪,如同悲伤?
欢乐是怎样来的?从什么地方?
萤火虫一样飞在朦胧的树阴?
香气一样散自蔷薇的花瓣上?
它来时脚上响不响着铃声?
对于欢乐,我的心是盲人的目,
但它是不是可爱的,如我的忧郁?
诗人以“欢乐”为核心意象,从欢乐的颜色、声音、形态、性质、来源等方面发出疑问的射线,而这些射线都不需要折回,其疑问只是抒发诗人对“欢乐”的诗意认识,在疑问中不证自明,增强了诗人抒情的力度与诗意的厚度。《预言》《慨叹》《圆月夜》《月下》(《关山月》)《休洗红》《雨天》等诗都无不采用疑问的对话体。正是循此“对话”“追问”路径,何其芳对爱情与青春的追忆逐层展开,步步导入过往时空的深处,抵达“追忆”之事、情的深处,从而增加了“追忆”的力度与感染力。
何其芳在回望古典诗传统、重新阐释古典诗词时重新发现了古典诗中“追忆”之抒情方式的魅力,并用之于自己的诗歌建设中,追忆过去的爱情和青春,采用“化古”手法和对话体展开“追忆”,一方面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一方面对“追忆”这一抒情方式进行了实践与探索,促进了新诗建设。
[1]何其芳.写诗的经过[M]//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2]金克木.试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J].新诗,1937,1(4).
[3]何其芳.论梦中道路[N].大公报·文艺·诗歌特刊,1936-07-19.
[3]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4]郭沫若.论诗三札[M]//郭沫若.文艺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何其芳.《刻意集》序[J].文丛,1937,1(4).
[7]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俞陛云.唐五代两宋选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尘无.画梦录[J].光明,1937,1(4).
[10]尹在勤.何其芳评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11]艾青.梦·幻想与现实[J].文艺阵地,1939,3(4).
[12]孙玉石.论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J].文学评论,1997,(6):11-23.
[13]何其芳.燕泥集后话[J].新诗,1936,(1).
[14]何其芳.金钥匙[N].华北日报·文艺周刊,1934-10-15.
[15]何其芳.《效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J].诗刊,1964,(5).
[16]何其芳.我们的城堡[M]//何其芳.还乡日记.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9.
[17]何其芳.街[N].大公报·文艺,1936-11-29.
[18]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J].中国青年,1940,2(10).
[19]何其芳.书信·致吴天墀[M]//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八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0]何其芳.燕泥集·柏林[M]//何其芳.汉园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1]任洪国.忧郁的追问者——何其芳《预言》疑问手法的解读[J].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3,(1):4-6.
(责任编辑 周亚红)
He Qifang’s Rediscovery of the Lyric Method of“Recalling”
LUO Xiao-feng
(School of Arts,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01,China)
When He Qifang reinvestigated the classical poetry,he rediscovered the charm of lyric method of recalling from classical poetry.Meanwhile,He Qifang put this lyric method into his own writing,with which he recalled the youth and love in the past.He took the way of classics and style of dialogue for recalling,thus the discovery of poetry writing experience of his own took shape,which promoted the new poetry construction.
He Qifang;recalling;lyric method;rediscovery
I207.25
:A
:1673-1972(2015)05-0039-07
2015-05-27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倾向研究”(12YJC751057)的阶段性成果
罗小凤(1980-),女,湖南武冈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南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兼及一类史料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