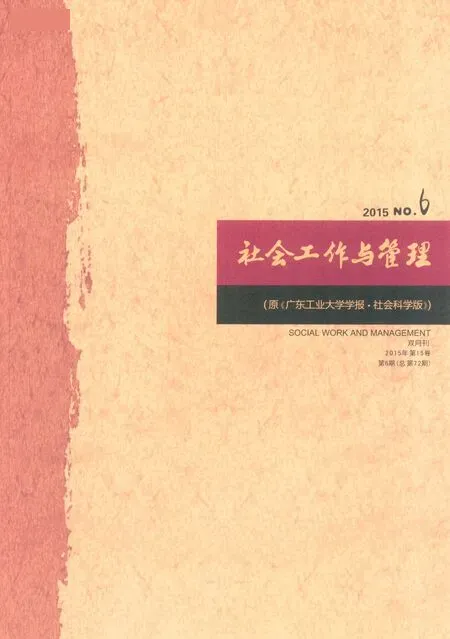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启示
王慧娟
(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广东 广州,510090)
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启示
王慧娟
(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广东 广州,510090)
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被动同化取向的政策,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被动整合取向的政策,第三阶段主要表现为多元文化基础上的融合政策。在积极融合取向、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府功能的定位、多元文化等几个方面,欧盟解决流动儿童教育的经验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
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启示
“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推算,0—17岁流动儿童规模为3 581万,在2005年的基础上增加了41.37%,且有增长的趋势”[1]。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最为棘手且十分紧迫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同时它也是构建新型社会管理、促进流动儿童与社会之间整合的重要内容。如何妥善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成为一个引起社会大众关切的实际问题。
历史上,欧盟就是流动儿童大量集中的地方,现在其流动儿童数量依旧居高不下。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上,欧盟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其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方式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如在积极融合取向、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府功能的定位、多元文化等几个方面,欧盟的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
一、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
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发展同欧盟劳动力流动的开放程度紧密相关。因此,其发展演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缓慢发展过程。一般来讲,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政策是被动同化取向的政策。此时的教育政策只是试图保障流动儿童对国家教育设施的使用权利,缺乏文化上的融合举措。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从流动人口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了当时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如西北欧。流动的主体多为单身闯世界的年轻人,他们多未婚,即便已经结婚生子,他们也不急于携妻带子闯世界,处于单枪匹马打拼阶段。因此,这一阶段,欧盟面临的流动儿童教育的压力还不是很大。再者,此时的流动人口主要争取的是自由流动权利,经济动因是主要方面,流动儿童的教育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从欧盟的角度看,欧盟此时的法律政策中尚缺乏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价值观念被赋予在保护这些具备特定文化背景的流动儿童之上。当时的观点主张,这些儿童在流入国的教育体系下依旧可以取得跟母国一样的教育成就。这样的取向被认作是形式上的平等,主要通过将流动儿童暴露在流入国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下达到被动同化的目的。[2]
所以,第一阶段的教育政策主要侧重为流动儿童提供接近教育设施的允许权。在欧洲的相关法律中,陆续确认了流动儿童对所有层面教育的可接近权利和对教育资金的可接近权利。这些可接近的基本权利成为国际层面上同类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典范。
第二阶段,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政策目标导向比较模糊,是积极、消极同时并存的被动整合取向的政策。如果说第一阶段只是属于准许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就学的一席之地、缺乏其他举措的被动同化取向的政策的话,第二阶段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显示出较为积极的一面。其积极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此时的政策聚焦点转移到对流动儿童文化权利的关注上。他们认为流动儿童有用母语获得指导的权利。但是,此时的政策并不是融合性的,具体表现在此时的政策较少关注流动儿童的文化认同问题,而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促进流动人口返回到他们的母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盟国家政治上出现了阻止移民的趋势,一些国家甚至倡导移民返回母国。[2]
如此矛盾的措施导致了基本的政策悖论:对流入国语言的更多学前教育和对母国语言的教育。应该说,它虽然缺乏清晰的目标,但是却包含了三个要素。其一,强调对流入国语言的接纳性教育,由此使得同化更加积极和正面;其二,虽说存在对母国语言的教育,不过此时对母国语言的教育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一些规定甚至明确倡导移民应该在一定阶段返回母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政策客观上赞同文化多元的价值。其三,在政策的适用性方面,国会指出,这些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移民,而不是只有那些社区权利。[2]
第三阶段,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在前两个阶段政策累积的基础上,一些问题相继暴露,因此在第三个阶段,欧盟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教育政策,应该说,第三个阶段的政策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融合政策。这一阶段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主要旨在促进教育中的整合、多元化、机会平等和融合。相比前两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政策目标更加明晰,更具可操作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盟社会中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趋势和定居化趋势明显。此时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多数流动人口是不会回到母国的,但是他们在流入国的社会融合却依旧是个问题,具体表现为:一部分流动儿童就是在流入国出生和长大的,对母国一无所知;他们中的许多人有了孩子,但是他们依旧生活在他们背景的文化环境中,只是部分融入流入国。因此,针对流动儿童的教育就呈现出新的意义,教育承担着促进他们在流入地完全融合的功能。单有对教育设施的接近并不能使他们恰到好处地拥有当地社会的完全成员资格。并且,官方认为“流动人口不是永久居民,因此不是市民或者是不同类别的市民”的观点也导致了流动人口和当地社会整合失败的后果。[3]这就使得旨在促进机会平等和多元主义的价值观的跨文化教育成为可能[4]。再者,2000年里斯本会议确立了欧盟在新时期的战略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有更多更好的工作,以及更强的社会凝聚。”促进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和社会整合(social cohesion)成为欧盟核心战略目标,教育被认为是主要的整合工具之一,它在促进欧盟集体文化认同和构建欧洲公民意识方面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11月在尼斯举行的论坛和欧洲理事会上,每个成员国都被要求签署两年的国家促进社会融合实施计划(National action plan against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NAPS),内含能够衡量这一计划进展的专门指标和监督机制。其中,教育和培训在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作为一个关键部分而得到高度强调,并在2010年7月实施的欧洲2020就业和增长战略中得以再次确认。[5]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第三阶段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更加强调促进机会平等和尊重多元主义的教育,突出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政策不会强迫流动儿童在家庭和流入国之间做出选择,流动儿童对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的可接近性问题得到解决,更加突出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并且这项权利被整合进主流的强调合作而不是积极强力的社区教育政策之内。这一时期,欧盟采取了多层面的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不仅涵盖宏观层面制定反歧视和政策法规,如为了扫除移民融入的障碍,欧盟各国普遍修改入籍法规,规范和降低入籍限制,加快永久性移民的归化进程,对某些过于严格的规定加以放宽,尤其使移民第二、三代子女的归化入籍变得相对容易,从而从根本上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及其在流入国的经济社会整合;中观层面上以学校为组织单位开展相关对流动儿童所在学校、教师、师生关系等的支持;还包含微观层面上开展专门针对流动儿童的支持举措,如儿童早期发展支持项目、流动儿童语言适应项目、移民社区的额外教育、语言学习夏令营、资优儿童支持项目等。[6]通过这些多层面的举措、行动等干预措施,欧盟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举措不仅实现了系统之间的融合,也实现了流动儿童在流入国的社会融合,更通过各种教育行动计划促进了各成员国教育与培训的协调与合作,为各成员国在学生交流、教师交流、学分转换、课程开发等方面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从而建构了教育的“欧洲维度”。
二、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演变的特点
从上述对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欧盟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演变体现为循序渐进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政策动机上,从保障个人迁徙自由的经济动机向保障流动儿童教育权利的权利动机转变,从保障流动儿童对教育设施的使用权向保障流动儿童的文化权利的转变;在政策主体上,从一元的政府参与向多元主体协作模式转变;在政策地位上,从附属地位向独立政策地位的转变。如今,教育已经成为欧盟促进流动儿童社会整合的主要工具之一。
其二,政策的多层次性和交错性特点。欧盟出台的相关流动儿童教育政策中,从政策所涉及的层面来讲,既有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整,又包含对中观层面的学校组织的相关支持措施和微观层面的对流动儿童个体及其家庭的一些扶助措施,从而保证了政策系统之间衔接的有效性和政策之间的系统融合①。从政策的维度来讲,既有经济维度,还有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且后来越来越注重对文化维度的相关支持,如,对流动儿童语言的相关支持措施、对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干预等。各个维度彼此交错,共同发挥作用,使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得到较好保障。
其三,多元力量的协同。在欧盟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存在多元力量的参与,欧盟、欧盟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相关力量广泛参与到该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并有序地发挥作用,是多主体的协作模式,这从根本上有别于一元的政府参与。其中,欧盟、欧盟成员国和非政府组织分别承担着相应的职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非政府组织使欧盟的教育政策没有简单地脱离实践,而是配合了大量的教育行动。自1976年设立《联合学习计划》至今,欧共体或欧盟的教育行动计划先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单项到综合,由零散到系统化、制度化的过程。伴随着这些教育行动,欧盟的教育政策实现了从手段到目的的渐进发展过程。
其四,教育政策与社会的整合。公平原则、权利原则和融合原则等的并进,真正贯彻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凸显了社会公平和儿童权利,极大保障了流动儿童与社会的整合,避免社会分裂。最初的欧洲共同体的条约中几乎没有涉及教育的条款,教育只是作为经济增长的辅助手段而存在。但后来随着欧盟的发展和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盟政策的制定者开始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意义,并先后启动一系列教育行动计划,建立了各种教育与培训组织以及各种与之相关的信息与技术设施。教育逐渐成为欧盟社会模式的基石之一。
三、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积极面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并寻求解决该问题的社会政策的行动方案。在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中,欧盟把促进流动儿童与社会的整合作为最需解决的问题。在一体化的过程中,欧盟着重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与欧盟社会政策的推进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盟开始调整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方向,致力于推进流动儿童与社会的整合,把教育作为流动儿童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公民权利来看。由此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欧盟的经验为中国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借鉴的样板。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上,至少可以得到四方面的启示。
其一,多层面的积极融合取向的政策。当前,我国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成为社会政策创新的强大推动力量。因此,亟需制定有利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教育政策。该政策应该广泛涉及到宏观政策和制度、中观的学校组织和微观的流动儿童个人及其家庭。只有通过整合的教育政策,才能达至保障流动儿童个人权利,减少未来社会、政治和文化上冲突的目的。
其二,非政府部门的参与。在欧盟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实践中,非政府部门在执行相关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及时有效反馈教育信息、促进流动儿童各个层面的教育融合等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非政府部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监督成员国是否采取和落实反歧视的政策;当成员国部门侵犯到一些群体的教育权利的时候,为欧盟委员会等提供精确的数据和生动的个例;在地区、国家和欧盟的层面上,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成功的经验,并促进经验和信息的分享等。[5]通过这些措施,非政府部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策和制度的不足。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流动儿童教育中的参与还相当少,主要局限在对微观的流动儿童个体教育方面的支持性服务,而对中观层面上的学校组织和宏观层面上的政策和制度,缺乏相应的回应。因此,如何扩大非政府组织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中的参与,必须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
其三,政府角色的定位。从根本上说,教育是一项政府对人民的福利事业。在当今世界,正规的、普及的主要是由政府推动和提供的教育,仍然是世界上主流发展趋势,而教育仍然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提供的社会政策,人民亦应享有接受教育的福利权。[7]因此,在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相关事项中,政府的参与必不可少。欧盟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政府的参与始终贯穿其中,问题在于政府的功能定位。在欧盟经验中,政府并不是包办一切、无所不能,而是适时放手将“政府办不好、也办不了”的事情交给第三部门。而我国目前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模式依旧是一元的政府参与,这导致政策在实践中被扭曲变形、政策的低效能。非政府组织虽有热情、有能力开展相关服务,但囿于财政支持的缺乏和施展空间的不足,不能完全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上发挥其应有功能。这种情况的存在,意味着需要重新定位政府的功能。在笔者看来,政府在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相关事项中,可以发挥如下作用:其一,完善体制改革,纠正歧视性规定;其二,制定流动儿童教育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给予流动儿童教育相应的法律地位,并监督政策和法规的执行与落实情况,从法律和政策上分配给流动儿童平等的机会和资源;其三,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切实把获得有质量的教育变成流动儿童的重要福利和应得权利;其四,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的相关事项,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流动儿童教育支持中的作用,给予非政府组织足够的作用施展空间。
其四,多元文化共存的观点。多元文化政策强调不同的文化的独特性并尊重和倡导文化之间的平等共处。欧盟在对待移民群体和文化时,注重对移民群体背景文化的尊重,保留了移民群体的自身文化,且在此基础上促进移民群体与其他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我国是个多民族广地域的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每个地方的特有地方文化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文化差异,都值得在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引起深思和关注。
注释
①洛克伍德(Lockwood)提出系统融合与社会融合的区分,他指出,社会融合问题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有序或冲突关系,而系统融合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有序或冲突关系。
[1]中国新闻网.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数量大幅度增长[EB/OL].[2013-05-10].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30510/17826771.html.
[2]HOLLY CULLEN. From Migrants to Citizens? European Community Policy 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1996(45):109—129.
[3]HINNENKAMP V. The refusal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interethnic contexts[M]∥GILES H, ROBINSON P, SMITH P.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Pergamon, 1980:179—184.
[4]CULLEN. Education Rights or Minority Righ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Family, 1993(7)2:143—177.
[5]JANA HUTTOVA,ELIF KALAYCIOGLU,LINA MOLOKOTOS-LIEDERMAN.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An NGO Guide to EU Policies and Actions[A][2014-08-05].2010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New York, USA,http://www.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reports/education-migrant-children-ngo-guide-eu-policies-and-actions
[6]FRIEDRICH HECKMANN.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migrant children in European schools and societies[R/OL].European Commission,[2014-08-06].http://www.nesse.fr/nesse/activities/reports.
[7]蔡文辉. 社会福利[M].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1999:166—167.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徐朝科)
2014-09-10
■ 基金课题:广东工业大学团队平台重大成果培育基地项目:“社会工作介入社会管理的作用机制研究”(251131053);广东工业大学校内博士启动研究课题“流动儿童贫困与社会排斥:一项基于广州的调查”(14ZS0041)。
王慧娟(1981—),女,汉族,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社会政策。
王慧娟.欧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与启示[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15(6):24—28.
C916
A
1671-623X(2015)06-0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