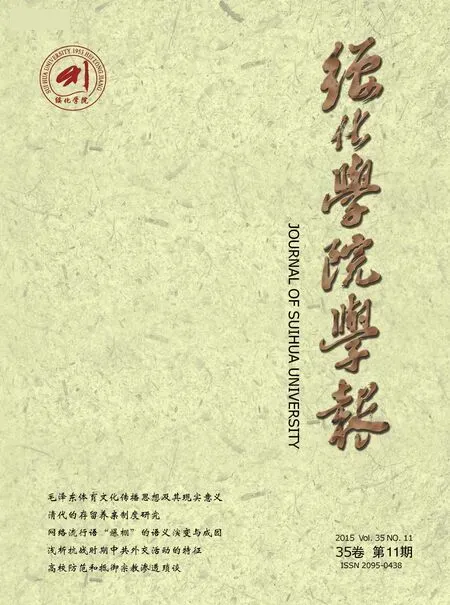“鱼”原型意象的当代文化隐喻
——阿来的《鱼》和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之比较
孙胜杰(黑龙江东方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6)
“鱼”原型意象的当代文化隐喻
——阿来的《鱼》和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之比较
孙胜杰
(黑龙江东方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6)
文章通过“鱼”原型意象来探讨当代文化中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感和通过“鱼”原型意象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生命活力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当代文学中“鱼”意象原型的文化隐喻的揭示可以为在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代如何对待异质文化、民族文化的问题提供一种借鉴——以开放、平等和尊重的心态。
鱼原型意象;阿来《鱼》;谭恩美《拯救溺水鱼》;文化隐喻
在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代,物质文化的发展程度对社会变革的阻碍并不十分难以克服,反而难以征服的是精神文化,特别是长时期积累形成的那些与现代化不相符合的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一方面,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影响和融合,对于民族文化的坚守都在不约而同地面临着在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化的矛盾和调适中发展。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之间是相互学习交融,而非冷漠隔绝,但如果要移风易俗、转变观念,这个任务还是长期而艰巨的。在《拯救溺水鱼》中,谭恩美运用“鱼”意象深刻提示了东西文化间的冲突,并且可以看到作者从超越种族与民族的狭隘视角关注其隐藏在东西方文化冲突深层所蕴涵的人文精神的人类共性。
一、“鱼”禁忌的超越
对于藏民族文化心理的书写,阿来在两个同题的短篇和中篇小说《鱼》中通过“鱼”意象进行了描述,在作品中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神秘的意象世界。两篇小说都对藏民族鲜为人知的文化禁忌进行了阐释。阿来曾说自己“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命中注定要在汉藏两种语言之间长期流浪,看到两种语言下呈现的不同心灵景观。”[1]藏民族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具有双重性的,对于现实物质文明生活他们并不排斥,对于精神内心的佛祖世界他们也很虔诚,所以,对于藏民族来说,现实的功力性和神佛的超脱性相互交织,现代藏族人就在这两种文化生活夹缝的焦虑中生存,正如阿来在短篇小说《鱼》中所表述的,垂钓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娱乐休闲方式,但对于藏族人来说这种娱乐方式是一种内心煎熬的体验,因为鱼对很多藏族人来说,是一种禁忌。“草原上流行水葬,让水与鱼来消解灵魂的躯壳,……藏族人在举行传统的驱鬼与驱除其他不洁之物的仪式上,要把这些看不见却四处作祟的东西加以诅咒,再从陆地,从居所,从心灵深处驱逐到水里。于是,水里的鱼便成了这些不祥之物的宿主。”[1]因此,藏民对鱼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恐惧、敬畏,时间久了自然做为一种禁忌扎根于藏族的传统文化之中。
短篇小说《鱼》中的主人公“我”是藏族,接受了多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在现代文明的熏染下,我对于本民族文化禁忌进行了一次反叛。作品中“我”和同人扎西进行的一次日常采风活动,扎西和“我”在采风活动中被迫不得不去钓鱼,对鱼有禁忌的藏族人无疑面临的是一种战胜自我的挑战。我和扎西对于本民族的禁忌做了不同的选择,扎西的逃避让“我”选择了勇敢挑战,“我今天钓鱼是为了战胜自己。在这个世界,我们时常受到种种鼓动,其中的一种,就是人要战胜自己,战胜性情中的软弱,战胜面对陌生时的紧张与羞怯,战胜文化与个性中禁忌性的东西。”[1]但禁忌是很难被战胜的。这篇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在对故事叙述中自然地把藏族文化中的鱼禁忌和日常采风活动中休闲娱乐的垂钓生活融会到叙事中。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形容禁忌为‘对某种物体产生了一种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畏惧心理的本能’”[2](P29),并且随着社会时代文化形态的转变,逐渐形成为“一种有它自己特性的力量”[2](P30),“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变成了法律”[2](P30)。所以,在“我”试图战胜禁忌的过程中总是感到恐惧,在第一条鱼上钩后也不直视它的眼睛,内心一直处在矛盾纠结中,钓鱼但又不想钓到很多,所以选择清浅的小溪,可是世上的事总是事与愿违,小溪底下可能是深潭,竟然很轻易就钓着了很多鱼。“我”突然感到一种仇恨和恐惧感袭来,“因为不是我想钓鱼,而是很多的鱼排着队来等死。原来只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想活的人,想不到居然还有这么多想死的鱼。”[1]在“我”的信仰世界里依然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起作用,而且当“我”面对钓上来即将死亡的鱼时,那种发自心底的孤独与恐惧、仇恨与痛苦让“我”瞬间变得虚无,一次次拿起令自己都感觉恶心的鱼饵,开始实现对自己民族禁忌的超越,实现一次精神的历险。阿来在作品中能够把文化禁忌和现实日常生活的描写相融合,并且能够通过文化禁忌的阐释对藏民族历史与现实、宗教与生活进行超越。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和调适
阿来的中篇小说《鱼》中,从柯村文化变化发展的痕迹来看,传统与文明的矛盾和调适正在逐步得以实现。小说为我们展现了柯村人既美好、善良又保守、落后的双重性格,柯村人生命力旺盛,生命的光芒在小说中通过“鱼”原型意象的塑造得以体现。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与自然界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环境的征服和适应是人类本身及其所创造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孟得斯鸠曾说:“一个民族的道德风貌、风俗习惯,甚至法律制度和政体,都是由这个民族所居的地域的大小、气候、土壤等地理环境决定的。”[3](P49)所以,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文化心理的生成也必然和地域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柯村人思想的固执、落后与其原始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但大自然的启迪也让柯村人焕发着原始的生命活力,闪耀着人性光芒。只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柯村中的寡妇秋秋和小叔子以及遵照秋秋丈夫生前嘱托来照顾秋秋母子的昂旺曲柯才能融洽地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鱼是作家根据藏民族的文化传统演绎出的一个原型意象,在柯村人的情感世界中,鱼是可厌与可怜的情感交织,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原型意象,并且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中对“鱼”原型意象的象征意义解读包含着多种可能性。阿来在作品中阐释出有着鱼禁忌的柯村人和吃鱼的一些民族人对鱼的观念以及因为鱼所遭遇的不同命运。夏佳惧怕鱼,但他一生都在克服这种恐惧。他的恐惧是因为十六岁时在天空中看到一条被鹰叼起的鱼,苦苦挣扎的鱼最后从空中摔下,鱼腹破裂,当天夏佳的伯父也就是秋秋的父亲去逝,夜晚他梦见伯父变成了鱼。对于柯村人来说,鱼是缺乏美感,令人生厌的东西,而且还会让人产生不祥之感。对于禁忌的超越,夏佳努力克服恐惧,在人们祭祷伯父的时候,他选择去看那条让他产生恐惧的死在麦地里的鱼。然而夏佳对于禁忌的超越并没有成功,看到吃鱼的情景,他最终跌落河里,没有完成对禁忌恐惧的战胜。夏佳多次梦见鱼,对藏民族来说,梦见鱼是不祥的征兆。夏佳第一次梦见鱼是在栅栏的阴影下假寐,忽然朦胧地感到一条条鱼游进脑海中,顿时感到心烦意乱,也就在这年冬天,现代文明走进柯村,汉文报纸、书籍、连环画和一些文件渐渐出现,鱼眼夺科也是从这些“文明物”开始认识汉字,说出母亲是地主婆的预言。
鱼是令人敬畏而又神秘的东西,“引人注目的是那双鼓突的眼睛:明亮、天真,以及遗传性的深重的忧伤”。[4](P76)遗腹子夺科因为长久地观鱼,他的眼睛变得也和鱼眼一样,被柯村人叫做鱼眼夺科。1965年,这个有着怪诞不祥的鱼眼的夺科家被划为地主,这个家族的命数算是尽了。索南家族开始兴盛后,一群村外的伐木工人也进驻柯村,这些人都属于食鱼的民族。昂旺曲柯虽然不属于食鱼的民族,但他已经接受了吃鱼的事实。在昂曲旺柯的影响下,夺科征服了对鱼禁忌的恐惧,并且尝试摹仿钓鱼人,在无数次的演练后开始钓鱼。昂旺曲柯和夺科的死亡是现代文明的结果,新架的桥梁因为质量问题,使得昂旺曲柯和夺科随着河水暴涨后桥的消失一起消逝了。“阿来擅长将家族、家庭兴衰史和生活环境中那些‘有意味的形式’,作为自己窥探、认知和把握亘古、诡秘、浩瀚的历史律的具体方式与契机;进而逐步触摸本民族烙刻于历史表象上的深层心性结构,努力显示文明进程中千姿百态的历史生命的生长与衰微所带给历史本身的深刻启示”[5]。
“文化传统为艺术家提供了表现创造力的工具,并决定了所能采取的形式,如果离开了文化传统,艺术家就既不能思考,也不能表达自己。”[6]阿来生长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从小就受着藏民族神话、传说和寓言等文学传统的影响。成年以后,对于自己灵魂深处对“彼岸与此岸、神性与人性、精神信仰与肉体原欲、生与死、苦与乐等生命的必然之思”[7]借助汉语这一媒介形式表达出来。当下人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文化的态度很复杂,两种文化的重铸与整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阿来的立场既同情又有着批判,在批判的同情中提示了其作为本民族用双语写作的作家的情感立场。“我唯一想做的是在社会文明进步、物资生活日趋丰富的时候,寻找到一种令人回肠荡气的精神,在藏族民间,在怀旧的情绪中,我找到了这种精神。”[8]阿来说出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追慕和怀念。
三、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
鱼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在西方文化中,鱼也是基督教的象征,耶稣在渔村开始布道生涯,其12门徒中的不少人的最初职业就是渔夫,《圣经》中也有“得人如得鱼一样”的说法。谭恩美作为华裔美国作家,有着双重的文化身份,这使得她在其创作中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鱼意象来表达她对东西文化冲突与善恶冲突的理性思考,《拯救溺水鱼》就是通过鱼意象对这一思考的集中体现。
一直以来,相对于西方,东方都是沉默的“他者”,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民族与文化,并且还以拯救者的姿态站在他人面前,对于东方进行的是“妖魔化的描述”[9](P1)的想象,而且将“将东方变成西方卑贱的‘他者’,从而强化西方文明高贵优越的形象,以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9](P1)。东西方之间被隐喻为被支配者和支配者、被拯救者与拯救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小说中,作者用“拯救溺水鱼”的意象解构了这种关系,倡导的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都应该彼此尊重和关爱。另外,从美国组团成员中可以发现,虽然他们个个都是拥有金钱和地位的成功人士,但都处在爱情和性关系的矛盾困惑中,都是失败者,物质生活的丰富抵挡不住精神世界的贫乏,现代文明带给人们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工业科技给人带来的一种无形的压力及烦躁,让人类最初的原始野性失去了自由存在的空间,感性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受到限制。究竟谁是拯救者,谁又应该被拯救,这还是个疑问。
小说的叙事采用了西方文学的古老模式:一群来自美国文明世界的西方人闯进古老而神秘的东方世界后所遭遇的种种戏剧性的离奇事件。但她采用了和以往的小说不同的全知全能的幽灵叙事视角,故事空间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主要人物也从华裔家庭变为美国白人。美国旧金山的十二个所谓的成功人士集体来到神秘而古老的东方旅游,在中国云南和兰那王国的旅途中陷入了种种尴尬困境和遭遇了诸多矛盾冲突。比如在兰那“无名之地”,他们对在那里深受苦难的部落表示同情,竭力帮助他们去美国从事商业性的演出活动,可是结果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因为他们的拯救反而让部落人被王国政府军队所枪杀,加速了他们走向死亡的深渊。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还因为拯救别人而遭到绑架,最后,无可奈何地被迫结束旅行,被救出后又回到原本生活的城市——旅行的出发点美国旧金山。这一切看似偶然所致,但仔细分析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这些矛盾、冲突事件的根源主要是由于不同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政治和种族等的差异而产生的误会。
文化冲突必将导致大规模战争,给人类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避免悲剧发生的关键是增强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用尊重和宽容的态度相互沟通。乐黛云说:“文化相对主义赞赏文化的多元共存,……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10](P32)所以,理解和尊重是与异质民族、文化进行交往时最重要的,不能用自我思维定势中的文化标准和价值去肆意判断和践踏他种文化,如果那样,我们就会如同“拯救溺水之鱼”一样愚昧可笑。谭恩美透过“拯救溺水鱼”的意象想要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关于对待异质文化所应该持有的态度: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传统都有着与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相别的自主性与自适性,只有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受、了解异质文化,尊重文化的多元共生,才能保护人类文化生态和谐、促进世界文化发展。
四、“拯救溺水鱼”的苦难拯救主题
关于东西文化冲突的思考应该说是华裔作家最集中表现的主题,那么谭恩美通过鱼这一古老的原型意象是否只是为了表现东西文化冲突呢?笔者认为表现东西文化冲突这只是作品表层涵义,实际上还应该有着更深层的含义,深层的含义还是要通过鱼意象的分析来获得。《拯救溺水鱼》不但题目是一个哲学的悖论,而且整个故事也是一个隐喻。从题目来讲,“拯救溺水鱼”这个意象出现在小说最开始的一段寓意性很强的话中:
“夺取生命是邪恶的,拯救生命是高尚的。每一天,我保证要拯救一百条生命。我将网撒向湖里,捞出一百条鱼。我将鱼放在岸上,它们翻跳着,不要害怕,我告诉那些鱼儿,我将你们救起,不至于淹死。一会儿,鱼儿安静下来,死掉了。是的,说起来很悲惨。我总是救得太晚,鱼儿死了。因为浪费任何东西都是邪恶的,所以我将死鱼拿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有了钱,我可以买更多的网,用来拯救更多的鱼。”[11](P扉页)
这段话很明显地是告诉我们,在没有沟通和理解的前提下,以自己的生活习性和价值标准来判断作为他者的鱼类,这种只从自我思维定势出发的对他者的“拯救”,实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伤害,表现理性,实则荒谬。
小说以陈璧璧的幽灵之旅,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叙事。时间上,是一个灵魂的流浪到回归的生命历程。这个时间上的生命历程,从死亡开始,然后倒叙其成长经历,最后揭示出死亡的因由,整个叙事因为叙述者的幽灵身份而使整个故事没有终点,无限循环;空间上,陈璧璧和好友一起游历东方,出发点是美国的旧金山,首先历经中国的云南丽江,然后进入古老的兰那王国来到“无名之地”,最后又回到起点——美国的旧金山。空间上的地点是从西方开始又回到西方。小说的最开始,作者引用加缪和无名者的话——“如果缺乏了解,好意也会造成他人的苦难”[11](P扉页),向读者暗示出因为美国旅行团员们缺乏了解给部落人造成的悲剧命运的故事结局。所以无论是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还是结构布局,小说都呈现出往复循环的圆形特点。杨义[12]认为,圆形轨迹是中国人宇宙论和生命论的动态原型,圆形结构的运转和破毁,实际上是由阴阳两极提供内在的驱动力的。而两极性的构想,最初是与男女两性关系相联系的。
作者这种独具匠心的圆形结构布局也与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论述相符合,而且在诺伊曼在对大母神的原型分析中,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原型意象,就是乌罗伯洛斯(Uroboros),即大圆,它的原始意象是一条用嘴咬住嘴巴雌雄同体构成“8”字盘绕着整个世界的巨蛇,它是“统一的原始本原的象征”[13](P18)。大圆意象的一个原型具象就是中国的太极,而太极就是由双鱼构成,黑白二元既对立又共生,在交互作用中衍生出天地万物。“希腊哲人柏拉图曾说:宇宙的造化者,把自然造成球体,这球形的半径由中心至圆周,处处相等,这是一切形体之最完美者”,[14](P154)这个大圆的圆心是“爱和尊重:人类和动物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母亲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以及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都需要尊重和关爱。”[15]这个由爱与尊重形成的大圆正如谭恩美所说,是一个“应该保持神秘,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传奇。”[11]这可以理解为美国华裔作家情不自禁的深层心理结,对文化之根的寻找,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她用南夷人的信仰告诫人们,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生命的摇篮和沃土,放弃根本而信仰他国文化,最终会导致文化之根的丧失。这是对母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同,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对于彼此民族、文化的认识只有“简单的同情是不够的,你应该成为那个人,理解那个人的生活和希望,你应该感受那种想要活下去的绝望。”[11]只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理解“拯救溺水鱼”这个隐喻的真正内涵。
[1]阿来.鱼[A].阿坝阿来[C].北京:工人出版社,2004.
[2][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文良文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3]丹纳.艺术哲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4]阿来.鱼.孽缘[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
[5]罗庆春.族性人性诗性——阿来小说《孽缘》、《鱼》叙事解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8).
[6]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M].靳大成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1992.
[7]刘琴,毕耕.阿来小说中的意象分析[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6).
[8]黎曦.存在并表达着——盘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J].中国民族,2002(6).
[9][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0]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1][美]谭恩美.沉没之鱼[M].蔡骏,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12]杨义.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J].中国社会科学,1994(1).
[13][德]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M].李以洪,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4][英]卡纳.人类的性崇拜[M].方智弘译.海南: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15]朱颂.闪光的球体:《沉没之鱼》主题的多重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8(6).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106.4
A
2095-0438(2015)11-0028-04
2015-05-26
孙胜杰(1982-),女,黑龙江大学在站博士后,黑龙江东方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地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藏地汉语长篇小说研究”(14CZW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