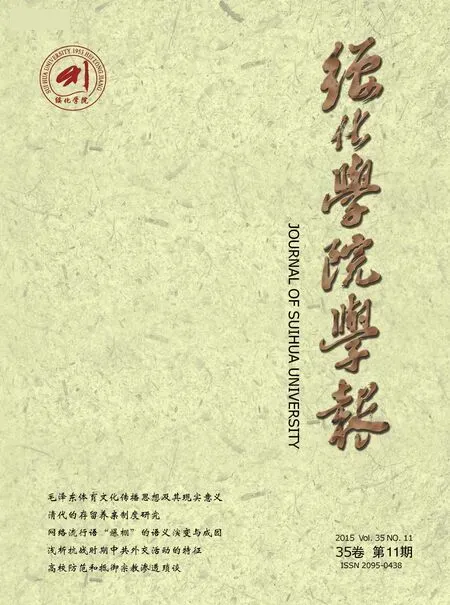不一样的美少女:《鸫》的主人公形象分析
许军(洛阳外国语学院 河南洛阳 471003)
不一样的美少女:《鸫》的主人公形象分析
许军
(洛阳外国语学院 河南洛阳 471003)
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多描写失去至亲至爱的孤独少女,她们在拥有超能力人物的帮助或凭借自身的神奇预感与梦境,获得治愈、积极成长。而《鸫》的主人公——羸弱的美少女鸫——却颠覆其一贯的创作模式,被塑造成为一个爱憎分明、激烈霸道的美少女。这个形象与日本传统女性的隐忍含蓄相去甚远,也不同于其他“吉本女孩”的颓废无为。鸫象征了短暂热烈的青春,其中寄托着吉本芭娜娜的无限追忆和留恋之情。由于主人公形象和创作意图不同于其他吉本小说,作家不得已一改惯用的主人公视角,采取主人公的表姐玛利亚充当见证人视角来叙述文本。
鸫;粗野活泼;追忆青春;见证人视角
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在中国深受20岁左右年轻女性的追捧,这与其创作人物的形象密不可分。在她细腻的笔致下,现代社会里少女的孤独心态、与他人的交流与和解、预言式的梦、将主人公治愈的超能力现象或人物,构成一个水墨淡彩的世界,以一种和风细雨式的敲打触动了都市人的灵魂。主人公的情感淡漠、行为疏离,这种点到为止的叙事反而引起读者们更多共鸣。每个读者都能从主人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在阅读中与主人公携手同行,共同完成心灵的成长。也正因如此,吉本笔下的少女有着以下几个显著特征:1.失去至亲至爱之人,此后生活将无依无靠(《厨房》中“天涯孤独”的美影);2.不喜交际、活动较少,存在感不强,性格特征不显著(《白河夜船》中深陷睡眠的寺子);3.心思敏感、拥有奇特的预感或超能力(《哀愁的预感》中找寻身世之谜的弥生)。
然而,《鸫》[1]的女主人公——鸫——则违背了以上原则,成为吉本芭娜娜小说中别具一格的人物。她住在家庭旅馆最好的房间,父母健在、对她迁就宠溺,姐姐阳子温柔体贴,恋人恭一善良包容。她不存在吉本芭娜娜其他作品中少女孤苦伶仃的预设前提。在撕掉了死亡、预感、超能力等“吉本标签”后,《鸫》讲述的是平凡世界里一个普通女孩子的故事。梗概如下:主人公鸫,美丽、羸弱、粗鲁刁蛮,与恭一谈恋爱时直率投入。一群暗恋鸫的不良少年殴打恭一,并杀害了他的爱犬。鸫为了报复,瞒着众人挖了一个大陷阱,费尽心力而累倒住院。故事发生在海滨小镇,有阳光沙滩、夕阳焰火。可以说,这部小说的底色是透明的、灿烂的、流光溢彩的,它流露出淡淡的追忆之情,赞美了少女们美好的青春。与其说这是部“治愈系”小说,倒不如“夏日风物志”的表述更为恰当[2]。
一、温柔谦让的传统女性与霸道粗俗的鸫
在日本传统男权社会制度下,社会习俗对女性的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进行约束和限制。正如日本谚语“男は度胸、女は愛嬌”(男子凭勇敢,女子靠温柔)所说,女性要表现出温柔、恭顺和可爱的特征。从这点看,鸫绝对是另类的日本女性。参阅小说,笔者试举几例鸫的语言和动作,来分析鸫的心理。
“おまえら、あたしが今夜ぽっくりいっちまってみろ、あと味が悪いぞ-。泣くな,鸫使用的是男性用语。而日语中存在男女性别语,女性使用男性用语是极为不雅的。鸫的举止粗野,没有“女生应有的样子”,如“つぐみが立ち上がり、冷蔵庫うへペタペタ歩いて行って、昔、酒屋でもらったミッキーマウスのグラスに麦茶を注ぎ、ごくごく飲んだ。そして空のグラスを磨きこまれた流しにことり、と置いて言った。[3](P66)”(译:鸫站起来,啪嗒啪嗒地走到冰箱前,拿出很久以前从一个居酒屋得来的有着米老鼠图案的玻璃杯,倒了一杯麦茶,一口气喝完,然后把空杯子扔进了被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洗碗池里。)此外,“家の中では相変わらず家族に当たり散らし、ポチのえさをけり散らしてあやまりもせず、お腹を出してそこいらでぐうぐう寝ているのだが[3](P120)”(译:鸫在家里时,依然是对谁都乱发脾气,小小的狗食被她踢翻了,她连个歉也不道;不管在哪里躺下就睡,肚皮露在外面很是不雅。)这一串动作,即使在讲究礼仪的日本以外的国家,也会被视作没有教养吧。值得指出的是,鸫想尽办法故意把粗俗不堪的一面展露给家人,而在外人面前则表现乖巧,讨人喜欢。这意味着,鸫自身知道且能够实现社会对她的角色期望。她对家人表现出的刁蛮任性,是其本性,抑或说其刻意为之?若是有意,是何意图呢?
首先,不可否认,家庭对鸫的溺爱是形成其刁蛮性格的环境因素。出生时被诊断活不长的鸫,受到周围人的百般宠爱。但它无法解释鸫缘何在外人面前注重礼貌。事实上,鸫害怕的是被遗忘。正如玛利亚所说,“つぐみがあんなに確かな存在に見えるのは、か弱い肉体に抵抗して暴れる底力のせいに過ぎない。”[3](P11)(译:大家之所以对鸫的存在印象深刻,只不过是因为她在用那种强悍的方式抵抗着躯体的病弱而已……)她不愿因身体羸弱、生命逐渐干枯而被人遗忘。她用过激的言谈举止博得亲人的注意,冒犯他人也要强过被人同情然后忽略。同时,鸫知道家人会无私地包容她、谅解她,才会对家人横冲直撞,在外却规规矩矩。可以说,鸫的潜意识里既有对被人忘却的恐惧,又有对家的无限信赖。
二、懒散无为的“吉本女孩”与热烈多动的鸫
吉本芭娜娜塑造的女性,大多存在感薄弱。她们形象模糊,淡若烟尘。遇到打击后,消极慵懒、无为度日。《白河夜船》的主人公寺子最为典型。她是有妇之夫岩永的情妇,对彼此的未来怀抱不安。没有工作,睡眠占据了她几乎整天的时间。她用嗜睡回避现实,结果越发深陷其中,险些被睡眠“反噬”。与外界接触不多,疏于行动,缺少存在感,这些特征同样也出现在《厨房》失去亲人的美影,《哀愁的预感》深居简出的雪野等主人公身上。
然而,鸫的生活却是热烈活泼的。“つぐみは過去を振り向かないからだ。つぐみにはいつも「今日」しかないからだ”[3](P57)(译:她是一个不会纠结于过去的人,生活里只有“今天”)。她喜欢恶作剧,乐于探险,爱憎分明。她发怒的样子,不顾一切,就像狂人一样。跟一个讥讽她的女生打架时,“あの時のつぐみの全身から発散していた強い輝き、そして相手化、もしくは自分を殺しかねないような憎しみのエネルギーをたたえた瞳を。”[3](P159)(她全身散发着强烈的光,眼睛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让人害怕:她会不会杀了那个女孩儿?甚至杀了她自己?)
有一天深夜,鸫和阳子、玛利亚三人去海边散步,一直走到邻近渔村才回来。一片黑漆中,玛利亚和阳子是手拉着手摸索着往前走,而鸫呢?“一人ですたすたと歩いていた。その足取りがあまりにしっかりとしていて、とても闇の中を歩いているようには見えなかったことをおぼえている。”[3](85)(译:一个人健步如飞。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她的脚步是那么稳健,迈出去时毫不迟疑,那样子实在不像是在黑暗中走路。)
鸫与恭一谈恋爱时,感情也是直率奔放的。与恭一心意相通后,鸫主动告白,“つぐみが恭一をまっすぐ見ていった。「お前を好きになった」”[3](P119)(译:注视着恭一的眼睛说:‘我喜欢上你了’”)。她甚至畅想婚后生活,“「恭一、あたしと結婚してさ、ホテルの庭中犬だらけにして、『犬御殿』と呼ばせよう」つぐみが無邪気な声で言う。”[3](P177)(译:“如果我们结了婚,就在饭店的庭院里养一群狗,建一个‘狗的宫殿’。”鸫天真地说。)送别恭一时,她的反应很激烈。“つぐみは途端、「握手なんて求めたらぶっ殺す」と言って恭一の首に抱きついた。”[3](P199)(译:鸫突然说,“如果你要是和我握手的话,我就杀了你。”说完,扑上去抱住了恭一的脖子。)
尤其是小说的高潮——鸫耗尽心力深夜独自挖了一个大大的陷阱,制定了周祥的计划,报复杀害权五郎(爱犬名)的不良少年,事后病倒入院、生命岌岌可危——这个过程中鸫“その妙にまっすぐなそしてどことなくひねくれた方法がひどくつぐみらしくておかしかった。”[3](P120)(译:那难以形容的义无反顾的气魄和诡计多端的手段),越发凸显了她强烈的生命之光。
就像玛利亚所观察到的那样,“感情が肉体を引っ張りまわしているようで、刹那に生命を削るようで、まぶしかった。”[3](P120)(译:鸫的肉体被感情牵引着旋转,好像瞬间生命就会被耗尽似的。)她竭尽全力去感受、去体验,去对抗无常且不堪一击的人生。这样的女孩与其他“吉本”女孩大相径庭。她的成长不借助旁人的点拨,不依靠神秘玄幻的梦。躯体的束缚没有让她颓废消沉,反而清楚认识到时日不多,应纵情生活。她看似霸道,实则通晓人情。外公去世,“我”悲伤难抑,鸫竟然仿照外公口吻写信投递到“妖怪信箱”来安慰“我”。她这种恶作剧的方式固然乖张,却也用心良苦。
三、从创伤治愈到隐喻青春
吉本芭娜娜一直在努力实现作家对社会的作用与责任。她认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写书治愈人们绝望的心理,挽救更多年轻人生命。尤其着力刻画现代都市年轻女性的空虚无力,以及她们努力转变积极重生的过程,使读者在阅读中,既感同身受、产生强烈的共鸣,又能从主人公身上汲取力量、重塑生活的信心。以《大海》为例,此类小说如同潜水,开篇阅读时,读者感到千钧重压、呼吸困难。继续阅读则能豁然开朗,看到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心情随之放松且愉悦。而阅读《鸫》,更像一场冲浪,有刺激、有危险,但大体是阳光明媚、令人兴奋的。
吉本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美少女,她不再背负沉重的创伤,不再经历暗黑苦闷的折磨,而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明亮、美好、易逝、至情至性,像上帝精心创造出来的洋娃娃。在这部小说中,吉本抛弃了对沉重死亡和疏离人际的书写,转向对潇潇洒洒青春洋溢的赞美。她在后记中写道:“夏はいつも、西伊豆に家族と行きます。10年以上、同じ場所、同じ宿に通っているのでそこは私にとって故郷のようなものです。”[3](P236)(译:每年夏天,我们一家都会到西伊豆去度过。已经十多年了,我们总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同一家旅馆。所以,那里就像是我的故乡一样。)这个“故乡”大概是所有青春已逝之人的原乡吧。海滨小镇的夏日少女,热烈、激情、自由、奔放,“私にとってこの夏は過去の懐かしいことのすべてを凝縮したエッセンスだったのだ。[3](P217)”(译:是所有往昔那些令人怀念的东西浓缩而成的精华)。鸫隐喻了每个人一生只此一次的青春。当然,鸫身上有着任性蛮横、恶言恶语、行为粗野的一面。可青春不正是莽撞、轻狂的吗?而家人对鸫的宠爱隐喻了吉本芭娜娜对青春的誉美。这点无需过多解释,有谁在追忆青春时不是目光柔和、无限怀念的呢?
四、从主人公视角到见证人视角
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主人公设置为叙述者,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的模式讲述故事。然而,《鸫》中的叙述者变成了次要人物——玛利亚。叙事学将之称为“次要人物内视点”或“见证人视点”。相较惯用的“主要人物内视点”,吉本芭娜娜为何要变换视角呢?
徐岱认为[4](P312),第一人称叙述以概述手段为主干,且叙述者“我”总是作品中的一个具体人物。其长处在于强化叙述趣味,便于描写其他人物。第一人称叙述的真正重心其实不在“我”而在“我”周边的其他人物,处于光圈中的那个“我”其实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主角。作者常常只能牺牲叙述者的性格化来换取叙述话语的艺术化。这就合理解释了以主人公为第一人称叙述的其他吉本小说中,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反而不那么鲜明的原因。在《鸫》中,吉本选择玛利亚担任叙述者,反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鸫既惹人怜爱又蛮不讲理的性格。玛利亚是个细心的旁观者,也是个公正的评价人,寄人篱下和表姐的身份使得她能够近距离观察鸫的言行举止,同时能够客观审视和评论鸫的个性。
假设文本以鸫为叙述视点,鸫的内在统一性必然使她意识不到自身性格的矛盾和冲突,小说的精彩至少要折损一半以上。此外,鸫的内心活动而非外在行为将占据大段篇幅。情节设置也将发生较大变化,如解开谜底般倒叙的报复计划,在主谋者鸫的叙述下,可能会成为平淡无奇的事件罗列。
之所以选择玛利亚而非鸫作为文本的叙述者,除上述原因外,还应考虑一点:鸫隐喻的青春往往是不自知的。试问,谁会赞美青春呢?不是恰值青春的少男少女,而是青春不再的追忆人。他们意识到青春是美好和冲动混合的体验,是纯粹自我的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吉本芭娜娜坦言:“つぐみは私です。この性格の悪さ、そうとしか思えません。”[3](P236)(译:鸫就是我。这么不好的性格,除了我,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人。)其实,叛逆任性、自我中心,存在于每个人的青春里。而吉本芭娜娜借助玛利亚之口,与鸫站在相同的空间里,像录像般清晰再现了本已远去的青春,艺术化地将时间维度统一于空间维度。“这个世界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离别,而每一个离别我都不想忘记。”也许,正是不想忘记与青春的离别才是吉本芭娜娜创作的初心吧。
[1]吉本芭娜娜.鸫[M].弭铁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2]周阅.吉本芭娜娜的文学世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3]吉本ばなな.つぐみ.中央公論社,1989.
[4]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106.4
A
2095-0438(2015)11-0035-03
2015-05-26
许军(1991-),女,河北邯郸人,洛阳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玛利亚·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