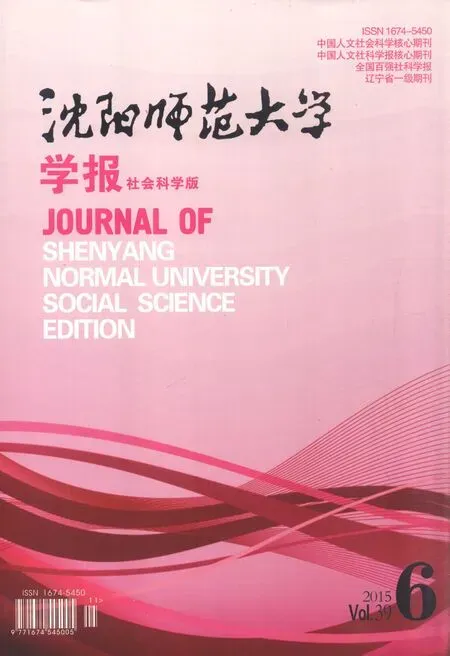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的困境与突围
王颖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的困境与突围
王颖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受西方生态文学观的影响,中国生态文学批评多集中于工业文明之后问世且强调“自然中心”的当代文学作品,一些学者尝试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生态解读,被指出有使生态文学判别标准和生态批评泛化之嫌。生态批评对象的固化致使古代小说的生态研究明显不足。拓宽生态批评的视野,打破传统认知,摆脱生态文学时间观念约束的同时,深入挖掘“生态”之内涵,将涉及生态危机表象书写和根源探索的作品均纳入研究领域,是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突围的首要选择和必由之路。
古代小说;生态批评;困境;突围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各种资源减少或枯竭等问题的频繁出现,人们对生态问题变得尤为关注,生态学、生态文艺学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关心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生态小说创作与研究一时成了当代文学的热点,并迅速成为整个生态视野下的文学批评的中心。与之相比较,古代文学的生态研究却有些受冷落,致使同样为叙事文学的古代小说的生态批评相对不足。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大量关注生态问题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当今的生态救赎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客观价值的存在与实际研究的不足不得不令人思考以下问题:古代小说生态批评薄弱的原因是什么,古代小说生态研究中存在哪些问题,古代小说生态研究如何突围?本文试从这几个问题入手展开详细分析。
一、生态文学批评对象的固化与古代文学生态批评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生态文学批评即已展开,受西方生态文学观的影响,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基本上遵循“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的原则。在具体的实践中,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2],成为研究者集中关照的对象。由于“自然取向”和“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强调,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当代文学相关作品上,因为这部分作品或者较好地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日渐凸显的生态问题,或者深刻反思了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与文化根源,生态意识与生态思想表达十分明显。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及研究与西方生态文学理论所强调的“生态文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生态文学研究产生的现实背景是生态恶化和生态危机”相吻合。反观之,强调“自然中心”,以当代作品为批评对象的实践也对生态文学的研究理念起到了固化的作用,以致于一提到生态文学批评,学界便指向当代文学中那些以自然为中心,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相生关系的作品。这种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固化,致使生态文学批评将古代文学作品排除在外。一些学者也曾尝试对古代文学范畴内的作品进行生态解读,如《庄子》、陶渊明的田园诗、王孟的山水诗、《聊斋志异》等,但很快便被指出这些作品或者是“人学”的自然陪衬,或者是“文化上的怀旧仿古”[3]。所谓人学的自然陪衬,即以人为中心,作者对自然的态度不过是借用,“自然描写”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抒发人的情感,刻画人物的性格,笔下的自然只是便于人的主体意识与主观情绪传递的人文意象和符号;而文化上的怀旧仿古,则是人在社会中遇挫后为了逃避现实,用文字中营造出来的类似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远古先民世界,作用是为文人提供一个疗救精神创伤的心灵避难所,究其实质,文化仿古的自然书写还是为人服务。因此,将古代文学作品纳入生态文学研究范畴,无疑使生态文学判别标准和生态文学批评有泛化之嫌。尽管批评者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但生态文学研究的实际成果足以表明:学者们普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生态文学理论并对国内相应文学资源展开研究,古代文学与生态文学的标准尚有一段距离。
二、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的现状与问题
生态文学批评的大环境使得古代文学的生态研究相对不足,但不等于没有研究成果。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态研究成果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问世,如肖波的《浅议老庄的生态伦理思想》(《医学与社会》1996.9),就老庄对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独特理解,即“主张崇尚自然,不要盲目伤害自然”论述了老庄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文明社会的警示意义;黎明的《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生态美》(《广州大学学报》1999.3),从中国山水田园诗表现的对“蓬勃生命力的赞美,对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的展示,以及对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生命间和谐关系的感悟”,来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家的生态智慧和对美的敏锐感受;王先霈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文学评论》1999.6),分析了古代诗文和文论有关绿色的吟咏、描写和论述,总结出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生态主张,即人要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养互惠等等。总体上看20世纪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古代诗文的整体观照和老庄作品的研究,而古代小说的生态批评鲜有人触及。
进入21世纪,古代文学的生态研究延续前一时期关注诗文领域的传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作家的作品倍受青睐。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小说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聊斋志异》、《西游记》、“三言”、“二拍”、《红楼梦》等作品的生态批评成果多有呈现。如沈传河的《〈聊斋志异〉生态展现之阐释》(《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7.1)一文认为“小说中人与自然物奇异的对话无不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对话更应被界定在良性的范围之内。幻化的笔法,使小说中的自然物得以获得其生态主体性,这对于当今生态文化之建构无疑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刘衍青的《〈聊斋志异〉生态表达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宁夏社会科学》2009.3)尝试从《聊斋志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意识的具象化演绎与延续,对创作主体心理疗救、对接受主体心理的平衡作用等方面,探究了作品生态表达内容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刘国和、邓永芳的《〈西游记〉生态想象及其文化意蕴》(《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4)从生态想象的角度,对《西游记》所表达的对美好生态世界的向往及体现的生态文化自觉予以论析;杜娟的《大观园——生态美学视角下的一种解读》(《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4)对《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景观布设多取法自然、大观园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生态美学观念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大观园实现了红楼女儿们的“诗意的栖居”。与上述个案研究相比,杨立琼的《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明清经典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9)将明清的七部经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作为整体考察对象,挖掘了小说生态描写的主题、生态表达的方式与生态思想的价值。文章最为可贵之处是突破了生态批评界遵循的“自然中心”原则,将小说的生态主题分为“人与自然相辅相生”“人与社会密切联系”“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三个方面,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为古代小说生态批评视野的拓展提供了不小的启示。只是论题定位于经典小说而忽略其它涉及生态描写的作品,也使文章对明清小说的生态研究显得相对狭隘和单薄。
总结古代小说生态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尽管受西方生态文学观的影响被生态批评界所排斥,但研究者却在努力找寻合理的对接点,使自己的研究既对古代小说的生态资源有所挖掘,又使生态批评界能够接受。从上面提及的论题中可以看出,用“生态表达”“生态想象”“生态展现”“生态解读”来命题并展开研究,挖掘作品蕴含的生态思想、生态精神是大家普遍的选择,而且文中也没有径直将作品定性为生态文学。这种规避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智慧,而且也从侧面对生态文学批评做出了较好回应。只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虽美但毕竟是有束缚。受生态文学所强调“自然中心”的影响,古代小说生态研究取得些成绩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仅限于明清两代涉及自然描写的作品;研究对象相对集中,经典性作品之外的相关小说少有论及。二是个案研究多,整体性把握少,且研究深度有加强的空间。近年来的研究往往是单篇作品解读多,总体性关照少,专门针对古代小说进行总论式研究者更是鲜见,有些研究仅仅触及明清小说个别作品的生态美学的外在表现,并没有深入探讨其内在意义和价值,这就使研究流于表面化和浅显化。
三、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的突围
古代小说生态研究呈现的特点,与古代小说作品数量浩繁梳理起来较为困难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受生态文学概念的影响所致。生态文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生态文学及其研究产生的现实背景是生态恶化和生态危机,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强调“自然中心”,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及生态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范畴之事,与古代小说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这种认知导致许多学者对古代文学生态批评的疏离,即使有学者从生态美学视角对古代小说作品予以关照,也是相当谨慎地行文,以免招致诟病。很显然,与当代小说的生态研究相比,古代小说的生态批评处于十分困窘的境地。如何从窘境中突围出来,是古代文学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以为,既然生态文学创作及生态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是从文学的角度唤醒人类对自然的关注与尊重,进而成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理想,那么凡是与之相关的文学书写都应该被关注,而不应过多地强调这类文学书写产生的时间问题,忽略了作品所蕴含的生态资源及其对当今全球性的生态救赎所具有的参考价值。众所周知,古代小说领域涉及生态书写的作品数量相当可观。从小说成熟的唐代起各种文体的小说作品都对生态问题有所关注。传奇小说《玄怪录·柳归舜》描绘的君山胜境、《传奇·孙恪》叙述的袁氏化猿归山“而复反视”的故事都是时人对质朴自然的向往和人性认知的反映;话本小说《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既承继了唐及唐前小说生态书写对自然环境的偏好,又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生与冲突有了进一步的描摹,为后来明清小说的生态书写带来了启迪。明清长篇章回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书写的自然之境和人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挣扎不仅显示了人们对生态自然的怀恋,更揭示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的权利的实现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平衡法则等等。如此丰富且对当代生态问题有着重要参考意义的生态资源由于观念的影响而被轻忽实在是遗憾之事。因此,打破传统认知,拓宽生态批评的视野,不受生态文学时间观念的约束,将涉及生态问题书写的作品均纳入研究领域,是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突围的首要选择。事实上,用引进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关照中国古代文学并突破理论所框定的时限,学界并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将60年代确立于法国的叙事学借鉴过来,开始了本土化的研究,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都是借用西方叙事理论对中国文学(主要是古代文学)资源展开研究并取得成功的案例。叙事学本土化的成功缘于化用者“在双方的理论构架中寻找共相,在相互的发明和贯通中建构出自己的研究模式”[4],即研究者并没有完全拘泥于西方理论,而是既不违背西方理论的一般原则,又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更适用于中国文学的实际和话语形式。叙事学本土化研究的成功经验为古代小说生态研究的变通性尝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打破生态文学所谓的“时限”,将蕴含生态意识与生态思想的作品全部纳入批评视野并展开深入的研究,不仅可行,而且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有丰富与深化的意义。其次,深入挖掘“生态”内涵,除了将涉及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外,那些探索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及人的精神与心灵归属等问题的作品也纳入研究领域,是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突围的必由之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对“生态”内涵的理解多停留于“自然”“人与自然”层面,从生态学、生态文学产生之初的界定看,这种理解有其合理性,但如若打破生态危机的“工业化”背景,单就“生态问题”的发生及根源的探索来看,这种理解有以偏盖全的倾向。从近年来出现的生态问题中不难发现,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只是生态危机的表象,究其根源实则与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及人的精神归属等问题都有直接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体的人乃至人类的精神归属出现了问题,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过分膨胀的物质享受而肆意破坏了整个世界的正常的循环,这世界既包括纯粹的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被国人普遍理解为“自然之道”的循环演化思想,曾被美国著名的学者卡普拉给出了如此评价:“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5];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也不仅仅是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应遵循这一规律”,其中也蕴含了“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我们深入挖掘生态内涵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实际也很好地诠释了生态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如果将明清之前的小说所演绎的生态内涵归于人与自然相辅相生、互养互惠的思想,那么明清及以后的小说则更多地关注了人与社会冲突与融入及人的精神归属等生态问题,《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等作品皆是高度关注这些问题的作品。既然有理论依据又有资源可供研究,拓展生态的内涵,在古代小说界不但可行,而且势在必行。深入挖掘“生态”之内涵对古代小说展开生态批评,不仅对生态危机的根源的把握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且对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当代精神文明建构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J].文学评论,2009(1):66.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
[3]高旭国.“自然描写”:生态文学判别上的误区[J].学术论坛,2010(8):77-99.
[4]陈跃江.读《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J].读书,1989(6):100.
[5]FRITJOF CAPRA.Uncommon Wisdom:Conversations with Remarkablepeople[M].Simon&Schusteredition,1988:36.
【责任编辑 杨抱朴】
I207.4
A
1674-5450(2015)06-0083-03
2015-06-03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L14DZW 018)
王颖,女,辽宁铁岭人,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