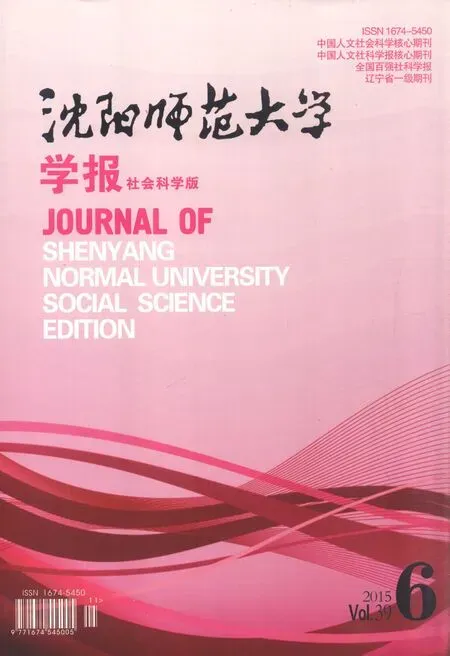文化危机与世界重建
——马尔库塞新感性思想
李闯,张岩,2
(1.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110036;2.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沈阳110031)
文化危机与世界重建
——马尔库塞新感性思想
李闯1,张岩1,2
(1.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110036;2.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沈阳110031)
近代科技革命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物质日益丰裕,但人们的理想、价值、信仰却出现了缺失和危机:科技理性、工具理性极度张扬,理性作为反思、批判、革命的含义被忽视与遮蔽,人们生存的真实感丧失,对现实盲从、感性被压抑、思想走向“单向度”化。有鉴于此,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社会状态与其文化状况进行反思,以寻求人的解放之途。新感性是马尔库塞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他把有关建立新社会的政治实践问题与人的感性解放的审美问题结合起来,期待建立人的心理层面的解放理论。但是他在论述新感性的超越性时,漠视社会环境的意义,没有给予社会现实环境对人的解放作用以足够的重视,把人的解放完全寄托在个人的感性解放,这未免走向了极端。
马尔库塞;新感性;重建世界;人的解放
一、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危机
(一)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危机
启蒙运动在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作用,它号召用“理性之光”来摆脱封建和宗教的束缚,将人类引向光明。然而,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却将理性逐渐变为科技理性与经济理性,并向着带有抽象性与经验性的工具理性迈进。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清醒地看到了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理性危机,他指出:“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在开始结出累累硕果时,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它所具有的精神意义。对人类和自然环境进行理性改造的自我表明,它自身本质上是一个攻击性的、好战的主体,它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控制客体。它是与客体相对抗的主体。”也就是说,这种主客体相分离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外在自然成为人类统治的对象,也造成人类自身之间的相互斗争,斗争的最终结果就是赋予理性作为统治工具的合理性,满足现实社会统治的需要。
工具理性成为发达工业社会使人单一化的强大力量。马尔库塞看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问题,他的批判直指现代文明的核心——启蒙精神。启蒙精神曾经代表张扬人的主体性,破除迷信,去除蒙昧,倡导科学技术的积极意义,但此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它使人受制于工具理性,其强大的控制力量不仅在公共领域,而且延伸到个体的私人空间,人性丰富的感受性在工业社会的机械化条件下被固化和单一化,个人只能顺从现实,只有接受的维度,批判的维度消失,不能对社会提出抗议。工具理性造就的文化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性,又不表现为政治性,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和需求。这种虚假的需求代替了人的真实需求,感觉被麻痹了。我们必须深思,科学技术的确能给人带来物质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但它同样也制造问题,它不会解决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等关乎生命的本体论问题,它置理性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二)现代社会感性的被压抑
马尔库塞明确指出,感性自身的含义在工业社会中发生了变异:感性接受性丧失了自我创造性和选择性,甚至主动地去迎合社会通行的时尚标准;在虚假需求意识支配下,人们获得的是虚假的满足,是不真实的幸福;劳动的异化否定了快乐原则,快乐被理性化了,伴随而来的是“工业文明”的诞生。
同时他还进一步认为:“在一个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人的感性是迟钝的”。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感性、需求都变为既定的了,人们在感知事物时,感受是给定的,也就是说人们所感受到的事物只是事物在现实中被给予或被使用的形式,从而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只是被动地去感知由现存社会所规定的变化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就是一种病态社会,它的病态就在于压抑、扭曲了人的丰富的感受性和批判性及创造性,造成了人的异化。在这种只有接受没有批判的单维度的社会里,人类所追求的幸福就是一种对现实的顺从,也就是相信现实就是合理性的存在,并相信现实不会辜负信念,这种“顺从”己成为社会技术合理化的一个方面,也赤裸地表现出感性的被压抑状态。
二、新感性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尔库塞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传统中关于感性的理解,积极肯定了马克思的感性意识,此外,他又吸收弗洛伊德的理论,并继承改造了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需求源于主体性”的观点,将个体的感官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出发点,建立起他的新感性观。他认为,自由社会必须植根于崭新的本能需求之中,进而从人的本能、生命、爱欲等层面来理解人的感性存在,将人的解放理解为审美维度的感性解放。
《爱欲与文明》一书初步描述了人类获得解放的蓝图,而《论解放》一书则进一步指出,人类获得解放必须由一种政治实践去实现。在《论解放》一书中,马尔库塞要求有“一种触及人的深层结构的抑制和满足之根源的政治实践,一种有步骤地脱离和拒绝权势集团的政治实践,以便按照新的原则来评价社会准则。这种实践必然破除了看、听、感觉了解事物的惯常方式,使有机体变的善于接受一个非攻击性的、没有剥削的世界的潜在形式。”而这种政治实践在马尔库塞看来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新感性”,正是由于这种新感性使人的视觉、听觉等感官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马尔库塞在专门论述新感性时指出,新感性己成了一个政治要素,它预示着当代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所谓“新感性”就是超越旧感性那种受压抑的、缺乏丰富性和自由性的感性。新感性要求从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与理性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因此,新感性产生于这样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时代中,曾经带来工业社会成就的抑制性合理行为完全成了退步的行为——只是在其“包含”着解放效能这一点上才是合理的。超越作为压抑感性的理性的界限,便出现了感性和理性的一种新型关系,即感性和一种激进意识的和谐。具体来说,“这种新感性表明生活本能克服了攻击性和犯罪感”。攻击性使他人不自由,“犯罪感”使自己不自由。因而,这种新感性通过对攻击性和犯罪感等一切不自由因素的克服,促进了“生活标准”的发展,“使人感到必须废除不义和悲惨”。由此可见,新感性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它将摆脱人的一切限制,促进了发现和实现物与人之间在保障和满足生活方面的种种可能,主宰了达成这一目的的形式和内容的种种潜能。
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这种新感性现在已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变成了实践,它们出现在反对暴力和剥削的斗争中。在马尔库塞看来,现实中所出现的这种建立新感性的努力,是为了争取新的生活方式,推翻一切现存的制度以及在这个现存制度基础上的道德文化,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的要求。一句话,是为了谋求一种“新的道德和文化”。对此,马尔库塞赞赏地指出,在这样一种建立新感性的努力中,终将出现一个新天地,一切感官的、好玩的、平静的和美的事物在这里都成了生存的形式。
可见,马尔库塞所推出的新感性这个范畴并非只是在文化领域,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政治革命的内容与手段的统一,新感性可以使人从现实的压抑中获得思想的解放。在这里,马尔库塞通过使用新感性这个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概念来论述艺术与审美的解放,赋予了其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品质。
三、“新感性”对世界的重建
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改变,更是一场人类感性的变革,是通过对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变革,进而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审美环境。这种感觉革命就是“培养一种新的感官系统”,就是对新感性的造就。因此,审美也罢,艺术也罢,它们对新感性的造就并通过“新感性”来重建一个新世界。
1.新感性对重建世界的规划与指导。在马尔库塞心目中,美和艺术能够打破旧世界、重建新世界。在这个重建过程中,新感性起到了一种“规划和指导”作用,美与艺术对世界的重建过程就是其所造就的新感性对世界的重建过程。马尔库塞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新感性作为规划和指导这种重建工程的核心理论、基础要求有一种新的语言体系来限定和传达并表现新的价值。同统治的连续统一体的决裂也一定是同统治的词汇的决裂。美和艺术所造就的新感性就是通过这种对传统作彻底否定的新语言来重建世界。
2.艺术与现实的间距以及对现实的超越。针对西方的文化革命中曾出现的那股反艺术论调,马尔库塞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提出了形式这一概念。马尔库塞对形式的界定,首先形式是艺术自身的本质属性,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形式是艺术中区别人类其他文化成果的本质规定,艺术因为形式的存在而获得自身独立存在的特有品质。在马尔库塞看来,形式不仅是艺术具有独立价值的特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形式看作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
马尔库塞在指出形式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固有特质之后,便着重论述由形式所决定的艺术与现实的间距以及对现实的超越。他认为,尽管艺术来源于现实,但艺术却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一个不同于当下实现的另一个现实。艺术用美与崇高、庄严与快乐超越于既定现实,使自己面对另一个现实:艺术所呈现的美与崇高、快乐与真理等不仅仅是从真实的社会中获得的,而且具有自己的更为真实的超越性。尽管现实的经验、价值和趣味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制约和影响着艺术,但艺术总是要超越现实并对现实进行升华,创造出高于现实的存在。比如最常见的艺术品,它所表现的形式往往都是现实生活中所不曾出现的景象。因此,马尔库塞心目中的艺术,就是一种与现实保持距离的另一个世界,它尽管来自于现实,从现实中提取材料,但是,它最终所造成的却是一个不同于现实的另一个世界。这种从既定现实而来又创造出与当下现实不同的世界,这就是艺术对现实的超越。
马尔库塞在阐述了艺术超越现实这个间离原则之后,着手对现实形式的艺术进行界定,他认为现实形式的艺术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对当下既定现实的美化,而在于建立一个与既定现实完全不同并与其相对抗的现实世界,也就是按照艺术的形式的规律进行创作的世界。他本人在《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一文中指出:支配艺术的形式,是无限多样的,但是古典美学的传统已给它们一个共同的名称:美。
在马尔库塞看来,美的观点,唤起了人类的理性,也唤起了人类的感性,唤起了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所以,所谓艺术创作也就是按照形式法则、按照“美的规律”对感性与理性分裂的既存现实的重建。所以,马尔库塞说,这种艺术,即按照形式法则重建的世界,是一条通向主体解放的道路,这就为主体准备了一个新的客体世界。正是基于这种对世界的重建,马尔库塞指出:艺术凭借它自己的内在动力,正在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3.在形式的法则下艺术对世界的重建。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按形式法则对世界进行重建,这里既有精神意义又有物质意义,是技术与艺术在世界总体重建中的契合点,是对商品化的剥削和美化的恐怖的拯救,是解放城市与乡村以及工业与自然的接合点。这里,马尔库塞表明了这样一个唯物观点,即艺术对世界的重建要依赖于对现存社会的总体的改造;依赖于一个新的生产模式、新的生产目标以及新型的生产者;依赖于人在约定俗成的社会生产劳动中形成的固定角色的消失。可见,马尔库塞在这里强调艺术对世界改造的同时,并没有忽视艺术最终受制于物质生产发展状况的唯物主义前提。马尔库塞把艺术对世界的重建具体落实到形式法则上,充实了艺术批评和解放的具体内容,使艺术对现实的批判和重建过程获得了现实的艺术形式,进而揭示了艺术的革命性。
四、对马尔库塞新感性思想的评价
(一)建立新秩序——揭示艺术和审美的力量
马尔库塞在对新感性的论述中揭示了艺术和审美的力量,认为艺术与审美对现实的超越过程就是形成新感性的过程,就是打破旧的感性、建立新的秩序的过程。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充实了以往艺术超越现实的具体内容,从而使艺术超越现实具有的鲜明的革命意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与审美固然是对旧秩序的打破,更是新秩序的建立。有关“新感性”理论的充实和发展还表现在揭示了艺术和审美的实践力量,看到了艺术和审美不仅能超越现实,而且还能对现实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突出了艺术和审美的感性特点
马尔库塞用新感性这个范畴去界说艺术和审美使人解放的理论很有意义的,它准确地从艺术和审美的自身特点把握了它们的革命意义。艺术和审美能使人从现实中获得解放,但这种解放的方式显然与现实的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艺术与审美所实现的解放是一种感性解放,因为,艺术与审美首先诉诸于人的感官,作用于人的感性,也就是说艺术与审美对现实世界的打破与重建是通过感性的方式来实现的。它在打破旧有的感性秩序、重建新的感性秩序的过程中将艺术与审美的感性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在康德与席勒的理论中已经潜在地蕴含着新感性的部分思想,但马尔库塞首次提出新感性这个概念并加以科学规定,在哲学发展史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乌托邦式的浪漫格调与激进主义的革命方式
马尔库塞对艺术和审美问题的哲学思考,更明显地表现出浪漫派的特征,而且这个特征还带有现代乌托邦色彩。马尔库塞在他的哲学思考中,明确要求艺术超越既存现实,展现异于现实的另一个世界,但他所说的对现实的超越都是驻足在个人感性之中的,但他漠视社会环境,更把人的解放寄托在个人的感性解放中。在他审美哲学的致思中,他除了专门推出“新感性”这一为其所独有的范畴外,在其他美学著述中,他无处不强调,个人感性的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序幕。而且,他漠视一切个人感性解放的前提,把个人感性的解放奉为至上的原则,这又使他的浪漫格调带有了一种现代乌托邦色彩。听起来娓娓动听,现实中却到处碰壁。
马尔库塞把艺术和审美当作革命的武器,并将艺术与审美的功能限制在革命与解放作用上,人们只有借助审美与艺术,才能反抗并改造现实,这就陷入了激进主义的窠臼。马尔库塞在他的审美哲学思考中尽管不遗余力地鼓吹艺术是武器,是革命的武器,但是,他并没有向我们说明,艺术如何并在何种程度上使自己成为革命的武器,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明,艺术何以成为革命的武器。
[1]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3.
[2]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38.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8-129.
[5]HerbertMarcuse:An Essayon Liberation[M].Boston:BeaconPress,1969:6
[6]MARCUSE.Art as Form of Reality[J]//New Left Review,I/74. London:July-August1972.
[7]马尔库塞.审美之维[C]//马尔库塞,等.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曹萌】
B516.5
A
1674-5450(2015)06-0033-03
2015-07-25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3BDJ040);2014年辽宁省规划社科基金一般项目(L14Bks013)
李闯,男,辽宁黑山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张岩,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辽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