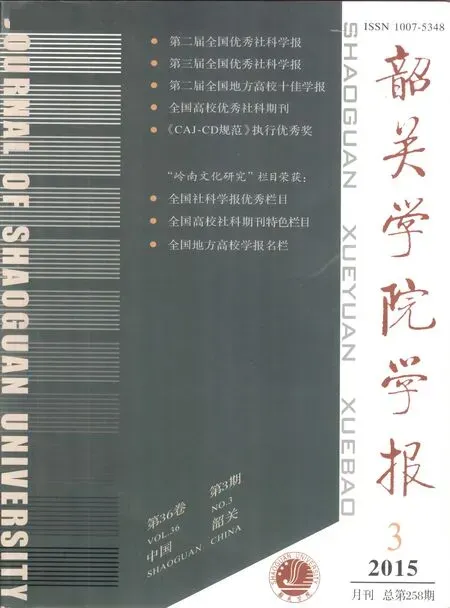“革命人”与文学自由
——革命文学论争视野下的文学主体论
燕世超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革命人”与文学自由
——革命文学论争视野下的文学主体论
燕世超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要从事革命文学,首先要做“革命人”。要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有正确的认识,就要参加社会实践,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有深切感受,还要敢于正视现实和黑暗。文艺是独立的,但文学家却是不自由的;文艺应该通过竞争获得发展,但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自由竞争又是不可能的;左翼作家要团结“同路人”,不应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排斥他们。
文学主体;“革命人”;文学自由
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在论证革命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同时,就革命文学主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问题的焦点是: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称得上是革命作家?这个在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共识,后来的左翼作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在文艺自由问题上的争论,可视为革命文学主体问题论争的延续和发展。
一、革命作家必须是“革命人”
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倡导革命文学时,对革命文学主体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只要有无产阶级意识或立场,就可从事革命文学,而无产阶级意识或立场似乎是轻易就能够获得的。至于革命立场如何获得,则没有进行论述。那么,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从事革命文学呢?
鲁迅反复强调,“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1]335“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420而要做一个“革命人”,并非具有革命意识或革命立场那么简单,同时革命意识或革命立场也不是轻易就能够获得的。在鲁迅看来,他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有正确的认识
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要有正确的认识,而要获得这种认识,就要做到:
一是参加社会实践。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也才能够创作出表现那个时代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家要立足于现实,才能塑造出反映那个时代的人物形象,浪漫主义诗人也必须以丰富的社会生活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抒发表现那个时代的情感。在鲁迅、茅盾看来,社会实践的方式多种多样。作家不一定要拿起枪杆、参加武装斗争,他只要能够深入社会,亲身感受底层民众的命运,对耳闻目睹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思考,从而为自己的创作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就是参加了社会实践。当然,每个作家都不可能对于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各个地域的人十分熟悉,但他可以通过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环境的分析进而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鲁迅选择农民题材,茅盾选择城市小资产阶级题材进行创作,均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社会实践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然而,社会实践正是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所忽略的,正因为此,他们的作品缺少生活基础,只能以标语口号相标榜,自然也缺少感人的力量。
二是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也就是说,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他才能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产生科学的认识。然而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仅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况且这些知识大多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现在看来,他们根据日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而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缺少社会实践,当他们把这种理论用之于分析中国社会时,其认识必然流于空想。作家不是看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就是真正的“革命人”,“革命人”的思想转变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这些所谓的革命文学家在做革命文学时,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理解革命,当然只会歪曲革命。
三是对于中国革命有深切感受。作为“革命人”,作家还要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有深切的感受,因为他先被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所打动,他的作品才能产生激动人心的力量。所以鲁迅说:“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2]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茅盾自然也持同样的见解。遗憾的是,创造社、太阳社大多成员既缺少丰富的生活阅历又缺少文学创作的基本经验,认为只要有革命理论就会有革命立场,有了革命立场就可以从事革命文学了。在这些作家之外,郭沫若有所不同,他有一定的创作经验,但作为浪漫主义诗人,他更强调的是意识对于创作的决定作用,没有把自身的创作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反而提出作家要做政治的“留声机”这样荒唐的口号。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该口号在创造社、太阳社成员那里大行其道,可见郭沫若与他们一样,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作家感受革命的重要性。
(二)敢于正视现实和黑暗
鲁迅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敢于直面鲜血淋漓的人生,敢于在作品中揭露残酷的现实。从《狂人日记》开始,他在《祝福》、《故乡》、《孔乙己》、《阿Q正传》和《伤逝》等小说中,始终把暴露社会黑暗、揭示国民劣根性作为创作的首要任务。但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他发现“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3]这些作家之所以不敢正视现实和黑暗,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他们最初把革命视为轻而易举的事。他们认为当时已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决战的时代,而决战的结果,必定是无产阶级胜利,且这种胜利指日可待。他们把“五卅”运动视为群众已经觉悟、革命的浪潮已经汹涌澎湃的标志,根本不了解中国绝大多数民众仍处于麻木、愚昧的状态。明明是处于革命的低潮,他们却视为高潮。当他们的理论与现实产生绝大反差时,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也就是不敢承认自己的理论经不起实践检验。鲁迅多次举俄国十月革命后叶赛宁自杀和辛亥革命后南社沉寂为例,希望革命文学家引以为戒,对革命有清醒的认识。
二是过于看重文学的武器作用。文学诚然有政治功能,在特殊时期还能够起到很大的政治作用。但在群众还处于麻木、愚昧的状态时,文学的政治作用却是有限的,不可能像李初梨所说“实践地在变革‘社会生活’”,更不可能像钱杏邨所说具有“超越时代,创造时代,永远的站在时代前面”的改天换地的功能。鲁迅认为,在这过于看重文学功能的背后,是创造社、太阳社成员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心态,而革命的目的恰恰相反,是为了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而非再造出一个精神贵族阶层来。他举法捷耶夫《毁灭》中的知识分子美蒂克在革命队伍中不但没有受到额外尊重,反而处处被人嘲笑为例,说明“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2]这种精神贵族心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鲁迅多次举海涅“相信诗人死后,上帝会请他吃糖果”为例,说明这是决不可能的。
敢于正视现实和黑暗,其实质就是敢于和黑暗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描写社会黑暗,暴露旧势力的罪恶与腐朽,这是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又一根本区别之一。不仅如此,鲁迅还意识到与黑暗势力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提倡“韧”的战斗精神。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鲁迅就意识到:“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4]左联成立时,他再次强调:“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2]为了持续不断地和黑暗势力斗争,鲁迅还主张“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注重培养年轻作家,胡风、冯雪峰、肖军、萧红以及未名社作家等都是在鲁迅的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二、文艺的自由与作家的不自由
革命作家不但是“革命人”,还应该是作家,这是无须求证的。但文艺有没有自由?1932年,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之间展开了历时一年的论争,此次论争可视为1928-1929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延续和发展。总括起来,论争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
1.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还是独立的存在。论争是从胡秋原批判国民党政府倡导的民族文艺开始的,胡秋原接着阐述道:“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因此,所谓民族文艺,是应该使一切真正爱护文艺的人贱视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也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趴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5]他同时谴责钱杏邨所谓“标语口号文学对于革命的前途是比任何种种的文艺更具有力量”的极左论调。胡秋原对钱杏邨的批判引起左翼文坛的不满,冯雪峰把它上升到对整个普罗革命文学的批判,瞿秋白、周扬也纷纷撰文进行反驳。苏汶接着撰文为胡秋原鸣不平。
胡秋原、苏汶与左翼文坛的论战不存在个人恩怨,而是整个文艺观的分歧。后者取消文艺的独立性,把文艺视为政治的留声机,而无论是胡秋原还是苏汶都没有否认文艺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所否定的,是文艺不要因为当前的功利目的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作家不要主题先行、不要仅仅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创作,因为文艺要忠实地表现社会人生,而政治仅仅是社会人生的一个侧面。他们还认为,作家在创作时不为政治所左右,但由于作家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所以,他的作品自然就会有一定的政治性。革命文艺也是文艺,当然也是一种虽与政治有关但又不从属于政治的独立的存在。胡秋原、苏汶与鲁迅的观点其实不谋而合,鲁迅一贯认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6]但是,鲁迅却没有支持他们,反而反对胡秋原、苏汶的观点。这是因为,“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7]左翼文艺正需要以抗争来争取自己的创作自由,这个时候提出政治“勿侵略文艺”,无疑等于要求左翼作家不要抗争。所以,不应抽象地评价某种文艺观,而应把它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当然,左翼作家取消文艺的独立性,视文艺为政治的留声机,是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翻版,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左翼作家的上述观点无疑直接受到列宁“党的文学”的影响。据考证,列宁那篇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之作的文章自1926年以来多次被翻译,1949年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其中有些词本是多义词,仔细考察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列宁的真实意图,最终把“文学”改译为“出版物”,“党性”、“阶级性”改译为“倾向性”,“创作自由”改译为“出版自由”等。这篇文章旧的译文曾经支配许多左翼作家的思维方式并对党的文艺政策产生重大然而却是负面的影响。“苏联对列宁本文所作的不符合列宁原意的阐释误导了我国的译者,而我国译者的不确切的译文又误导了我国广大的读者。”[8]
2.文艺能否通过自由竞争获得发展。在主张文学自由的同时,胡秋原进一步认为文学应该自由竞争,而不应以政治的手段扼制它。他多次强调:“‘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云者,不过是说文艺要自由竞争,非强制或独占所能产生繁荣之意……。”[5]苏汶也认为,“文学家可以拿他的所作当做商品到市场上去自由竞争,而无需乎像封建社会下似地定要被收买,被豢养才能生活了。”[9]笼统地看,胡秋原、苏汶的观点确是很有道理,因为谁都知道,历史上文学繁荣的时代,无不是政治上相对宽松、文学在自由竞争中获得发展的时代。当时,民族文艺依靠政权的力量操控文坛,而一些左翼作家也动辄以粗暴的手法排斥异己,搞宗派主义,确是严重制约了文艺的发展。但若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他们的提法实在不合时宜。首先,在政治极度黑暗,文艺领域充满尖锐的斗争时,提倡自由竞争,只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根本上是行不通的。1926年初,鲁迅曾就林语堂提倡“费厄泼赖”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认为“费厄泼赖”自然是好事,然而在当时不可能行得通。胡秋原、苏汶此时提倡文学自由竞争与林语堂当年提倡“费厄泼赖”一样,都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其次,文学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受资本主义市场规律支配。既然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容许,那这种自由竞争在根本上还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是不自由的。
3.是否存在“同路人”?革命作家应该如何对待“同路人”?胡秋原、苏汶之所以分别称自己为“自由人”或“第三种人”,其本意在于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也不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作家,他们只是左翼作家的“同路人”或中立者。他们认为,苏联都承认并团结“同路人”作家,可左翼作家却不允许有“同路人”存在,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对待这些人,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左翼拒绝中立。单单拒绝中立倒还不要紧,他们实际上是把一切并非中立的作品都认为中立,并且从而拒绝之。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我觉得是认友为敌,是在文艺的战线上使无产阶级成为孤立……我们认为文学的阶级性不是这样单纯的,不要以为不能做十足的无产阶级的作家,便一定是资产阶级作家了。”[9]苏汶在这里把两个问题混同为一,即没有认清“同路人”与中立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苏汶提出的问题,其实正是许多左翼作家的症结所在。他们认为无论是谁,不属于资产阶级作家就一定属于无产阶级作家,反之亦然;既然文学具有阶级性,那么,每个作家也必然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所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也就不存在“同路人”。瞿秋白、谭四海、周扬、冯雪峰、舒月等纷纷撰文,批评苏汶表面上中立,实际上是企图掩盖自己的资产阶级倾向,因为无产阶级敢于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而资产阶级已经衰落、将要进入坟墓,才拼命掩饰自己的阶级观点。无疑,他们把“同路人”与作家的阶级性混为一谈。论争到最后,何丹仁科学地指出,“真的中立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但客观上确实存在着“同路人”,他们既不属于资产阶级又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文学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苏汶关于“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未必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学”的观点是对的。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根源在于左翼作家的“机械论(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10]鲁迅更是明确地主张要团结“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些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7]这样,从1928年春成仿吾提出“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11]到1932年秋冬之交鲁迅、何丹仁相继承认并团结“同路人”,左翼作家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总算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当然,这种“狭窄的排斥异己的观念”还远远没有肃清。
[1]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M]//鲁迅选集: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35.
[2]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M]//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0-241.
[3]鲁迅.太平歌诀[M]//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4-105.
[4]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M]//鲁迅全集: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6-197.
[5]胡秋原.阿狗文艺论[J].文化评论,1931:期号,页码不详.
[6]鲁迅.文艺与革命[M]//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5.
[7]鲁迅.论“第三种人”[M]//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1.
[8]丁世俊.记一篇列宁著作旧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修订——兼记胡乔木与修订工作[J].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2):起止页码不详.
[9]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J].现代,年号不详,1(6):起止页码不详.
[10]丹仁.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M]//苏汶.文艺自由论辩集.北京:现代书局,1933:280.
[11]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J].创造月刊,1928(9):起止页码不详.
Revolution and the Literary Freedom——On the Subject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Controversy Perspective
YAN Shi-chao
(College of Literature,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 515063,Guangdong,China)
To engage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the first thing"revolutionary people."To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it is necessary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practice,be able to apply the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scientific analysi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Chinese revolution has deep feelings,but also the courage to face reality and darkness.Literature and art are independent,but the writer is not free;literary should grow through competition,but in the sinister political environment,free competition is impossible;left-wing writers to unite"fellow traveler",this should not be a non-Ji Bi way exclude them.
literary subject;revolutionary people;freedom of literature
I106
A
1007-5348(2015)03-0015-04
(责任编辑:宁原)
2015-02-0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研究”(2009JJD750009)
燕世超(1954-),男,安徽涡阳人,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世界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