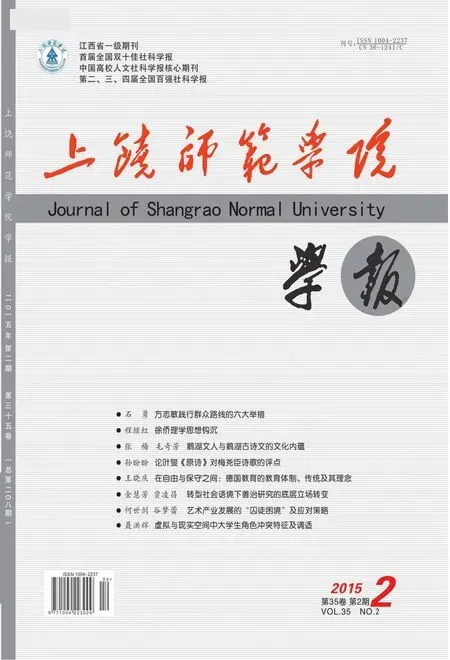转型社会语境下善治研究的底层立场转变
金慧芳,贾凌昌(.上饶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上饶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江西 上饶33400)
转型社会语境下善治研究的底层立场转变
金慧芳1,贾凌昌2
(1.上饶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2.上饶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江西 上饶334001)
转型时期的底层立场依然没有获得想象的青睐和厚重的学理支持,然而,底层立场的社会视角新维、精英治理遭至的诟病和底层自主性的觉醒为善治研究关注底层提供了可能。善治研究聚焦底层,需要研究者具备真实意义上的底层身份,并能够真实地进入到底层社会。但是 ,进入底层也要超脱底层,如果能从底层社会之外审视底层,善治研究会在批判性的康庄大道上行走得更远。
转型社会;善治研究;底层立场;转变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不同社会资源进行着深度地分合与重组,在此进程中,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底层群体,相应地,形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底层社会。善治无可避免地与转型社会发生了交织,这意味着,善治的研究与实践亦见证了底层社会的生长现实和逻辑,其学科建构与底层社会交融相生。具体地说,转型背景下,纷繁芜杂的新现象冲击着人们的视野 ,五彩缤纷的新问题激荡着人们的心灵,司空见惯的新诉求荡涤着人们的心扉,凡此种种,共同构筑了善治理论发展的多样性空间。在诸多悖谬的情形下,权力扩张与权利分享之间的冲突,精英仰赖与底层框架的矛盾,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地的交织,这些都需要善治理论给予合理地回应。虽然国家从制度设计层面寄予了善治美好的期望,让我们感受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春天的来临 ,但是,国家治理的实效性依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的情形似乎是这样:“我有一双美丽的翅膀,但我没有用它来翱翔,反而用它煲了汤。”换言之,善治似乎一直在国家制度层面和精英角度“展翅飞翔”,但其实效性依然没有获得突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善治理论与实践没有真实地考量底层社会,没有将真实的底层生活纳入其框架。
诚然,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获得了急速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精英阶层以及与之相随的精英生活毕竟是少数,相反,底层生活依然是目前中国社会和善治需要考察的最主要视域。因此,如果善治能够与底层社会生活有效相容 ,作为善治改革和发展的设计者与执行者将不仅能破解善治遇到的种种难题,而且能拓展政治伦理的发展空间。
一、底层立场 :善治研究的域间扩展
在当下中国,无论我们意识到与否,社会转型都在悄然发生并将持续下去,社会转型高扬的逻辑行走于精英和底层之间。在此过程中,精英逻辑远远超越其本身的意义而得到了深度的彰显,“我们已经习惯了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来自上而下地打量底层社会 ,习惯了替底层群体说话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说话,习惯了外在的冷眼旁观而不是深度地价值介入”[1]。这样一来,底层的生存景象在无形之中被屏蔽殆尽,底层只能在精英的背景下无声地甚至“屈辱”地前行。社会底层的抗争并不是一时的哗众取宠,更不是博取同情的舞台表演。在很大程度上说,它展示的恰恰是制度逻辑与制度实践的悖谬之维,展现的恰恰是中国善治研究与实践的缺场之地。的确,善治研究并不缺乏推进的源泉和想象的空间,在制度和精英的互动过程中,善治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蓬勃的展开。然而,中国治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精英如何将其逻辑更好地展示在舞台上,更不是制度文本的实践表演,它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发展,更多地关注作为底层的人的发展,换句话说,底层生活世界作为底层人民安身立命的家园更应该进入善治研究的视野。善治研究关注底层立场,并不在于我们发现了新的研究视域,亦不在于这种研究能够为学者带来新价值 ,也不在于我们要完全摒弃或解构精英主义价值观,而恰恰在于,底层生活现实是善治研究必须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现实状况来说,转型时期的底层探讨尚未获得想象的青睐和厚重的学理支持,这首先是因为,在善治研究之中,存在着“精英式”的思考范式。善治研究固然需要强调此范式,但此思考范式往往也导致了一种难以回避的束缚,即我们经常用精英式的思考方式来思考中国治理问题,从而导致善治研究似乎一直漂浮在空中,而没有真实地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诚然,不能否认,善治研究在事实上已经开始关注底层,但是,底层社会被理解并不是通过底层群众来理解的,反而是通过精英话语获得建构的,所以,底层在文本中可能拥有显眼的位置 ,但其表述却呈现出碎片化、非连续性和不真实的特征。其次,在精英内嵌于治理的话语体系中,我们意识形态的组织传播强势地屏蔽了底层社会的发声渠道,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在国家和底层生活世界之间造成了一个无法沟通的鸿沟:“底层群体话语通道的缺失导致来自底层的声音不能被倾听,这无论对于底层群体还是对于社会发展本身都是极为不利的:一方面,失声的底层可能找不到诉说困难、表达怨恨的渠道而始终处于利益被侵害状态;另一方面,整体性社会结构中底层的凹陷可能成为阻滞社会良性发展的最大障碍。”[2]在此种语境下,国家治理必然表现为精英政治的代言人,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底层被遮蔽的事实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固定框架,底层社会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在与不在似乎已经无关宏旨。再次,社会的运行生态淡化了底层的诉求。有人说,当一个社会的运行被宰制时,底层人民就是傻子。然而,即使是傻子有时也能成为击败权势的伟大英雄,因此,这里的关键是傻子如何成为英雄。当然,这需要傻子自身的绝对努力 ,但谁也无法否认社会的塑造作用。从社会塑造这个角度上说,这主要是看社会祈求的是开放性还是封闭性 ,开放性的社会将傻子塑造成治理社会天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相反,封闭的社会更可能使精英沦落为傻子。在王焱看来,在开放、法治社会中,那个愚昧盲从乃至暴力的群众能够变得高尚起来,变得富于理性和智慧,具有道德和责任心,更能体现出人的高贵和尊严。显然,从此角度上说,之所以底层没有受到关注正在于社会生态的开放程度。
底层研究作为一种范式进入人们视野并不是新近的事情,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70年代,斯时,印度的一些作家在对历史上流行的精英史观进行反思性追问时,认为存在一个与精英研究相对的底层研究。“底层”这一概念要早于底层研究而出现,最早使用“底层”概念的是意大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 ,他在《狱中杂记》中使用了“subaltern classes”,意指那些从属于欧洲国家的被统治群体。直到1982年,古哈等一些专注于历史的学者在《底层研究》中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探讨。他们的学术兴趣在于对精英主义提出一种批判,特别强调要赋予底层群体意识以历史理念和想法,其实质是一种对精英主义框架进行解构的立场和重要方法。以此作为基本立场和方法,他们希望通过对历史上存在的文本进行批判式考察,挖掘和注意底层的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是这些学者重新呼唤了被遮蔽的底层研究对象,毋宁说他们从比较的角度使被遗忘的底层群体重新回归到社会学或政治学的空间,换言之,底层本来就已经是一种实际的存在 ,只不过由于学者的聚焦不同导致在相似的时空中受到了不同的学术待遇。
这样看来,底层研究的善治价值就显得格外重要:(1)底层关注的意义在于它提倡了一种研究社会的新角度,能够拓展善治的研究主体和参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立场批判了把精英政治事实强加给底层立场的做法 ,能够使底层群体在社会转型中以新的姿态重新进入到政治框架的视野 ,进而引起精英群体的注意;(2)这可能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精英治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伪命题。虽然的确存在着一种生存意义上的底层 ,这种底层和精英的差别也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在精英进化的最初阶段,精英面向的世界与生成的背景和底层是惊人相似的。精英的确超越了底层的某些局限,但是精英不可能将自己与底层的共有属性完全地区分出来。或者换句话说,精英超越的所谓的局限在一定意义上也依赖于底层的某些特征,精英的身份本质就存在于底层之中;(3)相较以往,社会结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对人类的“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复杂情势倒逼善治必须超越传统治理立场,它必须内摄精英立场,又必须俯身底层。我们必须重新拾起对底层自主性的关注。麦金泰尔论证了现代德性伦理中依赖性的不可避免:“如果要充分实现独立的理性行动者的德性,就要伴以我所说的承认依赖性的德性,而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会掩盖理性行动者的某些特征。”[3]但即使如此,人们的独立性依然是最主要特性,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只是辅助性属性。毕竟,“人之为人就意味着按照我自己的意图(不一定是理性的或有益的)来造就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有资格被别人承认是这样一种人。因为,如果我不能获得这样的承认,那么,我就无法承认并怀疑我自己的要作为完全独立的人的那种要求”[4]。从此意义上说,底层研究方法值得善治研究进行借鉴。
二、善治研究的底层介入
底层社会的现实性构成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并可能生发出巨大的威力,在它还没有能够对国家产生足够大的毁坏力之前,不仅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反思性诠释 ,而且需要改革者先行对其进行回应式关切,这种回应必须将底层的主体性维度纳入到我们的理想和实践维度中,因为我们并不期望“权力、法律和知识都要遭受激进的非决定论者的折腾 ,社会本身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冒险的剧院;结果,任何体制化努力都无法完成,已知者因未知者而仍旧是不确定的”[5],否则,“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6]。因此,善治研究进入底层视野是自然且必然的。
善治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真实意义上的底层身份。从底层研究的意义来看,如果欲想对底层有所关注,就必须进入底层,毛泽东说,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进入底层可以有多种方式,一种是作为底层社会的人员直接进行的底层研究,但这并不现实,这不仅是因为分工的不同,更在于学术研究有着内在的规范和知识要求。所以,我们祈求的只能是“精英”意义上的研究。不过,这里要区分两种意义上的精英,一种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精英(底层精英),一种是来自社会上层的精英(上层精英)。不能一概否认来自上层的精英对底层研究的有效性,但有时,“社会中生活舒适的成员所亏欠于不舒适的同胞们,并不是平等,而是稍微体面一些的最低生活标准,那么这就是让太多的事情取决于低到什么程度的标准还算体面这个本质上主观的问题,而当代史表明 ,生活舒适的人是不愿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慷慨的回答的”[7]。所以,来自底层的精英进行底层研究或许更能具有一种底层情怀 ,这样的研究也可能更加具有有效性。这就要求出身于底层的精英真正地不忘底层,委身底层,回归底层,以底层的生存和生活经验装饰自己的研究身份。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并不期望底层精英与上层精英不发生任何意义上的瓜葛,关键是底层精英要学会携带底层意识与上层精英进行沟通互动 ,从而更好地为底层治理提供回应性策略和帮助。
善治研究者要真实地进入到底层社会。善治研究者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底层身份,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真正地进入到底层社会中来。必须承认,底层社会是底层的真实生活,底层不仅是生活背景,也是生活需要超越的向度。那么,对善治研究者而言,如何才能进入到底层社会呢?具体地说,作为一个关注底层的国家治理学者,(1)需要在抽象和具体之间互动切换。社会科学研究中抽象是必要的,抽象本身就是一种距离的映射,但抽象不是为了拉大距离,而是为具体找寻真实的学理支撑 ,学术研究不能为了抽象而抽象,只能是为了具体而进行必要的抽象,即是说 ,要在逻辑的底层世界和生活的世界之间游移省思;(2)要学会关注“微小”事件和智慧。底层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宏观世界,在那里,宏观叙事是没有空间的,相反,“小”和“微”是底层世界的重要表征。在底层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和经历“小事件”和“小问题”,它们是如此地琐碎以至于它们好像根本无法进入到学者的知识框架,但恰恰是这些小问题和事件构筑了底层生活 ,而这也恰恰是善治不能忽视的。善治需要关注民生,而民生实质上就是由琐碎的生活组成的。因此,切忌忽视抹杀小问题,它们可能恰好揭示了某种微观的权力运作和关系 ,也可能张扬了某种意义上的公共精神;(3)要建立与底层的交往框架。通过关注底层生活,形成一种对底层的反应性同情。即要学会理解底层行动,通过这种理解和传递也使底层能够对善治研究者做出反应。善治理论的研究者与底层生活的行动者需要共同建构一个基于底层文化的经常性对话通道,从而实现善治研究者从某种单一的学理身份向复杂的底层生活身份的转化。当然,研究者要内摄于底层人民构筑的世界之中,力争用他们的生活概念和符号表达和理解他们。
善治研究要学会从哲学维度批判性地看待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上述已论,善治研究者需要具备底层身份或者进入底层方能拓展善治研究视野,然而,我们还必须学会在进入底层之时超越底层,如果仅仅学会了进入底层 ,遭到底层的迷雾侵扰时,我们的眼睛就可能会被蒙蔽 ,因为当局者迷。因此,这要求我们超脱底层 ,以一种外在的眼光审视底层社会的治理运行。这需要引入社会批判概念。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批判都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在当代社群主义者沃尔泽看来,批判并不能局限于哲学或文学领域,我们必须把批判理解为一种更广泛的人类活动,即一种文化阐述和文化表达活动。换句话说,批判不只是要对社会持“反对或抨击”态度,而是对社会的一种思考。以沃尔泽的想法,“社会”这个词告诉我们这项事业的主体是谁,即是说,社会批判必须要诉诸一定的主体 ,社会批评家是社会批判的当然成员 ,但是他们也身兼二任,也可能成为批判的对象,但其更主要的是以社会批判身份出现的——他们在公共领域对其他参加对话的社会成员发言,他们的话语是对公共生活状况的集体反思(collective reflection),也是对国家治理现状的思量。批判需要批判的距离,由于批判是一种外部活动,因而,如果能对社会保持一种超脱的立场和态度,就能够进行更为彻底的批判。社会批评家必须在情感上脱离、超脱于成员之间的亲密友好情感;超脱厉害关系,公正无私;超脱好恶情感,冷静客观。他们还必须在知识上超脱,超脱于他们自己的社会,避开社会的狭隘想法 ,要开朗、虚心和客观。只有当我们崇尚客观,把自己置身于底层社会之外,站在底层社会的上空才能发现底层社会的现实恰恰需要从反面对社会的治理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如果能够承诺一种批判性维度和心态,我们就可能会真实地看到底层社会被精英群体“抛弃”的事实,就会将久违的底层社会重新捡起纳入到国家治理框架的核心维度,这样一来,一个包容他者、卫护底层、捍卫权利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局面方能显现。
三、结语和希望
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治理能力支撑 ,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国家框架下的不同主体在经济逻辑和政府逻辑的双向支配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在不同的位置上创造着人生的传奇。然而,这个位置是多元的。无论国家提供的通向精英的渠道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着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愿景和行动,转型社会的“非精英化”趋向依然是无法阻挡的,无论处于“精英地位”还是“底层地位”的群体似乎都存在或隐或显的“弱势心态”。换言之,底层语境与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闯入了人们的视域。因此 ,底层关注似乎已经从阴暗的角落开始走向阳光的边缘,其自主性日渐获得精英群体的青睐,也渐次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聚焦 ,善治研究更不例外。随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改变过去政府是唯一治理主体的做法,要把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 ,转向多主体治理,要扩大公民参与治理的渠道和机会。这为善治的底层关注提供了明确的指示,必将为善治研究的底层探讨和关注带来更广阔的空间。如果能够保持对底层的热情,并且偏好于底层思虑的价值和方式 ,倾心底层的心理诉求,关注底层的生活现实,使底层能够驰骋于国家治理的轨道,那么,善治必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域中获得完美的呈现。
[1]刘威 .“朝向底层”与“深度在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立场及其底层关怀[J].福建论坛,2011,(3):144-149.
[2]赖伟军,吴志明.底层中国的主体性建构:一个研究评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19-26.
[3]麦金泰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M].刘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4]以赛亚·柏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墨菲 .政治的回归[M].王恒,臧佩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6]Scott J.The 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7]德沃金.至上的美德[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邱忠善]
On the Change in the Bottom Stand of Good-governance Research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JIN Hui-fang1,JIA Ling-cha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Shangrao Jiangxi 334001,China;
2.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Shangrao Jiangxi 334001,China)
The bottom stand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has not yet gained the desired favor and firm doctrinal support.However,the new social dimension of bottom stand,the reviled elite-governance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 bottom autonomy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good-governanc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bottom.Good-governance's concern about the bottom requires the researchers to have the real identity of the bottom,and to truly go into the bottom.But as they go into the bottom,they are supposed to go beyond the bottom,for,if they examine the bottom from outside the bottom,good-governance researches can go further on the way of critic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good-governance;bottom stand;change
D63-3
A
1004-2237(2015)02-0066-04
10.3969/j.issn .1004-2237.2015.02.015
2015-03-22
201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ZL39)
金慧芳(1975-),女,江西上饶人,副教授,从事管理伦理研究。E-mail:8544330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