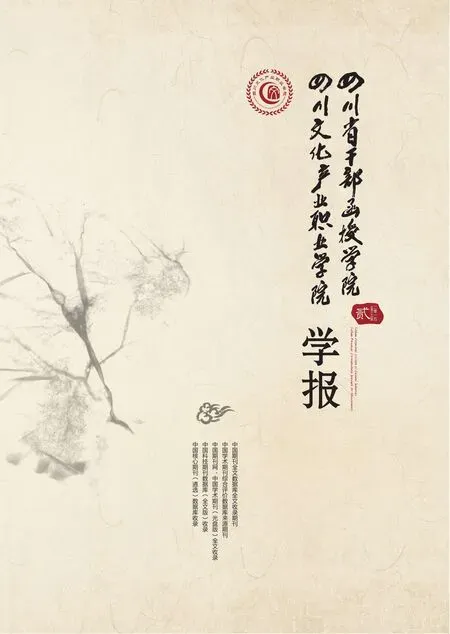思考语言和言语美之所在
邱 爽(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1330)
语言、言语的生产,离不开主体和世界的对话,此过程是连绵不息的。这种有机体同主体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斗争的共时场域。其中斗争的参与者为主体、世界,在对话中所交流体会的便是美。
言语带动语言,将语言“遗忘”并隔留在消散时间之中的“自在的存在”,自在存在的在被言语拉回共时,自为生成。在“过去”和“未来”的获得自在存在语言在虚无中。在人类意识中所体会到的美,从中而来,在言语的流逝中消失于虚无之中,共享的只在当下。
一、言语同“时间”
在对语言和言语美之所在的思考中,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言语对意象的生成过程。当言语——包括构成言语的语音、字词、句子、语法等方面——不管是来自生理还是自然科学——在物理性时间结束之后,立即成为“过去”,“过去”是每一个言语细节或多个同时出现的言语细节呈现完结之后,“过去”便为了一个是其所是的自在的存在状态。同时,在时间的“过去”中,言语形成一个充满空间的“意象”,此“意象”在接受者的意识的“现在”中形成,在此过程中,言语达到自为的存在饱和,逐渐形成自为意象,在意象形成之后,以及在形成过程中每一个言语细节或多个同时出现的言语细节在“过去”的自在存在中构成接受者自为存在意象空间组合之后,此意象则在接受者意识中完成自为存在。此过程循环往复,接受者在将言语在自我意识中完成其自为存在之后,接受者也就完成了从接受者到表达者的身份转变。当接受者的意象没有得到具体言语的表露转变为表达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未来”的预期性的自在存在。言语在彼此的意识中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完成属于彼此作为单独个体的空间独立性,而在交流过程中每一个独立的言语细节所呈现的都是“现在”的自为存在状态,只有当“现在”转变为“过去”或预期“未来”才具有自在的存在。
对于“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其区分来自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方式”[1]就是“自为的存在”,“是其所是的存在方式”[2]就是“自在的存在”。“自为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自在的纯粹虚无化,它作为‘存在’的洞孔包含在存在之中。”[3]“自在的存在”是独立于意识的,即是物的存在,“自为的存在”则不能独立于“自在的存在”并依靠其存在,也就是人类意识的存在。“自在的存在”独立于人类的意识之外,但是在萨特之前的海德格尔则认为事物的存在必定来自人的意识,人的意识赋予了事物的存在,这个“自在的存在”的事物。萨特指出:“现象的存在超出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为这种认识提供基础。”[4]自在的存在在人类意识之前,它作为存在的东西就已经存在了。人类意识中的存在,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论述的赋予事物存在的存在,就是“自为的存在”。在现实中的客观事物,同人类意识发生交流之后,进入到人的“世界”,从而获取超越自身“自在存在”之外的意义,成为了工具性的事物。“言语”从口而出,未到达接受者的意识中时,就是这样“自在的存在”着,“言语”本身具有高度的事物形而上抽象化,但在抽象化之后,脱离人类意识独自具有有别于其他事物的物性。在此,实际上就是言语进行了一个隔离化,隔离人类意识,切断其交流功能,故而,言语完成了一个有别于它物的“自在的存在”状态,在与他者进行交流的时候才能具有“自为的存在”,并进入意识世界。其他事物可以通过言语来通过“自在的存在”转变为“自为的存在”,其中所涉及到的实施者和履行者,只需要个体便可生成,但言语的“自在的存在”到“自为的存在”的状态的转变却必须在交流条件存在时才可以完成。
在言语从“自在的存在”转变为“自为的存在”,再从“自为的存在”转变为“自在的存在”这样一个循环不断的过程中,所牵连的“时间”必须交代清楚。海德格尔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中强调存在的时间性,时间性必须返归为人。人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在时间的统一中,在过去、现在、将来的统一中才可以可能。海德格尔指出,在科学领域中的时间和人生经验中的时间都为时间性存在的衍生物,其用于衡量时间的工具为时钟系统,在时钟系统中人们以能够经验到当下来对现在做确定,再通过现在确定过去和将来,“于是,时间就已经被解释为当前;过去被解释为不再当前,将来被解释为不确定的尚未当前。”在历来的时间解释中,时间是线性不可逆转的。同时,时间的先后流转时,一系列的现在时间点以及时间成为空间化的时间,也就是当下-在场时间。这样,当下-在场化时间经验者即在场化的人自身。由此,海德格尔就展开了“此在”的讨论。而在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所讨论的时间的三维性,则把时间的“过去”作为一个重点来讨论,其目的是为说明“自在的存在”,对“过去”的事物相对“现在”来说,在“过去”的时间段并不能完成任何“现在”能进行的意识行为,当在意识中“加工”,“过去”就不再是“过去”,而是“现在”,“过去”在“自在的存在”,完成了如其所是。“自为的存在”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存在,因为此存在才涉及到人,交涉到人,所进行的研究才显得有意义。“自为的存在”必定依靠人类意识,而人类意识则必须通过虚无化行为从自在的存在中生产。
二、语言同“虚无”
在言语之中“过去”的言语就是被存在化的语言,语言就是虚无。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正是通过其虚无的否定力量来确立存在。语言本身同人类意识息息相关,但语言不能被表达。当语言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言语,语言退居虚无之中。语言的虚无就是意识的虚无。语言,具有“语言”的名称实际上就是言语的命名,使得语言成为一个被存在的抽象名词,在意识中转化成意象,以感性的形象出现,虽不可描述其相貌以及其本身性质,但又以言语的自身代言可感。语言存在于人类精神领域,借言语的“过去”而如其所是的自在存在。在“当下”进行活动的只能是“言语”。语言“被”当做对象,之所以可以进行研究的前提就是有时间的隔绝。在过去之中的语言,失去“在场”,成为一客观“事物”。言语就是把虚无的语言变成一个可感知的被自在的如其所是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的时间性中,“过去”和“将来”就是在“现在”、“当下”在场的意识中完成。言语就是一个“当下”、“现在”通过言语来进行的“语言”方面的思考。在海德格尔的时间性中,最终所归属到的是“此在”,而“此在”能够对事物实现“存在”的就是“语言”。语言之所以同样能够给自在的存在之物以自为的存在,这就是言语给予的存在,凡是在意识能够通过言语进行表达的就是语言虚无化的否定能力给予的。言语所到之处就是存在,其先行者就是语言。
那么“虚无”到底是什么?在生活中,或艺术中,在所有言语活动中,存在的言语是绝对的,充实的,它本身既不是肯定的,也不是否定的。言语本身不包含任何否定。无论在对言语进行任何研究,包括在否定句式或者判断性问题中,言语自身并没有任何否定,只是在言语中否定性的针对事实事物,而不是对待言语本身。但是,在反思过程中,将过去的如其所是的自在存在的言语作为一个反思对象时,有问题对“言语”提出,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了一个否定的基础,也就是作为存在的言语将言语从言语中脱离,有了非存在的基础。否定,唯一出现的机会则在判断行为之中。正如康德说,他是用内在结构对否定判断活动和肯定判断活动进行了区分,二者都是概念综合的结果,用“是”和“不是”的系词来起作用。否定在萨特看来则像两个充实的实在之间的非实在物,这两个实在其实就是自在的存在和判断表述。过去的言语作为自在存在完全自身,留下反思空间和余地来做出判断的权利则交给人类意识,再通过人类意识在“当下”完成判断表述,那么在中间这一块反思空间和余地就是一个非实在“无”,与之后的言语存在相关的,本身却是超越性质的否定。萨特指出,在人的期待范围之内,非存在就显现出来。
这样说来,在用言语表述时,一直希望表述完整和完善表达者的欲表达的意思和事件,对于表达者来说却时常“言不尽意”,而对于接受者来说,同样如此。其中的否定性的非存在一直在缠绕表达者和接受者。虚无,就是这种否定判断的概念性同一。我们时常能感受到它,却不能进行详尽的描述,能描述的就已经不是否定判断。语言就一直是虚无的。
语言不能补充言语,语言是虚无的,虚无不能接替存在,语言不能接替言语。言语可以行云流水般顺畅的表达,语言则通常是不知所措和不知所云的状态。语言是在言语的内部出现的,正如在欲表达的事物无法找到合适的字眼形容的时候,这其中交织的便是语言,语言并非在言语之外。那么是否语言就是从言语孕育而生的呢?言语已经是存在,存在就是完满的充满肯定性,它中间并没有任何空隙。语言来自人类意识。因为人类意识对自在存在物的把握永远无法做到真正的客观,只能在主观的视域里进行自我世界中事物的定型,而在与他人交流之中所涉及到的言语,需要有一个共同理解的中介或者说是共同基础,在此所形成的就是语言,在人类的意识中就是把虚无定向性的公共预订作为虚无的被存在席位。正因为如此,语言同人类的意识才得以联系到一起。
三、语言同“时间”
在前面讨论语言是虚无时,又回到了一个时间问题,语言是言语的过去,言语的当下是显现,是自为的存在。当言语成为过去或面向将来时,言语就成为自在的存在,同时,将语言被存在。语言的被存在建立在一个时间性之中,而且是同现在明显有差异的区别性之中,也就是过去和将来之中。这是被存在的语言,而不是语言的本身,语言的本身是虚无。在过去、现在、将来这三维时间中存在着另一个主导因素就是意识的“异延”。“异延”这个词语,来自德里达利用文字游戏,从difference演变生成difference,在英文difference和法语difference有一共同拉丁文词源differre。在拉丁文中却只有第一层含义——差别、区别、不同,却没有另外“延续”之意,德里达的difference则将此两方面意思含蕴。对于异延的写法,德里达说:“异延一词中的字面a表明主动状态与被动状态的不同,而且这种不确定也不再受二元对立的控制和组建。”[5]异延的实际意思就是区分和延搁同时进行的双重运动。在一定的共时态空间上,符号为生成自身意义就必须同其他符号相区别,在历时态的时间上,符号将所指的在场延搁。
德里达的异延,是在空间中承认差异,在时间上存在延迟。德里达建构“异延”解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来自海德格尔,“存在的遗忘是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的遗忘。”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本体的差异,存在时在场,存在者是在场者,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在场与在场者之间的差异。德里达试图用“异延”来代替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在场,但在场时存在,在在场之后的依然是存在,不过德里达的“异延”不是存在的显现,它是生产差异,而且延迟。德里达用“异延”来说明任何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都不是自足的,任何一个符号同其他符号的牵连都是无穷尽的,不仅如此,其中在“异延”下,任何符号都变成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为了区别他者就在差异之中凸显自身的价值。照此延伸推广,德里达就说明在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以及在文本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但,在原始踪迹的刻画中,最终赋予其意义并能展开虚无和存在较量的只是在人类的意识之中。一个自在如其所是的存在事物,在其中有同他物进行区别的客观属性,这由大自然的自然生成,客观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然而,真正的区别和差异在人类拥有了言语之后却又是不存在的,言语对区别和差异的刻画,是其反映在人类意识中之后经过抽象之后的表述,其中的抽象过程就是延搁,此过程也就是语言的虚无。事物进入人类意识,唯一的存在状态就是自为的存在。自然的言语将差异呈现,与人类进行沟通的时候,人类自身就是自己的翻译者,通过人类独有的语言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创造。人类观测自然言语,通过不断的修改或者推迟自然言语的过程,也就是在语言的虚无的否定性来确定存在的言语。在意识中并没有纯粹的所指,人类则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自然言语的意义,并发掘出使得自然语言能够得以理解以及存活的因素,在此过程中,选择和判断着的虚无,是言语清晰。由于自然言语所表达意义(在这里,假设它真的有它自身的,从来没有被人类真正理解过的意义)不确定,在人类语言的翻译过程中,可以摆脱存在的圆满实在限制,进行对自然语言的扩展。这整个过程就是意识的异延。语言通过自身的虚无来确定言语的存在,而在两者的斗争中显现的张力就是来自意识的异延。
德里达了解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字”,其中一个多元化的差异是先于任何因素的存在,反之,任何存在分歧的系统则可能被视为“文本”,其意义是,每一个文本元素的差异决定了它在所有同一系统的其他要素。在文本中的字面意义系统中,没有一个元素可作为一个文本元素或者说没有能同“能指”真正站在一起的。德里达通过解构显示出,有限系统不可以与它的元素加入其他系统,此有限系统实际上是被隔绝的,这些系统将这样做的原因是此系统的理解空间被其他理解“包围”。这样自我隔离的事同样适用于此有限被隔离系统的循环往复。其结果是,一个原文系统的每一个元素由它从无限编码元素的区别来定义,同样和无限编码区别。此无限是在有限知觉的领悟之外,因此往下进行其引用到一个能指,其所指都有无限的意义。这个意义也是无法确定的。故而,任何企图在有限的文字中存在一个自我独立意义领域,其方式就是必须消减其他能指,使其从这个无限意义区域自行关闭,以达到一个确定的意义的形象。它同时也必须从一个其他参考中设置一个限制的迹象,从而制作其他有限整体。它必须假定事情完全是文字之外的其文本性设置的一个明确的限制。这以外的文字,就是“先验所指”。解构演示着所指的任何一个或文本引用到其他的无穷大。语言的范围是无限的,它在以外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形成某种身份的结果。象征元素的任何身份将永远在过程中,是一个正在展开的事件,因为人们意识到的越来越多,人的参考就更多。构成这个进程的意义,从一元,到另一个,从此处到他方。一个永远无法完成找出某人的确切身份,或者事物的真实本质。区分自己的事件是一个世界,是从来没有了结的事件。这意味着一个无限的身份,任何一个人所说的文字是永远不会完全符合一个人的控制。解构说明,一个人的意义不能完全自主确定一个被迫能指的使用。同样,它不仅表明了对文本或上下文含义的依赖,而且,由于这种文字是无限的情况下有无穷多个,其中一个意义都可以使用,因此,从来没有一个独立于文本的确定的所指意义。未来意味着“什么”,有必要建立一个限度,一个人的文本性。但在同一时间,却又不可能全然建立。解构注意是试图承认这一必要性和不可能性。因此,它表明:能指不能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目的是因为他们保留其平均引用到其他无穷能指。任何有限的文字取决于它在一个超过其本身含义的无限文本中,从无限的上下文切除自身。它找到了这个时刻,都依赖于独立的企图。实际上,解构是最真实的阅读。所指的能指失去意义的时候,能指的意义又在何处呢?实际上,能指意义的消解就是通过“抹去”来记录事物。呈现出自己又吊销掉自己。“抹去”是一动作形态的何种时态?“抹去”的目的又在哪里?其实,“抹去”的意义就在张显其本身的意义,此举动一直是吊销在“虚无”之中的综合时态。这种“抹去”雷同于海德格尔将“存在”之上打上“x”,海德格尔的目的是要证明“存在”在场的不可言说性,而德里达则是从其中明白了存在的永远缺席的存在。德里达的消解是在追寻一种踪迹。德里达赋予了“原始踪迹”以哲学意义。对于德里达来说“原始踪迹”就是一种原始的文字,由此,文字乃是先于语言之前。在此,再往“先”反思,这种原始踪迹,到底又是何物?德里达言明“我们要从古典的先验图示中提取踪迹的概念”。对于“先验”,拉康则从心理解构其本质,同样,来自于人类之思。一种原始的人类之思。语言本身并不能行走,但是却可以以一种姿态,一种和其他物质都不同的传播给正在或即将或其他个人。如果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任何关于此行为都是真正的先验派生。
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所转的方向实则回归心理信仰的自由,从逻辑定义的规定性中解放出语词,并从逻辑句法的束缚中解放语句,把语言从逻辑法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正如海德格尔所提及,对语言的介绍,西方很早就被“逻辑”和“语法”的形而上学形式所霸占了,只是在当下才开始察觉到在这一过程中所遮蔽的东西,思和诗的“事”就是将语言从语法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一个更原初的本质构架。当代欧陆哲学家那里并不存在审美“非语言能表达”的东西,他们并不希望也不主张回到神秘的内心体验。正是在有章有则的,在语言强大的局限性和约束性中,通过语言的反作用来体味从其中散发出来的“存在”意义上的自由。语言能够不断的自我否定,并不断的打破更新自身。这就是语言同美之真谛的渊源。
[1][2][3][4] 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745.
[5] Joshua Kates. Essential History--acques Derrida and he Development of Deconstruc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