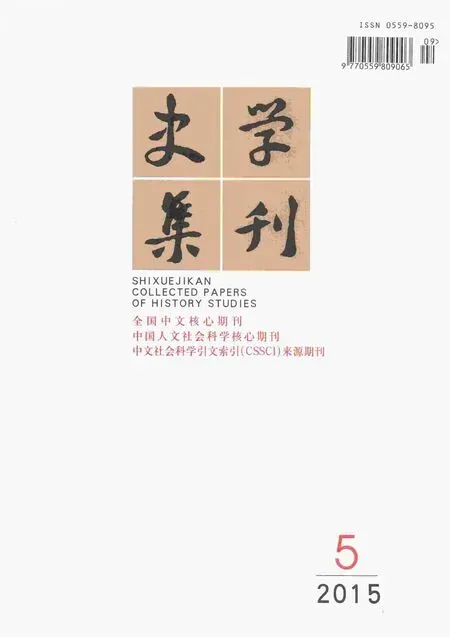帝国的类型学分析:基于边界的视角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在主权国家已经普遍化的世界中,“帝国”似乎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话语,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及其幕僚罗伯特·库珀在谈论帝国的时候还不忘加上一个含情脉脉的限定词,即协作性帝国。然而,就像罗马帝国及其传说一直流淌于西方历史的血液中一样,汉唐帝国的辉煌也成为中国历史浓墨重彩的一页。在世界历史上,帝国留下了多姿多彩的背影,草原帝国、游牧帝国、官僚帝国、殖民帝国等等,如此之多的类别既说明帝国的重要性,也折射出帝国研究的混乱,言人人殊意味着要总体把握帝国运行与演变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是非常困难的,对历史学而言,只有帝国的历史才能将帝国的逻辑说清楚,然而在各种帝国历史的作品中并没有对帝国的含义以及类型进行理论的概括与界定。帝国的内部结构以及运行复杂多样,难以进行理论的简约,而帝国边界则是可行的替代观察与研究的角度。
一、以边界界定帝国
帝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诸多帝国研究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或者从宗主国角度,或者从被征服者角度。而帝国的研究总是需要一个参照物,也就是现代主权国家。帝国区别于现代主权国家的特征在于它没有明确的边界线,或者说只有边疆没有边界,统治者扩张止步的地方就是边疆之地。
从政治权力边界而言,帝国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政体,帝国的中心会形成一个权力集中的统治机构;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帝国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国际行为体,在主权国家兴起之前,欧亚大陆的历史变迁是由几个大帝国的兴衰决定的;从帝国本身的权力结构而言,帝国又是一种国际体系。帝国的政治统治边界与文化边界、经济权力 (尤其是征税)边界并不能契合,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帝国有不同的形态与功能。综合各种观点,帝国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具有多重权力边界属性的人类组织。帝国的多重权力边界属性使之不可能有一条清晰的边界标示出帝国的疆域,现代历史地图中所划定的帝国边界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也是将帝国想象为主权国家。可将帝国等同于主权国家造成了一种“时代倒错”的问题,掩盖了从帝国到主权国家转折给国际关系带来的深远冲击。
帝国的多重边界属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第一,多重边界使研究者不能以现代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理论来研究帝国这种复合型的组织。第二,多重边界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稳定的帝国统治需要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容许不同的政治身份、文化传统、社会习惯共存于帝国这样一种组织之中。第三,多重边界也是冲突汇聚的地带,“边界总是陷入争端之中”,①[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多种边界意味着多重矛盾,帝国边疆是个各种权力网络混沌杂处的地带,一旦要划出清晰的边界,必然造成剧烈的冲突。“在两个毗邻的国家之间,通常都会有一块纷争地,它被两个国家轮番操控。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就成为一个烙上了双边国家的民族和文化特点的区域”。②[美]乔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宁娜译:《未来100年大预言》,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帝国的边缘地带在向主权国家体系演变的过程中多伴随着暴力与冲突,当下国际热点基本集中于曾经的帝国边缘地带,比如从北非到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欧亚大陆“冲突弧”。第四,帝国边界是帝国内/外区隔的地带,是一种模糊难辨的边缘地带,它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帝国权力结构与分布特点,而且也取决于帝国的外部环境,边界是帝国及其帝国以外的世界博弈与互动的结果。帝国边界的多重性使之无法在地理空间上将自己的边界固定,边界处于或快或慢的移动之中。秦汉帝国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北方游牧部落的征战中形成的,正如王明珂指出的,“不同的游牧化进程下,汉帝国北方周边出现不同的游牧社会,也是不同的华夏边缘”。③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与西汉帝国对峙最激烈的北方草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匈奴帝国,而在东北地区依然停留在部落联盟阶段。
从文化心理而言,帝国更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无论罗马帝国还是汉帝国都有“蛮族”的存在。蛮族既是帝国安全的威胁,也是帝国进行扩张的理由,即便在帝国强盛时期也无法彻底消灭蛮族,完成大一统的普世帝国的建设,因为帝国受到其边界的约束,边界的变动本身就是帝国演变与兴衰的“故事”。
首先,边界是一种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界限与区隔。不同的气候、地形分布等地理要素在地球表面上画出不同的生态界线,这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界线。各种资源构成了不同的资源界线,为了获取相关的资源,生存于地表的人群在各种资源边界线上移动并形成了与自然资源配置相符合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拉铁摩尔认为,边界是人类政治经济活动长时间累积而形成的,“当某种最主要的经济渐渐依赖于某种基本的条件时,建立于这些条件上的社会及国家在适应性及扩张性上就受到限制。当经济、社会和国家互相影响结合,便会达到一个最有利、最适合于它们的活动范围,也就造成了它们发展的地理与环境的限度”。④[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58页。无论中国的长城还是罗马帝国的长城,都以人为的防御工事框定了资源的边界,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的边界,也是自然环境的分界线,是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
其次,边界是一种心理空间构建。人类之所以群居,不仅仅是为了共同获取衣食来源还需要集体认同感。王铭铭指出,“传统国家的核心——边陲分化不是地理空间上看得见的距离之别,而是潜在于行政等级及象征差异中的社会距离”。①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核心区的文化辐射能力随着距离而不断衰减,从而形成了模糊不明的文化认同的族群。而族群的维系需要“依赖于边界的维持”,②[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页。而这一边界则是文化差异的标志,每个族群都需要一整套有限的文化特质来维持自己的边界。帝国的兴起并没有消灭族群的边界,而是囊括了不同的族群,而帝国的核心地带会形成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化,拜占庭帝国在罗马陷落之后维系了将近千年,它是东正教文明的代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能够延续下来也是依靠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帝国与文明往往具有同一性,帝国是文明的“代理”,因此帝国的边界也就有了文明的含义。帝国不仅要保卫自己的领土,更要捍卫自己的文化与认同,反对“文明”的敌人——蛮族。“随着文明的扩大、需要探索的新空间的扩展、对更广阔的地理以及更高的文化水平的获得,边疆的意义也不断发生着变化”。③[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帝国的边疆地带各种族群共处,从而形成了一个灰色和游离的文化空间。
最后,边界还是各种组织化的权力系统的界线。在一个复杂的组织之中存在着不同的团体,这些团体之间“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变动的边界,限定着其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④[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大致来看,团体之间的边界可以分为刚性边界和柔性边界两种类型,二者的区别在于,柔性边界的是可以跨越的,比如一些饮食、服饰等风俗并没有明确的边界;而刚性边界则明确划定了两个不同的团体,形成了明显的“我者”与“他者”的区隔。组织的边界也是框定了一种秩序,而秩序的维系需要政治组织、制度、以及权威,边界的存在意味着一个人要被约束在一种权力的笼子之中。
从边界来界定帝国完成了帝国研究的视角转换:第一,以边界为着眼点能够避免“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以宗主国为立足点,帝国研究也就集中于帝国兴衰之谜;从弱者或者被殖民者的角度研究帝国,容易陷入一种悲情之中,以道德的批判来代替帝国统治的逻辑。第二,以多重权力边界界定帝国能够打通帝国内外,通观全局。帝国的边界具有多重性,能够避免通过单一要素分析帝国的发展轨迹,或者以经济因素,或者以军事征服,或者以宗教改宗等,多重权力边界的伸缩标志着帝国的消长。第三,以边界作为研究帝国的核心内容能够完成视野的转换,从帝国繁荣奢华的都市中转向帝国生存所系的边界,能够重新认知帝国兴衰荣辱的历史。第四,帝国多重权力边界的属性是相对于现代主权国家边界合一而言,因此以边界界定帝国能够将帝国“带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之中,以此审视帝国与主权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帝国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化的权力形态,如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这些权力存在着不同的边界,从而造成了帝国中心—边缘、中心—空隙这样的结构形态。因此,对帝国的认知就需要与国家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帝国边界的角度入手,能够对帝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帝国也是由不同的权力构成的组织,帝国境内各种权力网络的分布不仅决定了帝国的结构,也塑造了不同的帝国形态。权力边界的调整便是帝国演进的根源与动力所在。一种理想状态的帝国应该是各种权力边界处于动态均衡之中,最终形成一种普世性的帝国秩序。衡量帝国在历史中的影响力需要兼顾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有学者以“面积—时限函数”(size-time integral,缩写为I)作为帝国影响力的指标,I指一个帝国将一定区域置于面积VS.时限之下的曲线,以百万平方米·世纪(缩写为 (Mm2c)为单位。①Rein Taagepera,“Size and Duration of Empires:Growth-Decline Curves,600 B.C.to 600 A.D.,”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3,No.3/4(1979):119.面积与时间成为衡量帝国的主要指标,而二者通过边界能够更直观地反映出来,边界的扩展与存续就成为衡量帝国的两个指标。从边界的延伸以及存续时间,可将帝国分为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两种类型。
二、两种帝国类型
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帝国形态,也是两种帝国生存的逻辑。前者生存于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中;而后者则存在于固定的空间之中。时间性帝国存在三种不同的状态:第一,边界时刻处于变动状态中,或者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或萎缩;第二,各种边界处于变动状态,在边缘地带成为各种势力交错争夺的地带,权力网络并没有呈现稳定状态;第三,时间性帝国中,多数依靠单一权力实现统治,或者军事征服,或者宗教教义等,权力边界的不均衡性增加了边界的脆弱性。
空间性帝国并不意味着这种帝国的边界是一种封闭状态,而是指代各种权力边界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相对均衡。中华帝国是空间性帝国的范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帝国虽然有所中断,但是屡仆屡起,延续几千年。空间性帝国既可以看作一种帝国的类型,又可以视为帝国发展的阶段。从时间延续的角度而言,空间性帝国有两层含义:第一,空间性帝国是帝国“进化”历史上的一种产物,形成空间性帝国需要更高的互动水平,在帝国形成之初,多数为支配性帝国,只能对周边有限的区域实现有效统治,呈现出强烈的中心—边缘的色彩,随着互动范围扩大,互动水平的提高,这种支配色彩就会淡化。第二,空间性帝国也是一个帝国走向稳定化、制度化的阶段,帝国从军事征服开始其创建过程,边界开始迅速扩张,是一种时间性帝国,等到军事征服达到其最大边界之后,便需要其他权力与之相配合,进而巩固征服土地。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罗马帝国在被征服地区扩大公民权,以此来强化被征服族群对帝国的忠诚。为了防止征服过程的逆转或半途而废就需要帝国从时间性帝国转向空间性帝国。空间性帝国最明显的标志是雄伟建筑的出现,如吉登斯所言,“在人类社会中,空间的固定性就意味着将场所固定在一定的‘建筑环境’中,特别是以城市的形式出现的‘建筑环境’。这种固定性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出发点”。②[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廉、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0页。伟大的帝国可能会灭亡,但它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大都市,比如罗马、伊斯坦布尔、西安等等。
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一种辩证关系。依据本文对帝国的界定,将对帝国的两种类型 (逻辑)进行分析。
首先,在军事上,时间性帝国呈现进攻性的倾向,而空间性帝国则采取防御态势。
“古代军队实际的军事打击范围比他们的思想家所宣称的要小得多,也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坚信的要小得多”。③[美]约翰·A.霍尔、G.约翰·艾坎伯雷著,施雪华译:《国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直到草原上发生交通革命之后,军事征服的半径才得以延展。随着马匹作为骑乘工具,草原民族在军事机动性上占据优势,军事征服或者慑服的边界会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但是时间性帝国的致命弱点在于帝国的军事权力是孤立的,后勤保障问题是时间性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帝国边界缺乏任何安稳的静止之地。其边界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军队造成的。……在所有帝国,地方居民和边地贵族的忠诚都是有条件的”。④[英]迈克尔·曼著,刘北城,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7年版,第225页。
征服,对于时间性帝国而言是生存的必需品,当征服停止之后,时间性帝国权力结构的脆弱性就会暴露出来。“罗马帝国早期有一种越过边界用战争来确定关系的倾向,到公元4世纪,当进一步扩张不再可能,罗马人别无选择,只好诉诸基于世俗形式的外交去稳定边界”。①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第186页。古典历史研究专家芬利认为,“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三百年里,罗马军队不在外作战的时间可能不超过十余年”。②[英]M.I.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页。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掀起了征服风暴,当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帝国分为四大汗国,可以说,“蒙古最终的立国建政,直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位时期方才完成”。③[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由于时间性帝国意在扩张,防御战略中并不占据优势,他们对领土的征服欲胜过占有欲,征服“蛮族”成为帝国扩张的动力。然而,“蛮族并不是一个来自远方的有着固定领土的势力,而是从一个领土基地迁往另一个领土基地的名副其实的时间性势力……其灵活性的本质又使蛮族的重要意义表现为更具地方性,而非地区间性质”。④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第202页。时间性帝国虽然可以慑服广大的地域,但是其军事权力集团规模并不大,一旦军事首领死去,帝国便陷入崩溃,被征服地区又重新回到地方武装集团的状态。典型的代表是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最终广大的帝国一分为三。
空间性帝国在军事上多采取防御性战略,至少是攻防兼备的战略。自中国战国时期,北方的燕国、赵国、秦国便开始修建长城防御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入侵,罗马帝国也在北方蛮族地带修建了防御性长城。这些防御性工事便是空间性帝国的标志,也是帝国防御心理的外化。中华帝国历史上曾经多次以和亲或互市等防御性策略与时间性帝国保持边境的安全与和平。空间性帝国之所以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性战略在于它的边界已经相对稳定,帝国呈现稳态结构,进攻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势必会对帝国造成侵害;其次,空间性帝国存在“自然边界”,过分扩张要承受边际成本急剧上升带来的烦恼,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同时不得不增加税收筹集战费,汉武帝晚年停止远征也是帝王雄心对距离的屈服。
其次,在政治上,时间性帝国未能完成权力集中化的过程,而空间性帝国则实现了统治的规范化、制度化。
人类学家对比几种不同的游牧部落的社会与权力结构发现,流动性越强的部落,其权力越呈现流散的性状;越趋于定居生活,权威越容易建立。游牧部落的生活中,血缘关系是重要的纽带,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氏族与部落,都与血缘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寻找共同的祖先,进而形成超越家庭之上的组织团体,庞大的游牧帝国虽然地域辽阔,但是其社会组织却相对单一与原始,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官僚机构,最高首领的命令很难在千里之外生效,另外游牧部落具有很强的移动性,如果不愿服从就可以迁移。⑤[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孙岳等译:《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页。时间性帝国依靠血缘关系建立起来,帝国依靠统治家族的权力。韦伯认为,“在建立大帝国的民族中,家族共同体内部的财产法结构的发展,是不断削弱父亲的不受限制的权力”。⑥[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17页。建立长久有效的政治统治,就需要实现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变,这正是时间性帝国的软肋所在。
从合法性 (权威来源)的角度而言,时间性帝国基本是由克里斯玛型权威领袖建立起来,因人而起,人亡则政息;空间性帝国则是传统型或者法理型。“个人魅力只能为克里斯玛型权威提供一个片刻的、短暂的生存基础”。⑦[美]罗伯特·杰克曼著,欧阳景根译:《不需要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马克斯·韦伯认为,“魅力型统治按其先天的形式,具有特别非凡的性质,是一种严格与个人,即与个人的魅力品质的适用及其经受实践考验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然而,如果这种关系不再纯属短暂的,而是具有持久关系的性质……那么魅力型的统治就仅仅存在于纯粹理想类型的起源状态之中,这必然会大大改变它的性质:它将传统化或者合理化 (合法化),或者在不同的方面,二者兼而有之”。①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74页。
政治权力在各种权力构成的网络中具有枢纽作用,它能够集中并平衡各种权力的边界,使帝国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合法性从克里斯玛型向传统型或者法理型转变需要继承方式的转换与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创建,否则时间性帝国便会面临“朝生暮死”的命运。
制度的稳定性依赖于权威的合法化与制度化,只有摆脱对个人权威的依赖,才能实现组织的有效与有序运转。中国在古代世界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和稳定的政治权力架构,许倬云先生说:“中国的政治结构,相对于同时代的罗马、波斯和印度,具有较明确的制度化,不至于完全依赖皇权的人治和贵贱的阶级特权。”②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而跛子帖木儿创立的帝国在其死后便陷入纷争之中,因此有学者认为,“1405年帖木儿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③[英]约翰·达尔文著,陆伟芳、高芳英译:《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衰》,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页。帖木儿之死意味着他筹划的远征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同时也意味着自阿提拉、成吉思汗等来自草原的“世界征服者”时代的终结。
官僚体制是维系政治权力有效运转的关键所在,官僚制度是理性的外化形式,官僚制度是理性与纪律的结合体,虽然存在低效与冗繁的缺点,但是相对于时间性帝国中的家族政治,无疑是巨大的进步。拉斯韦尔认为,“危机要求专政、集权、集中、服从和倾向性。危机的间歇期则允许对民主、分权、分散、首创性和客观性作出让步”。④[英]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6页。政治权力的松弛都是需要建立在稳定有效官僚制度基础之上,否则,政治权力只会沦为暴力。
与时间性帝国相比,空间性帝国具有程序化的继承制度和完整的官僚体系。嫡长子继承制度虽然不能保证将最有才能的人扶植到最具有权力的位置,但是却保证了继承的有序化。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和官僚制度能够使帝国应对内外危机与挑战。秦汉帝国建立了一套包括官僚制度和道路网络在内的讯息回馈体系,从而保障了帝国在相当长时间里能够基本稳定运行。⑤许倬云:《大国霸业的兴衰》,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8页。
罗马帝国也经历了至关重要的转折即从时间性帝国向空间性帝国的转型,多伊尔将其称为“奥古斯都门槛”。“罗马帝国实际上是城市国家构成的盟邦 (federation),一个以武力强制为基础的盟邦,只是到了安东尼、图拉真时代才被逐渐自由地接受与认可”。⑥S.A.M.Adshead,“Dragon and Eagle:A Comparison of the Roman and Chinese Empires,”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Vol.2,No.3(Oct.,1961):16.
第三,在经济上,时间性帝国未能建立起弥散性经济网络;而空间性帝国则实现了帝国境内经济秩序的有效调控。
游牧帝国是典型的时间性帝国,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以“移动”来标识的生产模式。只有在广大的草原上移动才能维持生存,尤其是顺应季节变化而在不同的牧场之间移动,可以说,这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生存方式,从而形成了一套迥异于农耕民族的上层建筑,他们对土地使用权的重视远胜于所有权,因为他们“逐水草而居”,水草才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哪里的水草并不重要。因此,游牧帝国生活在“时间”的脉络之中,他们对于季节的转换更为敏感,因为数千亩土地才能养活一户人家,游牧民族通过“移动”才能占有与使用土地,因此,与其说他们被关闭在空间的牢笼中,莫不如说他们是时间抑或时机 (timing)的奴隶。
经济权力需要更为细致的权力基础,货币、市场网络、安全秩序都是经济权力存续的基础。空间性帝国不仅在帝国境内建立了稳定的安全环境,扫除盗匪,荡平割据势力,而且还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运河、驿站等交通通讯体系。这些都是时间性帝国难以企及的。此外,空间性帝国还在帝国政府中建立了经济部门,通过征税汲取国内资源,维护市场秩序。“像罗马和迦太基这样可以兴盛数个世纪的帝国通常是因为它们实现了一种商业繁荣,而商业的繁荣使帝国境内的经济精英与统治者达成同盟”。①Martin Walker,“Wkat Kind of Empire?”The Wilson Quarterly,Vol.26,No.3(Summer,2002):40.
最后,在意识形态上,时间性帝国没有建立稳定的认同感;而空间性帝国则拥有稳定的意识形态体系。
持续而稳定的互动是帝国维持长久统治的关键要素,在频繁的互动基础之上能够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空间,最终形成认同感,古代帝国在塑造文明,而这恰恰印证了认同是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的文化身份是形成国际社会的前提,但共有的身份是历史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文化的力量和吸引力对其统治的持久性及其影响至关重要”。②Dominic Lieven,Empire:The Russia Empire and It's Rivals,London:John Murray Ltd,2000,p.xvi.
在普世性宗教诞生之前,“宗教都是地方性的,与特定的部落或者聚落相联系”。③Viscount Bryce,“Religion as a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Empires,”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5(1915):2.王明珂指出,“游牧民族志数据显示,一个以共同部落名号及共同记忆凝聚的游牧部落,其历史可能很久远,但其族群范围、边缘与内部成员可能因情势而有相当变化;所谓‘因情势变化的族群认同’(situational ethnictiy),最常见于游牧社会之中”。④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第104页。这种地方性的认同感难以对帝国的巩固有帮助,时间性帝国难以形成稳固的身份与认同,草原民族信奉原始的萨满,即便征服了南方的农耕帝国,也无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占据统治地位,蒙古帝国之下的四大汗国很快被同化。
在普世性宗教诞生之后,宗教信仰成为促成时间性帝国诞生的精神基础。伊斯兰教使穆斯林征服的广大地区在公元800年之后的几百年之间“种族、文化分隔迥异的统治贵族发生了高度的同化,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兄弟意识 (sense of brotherhood)和隶属于共同体的意识”。⑤W.Montgomery Watt,“The Place of Religion in the Islamic and Roman Empires,”Numen,Vol.9,(Sep.,1962):112.普世性宗教带来了扩大的心理认同边界,但是内部的教派纷争及其对异教徒的征伐使宗教纽带难以演变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因而,神权帝国也难以摆脱时间性帝国的宿命。
空间性帝国则在建立统一的信仰方面用力颇深,罗马帝国的皇帝崇拜、汉帝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都是为了建立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权力基础。当然,空间性帝国内存在多元的信仰与身份,但是必然有一个主流的价值观在统摄各种民族、种族、宗教的人群。只有帝国境内的各个族群相信:“这是我们的帝国”时才能保证帝国的稳定。罗马帝国的稳定延续与公民权的扩散有重要的关系,罗马公民已经突破了地缘与血缘的限制,而成为一种政治认同。
三、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边界的廓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退场,即便是拥有长久历史的空间性帝国也已经被民族-国家取代,联合国成员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迅速增加。然而,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缘地带,也就是多重权力边界交叠的地区,要建立起具有自我治理的国家殊非易事,民族-国家意味着将各种权力边界合一,边界的廓清意味着权力的调整,也就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边界与权力实施的边界必须合一,比如一个国家不能跨过界碑对另一国人民进行征税或者审判。
欧洲迈向主权国家体系的过程伴随着无休无止的战争,即便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欧洲国际关系还是按照王朝政治的原则运行。①[英]贝诺·特士科著,李清敏、孙兴杰译:《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之理论化:国际关系从绝对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向》,《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而王朝政治将家族利益放在首位,领土边界的变迁与王室联姻关系密切相关,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到1806年才被拿破仑推翻。因此,欧洲边界调整的过程也是非常漫长与痛苦的。欧洲扩张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奥斯曼帝国,而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交汇,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均有利益,三个帝国的边界在巴尔干地区叠加在一起,各种权力的边界可谓犬牙交错,要在这样一块区域建立主权国家必须将处于“混沌”状态的边界廓清。与欧洲国家一样,廓清边界意味着流血冲突,巴尔干地区就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火药桶,从南斯拉夫王国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均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冷战结束之后,从波黑战争到科索沃战争,巴尔干经历着血腥的边界调整过程。而现在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体系,这应该算得上是巴尔干回归自己的历史宿命,即作为帝国的边缘地带,主权国家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帝国边缘地带的转型。
那些被迫转型的古老帝国不得不重新划定与定义本国边界,从有边疆无边界的帝国向有明确领土边界的主权国家的过渡意味着边疆地带或者被吞并或者变成独立国家,土耳其、伊朗等帝国都是如此。这种转型可以被视为国家的再造,或者说“再构建国家”(rebuilding state)②刘德斌:《国家类型的划分——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思路》,《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主权国家与民族主义的联姻使帝国中心与边疆同时进入“建国”的进程,这一过程至少导致了三种结果:其一,帝国中心地区拥有比较稳定成熟的国家机构以及国家认同,向主权国家的转型也相对顺利,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战之后“崩溃”,主要是帝国的边疆地带几乎丧失殆尽,而继承帝国衣钵的奥地利、土耳其则完成了国家再构建的使命。其二,在帝国边疆地带,长期以来保持与帝国中心的“轮毂结构”,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更谈不上成熟的公共管理机构,很多地区是从部落跨入主权国家的俱乐部,从而产生了部落式的国家,北非、中东以及中亚地区存在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有主权国家之名,但无主权国家治理能力之实。“阿拉伯之春”暴露出从奥斯曼帝国边疆变身为主权国家之后,很多国家的治理能力非常低下,国家构建处于进行时。其三,帝国中心与边疆同时走向建国之路,造成彼此之间芥蒂与怨恨,国家认同必须寻求“他者”(或者敌人),帝国中心并不愿意看到失掉边疆,而边疆则力图脱离帝国,两者之间的对立与战争不断,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就是几个巴尔干小国联合起来对抗土耳其,试图终结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吊诡的是,打败奥斯曼帝国之后,巴尔干的小国很快就陷入“内战”之中,因此帝国边疆地区并没有形成有机的联系,帝国统治衰弱或者终结之后,边疆地区就陷入“裂变”之中。20世纪60年代之后,新独立国家基本是裂变而来,苏联帝国的崩溃出现了十几个独立国家,帝国边疆的裂变还在继续,比如乌克兰危机以及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等。
当下世界秩序的危机一大根源来自于昔日帝国的边疆地区陷入持续“裂变”之中,难以建立其稳定的边界合一的民族-国家,却又很难退回到帝国时代。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就建议美国应该承担其帝国的责任,因为美国不敢称自己为帝国,也不向落后地区提供资金、人口与文化,这是国际安全的一大威胁。③[英]尼尔·弗格森著,雨珂译:《帝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22页。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虎头蛇尾式的战争并没有真正提升这两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帝国边缘地带要建立起稳定的安全秩序并非易事,巴尔干地区是个例外,再次融入欧盟体系之后,巴尔干地区的“裂变”可以暂告段落。美国能将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边疆再次纳入一个帝国体系吗?奥巴马的“战略再平衡”政策意味着美国不愿承担中东诸国“重建”的成本,虽然诸多美国学者要求美国要注重战后秩序的重建,缝合破碎地带。④[美]托马斯·P.M.巴尼特著,孙学峰、徐进等译:《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后帝国时代,全球治理依然面临着帝国留下的沉重的边界遗产,2008年之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开始退潮,地缘政治回归,而昔日欧亚大陆帝国的多重边界相交之地再次成为国际秩序的威胁。这是一个没有帝国的时代,同时又受制于帝国遗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