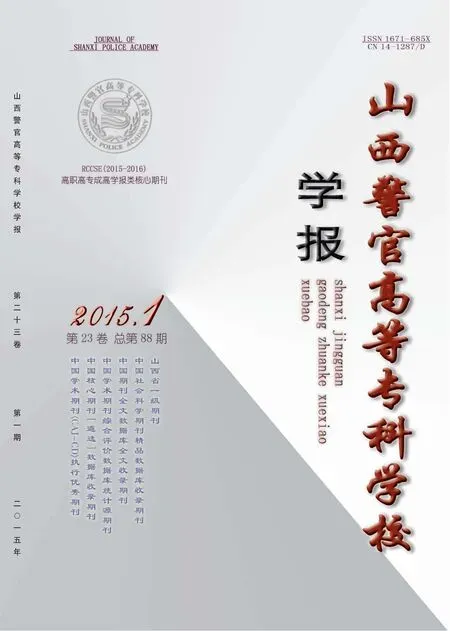梁治平法律文化论逻辑理路的反向思考
□杨之涵
(西藏大学政法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法学研究】
梁治平法律文化论逻辑理路的反向思考
□杨之涵
(西藏大学政法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中国文化渊源流长,依凭历史理性,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前者应当发扬,而后者则应剔除。中国法律文化应摒弃其潜藏的诸如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等文化传统元素,从深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扬光大,而不是深陷“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梁治平法律文化论式的错误解读,从而为“回”到当下的中国作出应有的努力。
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中国法律文化;梁治平法律文化论
一、中国传统文化前途的反思
(一)历史性背景
余英时在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中说,有时“退回”“乃是最积极的进取”,“退”是为了“回”。[1]
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已成常态化,在“打倒孔家店”与全盘否定传统的声浪中,中国传统文化已渐行渐远。至此,中华文明的文化优越感销声匿迹。相反,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遭受了太多苦难的中华民族,内外交困的中国人民,在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上,知识精英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认为国家衰败的根源是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所致,欲使民族跳出落后挨打的藩篱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抛弃传统而拥抱西方。批判的力量一再急剧膨胀,批判的指向也越发一路高歌猛进,丝毫没有停下脚步或掉转方向的征象。以致到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几乎听不到异样的声音。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往的深入与国力的渐长,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的号召渐成气候。余英时、杜维明等新儒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也被大量引介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
中华文明已历经五千余年,如果把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比喻成一个恰好是一百岁高龄老人的话,那么近代以来不到二百年的屈辱历史还不到这个百岁老人的4岁,而传统文明却历经了96岁之多。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4岁就简单否定这个沧桑老人走过的96岁的坚实脚步。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其正确与否,而是以其历史的跨度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传统文化的成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想当然地粗暴抹杀与随意篡改的。中华民族是在传统浸染下的民族,中华文明是在传统文化的庇佑下唯一未被中断而一直连续的人类文明。其历史之久远,影响之深刻,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血管里流淌的一直是传统文化的血液。这不仅是过去,而且更是现在与未来。
或许在“国将不国”的动荡历史中,非理性的声音淹没了理性的呐喊,充斥的大多是情绪化的话语暴力;也或许内外交困的乱局里,民族悲情主义与激进主义滥觞,以致矫枉过正,这些都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新千年的当下,在上述二者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还一味地只是彻底否定与简单批判传统文化就变得不可原谅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佛学、道家的强有力挑战与冲击,但是,传统文化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分崩离析,尔后改弦更张,而是儒释道三家相互吸收借鉴,最终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更为开放、完备的传统文化体系。如果把这一时期视为一种“退”,唐代的全面强盛视为一种“回”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1840——1919——1978年代以来这一脉历史作为一种更广阔视野下的“退”。
但令人遗憾的是,时常在我们耳边回响的却是激进主义的喧嚣。[2]
其实,当下我们需要的是“退”之后的“回”,即需要的是“退”之后的悄然转身,擦亮眼睛重新审视我们的自身。
然而,我们应该怎样地“退”,又应该怎样地“回”呢?或者,更确切地说,“退”应该“退”到何时,又应该“退”到何处?“回”应该“回”到何时,又应该“回”到何处呢?
(二)传统文化的“退”
在“退”这个问题上,李慎之先生的论述很有启发。李慎之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中论述到:
“必须分清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如果是前者,可以继承发扬的当然是极多的;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以为无论如何不能继承作为顽固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只要拔除了专制主义这个毒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部分,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可以而且应该继承发扬,即使儒家与法家的学说,也都有应该继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古人的许多嘉言懿行都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的民主之一的源头。”[3]
在这里,李先生首先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进行了精心的切割。照此理解,传统文化应该是指中国数千年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文化遗存;而文化传统却是封建皇权专制主义。
区分并切割这二者,我们可以剔除专制主义的“毒根”,又可以毫无顾忌汲取传统的营养。
同理,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应该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剔除过时陈旧的专制主义毒素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内涵,进而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切有益元素。
(三)传统文化的“回”
“回”就是应该“回”到当下,“回”到未来。
实际上,在我们真正明白“退”之后,“回”的问题也不再是个棘手的难题。既然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及现实存在不能抹杀,那么,从传统文化汲取养料也就变得无可厚非了——因为,就目的而言,一切“退”都是为了更好地“回”,“退”“乃是最积极的进取”。这种目的性指向意义,同史学界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异曲同工。
还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退”与“回”是一个开放而不自我封闭的体系。它并不是简单地“退”到个别原始的基点或“回”到当下某些激进的误读上,而是在认同传统文化的根基性的前提下,批判性地借鉴与吸收一切外来优良的文明,进而进行创造性转化与整合的体系。
二、传统文化命运下的中国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子集、一个部分,中国文化的命运自然也就决定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命运。毕竟,部分背离不了整体,偏离不出整体的历史大方向。这也就是通常说的整体决定部分的哲学原理。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的命运决定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命运。唐朝时期中华文化繁荣昌盛,中国法律文化也随之方兴未艾;而近代以来,传统文化遭受空前危机,中国法律文化也跟着摇摇欲坠、分崩离析。可以说,中国文化兴盛则法律文化也兴盛,中国文化衰败则法律文化也衰败。所以,中国法律文化必须依存于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中国法律文化的症结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解决中国文化的困境,只有在整体的文化观视角下才可以避免法律文化一叶障目的危险,而不只是单纯地就法律文化而论法律文化。
因而,正如前所述,在传统文化“退”与“回“的理论预设下,也可以同理可证式地把中国法律文化的种种遭遇视为一种“退”与“回”。即把1840年以来中国的诸多遭遇看成是一种“退”,看成是一种为前进、为“回”——“回”到当下,“回”到未来——而作必要的“力量积蓄”与“忍辱负重”。在这种“退”与“回”中,我们重新发掘其固有的价值与内涵,摒弃其表面或潜藏的“糟粕”。这样,才不至于如当下世面上所充斥的那样,不是不问是非的矫情浮夸,就是不管青红皂白的来个彻底批判,而没有做到真正的理性哲思。
或许有人说,对我们这个遭受太多苦难的中国来说,这样的“力量积蓄”太过漫长,这样的“忍辱负重”也太过悲凉。不过,这也不妨是个新的视角——就像邓小平所说的换脑筋——来看待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棘手难题时,会不会有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的可能,从而给我们一种新的启迪?
三、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粗浅解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股法律文化研究的热潮,梁治平无疑是众多研究者中的佼佼者。梁治平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构建起来的以探寻不同法律制度异同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上的根本缘由为基本路径的“法律文化论”,显然比80年代的大多数法律论者的研究要深刻得多,他的研究告诉我们法律制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功能系统,他从根本上受由特定社会环境的观念、意识、价值等要素构成的“文化类型”的支配。[4]
根据这种“文化类型”对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或“决定论”,梁治平在对个案的分析中指出:“比较的目的是要找出异同点”。[5]要真正理解它们必须进入这些术语背后去追寻各自在文化上的依据。而且,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采用了一种语词分析的方法。梁治平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其实是与他强调语言或语词与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法律制度之间具有高度同构性的假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194-195的确,这种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仅试图透过对“法”、“律”、“刑”、“治”“礼法”等语词的严格分析是很难揭示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种具有几千年传统复杂的鲜活的历史文化,更不要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予以一种“同情的理解”。[4]194
不过,梁治平这种以“文化类型”决定论为基础的“法律文化论”,把有关法律的认识从“制度层面”推到“文化层面”确实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乃至中国法学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论述的中国“文化类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根据西方的“文化类型”加以型构或评价的。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认为,“谈论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能不加入关于西方法的考虑;讨论中国法的现代化问题,也必须在这一背景。”[5]132,[4]184例如,他在研究的过程中根据西方的“文化类型”对中国法律文化进行对比评价后认为中国产生不了发达的私法文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缺乏权利意识。认为中国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就其自身性质而言,中国古代法实在不能适应这个世界的要求,注定要在社会‘自然竞争’中被淘汰”。[5]56实际上,梁治平在这里有意无意地且隐蔽性地预设了一个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判断的依据。
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是一种以辨异为基本途径的“文化类型学”,这一经由中西“文化类型”的辨异和评价的理论认为,中国“文化类型”以及由其决定的中国法律制度必须予以彻底的清算和彻底的否弃。在他看来,第一,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之所以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实是因为中国“文化类型”无法适应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和要求;第二,中国“文化类型”的整体性和同质性又在根本上规定了它的不可通约性以及它的变迁或修正的不可能性。[4]191正是根据上述两种基本的规定性,梁治平得出结论认为,欲使中国法律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必须以西方的“文化类型”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类型”,换言之,在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仅仅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并非足够有效,还必须彻底地移植西方“文化类型”。[4]191
在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的研究路径中时时隐藏着一种被邓正来称之为“‘文化基因’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西方发达的法律文化早在其最初的文化“胚胎”中就决定了,同样中国现今的法治现状亦由我们文化中“胚胎”决定着。[4]198-200惟有彻底否弃其原有的胚胎、移植进西方文化这一新的胚胎,才能使中国法律制度的改革发生性质的变化。同时,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受如邓正来所称的“现代化范式”支配,直接把经验层面的西方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或价值,转换成具有评价中国法律制度功效及其道德优劣之判准意义的理想图景。[4]20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主张把西方的文化都移植到中国来。
梁治平上述一系列研究路径与思维模式,在根本上决定了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去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当下现实,更不需要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思量。因为,根据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中国所有当下的现实,在本质上早都由他所建构的中国固有的那种“文化类型”之胚胎决定了,而且关于中国现实的“答案”也完全可以从对他所定义的那种“文化类型”胚胎的分析中获致,彻底否弃其原有的胚胎、移植进西方文化这一新的胚胎,是中国法制改革的唯一出路,别无他途。这陷入了宿命论的论调——按照这一论述,就中国法律文化自身而言,古代的中国,不管怎样的努力,也改变不了这一历史的方向吗?
依凭这一逻辑理路延伸开来,中国文化只能推倒重来。不仅优良的传统文化要彻底摧毁,更不必说带有“糟粕”性的文化传统了。然而,文化这种东西不是像建筑物那般,可以彻底摧毁了再造,它是不能全然地砸碎与所谓的不破不立——文革中所倡导的这一观念的破产就是一个明证。如果说要有所改变的话,那么文化只能是一定意义上的改造,即通过注入新的元素到传承下来的文化精华,再进行有效的整合与良性的互动,才可能成功。
四、反向的思考
(一)前提性说明
应该关注的是,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子集,它有与中国文化共性的一面,但由于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也有其自身独特的一面。把其纳入这种“退”与“回”的理论框架下,需要深入挖掘其特性的或者说独特的一面,而做好这一面还需花费很大的力气,以免在重新审视时又误入梁治平“法律文化论”式的错误解读。这一特性本身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与西方法一样,有其自我可欲与本身良善的一面,这一面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流逝,反而被历史的长河与传统的文化所固化并传承下来。比如,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天地人这个大系统的一分子,这一“天人合一”思想对当下的中国甚至全球环境法的发展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当下的中国与世界,深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所形成的物质主义及消费主义的影响,并作为一种普世理念传播,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滥用和环境问题与环境灾难日益突显。中国传统哲学可以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终极意义上的哲学关怀,这对解决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具有巨大的指引作用,从而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文化本身与政治制度或权力政治的联系极为密切,以致发生变异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都极高。这是与权力纠缠不清或相互纠缠的必然结果。而且,法律文化特性中“恶”的一面还与前述的中国文化共性中诸如专制主义、民粹主义毒瘤彼此牵连作用,以致“恶”“恶”相碰,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使得原初意义上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愈加偏离了它自己良善的轨道,从此渐行渐远,甚至南辕北辙。
对法律文化的解读,对特性中的二面都应同等看待,不能厚此薄彼。但是,当下的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却似乎比登天还难,尤其在看待特性中的后者方面来说,都或多或少地误入了梁治平“法律文化论”式的错误解读。只不过有的偏颇激进,而有的看似公正罢了。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就是在这种变异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中寻“词”摘句的,即更多地是从集权制度下被扭曲、被阉割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中所作的各种他认为颇为有效的语词分析方法进行文化的比较研究。[6](如“法”与“law”的概念性比较)此种从变异而非原生态或初始意义上的文化所作的各种努力研究,其结论也就很让人生疑了。试想,西方法学者如果从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黑暗面中寻找更多的法的精神与理念,估计他们也大多会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因为只从黑暗面(即认为法学只是神学的婢女与附庸)出发,而对光明面视而不见,那么,这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无论再作怎样的努力,注定都徒劳无功。他们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所以,要寻找中国法的精神与理念,我们也不能更多地从集权制度下变异了的法律文化下进行探究,而是应从先秦儒家和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甚至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中,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本。
(二)只看“优”与“好”——即只就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
然而,现实的情况远不是想象中的那般。有的论者只看中国文化的“优”与“好”,而对其“劣”与“坏”视而不见,认为所有的中华文化都是好的,是全世界最优良的,不容半点批判。典型的代表如倭仁和辜鸿铭,特别是辜鸿铭,尤显得可爱。这位号称精通13种语言,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步入了民国,头上仍旧是拖着清代的长辫,身上仍旧穿着旧代的长袍,讲学布道,在向西方弘扬中华文明的同时把纳妾与留辫子都当作中国国粹,蔚为大观。
辜鸿铭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且成了他特有的一大癖好。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7]
美国的妇运分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鸿铭争论这个问题,最后辜鸿铭问她:“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有四个。”“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当然是用一个。”“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7]
这种只就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把文化传统也当成了传统文化,自高自大、不加明辨地予以全部吸收与继承,泥沙俱下,又有多少意义呢?
这正如同前面李慎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对于中华文化,应该首先分析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对于前者应当发扬继承,对于后者则应该否定剔除。不能只看其“优”与“好”,而忽视了其“劣”与“坏”的一面。
然而,什么又是中国文化的“优”与“好”,或者更形而上地说什么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呢?
个人认为,中华文化的一大亮点就是其包容性。远的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传播,日益挑战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遭受了空前的文化危机。但是,中华文化并没有分崩离析,而是儒释道三家相互交融、兼收并蓄,重新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随后的唐朝也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吸收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与外国文化,中华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古代中国封建政权的更迭中,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也不乏其例,如元代的蒙古族与清代的满族,但中华文化并没有被这些游牧民族的文化所击败,反而这些权力统治者被博大的中华文化所同化,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力量。如果以近代中华文化所有的悲惨遭遇,对比以上的历史史例,不由得心生一问,中华文化能否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进而重新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再一次地走出其与当年似曾相似的当下中华文化的巨大危机?
此外,诸如儒家的“民本主义”,中华文化的和谐性主张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等等,都是可待发掘的文化宝库。
(三)只看“劣”与“坏”——即只就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
但是,更令人担忧的是,比起只看“优”与“好”来说,只看劣与坏,即只盯着文化传统,只就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无视优良的传统文化,更占据了思想的市场份额。自“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的衰败都是传统文化惹的祸,进行了全力的批判。虽然,当下的中国学人不至于这般的激进了,但“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取向仍旧得到继承,很多学者也以此为荣。这正如梁治平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最近几年里面,我听到和读到对我那些已发表的文字的各种评说。一位域外的评论者……说我继承了‘五四’传统,而能以冷静的学术研究作基础,全面批判传统,探索中国文化的自救之道,是成熟的‘五四’青年。[5]281
其实,这种做法并不比只盯着中国文化的“优”与“好”危害更小,相反,它为祸尤烈。
从现实的层面来看,无论进行何种法律制度的改革乃至法律文化的移植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一直的庇佑着我们。想要超脱这一现实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移植西方文化类型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的变革绝非一朝一夕之力可行,文化传统的识别、剔除也绝非一蹴而就。假如我们简单地否定中国文化,不加区分地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连同变异的文化传统都给彻底铲除了,移植了西方文化类型,到那时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会惊奇发现:原来西方文化类型也不适合我们。这时想回头,已为时已晚,因为我们早已经把自己的文化根基丧失掉了。文化根基的丧失也意味着民族性的丧失,这是不是更为祸不浅?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一悲剧呢?
其实,答案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要义之一就是要着力鉴别并剔除文化传统。但是,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呢?
或许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是这一问题的最主要答案。
对于什么是专制主义,我们还是可以作出比较明晰的辨识。它与民主相对,不是多数决定少数,而是少数决定多数。它是赤裸裸的权力决定论,谁最有权力,谁就掌握了真理,权力可以理所当然地强奸公意,成为任凭自我情绪好恶行事的恣意者,全然不顾权力与真理是否会真的天然联姻。
而对于什么是民粹主义,或许比较难作出区分,在这里引用以下给出的一种可能答案,或许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认识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是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但他们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8]
当下的中国必须极力反对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防止如文革那般借着人民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彻底地清除文化传统。
(四)一点反思
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的一百多年历史,透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一次次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自高自大、不加明辨地全部吸收与继承中国文化,是不能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完全否定中国文化,也不能让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文化支撑与精神食粮。过往的历史中,我们不是单只眼睛地盯着中国文化的“优”与“好”,就是单只眼睛地盯着中国文化的“劣”与“坏”,这些都是不足取的。其中的教训之大,也不用再添笔墨。在东西文化相互撞击的岁月里,我们就是在这两个历史怪圈中轮回,各自的论者总在自己单一的话语圈中顾影自怜、自说自话,极度缺失了用二只眼睛全面地看待问题。譬如,进行的一波波“洋务运动”中,我们只是单只眼地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远胜于西方,不如的只是技术而已,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而“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也是单只眼地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尤其是中国文化,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最终仍旧惨淡收场。
中国文化如此,中国法律文化何尝不是如此呢?
中国法律文化本身就与中国文化一样,存在着文化传统这一共性的一面,加上,中国法律文化与政治权力密切联姻,出现的变异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就使得中国法律文化更加复杂,迷局环生。种种的迷局和非理性的情绪化话语暴力相互叠加,中国法律文化从此被打入了冷宫,再想回过头来理性地对待,已是难上加难。
法律文化的这种状况进而影响了现实的法律制度。一方面,优良的法律文化被粗暴地抛弃,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法治理念也未被适时消化或有意无意地念歪了经,使中国现实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往往出现了像贺卫方笔下的所说的“申公豹”式的前进,一边前进,一边后退,前进就意味着后退,走不出历史的循环。
(五)小结
我们不断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并加以引进吸收。这些历经西方社会实践、完善的“它山之石”被我们直接用来“攻玉”,相对于我们落后的现代化进程诚然是一种巨大的前进。但我们在前进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西方的月亮就是圆的”、“它山之石就是金”,以“他山之石”作为价值判断的基准去判断我们固有的体制与文化,进而得出它一无是处而加以彻底的批判与否定,而忽视了其中某种先进的至少是适宜中国社会的基因与细胞,与引进吸收的“前进”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后退”。其结果使我们不断地引进与吸收却不能最终消化,不能建构一种适合中国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法律体系与理念。
另一方面,我们在对西方先进法律制度学习引进的过程中,几乎在所有的领域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水土不服”的现象。一些先进的制度设计往往因我们缺乏相应的文化观念为依托而被“架空”,不得不充当“花瓶”的角色。在学习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同时,介绍与引进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确是现今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所必须的。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像梁治平先生所主张的那样彻底地批判与否定传统文化,以西方先进文化为模子而重构中国“文化类型”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而法律文化也差不多的同样久远),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这一传统文化的庇佑下繁衍生息,期间有傲立东方的辉煌,也有短暂的“国将不国“的屈辱史。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中华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同样的文化氛围中经历过辉煌与衰败的天壤之别;我们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礼法文化”为根基,也可以“打到孔家店”……这些中国文化生死成败冰火两重天的命运,清晰地表明我们的中国文化有着其优秀深邃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面,也有其无法回避的一些“劣根性”。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时的落后而断然的全部否定文化遗存,将一切罪责归因于中华文化。
五、余论
太过漫长的集权制度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把许多不利于集权统治的优良文化都给阉割掉了,远的如秦朝的焚书坑儒,近的像清朝的文字狱,严重戕害了中国文化。历代封建王朝不断地权力强化与政治阉割,不仅先秦诸子百家饱受践踏,而且儒家思想自身也倍受摧残——这种摧残是权力统治者对其进行自我筛选与正确“误读”的逻辑结果。这种自我的筛选或正确的“误读”和强力的政治权力相互交织,逐渐走向了不归路,思想日益丧失了其独立的品格,成为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强力者可以进行恣意地取舍与涂抹。
这也影响到了今人对源渊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法律文化的同情理解与理性认识,造成了当下思想的极度乱像,这不仅让局外之人迷惑难解,也让局中之人倍受煎熬。一方面,我们妄自尊大,不可一世;另一方面,我们又妄自菲薄、全部否定。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无疑是后者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有意无意地且隐蔽性地预设了一个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判断的依据,并不能做到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同情的理解”。梁著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持彻底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只不过他把后者“形而上”的给概念化为“文化类型”,论述得更加隐蔽,也更加不易发现罢了。
当下重新崛起的中国给了我们挺起胸膛,冷静思考的历史机遇,在这一历史机遇下,不允许我们在这两种极端的思想倾向中徘徊游走。只有屏弃专制主义毒瘤的文化传统,继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同时,大力引介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与法治理念,相互吸收,取长补短,才是我们当下中国文化的正道,也是我们当下中国法律文化的正道。这是历史给我们作出的唯一选择。
[1]王人博.初创与奠基:张晋藩先生两部早期著作的价值[A].朱 勇,王人博,张中秋,等.读书读人:张晋藩学记[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余英时.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62.
[2]薛 涌.中国文化的边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35.
[3]王学泰.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怀念李慎之先生[N].南方周末,2008-04-24(23).
[4]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179.
[5]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0.
[6]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国学大师辜鸿铭: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EB/OL].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7-04/26/content_8175094_6.htm
[8]刘 诚.什么是民粹主义[N].环球时报,2005-06-29(9).
(责任编辑:王战军)
Counter Thinking on the Logic of LIANG Zhi-ping’s Theory on Legal Cultures
YANG Zhi-han
(SchoolofLaw,TibetUniversity,Lhasa850000,China)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lture tradition.The former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the latter should be eliminated.Several factors from culture tradition hidden in Chinese legal culture such as absolutism and populism should be removed.Nutritive elements from deep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be absorbed and encouraged instead of getting caught in incorrect explanation of LIANG Zhi-ping’s theory on legal culture since May Fourth Movement so as to make efforts for returning to the present China.
culture tradi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legal culture; theory of LIANG Zhi-ping on legal culture
2014-11-03
杨之涵(1985-),男,江西赣州人,法学硕士,西藏大学政法学院教师。
DF08
A
1671-685X(2015)01-0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