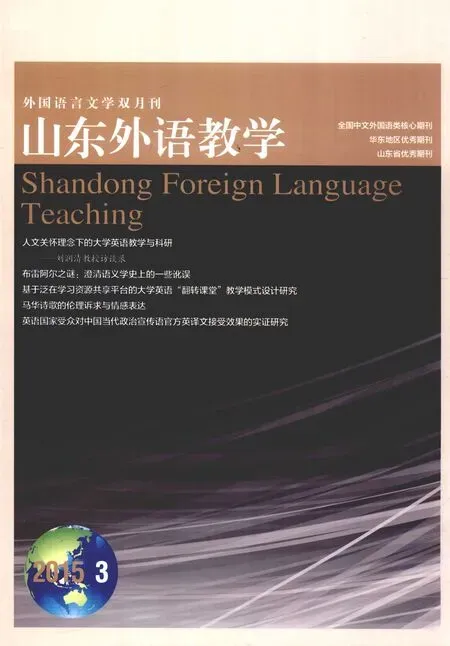西尔维亚·普拉斯家庭诗与心理分析的伦理学批评
曾巍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湖北武汉 430079)
西尔维亚·普拉斯家庭诗与心理分析的伦理学批评
曾巍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湖北武汉 430079)
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家庭诗,毫无保留地袒露了她对父母双亲的爱恨交织的情感,以及对丈夫的诸多抱怨与指责,更多地表现了诗人主体与家庭成员的伦理冲突。这些冲突是在诗人的内心世界展开的:对双亲的复杂情感是一个伦理结——厄勒克特拉情结作用的结果,展现了诗人内心的伦理困境;对丈夫的怨言,反映出自我意识与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伦理身份的批判性反思。
西尔维亚·普拉斯;家庭诗;心理分析;伦理学批评
1.0 引言
西尔维亚·普拉斯是20世纪美国重要的诗歌流派自白派的代表性诗人之一。1963年,31岁的她就选择以煤气自杀的方式终结了尘世生命,留下了近三百首诗歌。她生前仅仅出版过一部诗集《巨像》(The Colosuss),去世前她还整理好了另一部诗集《爱丽尔》(Ariel),后来由前夫特德·休斯交付出版。休斯后来又相继整理出版了两部普拉斯诗集,《渡水》(Crossing the Water)和《冬天的树》(Winter Tree),直到1981年,休斯才整理出版了《普拉斯诗选》(The Se-
lected Poems),比较全面系统地收录了普拉斯的诗歌,其中按编年方式收录普拉斯写于1956年至1963年的诗共224首,含长诗1首,组诗2首,还以附录的形式选入1956年前的诗歌50首。这部《诗选》堪称普拉斯诗歌全编,几乎毫无遗漏地反映了普拉斯诗歌创作的全貌。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普拉斯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近半个世纪以来,其关注者越来越多,研究也不断深入,专论普拉斯及其文学创作的著作已达近百部,论文更是层出不穷,研究视角也趋于多元化。其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到广泛认同的研究路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她的诗歌作为自白诗的优秀篇什,发掘自白诗的显明特征:毫不遮蔽的自我袒露,并将这种袒露和生活与社会现实、心理学分析、女性主义结合起来,试图寻找出普拉斯诗歌的心理学根源与社会学价值。中国的普拉斯研究,目前看来也没有超出这样一种模式。自白诗成为了贴在普拉斯诗歌上的一个“标签”,似乎只有将分析与它联系起来,所有的阐述才显得有理有据。这样的先入之见导致的结果是,研究的诗歌对象几乎完全集中在《爱丽尔》诗集中的作品,因为这些后期诗歌是最“自白”的,而深层的没有挑明的原因则是,较之诗人的前期作品,这些诗也是诸多理论如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易以显示其批评效用的对象,但这无异于将一种“标签”贴在另一个“标签”之上,看似在揭示,实际可能造成更深的遮蔽。
因此,对普拉斯诗歌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普拉斯诗歌的全貌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而一旦我们将考察的视野拓展到整体,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的发现:一是普拉斯的创作有阶段性,她的诗艺是日臻成熟的,“爱丽尔”时期是顶峰期,在此之前也有演化,能够分出层次;二是普拉斯的创作,从早期到高峰期,存在着几个显明的基本主题,贯穿着两条突出的主线:童年的不快记忆与当下的黑色经验。而家庭诗、医院诗、死亡诗则是普拉斯所偏好的诗歌题材。在这几种题材中,医院诗与死亡诗呈现出阶段性的集中,只有家庭诗,贯穿于整个写作历程之中,在各个阶段都有涉及,并且表现出诗人情感态度的变化。风格的变化是选择的结果,既然家庭诗在各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的篇章,我们就可以这一基本题材为考察对象,分析其流变的内在原因,梳理情感变化是如何影响风格变化的,以及这种选择的动机、后果如何,而且是否具有必然性。
以诗的形式记述家庭生活中的事件,表达个人对家庭成员的感情,这一类诗在普拉斯的作品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可以称之为家庭诗。在普拉斯的诗中,家庭所常有的和睦气氛和关爱情意几乎荡然无存,她对其他主要家庭成员(包括与父母、丈夫)的感情显得矛盾而复杂,常常是爱恨交织的,只是若干首写给孩子的诗显得情意绵绵。换句话说,普拉斯的家庭诗,并非人们习以为常的家庭伦理的诗意书写,而将笔触伸向自我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以及自我对家庭成员的情感冲突。亚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认识到不能在普拉斯的诗中去寻找某种一致性,并指出“冲突”是激起其诗歌创作的恒在的力:“普拉斯既不是一种身份,也不是简单的分裂的多重身份。她尽力描写某种张力──愉悦/危险,你的/我的过失,高级/低级文化──但并没有解决或消除这两者之间冲突。”(Rose,1991:10)在家庭中,冲突必然地表现为伦理冲突,因之,普拉斯的家庭诗中的情感冲突其实质就是伦理冲突,反映了诗人主体对与家庭成员的伦理关系的矛盾性态度。而冲突,不可能是持存的状态,必然朝着某一方向转变,最终成为人的行为实践。这一过程是通过人的选择实现的,这种选择体现着人的理性,因而是伦理选择。这就为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普拉斯的家庭诗提供了可能性和方向性。
2.0 心灵世界:伦理选择的内在场域
传统的伦理学,是以人的行为实践为对象的。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就说“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亚里士多德,2003:3),就既指明了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也指明了伦理学研究的中心,那就是对善的研究。在他看来,善同时是行为的目的与行为的属性,人的行为既趋向善,也体现善,由此展现出人在行为实践中的德性。而究竟何
谓“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以此为争论的焦点导致了分野,快乐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情感主义、经验主义各自有不同的解释。各种争论在将问题讨论引向深入的时候也分明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就是从研究人的心理的角度来分析伦理行为。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学要研究的行为是“出于意愿的行为”,是“行动的始因在了解行为的具体环境的当事者自身中的行为”(同上:64),他又说人的行为在选择之前,是需要经过“考虑和决定”(同上:68)的,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行为背后的心理作用,心理是行为的动因。因此,伦理学的每一次革命性发展,既有适应社会阶段性发展,适应新的伦理环境的要求,同时也与人类认识自身心灵世界的不断突破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行为选择,无论其主导力量是理性还是情感,都是人的心灵做出的。在此之前,心灵的判断、考量、权衡,有可能面对复杂的伦理冲突,甚至陷入两难的境地。心灵世界,也成为了人的伦理选择的实际发生的内在场域。由此可以说,自白诗大胆揭露内心世界,正是在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展示诗人主体伦理选择的具体过程。我们也看到,这种选择过程交织着理性的克制、情感的起伏、欲望的抗争,是满是创伤的个人的心灵史和伦理斗争史。
普拉斯的家庭诗中所描绘的对父母双亲的情感纠葛,正反映了这种伦理冲突。她早期以书写父亲为对象的诗,《巨像》最具代表性。由于父亲早逝,诗人只能依靠零碎的童年记忆来拼贴父亲的形象,一尊“巨像”从诗人笔端拔地而起,组成巨像的质料——每一个记忆碎片都饱含着诗人对父亲的尊崇和敬爱,因为她意识到父亲是“自身的来源”。(亚里斯多德,2003: 252)于是,诗人尝试以碎片重塑父亲的形象,她通过“超现实主义艺术与流行影像记录法的交互运用”(Rees-Jones,2001:276),将之改造重构为一个高不可攀的巨像于是顺理成章。在父亲的巨像前面,女儿感到卑微,如“慢慢向上爬像悲悼的蚂蚁”(Plath,1981:129)①,父亲只能仰视,眉宇自然成为“丛生的杂草”,眼睛则是“煞白的墓地”,当她沿着这身躯费劲气力攀爬到巨像的耳际,抬眼就能看见星星与太阳就在近前升落,被置于雄奇自然中的父亲愈发显得伟岸,仿佛成了一尊天神。对子女而言,父亲显然是个体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伦理关系对象,是应该给予“回报”的对象。当她意识到回报的对象在现实中的缺席,爱的情感与行为指向虚无之时,内心深处必然感到巨大的失落与压抑,对象缺失导致伦理行为无法付诸实践,只能倾注伦理情感,转而通过在心中重构对象求得心理的安慰,这样,父亲形象就成了情感和压抑感受与形象融为整体后的自然表征(Kendall,2001:23),是一个被虚构了的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可是,从随后的诗歌中可以发现,普拉斯对父亲的情感却远远不仅是“爱”那么简单,其中交杂、流露出矛盾的情感态度,表现出复杂错综的伦理情感。
《爹地》(Daddy)是普拉斯诗歌的名篇,也是直接以父亲为书写对象。诗的开篇就可谓惊世骇俗:不客气地说自己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已经30年,即使他早已不在人世,并扬言说:“爹地,其实我早该杀了你。”但父亲没有给他这次机会,“在我有机会下手前你就死了”。诗人随之以较大篇幅描绘了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形象: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神灵般的雕像,脚趾都有“弗里斯科海豹那么大”;他有纯正的德国血统,被诗人和纳粹联系到了一起,而女儿在父亲面前犹如犹太人,战战兢兢,噤若寒蝉,心中满是敬畏:“你的德国空军,你的夸夸其谈。/还有你修剪整齐的短髭/你雅利安式的眼睛,明亮的蓝。/装甲队、装甲队,哦,你——”于是父亲又变身为一个恶魔,有“野兽一般残暴的心”,把女儿的“红色心房咬成了两半”,并将她拉到“拉肢台和螺旋刑具”前。在严刑伺候面前,女儿只能表示愿意招供,而她的供词却流露出对父亲的复杂情感,既爱又恨,既感到畏惧又充满崇敬,她甚至愿意随同父亲一起去死,以极端的方式回到父亲身边。在这首诗中,父亲在女儿心目中的形象虽然依然高大,但“巨像”已经轰然倒塌,神性的“善”的光环荡然无存,代之出现的却是“恶魔”、“野兽”、“纳粹”、“吸血鬼”、“恶棍”等等否定性的“恶”字眼。此时,当父亲成为了“恶”的对象,女儿由爱转向恨,随着伦理对象属性
的颠覆性改变,伦理情感也发生颠覆性倒置。但这种倒置是如何发生的呢?亚奎琳·罗斯指出,诗歌对父亲的描绘的确反映出诗人内心的矛盾冲突,她认为这种描绘存在着“危机”,因为父亲给予普拉斯特殊的身份——这种给予甚至是强迫性的——既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犹太人(Rose,1991:227),这让普拉斯对父亲以及父亲赋予“我”的伦理身份产生了焦虑。身份的不确定性和缠杂不定始终萦绕在同一主题的诗中,无论是《水深五英寻》(Full Fathom Five)、《养蜂人的女儿》(The Beekeeper’s Daughter),还是《小赋格曲》(Little Fugue)和《月亮与紫杉树》(The Moon and the Yew Tree),父亲的形象都没有表现出某种统一性,而是矛盾与分裂的。这种分裂反映的,正是诗人内心的伦理冲突,冲突让诗人内心难以抉择,伴之以深刻的“内心检视”(Rose,1991:219),不仅检视父亲的善恶,同时也检视自身的道德罪恶感,将自身的罪感来源与父亲的伦理身份困境联系了起来。
普拉斯对母亲的情感更为复杂。父亲去世后,普拉斯和弟弟与母亲相依为命,她对母亲是依恋的,当她离开母亲身边去异地求学时,与她嫁给休斯后与母亲远隔重洋时,普拉斯始终保持着经常给母亲写信的习惯,在从这些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是普拉斯无话不谈的交流对象,她在家书中与母亲分享着自己成功的喜悦,也向她倾诉情感上的苦闷。可是,诗歌中的母亲却化身为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墨杜莎,面目狰狞,将女儿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爱的空气里。她没有呼叫母亲,可母亲仍持续不断地通过越洋电话来嘘寒问暖,她觉得这种关切已经转变为了监视,是对私人生活的干涉:“你越洋朝我逼近/臃肿而猩红,一只胎盘//让挣扎的情侣无法动弹。”在普拉斯看来,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让自己几乎没有私人空间,一切暴露在母亲的监控之下:“我几乎无法吸气/奄奄一息,不名一文,//被曝光过度,像在X光下。”(《墨杜莎》)最后,女儿终于鼓足勇气发出反抗,表示“对这刺激性的咸味厌恶得要死”,希望不对等的母女关系能够终结。然而,对母亲的怨恨仅仅出现在诗中,普拉斯自己也担心母亲看到《墨杜莎》(Medusa)感情上会受不了。写《墨杜莎》之后两天内,普拉斯又给母亲传书两封,诉说在病中的孤独无依,并渴望得到亲人的关爱,意识到“家庭是不可或缺的”(Plath,1992:468-470),这说明普拉斯对母亲的情感也同样具有两面性,同样反映了她内心深处的伦理困惑。
家庭伦理关系还包括与子女与配偶的关系,普拉斯的家庭诗中,对这两者也有很多的涉及。在写给孩子的诗中,普拉斯难得地展现出温情脉脉,诗歌始终洋溢着深沉的母爱,表现出“强烈的爱”,“具有更多的欢乐与用处”。(亚里士多德:2003:252)而出现在诗歌中的丈夫休斯,其形象却随着两人情感关系的起伏和婚姻的变故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对伦理身份、伦理责任的困惑与反思所导致的伦理情感的变化。关于这一点,后文将着重论及。而综观这些家庭诗中表现出的伦理冲突,正反映出诗人内心面临着两难选择,是爱还是恨,的确成为了一个问题,让诗人陷入持续的不能自已的内心焦虑中。在家庭诗中,普拉斯展现的正是内心的伦理困境,并且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心灵世界成为了伦理斗争的鏖战之地,我们甚至难以分辨出究竟交战双方是那一边最终取得了优势和胜利。但此时要问的是,在两难的伦理选择中,交锋的双方是谁?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交锋?
3.0 厄勒克特拉情结:伦理结的分析
普拉斯的传记作者安妮·史蒂文森在谈到普拉斯的家庭诗时曾经阐述过其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关联。她说:
西尔维亚的精神心理疗法,也当然开拓她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心理表演疗法的范围,显露她已故的、“销声匿迹”的父亲的形象,他是一位研究各种蜜蜂的大师,她既不能宽恕她自己,也不会允许忘却他的去世;精神分析疗法也加强了她十分热爱而最终对母亲很不满的态度,她必须成为与她母亲极像的人,由于内疚或自负的弱点,对于母亲,她为一种精神上的核心所紧紧地束缚着,太根深蒂固而难以自拔。(史蒂文森,2004:52)
史蒂文森论及普拉斯以父母为对象的诗时,已经隐隐指向了这种矛盾情感的致因:普拉斯的内心深处存在的“厄勒克特拉情结”。这一情结正是她的伦理困惑的根源,并展现在她的诗歌中。
普拉斯有关父亲的诗,其身躯几乎都是挺拔、高耸入云的。《巨像》如此,在《爹地》里,父亲还被比作“黑色的鞋子”,而女儿只是其中的一个脚趾。普拉斯还将父亲比拟为紫杉树,“向上高耸,它有哥特式的外形”(《月亮与紫杉树》),“井然有序的紫杉树篱,/哥特式,专横,纯血统德国人”(《小赋格曲》)。《养蜂人的女儿》中,与父亲对应的隐喻则成了花园中直立的雄蕊:“粉囊频频颔首,威严犹如国王”。这些喻体的外观,隐隐指向对阴茎的崇拜。而对阴茎的崇拜和对阉割的恐惧正是弗洛伊德分析“俄狄甫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关键所在:在儿童期,男孩与父亲争夺母亲的爱,但由于害怕遭到阉割失去阴茎只能压抑欲望;而女孩则“因为缺乏一个有目共睹的阴茎,所以深感欠缺”(弗洛伊德,1984:251),同时也认识到第一个爱的对象──母亲不具备阴茎而将爱转移到拥有阴茎的父亲身上。拉康接着分析时使用了一个术语“菲勒斯”来取代阴茎,因为在他看来,“关系到精神分析的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阴茎指的是身体器官,而菲勒斯指的是这个器官所起的想象和象征作用”。(马元龙,2006:76)拉康认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母亲都是其欲望对象,父亲则是一个具有侵凌性的破坏者。他打破了母亲与孩子的二元关系,建立了一个他者、自我与对象的三元关系。而“俄狄甫斯情结”的解决使主体实现了自我的重塑,这其中的关键仍然是“菲勒斯”,对“菲勒斯”的认识,肯定或者否定,不仅决定了儿童对父母亲的爱憎,也决定了他如何实现自我,在语言和家庭的象征界获得自己的位置和个人身份,从而将自己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人来把握。如是来看,普拉斯在上述几首诗中对父亲的喻象所流露出的矛盾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父亲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所以主体自然会感觉到自我是渺小的,她也因此表现得战战兢兢,张口结舌,在《巨像》中只是“蜷伏在你的左耳/丰饶的一角,背着风,//数着这些朱红色和深紫色的星星”,在《爹地》中面对严刑逼供,只能絮絮低语“我招供。我招供”,“爹地,我完了”,可这声音如此微弱,“根本爬不出去”,但由于对父亲所拥有的阴茎或“菲勒斯”的认同,女孩迅速从对母亲的爱欲中挣脱出来,转而将爱投诸曾经是竞争者的强力父亲身上。因为,她对父亲的情感,除了由需要仰视导致的崇敬,以及对拥有阴茎者的爱慕之外,更多的是爱,而这种爱在童年时是受利比多驱动的,在《养蜂人的女儿》中就掺杂了若隐若现的情欲成分。父亲出场后,普拉斯连续使用了两个看似实写的暗喻:“喇叭一样的喉咙朝着鸟喙张开”,“这金雨般的树洒落一地细粉”。这两句的言外之意仍然指向了由利比多驱动的性欲。然而,这潜意识中的性欲显然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因为还有代表母亲的“女王的统治”在虎视眈眈。在诗歌结尾处她发出呼喊:“父亲,新郎,在糖玫瑰的花冠下/这只复活节的彩蛋中//蜂后嫁给了你岁月中的严冬。”她渴望父亲能够起死回生给予她完整的爱,并且,此处父亲的身份突然成了“新郎”,“弗洛伊德的象征主义”使得“乱伦战胜了复仇”(史蒂文森,2004:175),但这一结局显然不过是女儿的幻想,终将被现实无情地击碎。她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由于自己的“乱伦”的“糟糕情感导致了父亲的死”(Ramazani,1994:397),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当中。
《养蜂人的女儿》中母亲的形象是昙花一现的,她表现为一种的“女王的统治”,在和女儿竞争爱的对象的角逐中占有先机,让女儿感到“无与抗衡”,但她心中满是积怨,将母亲的统治权描述为“尝过便一命呜呼的水果:黑果肉,黑果皮”。因此,对这个曾经爱的对象,对这个天生的敌手,普拉斯的情感自然是爱恨交织的。《墨杜莎》中,普拉斯写到了母亲监狱般的呵护,她反而产生了窒息感:“我生活在瓶子里,/犹如在可怖的梵蒂冈。”而在最后,她厌恶地咒骂母亲,将她的关心比作“章鱼的触须”,并说她“缺乏经验而像个阉人”,在这里,普拉斯使用了“阉人”(eunuchs)一词,显然是受到了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儿童发现母亲缺失阴茎而导致爱的转
移的影响,由于意识到母亲也是不完整的,她开始由爱转向憎恨,但是,对于自己情感上的背叛,她还是深感内疚,并陷入了持续的苦恼之中。
对双亲的纠结情感甚至让普拉斯直接搬用了厄勒克特拉的“原型”,让她附身于自己,来到父亲的葬身之地──杜鹃花路。在诗歌《厄勒克特拉身临杜鹃花路》(Electra On Azalea Path)中,父亲的墓地被描写得不堪目睹,表明普拉斯对母亲给予父亲的爱并不认可。而在墓地里,只有雨水溶解了“人造的红色圣人”上的染料,“仿制的花瓣掉落下来,跌得一地胭红”。这一片红让厄勒克特拉附身的女儿想起了曾经的杀戮:希腊神话中厄勒克特拉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杀死了父亲阿伽门农。母亲对父亲的死的描述是轻描淡写的:“是坏疽把你啃得只剩下骨头/母亲说;你像普通人一样死去。”这让女儿显然心中不满。对父亲无望的且不被允许的爱,对母亲的仇视让女儿痛不欲生,她也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对父亲而言,自己究竟是“惹人厌的荡妇”,还是“女儿”或者“友人”?这样的困扰折磨着她,让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是声名狼藉的自杀者的幽灵,/我自己的蓝色剃刀在咽喉里锈蚀。”在全诗的最后一行,对乱伦之爱的自责又萦绕在女儿心头:“恰是我的爱把我们双双引向死亡。”
诗歌以艺术性的虚构实现了对“厄勒克特拉情结”的注解,也展示了固着在其中的伦理纠葛。就实质而言,厄勒克特拉情结就是一种伦理结。伦理结是“文学文本的横向伦理结构”(聂珍钊,2010:20),对普拉斯诗歌中厄勒克特拉情结生成原因和形成过程的分析,其实质也是一个解开伦理结的过程。一般而言,“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所有的伦理结几乎都是在伦理混乱中形成的”(同上:20),几种不同的情感力量在这个结点上相互抵牾,形成冲突,甚至争执不下,通常表现为理性与情感的冲突,或者道德感与欲望的冲突。当心理学发现进入到精神分析领域之后,弗洛伊德对人格进行了深入分析:“自我”是心理结构模式的三个代理之一,它和“伊底”“超我”共同构成了人的心理人格,“自我”在三者中处于主体的中心,肩负着压抑“伊底”的潜在欲望和导向“超我”的良知约束的双重功能,成为了思想与行为的监控者。通过对普拉斯家庭诗的分析可以发现,“厄勒克特拉情结”正是代表欲望的“伊底”与代表道德的“超我”争夺“自我”认同的伦理冲突,它们在普拉斯内心世界的角力,以诗歌的形式,真实地展现了诗人内心的伦理困境。
4.0 自我意识与女性意识:家庭伦理身份的批判性与反思
如果说普拉斯以双亲为对象的诗更多展现的是“超我”对“伊底”的道德约束,或者说“自我”疏泄压抑的方式在诗歌中让“伊底”发言的话,普拉斯以丈夫休斯为对象的诗歌,尤其是后期的诗歌,则是“自我”对“超我”的质疑。这些诗歌中的“超我”是由社会习规对女性的规训造成的,它要求女性对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尽到做妻子和做母亲的义务。但这种义务与男性相比是不对等的,是以牺牲女性的自我为代价的。社会认识始终为“男性中心主义”把持,女性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自由。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要想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承认,就必须适应生理和社会强加给她们的社会角色。种种社会关系中,女性尤其与家庭联系紧密,她被要求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仿佛这样她才被视为真正的女性。因此,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以及女性代表“家庭”参与社会交往对女性而言就十分重要。由于男性主要是作为生产者和公民融入社会的,女性则处于背后去协调社交,这进一步将女性置于从属的地位,让她的“自我”似乎需要通过维护家庭中男性的主导,通过维系家庭和谐来实现。这就让女性的处境显得更为矛盾:“她们在同一时间里既属于男性世界,又属于向其挑战的领域;她们被关在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包围着,所以她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以安生。”(波伏娃,1998: 596)由此来看普拉斯,虽然她在诗歌中竭力展现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自我,但她却始终无力摆脱家庭对她的影响,也无力将对丈夫休斯的情感纠葛斩断,她的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泣诉,以及对男性饱含血泪的声讨。
休斯出现在普拉斯诗歌之中的形象,随着两人情感关系的起伏和婚姻的变故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他们处于热恋之中时,普拉斯认为休斯英俊伟岸,充满男子气概,几乎可以和自己心目中完美的父亲形象相媲美。她对休斯不吝赞美之词,一首诗甚至直接命名为《特德颂》(Ode for Ted)。可婚后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家庭生活中的琐屑,不可避免的摩擦让普拉斯对婚姻有了新的思考,《动物园管理者的妻子》(Zoo Keeper’s Wife)中她已经对休斯有了一些怨言:“过去的积怨你推我搡,如此多松动的牙齿。/然而你究竟如何看待/我做的肥腻猪肉,我强壮的情人,面对着墙壁?/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难以消化的。”普拉斯以捕猎来比喻夫妻关系:“钩子太深无法拔出,而一个念头仿佛指环/滑落下来罩住某种稍纵即逝的东西,/这种压迫感也正在谋害我。”(《捕兔器》)双方互相牵制,在亲密中互相伤害,矛盾一触即发。当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后,休斯则被描绘成了负心汉。在《事件》(Event)中,两人并排躺在有裂缝的“白垩峭壁中”,背靠着背,丈夫的声音听来像是枭叫,“不堪的原音进入我的心”,隔阂与冷漠让生活了无生趣,变得百无聊赖,“我绕着圈子走动,/过去错误的沟痕,又深又苦。//爱不会飘然来临。”
婚姻生活渐渐让普拉斯感到索然无味,并认识到在婚姻中逐渐失去了自我,普拉斯的诗歌中更多地开始描述家庭对女性个性的戕害,以悲剧性的口吻反思女性的命运,并直接将愤怒的火对准了男性世界的威权。在《一生》(A Life)中,她这样描述一个女人苍白的生活状况:“一个女人拖着她的阴影,围着/空无一物的医用托盘绕成一圈。/它像极了月亮,或空白的纸/仿佛在私密的闪击战中创巨痛深。”过往的生活对她而言几乎没有意义,只是“被压扁为照片”,而未来也无可指望,“是只灰色海鸥”,只会让人心生离去之念:“用猫的嗓音絮叨着:离开,离开。”《情书》(Love Letter)一开篇就直指婚姻中爱与激情的消失,剩下的只有无趣的周而复始:“如果现在我一息尚存,那过去就死了,/尽管,如一块石头,与它无干,依从于习惯岿然不动。”《事件》则还原了已无爱意可言的夫妻极其勉强的共同生活,两个人“背对着背”,丈夫的话语异常冷漠:“我听到一声枭叫/从它冷冷的靛蓝传来。”这种生活让普拉斯觉得,虽然通过婚姻和生育,实现了自我的女性命运,但自我却因此而消失了:“我的肢干,同样,已弃我而去。”或者说,她认为自我是不完整的:“我们像残疾人那样触摸。”这正说明,普拉斯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实现自我的愿望,和女性的现实处境,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而这也是导致她精神上的压抑和焦虑的心理原因。
普拉斯还在一首题为《侦探》(The Detective)的诗中以一个侦探的口吻写到了一个女人的被害案件。侦探首先关心的是,当这个女人被谋杀时,她在干什么?答案是“她在整理杯具”,然后侦探说“这点很重要”。何以这点重要,因为它指出了女人是在从事家务劳动,实际已经在凶手锁定在繁重的家庭义务上,认为它戕害了女性。凶手露面的时候,他是用手指“把一个女人往墙里塞”,往一个浓烟升腾的管子里塞,围成四壁的墙,厨房里生火的烟管,所指也是家庭。而诗人笔锋突然一转,侦探说其实根本没有尸体,“只有上光剂的味道,只有长毛绒挂毯”,是日复一日的家务导致了这起没有尸体的谋杀案,它对女性的伤害不是突然的,而是日积月累的折磨。它将一个曾经的妙龄女性从“人间蒸发”了──让她嘴角生皱,乳房下垂,让她们在孩子的养育中疲于奔命──家庭让女人实现了社会赋予她的性别和身份,但她却死了,她失去了自我。虽然女性要求获得独立性,但是“社会结构并未由于女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有多大改变;这个始终属于男人的世界,现在仍然保持着他们所赋予它的形式。”(波伏娃,1998:772)而家庭以及由家庭所强加给女性的义务,就是男性世界所赋予的现实中的形式。《侦探》这首诗,是普拉斯对男性世界的一篇严厉的控词,将男性和他的代言人直接推到了戕害女性的罪犯的被告席上。
自康德的自我意志论之后,关于自我意识的阐论成为了伦理学的重要组成方面。费希特
的知识论伦理思想,关心的也正是人如何在伦理关系中实现自我,尤其是如何实现人的本质——自由。然而,处于社会中的个人,又必然受到社会伦理的制约,这就造成了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宋希仁,2010:341)从普拉斯的家庭诗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冲突。社会对女性家庭伦理身份的规定性要求,以道德律则和习俗成规的形式规范着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行为,甚至内化为了女性主体的“超我”,不断地对女性自我实现的愿望进行压抑。而具有独立思想的普拉斯,对这种被规定的角色不仅充满了抱怨,而且发出了抗议。她独特的声音,正是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觉醒。这是女性自我实现自由的吁请,是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伦理身份的批判性反思。而也正是在一个又一个先行者的反思和抗争中,女权主义得以后续地蓬勃发展,并有力地改善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重建了全新的性别伦理关系。
5.0 结语
综观普拉斯的家庭诗,其指向都是伦理的。只不过,她在诗歌中所展示的家庭伦理关系,并非如普通读者所期待的温情脉脉,也与传统社会道德所赞许所褒扬的有较大的距离。她对父母双亲的复杂情感,她对丈夫的颇多怨言,其中所隐含的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思考,都是有心理根源的。当运用精神分析等心理学的“透视镜”去观察这些诗歌时,就可以发现这些诗歌的写作过程,实质也是一个伦理选择的过程,有些映照出诗人对欲望的疏泄,有的则折射出诗人对家庭伦理身份的批判性反思。因此,自白诗(Confession Poetry)的命名也得以验证,它揭露自身,审视灵魂,展示出对心灵之恶的洞见和省察,也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伦理困惑以及伦理选择之难。
注释:
①文中所引普拉斯诗歌均出自这部Plath,S.The Collected Poems of Sylvia Plath(1981),为笔者自译。此后引用不再加标注,只标明诗题。
[1]Kendall,T.Sylvia Plath:A Critical Study[M].London:Faber and Faber,2001.
[2]Plath,S.The Collected Poems of Sylvia Plath[M].Ted Hughes Ed.New York:Harper&Row,1981.
[3]Plath,S.Letters Home:Correspondence1950—1963[M].Aurelia Schober Plath Ed.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2.
[4]Ramazani,J.Poetry of Mourning:The Modern Elegy from Hardy to Heane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5]Rees-Jones,D.Liberty Belles and Founding Fathers:Sylvia Plath’s“The Colossus”[J].Women:A Cultural Review,2001,12(3):276-291.
[6]Rose,J.The Haunting of Sylvia Plath[M].London:Virago,1991.
[7]安妮·史蒂文森.苦涩的名声──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M].王增澄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8]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9]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1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12]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The Ethical Criticism of Psychoanalysis:A Case Study of Sylvia Plath’s Family Poems
ZENG W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Wuhan 430079,China)
In her family poems,the American confessional poet Sylvia Plath unreservedly exhibited the love-hate feelings for her parents,laid numerous blame on her husband,and showed ethic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poet and her family members.These conflicts are unfolded in the poet’s inner world:the complex emotions to her parents form an ethical knot developed by the Electra complex,which reveals the poet’s inner ethical dilemma;the com plaints about her husband,which reveals the awakening of the selfawareness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function as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of female’s ethical identity in the family life.
Sylvia Plath;family poems;Psychological Analysis;Ethical Criticism
I106
A
1002-2643(2015)03-0078-08
10.16482/j.sdwy37-1026.2015-03-010
2015-02-2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3&ZD128)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研究”(项目编号:13CWW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曾巍(1976-),男,汉族,湖北枝江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英美当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