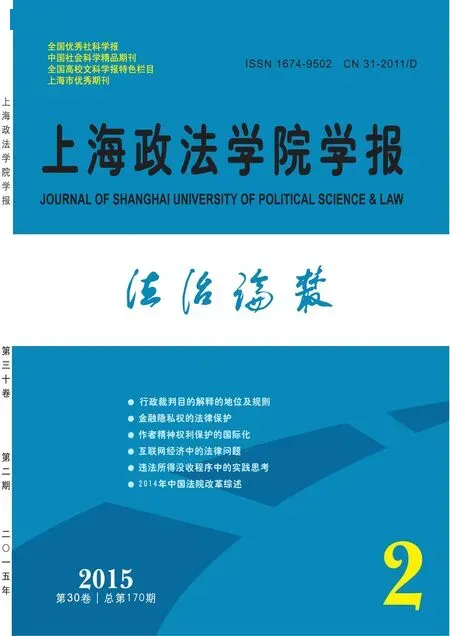财产犯罪既遂标准中的控制说及其司法认定
杜文俊 赵拥军
(1.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031;2.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上海 200030)
财产犯罪既遂标准中的控制说及其司法认定
杜文俊1赵拥军2
(1.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031;2.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上海 200030)
在财产犯罪中,“占有”和“控制”应当可以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而控制即为实际支配,进而,控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范围内的支配,也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支配人的状态。进而,在以控制说作为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对“占有”作整体的判断、以被侵害财物的特征作具体的认定和以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时点作占有判断的补充,对控制说进行规范意义上的理解,而不能通过生活事实上的情况来进行认定。财产犯罪既遂与否的认定,与财产犯罪既遂后,在现场尚能挽回损失的情形下可以正当防卫不是一个问题。财产犯罪的不法侵害尚未结束与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不能作等同理解。
财产犯罪;既遂;控制说;正当防卫
一、问题的缘起
从应然的角度而言,刑法分则每个罪名的既遂标准应当是唯一的,即每种犯罪既遂的认定应当是单一的。但刑法学是一门规范学,对规范概念的理解必然由于不同认知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样态。由此导致的实然现象是采取不同的学说便有不同的既遂标准,从而可能会使得认定某罪的犯罪既遂情形迥异,以及会影响到一罪与数罪、罪与非罪甚至自首的认定等。不仅如此,即便是在同一个学说标准下,如何具体地理解该标准也同样会导致上述情形的出现。以刑法分则中侵犯财产类犯罪(以下简称财产犯罪)中的盗窃罪为例,其犯罪既遂的学说标准主要有接触说、隐匿说、失控说、控制说和失控加控制说等,目前理论和实务中较为一致的便是控制说,以行为人控制了财物为既遂标准。
但如何理解“控制”,则又成为认定既遂的关键。对此,有论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不同的财物,往往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如随身穿着的衣服与家中存放衣物的橱柜,虽然都在主人的控制之下,但方式明显不同,在相关财产犯罪既未遂标准的掌握上也有一定差异。以盗窃为例主要有身体掌控、目击控制以及场所、器具控制等。所谓身体掌控是指将财物随身携带,置于身体的直接控制之下,如随身穿的衣服、佩戴的手表、拎包等财物。在扒窃场合,行为人将财物从主人的衣袋、拎包中取出即意味着财物脱离主人的控制范围而被行为控制和支配,其为既遂。所谓目击控制是指将财物近距离地置于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以便保管、掌控……”。①黄祥青:《刑法适用要点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251页。如行为人扒窃被害人的拎包后转身逃跑,被害人发现后紧追不舍,将行为人抓获。根据前文的目击控制说,行为人在扒窃后逃跑,被害人紧追,此时拎包处于被害人的目击控制范围内,因此行为人并未控制拎包,故应当认定为盗窃未遂。②黄祥青:《盗窃罪的认定思路与要点》,《上海审判实践》2013年第11期。但是根据前文中的身体掌控说,行为人将财物从主人的衣袋、拎包中取出即意味着财物脱离主人的控制范围而被行为控制和支配,就应当是既遂。
可见,在呈一维发展的犯罪形态中,当犯罪已然既遂的情形下,如何还能够再通过其他方式(如目击控制)进而认定为犯罪未遂呢?由于“占有”和“控制”都是对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物后的状态进行了说明,核心含义并无二致,细微的区别仅在于,行为人取得对财物的实际控制比行为人取得对财物的现实占有在程度上稍显得紧密些。即,当行为人实际控制财物时也就意味着行为人对财物的占有达到持续平稳的程度。③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同时,由于占有既是判断此罪与彼罪的要素(如盗窃罪和侵占罪),即占有的有无问题,亦是判断既遂还是未遂的要素(如在别人家中浴室发现了戒指,为了便于日后窃走将其藏在浴室的缝隙中),即占有的归属问题。所以,以下若未作特别说明,将是在占有的归属意义上论及“占有”,即“控制”。因而,笔者将以此为契机,以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为起点,对控制说及其相关内容进行展开,希冀对实践中合理的认定财产犯罪的既未遂,以至罪数等相关问题提供些许裨益。
二、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
对于犯罪既遂的概念,世界各国大多没有通过立法例对其予以规定,我国现行刑法也一样,而是通过刑法理论予以解释。综观中外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既遂的解释,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主张:一是“结果说”,④如我国国内学者持此观点,其认为犯罪既遂指行为人着手实行犯罪并造成了危害结果的情形。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二是“目的说”,三是“构成要件说”。其中“构成要件说”是中外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既遂较为通行的观点,“当犯罪完全实现刑法分则的犯罪构成要件时,是为‘既遂’”,⑤[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评注版),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即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具备了刑法分则规定的该种犯罪构成要件全部要素的情况。⑥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9页;刘宪权:《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由于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罚权因法益受到侵害或有被侵害的危险而发动,故法益具有规范性。现代刑法中侵犯财产犯罪的法益要保护的便是实实在在的财产权利。一般而言,由于财产类犯罪是行为人实施了引起他人财产损失这一法定的构成要件实害结果的行为,⑦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8日《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规定,具备窃取财物或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因此其“在犯罪既遂构成的检验上,除了行为人一定的行为之外,尚须检验侵害结果的实现,以及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⑧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并且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侵害了财产法益后便完成犯罪,且法益被侵害的状态已不随后续侵害行为而论。所以,财产犯罪应当属于犯罪分类中的侵害犯、结果犯和状态犯。
从法益侵害的角度而言,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便意味着其财物受到侵害。同时财产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排除被害人的占有,由行为人自己或第三人占有。只有破坏他人的占有建立新的占有,即由被害人控制转为行为人控制,是为建立了新的占有关系。由此,以控制说作为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应当是妥当的。即“行为人实际取得财物的控制权,排除他人的占有而将财物处于自己的事实支配之下”。①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同时,现代汉语词典将“占有”解释为“掌握”,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13页。而“掌握”意味着“控制”,③同注②,第1718页。因此,在财产犯罪中,“占有”和“控制”应当可以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而“‘控制’即为实际支配”,④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50页。进而,控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范围内的支配,也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的支配人的状态”。⑤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73页。进而,在对个案财物“控制”的具体判断上应结合以下几点:
(一)以“占有”作整体的判断
“刑法上的占有,应该综合考虑客观要件(占有的事实),即对物的支配,以及主观要件(占有意思),即支配意思,然后根据一般的社会观念来进行判断”。⑥[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第2版),付立庆、刘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而这种支配,“以具有直接的、事实上的支配的情形(如实际持有财物、财物处于封闭的支配领域内)为核心,业已扩大到具有支配的事实可能性的情形。对于后者需以支配意思为必要,即排除他人取得,确保自己支配的意思”。⑦[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206页。也可以说,“占有(持有)作为事实上的支配,不尽是单纯的物理的有形的支配,即便具备物理的、有形的支配人的占有(持有)按照社会观念也有被否定的。如在主人的店里,雇员即便现实中持有财物也不具备占有。所以占有是一种规范的社会要素,即便在物理或有形的支配达不到的场合,从社会观念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占有(持有)”。⑧[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87页。比如,财物处在像住宅那样的排他性强的场所内的场合,对于主人一时找不到的财物仍未失去占有。一般而言,使得财物离开此场合即为既遂。但根据财物的性质、大小等特征会存在例外情形,下文详述。
(二)以被侵害财物的特征作具体的认定
在以事实上的占有(持有)和支配理解控制说的前提下,对财产犯罪案件仍需要根据财物的性质、形状、行为样态等进行具体的判断。若财物体积较小,便于携带的,如手表、钱包以及拎包等等,行为人通过盗窃、抢夺、抢劫等手段将其拿在手中、放入口袋以及随身携带等(或者反过来说,行为人使得这些体积较小的财物离开被害人的手中、口袋或不能随身携带等就不能认为是处于被害人的控制之下)即为既遂。如抢夺他人手机,当行为人夺取手机后即为既遂。又如在别人家中卫生间内发现一枚钻戒,当时不方便窃走,为了日后窃走便将其藏在抽水马桶的储水器中。尽管钻戒仍然处在被害人的住宅这样排他性强的场所内,但由于其行为人事实上支配了钻戒,是为既遂。再如,保姆盗窃主人家抽屉里的黄金首饰后藏于主人家里准备隔日带走,藏好后即为既遂;⑨实务中,有法院认定为盗窃未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6)浦刑初字第2202号若财物体积较大的,(一般只能盗窃)则需搬离出商店、工厂、房屋等场所,才是既遂。在有些情形下,“如在工厂行窃,如果工厂是任何人都能自由进出的,则将财物搬出原来的仓库、车间,就是既遂;如果工厂的出入相当严格,出大门要经过检查,则只有将财物搬出大门,才是既遂”,⑩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50页。否则仍是未遂;⑪实务中,行为人将被害人单位的镀锌铜丝从车间窃出,搬运至围墙,将其中的一半搬出围墙,一半仍未搬出围墙,被联防队员发现并扭获。两审法院均认定为盗窃既遂和未遂。详见: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松刑初字第850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沪一中刑终字第889号。“若体积较大的财物以及其他难以搬出的财物,只要行为人使该财物处于可以搬出的状态,即为既遂。如盗窃汽车时,使汽车发动处于可以逃走的状态即为既遂”,①张明楷:《外国刑法学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页。等等。
(三)以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时点作占有判断的补充
当行为人控制时和被害人的失去控制并非一致时,司法实务中的通常情形是以被害人对财物的控制作为判断时点,但即便是最大限度的考虑被害人与财物之间的时间、距离的隔离的场合,也并不能够肯定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反而言之,只有当行为人取得财物之时点时被害人是否丧失占有才是问题的本源,即当行为人取得行为的时点已确定的前提下,直接以行为人取得的时点判断被害人是否丧失占有。②[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第2版),付立庆刘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比如在商场柜台,行为人乘营业员不注意,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将钻戒攥在手中。随后(数秒)担心被发现,又放回去的,就应当认定是盗窃既遂,而不是未遂。其返还行为只能认定为盗窃既遂的时候返还财产行为。不能认为行为人只是短暂的攥着戒指,商场营业员尚未丧失对钻戒的控制而认为是未遂。
“刑法学是最精确的法学,而精确的刑法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确的刑法规定,就是在为社会及其成员规定精确自由程度”。③[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因此,通过规范的设定,犯罪既遂就应当是一个点,一个精确的瞬间的点。在对具体的犯罪既未遂进行认定的时候只能进行形式的而不能是实质的判断。如行为人抢夺被害人拎包中的手机后逃跑,被害人即大声呼救并追赶,行人和民警等人闻讯后相继加入追赶,将行为人人赃俱获。在行为人将手机抢夺在自己的手中逃跑之际,其抢夺行为已然既遂,不能因为手机处于被害人及抓捕者的目击控制范围而未丧失控制,进而认定为抢夺未遂。④但实务中二审法院便是以抢夺未遂改判。详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沪一中刑终字第394号。此外,在盗窃场合,亦应当如此。但目击控制说认为,“之所以被害人自己抓获扒手应当认定为盗窃未遂,惟因财物虽然脱离被害人的身体掌控(方式),但无缝连接上了目击控制方式,被害人可以在目击控制状态下自己追回财物,也可以通过呼喊与第三人无缝地继续形成目击方式的控制连接,由第三人追回财物的情形均应认定盗窃未遂”。⑤黄祥青:《盗窃罪的认定思路与要点》,《上海审判实践》2013年第11期。可是,按照目击控制说认同的身体掌控说,既然拎包属于身体掌控,行为人将财物从主人的衣袋、拎包中取出即意味着财物脱离主人的控制范围而被行为人占有、支配即为既遂,在犯罪形态呈一维发展的过程中,犯罪既遂后如何又能未遂呢?如果按照所谓的身体掌控到目击控制的无缝连接说法,则对于下列情况的既未遂的认定将会是个矛盾的难题:行为人在地铁快要关门时将站在地铁门边一对恋人中女方的手机抢夺后夺门而逃。以下四种情形该如何判断:
1.行为人将手机抢夺出门后,这对恋人只能眼睁睁的在门里面看着行为人将手机拿走,抢夺既遂还是未遂?
2.行为人将手机抢夺出门后,这对恋人大声叫喊,在车门关上后,车门外的乘客由于听到叫喊声,将行为人抓获,此时抢夺既遂还是未遂?
3.行为人将手机抢夺出门后,女方的男友也冲出门去将行为人抓获,此时抢夺既遂还是未遂?
4.行为人将手机抢夺出门后,旁边有位乘客跟着跑出门将行为人抓获,此时抢夺既遂还是未遂(下称地铁抢夺案)?又如,行为人预谋抢劫银行,通过暴力、胁迫手段在银行理财室劫得钱款后,进入银行大厅并携款离开后,在银行工作人员等人的追赶下,为逃避抓捕而丢弃钱款。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携款离开银行大厅时,并未有人追赶而认定为抢劫既遂。是否可以认为,若当时行为人在离开大厅时有人在追赶,是否就意味着其劫得的钱款处于目击控制之下而认定为抢劫未遂呢(下称银行抢劫案)?①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沪一中刑终字第184号。
其实,目击控制属于在支配的意思下按照一般社会观念对财物进行的控制,在一般的社会观念控制下与视线范围无关。其对财物的控制应当按照上文笔者提及的首先根据占有作抽象的判断,然后根据财物的特征、行为样态等作具体的认定。对于不是体积较大的以及其他难以搬出的财物,只要是行为人使其脱离被害人的身体或者使财物离开由被害人(单位)控制的排他性强的场所(如前文的地铁抢夺案和银行抢劫案)就应当是由行为人支配和控制,即为既遂,与财物是否处于被害人及他人的目光视线范围没有关系,和被害人是否发现财物被偷、被抢也没有关系。若按目击控制说法,将财物近距离地置于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以便保管、掌控,如学生、运动员等在运动场上活动时,将衣物等随身财物暂时放置于篮球架旁或运动场一隅。②黄祥青:《刑法适用要点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251页。但问题是,在视线范围之内就是有效控制,若一旦超出视线范围之外就不属于有效控制了?若一群学生在打篮球,将衣物放置于篮球架旁,其视线能所及篮球场,当有人提议衣物不便放置在篮球架旁,而全部挪放到篮球场之外的教室里面的时候,这些衣物便不属于学生们的有效控制?若有个学生视力特别好能够看到自己的衣物,则他目击控制着自己的衣物,否则便没有控制?如此而言,视力的好坏便决定了犯罪既未遂、此罪与彼罪等等。果真如此,刑法学将不再是门规范学。
综上,作为一门规范学的刑法学,其规范评判标准的实质就是通过规范的方式设定的,而不能通过生活事实上的情状来认定。但是,即便如此,由于财产犯罪的样态复杂多变,即便是在控制说的标准下,具体认定犯罪的既未遂仍然争议不断。对此,笔者将进一步的展开。
三、控制说与罪与非罪及罪数关系
(一)控制说与罪与非罪之间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对刑法中规范概念的不同理解致使认定犯罪既遂标准的迥异,如何理解财产犯罪既遂标准中的控制说,实践中会影响到罪与非罪,甚至是自首的认定。如2013年1月1日,行为人王某在火车站售票大厅内,乘被害人张某排队买票之际,窃得张某放置于口袋内的手机一部(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632元)后逃离现场。2013年12月2日,行为人王某又在火车站售票大厅内乘被害人陈某排队买票之际,窃得其口袋内的手机(经鉴定,价值人民币932元)后转身逃跑,被害人发现后紧追不舍,将行为人抓获。后主动交代上述第一节犯罪事实。
应该没有疑问的是,行为人王某的第一节事实构成扒窃既遂。③严格来说,应当是扒窃型盗窃罪既遂,为了行文方便,简称扒窃既遂,下同。问题是:若将其第二节事实认定为扒窃既遂,则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3条等规定,王某如实供述的第一节犯罪事实不得认定为自首。
若将王某的第二节事实认定为扒窃未遂,则根据2013年4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盗窃未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二)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规定,可以得出:若不满足上述(一)、(二)、(三),则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因而“盗窃未遂,情节轻微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④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页。因此,若行为人王某的第二节扒窃未遂的事实不构成犯罪的话,则结合前述相关规定,王某如实供述的第一节事实将构成自首。而一旦认定为扒窃未遂,不但不作为犯罪处理,而且可以据此认定为自首,进而又可以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对于上述行为人的第二节事实,由于笔者的观点是扒窃既遂,理由不再赘述,故不得认定为自首。
(二)控制说与罪数之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控制说,不仅影响罪与非罪,以及自首制度,还影响着一罪与数罪的认定。行为人陈某经济拮据,预谋以其结识的驾校女同学张某为抢劫对象。某日,陈某约张某至预定的酒店客房,采用麻醉、捆绑等手段,从张某身上搜得两张银行卡,并逼问得知密码。之后,陈某将张某勒死、抛尸野外;然后分数次提取银行卡内钱款8万余元。对此,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陈某劫取银行卡以及密码以后,因系熟人作案,为杀人灭口而勒死张某,其行为应当分别认定为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陈某劫取银行卡以及密码,与其后连续提取卡中钱款的行为,都是抢劫罪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陈某在实施抢劫犯罪过程中故意杀人,应当认定为抢劫一罪。
本案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抢劫银行卡以及得知密码后,是否控制占有了银行卡内的钱款?笔者认为陈某从张某身上搜得银行卡并逼问得知密码后属于已经控制占有了张某银行卡内的钱款,陈某抢劫既遂。同时根据2001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本案中,陈某在劫取银行卡和密码后,其属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已经侵害了抢劫罪所保护的法益,并由此完成了犯罪,其后连续提取卡中钱款的行为已不属于新的犯罪事实,不应当认定为抢劫罪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且本案无证据表明陈某是为了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陈某实施的抢劫行为已经既遂,也不属于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因此应当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四、财产犯罪的既遂与正当防卫
根据《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的规定,要求的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一般而言,就应当是犯罪既遂之前。而犯罪既遂表明犯罪已经完成,不法侵害结束,除非有新的不法侵害发生,则不允许正当防卫,否则便是事后防卫。尽管刑法中规定的正当防卫要求的时机条件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但在财产犯罪情况下,行为虽已经既遂,但在现场还来得及挽回损失的,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即被当场发现并同时受到追捕的财产犯罪的侵害行为,一直延续到不法侵害人将其所取得的财物藏匿至安全场所为止;在此之前,追捕者可使用强力将财物取回。如抢劫犯使用暴力强取财物后,抢劫罪虽已既遂,但在当场对抢劫犯予以暴力反击夺回财物的,应认为是正当防卫。①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196页;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请详见: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但问题是,财产犯罪既遂后,在现场还来得及挽回损失的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可以实施正当防卫,认为其中的“不法侵害尚未结束”与上述的《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的“在劫取财物过程中”能否作等同理解?
如李某夜间持匕首伺机拦路抢劫。当路人王某途经该处,李某即上前猛击王某头部,致王倒地,并劫取王某随身携带的挎包逃跑。因包中除钱款外还有重要文件,王某爬起后追上李某欲夺回挎包。李某遂持刀猛刺王某胸腹部数刀,致王某不治身亡。对此,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在劫取他人财物以后,为抗拒抓捕,又持刀捅刺他人致死,应当分别认定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在抢劫犯罪过程中为抗拒抓捕而杀死他人,符合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在抢劫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情形,应当认定抢劫罪一罪。
可以肯定的是,“抢劫犯使用暴力劫取财物,即使抢劫行为已经既遂,但被害人为夺回被抢财物,而当场对抢劫犯使用暴力的,应当根据《刑法》第20条第1款成立正当防卫”。①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该案中当李某猛击王某头部,致王某倒地后劫取其随身携带的挎包逃跑属于已经取得控制了王某的挎包,应当认定为抢劫既遂。后被害人王某爬起追上李某欲夺回挎包,此时可以视为李某造成的不法侵害尚未结束,王某若使用暴力抢回挎包理当属于正当防卫。但该案中的王某不仅未能使用暴力抢回其挎包,反而被行为人李某持刀猛刺胸腹部数刀致死,应当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
尽管该案存在正当防卫的条件,抢劫行为既遂后,不法侵害尚未结束。但此种情形下的“不法侵害尚未结束”不能等同的理解为“在劫取财物过程中”。因为,犯罪既遂意味着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原则上便不存在正当防卫的条件。财产犯罪既遂后,在现场尚能挽回损失的可以正当防卫,其“实质上是一种自救行为,但我国刑法中又没有明文规定自救行为,所以一般将其理解为正当防卫”。②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脚注。否则,当行为人抢劫被害人财物既遂后,被害人又暴力夺回财物而将行为人打成轻伤的,由于没有正当的合法化事由而对其定罪,便明显的违背了公平正义。易词言之,突破正当防卫要求“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规定,允许财产犯罪既遂后的正当防卫,可以说是一种对公平正义的补救,并非规范的规定。而上述《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在劫取财物过程中”的表述,是对抢劫罪构成要件行为中的要素的规范的规定,就只能规范的理解为抢劫行为既遂之前。因此,该案中李某持刀猛刺王某胸腹部数刀致死不属于在劫取财物过程中的行为,不能认为在抢劫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情形而认定抢劫罪一罪。
可见,财产犯罪既遂与否,与财产犯罪既遂后,在现场尚能挽回损失的情形下可以正当防卫不是一个问题。进而,不能将财产犯罪既遂以后的行为(包含正当防卫行为)与既遂标准的判断混淆。于此,或许可以在司法实务中对样态复杂多变的财产犯罪,合理的认定其既未遂。
(责任编辑:丁亚秋)
DF625
A
1674-9502(2015)02-028-07
1.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2.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2014-11-21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产犯罪基础理论、审判实践的本土化考察(项目批准号14BFX15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