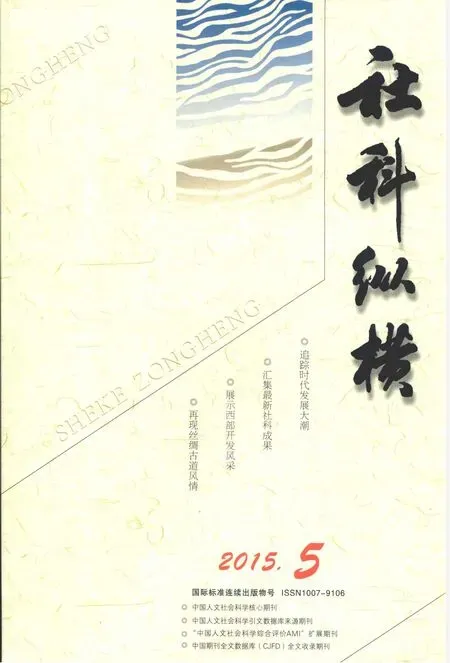杰克·伦敦《中国佬》的解构与重构
李 滨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1)
一、杰克·伦敦涉华作品研究现状概述
杰克·伦敦的作品从1919年开始就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其作品的译介达到了高潮,几乎所有杰克·伦敦的长、短篇小说都能找到汉译本,成为我国译介最多的美国作家之一,仅《野性的呼唤》在中国就有近40个译本。与其大量的翻译文本相比,国内对杰克·伦敦研究方面的成就却很少,形成巨大反差。以国内权威的外国文学核心刊物《外国文学评论》与《外国文学研究》为例,目前能检索到的相关论文不到10篇。纵观建国以来国内学界对杰克·伦敦的研究,其分析常集中在主要的几部作品,对其作品中有关华人的分析、论述相对较少。90年代末以来,杰克·伦敦有关华人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国内学者对其涉华作品的普遍看法是其对华人的描写带有浓重的种族歧视色彩。其中对《中国佬》的评价也都基本持否定态度:在《跨越太平洋的雨虹》中,冒键认为杰克·伦敦刻画了一个“丑陋的《中国佬》”,故事中的中国劳工逆来顺受、沉默、麻木,令人悲哀[1](P64-66);朱刚也认为在《中国佬》这篇小说中“中国人逆来顺受,麻木至极,完全印证了东方主义笔下的中国人”[2](P159);韩红梅认为《中国佬》中的“中国劳工被描写为一种受歧视、胆小怕事、麻木不仁、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奴隶形象”[3](P50);王丽耘认为《中国佬》刻画了“愚顽、麻木、可怜的种植园中国苦力形象”[4](P92),但她强调的是杰克·伦敦的中国观有一个“从刻板书写到理性描画”之“渐变性”[4](P90),《中国佬》中阿卓的形象也“都不再是一味丑化了”[4](P94);李怀波认为“在杰克·伦敦有关中国与华人的小说中,确实集中体现了一个东方主义的中国形象和东方主义的华人形象,在对这些东方主义形象的表征建构中体现了西方列强的帝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但他同时指出“若就此把杰克·伦敦与种族主义者等同起来却有失公允,需要对他的种族观作进一步深入的解读”[5](P15)。值得中国学者关注的是《中国佬》这篇短篇小说在美国批评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它一直被认为是杰克·伦敦最好的作品之一。亨迪克斯指出杰克·伦敦是一位“讽刺大师”[6](P27),他通过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对白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野蛮霸道及司法公正进行了讽刺与抨击,《中国佬》无论从制造气氛、叙述故事还是从讽刺的发展效果来看都是“伦敦文学生涯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各个时代中的小说杰作之一”[6](P30)。为什么对于同一篇小说,中外学者却给出完全不同的评价?是西方学者赞美过度,还是中国接受者反应过激?本文试图综合比较文学形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批评理论对杰克·伦敦的《中国佬》进行重新解构和重构,以期能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杰克·伦敦,并藉此希望能为研究者对杰克·伦敦进行更为客观、全面、创新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域。
二、是种族歧视,还是讽刺鞭挞
其实,《中国佬》中杰克·伦敦对白人统治者的讽刺在小说开头第一段就有所显现,杰克·伦敦借华工阿卓(Ah Cho)的内心独白讥讽白人法官的愚蠢与无能:他们在法庭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想要找出真凶,结果却根本没找对!对于一个被捅两刀致死的人,在阿卓看来,充其量也只能判两个人有罪,但最后白人法官竟硬是判了四个人都有罪!阿卓本以为案情如此简单明了,他和同伴们不可能被判有罪,结果却都被荒唐地错判了!难怪杰克·伦敦要借阿卓之口讥讽白人法官“愚蠢至极”[7]①。又如当描写阿卓在等待漫长的审判结果时,杰克·伦敦再次借阿卓的内心独白对白人统治者进行直截了当地揭露与鞭挞:“白人都一样,他们会毫无来由地发火,他们发火的时候会像野兽一样危险”[7];他们喜怒无常,野蛮凶残,与华人的克己忍让,形成鲜明的对比,“华工永远弄不明白一个小小的举动什么时候会讨好他们,什么时候又会招来一顿猛烈的皮鞭。相同的行为,这次能使他们很高兴,而下一次却可能使他们变得暴怒”;“他们是恶魔:看看那个监工就知道了”[7]。“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形容词通常被19世纪的西方用来总结对中国人的看法,而在《中国佬》中这些形容词所表达的意思被杰克·伦敦极具讽刺意味地用在了白人统治者的身上,这不能不说是杰克·伦敦的匠心独具,展示了杰克·伦敦赋予小说的强烈的他者隐喻——借助他者而言说自我,揭露西方自身的残忍与黑暗。小说中对白人的嘲讽还表现在对押解阿卓去刑场的宪兵的描写上:文中的宪兵被杰克·伦敦形容成出身于法国南部的农民,“20年的当兵经历也没有使他愚钝的心变聪明,他还是像以前当农民时那样反应迟钝与愚蠢,对上司只会一味地畏惧与奴性地遵从”[7]。短短几句话就把作者对白人宪兵唯唯诺诺、惟命是从的奴性形象的讽刺与调侃显露无遗。小说中最能体现杰克·伦敦讽刺鞭挞白人统治者的就是描述这些自诩为代表先进文明和道德规范的白人竟然在明知自己弄错了行刑对象的情况下,都因各自的私心而毫无愧疚地把冤枉的阿卓斩首了。在他们看来,处死的只不过是一个“中国狗”,至于是哪一个“中国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们并不在乎[7]。白人的这种肆意草菅人命的荒唐行径与其标榜的所谓“文明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一次表明了杰克·伦敦借助他者言说自我的本意:作者只是借用华人劳工这一他者形象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西方人在文明的表象下隐藏了灵魂中残忍、嗜血和卑鄙的本能”[8](P259)。小说中杰克·伦敦对白人愚蠢、荒唐、草菅人命的这些直白描述与刻画无不显现了作者对白人殖民者的讽刺与鞭挞及对华人劳工悲惨遭遇的同情。在杰克·伦敦的笔下,《中国佬》中的华工阿卓年轻、快活而温良。他的脸圆圆胖胖,如同满月,映射出对生活的知足和心地的善良。在酷热的棉花地里劳作一天之后的休息与宁静对他来说便是无尽的满足。他可以对着一朵花呆坐几个小时思考生命的神奇;弦月下沙滩上的一只苍鹭;溅起银色浪花的飞鱼;亦或是夕阳下礁湖旁的一只蚌和一朵玫瑰都能使他忘却一天的劳累和监工的皮鞭[7]。所有这些描述都显示了阿卓是一个生活要求简单、易于知足、善良纯朴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从不与人口角”的人最后竟被错判,甚至被错杀!这样的故事结局显然表达了杰克·伦敦对当时白人统治者野蛮、荒谬行径的极大讽刺与强烈抨击。
《中国佬》从开篇到结尾,对白人统治者野蛮、愚蠢、残暴、荒谬行径的直白描述随处可见,俯拾皆是;而对华人劳工的描述,笔调温婉、平和,字里行间透露着欣赏与同情,毫无种族歧视之嫌。综上所述,显然杰克·伦敦在《中国佬》这篇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是对白人统治者野蛮、荒谬行径的讽刺与鞭挞以及对华人劳工温良品质的欣赏及其悲惨遭遇的同情,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种族歧视。中国接受者之所以把《中国佬》解读成种族歧视是因为他们在理解作品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体现自己个人视域的“前见”[9](P199),是其在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在特定历史时期民族主义情结的作用下,对《中国佬》中某些片段的描述进行过度阐释、解构的结果。而中、西学者对同一部作品给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则是因为双方在“期待视域、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9](P211)等方面的不同而出现的多元化的接受。由此可见,作为审美主体的接受者的带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接受行为与作品的文学地位和艺术生命力直接相关。处于文学活动核心地位的接受者如果能够超越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以更加客观、平和的心态去解读《中国佬》,也许能够更加接近那个真实的杰克·伦敦。
三、是丑化,还是写实?
乍看之下,杰克·伦敦《中国佬》中的华人劳工似乎被丑化成沉默、怯懦、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的奴隶形象:在一场因口角而引发的斗殴致死事件中,杀人者趁乱逃跑了,监工凶狠的皮鞭把阿卓和阿周等余下的目击者赶到了角落。由于无人指正,愚蠢的法官就蛮横地认定几个在旁目击的中国劳工是凶手和帮凶,并根据他们身上留下的鞭痕的轻重判处阿周死刑,阿卓20年监禁,另外两名劳工各判监禁12年、10年。蒙冤的华工对这始料不及的判决却表现得出奇的平静,他们既不震惊,也不悲伤,更没有申诉,每个人脸上都面无表情,就连即将被砍头的阿周也像木乃伊一样沉默不语。华人劳工沉默、怯懦、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的形象似乎跃然纸上。但是细读之后不难发现杰克·伦敦在《中国佬》中对华工的沉默做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因为劳工们心里很清楚,根据过往的经验,他们再怎么愤怒、抗议都是没用的,白人统治者是不会理会的。事实上,小说中的阿卓曾多次向押解员、监斩官、监工提出申诉,却都不被理会。判决结果的出人意料对劳工们来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早已对鬼佬的这种行为方式习以为常了。白人对待中国佬从来都是超出常理、出乎意料的。这荒唐的判决只不过是白人干过的数不清的荒唐事的其中之一,因此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7]。既然明知厄运无法改变,与其大吵大闹、哭哭啼啼而无济于事,倒不如坦然面对,照常生活。于是阿周等“照吃、照喝、照睡,一点儿也不忧虑”[7]。由此可见,杰克·伦敦笔下的华人劳工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麻木不仁,而是他们清楚白人统治者野蛮霸道、蛮横无理的本质,深知抗议无用后而采取的坦然面对的态度。细想之下,这何尝不是鸦片战争后海外华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呢?19世纪中后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落败,再加上“淘金热”的吸引,大量华工去了美国。由于中国劳工具有异乎寻常的吃苦耐劳精神且任劳任怨、要求极低,对严酷的工作生活环境很少提出异议,因而对美国当地工人、农民的就业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引发了大规模的排华、反华浪潮,并迅速波及全国,华人被置于被敌视、歧视和排斥的悲惨境地之下。再加上受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华人在面对残酷剥削、压迫与统治者的暴行时多采取沉默、忍耐、逆来顺受的态度。中国读者可以接受并认同梁启超、闻一多、鲁迅等笔下对国人这些国民性的描述与批判,认为其真实地刻画了当时国人的精神面貌,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描述是为了达到唤醒国人的初衷,而当相同的描述出现在杰克·伦敦笔下19世纪末鸦片战争后的海外华工身上时,中国接受者却认为这是对华人的歧视与丑化。这表明中国接受者对杰克·伦敦有关华人的作品存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误读。受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批评和东方主义理论对种族、身份的关注的影响,当代中国接受者忽略了杰克·伦敦在《中国佬》中对白人统治者的讽刺与抨击,而仅仅关注并耿耿于怀杰克·伦敦在其作品中对华人的所谓“丑化与歧视”,忽视了这其实也是鸦片战争后海外华工真实生存状态的写照。其实,如果中国接受者能够“超越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可以看到中西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与国民性的观察与表述基本一致”[10](P19)。综上所述,杰克·伦敦在《中国佬》中书写的是海外华工真实的生存状态,而非所谓的丑化。正如虞建华教授所言,杰克·伦敦“在追求真实客观地反映生活的同时,融入了哲学和科学的理论,…每一篇写实或离奇的故事背后,都寄托着他对自己的生活、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感悟和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11](P340-341)
四、结语
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特别是赛义徳的东方主义成为国内学者分析、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主要理论依据。在这些理论观照下,西方是文明、先进的化身,代表着强大、优越、理智、人道;东方作为与西方对立的“他者”存在,是野蛮、落后的象征,代表着软弱、卑劣、不理智、非人道。在东、西方处于对立、对抗的思维定势下,同时在民族主义情结的作用下,国内杰克·伦敦研究在评论其早期涉华作品中对中国与华人的描述存在明显歧视与丑化时,对其后期涉华作品的评论也不自觉地出现了惯性的误读:即套用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观点对其后期涉华作品进行了过度地阐释与解构。在《中国佬》中表现为忽略了杰克·伦敦对白人统治者的讽刺与抨击,而过度解构文中对华人劳工的“丑化与歧视”。纵观杰克·伦敦研究在中国的90余年,中国接受者对其作品的解构与建构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及期待视野的影响下,通过自身的文化过滤而形成的一种阐释与解读,是一种选择性地接受、创造性地重塑;再加上杰克·伦敦自身经历与思想意识的复杂性,因而也就形成了杰克·伦敦研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杰克·伦敦《中国佬》的解构与重构希望能够纠正对杰克·伦敦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及对其作品理解上的一些片面性,挖掘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掩盖的杰克·伦敦形象的其他方面,以期能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杰克·伦敦,并为研究者对杰克·伦敦及其作品进行更为客观、全面、创新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域。
注释:
①文中对《中国佬》内容的引用均来自杰克·伦敦的英文原版The Chinago,出处:http://www.jacklondons.net/writings/GodLaughs/chinago.html中文为笔者自译。
[1]张弘等.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2]朱刚.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韩红梅.试论《中国佬》中的中国劳工形象[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2.11:50-53.
[4]王丽耘,朱珺.从刻板书写到理性描画[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2(5):90-95.
[5]李怀波.选择·接受·误读:杰克·伦敦在中国的形象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King Hendricks,“Jack London:Master Craftsman of the Short Story”[A].Ray Wilson Ownbey,Jack London:Essays in Criticism[C]Santa Barbara,Ca:Peregrine Smith,Inc.1978.
[7]The Chinago[DB/OL].http://www.jacklondons.net/writings/GodLaughs/chinago.html,2013-7-2.
[8]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黄源深,周立人.外国文学欣赏与批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0]姜智芹.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虞建华.杰克·伦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