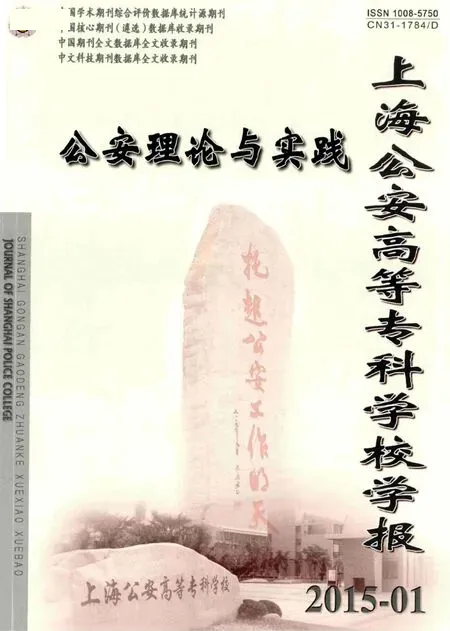证人资格评价体系的去道德化与本质回归
蔡震宇(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检察院, 上海 202150)
证人资格评价体系的去道德化与本质回归
蔡震宇
(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检察院, 上海 202150)
我国的刑事证人资格制度因存在道德化与形式化的缺陷,导致证人资格规则在实践中的空转与理论上的混乱。证人资格应以证人能力为前提。证人能力包括事实能力与法律能力,具备一定的事实能力才能获得证人资格,证人的事实能力影响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证人的法律能力则与证据能力相对应,证人资格与证人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应使具备基本的感知、记忆与表达能力的人都具有证人资格,既保证对证人的合理取舍,也防止对证人不适当的排除。
证人资格;证人能力;感知;记忆;表达
DOI:10.13643/j.cnki.issn1008-5750.2015.01.010
一、引言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确立了证人出庭及作证豁免制度,第62条、第63条分别确立了证人保护和作证补偿制度,使证人出庭作证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资格的规定存在严重的形式化与道德化倾向,不适当地将生理上、精神上、年龄上的形式化缺陷与证人的作证能力等同,不适当地将能否辨别是非的道德化认知能力与证人的作证能力相等同,导致证人资格的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又因证人出庭率低而被架空。学界对证人资格的探讨拘泥于字面意义的争论,也没有对证人资格与证人能力、证人适格性等概念作出明确的区分,导致讨论的片面化与分散化。刑事证人资格问题在实践中被架空,理论上的讨论又不深入,导致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立法的重视。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得到进一步确立,司法实践中法庭对出庭证人的资格审查也将相应地提上日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理论上廓清证人资格与相关概念的基本界限,在实践中推进证人资格评价标准的去道德化与本质回归,将成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迈向行动的第一步。
二、证人资格与证人能力的概念澄清
证人资格,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资格,英美法上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the competencyof witness”,即“competence refers to a person’s ability to testify”①参见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7.。“competence”,一般译为“能力”,那么“the competency of witness”直译过来应该是“证人能力”,所以国内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将证人作证的资格称为“证人能力”②参见罗筱琦,陈界融.证据方法及证据能力研究(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陈界融.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04)译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高忠智.美国证据法新解-相关性证据及其排除规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将证人能力转译为“证人资格”③参见刘晓丹.美国证据规则[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王伯庭,陈伯诚,汤茂林.刑事证据规则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还有学者译为“证人的适格性”④参见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那么,证人能力与证人资格究竟存在何种联系?
“能力,指能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1]根据具体语境的不同,能力可以划分为事实能力与法律能力。事实能力,指的是事实上实施一定行为的能力。当这种事实行为的后果被赋予某种法律效果时,这种行为被称为法律行为,其事实上的能力自然也被确认为法律能力。资格则是联结事实能力与法律能力的桥梁。“资格,指从事某项活动所应具备的身份。”[2]“当规范将某个人的行为当作法律条件或法律后果时,意思是只有这个人才有‘能力’作或者不作这一行为;只有他才有‘资格’(competence,最广义的资格⑤沈宗灵先生在此也将“competence”译作“资格”。)。只有当这个有能力与有资格的人作或不作时,才发生根据规范来说成为法律条件或法律后果的行为或不行为。”[3]可见,资格是对个体在法律上主体性地位的一种确认。个体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确认之后,其实施的事实行为便可以转化为法律行为,从而实现了从事实能力向法律能力的转化,进而与一系列的权利义务联系在一起。当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被法律承认为一个法律上的主体时,其将享受到一个法律主体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并承担相应的各种义务。“说法官有资格作出判决,这意思就是,法律秩序所决定作为司法职能的就是一定人的一定行为,因而这个人就有能力作出判决。”[4]所以,法律资格本身是以事实能力为基础的,不具备一定的事实行为能力,将无法获得一定的法律资格。同时,法律资格又是法律能力存在的前提,取得一定的法律资格以后将保证个体具备一定的法律能力实施一定的法律行为。
对于证人能力与证人资格也可以上述思路从两方面进行认识,一是证人作证的事实能力(以下简称事实能力),二是证人作证的法律能力(以下简称法律能力)。证人的事实能力,指证人事实上是否有能力对发生的案件事实进行感知与记忆,并在法庭上将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表达出来的能力。证人的事实能力决定了证人是否可以取得证人资格,并且证人所具备的这种事实能力将影响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在取得证人资格成为证人以后,证人便具备了作证的法律能力,也即其出庭作证的行为“有能力”被法律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换句话说,该证人的证言将具有证据能力。
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可以将证人的事实能力、证人资格与证人的法律能力置于这样的一个逐级递进的逻辑链条中:第一,证人的事实能力是与证人资格相联系的,具备一定的事实能力才能获得证人资格,并且证人的事实能力将影响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第二,证人资格是与证人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比如证人享有费用补偿权、隐私保护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特定的作证豁免权等权利,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宣誓或具结的义务、客观陈述其所观察之事实的义务等。第三,证人的法律能力是与证据的证据能力相对应的。“只有有证人能力的人作证,其陈述才有证据能力,也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反之,没有证人能力的人,其陈述则无证据能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5]
三、证人能力的演进机理及其制度确认
“早期有关证人资格的各种排除规则都是以证人所具有的某种身份为依据,将证人的某种身份与证人的可靠性及其证言的可靠性不适当地进行挂钩。”①有关早期证人资格的内容介绍参见[美]约翰・W・斯特龙等:《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41页;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0页。这种未经审查便对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作出评判,并以此为理由剥夺证人资格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现代程序理性,武断地将相当一部分合格的证人排除在证人的范围之外,人为地对案件事实的发现设置了不必要而且不经济合理的障碍。现代证据法已经普遍放弃了这种做法,转而从程序理性的角度对证人能力进行认识与把握,对于证人能力的审查从形式上的身份标准转变为实质上的能力标准,即要求证人应当具备基本的证人能力。
证人能力,也称证人的一般能力或者证人的普通能力,指自然人从事各种活动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的、普遍的能力,如基本的观察、记忆、思维、理解都属于一般能力。根据心理过程阶段的不同,可以将证人的一般能力划分为感知能力(capacity to perceive)、记忆能力(capacity to remember)与表达能力(capacity to narrate)②陈朴生将这种分类下的证人能力统称为特定供述能力,指证人就特定事项为实现供述之能力。参见陈朴生:《刑事证据法》,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05页。。“心理学研究表明,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客观刺激物作用于人的感受器,引起感受器神经的冲动,由传入神经将神经冲动传导到脑中枢,在脑中枢发生神经活动过程,再通过传出神经把神经冲动传到效应器官,对客观刺激物作出效应话动。这一过程也就是外界信息向大脑的输入,是大脑对信息进行储存、加工与提取,并向外界输出信息的过程。……证人证言也是大脑对客观事物——案件情况的反映。因此,上述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模式同样适用于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这就是说,证人感知到客观存在的案件情况(输入信息)后,便将案件情况的印迹存留在头脑之中(储存储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陈述有关案件情况(提取与输出信息)。简言之,证人证言形成的心理过程可以分为感知案情——记忆案情——陈述案情这三个阶段。”[6]因此,证人对案件事实进行作证的能力也就是证人的感知能力③陈朴生先生认为感知能力即为感知机会,即有知觉问题行为或发生事件之机会。参见陈朴生:《刑事证据法》,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05页。实际上,感知能力是证人天然具备的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能力,属于主观因素。感知机会是外界环境对证人所产生的影响,属于客观因素。相对于感知环境而言,感知机会又是一种特殊的客观因素,其作用在于将外界的刺激输入证人的感觉系统,由此引发证人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过程。可见,在感知能力和感知机会共同作用下,证人才对发生的案件事实进行了感知。感知能力和感知机会共同构成了证人资格的基础,两者分属不同的范畴,不能混为一谈,故陈朴生的这一说法有待商榷。、记忆能力与陈述能力的综合。证人所应当具备的这三种能力又被称为“证人必须具备的作证属性”[7]。证人能力的考量因素主要包括证人的生理器官以及心理过程两个方面。良好的感知、记忆与陈述器官是证人能力的生理基础,通常感知能力会受到先天遗传、后天培养、年龄、疾病的影响。证人能力的生理基础可以通过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科学手段予以判断。除此之外,证人证言在形成的心理过程中还将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将对证人证言的内容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证人本身对这些影响的接受能力与处理能力也应当属于证人能力的范畴。
证人证言的形成在证人心理中经过了感知、记忆与表达的过程,于是在对证人能力进行评价时也应当以证人的感知、记忆、表达能力为基本标准。在证人具备保证基本的感知、记忆与表达能力时,其便已经具备了将其感知的案件事实传达给审理者的能力,法律便应当赋予其证人资格。当然,上述三种能力不仅是证人能力的评价标准,也是证人可靠性的评价标准①证人可靠性与证人资格在评价标准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在早期的证据法上证人资格是与证人如实作证的意愿联系在一起的,不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曾受有罪判决的人、案件当事人以及案件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由于被法律认为不具有如实作证的意愿而不具有证人资格,不过这一做法已经基本为现代证据法所摒弃,如实作证的意愿不会对证人资格产生影响,而只是证人可靠性的考量因素。另一方面,证人如实作证的能力在作为证人可靠性的考量因素的同时,也可以是证人资格的考量因素,证人如实作证的能力通常会在不同的场合对其证人资格或者可靠性产生影响。在对证人资格进行审查的程序中,主要的审查对象便是证人如实作证的能力,这个时候如实作证能力影响的是证人资格,不具备一定如实作证能力的人不得成为证人。在交叉询问的过程中,主要的审查对象之一便是证人如实作证的能力,于是交叉询问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一方律师对证人如实作证的能力进行攻击,进而削弱其作为证人的可靠性,故在交叉询问的过程中如实作证能力影响的通常是证人可靠性。但若证人在交叉询问中的表现表明其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如实作证的能力,那么一方律师将对其证人资格提出异议。若这一异议得到法官的首肯,该名证人将不具有证人资格。当证人如实作证的能力较强时,证人的可靠性较高;当证人如实作证的能力较低时,证人的可靠性较低;当证人如实作证的能力被证明低于一定的限度时,证人便根本不具有可靠性,当然也就不具有证人资格了,即使其已经出庭作证,其所作的证言也是不具有可采性的。。正如华尔兹教授所言,“若上述三项属性或能力中的任何一项有所降低或减小,调查人员只能将其作为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有所改变,而不应使证言完全失效(不被承认)。然而,一个证人也可能在作证能力上有严重缺陷而完全没有能力作证。例如:一起案件的目击证人仅仅能靠抬起膝盖以表达‘是’,这个人没有作证能力,因为对他的交叉询问将会受到严重障碍。”[8]
在通常情况下,上述三项能力为一般自然人所具备,各国法律也普遍存在对证人具备证人能力的推定,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广泛的证人资格的确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1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作为证人的资格,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英国《1999青少年审判和刑事证据法》第53条(1)规定,在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所有的人(不管其年龄)都有资格给出证据。[9]印度《1872年证据法》第118条规定,一切人均应有作证资格作证;除非法庭认为,这些人由于少不更事、垂暮之年、身体或心理疾病以及诸如此类因素,致使不能理解所提问题或者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理性回答的。[10]证人能力的推定并非意味着所有自然人都能获得证人资格,当事人一方有证据证明证人不具有证人能力,或者具有不能获得证人资格的法定情形时,该名证人将不具有证人资格②这意味着其将既不享有作证的权利,也不负有被强迫作证的义务。,而这一决定则应当通过证人资格的审查规则产生。
四、我国证人资格制度的双重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这条规定属于证人资格的实体规则。第60条第1款虽然不是直接关于证人资格的内容,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的规定,实际上便赋予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以证人资格,故可以将该条规定视为证人资格的积极规定,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证人资格。第60条第2款属于证人资格的消极规定,当证人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时,便不能作证人,即不具有证人资格。
(一)实然视角下证人资格制度的疑惑澄清
对于第60条第2款规定,有学者认为,“在语言的表述上,该条文的含义令人费解。到底是‘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和‘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之间是递进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模棱两可。”[11]实则不然。第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分析,“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与“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之间以逗号隔开,而“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与“年幼”之间以“或者”隔开,“不能辨别是非”与“不能正确表达”之间以顿号隔开,表明“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与“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与“不能正确表达”分别属于并列关系,但是“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与“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之间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如“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与“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之间亦属并列关系,那么应当是“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同为并列关系,应当统一用顿号或者“或者”隔开,而非该条所采用的分隔方法。第二,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分析,该条文的意旨并非欲将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者的证人资格排除,而是欲将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者的证人资格排除,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者只要能够辨别是非或者正确表达的,便应当具备证人资格。第三,从历史解释的角度分析,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摒弃了将某种外观身份作为证人资格的唯一的评价标准的做法,不论是生理上、心理上缺陷者还是年幼者,只要法庭认为其具备一定的感知、记忆、表达能力,其便具有证人资格。故从本条规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证人资格的消极条件应当为不能辨别是非或者不能正确表达,而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只是不能辨别是非或者不能正确表达的原因而已。
(二)应然视角下证人资格制度的缺陷审视
第60条第2款的现实缺陷在于,将“能否辨别是非”作为证人资格的评价标准的做法欠妥。“是非”并非一对法律上的概念却是存在于传统道德伦理的概念体系之中。法律的内容是立法者在经过价值评判、衡量之后的一个价值选择的结果。道德上的判断标准通常是“是或者非”,法律上的判断标准通常是“合法或违法”。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并不能够完全地吻合,两者经常在一定的场合发生激烈的冲突,如按照传统的道德观点,同性恋是不可容忍的,其在道德上的评价便是“非”;而在法律的角度,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同性恋,那么法律对同性恋的评价便是“合法”。道德上的“非”在法律上并不都是“非法”,而道德上的“是”在法律上也不都意味着“合法”。一个善良的父亲杀死一个恶贯满盈的儿子,在道德上得到的评价也许是“是”,但在法律上得到的评价更可能是“非法”。道德与法律的上述区别便是将道德标准引入法律评价的障碍之一。此外,道德标准的差异性、模糊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即道德并不像法律那样统一、明确。道德在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一点在地域辽阔的国家更为显著。道德本身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明确性,除了“大是大非”是非常明了的以外,在“小是小非”的一些问题上,道德也许会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对于法律而言,不统一性与不明确性将使其丧失本应具有的优良品质。
五、证人资格评价体系的去道德化与本质回归
证人资格评价标准的设置应当注意其对证人范围的调整作用。一方面,由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对证人资格设置较高的资格准入会将过多的证言排除出审理者的视野,导致发现案件事实的障碍。另一方面,如果不对证人设置资格准入,将导致一些不具备基本的证人能力的证人进入诉讼程序,虽然其证言对于发现案件事实也许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类证人不具备基本的证人能力,其证言为真的概率较低,由此可能会造成案件事实认定的混乱。前者实际上是证人证言给发现案件真实所带来的正价值,后者则是证人证言给发现案件真实所带来的负价值。
对证人资格所设置的准入标准应当对两者进行合理的平衡,一方面尽可能地使更多的证人作证以更好地发现案件事实,另一方面又应当将不合格的证人证言排除以保证案件事实的可靠性。这就要求合理的证人资格标准一方面不能将所有的证人都纳入合格证人的范畴,而应当对证人进行合理的取舍;另一方面,证人资格标准还要保证不能将过多的证人不恰当地排除。
目前,我国对证人所要求的“能够明辨是非、正确表达”显然并不符合一个基本标准的要求。一方面,“明辨是非”在含义上并不符合法律自身所要求的明确性,在实践中也并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应当舍弃。另一方面,“正确表达”实际上只涵盖了证人能力的一个方面,没有涉及证人的感知能力与记忆能力。故建议将《刑诉法》第60条第2款修改为“具备基本的感知、记忆与表达能力的人,都有作证资格”。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140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2537.
[3]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01.
[4]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01.
[5] 罗筱琦,陈界融.证据方法及证据能力研究(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70.
[6] 罗筱琦,陈界融.证据方法及证据能力研究(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13-14.
[7] [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417.
[8] [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417.
[9] 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册)[M].王利民,何家弘等,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33-134.
[10] 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册)[M].王利民,何家弘等,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33-134.
[11] 姚莉,吴丹红.证人资格问题重述[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5).
Study on De-moralization and Essential Returning of the Competency of Witness
Cai Zhenyu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Chongming County, Shanghai 202150, China)
The capacity of witness is the premise on which the competency of witness is based. The capacity of witness includes the actually capacity and the legal capacity. The competency of witness can not be achieved with out the actually capacity wh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 The legal capacit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ompetency of evidence. The competency of witness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 of witness. There are uncertainty and inconsistency in our rule of the competency of witness because of the moral involved. People shall be witness when they have radical capacity to perceive, remember and narrate to make the fi ltering witness reasonably.
Competency of Witness; Capacity of Witness; Perceive; Remember; Narrate
D918
A
1008-5750(2015)01-0062-(07)
2014-11-20 责任编辑:孙树峰
蔡震宇(1983— ),男,汉族,浙江温州人,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助理检察员,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刑法、刑事诉讼法、证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