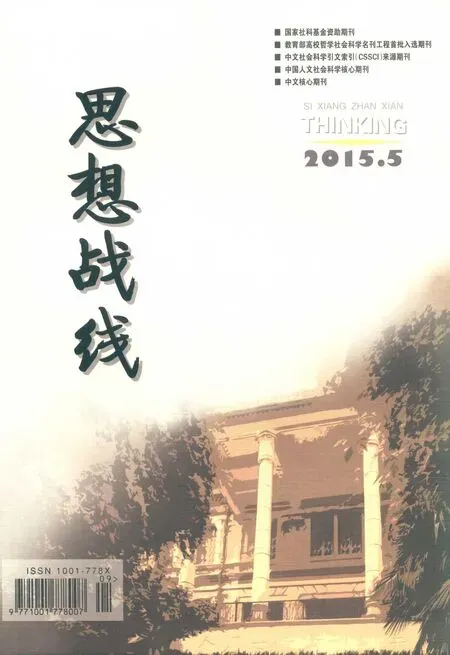神山下的王权:嘉绒藏人“代汝节”仪式考察与神话分析
张 原
神山下的王权:嘉绒藏人“代汝节”仪式考察与神话分析
张 原①
“代汝节”是嘉绒藏人最为重大的年度仪式,其仪式过程与神话意义所显现的“神圣历史”,对于嘉绒历史上王权观念之辨析极为关键。这种介于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王权观念恰是藏彝走廊社会人文特质的一种反映,也是地方封建的文化前提和政治结果。其对反思当代西方学界基于神圣王权而衍生出来 “绝对主权”之学说,以及基于中国历史现实建构一种更为包容的社会理论,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王权二重性;嘉绒藏人;“代汝节”;神圣历史
在首提 “藏彝走廊”概念时,费孝通先生就注意到这一区域社会人文特质的形塑与其历史上复杂的地方政权形态相关,他指出:“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①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在论及藏彝走廊的研究意义时,王铭铭则专门强调当地介于西藏高原的“神王体系”和东部汉人的 “非神王体系”之间的王制类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认为:“这当中或许存在一种中间型的新社会理论,对这一理论的求索应为西南人类学在世界人类学中的理论立足点。”②王铭铭,张 帆:《西南研究答问录》,《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可见,无论在历史现实的把握还是学术理论的追求上,王权研究都是支撑藏彝走廊这一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重要版块的一个核心议题。而位于藏彝走廊腹地正处汉藏互动要冲的嘉绒地区,其历史上独特的王权形态就值得特别关注。通过仪式考察与神话分析,本文将对嘉绒藏人纪念英雄阿米格尔东的 “代汝节”所呈现的王权形态加以辨析,并基于王权二重性的类型比较之讨论,来就藏彝走廊的区域人文特质和社会理论启发展开一定的认识提炼。
王权二重性:王权研究的问题拓展与个案类型
在社会人文科学中,王权研究是展开社会类型比较和文明形态考察的一个重要路径。特别是围绕王权的二重性所展开的关于自然与社会、丰产与秩序、继嗣与联姻、巫术与宗教、神权与政权、国家与地方等关系的议题讨论,均是经久不息的经典问题,并贯穿于从古典世界到民族国家的研究之中。
作为王权研究的开山之作,弗雷泽(J.G.Frazer)的 《金枝》对于学界各种王权二重性的探讨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③Feeley-Harnik,“Gillian.Issues in Divine Kingship”,Annual Review ofAnthropology,no.4,1985.在指出“祭司兼国王”这种将神职与王权合一的神圣王权 (divine kingship)是一个曾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过的事实之时,《金枝》也极具启发性地区分了王的两种面相:深居山川森林中的 “自然之王”,有驾驭自然的神力和促成谷物丰产的神职;身处城市宫殿中的 “城中之王”,则有统治社会的权力和维系人类秩序的权责。④[英]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107~111页。弗雷泽强调,在有别于宗教思想但更具普遍性的巫术思维中,其 “交感律”的意识原将自然与社会的生命力相等同一,并由神性君王所整体性地代表,所以周期性地杀戮体衰神王之弑君古俗实为一种更新世界生命灵力的丰产献祭。以金枝实为橡树槲寄生之隐喻,这部经典还揭示了古代社会“灵魂寄存于体外”之思想所秉持的神圣之灵本在社会之外的观念。⑤[英]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265~271页、第651~660页。受 《金枝》影响,葛兰言(M.Granet)的古代中国研究认为,乡村节庆中于山川圣地举行的两性合和仪式,正是基于“万物一致的至上规律”所进行的丰产献祭,而古代中国的君王则通过一系列礼仪与圣地的改造,将神圣性和整体性寄寓于自身以确立王权的合法权威性。①[法]葛兰言:《中国文明》,杨 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5~234页。霍卡 (A.M.Hocart)的 《王权》一书则基于斐济的田野研究更为经验性地证明,通过祖陵、圣坛、神山之献祭仪式,最初代表太阳的神王能与祖先和大地相联系,并成为代表祖先的神王,从而为世界带来丰产和秩序。这种基于 “神性的继嗣关系”将 “自然神”与 “祖先神”合一的既为大地丰产来源又是社会秩序保障的王权形态,不仅受到古埃及神圣王权的影响,也普遍存在于从古希腊到东南亚直至太平洋斐济岛的一大片区域中。②参见Hocart,A.M.,Kingship,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7。受葛兰言古代中国研究的启发,杜梅齐尔 (G.Dumézil)以一种类似“阴阳观”的圣孕 (hierogam ic)关系模式描绘概括了王权的二重性:即 “巫术性王权”与“祭司性王权”在诸如丰产创造性与秩序稳定性、好战武力与和平智识、外来征服者与土著本地人等二元关系中互补互生的,且二者最初往往存在一种联姻关系。③参见Dumezil,G.,Mitra-Varuna,New York:Zone Books,1988。针对印欧语系社会中较普遍存在的 “双王制” (pairing sovereign),杜氏还用一种 “等级观”,论述了祭司王权的司法秩序功能作为 “高尚魔法”可将巫术王权的丰产功能这一 “低级魔法”包含在内,从而建构起社会的整体性。④[法]杜梅齐尔:《从神话到小说:哈丁古斯的萨迦》,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0~89页。上述经典的王权研究表明,自然丰产与社会秩序作为王权的二重功能面相,在强调自然与巫术的社会中常会同构合一,而在看重社会与宗教的社会中则会等级分化。这其中,古埃及神圣王权形态中神圣整体的神王是前者的典型代表;⑤[美]富兰克弗特:《王权与神祇:作为自然与社会结合体的古代近东宗教研究》,郭子林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13页。而古印度世俗王权观念中世俗局部的君王则为后者的典型表现。⑥[法]杜蒙:《古代印度的王权》,《阶序人II》“附录3”,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
虽然印度是世俗王权的典型,而中国的神圣王权传统在进入周代之后就已式微,但夹在这两大文明中且受其深刻影响的西藏吐蕃文明却保留着神圣王权的传统。特别是依托于神山体系象征价值的稳定性,吐蕃赞普神话基于 “恰神族”与 “木神族”的联姻关系,以及巫术王权与祭司王权的兄弟关系,维系了吐蕃王权的神圣性。⑦张亚辉:《亲属制度、神山与王权:吐蕃赞普神话的人类学分析》,《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而作为印度与华夏两大文明体系的接触过渡地带,夹在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藏彝走廊地区,其历史上所出现的王权类型不仅受到吐蕃神圣王权的深刻影响,也与古代中国和印欧传统的王权类型相关联。特别是位于藏彝走廊腹地的嘉绒社会,不仅有着较为独特的神山信仰与政教制度,且当地土司也体现了汉藏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在走廊地带的拉锯与交融。⑧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边政公论》1947年第6卷第2期。在受中央王朝册封之初,多数嘉绒土司兼有宗教与政治首领的双重身份。⑨邹立波:《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二重性王权形态,实为藏彝走廊独特的历史人文特质之典型表现,并与经典王权研究的诸多个案构成了强烈的可比性。恰如石泰安 (R.A.Stein)在论证 “汉藏走廊”中的文化连续性时所指出的,在这一区域内具有武力性格的神山,往往是与各古部族的神王和先祖相联系的,节日中人们用歌舞来赞颂着神王的英雄功绩和部族的荣耀世系,就是为了证明这一联系。⑩[法]石泰安:《汉藏走廊古部族》,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8页。因此,基于对嘉绒地区集中展现神山、神王 (战神)与祖先世系关系的“代汝节”之考察,本文试图就当地王权形态的二重性特征加以呈现分析。
神圣的业绩:“代汝节”仪式习俗的场景呈现
“代汝”又称骀日,在嘉绒语中意为 “功成圆满之日”,直译为汉语就是 “节日”。相传英雄神王阿米格尔东在嘉绒地区完成降妖除魔的征战大业后,人们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活动,这个歌颂纪念格尔东丰功伟绩的庆典年复一年地举行,最终约定俗成为 “代汝节”。由于嘉绒百姓一般不用藏历,因此少有人过藏历新年。而农历春节虽受重视,但非当地传统节日。如此,意义重大且庆典隆重的 “代汝节”就被视为 “嘉绒新年”。⑪李 茂,李忠俊:《嘉绒藏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2~214页。作为嘉绒独有的一个重大节庆,“代汝节”独特的礼仪风俗生动地展现了嘉绒社会的人文特质,人们在这个年度仪式中所歌颂追忆的“神圣业绩”,则是其生活世界神圣实在的一种例证模式。
在整个嘉绒地区,“代汝节”的举行时间并不统一。据地方学者考证,这是因为嘉绒各地多是以传说中阿米格尔东征战到此的时间来过节,如马尔康的梭磨、松岗一带的村寨是在每年农历十一月的上弦日,而小金、丹巴和理县的一些村寨又是在农历二月。①雀 丹:《嘉绒藏族史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530页。小金县登春沟老协会的老人们则告诉笔者,从前嘉绒地区有3个骀日,农历十月十二日为土司骀日,各土司的官寨和家庙会举办法会祭祀活动、并上演 《格东特青》的跳神戏;农历十一月十二日为河坝骀日,各个寨子的百姓家户要制作阿米格尔东及其妃子娘娘的糌粑面塑来供奉,并要跳专门纪念阿米格尔东的锅庄舞来庆祝。农历二月十二日为山上骀日,人们会到当地较大的神山上举行 “送阿米格尔东”仪式,焚烧供品并诵经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恢复 “代汝节”传统时,将3个骀日合并在一起,但各地选择的日期并不统一。实际上,在嘉绒各地 “代汝节”的名称也有差异,如小金称 “格尔东节”或 “战神节”,理县称为 “甲纳节”,金川、丹巴又称作 “糌粑年”,马尔康的一些寨子则叫做 “骀日”。②张学风 (博洛·措斯曼),俄玛塔等:《嘉绒藏族的阿米格东文化》,《西藏艺术研究》2011年第3期。本文主要以笔者在马尔康县木尔宗乡斯鸟村所参加的骀日祭祀活动为例,来呈现典型的“代汝节”之主要仪式过程和关键程序步骤。
木尔宗乡位于马尔康县西部杜柯河北岸沟壑深幽的山谷台地上,原为松岗土司领地,该乡下辖的6个行政村的地名据传均与阿米格尔东在骀日降临此地的经历相关。传说格尔东降魔征战到木尔宗乡时,是从腾古村后面的大山上下来的,他在一半山坪地处停下来修整了一下,而腾古就是 “停下来”的意思;由于前面的一道山梁挡住了格尔东的视线,于是他飞身一跃而过,哈尔宾村由此得名,意为 “飞过去”;之后格尔东来到一村寨,人们为迎接这位降魔神王兴高采烈地跳起了锅庄舞,这个村庄就是斯鸟,其意 “狂欢”;格尔东继续前行征战时,一个村子的人看见了他的身影,一个村子的人听见了他的脚步声,前者叫莫尔多,后者叫斯眯,分别为 “看见了”和 “听见了”之意;最后格尔东来到一个村庄询问何处还有作恶的妖魔,当地村民过于紧张竟没人搭理作答,感觉自讨没趣的神王骂了一句 “聋子!”便飞身前往南方,从此这个村就被称为板登龙 (聋子)。第二天,人们在木尔宗南面的一个地方发现了格尔东下的一个白蛋,这就是今天观音桥镇的斯涛村,其意为 “下的蛋”。所以,在木尔宗乡真正过 “代汝节”的村寨其实只有腾古、斯鸟、斯眯、莫尔多4个村,而哈尔宾与板登龙两寨要么因被格尔东 “飞过去”所忽视,要么因被格尔东骂了句 “聋子”而受辱,都不愿过这个节日。③感谢木尔宗乡斯眯村扎西老人对这一地方典故的生动讲述和精彩解释。这个地名传说虽有后人对格尔东神话的牵强附会之意,但也可见“代汝节”对于木尔宗乡的嘉绒藏民而言意义极为重大。
每年农历冬月 (十一月)初十这一天,木尔宗乡的村民就开始用白色颜料重新粉饰家屋的外墙,将房屋染白并画上日月星辰图案和苯教雍仲符号,这正是 “代汝节”节庆将要开始的一个信号。村民们说,从前当地的 “甲蕃” (王)规定,每年农历冬月十三日为木尔宗纪念阿米格尔东功绩的骀日,人们要以染白房屋为约,请他从天界神山下凡到人们的家中享受祭祀,所以在骀日的前3天,各户要用白色颜料重饰外墙,迎接神王降临。农历冬月十一日这天,村民们开始打扫家屋内部,并用柏树枝熏除屋内的秽气,此时除旧迎新的过年意味加强。当天人们还要在家屋的内墙上作各种装饰,特别是要在火塘屋这一家屋中最神圣的房间之四壁墙裙上绘各种吉祥图案。通常村民们是用白色的青稞面粉在藤编的筛子上绘日月星辰和八宝图纹等,然后将其用力倒扣于墙上,这样面粉附着在墙上会留下具有晕染效果的图案。此外,人们还要用拇指沾上面粉在屋内所有的柜架沿边上涂白点,并在有神龛的墙上画 “雍仲符”。农历冬月十二日,天未亮,各家的主妇就纷纷早起到村外去取 “新水”,据说鸡鸣之后第一户取回净水的家庭来年将交好运,女人们都在暗中争先,男主人们则在家门口持哈达等待主妇们归来。取来新水后,一家人就开始制作被称为 “甲纳”的面塑馍馍。面塑的人物除格尔东和他的妃子娘娘外,还有家屋的各成员。另有日月、法宝等圣物,以及格尔东的弓箭、宝刀、长矛、盾牌等武器和五谷六畜等若干造型的 “甲纳”。家庭成员在作馍时会相互逗趣,其乐融融。 “甲纳”经烘烤后被穿上柏枝,分三层陈设供奉于火塘正中上方的壁坛神龛上,上层是格尔东和他王妃的面塑,二层为家屋成员的面塑,底层为五谷六畜。 “甲纳”陈列完毕后,祭坛前还要摆上糌粑、猪腿、水果、咂酒等供品。到晚上,家里的男主人要在坛前熏烧柏枝、上香点灯,进行简单的供奉仪式。
农历冬月十三骀日当天,传说这一天如能在太阳快升起之前抢早煨桑,能让家庭来年福运昌盛,所以各户长者一大早就到房顶上煨桑祭祀。煨桑前先要将神箭与柏枝插进屋顶的煨桑祭坛上,并在熏烟的龙口贴上白色的羊毛;煨桑时要不断向龙口内撒糌粑,并口念祭祀阿米格尔东的颂辞,祈请格尔东降临世间、庇佑家人安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屋顶的煨桑礼仪结束后,家户主人还要回到屋内的火塘边熏烧柏枝,并跪在阿米格尔东塑像前祈福。午后,全村男女会聚集到寨子后面的神山上,举行一系列的祭祀祈福、欢聚娱乐活动。隆重的煨桑插旗祭祀山神的仪式结束后,人们围成一圈饮酒欢唱,并跳起专门纪念阿米格尔东的锅庄舞,其唱词大意为:“阿米格尔东下山降魔来了,十一月十三日来到这里,给我们带来了吉祥幸福,百姓们为他献上这支锅庄。”在一些村庄,男人们还会跳模仿神王征战场景的盔甲舞,其最后颂辞为:“胜利了,阿米胜利了;感谢啊,感谢格东啊,胜利了,白色的人类胜利了;消灭了,黑色的妖魔消灭了!”①张学风 (博洛·措斯曼),俄玛塔等:《嘉绒藏族的阿米格东文化》,《西藏艺术研究》2011年第3期。傍晚时村民各自回到家中,按尊卑长幼顺序逆时针围坐于火塘边,简单祈祷后开始享用一年中最为丰盛的晚宴。宴席上人们要放开肚子吃美味的食物,大人们常会向小孩打趣,要吃得越多越好,否则阿米格尔东会生气带走村中吃得最少的小孩,年长者甚至还会鼓励家人要在此时畅饮美酒,因为吃过这顿饭不显醉意的人来年将不交好运。酒足饭饱之后,全家人会一边跳锅庄舞,一边追忆格尔东的事迹。之后的两天,人们走亲访友,常聚在一起通宵达旦地喝酒跳舞。
农历冬月十六日是节日的最后一天,村寨要举行 “送神仪式”。当天各家各户将供奉在壁坛神龛上的 “甲纳”取下,切下一小块交给村中专门选派的村民,将其送至神山上焚烧敬神。以前从村中各户收集起来的 “甲纳”馍块要交由土司或头人,并由其专门派人代表全寨来火祭献给阿米格尔东,现在则由各家之长者在村中推选数人来代表全村完成这一程序。村里一长者告诉笔者,到神山上火祭送神的人担了很大的风险,所以从前这些人回村后,会有一些专门针对他们的神秘禁忌和隐秘仪式,但今天这一习俗已极为简化,在斯鸟村送神的人,只要从山上取一些白石置于自家屋顶即可灭灾。而在村中,各家各户则要将剩下的 “甲纳”面馍全部分由家人和牲畜一起共食,以享神佑。 “甲纳”吃完后, “代汝节”也就此圆满结束。
作为一个在特殊的时空节点周期性地回归神圣原点的年度庆典,嘉绒藏人的 “代汝节”充满了 “显圣”的意义。伊利亚德 (M.Eliade)指出,社会常通过节日来与一个元始的神圣时间重新合一,从而使得人类能定期地与诸神同在。并且人们在节日中所体验到的时空是神圣原初的,诸神与祖先正是在这个原初状态中从事创造宇宙和组织世界的活动,或向人类揭示生活与文明的基础。节日则基于神圣历史和神圣业绩的反复模仿与再现,确认并复归了世界存在的神圣范式,并循环不断地更新再生宇宙。②[美]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0~55页。所以,将“代汝节”视为嘉绒新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风俗比附,这个节庆确实充满了一种周期性神圣回归和宇宙更新的 “复始重生”之年节意味。很明显,“代汝节”的仪式过程,是围绕着对英雄神王阿米格尔东的祭祀而展开的,落实的则是人们对丰产兴盛与秩序平安的祈求。仪式作为一种“社会戏剧”,其过程步骤充满了极具社会文化隐喻的象征性行为和场景。③[美]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刘 珩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3页。在 “代汝节”习俗活动所设置的象征场景中,充斥着对王权二重性的种种隐喻化表达。当然要理解在仪式过程中,房屋外墙染白、供奉面塑馍馍、神山歌舞相聚、家屋欢宴畅饮、“甲纳”的山上火焚与家中分食等一系列仪式情景的显圣意义与象征隐喻,以及人们在节日中追忆纪念神王阿米格尔东 “功成圆满”的事迹所突显的神圣原初的范式内涵,则需要基于神话传说的阐释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来完成。
神圣的历史:格尔东神话传说的意涵解读
如果说 “代汝节”是嘉绒社会每年重复上演的一出富有深层意味的 “社会戏剧”,那么在节日中所传颂的格尔东神话则是 “永恒的剧本”,其讲述展演的正是嘉绒藏人 “神圣的历史”。恰如伊利亚德所指出,那种把有意义的神话在整体上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原始而神圣的历史,以其原始而神圣的论证方式解释了世界、人类和社会的存在,由此成为整个宇宙最根本的实在。而这恰是构成神话一度被看做 “真实历史”的理由:它叙述了事物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例证的模式,还论证了人类之所以如此言行的根据。①参见 [美]伊利亚德 《宇宙创生神话和 “神圣的历史”》,载阿兰·邓迪斯编 《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作为在仪式中传颂展演的一种神圣的原初经典,格尔东神话所显现的 “神圣历史”赋予了嘉绒社会一种终极实在的例证模式。
嘉绒地区的格尔东神话流传版本颇多,各地传颂不一。从情节设置和表现形式上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为民间口承的传说 《阿米格尔东》,一为仪式表演的戏剧 《格东特青传》。前者可视为该神话的一种质朴传说形态,其遵循了一个大致的叙述框架,又留给民间大众丰足的情节改造空间,使其能够具体地嵌入于地方场景中,从而能将永恒典范的神圣历史生动地转化为一种民间地方的事迹典故;后者则为该神话的一种精致文本形态,其完善了神话的基本展开逻辑,又让上层精英可以能动地设置新的关系结构,使其能够动态地反映历史的情景,最终使得终极范例的神圣历史更为灵活地与现实的政治历史态势相嵌合。由于民间传说 《阿米格尔东》与嘉绒藏戏 《格东特青传》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互文影响关系,所以二者发生的先后关系今天已难考证。因此只能选取有代表性的版本,来对比传说与戏剧两种类型的阿米格尔东神话之异同与流变,以窥探作为嘉绒藏人神圣历史的阿米格尔东神话有何独特历史文化内涵。这里以木尔宗乡民间流传的 《阿米格尔东》传说和松岗土司戏班改编的 《格尔东特青》戏剧为蓝本,就格尔东神话的内容情节进行大致总结。
传说 《阿米格尔东》梗概:
从前,一对夫妇年近六十未有子嗣,一日老妇误将神鸟在山上所下的1个白色大卵当作白石抱回家中。一道白光闪过,卵内窜出一男孩,被夫妇所收养,两人用各自名字的首音为其取名 “格尔—东”。格尔东见风就长且饭量太大,3日后老夫妇怕养不起,不得已将其送回山中 “放生”。又过3日老妇前去探望,发现格尔东已长成一个靠打猎为生的强壮青年,格尔东打了大量猎物让老母带回家与老父同享。这件怪异事情让族人甚为惊惧,因害怕本领异常的格尔东会吃空人们的粮食,决定将其驱赶流放至远离村庄的大山中。3年后,嘉绒地区有一群黑妖兴乱,毁庄稼,吞百姓。人们处于绝境时,格尔东从山上下来,用山中的白石击杀黑妖,将其赶到河中。为感谢格尔东挺身而出降伏妖魔拯救百姓的行为,人们将他从山上抬到村中,拥戴他为首领。然而格尔东却担心自己饭量过大,不愿留下。众人为难之际,一位巫师作法将格尔东的饭量降为常人水平,格尔东得以留在世间,并娶妻生子。之后格尔东带着他的儿子们四处降魔,为嘉绒地区带来平安幸福。妖魔除灭后,格尔东成神回到了山上,他的儿子们则留在世上成为各地的首领。为纪念格尔东的功绩,每年人们都要从山上迎请格尔东回来享受祭祀,并祈求他带给世间兴旺与吉祥。为表示对格尔东的尊敬,人们在他前面加上 “阿米”的尊号,意为 “先祖老爷”。②本神话传说情节梗概总结自木尔宗乡斯眯村扎西、阿让初等老人的口述记录。
戏剧 《格尔东特青》梗概:
远古时期,嘉绒地区深受崇尚血祭人殉的原始苯之荼毒残害,妖魔兴乱世间,百姓苦不堪言,天王决定派出战神下凡除妖降魔。正好有一对年过六旬未有子嗣的夫妇向雍仲苯求子,于是天王让老妇梦中受孕,战神由此转世到这户人家,成为这对夫妇的长子。夫妇俩高兴地用各自名字的首音为其取名 “格尔—东”,因是家中长子,又称呼其为 “特青” (大哥,长兄)。格尔东出生后的第一天就吃了1升糌粑,第二天吃了2升糌粑,第三天吃了3升糌粑。夫妇俩无力供养,只好求助部落首领,但首领怕格尔东吃空部落的粮食,下令老夫妇将出生仅3天的格尔东送到后山森林中 “放生”。山林中的格尔东以打猎为生,并练就了一身本领,还发明了弓箭、宝刀、长矛、盾牌等武器。3年后一群练就原始苯黑魔法的妖魔在魔王卡巴劳让的带领下到世间兴乱,每日吃掉3户人家,并生出3窝妖魔。世人无力抵抗,绝望之际,藏王波德贡甲遵照雍仲苯教师祖旦巴辛绕的预言,派老夫妇去山林中请格尔东特青下山除妖。老母在一条溪流处喝水时遇见了格尔东,格尔东遵母命毅然出山。带着他制作的兵器从天而降来到校场上,受藏王之托率领将士出征伏魔。格尔东在战场上大显战神之威,用闪着白光的神弓利剑击杀群妖,并与魔朱、岗朱、卡巴劳让等魔头斗智、斗勇、斗法,最终将其降伏收服,嘉绒地区获得太平,雍仲苯教也昌盛起来。藏历虎月十三日,盛满五谷六畜、山珍美味的宫殿内,万民欢呼同庆格尔东降魔胜利。藏王波德贡甲想把王位让给格尔东,可因担心人们承受不起他过大的饭量,格尔东不愿为王执意回山。最后,格尔东与波德贡甲约定以房屋染白为号,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下凡到嘉绒各地去巡视,除妖降魔给百姓带来兴旺吉祥,而人们在这一天则将以最为丰盛的晚宴,特别是吃不完的糌粑来感谢招待格尔东特青。①本神话戏剧情节梗概总结自科乐柯·若拉的 《论我国藏戏系统中的嘉绒藏戏》。参见中国戏剧志·四川卷编辑部编印 《四川省嘉绒地区藏戏问题研讨会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93年,第63~64页。
对比民间大众流传的 《阿米格尔东》传说与土司戏班改编的 《格尔东特青》戏剧,二者在情节叙述上的异同之处值得关注的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身世经历上,英雄格尔东的神奇生育对这个本无子嗣的家庭而言是件喜忧参半的事。实际上无论是传说中的 “神鸟降世卵生”,还是戏剧中的 “梦孕转世胎生”,都在表明格尔东的出生显世是对以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生育方式和亲属制度的否定与超越。虽然通过父母双系并重的命名方式,格尔东被纳入到家庭之中,然而其过大的消耗能力却使得其被整个社会放逐排斥,而他之后在野外山林中的游猎生活,则又一次构成了对家庭与社会的否定与超越。特别在传说中,猎人格尔东在打猎时表现出的过度丰产能力,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弹,使其被族人驱逐于离人类村庄更远的旷野山林中,而这个细节则与戏剧中部落首领的 “荒野放生”命令构成了一种呼应。家庭夫妇的乏力无奈与族人首领的惊惧无情,均表明了个体家屋的过度丰产对整体社会的秩序维系是一种威胁,因此社会将要求家庭做出一种牺牲。当然基于格尔东的身世经历,神话所最终要强调的是,格尔东最初是一个与社会有诸多结构性对反的异质性 “他者”。
其次,在功绩创造上,英雄格尔东的超凡本领与伏魔业绩对处于危机绝望的社会而言,是一次让人铭记感念的神圣拯救。而无论是传说中的“白石击黑妖”,还是戏剧中的 “白光神箭杀群魔”,这场白与黑的神话战争很明显是对古代中亚文明的正义光明与邪恶黑暗之宇宙大战的模仿,由此宇宙秩序得以建立。不过在传说中战斗所创建的是 “白/天 (山) /神—黄/地/人—黑/水/鬼”之等级秩序,这是原始苯教萨满式宇宙观的一种反映。而在戏剧里则是战争中雍仲苯教对原始苯教 “智、勇、法”的全面压服,这是雍仲苯教地方传播史的一种提炼。并且戏剧中练就原始苯黑魔法,每日吃3户人家、生出3窝妖魔的卡巴劳让最终被格尔东所降伏之情节,则类似于杜梅齐尔所强调的丰产之低级魔法向司法之高尚魔法臣服之过程。②[法]杜梅齐尔:《从神话到小说:哈丁古斯的萨迦》,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16~118页。此外,拯救村庄百姓和领军校场将士的格尔东是在山中修炼并从山上下来的,以及 “山中的白石”和于山中制造的“闪着白光的”武器等神话情节表明,拯救社会的神力并不在社会之中,而是在社会之外的山上。由此,山的神圣性被彰显出来,此时作为一个与社会有诸多结构性对反的异质性 “他者”,格尔东反而成为社会秩序的创造守护者。
最后,在功成圆满时,英雄格尔东最终离开了凡世回到山上,其每年按约定周期性回归凡间巡视嘉绒的日子,则成为整个世界复始更新的重要节日。当然,无论是传说中的阿米格尔东的尊号,还是戏剧里格尔东特青的称呼,均表明格尔东虽为社会的一个异质性 “他者”,但其在亲属关系中有自己的位置。民间传说中的 “阿米”(祖爷)称谓强调的是拟制性的继嗣关系,因此在节日中周期性下凡的英雄格尔东被作为 “祖先”来供奉,并以 “家神”与 “先王”来享祭;而土司戏剧中的 “特青”(长兄)称谓呈现的是拟制性的兄弟关系,格尔东在仪式周期回归时,则被作为 “客人”来接待,并以 “战神”与“护法”的身份来显现。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取得降魔胜利后,当人们试图接纳格尔东并拥其为王时,他却因担心饭量过大表露出不留世间回归山林的意愿。此时,在传说中出现了一个巫师帮助格尔东降低了饭量,使他成为了王留在世界继续去征伐妖魔保护人民,但妖魔被消灭完后,格尔东最后还是回到山上成了神;而在戏剧中,格尔东则直接拒绝了藏王的让位提议毅然回山,人们无非是在他每年定期下凡巡视时要慷慨地招待胃口大的格尔东。这样,格尔东之社会的异质性“他者”形象在神话的结局中最终被保持下来,只是这种异质性成为了一种超凡脱俗的神圣性。
英雄格尔东的身世经历、功绩伟业与结局命运作为嘉绒社会一种 “永恒回归的神话”之主题,是一个需要在节日仪式中被不断反复的原型范式,如此世界才能周期性地回归到所谓的“神圣的历史之初”,从而成就宇宙的年度再生。③[美]伊利亚德:《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杨儒宾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73页。实际上,一旦把握了格尔东神话显见而表层的情节框架,“代汝节”仪式活动中那些充满了感官性象征的 “浅层隐喻”就能彰显其意义,如全村染白房屋外墙,正是通过回归神王的“卵生”原点来重启神圣的历史和约定;家庭成员在家屋中欢快地制作和供奉 “甲纳”面馍,则是用家庭亲属关系来接纳神王的回归;到村外争请新水,以及在神山上插箭祭祀和于旷野中歌舞相聚,是在重现迎请英雄出山征伐妖魔的情景,并在盔甲锅庄舞中重演那场圣战;在晚宴中放肆的吃喝则表现了人们对格尔东超大饭量的模仿和包容;将 “甲纳”面馍的一部分送回山上火焚是在送神王英雄回归山林离开凡间;在家中分食大部分 “甲纳”面馍则表明其开创的神圣业绩和留下的神圣福泽已经被整个社会所吸纳。一旦理解了这个神话隐秘而深层的逻辑内涵,就能对其具有强烈引导性的 “深层隐喻”(即社会秩序关系实质之规定)进行感悟,如格尔东“神鸟卵生”与 “梦孕转世” 的身世、 “胃口大”和 “本领大”的特征,以及 “重回山林”和 “定期下山”的结局所突显的正是神王与凡人,或者战神与国王之间充满张力的矛盾关系。而基于白与黑、山与屋、神与人、秩序与丰产、克制与过度等类似的结构对立关系,嘉绒社会关于宇宙、山川、王权、家屋、社会等基本观念的意义指向变得明确,其王权二重性的地方特征也展现出来。
神王的回归:嘉绒王权观念的特征与理论启发
英雄神王格尔东每年按约降临凡间的 “代汝节”庆典,是嘉绒社会重获丰产生机与秩序祥和的宇宙再生节点,而围绕着格尔东的年度回归,嘉绒藏人的神圣历史也得以展开。这与王权研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夏威夷 “马卡希提”(makahiki)节庆中 “罗诺神” (Lono)的年度回归庆典,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对照关系。将二者进行比较则可基于王权二重性的讨论,来认识和反思现代社会理论的建构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
在当代学界,“马卡希提节”已经成为衍生社会理论的一个源泉。弗雷泽将此作为周期性弑君古俗的有力证据,以说明基于一种 “交感思维”之原则,神王的死亡与复活再生是维系生命之灵的不朽和拯救世界万民的生活之重要手段。①[英]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萨林斯 (M.Sahlins)则将其作为 “陌生人—王制” (stranger-king)的典型例证,以阐发在 “权力的他性”之观念中,神王的回归与权力篡夺是外在于社会且超越生命局限的权力被共同体所接受吸纳之关键路径。②[美]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159页。虽然格尔东的身世特征类似于弗雷泽所描述的那种身处社会之外山林之中的 “局部的自然之王”,不过其神力却不在于驾驭自然和激发丰产,而是秩序的创造与守护。尽管英雄格尔东周期性地回归社会的“代汝节”年度庆典可视为一种阈限 (liminali⁃ty),其归来也如萨林斯所论述的那样是将一种宇宙力量注入于社会之中,但这种神圣力量不是“宇宙的生命”,而是 “宇宙的秩序”。由此,可将嘉绒王权的第一个特征归纳出来:作为一种介于神圣王权与世俗王权的中间过渡形态,其对秩序的重视大于对丰产的关注,因此,来自社会之外的神圣力量并非是要触发更新大地丰产,而是在创建维系宇宙秩序。
“马卡希提节”与 “代汝节”的庆典仪式均为 “双王制”的一种地方呈现,但丰产巫术的王权与秩序祭司的王权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嵌合在一起的。萨林斯指出,夏威夷人的 “图神”(或“库神”Ku)作为国王的神灵或人民的祖先具有武力和篡夺的征服者战神性格,其与具有和平和丰产之神性的 “罗诺神”之间存在着对抗关系。因此在 “马卡希提节”中,战败且被驱逐的“罗诺神”虽然回归世间,但最终 “图神”再次战胜了 “罗诺神”,并将其等级涵盖,这是社会获得丰产的保证。如此在节日中地方土著与外来他者的功能属性出现了一次翻转,原为土著丰产神的 “罗诺”被逐于社会之外,而外来战神“图”则入世于社会之中。出世的 “罗诺神”在其年度回归中实为被献祭牺牲者,其被代表战神的入世国王所涵盖包容,由此身处社会之中的国王成为整个社会的最终担当者。萨林斯 “陌生人—王制”的这种终极宇宙秩序和最高精神价值最终被社会之内的国王所掌握的论述,实为一种 “文化本质主义”,其滋生出的将是一种现代性的 “绝对主权”(或 “最高治权”sovereignty)理论。而在 “代汝节”中,藏王和嘉绒人民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土著生产者的形象,英雄格尔东作为社会的异质性 “他者”则是创造维系秩序的神王,在年度回归世间之时,其与世间国王和人民间存在的是一种合作关系。石泰安曾指出,嘉绒地区最大的神山墨尔多 (Mu-rdo)是一座天神下凡的 “木”(Mu)神山。③[法]石泰安:《汉藏走廊古部族》,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而墨尔多在很多地方的嘉绒人看来正是格尔东最初下凡的神山。由此,出现于 “代汝节”庆典仪式中的双王制所要处理的实为 “木神族”和 “恰神族”之关系,即天的秩序与地的丰产。虽然木神山就在当地,但战神格尔东作为 “木神族”的一员其实是一个出世者,他功成之后的隐退,恰说明了所谓的终极秩序和最高价值处在社会之外的他处,因此,这里的王权观念并不在现代性的“绝对主权”之思想谱系之中。由此,嘉绒王权观念的第二个特征可总结为:入世的地方国王承担着社会丰产的功能,宇宙秩序的担纲者则是一个出世的英雄神王,而当地这种 “有地无天”的王权形态即是地方封建的文化前提,也是封建地方的政治结果。
最后与 “罗诺神”被视为一个 “给妻者”或 “舅父”的姻亲亲属身份不同,附加在格尔东身上的是 “阿米” (祖爷)与 “特青” (长兄)这样的血亲亲属称谓。这表明 “神性继嗣”与 “兄弟互补”这两种关系才是嘉绒社会关联神王与世人的根本机制。这正恰如石泰安所指出的,具有战争特性的神山总是与王统世袭、氏族祖先、英雄战神相联系,且这种联系集中展现于为表现这一关系而举行的节日活动中。①[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224~235页。在 “代汝节”中,仪式的辉度性与神山的稳定性正是社会彰显与获得神圣性之关键。实际上,被称作“代汝石雷” (意为 “节日中的戏耍”)的 《格尔东特青》正是当地的 “甲蕃” (国王或土司)为彰显自己的功绩而排演的仪式戏剧,相传最早的演出是金川甲蕃在公元758年为庆祝其建成嘉岭青王宫和雍忠拉顶寺的庆典中上演的。乾隆十四年 (1749年),十一世松岗土司昌旺扎尔甲为庆祝自己被朝廷由安抚司升封为宣慰司而组建戏班改编排演了 《格尔东特青》戏剧,被视为嘉绒戏剧的成熟之作。②赞拉·阿旺措成,张锦英:《嘉绒藏戏的历史渊源及艺术特征》,《四川戏剧》1994年第1期。所以,编排上演代汝石雷戏剧的 “代汝节”,实为一种建构王权辉度的庆典,当然这种辉度是基于土司与战神间的拟制性兄弟盟约关系之再现而生成的。在百姓传颂讲述的传说中,由于英雄格尔东被纳进了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亲属制度之中,其子嗣作为嘉绒各地的祖先则不可避免地存在神性 “等级衰降”问题,此时能挽救世系神性衰降的就是神性恒定的神山。因此,嘉绒王权观念的第三个特征可归纳为:神山与继嗣关系是其王权神圣性的恒定价值之表现,也系嘉绒社会展开历史的一种根基性观念;而仪式与兄弟关系则是其王权世俗化的声望竞争之呈现,也为嘉绒社会的政治宗教精英应对“改土归流”的一种策略,二者的混融是历史的结果和反映。
作为嘉绒藏人独有的年节庆典, “代汝节”的仪式习俗和神话传说是极其杂糅的,从中可看到诸如印度婆罗门的 “卵生起源”、吐蕃赞普的“神王出山”、伊朗摩尼教的 “光明黑暗大战”,以及萨满式 “三分宇宙观”等古文明的宗教文化因子。实际上,夹杂在华夏、西藏、印度、伊朗等文明之间的藏彝走廊本就是一个多重文明的复合体。③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而嘉绒地区则是这种文明交互关系的典型,基于仪式考察和神话分析,本文所粗浅辨析的嘉绒王权的观念特征,已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那种过于强调单一独立的整体性社会观,并呈现出一种充满弹性且重视 “关系”的社会形态。西方学者对于单一性特征的痴迷,导致了 “文化”与 “社会”两个概念的重建失败。④参见 [美]萨林斯 《整体即部分:秩序与变迁的跨文化政治》,刘永华译,载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9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年。在西方新近的王权研究中,格雷伯 (D.Graeber)通过对社会如何通过弑君来超越生死地追求绝对权力,以及如何通过对宇宙秩序的模仿来形成国家(state)及其权力治理之 “理想形式”,就 “绝对主权”概念进行了溯源式的理解。⑤David Graeber,“The Divine Kingship of the Shilluk”,Journal of Ethnography Theory,vol.1,no.1,2011.这种研究正如王铭铭所批评的那样:
为了建设国族,现代学界信奉了一种基于神圣王权神话衍生而来的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就是关于不朽的王冠与处于生死之间的王的 “不对称”关系理论,当其演化为国族时代的 “主权论”时,不仅带来了历史的断裂,也让人们陷于自我与他者的定位困境。⑥王铭铭,张 帆:《西南研究答问录》,《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实际上,嘉绒 “代汝节”所呈现的这样一个介于 “神王”和 “非神王”之间的社会体系观念,正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理论中的诸多困惑,其让我们观察到了一种既向 “他者”开放又不失“自我”的包容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因此,每当“代汝节”仪式开启之时,嘉绒藏人在神山下迎送英雄格尔东之际,一种针对现代社会理论的阈限式实践和思考就在不远的他处一年一年地重复进行着。
(责任编辑 段丽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藏彝走廊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经验的人类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13xsh030);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2014-xwd-s0304)
张 原,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四川成都,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