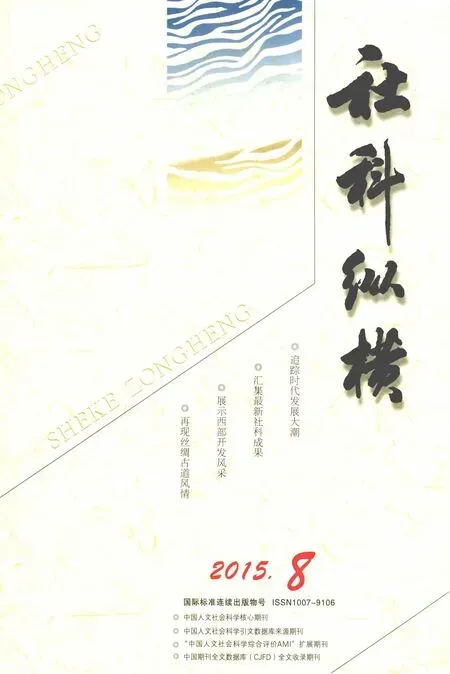哈耶克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任红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科部 北京 100038)
在20世纪的世界思想发展史上,英国思想家哈耶克以坚定地捍卫法治理想闻名遐迩。哈耶克的法治思维源出于对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与实践演进历程的深刻反思,对于当前我国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法治是良法之治而非实然之法之治
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法治思维都信奉法律之治,哈耶克的法治思维也不例外,他说:“真正与身份之治(a reign of status)构成对照的,乃是一般性的、平等适用的法律之治,亦即同样适用于每个人的规则之治,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法治’”[1](P191)。
英国法律实证主义者约翰·奥斯汀强调实然之法的绝对权威,主张纵然是所谓的恶法人们也必须毫无例外地严格遵循。美国思想家潘恩也主张,“对于一项坏的法律,一贯主张(也是我身体力行的)遵守,同时使用一切论据证明其错误,力求把它废除,这样做要比强行违犯这条法律来得好;因为违反坏的法律此风一开,也许会削弱法律的力量,并导致对那些好的法律肆意违犯”[2](P222)。然而,哈耶克对法律之治的理解却与约翰·奥斯汀等人明显不同,他并非机械地强调法律的至上性,而是强调实然之法与良法的区分,拒斥实然之法的至上性,只强调良法的绝对权威。在哈耶克看来,法治之法属于良法,是应然之法,而非实然之法,他说:“法治是这样一种原则,它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亦即关注具体法律所应当拥有的一般属性”[1](P260)。哈耶克致力于澄清实然之法(the actually valid law)与良法(the good law)的界限,强调只能赋予良法以至上地位,只能要求人们遵守作为正当行为规则的良法。他说:“只要我们想维护自由社会,那么我们就只能强制公民遵守那部分由正当行为规则(主要是指私法和刑法)所组成的法律并使它们对公民具有约束力”[3](P53)。
在相当一部分赞同法治的人看来,“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说法无疑体现了法治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在哈耶克法治思维的语境中,“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论断却不一定符合法治的要求。哈耶克认为,如果“法无明文不为罪”中的“法”所指的只是立法者所颁布的成文规则,该论断就和法治相去甚远;只有当该论断中的“法”指的是作为良法的正当行为规则,该论断才能体现出法治的精神。在一些人的思维框架中,政府只要依法办事就完全符合了法治的要求,然而按照哈耶克的逻辑,依法办事并不等于法治,关键要看所“依”的是不是良法。哈耶克说:“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4](P82)。
另外,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重要一点是,哈耶克的法治思维在强调法律至上性时,不仅不是指实然之法的至上性,而且也不是指每一个别的良法的至上性,而是指由良法构成的规则整体的至上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我所谓恪守规则,不是指那些一条条的孤立规则,而是指规则构成的整体”[5](P527)。这就意味着,哈耶克只是赋予了由良法构成的规则体系以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但却并不认为每个别的良法都是神圣的、至上的,都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不能有例外的。实际上,不去机械地固守每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很容易为法律规则的不断发展完善预留下充分的空间,而哈耶克毫无疑问是主张自发形成的良法并非完美无缺、一经形成就永恒不变,所以他特别强调良法的不断进化、强调要通过一致性和否定性检测不断对良法进行持续优化。
二、良法的基本属性
在哈耶克的各种文本中,指称良法的概念包括“应然之法”、“正当行为规则”、“真正的法律”、“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理想形态的法律”、“自由的法律”、“法治之法”等等。哈耶克认为,良法必须具有以下属性:
第一,自发性。在哈耶克看来,自发性是良法的重要标志。良法的自发性表现在,“法律并不是任何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进化和自然选择过程的产物”[3(P90)。哈耶克坚决反对把法律视为立法者意志的体现,“法律仅仅是立法者意志的产物,法律的存在以某个立法者的意志的事先构想为前提——这种观点事实上是错误的”[5](P527)。在哈耶克看来,良法并不是任何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演进过程中经由自然选择自发形成的。立法者的作用是发现并阐明未阐明的正当行为规则,实现未阐明的正当行为规则向成文法的转化,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创制法律。
第二,抽象性。在哈耶克看来,抽象性是良法的本质属性,缺乏抽象性的法律只是名义上的法律,只是针对特定情形的具体命令。抽象性意味着良法必须是目的独立的,是“指向不确定的任何人的‘ 一劳永逸’(once-and-for-all) 的命令,它乃是对所有时空下的特定境况的抽象,并仅指涉那些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及任何时候的情况”[1](P185)。
第三,确定性。在哈耶克看来,法律的确定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的判决可以被预见。确定性的关键要点在于“法院的判决是能够被预见的,而不在于所有决定判决的规则是能够用文字表述的。坚持法院的行动应当符合先行存在的规则,并不是主张所有这些规则都应当是明确详述的,亦即它们应当预先就一一用文字规定下来”[1](P265)。二是那些不导致诉讼的争议的结果也是确定的。哈耶克认为,法律确定性的程度并不能够根据案件的结果加以评断,“而必须根据那些并不导致诉讼的争议来判断,这是因为从符合法律的角度来考察,其结果实际上是确定的。正是这些绝不会诉诸于法院的纠纷,而不是那些诉之于法院的案件,才是评估法律确定性的尺度”[1](P265)。
第四,平等性。哈耶克认为,规则的平等适用对于维护法治是至关重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说,“法治的理想,既要求国家对他人实施法律——此乃国家唯一的垄断权——亦要求国家根据同一法律行事,从而国家与任何私人一样都受着同样的限制”[1](P267)。
第五,否定性。哈耶克认为,良法从根本上说是否定性的,“它们所含有的乃是旨在划定每个人(或组织起来的人群)的确受保障领域之边界的禁令”[6](P188)。良法“并不明确告诉我们应当去做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仅仅告诉我们不应当做什么”[5](P612)。所以,良法本质上不是规定特定行动的规则,而是约束行动的规则。
三、法治的核心是限权
哈耶克继承了高度重视限制政府权力的优良法治传统,他指出,“法治的基本点是很清楚的:即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4](P74)。在限制权力问题上,哈耶克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人类理性有限性的新视角确立限制政府权力的理论依据。大多数法治论者以人性恶为理论依据演绎出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认为如果没有必要的限制,人的贪婪、情欲等劣根性必定使拥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从而损害公共利益。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人性本善、道德境界很高的贤人君子掌握了权力,那么制约权力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事情。哈耶克的法治思维超越了人性是善是恶的纠缠,以人的理性有限为逻辑起点探讨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无疑为制约政府权力提供了新的更可靠的理论依据。在哈耶克看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知识则是分散的、多样的、多变的,任何人(包括贤人君子)、任何机构、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掌握和拥有影响个人具体行为的所有知识。因此,即使是以善良愿望为出发点的政府权力也必须用良法加以限制,否则强制的权力必定会损害人们的自由,阻碍社会的良性进化。
第二,从“四权分立”的角度构建限制权力的新模式。在西方社会,人们普遍认同的法治框架往往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维度设计权力制约的基本模式。哈耶克通过研究发现,在“三权分立”模式中,法律常常成为权力的帮凶,政府机构往往以法律之名对公民进行强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法治思维局限于用法律制约行政权和司法权,完全遗漏了对立法权的制约。人们把立法机构所制定的一切东西都称为法律,而立法机构往往会出于特殊目的为特殊情形颁布一些只反映特殊利益而侵害公共利益的法律,政府机构执行这样的法律,虽然行为合法,但却侵害了个人自由,背离了基本的法治精神。因此,哈耶克主张在传统的“三权分立”基础之上,再对立法权进行分立,设置专门的立法议会和政府治理议会,前者担当颁布实施良法的职责,后者负责具体的政府治理方面的任务,从而形成“四权分立”的权力结构。
第三,通过反思民主制度强调用良法限制多数人的权力。传统的法治理论往往迷信民主制度,忽视了对多数人权力的限制。似乎只要权力为多数人所行使,权力滥用就不复存在。然而,在哈耶克看来,“无视对多数权力施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这一论点极为重要”[1](P141)。哈耶克认为,“任何权力都不应当是专断的以及一切权力都应当为更高级的法律所限制”[1](P222),多数人的权力也不例外。在哈耶克看来,由多数投票决定的事项并非越多越好,对于应当由多数投票决定的问题必须在范围上加以明确限制,多数人不应当随意决定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以及实施这些权力的方式,多数的权力必须受到作为良法的正当行为规则的限制。
四、哈耶克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第一,提升法律的权威性。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法律的权威性不高,法律的至尊地位尚未确立。当一些群众认为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尤其是这种侵犯来自政府机构时,他们很少诉诸法律手段维权,反而频频采用上访、越级上访甚至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法律确有至尊地位,群众能够借助法律途径成功维权,那么,他们当然不会冒险采用比较偏激的维权方式。因此,提升法律的权威性、确立法律的至尊地位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而要提升法律的权威性,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必须处理好权力与法律的关系,真正使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权力的权威。哈耶克强调用法律制约一切权力,法律必须是限制权力的法律,而不能是充当权力工具的法律。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必须科学立法,用良法驱逐恶法,使法律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要确立良法之治,使法律捍卫人民利益的实质内容得以实现,法律必须具有一些不可缺少的形式特征。哈耶克对法律形式特征的高度重视,他对良法的自发性、抽象性、确定性、平等性和否定性的分析与阐述,对于我们实现科学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必须加强权力结构的科学化建设。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廉政风暴,铲除了一个又一个“大老虎”、“小老虎”。但是,反腐败的成效仍然与公众的期待有比较大的距离。问题的症结到底是什么?哈耶克的思想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哈耶克猛烈抨击西方的“三权分立”限权模式,主张用“四权分立”取代“三权分立”。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四权分立”模式本身,而在于通过权力结构的科学化建设最终实现有效限制权力的法治理想。要有效限制权力、遏制腐败,必须紧紧抓住权力结构的科学化建设这一根本问题。如果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无论思想教育如何创新,也不管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如何发展完善,腐败分子都会很容易找到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寻租空间。因此,权力结构的科学化建设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道,我们必须把反腐败的重心转移到权力结构的科学化建设上,把现行的权力结构中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设置不合理等弊端消除掉。对于查办出来的腐败案件,我们不能满足于弄清腐败分子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以警示后人,也不能满足于泛泛地谈论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而应当深入分析腐败行为发生的每一个环节,挖掘出现有的权力结构究竟存在哪些缺陷为腐败官员提供了腐败机会,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创新,消除权力结构的缺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腐败机会,真正从源头上保证权力的正当使用。
[1][英]哈耶克.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美]潘恩.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英]哈耶克.邓正来等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4][英]哈耶克.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C].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6][英]哈耶克.邓正来等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