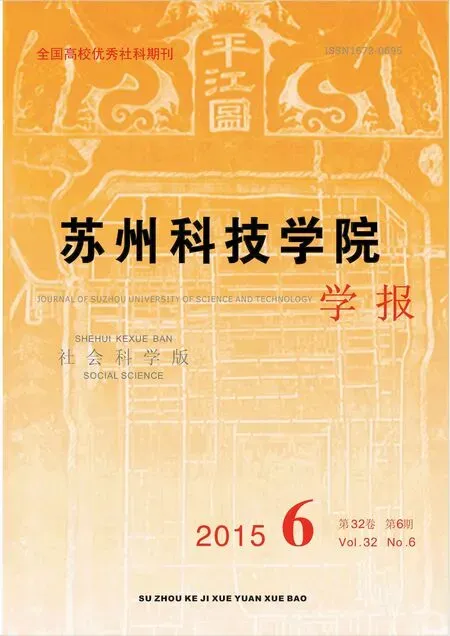康德式的动物伦理
王 珀
(山东交通学院 社会科学教学部,山东 济南 250031)
康德式的动物伦理
王 珀
(山东交通学院 社会科学教学部,山东 济南 250031)
康德认为人对非人动物不负有直接义务,这是因为康德的理论具有一种抬高理性、贬低动物禀性的倾向。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根据对康德伦理学的客观价值论解读,唯有理性是至高无上的客观目的,动物禀性只具有工具性价值,这种立场面临种种困境。然而,根据主观价值论解读,理性立法意志是道德价值之源,它可以将动物性利益(不管是人的,还是动物的)规定为道德法则所关注的目的本身,因此动物可以成为价值承载者。另一方面,动物本身可以因拥有感知能力而成为价值主体,为其自身赋予内在价值。
康德;人是目的;动物伦理;动物权利;内在价值;科斯嘉
一、康德的间接义务论及其问题
在动物伦理学界,康德的动物伦理思想常常被归为“间接义务论”。康德认为,我们对动物*人也是动物,但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提到的“动物”特指“非人动物”。不负有直接义务,只负有间接义务。我们之所以反对虐待动物,不是因为动物本身值得我们关心,而是因为虐待动物会使人性变得残酷无情,会导致人对人的残酷。所以,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人性,动物只是人的工具。[1]212-213也就是说,对动物的关心只不过是为人与人之间的严肃道德游戏做准备的一种“道德热身”[2]157活动而已。
与“间接义务论”相对的是“直接义务论”。后者认为虐待动物之所以错误,主要在于动物因其自身之故而拥有直接道德地位,而不仅仅在于这样做会败坏人性,或者会间接导致人对人的伤害。笔者认为,“直接义务论”比“间接义务论”更有说服力。
所谓的间接义务,实际上就等于不负有任何道德义务。举个例子。一个年轻人平时一发脾气就摔盘子砸碗,如果对这种暴力倾向不加以制止或合理引导,也可能导致他对人造成伤害。我们能不能说,人负有一种不肆意破坏餐具的道德义务,因为肆意损坏物品不利于培育善良的品格?但实际上,我们对餐具本身不亏欠任何道德义务,这种不破坏的义务是“关于”这些餐具的,而不是“亏欠”这些餐具本身的。假如一个人在摔打盘碗上的暴力宣泄可以减少他对人类的暴力行为,那么这样做就没有问题。同理,正如艾伦·伍德(Allen Wood)对康德间接义务论的批评:如果一个人在动物身上发泄可以减少他对人的暴力、使他变得更加与人为善,那么他反而有义务去虐待动物[3]194-195。
在现实中,残忍对待动物并不必然导致人对人的残忍。例如,医学院学生即使在经历了很残酷的动物实验之后,也未必会沦为冷酷无情的人,他们仍可以成为悬壶济世的仁医。那么,根据间接义务论,只要医学院学生的心理自控能力足够强,无论一种动物实验有多么的残酷,它都不存在道德问题。
动物不是物件,它们会感到痛苦与恐惧。把一只活生生的小猫撕成碎片与把一只玩具猫撕扯成碎片不是一回事。尽管两种行为都表现出一种残暴性情,然而一个造成了直接伤害,另一个没有。康德的间接义务论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动物的苦难本身不值得引起我们的直接道德关注。
随着人类道德文明的提高,对动物利益的漠视已经被视为康德伦理学的重大缺陷,即使当代最著名的康德主义者,如克里斯汀·科斯嘉(Christine Korsgaard)、艾伦·伍德等人也不同意康德的间接义务论。为了弥补康德理论的这一重大缺陷,他们纷纷对康德的思想进行更具包容性的解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康德式的直接义务论。
也就是说,对康德动物伦理学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康德本人的只言片语上。在康德著作中也可以找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言论,但我们并不认为康德伦理学是支持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的。所以,我们要区别对待“康德本人的观点”与“康德主义理论”。[4]对康德伦理学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康德本人的某些具体主张,而是要在深刻理解康德理论整体逻辑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动物伦理问题。
康德之所以贬低动物的道德地位,这是因为其理论具有一种抬高理性、贬低动物禀性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存在以下两种解读思路:
根据客观价值论解释,理性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客观价值,它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凌驾于各种经验层面上的主观偏好之上。无论理性者在现实中的主观目的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承认:唯有理性禀赋是目的本身,动物禀赋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康德似乎相信一种自然目的论,认为理性存在者是大自然目的链条中的最终目的,人之所以优越于其他动物,就在于被自然赋予了理性禀赋,人应当超越自己的动物本能,尊重并发展自己的理性能力。所以,“人是目的”实际上是指“理性是目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康德会认为动物性利益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在这里,客观价值论似乎推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结论,这看似与环境伦理学中的价值论立场相违背。因为在一些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主观价值论似乎就意味着人作为价值主体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而客观价值论则意味着存在某些独立于人类评价的价值,但这是一种误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客观价值论可以主张价值独立于任何个人的主观评价,另一方面主张只有人可以成为价值承载者。下文会看到,主观价值论也未必推出一切价值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因为有的人类个体不是价值主体,如永久植物人,而很多有意识的动物则可以成为价值主体。对于这个误解的澄清,可参见John O’Neill, “The Varieties of Intrinsic Value”, The Monist, 1992, Vol.75, No.2, pp.119-137.
根据主观价值论解释,价值源自有理性者的主观建构。建构主义者坚持“哥白尼革命”式的价值论立场,认为康德伦理学不必诉诸形而上学色彩浓厚的自然目的论,或者理性在自然秩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也不必诉诸什么神秘的客观价值实体。在康德那里,理性之所以具有崇高地位,是因为理性反思能力是道德价值之源,理性使人获得道德自律能力,人在做出道德行动的时候要克服感性偏好对自己的他律性影响。但是,建构主义并不认为动物秉性只能被用作工具,因为有理性的自我立法者可以从主观角度为动物性利益赋予非工具性价值。
二、客观价值论解读
“人是目的”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核心命题。这个命题似乎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学极不友好。人是目的,那么动物呢?为什么康德认为我们应当尊重人,而不是动物?“人是目的” 这个命题究竟什么意思?
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目的,一条狗也拥有自己的目的。仅靠人拥有目的这个事实,并不能推出人类具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道德优越性。然而,在康德那里,人的目的和动物性目的是有区别的。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分析了人类本性中的三种禀赋:第一,动物性禀赋,即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人拥有一种追求自然本能意义上的自爱目的,包括自我保存、繁衍和从事社会生活;第二,人性禀赋,即作为一种有生命、同时又有理性的存在者,人能够运用理性能力去理解幸福、去追求幸福(指自爱意义上的幸福);第三,人格性禀赋,即作为一种有理性同时又能够负责任的存在者,人尊重道德法则,能够按照道德法则而行动。[5]24-27由此可以区分目的性的三个层次:本能地拥有目的、自我设定目的、根据定言命令为自我设定道德目的。其中后两个层次要求具有理性能力。
很多动物有自己的目的,关心自己的生活。有些动物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些目的,例如,“忠犬八公”决定终生忠于自己与主人的承诺。有些灵长类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行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选择。动物学研究表明,很多动物的行动并不是“刺激—反应”这么简单。少数较为聪明的哺乳类动物也许可以达到目的性的第二个层次,它们为了长远目标而克制当下的欲求,它们拥有自我意识,甚至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有所反思。但是,这些目的大多是追求自爱意义上的快乐或幸福而已。当然,动物界也存在一些低层次的道德现象,例如,利他主义、合作与互惠、公平与惩罚等等。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哪个物种可以像人类一样,有能力基于对普遍道德律的尊重而为自己设定道德目的,它们很难达到第三个层次——即拥有人格性禀赋。*由于从动物界到人类之间的过渡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不存在明确界线,所以任何在人与动物之间明确划界的企图都很容易遭到动物学研究的反驳。但本文暂不考虑这种复杂性。笔者要论证即使那些仅有动物性禀赋的动物也具有直接道德地位,所以处于简化论证的需要,下文提到的“动物”,仅指那些只有动物性禀赋的动物,不讨论那些具有初级理性能力的动物。
“你要这样行动,把不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都同时用作目的,而决不能只是用作手段。”[6]38这是康德“人性公式”的经典表述。要弄明白“人是目的”究竟什么意思,就得首先需要弄明白究竟什么是“人格中的人性(humanity in one’s person)”?根据杨云飞的解读,在康德那里,“一般的人性指设立目的之能力,则‘人格中的人性’应指设立道德上目的之能力”[7]409-410。“倘若我们从人性中抽掉其人格性的部分,则人充其量只不过是比其他动物更懂得如何计算利益、满足欲望等略高一级的动物,在此,我们看不出人的任何崇高和神圣。”[8]65可见,“人格中的人性”实际就是指人格性禀赋,唯有人在道德上的理性自律能力能够彰显人的优越性。*当然还有不同的解读,有一种解读认为“人格中的人性”是指人性禀赋。但是,不管哪种解读正确,由于两种禀赋都与理性能力相关,所以这并不影响下文对理性(作为客观目的)地位的讨论。刘作认为,“人是目的”这个口号容易引起歧义,让人误认为人性中的感性要素也能成为目的,其实更为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人的理性是目的”。[8]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康德绝不是生物物种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因为他认为道德规律“不仅对于人,而且一般地,对于一切有理性的东西都具有普遍的意义”[10]58。如果我们发现某些外星动物也拥有理性,那么在他们人格中的理性自律能力也可以成为目的。所以,与其说“人的理性是目的”,不如说“理性是目的”。
“理性本性是自在目的这一原则,……它适合于一切有理性的东西,……人性不是主观地被当作人实际上作为目的的对象,而是被当做作为规律而成为一切主观目的之最高条件,被当做客观目的,不管我们所想的目的是什么……”[10]83在这里,康德明确区分了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尊重人的理性是一种客观要求,这个要求跟现实中的人们的主观偏好无关,不管人们主观上是不是重视自己的理性,理性都是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康德似乎认为人的感性偏好是不值得我们尊重的,他说过:“我也不会对爱好表示尊重,不论它是我自己的,还是其他别人的”[10]50。康德在很多段落中都透露出一种高扬理性、贬低感性的态度。“爱好……不能因它自身被期望而具有什么绝对价值,而每个有理性的东西倒是期望完全摆脱它。”[10]80人的理性本性“是客观目的……其实存自身就是目的,是种任何其他目的都不可代替的目的,一切其他东西都作为手段为它服务,除此之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了”[10]80-81。这显然是一种很强的客观价值论立场。
如果只有理性可以成为目的本身,在它面前感性偏好(包括那些动物性欲望)“一文不值”[10]46,又因为动物不具备康德意义上的理性自律能力,只拥有感性经验层面上的利益,就可以推出动物不能成为道德法则所直接关注的对象了。 然而,如果人性公式只尊重抽象的人类理性,而不讨论经验层面上个体的主观目的,那么它将面临“空洞化”的危险。如翟振明指出,如果主张把一切“把人视作目的”的人视作目的,将陷入一场“无止境自指的游戏之中”[11]81。我们可以设想如下无穷自指的问答:“人是目的”究竟要求我们怎么做呢?如果一个人把人视作目的,那么他就是个人,我们就应把他视作目的,就应当尊重他的目的。那么怎么做才算是尊重他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他实现他的目的。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那么“人是目的”究竟要求我们怎么做呢?……
一种可能被康德用来摆脱上述困境的策略,就是承认经验层面上的感性利益具有某种工具性价值。因为在经验世界中理性的存在需依赖于生物学身体,所以康德也许可以建立一种让生物学身体服务于理性能力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是不缺乏经验内容的,康德本人就经常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例讨论中。例如,在自杀例证中,康德认为因逃避困境而自我毁灭是错误的,因为这是把自己的人格看作一个维持舒适状态的工具*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在书中第73页,康德给出另一种反对自杀的理由,即自杀这种行为是不可普遍化的,人不能意愿一种不可普遍化的行动。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反驳理由,一种基于理性是客观目的,另一种则属于建构主义论证。,而且因贪图安逸和享乐而不发展自己的才能也是错误的。[10]74-75可见,“尊重理性”就是要求人们应当尽力去保存、培育和践行自己的理性能力,进而要求人们应尽量维持有理性者的生命、并且让“潜在的”有理性者发展出理性能力、让具有理性能力者去践行自己的理性自律能力。
尽管一个三岁的儿童不具备道德自律能力,但这个孩子内心中的理性萌芽也值得我们尊重,我们应通过教育来培育其理性能力。一个人自暴自弃,沉溺于感官享乐,毫不珍视自己的理性自律能力,但这也不能使其沦为任人宰割的动物,因为他的理性仍然埋藏在他内心深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客观目的/主观目的”的区别。也就是说,尽管一个人可能主观上更重视自己的动物性利益、对自己的理性能力视而不见,但在客观来讲,唯有他的理性是值得尊重的,他的动物性利益本身一文不值。
如果这种对客观目的学说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人的生物学身体只是一具承载理性禀性的容器,唯有理性可以成为目的本身,满足人的生物学需要只是为了间接地维持和发展理性能力。可见,这个论点不仅可以推出我们对动物只负有“间接义务”,也可以推出我们对自己的生物学身体也只负有一种“间接义务”。
但这种间接义务论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的身体只是一具用来承载理性的容器,这将推出我们无法接受的结论。杰夫·瑟伯(Jeff Sebo)对这种间接义务论提出如下反驳。众所周知,对很多人来说性欲是理性的头号大敌,如果把一个人阉割可以很好地帮助他发展和践行其理性能力,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义务这样做呢?饮酒容易让人丧失理性,我们是否应当禁酒?当然,我们有时出于健康考虑来反对饮酒。但正如康德本人所说,健康反而可能会导致一个人荒淫无度,那么此时健康就不具有任何工具性价值。有时身体残疾恰恰可以促进人的理性能力发展,从司马迁到霍金,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砍掉一个人的脑袋会让他丧失理性能力,但砍掉他的一只胳膊就未必减损他的理性能力。是否由此可以断言,我们负有不砍掉一个人脑袋的间接义务,但不负有不砍掉一个人胳膊的间接义务呢?[4]瑟伯马上想到一种为康德辩护的思路:也许因为我们的感性与我们的理性处于同一具躯体之中,所以前者因此就获得了直接道德地位。但是,这种说辞并不解决问题。凭什么说仅仅因为二者在同一具躯体之中,前者就可以获得直接道德地位?瑟伯认为这种辩护是失败的,正如我们不能说:因为一条狗和一个人恰好处于同一间屋子里,所以这条狗就获得了直接道德地位。[4]
然而,瑟伯并没有穷尽所有的辩护策略。康德主义者还可以给出其他的解释思路。例如,他们可以说:尽管感性欲望不利于理性自律能力,它仍然具有某种工具性价值,因为它的存在可以为自由意志在经验世界中的彰显提供条件。如果没有感性诱惑,就没有对诱惑的克服与超越,那么在经验世界中我们就观察不到这个人的自由意志了,所以感性诱惑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性价值——它为实践理性提供了一种“试练”环境。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辩护思路也行不通。假设在该例中,此人总是经不起感性诱惑的考验,那么感性诱惑就没有这种工具性价值。如果某人的性欲正在越来越严重地侵蚀此人的理性自律能力,我们处于对此人理性能力的着想而阉割他似乎就具有道德正当性了。另外,还有这样一种辩护思路:尽管这个人一味地沉溺于享乐、荒废自己的理性能力,但只要他没有去危害别人的人性,那么我们伤害他就是错误的。然而,这个辩护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质疑者可以继续追问“究竟什么叫危害别人的人性?”如果危害人性仅指危害别人的理性,那么为了提高一个人的理性而伤害对方的身体就不是不道德的事。
可见,如果认为唯有理性是客观目的本身,动物禀性只是维持和发展理性的工具,就会推出一系列荒唐的结论。我们必须得承认,人的动物性利益就是目的本身。
三、主观价值论解读*笔者着重讨论科斯嘉对康德的建构主义解读。当然,罗尔斯式的契约主义也可被归为对康德的建构主义解读,但限于篇幅,契约主义的动物伦理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笔者将在其他地方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康德主义伦理学对于上述反例只有一种可行的辩护策略。康德主义者可以这样说:残害一个人的生物学身体之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违背了此人的自主意愿。只要一个人在主观上赋予其自身的动物性禀性一种重要的价值,我们就得将他的正当的动物性利益视作目的本身。这是一种诉诸主观目的论的辩护思路,这样我们就走向了对康德伦理学的建构主义解读。
康德伦理学强调人的主体自由。在康德看来,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可以对自己的欲望冲动有所反思,人可以主观上自己决定自己的目的。但这不意味着人必须否定自己的动物性,一个人可以通过反思将自己的动物性视作自我同一性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科斯嘉所说的“反思性认可”。一个人不想无端遭受肉体伤害,这是一种完全正当的感性欲求,我们不能打着促进别人理性禀赋的旗号去伤害别人的身体。尊重一个人的自主性,就要求我们尊重这个人所重视的合理目的,这进而要求我们关注这个人的动物性利益。
那么在前文引文中,康德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贬低感性的态度又该作何解释?当康德说“爱好……不能因它自身被期望而具有什么绝对价值”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感性偏好的价值取决于理性评估。在经验世界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种必然被所有人普遍认可的感性偏好,即使是像疼痛这样的被大多数人所反感的负面体验,也是有可能具有正价值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此例参考了哈里·法兰克福用以讨论高阶欲求的一个类似的例子。。一个研究新型麻醉药的药剂师,为了体验这种新药对疼痛的缓解效果,自愿为自己制造了一种剧痛,在测试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强忍着这种痛苦。这是被他的自由意志所认可的痛苦,与普通人或动物所被迫遭受的痛苦似乎具有不同的价值。我们也许可以说,他的理性为自己设定的最高目的为这种痛苦赋予了正价值。可见,感性偏好的价值会随着理性为自我所设定的目的而变,所以感性偏好的价值是外在的、有条件的,它的价值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最终唯有理性才内在地具有无条件的绝对价值(即尊严)。
理性是价值之源,它使人具有反思能力,使人能够与自己的动物性拉开距离,反思自己的感性冲动,不受感性冲动任意摆布。这正是自由的体现。对有理性者来说,只有经过了理性反思而被自我认可的感性体验才具有价值。按照这个逻辑,痛苦作为单纯的自然事实是价值中性的,只是当它发生在那些不愿意无端遭受痛苦的理性者身上的时候,它才被赋予负面价值。由此似乎可推出,只有理性才是最终的目的本身,而那些没有理性、只有感性欲望的动物就不能成为目的本身。
我把以上推理概括为以下几步:
因为(1)人的感性偏好的价值取决于人的理性评估;
所以(2)唯有理性具有内在价值,感性偏好(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不具有内在价值;
又因为唯有人类拥有理性,动物缺乏理性,它们只有感性偏好;
所以(3)唯有人类可以成为目的本身,动物只具有工具性价值。
这个推导过程看似有理,但其中每一步都不成立。科斯嘉认为从(2)到(3)的推理是错误的,所以从康德的理论并不能推出动物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笔者同意科斯嘉,并还侧重分析了从(1)到(2)所存在的问题,但这里首先讨论科斯嘉的分析。
科斯嘉作为一名建构主义者,认为价值是主观建构的,而不是源自某些客观事实、或客观实体。根据这种立场,价值既不来自某种形而上学的客观秩序(如认为人类理性是自然秩序或上帝计划中的最终目的),也不是来自单纯的自然事实(如认为肉体痛苦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坏的)。价值只能产生自价值主体的主观评价。
以疼痛为例。根据科斯嘉的立场,疼痛之所以是件坏事,不是因为它内在地具有负面价值属性,而是因为有感受能力者认为这种体验是坏的、并努力避免这种体验。有时候人们反而会赋予某些痛苦以正面价值,此时痛苦就未必是一件需要避免的事情。科斯嘉举了一个例子,即当我们深爱的人去世的时候,我们愿意体验悲伤之痛,思念亲人的痛苦。[12]177所以,痛苦有时也可以被赋予某种正价值。
至此,科斯嘉的立场和康德一致。但是,科斯嘉区分了两个常常被学者们混淆的不同的二分法:“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和“目的价值/工具价值”。她指出,前一种区分关系到价值的来源,即某事物的价值究竟源自该事物本身,还是来自某种外在源泉;后一种区分则关系到我们赋予某事物以价值的理由:我们是因其自身之故,还是因其服务于其他目的而赋予它以价值。[12]127理性反思能力为感性利益赋予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感性利益的价值来源是外在的,但我们不能由此推出感性利益仅具有附属于理性的工具性价值。我经过反思之后,赋予我的动物性以重要价值,此时我就把它们规定为我所珍视的目的本身了。尽管我的生物学身体的价值源自于我的理性评估,然而一旦它获得价值,它就成了目的本身,不再仅仅是承载理性的“容器”,其他人不能以促进我理性发展的名义来伤害我的肉体。也就是说,感性利益的价值源自理性的赋予,但这不意味着感性利益不能成为目的本身。简言之,一个事物不具有内在价值,并不能推出它不具有目的价值。*我们还思考一个与这个问题相对称的问题:如果一个事物是价值的来源,就能断定该事物本身就具有目的性价值吗?因为理性是价值的“源泉”,就可以断言理性本身就具有最高的价值吗?这个逻辑就好像当我们看到“泉眼中流出水来”,就断定“泉眼本身也有水”,甚至断定“泉眼中所蕴含的水比流出来的水更多”。但问题是,理性不仅仅赋予感性以正价值。根据康德本人的观点,理性似乎更多地是在赋予感性以负面价值,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就推断理性是一个“价值黑洞”呢?这种类比思维是不恰当的,因为价值并不是一种像流水一样四处传递的形而上学实体,理性也不是什么“水源”或“黑洞”。价值的形成不过是价值主体对事物进行或好或坏的评价而已。按照科斯嘉的思路,如果一个人经过理性反思之后,把自己的理性能力本身认定为组成自我同一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那么理性就成为了目的本身。也就是说,理性是一个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对这个人来说具有一种目的性价值。所以,从(2)到(3)的推理是不成立的。
如果我认为我的感性利益是我所珍视的目的本身,那么根据可普遍化法则,类似的情况应做类似的判断,我也应当把别人身上、乃至其他动物身上的类似利益视作目的本身。
注意,这里追加使用了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康德那里,自律公式和普遍法则公式具有内在一致性。人是有理性自律能力的存在物,我作为有理性者是一个自律的人、是一个尊重原则的人。如果我不讲原则,我的行事方式朝令夕改,那么我实际上就是让自己服从于呈现在我眼前的任意感性冲动,那么我就是他律的、是不自由的。自律的人尊重规律,所以我的原则不仅仅是为我个人的特殊利益而任意建构出来的,它必须在形式上赋予其他类似存在物与我类似的道德地位。
康德之所以贬低感性,主要是因为他担心感性偏好会腐化一个人的善良意志,作为一个理性自律者,我既不能任由自己身受感性冲动的摆布,也不能让自己的一己私利凌驾于他者利益之上,但这不意味着感性利益不能成为目的本身。*类似的观点,可参见Michael Cholbi, “A Direct Kantian Duty To Animals”,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4, Vol.52, pp.338-358.如果我认为自己的感性利益是值得关注的目的本身,那么我也应当认为动物的类似利益也是目的本身。如果这些利益发生了冲突,那么我应当运用理性在自我与他者的类似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比较。作为有善良意志的人,我不能仅仅考虑我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仅仅把他者用作手段。
一名康德主义的素食主义者会这样对自己说:我作为有理性的自我立法者,不能仅仅为了满足吃肉的欲望就把动物用作手段,如果我将我自己的生命和感受视作目的本身,而且我知道动物也不想失去生命和遭受痛苦,那么我就应当将动物们的生命和感受也视作目的本身。如果我不想遭受它们那样的痛苦,那么我因为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而为它们施加痛苦就违背了定言命令的普遍法则公式。
正如科斯嘉所言,“我们和动物们共享着同一种奇怪的命运——即我们都是关心自己的有机生命体。……我们通过自我立法,将动物性(animal nature)规定为目的本身”[12]105-106。“不仅仅作为人,而且作为能感知的东西,作为动物,你赋予自身以价值,你就是你自身的目的。”[12]175
这里,反对者肯定会提出以下质疑:只有作为理性和感性之有机结合体的人才有能力赋予自身的动物性以价值,动物只有感性没有理性,所以它们不能赋予自身价值。科斯嘉借用黑尔(R. M. Hare)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来回答这个反驳:假设你的理性就要被抹除掉了,那么当那个不再具有理性的你的身体在遭受虐待的时候,你对这件事是否在乎?[13]32我们的答案显然是:在乎。“当你认识到你赋予疼痛和恐慌的负价值,不是源自你的理性本性而是源自你的动物本性时,那么,这就给了你一个赋予你的这些同类生物的痛苦和恐慌以负价值的理由。”[12]322
动物秉性必须成为目的本身,“如果你不赋予你的动物本性以价值,你将不能赋予任何东西以价值”。因为这最终会“削弱所有的价值基础”[12]175-183。正如前文所分析,如果认为只有理性是目的本身,这要么会使道德原则失去经验内容,要么会推出令人无法接受的结论。
四、动物的内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嘉似乎给出了两个不同的论证:第一,动物具有某种类似于人的同一性,我尊重我自己的自我同一性,所以根据普遍法则,我也要尊重动物的同一性,又因为痛苦会对动物的同一性造成威胁,因此我要关心动物的感觉体验;第二,仅仅拥有感觉体验就可以让一种存在物成为价值主体,所以动物的感觉体验本身就是价值之源,并因此具有内在价值。然而,科斯嘉所引述的黑尔的思想实验似乎验证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正如帕特里克·凯恩(Patrick Kain)对这个思想实验所提出的质疑:如果被剥夺了某种重要的本性,我还是我吗?[14]230如果那个被抹除了理性的人不再是我,那么我所关心的就未必是我的同一性,我之所以关心这件事,是因为这个思想实验让我以第一人称视角真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有感觉的存在物(不管它还是不是我、它是否拥有理性)不希望遭受无端的虐待,它为这种痛苦赋予一种负面价值。
因此,不仅理性能力是价值之源,感受能力单独就可以成为价值之源。科斯嘉承认, “很多事物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未必因为我是一个自律的理性存在者。食物、性、舒适、免于痛苦和恐惧,这些之所以对我有价值,是因为我是一个动物(animate being)”[15]13。可见,她也同意动物因拥有感性体验能力而拥有评价能力,它们赋予自身的感性体验以价值。*当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成为价值主体。例如,一只蚜虫也许能体验疼痛,但它能成为一个为疼痛赋予负面价值的主体吗?这种“反身性评价”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我意识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很多动物的感性利益的价值来源是内在的,它们不仅可以被人类视作目的本身,也可以把它们自己的利益视作目的本身。所以,由(1)到(2)的推理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 (1)人的感性偏好的价值取决于人的理性
所以 (2)唯有理性具有内在价值,感性偏好(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不具有内在价值;
即使我们承认前提(1)是成立的*这个前提是否成立,得看这里的“取决于”是什么意思了。人的理性的确可以为感性偏好赋予价值,但这种价值量的改变也许只是外在的,不是内在意义上的。考虑上文提到的麻醉师的例子,这个例子并不能用来证明麻醉师所体验的痛苦不是一种内在恶,只不过在那个麻醉师那里,这种痛苦暂时获得了一种外在工具性价值,他制造麻醉药的目的也许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也许是为了挣钱追求自己未来的更大的幸福,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为了追求其他目的而不得不自己承受这种痛苦而已,也就是说,痛苦的工具性价值量暂时压倒了痛苦的内在恶而已。邱少云为了战略大局而忍受火烧,我们不能说邱少云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忍受这种痛苦,一种更令人接受的解释就是:尽管这种痛苦本身是一件坏事,但邱少云因追求其他更高的目的而选择忍受了这种痛苦。,即人的理性反思能力会改变感性偏好的价值,这也不能推出未经理性反思的感性偏好“一文不值”。回忆科斯嘉的例子。一个人的妻子去世了,他认为此时最恰当情绪是就是体验悲痛,而不是享受快乐。但是,假如另一个人是天生乐天派,他不假反思地带着快乐甜蜜的感受去思念他逝去的妻子,他经历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喜丧”,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不能说后一种未加理性反思的快乐不具有内在价值。
这就涉及那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VS满足的猪”的经典难题了。苏格拉底具有理性反思能力,他认为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但这个论断仅限于他对于他个人生活价值的判断,对他个人来说,过上一种理性反思的哲学生活也许是幸福;但是,对于那只猪来说,它的幸福要简单纯真一些:晒晒太阳、在泥土中打滚、草地上的奔跑、和同伴玩耍、免受恐惧与痛苦。*那么,对于那些本来有理性能力却自愿选择过像猪一样单纯简单生活的人呢?如果他们的选择不伤及他者利益、不涉及道德问题,那么只要是他们自愿选择的,那么他们的生活仍然有价值。所以,从“人的理性为自己的感性偏好赋予价值”并不能推出“动物的感性能力不能为自己的感性偏好赋予价值”。作为感受主体的动物的感性和作为理性主体的经过理性反思的感受,二者也许属于不同意义上的内在善。尽管这些动物们缺乏善良意志,但从卢梭式的价值立场看来,这属于一种未经理性沾染的原始而质朴的善。从康德主义观点看来,如果享乐会腐化人类的善良意志,那么它就是坏的;但对于动物来说,它们没有善良意志可遭受腐化,那么它们的快乐就是一种纯朴的内在善。*迈克尔·乔比对这个论点给出了更细致的康德主义辩护。参见Michael Cholbi, “A Direct Kantian Duty to Animals”,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4, Vol.52, pp.338-358.
请注意,这里并没有犯“自然主义谬误”,本文没有试图由单纯的自然事实(即“痛苦发生在动物身上”这个事实)直接得出价值论断(即“动物的痛苦是内在恶的”)。笔者的主张是,如果体验痛苦的动物厌恶这种痛苦,那么它们就在主观上为痛苦赋予了一种负面价值。这仍是一种主观价值论立场。在这里,价值源自价值主体(即动物)的情感态度,而不是源自单纯的自然事实。
对痛苦的厌恶,意味着动物不仅仅消极地接受痛苦,还要对痛苦有一定的反身知觉,这种知觉能力不同于理性高度上的反思,它属于一种感性意义上的反思能力。一头猪虽然没有像人一样的理性,但它对疼痛的反应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它知道这种体验对它自己而言是不好的。对它来说,这种疼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事实,它知道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其他存在物身上;它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受到了威胁,于是它反对这种疼痛,当它体验到这种疼痛的时候,它抗拒并竭力摆脱这种疼痛,它还可以在疼痛真实发生之前就可以预见它,并由此产生恐惧,它还学会了在事先尽量避免这种疼痛……总而言之,它不是被动接受各种体验,而是拥有偏好,并且为满足偏好而行动,即拥有雷根所说的“偏好自主性”[2]72。它是价值主体,它的感知能力为感性体验赋予一种负面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动物的体验不仅仅具有目的价值,同时也是内在的价值之源,因为这种价值可以源自它们内在地自我评价。它们不仅仅可以被人视作目的本身,它们自己还能把自己视作目的本身。*科斯嘉对于“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和“目的价值/工具价值”两种二分法的区分也许会面临如下质疑:如果一个存在物本身不能为其自身赋予价值的话,那么为何我们要为它赋予目的价值呢?所以,本文在这个环节的论证也许对动物具有非工具性价值的证明也是必要的。
人作为有理性者,他们的理性和感性都能成为价值源泉,但对于没有理性的动物来说,它们的感性能力独自就能成为价值源泉。人区别于动物的唯一高贵之处,就在于人不仅仅拥有偏好自主性,还拥有道德自律性(即人格性禀赋),后者使他不能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对其他拥有相似利益的动物带来伤害。
综上所述,笔者首先讨论了对“人性公式”的客观价值论解读,这种解读思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否认动物禀性可以具有作为目的本身的价值,进而指出这种理性中心主义的客观价值论要么面临缺乏经验性内容的指责,要么在现实中将推出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康德伦理学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求诸主观价值论解读。其次,笔者探讨了以科斯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动物伦理学,这种对康德伦理学的主观价值论解读并不会排除动物的道德地位,动物禀性(不管是人的、还是动物的)可以被赋予一种非工具性价值。最后,笔者认为,因为动物拥有感受能力,所以它们成为价值主体,为其自身赋予内在价值。笔者承认,最后这个结论已经远远偏离了康德本人的立场,但退一步讲,即使动物不能成为价值主体,它们仍然可以作为价值载体而被赋予非工具性价值(即被视作目的本身)。*科斯嘉的主要思路侧重于从“理性者自我立法”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来论证动物可以被视作目的本身,尽管她不否认动物自己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赋予内在价值,但基于有理性者的第一视角论证有一个独到的优势,就是可以解决道德规范性的来源问题。一个动物会痛苦和恐惧,仅仅因为它们的生命具有内在价值,这也许还不足以向自我提出实质的规范性道德要求。科斯嘉认为,一个道德法则之所以对我有规范性,最终只能是因为这个法则是由我制定的,我既是道德法则的制定者,又是服从者,如果我不服从我自己立的法,那么我就是在否认拥有健全道德人格的自我同一性,因此我应当遵守我自己制定的道德法则。
[1] Immanuel Kant. Leaures on Eth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美]汤姆·雷根.动物权利研究[M].李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Allen Wood. Kant on Duties Regarding Nonrational Nature[J].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 1998, 72: 189-210.
[4] Jeff Sebo. A Critique of the Kantian Theory of Indirect Moral Duties to Animals[EB/OL]. http:∥www.animalliberationfront.com/Philosophy/A%20Critique%20of%20the%20Kantian%20Theory.htm.
[5]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六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 Immanuel Kant.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 杨云飞.康德的人性公式探微[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4):405-414.
[8] 王福玲.康德哲学中的“人性公式”与尊严[J].道德与文明,2013(4):64-69.
[9] 刘作.如何理解康德的“人是目的”的观念[J].兰州学刊,2014(5):6-10.
[10]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 翟振明.康德伦理学如何可以接纳对功利的考量[J].哲学研究,2005(5):80-85.
[12] [美]克里斯汀·科尔斯戈德.规范性的来源[M].杨顺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3] Christine M. Korsgaard. Fellow Creatures: Kantian Ethics and Our Duties to Animals[EB/OL]. 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korsgaar/CMK.FellowCreatures.pdf.
[14] Patrick Kain. Duties regarding animals[M]∥ Lara Denis.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 Christine M. Korsgaard. A Kantian Case for Animal Rights[EB/OL]. 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korsgaar/CMK.Animal.Rights.pdf.
[16] Michael Cholbi. A Direct Kantian Duty to Animals[J].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4, 52: 338-358.
(责任编辑:张 燕)
2015-09-25
王 珀,男,山东交通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动物伦理、伦理学理论研究。
B82-0
A
1672-0695(2015)06-003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