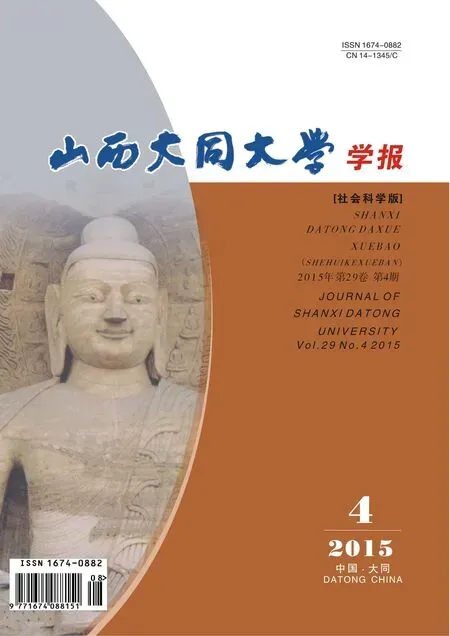史铁生知青文学的独特性
申朝晖,刘凡嘉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在知青文学“血与泪”的控诉、批判与反思中,史铁生陕北题材的知青文学却能横空出世、独树一帜。史铁生知青文学的独特性来自于现实境遇。首先,在轮椅上开始文学创作的史铁生在陕北插队时,还是一个身体健壮、乐观开朗的青年人,这就使得史铁生特别愿意以文学的方式来谈论自己在陕北的生活,“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1](P7)此外,陕北底层民众的忠厚、朴实、善良,以及对身处逆境的知青们的关爱与帮助,也使史铁生的回忆中,充满了温馨浪漫的诗意色彩。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陕北封闭落后的生活、劳作方式使得史铁生等人在“评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发现它对贫瘠的黄土地的文化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表现在北京城带来的城市文明,从牙膏、的确良、半导体,到故宫、中南海——对黄土地的渗透……”[2](P232)这就是说,史铁生的知青文学与建国后中断了的启蒙文学叙事传统衔接起来了。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史铁生的知青文学在同时期是如此地与众不同,如此地吸引读者。
史铁生关于陕北题材的知青文学收录在《回首黄土地》一书中,主要包括《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相逢何必曾相识》、《黄土地情歌》、《几回回梦里回延安》等。这些知青文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荣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关于史铁生知青文学的独特性,本文主要通过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陕北题材知青文学的启蒙色彩
史铁生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回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那便是在陕北插队时度过的岁月。在知青作家中,史铁生的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
史铁生有关陕北题材的文学作品能够区别于其他知青文学的主要特点在于文本中充满了浓重的启蒙意味,这种延续“五四”传统的启蒙思想,不仅针对作品中那些没见过世面的陕北底层民众,而且对整个陕北地区的民众在思想、文化上也有渗透作用。对自己故乡的特殊情感促使人们在阅读量很少的情况下能够格外关注书写自己身边故事的书籍,这些土得掉渣的陕北底层民众通过北京知青的文学作品看到了大山外面的世界,增长了见识,拓展了视野。
史铁生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这部充满着诗意美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促使清平湾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进入了多数人的视野当中。作品生动地描绘了清平湾老百姓劳作的画面,古朴的传统生产方式衬托出了陕北地区的封闭落后,“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3](P137)传统劳作方式下生活着的“受苦人”,听到了北京知青关于大都市的叙述,对外面世界的渴盼心理不言而喻。与知青“我”一起拦牛的破老汉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外来先进文化的濡染,在下雨下雪的休息天里,便会言语:“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做什么嘛!”[3](P145)而且,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史铁生说:“留小儿大了嫁到北京去呀!”[3](P143)这些话都反映了这位在大山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汉对外界的憧憬,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北京知青到来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破老汉的孙女留小儿对北京城更加向往,“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3](P146)在聊天中,留小儿了解了电影院、电视等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北京知青给陕北的老百姓带来了新鲜的事物和新颖的观念,诸如留小儿憧憬的电影院、电视等现代化设备,破老汉期盼的纸烟等。《插队的故事》是史铁生又一部关于陕北题材的力作,知青们拿着半导体、假牙等在陕北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来到知青窑开始插队的生活,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促使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来知青窑串门,在多次的接触中,这些很少外出的老百姓认识到了原来铺盖还可以这么舒服,半导体还能唱得如此红火,人还能靠假牙来咀嚼食物……新的事物、新的概念在老百姓的意识中逐渐渗透。在《相逢何必曾相识》中,史铁生也表达出了乡亲们对北京的向往,这些朴实的老百姓虽然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踏出黄土高原,但望不尽的山川沟壑却阻拦不住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若没有北京知青的到来,这些习惯了封闭生活的老百姓应该不会产生这样的心理,正是这些大都市的年轻人给予了他们思想上最初的“启蒙”。
知青们的启蒙作用还体现在对爱情的认识上。在《黄土地情歌》中,史铁生以和知青的第二代聊天的形式描写了一对知青在插队第二年便结婚生子的故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在农村尚未大有作为的知青谈情说爱,会被认为是革命意志消沉的表现,但爱情的力量促使他们冲破了阻碍,赢得了光明。这种自由的婚姻爱情对向来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陕北人民来说,是一种震撼,更是一种指引。《插队的故事》中随随与碧莲的自由爱情也是在无意识中承继了“五四”婚姻自主的精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敢于冲破封建旧思想,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阅读史铁生作品的陕北读者在这种新思想的引导之下打破了沿袭千年的婚姻律令,冲破束缚青年人情感的牢笼,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所爱。
北京知青所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想成了陕北底层民众认识外界的初步途径,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北京知青给这些在封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老百姓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孤陋寡闻、保守愚昧,而是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姿态迎接他们期盼的“好光景”。
二、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性思辨
有研究者称,“史铁生之于很多人,首先就是一种救心的药,懵懂于黑暗中抓过来一把,不想吃下去后竟然非常的止疼。史铁生笔下的世界是灰色沉黯的,但却是非常温暖的,能够让人内心不知不觉变得坚强强大。”[4](P78)短篇小说《命若琴弦》以陕北盲人说书为切入点,以简单却饱含人生哲理的故事启示人类对命运进行思索。
《命若琴弦》开门见山,点明了主旨:虽困境永存,但追求不息。苍茫的群山中走着老小两个瞎子,老瞎子自出生就在黑暗的世界中生存,他终年背着三弦琴奔走说书,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疲惫孤寂只有自己心里清楚;小瞎子三岁失明,14岁被父亲送到老瞎子那里学说书弹琴,从此他的命运便也奔波在了荒凉的路上。老瞎子已过世的师父给了他一个“承诺”:用心说书弹唱,专注地生活,凭借这样的态度弹断一千根琴弦作为药引,便可按照封进琴槽的药方抓药治病,重见光明。这样的梦想指引着师徒二人坚定地饱受了生活的艰辛苦难而生气依旧,是信仰促使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期待。“老瞎子一天比一天紧张、激动,心里算定:弹断一千根琴弦的日子就在这个夏天了,说不定就在前面的野羊坳……”[5](P4)老瞎子以改变生命的颜色成为他一生的信仰,支撑着他在困难中仍能够乐观向上。小瞎子的信仰是那位拨动了他心弦的兰秀姑娘,只要快到野羊坳,他就会心跳加速,一路哼着情歌小调,“嘴上嘟嘟囔囔的,心却飘飘的,想着野羊坳那个尖声细气的小妮子。”[5](P10)小瞎子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想很认真地爱一次。毋庸置疑,无论老瞎子还是小瞎子,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心中有着难以摧毁的人生目标,生命的航船就在这一过程中奋勇前行。史铁生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才能使我们成为人?什么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扩展?惟有欲望和梦想!欲望和梦想把我们领进一片自由的无限可能之域。”[6](P344)然而,并非所有指引生活的目标都能够达到,因为“它必将走向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7](P25)命运之手将老小瞎子从人生的高潮打入了低谷:老瞎子用50年的光阴盼来的药方却是一张白纸;兰秀被迫远嫁山外后小瞎子痛不欲生。老瞎子在现实中迷茫,在台阶上苦坐几天,“骨头一样的眼珠询问苍天,脸色也变成骨头一样的苍白。”[5](P33)但他终于想通了老师父说过的话,“咱的命就在这几根琴弦上。”[5](P35)琴弦对于老小瞎子来说,不仅承载着复明的梦想,更负载着生活下去的动力,只有将心中的弦绷紧,才能奏响人生的华美乐章。史铁生认为,“皈依是一种心情,一种行走的姿态。”[8](P54)最后,老瞎子虽然没有实现复明的愿望,但是他的人生却充盈有力。他明白了,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距离,而这距离就是生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瞎子以追求光明为目标,对目标的向往使老瞎子练就了“人人称赞”的琴技和口技,更获得了作为手艺人不同于叫花子的人格尊严,以及被人需要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文章末尾,老瞎子带着小瞎子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间小道上,继续以往那种坚韧乐观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是他们超越自身命运过程中渐行渐远的食粮!
生命中最好的景致,并不是浓墨重彩描绘而成的,而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希望叠加起来的。注重日常生活过程,正是史铁生提倡的超越困境之路。《命若琴弦》以文学的方式明确了这种生存主张,史铁生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性探索与思辨,促使更多的人在与困境周旋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三、带有乡土色彩的诗意写作
对于知青们而言,美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插队点便成为他们心中怀揣着特殊情感的“第二故乡”。对于史铁生这位“职业是生病,业余才是写作”的作家来说,插队时健康的体魄,陕北人民真诚的关怀,成为他日后更愿意回忆的部分,并且以充满温暖诗意的基调写下了有别于其他知青作家哀怨控诉的作品。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样一部看似“散漫”的小说能够在知青文学叙事中脱颖而出,基于文学史达成的“共识”:“史铁生这篇写知青的小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的笔触在委婉清俊中写出了知青与当地村民相濡以沫的情谊。知青生活不再是迷惘与愤慨,而是有那么多值得记忆和眷恋的细节。”[9](P298)文学史家们强调这篇小说与之前小说的差异在于:“已明显离开社会政治视角,而着重发现民间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人性品格,以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10](P269)前期知青小说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目的是“追赶现代化”,情感基调是“迷惘和愤慨”。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与此相反,是“理性与达观”的,是质朴的“诗意乡村”。“《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感觉像是一首悠扬的牧歌,背景是那种秋山的颜色:红的小灌木叶子,黄的杜梨树叶子,蓝蒙蒙的野山花,有牧笛从那秋色中透出来……”[11](P35-36)史铁生以“追忆”的手法拉开了与对象之间的时空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感营造了一种和谐浑融的气氛、情调,产生了美感。王蒙认为这篇小说的力量在于其风格,他说:“‘清平湾’触动的是你灵魂里那个最温柔的部分。像是一阵来自黄土高原的清风,吹动了你心中的涟漪。”[12](P44)《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从某种意义上讲,象征着史铁生受伤的躯体与灵魂在一片充满人情味的土地上找到了栖息之所。文学不仅为作者本人,更为人类提供了一片想象的净土,一块宁静的空间,如此浪漫和谐的家园让读者不忍去打破,只愿诗意地享受其中的美感。
《插队的故事》中同样散发着浓郁的乡土诗意之美,让人心旷神怡。“那条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们的村子叫清平湾。”[1](P10)史铁生笔下的陕北农村由安宁静谧所包围,乡民在劳作之余能够享受到城市没有的惬意,一种理想的、诗意的乡村世界便被勾勒得淋漓尽致。
四、运用口语化的语言形式
在史铁生陕北题材的小说中,方言、民歌等俯拾即是,这些接地气的语言形式,不但没有造成文章土气,反而使作品的艺术形式更为和谐。这便成为了史铁生陕北题材作品的又一独特性,也带给其他知青作家以语言应用上的启示作用。
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文中,作者称和他一起拦牛的白老汉为破老汉。在陕北方言中,“白”发“破”的音,称呼破老汉更显亲近,陕北百姓叫孩子为“心儿家”,体现出了他们的真诚友爱。史铁生在人物对话的描写中保留了“哩”等语气词,真实地描绘出了陕北人的语言特点。如留小儿后来到了北京与作者的对话,“清平河水还流吗?”“流哩嘛!”“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 在哩!老下了。”[3](P157)这些貌似平淡无奇的对话如实地表现出了陕北人的憨厚淳朴的气质。在《插队的故事》中,“还认得出我吗?”“咳呀,不是随随说你要来,就不敢认。腿一满不得动?”“随随收到我的信了?”“欧嘛。都说你是虚说哩,腿不得动咋能来成?倒真格来了。走!庄里回!”“那是谁?”“我婆姨。我来县上开会,这人就要跟得来。”[1](P146)作品中出现的这些口语化的表达生动地体现了陕北民众的质朴与憨厚,他们对知青们的关怀也在这朴实无华的表达中流露出来。另外,在陕北题材的作品中,史铁生插入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等艺术形式,也为作品增添了不少亮点。忧愁、爱恋、憧憬与希冀在老百姓那里都能改编为顺口的民歌。例如:“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三年两年忘不了你。有朝一日见了面,知心的话儿要拉遍。”史铁生认为陕北民歌唱出了陕北普通人的心声,它从没有哗众取宠之意,而只是将数不完的日子和心事以唱的方式诉说出来。
在知青作品中,鲜有像史铁生这样恰到好处地运用当地艺术形式的范例,这对其他知青作家不无启迪。
在普遍承载伤痛与苦难的知青文学中,史铁生凭借着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独树一帜。史铁生陕北题材的文学创作为知青文学作品开拓了一个新的叙述视角,为知青文学的艺术长廊描绘出了崭新的一笔。
[1]史铁生.插队的故事[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
[2]史铁生.回首黄土地[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2.
[3]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4]徐庆生.2011年之后,谁还记得史铁生[J].中国新闻周刊,2011(01):76-78.
[5]史铁生.命若琴弦[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6.
[6]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卷3)[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5.
[7]史铁生.灵魂的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8]史铁生.灵魂的事[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