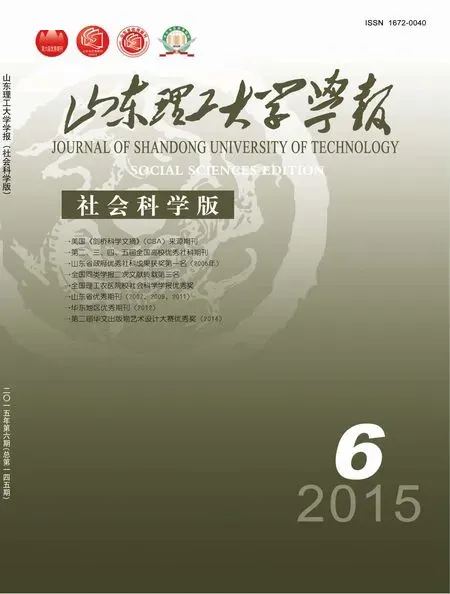治理主义法治观及其启示
刘建文,贾晓燕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治理主义法治观及其启示
刘建文,贾晓燕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全面把握中国国情与现状,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关键在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用法律统理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治理主义法治观对中国法治实践的意义重大,是重建社会政治信任的法治基础,为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同时也实现了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在现代制度框架中的结合。
法治;国家治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治理主义法治观
中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走资本操控的道路。2012年我国提出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折射出中国依法治国的递进过程。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多年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的党内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阐释了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一、工具理性主义法律观与价值理性主义法律观
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以手段与目的的分离为前提,将政治行为转化为更加趋于中立的技术性问题,近现代制度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意图通过诉诸人性趋利避害的计算,使人们服从于法的强制性,因此对人性的巧妙利用成为法律有效性的前提,法律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制度成为有利于达到最大的善和防止最大的恶的最佳社会控制手段。马克斯·韦伯谨慎地对待社会科学研究所信奉的价值中立态度,从而对法律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了深刻的阐释,并对法律的“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出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进行了古典风格的理解。韦伯认为法律的工具合理性重目的而不重手段,甚至为了正确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法律的价值理性更看重手段行为本身的价值,认为目的不在手段之外,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是当下的、即可的。技术理性在改造世界和社会管理上的有效性使得法律的工具理性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现代法律体系的高效合理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纯粹理性形式。[1]266而美国学者昂格尔则秉承了韦伯对法律实质公正即价值理性的关注,认为法治的标志在于法律的形式价值和实质价值的统一。[2]
(一)工具理性主义法律观阐释
工具理性主义法律观是一种“关于法律本质和法律功能的法学世界观和法学认识论。它强调在社会系统中,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3]沿袭的是手段—目的逻辑,重视的是法律工具主义价值,其衡量标准是法律是否完成预定的目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方式中,法律作为一种规则是以服务于君主权力需要为目的,以漠视权利为代价,这构成中国专制统治的基础。在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工具理性主义法律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依法治国起到了推进作用。
在当代中国,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法治观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引领中国社会前进”;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决定,工具理性法律观体现为法律是为大局服务的工具。[4]由此可见,法律工具主义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维护了社会秩序,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法律知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工具理性主义法律观是一种强调目的的法治观,在法律实践中奉行法律国家主义,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刀把子”,这种观念造成了法律价值的虚无。一方面,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需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保障人民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实现;另一方面,法律既然只是作为实现统治目的的工具,那么法律就存在被其他方式替代的可能性,而且目的是人的主观欲求,因此工具理性主义法律观里暗藏着“人治”的可能性,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二)价值理性主义法律观阐释
价值理性主义法律观强调手段与目的关系的内在性,认为工具理性应与价值理性重合于同一空间中,法律最终的社会功能应该是追求人自身的发展,体现法治实践中的伦理价值、理想价值、情感价值等,这也应是法治当然的出发点与归宿。“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5]法律的终极意义在于其实践理性,法律及法治文化的价值事关人的本质的提升,它虽然诉诸既定的人性来实现法的有效性,但是仍然需要保持其对灵魂的关注,并通过法律对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需求的引导,使社会主体认同、选择和信仰法及法治。[2]法律价值主义认为应该用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保持其以人自身作为目的的神圣性,把法治实践本身放置在善恶对错的空间中,以人类本质的提升作为实践的根本目的,培育公民的法律精神,使法治的实现成为可能。价值理性主义法律观弥补了工具理性法律观的缺陷,但是过于推崇道德伦理的作用,把法律当作了可用可不用的工具。
我国的法律制度及法律运转机制在社会转型期实现了法律价值体系的重建,摒弃了传统法律价值的沉渣与糟粕,吸取现代性国家在法治治理方面的成败得失,寻求全球法律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从而勾画出了中国法律价值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心灵版图,新的法治价值体系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历史使命和目标指向。[6]57
二、治理主义法治观内涵诠释
国家治理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艰难的一门学问,尤其是大国治理,更是难上加难。评判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标准,必须把国家治理体系置于该国人民实实在在的感受和客观现实的发展质量中来审视。
(一)治理主义法治观既强调制度约束,又关注社会和公民参与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要依靠宪法、党内法规,又要依靠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和团体章程等。这些都构成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法治资源。宪法是建设法治国家最为重要的法律保障。但是,法治国家所依赖的法律性资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例如,在社区治理中,很多纸面上的法律解决不了社区的问题。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其实就能够很好地协调和维系基层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它们在社区中的作用可能比专门化的法律更为有效,治理成本也更低。尽管市民公约不是专门化的法律,但它具备法律的某些特性,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性。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区治理”的概念。社区治理有其特殊原理,社区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石。这也说明,我们对法律的理解不是教条的,我们强调法律的专业性,但不迷信专业化的法律,而是将法治国家确立在广义之法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类型的法律和规则化解不同领域的冲突和矛盾,是治理主义法治观的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其独特的基本要义和独特的治理形态,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理性主义的法治模式,而应该在更加冷静、更加务实的道路上,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同时治理主义的法治观也不同于工具理性主义法律观,它在对制度硬约束吸收的同时也呼唤公民个体参政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呈现出一片活力。治理主义法治观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目标,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力量,治理主义法治观既不同于工具理性主义法律观的手段—目的逻辑,也不同于价值主义法律观的普遍主义逻辑,它强调的是根据本国具体国情灵活地运用法治思维,以元逻辑的模式调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二)治理主义法治观追求法治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高度契合
任何一个国家对其治理体系的选择都是与该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单纯从外部植入的治理体系大都是不成功的。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尤其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的治理体系,绝不是外来模式的翻版。国家的历史起源、文化宗教、经济社会现状都是文化基因的重要构成要素。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中国的文化基因孕育出来的,世代传承的民族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知常达变、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与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6]57
治理主义的法治观是一种建设性的更加务实的法治观。治理主义法治观的实质是以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性为评价标准,“政体如何,愚人多虑;其实好坏,全在治理。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是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7]348这种治理能力的有效性是在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综合协调基础上实现的社会利益最大化。
三、治理主义法治观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启示
(一)治理主义法治观是重建社会政治信任的法治基础
中国社会政治信任的重建取决于把社会冲突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上来予以化解。权力合法性统治的稳固性不能只建立在政治交易和利益偏好满足的基础上,也不能仅仅凭借对军事、暴力资源的垄断,这些还不足以显示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还要依赖法治这种有效的社会管理工具。国家治理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多重力量和逻辑合成作用的结果。我国基本国情和治理情境的变化,必然对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促使我党必须重新审视法律和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这一重大问题。在继续追求法治建设的同时,力求实现德治和法治在现实治理情景中的结合,逐步确立法治国家,国家治理应跳出中国伦理社会和现代法治社会的两极对立格局,使中国实现从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8]
改革开放的成就使得中国已经存在一个产权性的社会制度安排,社会对法治的要求自然驱使着国家治理手段的重新洗牌,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重建中国政治信任的法治保障,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在实践中的体现,因此要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这是治理主义法治观的重要内容。
(二)治理主义法治观为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治理主义法治观为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既不走西方式的道路,也不走暴力专政道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这条道路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而提出的,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超越西方和传统的一条法治道路。法治治理所提供的社会信任可以为诸多社会冲突提供权威性的化解选择,创造使社会抗争和集体行动迈向法治化道路的契机;而且它可以超越社会阶层的地位差异而缔造一个公平正义的衡量标准,使法律信仰成为支撑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最稳固的基石。
法律普遍性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调法律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防止权力腐败;第二,保护个人权利,防止巧取豪夺;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在法律面前对社会个体进行个人的抽象理解以保证普遍性高于特殊性。[9]所以,在法治治理确立的国家形态中,人们对政党、政客和政府可以抱失望的态度,但是对法律的社会调控功能却充满信心。法律约束相对于道德约束的有效性,使得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能够得到合法化的解决。政治对社会利益的制度安排必须依赖法律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才能杜绝利益集团对权力的政治投机,为多元社会力量的公平博弈提供良性的法治环境。[8]
治理主义法治观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人治与法治、伦理与权利、道德与法律等概念标准的超越性理解。如果所谓的“民主权利”“契约制度”“法律理性”等这些纯粹的西方价值原则不能带来有效的治理,不能带来高水平的治理,这样的概念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中国的决策者果断地提出了符合现代国家治理和适合中国历史传统与国情的治理主义的法治观。
(三)治理主义法治观实现了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的结合
治理主义法治观实现了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在现代制度框架中的结合。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因为对政绩的偏爱,魅力型权威的色彩终究难以祛除,为理性官僚制提供了灵活的动力;科层制虽然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统治,但是国家管理制度不同于企业科层制,而且政治对行政的掌控,以及政治对个人自由的拯救意义,使得政治行动必然要突破科层制“技术必然性”的统治。因此任何国家都要发挥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力量,既要追求政绩,又要把人治纳入到法治化的结构中来,这是所有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向法治型政治信任转变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政治是魅力型行动与理性行为的完美结合,绝对的技术型法理统治实际上是法律偏执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表现;同样,将政治视为纯粹魅力型权威的释放和个人意志的挥斥,乃是对政治秩序和法制规则的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将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进行辩证理解,并且使这种关系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实践中的统一,是我国进行大国治理中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8]
自政治与行政实现两分以后,政务官员与事务官员各自承当了不同的职责,政务官员个人的决策以及对政绩后果的承担,使得在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中人的因素依然处于重要的地位,中国政府的绩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府官员敢于承担责任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在政治实践中的辩证结合必须纳入到法治化的框架中运行,才能达到既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蔓延又可以产生出高管理绩效和高发展绩效的目的。当然,最终目的在于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法治型社会。
[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二卷)[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于群.依法治国与法律价值体系的重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3]谢晖.法律工具主义评析[J].中国法学,1994,(5).
[4]肖金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法治观及其实践形式[J].法学论坛,2011,(4).
[5]李金杨,本丽萍.比较研究法律工具主义、法律价值主义展望中国的法治发展[J].法制与社会,2013,(3).
[6]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在汉,舒逊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刘建军.论社会转型期政治信任的法治基础[J].文史哲,2010,(4).
[9][美]艾伦·S·科恩,苏珊·O·怀特.法制社会化对民主化的效应[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2).
D92
A
1672-0040(2015)06-0036-04
2015-06-19
刘建文,女,山东潍坊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贾晓燕,女,山西临汾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
(责任编辑 李逢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