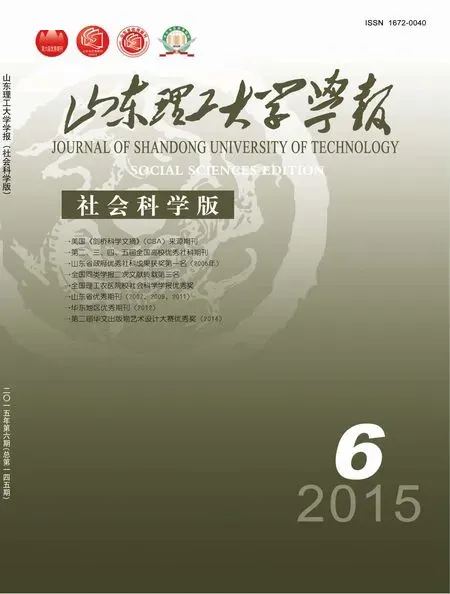韩非人性论的内在理路
李玉诚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韩非人性论的内在理路
李玉诚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韩非不是性恶论者,他本着“不破不立”的原则,在群己关系中以“计算之心”、功利之说,对人性、人伦关系进行了极端露骨的批判。转而以“道理论”作为哲学基础,以“圣人”与“众人”的对待关系作为依托,循着“即心言性”的理路,借助“心”之“虚静”而阐发了一种符合“道”与“理”的本然人性,并通过“虚静心”统摄“智”与“性”,规避了“改造”人性问题。
人性;道理;即心言性
①参见李玉诚.《〈韩非子〉历史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56-57。
学界关于韩非人性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围绕着“性恶论”及其衍生命题加以探讨,大致形成了性恶论、人性自为或自利论、自然主义人性论、人情论等几种观点。学者的研究聚焦于“计算之心”,而未对韩非人性论中“心”与“性”的区别,“心”、“性”与“道”、“理”的关系作深入阐发。而我们拟对“计算之心”重新评析,从韩非的“道理论”入手,循着“即心言性”的理路,对韩非人性论的深层含义加以阐明。
一、在群己关系中以“计算之心”揭批人性
今本《韩非子》中没有人性论的专篇,但是通本《韩非子》对人性的考察可谓深切入骨。韩非并非孤特地探究人性,他在揭批人性时,始终将性、情、欲等范畴混合使用,并且始终在群己关系中考察人性。
韩非从未反对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的合理性,民以食为天,衣食为生民之本,必须外求才能获得,因此人之“欲利之心”实属正常。他反对的是人在“利”的诱导下,放纵欲望、任用“私智”,无限度追求欲望的满足。他曾明确指出:“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劝诫世人“去甚去泰,身乃无害。”(《韩非子·扬权》,下称《杨权》)。但是,现实情形恰恰逆向而行,欲望横流,世人“不知足者之忧终身不解”(《韩非子·解老》,以下称《解老》),因此,他预设了“圣人”与“众人”的对待关系,强调“圣人”能够量腹而食、节制欲望,面对外部环境的诱惑,有自己的取舍标准,自持之道,自始至终不为外物所诱惑,处于超然地位。而“众人”则不管是权贵富豪,还是布衣平民,都囿于自身欲望,贪得无厌,受制于“欲利之心”,工于计算,趋利若骛,自私、自利无所不为,君臣、父子、夫妇等一系列人伦关系因之相继动摇。“众人”在现实中对“利”的追求没有限度,韩非通过对这些“过度”行为的考察,追本溯源将其归结于“计算之心”。因此,“计算之心”实质上是韩非通过对“众人”现实行为的经验省察而反向“归纳”出来的结论。那么,韩非提出“计算之心”的真实用意何在?
韩非对现实中人性、人伦关系的考察,文笔犀利,多有极端说法。学者指出,“他能够以极普通的常识为依据,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1]350但是,平心而论,从事实层面来看,春秋战国之世本就是人性的炼狱,君臣相杀、父子成仇、夫妻反目、手足相残、朋友相欺之事历历在目,韩非所指陈的种种极端情况并无多少新意。从思想层面而言,人好利恶害,“普通人”见利忘义、趋利无度、放纵欲望等认识,在当时诸子那里几乎是“共识”,韩非的观点并非“卓见”。那他为何还要不厌其烦地一一罗列?有学者指出,“韩非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坚持不破不立的原则”。[2]211详而言之,韩非以儒墨为“显学”,不遗余力地加以批判,而儒墨之说恰是将天、人性、人伦关系、人伦道德与德治扭结为一。因此,“韩非对父子夫妻之情的否定。此否定只是否定其间相亲之必然性,换言之,只要有一例为证,则其间之必然性即告溃灭,而吾人之政治哲学其必然之道即不可建立于此之上”。[3]439易而言之,韩非恰是在以“计算之心”这一特例批驳他人对于人性、人伦关系、人伦道德的种种“普遍性论断”,顺此也就否定了由其衍生的一切命题的“普遍必然性”。所以,他提出“计算之心”的真实用意,既是论辩之需,也是提出自己的人性论的必要准备。那么,在韩非看来人性到底是什么样子?
二、“道理论”的本体建构
韩非在道、物二分世界观的框架内,发挥了老子之“道”,提出了“理”作为中介,借以诠释道与物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的“道理论”,作为其学说的哲学基础。那么,在“道理论”的框架内,“道”、“理”与人性有什么关联?
从“道”的角度看,韩非认为“道”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原因。但是,“道不同于万物”(《扬权》),“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扬权》)这是韩非承继先秦道论的大框架,强调“道”之“生而不有”、“不干预”的品性。而从万事万物的角度来看,韩非又指出:“至于群生,斟酌用之。”(《扬权》)并且,万物又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道”,在生死成败的变化过程中遵循着“道”。至此,韩非的“道理论”依然未超出先秦道论的大框架,“道”与“物”的关系依然存在断层。那么韩非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在韩非看来,“道”是“万理之所稽”(《解老》),“《广雅·释诂二》:‘稽,合也。’《广雅·释诂三》:‘稽,当也。’即‘相合’、‘相当’的意思。”[4]108即各种各样的“理”尽与“道”相符合、相称当。“道”与“理”的关系,也是“一与多”、“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韩非又进一步指出:理者,成物之文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解老》)。
后一“理”字在“这里用作使动词,是‘使……有事理’的意思”。[4]351若此,“道”便撇清了与具体之“物”的直接关系,而是借助“理”这一中介来规制万物。而从万事万物的角度来看,“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解老》)。“制,裁也。”(《说文》)因为有“理”作为限定,具体的物与物之间有了分别,所以物与物才“不可以相薄”。在这个层次上,“理”成为万物自身外在的直接限定。但是万物要成为其“自己”,除相互间要有分别之外,还要有自身内在的规定性。
韩非认为:“理定而后可得道也。”(《解老》)因此,万物要获得“道”、符合“道”,就必须以“理”作为“中介”。同时,他又认为,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短长、小大、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解老》)。
易而言之,“理”包含着各种具体规定性,一旦寓于万物之中就成为万物自身的“定理”,同时也将这些具体的属性赋予万物。所以,相互分别的万物就具备了自身的“定理”,与“道”相通,并且内在地具备了各种具体属性。因此,万物都是通过“理”而分有“道”,从而获得自身的“定理”,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一言以蔽之,万物的现实存在状态都是“自然”或“自为”。所以,韩非不厌其烦、连篇累牍陈说的人之“自为”,就不能单一地理解成自私、自利、自我计算。“自为”是人自身的“定理”使然,是人最为本己的现实存在形态。既然如此,“众人”之“自为”为何会一味导向自私自利、趋利无度一端?
三、心性有别,即心言性
韩非以“计算之心”揭批人性,着眼点在“心”,理路是“即心言性”。“心”统摄着“性”,统理着人的行为。他在自己的学说中预设了“圣人”与“众人”的二元对立、不对等关系,“圣人”有独见之明,恰恰是源自心之“虚静”与服从“道理”。那么,在“道理论”的框架内,“心”、“虚”、“道”、“理”是什么关系?心与性又是什么关系?
荀子曾明确指出:“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荀子·解蔽》)庄派学者亦称:“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道、心、虚三者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先秦道论中当是共识。韩非精通道家学说,师从荀卿,对此当不陌生,亦强调“虚心以为道舍”(《扬权》)。同时又指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解老》),恰恰是指“心”无所固执,这样“虚”本身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但是,先秦时期“虚”与“道”的关系又十分密切。“虚无无形谓之道”(《管子·心术上》),从句式来看,“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5]22所以,“道”是“名”,“虚无无形”则是“实”,两者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一者其号也,虚者其舍也”(《十六经·道原》)。“一”在先秦时期通常为“道”之别名,“舍”为“舍止”或“留处”之义,那么,“虚”即是“道”的现实承载者。总之,“虚”与“道”的关系密不可分,韩非亦认为:“虚静无为,道之情也”(《扬权》)。若此说来,“虚”、“虚静无为”本身又是“道”之情实,“虚”这一范畴又关涉着本体论。
不过,韩非又认为:“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解老》)按此说法,“道”之情实又无不与具体的“理”相对应、相契合。至此,韩非承继先秦道论的大框架,在“虚”与“道”之间加入了“理”。因此,“虚”与“理”统合于“道”而相互贯通。而“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管子·心术上》,以下称《心术上》),这或许是稷下学者或整个先秦道论的共识。因此,从本体的角度看,“虚”是“道”的情实,圣人也是由“道”所生且具备自身的“定理”,所以圣人本然与“虚”相通;而圣人只要做到了“虚”,就必然在认识层面符合“道”。本体论与认识论在形而上的层次本然为一。那么,圣人如何在现实实践中做到“虚”,实现“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渡?韩非认为圣人在接应外部环境时能“啬”。“啬”本是老子使用的范畴,而韩非认为,啬之谓术也生于道理。夫能啬,是从于道而服于理者(《解老》)。所以,“啬”本身不仅仅是圣人遵循“道理”的能动行为和方法路径,同时也是由“道理”自身生发出来的路径。因此,“啬”与“虚”一样,也是兼合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综合范畴。只不过“啬”受制于“道理”,其本体涵义较之“虚”似乎低一位格。按照韩非所经见的老子的说法,“夫谓啬,是以蚤服”(《解老》),而韩非则认为,“虚无,服从于道理,以称蚤服”(《解老》)。“称”:似是指“相称,相合。谓圣人虚静无为,而服从于道理,以合于早服之旨”。[6]395因此,“虚”与“啬”内在相通,在韩非这里通过“虚”亦可以“蚤服”。“蚤服”在老子那里似是早作准备,服从于“道”,而韩非认为“虚无,服从于道理”也称合“蚤服”之旨,因此也能符合“道”。所以,韩非所选取的体道路径是“虚”、“道理”。同时,如上所言,“啬”本是由“道理”所生发出来的体道路径。因此,在韩非看来圣人体道的路径,其实只有“虚无,服从于道理”这一条。
至此,圣人借助“理”与“虚”实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合一,即在本体层面,“道”为宇内万事万物所设定的本然状态,与圣人在认识层面上体悟道、在实践层面“按照道的要求处事”被纽结为一。因此,韩非以圣人作为转关,以“理”与“虚”作为中介,将按照“道”展开认识实践活动转化成了服从“道理”。那么在现实实践中,“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解老》),难以把捉的“道”就转为具体的“理”,进而转成现实中人们认识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铁律。这就完成了“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渡。而韩非所说的人之“自为”是“道”赋予人的“定理”,是人“自然而然”或“自己如此”的存在形态。但是,“众人”囿于“计算之心”是否已经背离了这一本性?而韩非主张“因道全法”“因情而治”“以法治众”“以法教心”,是否是在改变“众人”之性?
四、以“虚静心”规避“智”,统摄“性”
韩非明确指出:“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显学》)由此看来,智识属于“性”,“性”并非后天可以改变。而有学者指出“计算之心”是一种“智性心”,[7]136由此看来,“计算之心”主导下的“众人”的行为取舍不可改变。那么,韩非法治如何能够弥乱息争,实现天下治平?
先秦时期“心”与“脑”不分,“心”兼有理性思考与感受性功能。“智”通常被作为本性的属性,但对于智的使用、管理则是属于心之官能,即“心也者,智之舍也”(《心术》)。人的现实行为偏离本性或者违背心之意愿,通常是由于外部环境对其他官能的影响,反过来遮蔽了心之官能的发挥。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心术上》)。而心具备某种自主能动性,趋向于“虚”、“静”、“安”。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
(《内业》)。
韩非深受稷下思想影响,尤其是《主道》《扬权》《解老》《大体》等篇,与《管子》“四篇”中论道、论心的理路十分相近。对于“智性”问题,韩非有一个先在的处置,他曾明确指出: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啬”(《解老》)。
在韩非的学说中,“天”不具备本体涵义,“智”是由“天”所赋予,是人性的特质,而“心”通过“啬”来统摄“智”,“啬”本身兼合本体论与认识论两方面依据。因此,对于“智”的规避,在“道”与“理”那里具备本然的合理性。“智”本身不具备本体依据,取消了“智”的本体依据,也就取消了“计算之心”的本体依据,进而也就取消了“计算之心”主导下的“众人”之现实行为的本体依据。而按照“道”与“理”的要求恰当地使用“智”,是“虚静心”的权能,并且人本然就具备“虚静心”,所以,是“众人”对“智”使用不当,囿于“计算之心”陷溺其“心”。因此,韩非“以法教心”并不是在改变人性,而是通过“道理论”的本体论建构,取消“智”的本体依据,进而在本体层面规避了“改变”人性问题。
转到现实层面,对于众人之智,韩非认为古今情况有别,在不同时代条件下,民智一直在变化。但是,先秦道论中对于智、智识等的处置,始终将其放在“道”之对立面。韩非亦寻此理路,他反对“前识”,认为:“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国危亡。”(《扬权》)屡屡批评“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的行为,特别强调在实践中要“不以智累心”。而现实中“众人”驰骋私智,为所欲为,虽然人人都想“富贵全寿”,但是“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因此,心之所欲与现实背道而驰,韩非认为: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谓迷,迷则不能至于其所欲至矣。今众人之不能至于其所欲至,故曰:“迷”。众人之所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解老》)。
所以,众人之“智”反倒成了背离“道”的“迷”。不过众人无论是“智”还是“愚”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在韩非看来,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显学》)。
韩非笃信法治,认为只要“因世为备”、“法与时转”就能带来天下治平,针对于民智问题,“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心度》),因此,“民愚”与“愚民”的主张在韩非这里依然适用,只是“智”本是可以在其法治框架之内解决的问题。
五、结语
韩非人性学说的关键之处在于“道理论”的本体建构,因此,他的人性论实则具备形而上的一面,因此不能在一般意义上称说韩非的人性论是“经验的人性论”,[8]43说“他完全不讲形而上”。[9]147但是,在韩非的人性学说中,“众人”始终被置于“圣人”的对立面,“众人”“亘古以来就处于“迷”的状态,其现实行为表现只是“不服从道理”、“迷”、“拔”。那么,“众人”这种形而下的“必然背离道理”与形而上的“本然符合道理”的错位又是如何产生的?韩非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颇为薄弱,仅仅提出了一种类似“环境论”的方案。[10]96并且,韩非整个人性学说的建构,始终依托着“圣人”,但他却在未来的法治社会中取消了“圣人”。他认为“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圣人极”(《用人》)。其中的“极”字,“松臯圆曰:山曰‘极,读曰殛’”,陈奇猷认为“极读为殛是也。殛,诛灭也。上文云‘释法制而妄怒’,此云
‘有赏罚而无喜怒’,则行赏罚皆循法制,既循法制而行赏罚,则无所用于圣人矣。既无所用于圣人,则圣人可以诛灭也。”[6]550而韩非自信“至治之法术已明”(《奸劫弑臣》),因此在法治的未来社会中已无需“圣人”,如此就只剩下了“道理”、“法”与“众人”。但是,孟子曾言:“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法家前辈也注意到:“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商君书·画策》),而在韩非看来,他主张“因道全法”,在“道理论”的框架内,“韩非的‘理论’因老子而形而上学化,都能变体为‘理’的‘道’,事实上已被‘法’所取代”。[11]339法变成了自足自洽、自促自动、普遍性、唯一性、至上性的人类社会准则。[12]124但是,他在“道”之外保留了“命”、“数”等观念,认同“规摩之说”,主张“中主政治”。那么,未来的历史依然是“治乱交替”的状态,只不过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难势》)。如果乱世再现,没有“圣人”他又当如何处置?这或许是韩非自身不能圆融之处,亦或是因为韩非所论之“道”的超越性相对贫乏,[13]28与权术的关联过于紧密,[14]282具有明显的“形而下化”趋势。[15]32而其认识论与本体论本然为一,形而上与形而下相互贯通的模式,无疑又强化了“道”、“理”的经验特征。[16]203这无疑弱化了“道”作为本体的唯一性、至上性,使其人性学说的有效性禁锢在“道理论”的框架之内。
[1]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高柏园.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根基[A].中国文化论文集(七)[C].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86.
[4]张觉.韩非子校疏析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商原,李刚.道、法人性论之维的现代审视[J].哲学研究,2006,(5).
[9]王邦雄.从儒法之争看韩非哲学的现代意义[A].中国文化论文集(五)[C].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84.
[10]知水.韩非人性思想论纲[J].齐鲁学刊,1997,(2).
[11]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2][美]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M].滕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3]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4]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5][日]池田知久.论老庄的“自然”——兼论中国哲学“自然”思想的发生与展开[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16]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On the Internal Logics of Human Nature Theory of Han Feizi
Li Yuc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464000,China)
Han Feizi,regarded as an advocate of the idea that human being were born wicked,exposed people’s utilitarianism and inclination of plotting in handling public and private relationship,and explicitly criticized human nature and ethics,abiding by the principle that construction comes after destruction.With“Dao Li Theory”a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sage”and“mass”as the foundation,he then exposited natural human nature that meets“Dao”and“Li”,making use of“emptiness”of“heart”,by following the logic of constructing human nature theory based on the heart.Through the calmness and emptiness of the heart,he avoided the problem of changing human nature.
human nature;Dao Li theory;constructing human nature theory based on heart
B226.5
A
1672-0040(2015)06-0024-05
2015-08-21
李玉诚,男,山东即墨人,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鲁守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