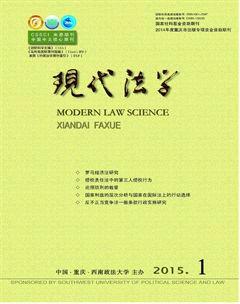论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碎片化结构与性质
郑蕴 徐崇利
摘要: 国际法的碎片化是一种中性的体系结构,是国际法体系以及其内部子体系发展中的客观样态。其中,国际投资法体系正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结构,它是国际投资法扩张发展的客观结果,根源在于其混合的性质。不仅如此,碎片化虽然给国际投资法体系带来了结构性困难,但对促进此体系的发展以及更宏观的国际经济秩序协调具有独特优势。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投资法;碎片化
中图分类号:DF96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1.15
国际投资法体系是由国际投资保护条约交错重叠构成的复杂网络。截至2013年,这个复杂网络中存在3196个投资条约(包括2857个双边投资协议以及339个其他投资条约)[1],使得国际投资法体系产生包括适用范围空缺或重叠、投资保护标准不一致、条约解释模糊不清、仲裁裁决不可预见等困难。由于投资政策与贸易、金融、环境、人权、企业责任等领域的政策关联紧密,解决投资问题需要对各领域的政策与规则进行综合考量。 国际投资法体系从形式到内容都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碎片化现象的典型缩影。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国际法碎片化现象的基本性状,探讨国际投资法体系碎片化的性质。
一、国际法碎片化结构的基本性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体系内出现大量针对专门问题且内部联系紧密的国际法规则子体系。自1999年到2001年,时任国际法院院长Stephen M. Schwebel与Gilbert Guillaume连续三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关注国际裁判机构扩散的问题。他们注意到多元、独立的裁判机构出现,并担忧管辖权重叠、挑选法庭、裁决冲突、国际法效力减弱等问题的产生。Stephen M. Schwebel法官曾于1999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认为新出现的国际裁判机构可能彼此冲突,虽然这一担忧还未成真。随后,在2000年与2001年,Gilbert Guillaume连续两年对此问题进行系统且直接的论述,尽管其担忧更多在于国际法院可能丧失对国际法体系的整体控制功能。(参见:Martti Koskenniemi, Pivi Leino.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Postmodern Anxieties[J].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2, (15): 553-555.) 自此,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即国际法碎片化现象,开始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讨论。
有学者注意到各子体系之间相互冲突,尤其是不同子体系内的执行机构会就相同问题作出不同裁决[2];认为子体系的扩散是对国际法整体的侵蚀,将削弱国际法体系的稳定、统一与效力。有学者认为国际裁判机构的扩散会产生负面影响。(参见:Thomas Buergenthal. Prolif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s It Good or Bad?[J].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14): 267 - 272.)有学者认为当这些裁判机构就同一个国际法规则作出不同解释时,国际法体系的正当性将岌岌可危。(参见:Jonathan I. Charney. Is International Law Threatened by Multipl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J] Recuil des Cours: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8, (271) : 105 - 125.)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国际法体系多元化的必然表现例如:Martti Koskenniemi, Pivi Leino.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Postmodern Anxieties[J].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2, (15): 553-579; William W. Burke-White. International Legal Pluralism[J].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25): 963-980.,其内部子体系的冲突可以通过技术性手段解决[3]。为了厘清国际法“碎片化”现象的本质,国际法委员会于2002年开始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起初,委员会将议题定为“国际法碎片化带来的风险”(Risks Ensuing from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两年后,委员会认为这一提法过于消极,将议题改为“国际法碎片化:国际法多元化与扩张产生的困难”(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由此,委员会综合许多学者的意见,以中性的态度看待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4]。有关国际法委员会对此问题的具体研究主题与研究过程介绍,参见: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R]. Gevena: ILC, 2006: 400.
所谓国际法碎片化,就是指国际法体系(system)内部存在的多个子体系(subsystem)缺乏统一协调而无序并存的客观结构。有关“体系”与“子体系”的提法,主要来源于对外文文献中措辞“system”、“sub-system”的翻译。最先促使国际法委员会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Gerhard Hafner教授就采用此措辞。(参见:Gerhard Hafner. Pros and Cons Ensuing from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J].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25): 849 - 864.)国际社会日益多元的需求推动国际法不断向新领域扩张,追求更多元的目标与功能[4]405。这些多元需求主要来自于诸如各专业领域追求的不同价值,全球、区域、双边体制的不同利益,以及多样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在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基础上,国际法体系针对贸易、金融、环境、文化、人权、发展等特定领域在全球、区域、双边多个层次发展出专门的子体系。这些子体系通常具备独立的实体规则与执行机制,并发展出专业的法律实践,其内部联系紧密[4]404。国际法碎片化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各子体系共存的国际法多元状态。endprint
现代法学郑蕴,徐崇利:论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碎片化结构与性质不过,多元的国际法结构也为国际法整体带来了困难——为了使新发展出的国际法规则行之有效,特定子体系的结构、规则通常具备与一般国际法规则或其他子体系不同的特征;一些独特的规则甚至正是为了偏离传统而被创设[4]406。尤其是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的中央机构进行协调,本就难以自上而下地形成一个有序、等级化的国际法体系。国际法体系内漂浮着全球的(universal)、区域的(regional)、双边的(bilateral)子体系(subsystem)、子子体系(sub-subsystem)[5],彼此摩擦、冲突,形成一个“无组织的系统”。有关“无组织状态”(unorganized system)的论述,参见:Karl Zemanek.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General Course o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J]. Recuil des Cours: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7, (266): 62.当学者在批判碎片化时,批判的其实就是这种无组织状态,即各子体系在适用过程中相互重叠、矛盾、冲突。这种无组织状态虽然是国际法发展、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却充分地满足了国际法对不断创制新权利、新义务、新规则的需要。
事实上,国际法正是从一个条约较少且彼此独立的体系,逐渐发展成为由不同多边子体系组成的、纵向复杂的网络。横向的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国际法体系必然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碎片化代表着国际法朝多元方向发展的趋势,是国际法体系的一种必然结构和形态。基于国际社会主要参与者“主权国家”的多元性,“碎”始终是国际法体系内含的性质[4]406。它的本质不是对国际法体系整体的冲击或挑战,而是国际法内容扩张与丰满的必然。同时,国际法体系在多元扩张时也总是具备相对应的另一趋势,即“一体化”[4]406。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碎片化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碎片化是一个‘自然进程……似乎总是具有同样自然的相反趋势,(将国际法)引向另一个发展路径。”一味注重国际法体系的多元,忽略各子体系之间的协调、统一,将影响国际法整体的完整与效力。国际法的发展总是呈现“一体化”与“多元化”两种张力。尤其是“多元化”水平越高时,国际法体系对“一体化”的要求就越强,碎片化所带来的困难也越发引人注目。毕竟,为维持国际法体系的完整性,专业分工越深入,就越需要保障统一,但各专门体制的离心力也使其协调、统一更具难度[6]。
二、国际投资法体系碎片化结构的样态国际法碎片化是国际法多元子体系扩散与并存的客观结构。事实上,碎片化现象也在国际法各子体系内部有所体现,其中,国际投资法体系正呈现出最典型的碎片化结构。
与国际法体系一样,国际投资法体系碎片化是其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它发源于美国独立时期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Friendship, Navigation and Commerce Treaty,FCN)。其中,“缔约方应当保护在其领土范围内另一缔约方国民的财产”的规定成为保护海外投资规则的雏形。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逐渐针对外国投资发展出一般国际法规则。“卡尔沃主义”代表的“国民待遇标准”逐渐成为东道国的主张。这一标准不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要求,并同时构成了拉美国家早期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承诺。对于“卡尔沃主义”的详细论述,参见:Santiago Montt. State Liability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Global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BIT Generation[M].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9: 31-82.发达国家主张外国人的财产应获得独立于东道国国内法体系的国际法保护,并延生出“最低标准”(minimum standard)待遇。该标准在1926年“尼尔案”中更进一步得到诠释。有关最低标准待遇的论述,参见:Andreas Hans Roth. The Minimum Standard of International Law Applied to Aliens[M]. Leiden: AW Sijthoff, 194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早开始缔结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失去大量海外投资。当时德国缔结BIT的主要动机即在于使其国内私人财产利益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其主要条约起草人Hermann Josef Abs是一个银行家,带有很强的商业意识。(参见:Rudolf Dozler, Christoph Schreuer.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8.)到20世纪90年代,BIT与其他投资条约扩散,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也得以建立。仲裁庭在案件裁决过程中专门适用并解释投资条约条款,探讨投资保护标准的具体内涵,作出了许多具有准先例作用的裁决[7]。国际投资法体系由一般国际法规则发展至今,内部散落了3000多个以双边形式为主的投资条约与临时仲裁机制,呈现出的典型碎片化结构,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不仅如此,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碎片化结构根源于其混合的性质。主权国家管理外国投资者,原本属于各国国内行政法管辖范围的国内公法事项,然而,国际投资法将其纳入国际平台,法律渊源主要来自于国家间缔结的条约。其次,该体系采用具有极强商事性质的仲裁作为主要争端解决途径,以解决公法问题;尤其是直接赋予投资者适用条约、提起仲裁的权利,将投资仲裁变成国家与投资者之间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博弈的平台。国际投资法体系融合了主权国家、投资者、国际社会等多个主体的利益有关国际投资法体系的混合型性质,参见:Zachary Douglas. The Hybrid Foundations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J].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74): 173.,很难用一个统一的体系一以贯之。具体而言,其碎片化结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内部层面——主权国家的不同投资政策要求建立多元的投资条约子体系;(2)外部层面——国内、国际、商事力量的博弈要求投资法规则与国内法体系、其他国际法规则在不同层面规制国际投资问题。endprint
(一)国际投资体系内部碎片化结构
国际投资法子体系以双边或区域性投资条约为核心。当外国投资受损时,投资者通常直接适用投资条约到ICSID或ICC等仲裁机构提起仲裁;仲裁机构组建临时仲裁庭(ad hoc tribunal),分别对案件作出裁决。因此,每一个投资条约匹配仲裁机构提供的临时仲裁途径,构成国际投资法的子体系。在形式上,国际投资法体系是3000多个投资条约并存与冲突的横向结构,然而在实质上,国际投资法体系更加立体。首先,国际投资法规制“东道国”与“投资者”间的关系。投资条约创新地赋予“投资者”向“东道国”求偿的权利,投资者直接参与国际投资仲裁,使国际投资法不再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横向关系,其内部结构向纵深发展。其次,国际投资法规制“合作法”领域的问题,各子体系间的关联程度高。在国际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投资市场蓬勃发展,东道国面临来自不同母国的投资者,同一投资者还可以在全球范围构建多层次的投资框架以“挑选母国”。国际投资法体系内部的碎片相互碰撞的概率更高,维持内部一致的需求相应地也更加强烈。
具体而言,国际投资法各子体系间的冲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较为传统,东道国(A国)市场向世界开放,面临来自不同国家(都与A国签订了投资条约,B、C、D国)的投资者(b、c、d)。若东道国的同一行为影响到多个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将分别依据AB、AC、AD条约解决争端,形成Ab/Ac类冲突。此处借用Pauwelyn教授对国际规则冲突的分类。他认为,在共处法时期,国际法主要由大量分散的双边条约组成。国际规则冲突主要发生于同一主权国家(A)对不同国家(B、C)分别作出相冲突的承诺、承担相矛盾的义务时,称为AB/AC类冲突。到合作法时代,多边体制增多,国际规则冲突则主要体现为主权国家(A、B)同时参与相互冲突的多边体制,各自引用不同体制内的规则对同一问题作不同主张的情形,称为AB/AB类冲突。(参见:Joost Pauwelyn. Conflict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8.)典型例子如20世纪末“阿根廷经济危机”,其比索汇率与美元脱钩的政策影响了几乎所有该国境内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使得阿根廷面临来自不同国家投资者提起的仲裁。针对阿根廷的汇率政策,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者分别依据不同投资条约对阿根廷提起仲裁,多达20几件,如Abaclat and Others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7/5;AES Corporation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7,Ambiente Ufficio S.p.A. and others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8/9; Teinver S.A., Transportes de Cercanías S.A. and Autobuses Urbanos del Sur S.A.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9/1; AWG Group Ltd.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UNCITRAL,Azurix Corp.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12; BP America Production Company, Pan American Sur SRL, Pan American Fueguina, SRL and Pan American Continental SR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4/8; Metalpar S.A. and Buen Aire S.A.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5;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8等。 第二类较为特殊,投资者(b)利用公司制度,在多国(都与东道国签订了投资条约的国家,B、C、D等)市场构建其庞大的投资集团,向目标国家(targeted state,即东道国A)进行投资。一旦发生投资争端,投资者可以利用不同国家投资者尤其是各国BIT对“投资”(investment)进行限定时,通常承认“间接投资”(indirect investment)。因此,即使投资者通过设立在第三国的公司、实体在东道国间接持有投资,也受投资条约保护。相应的BIT条款如:2004年加拿大BIT范本(Article 1 Definitions: …Investment of an investor of a Party means an investment owned or controll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n investor of such Party.) 或传统的定义方式如德国2008年BIT范本(Article 1 Definitions: ...the term “investments” comprises every kind of asset which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vested by investors of one Contracting State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other Contracting State.) 或1991 《美国-捷克BIT》(Article I(1)(a): ... investment means every kind of investment in the territory of one Party owned or controll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nationals or companies of the other Party, such as equity.)。的身份(b、c、d,但b是其多层身份的核心)分别依据AB、AC、AD条约规定解决争端。典型的案例如:美国公民Lauder与其位于荷兰的投资实体CME,分别依据《美国—捷克BIT》、《荷兰—捷克BIT》,就同一投资问题对捷克提起仲裁。参见:CME Czech Republic B.V. v. The Czech Republic, UNCITRAL(2003); Ronald S. Lauder v. The Czech Republic, UNCITRAL(2001).在形式上,捷克的同一行为影响了来自两个国家的投资者(b与c)的利益,相应投资条约(AB与AC)分别适用,构成Ab/Ac冲突;在实质上,却是同一投资者b与同一东道国A的同一冲突,通过多个投资条约获得解决(基于投资者的多元身份,这些投资条约的适用范围重叠),构成Ab/Ab冲突。由此,东道国的同一行为可能影响多个投资者的利益,东道国与同一投资者间的争端,又可能同时受其签订的多个投资条约保护。endprint
更进一步,在相互依赖的国际投资市场上活跃着的是“东道国”(A)与“投资者”(b、c、d),国际投资法体系规范的是“东道国”与“投资者”间的关系。即使投资条约由主权国家签订,各国在签订条约后几乎不以“母国”身份介入投资仲裁实践。母国通常仅在条约条款含义需要解释、明确时,与东道国一起作出意见,典型的如NAFTA的FTC(Free Trade Commission)对公平公正待遇(FET)条款的内涵进行解释。近年来,几乎所有签订投资条约的国家都具有东道国身份。随着国际投资市场的发展,传统东道国面临更多来自海外的投资,而传统母国也逐渐以“东道国”身份参与国际投资仲裁。例如,美国在NAFTA实践过程中发现其也陷入投资者提起的仲裁之中,因此,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具有东道国身份。主权国家每签订一个投资条约,就向潜在的投资者进行一次义务承诺。因此,投资法体系这个混杂的“意大利面条碗”,可以被视为各国对来自不同国家投资者所做的单方承诺,进而将其解构成以各“东道国”为核心的“承诺集群”。投资条约天然地具备双重功能:划分主权空间、保障投资者利益。因此,传统的AB条约可以被一分为二,成为Ab、Ba条约。此时,当我们分析投资条约时,就应当以每一个“东道国”为切入点,将投资条约划分为以“东道国”为核心的条约群。事实上,当各国逐渐同时具有东道国(A、B、C)与母国(分别代表投资者a、b、c的利益)双重身份时,这种条约功能的双重性将更为明显。由此,围绕于同一东道国的投资条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统和,以协调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内部碎片化结构。
(二)国际投资体系外部碎片化结构
国际投资争端涉及许多层面,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投资者是否拥有被东道国征收的财产,受国内物权法规制;东道国的行为是否构成征收,则取决于投资条约条款;在解释投资条约或判断国家征收等责任时,不能脱离国际法关于条约解释、国家责任的规则。ICSID临时委员会曾在MTD v. Chile案撤销裁决中判断投资者从与智利海外投资委员会(Chilean Foreign Investment Committee)签订的海外投资合同中获得的权利之性质。该委员会提到,判断海外投资合同与公平公正待遇间的关系是一个混合的问题——判断合同条款的含义是智利国内法事项,该合同对国际法争端(即国际投资条约争端)的影响则是一个国际法问题。参见:Decision on Annulment, MTD Equity Sdn Bhd. & MTD Chile S.A. v. The Republic of Chile, ICSID Case No. ARB/01/7, Mar.21, 2007, para.75.仲裁庭要解决的国际投资争端涉及的不仅仅是投资条约问题。
基于此,国际投资法构建了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时并不排除其他法律规则的适用。各国投资条约或者不专门规定仲裁庭解决争端时可以适用的规则投资条约有时会规定,基于东道国违反投资条约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投资争端可以被仲裁,但并不列举仲裁过程中可以适用的规则,也不排除其他种类的争端可以被管辖。如2012年《中日韩投资保护协定》15条第1款、挪威2007年BIT草案第15条第1款、德国2008年BIT范本第10条(但该条款没有将投资争端限定为违背此条约而引起的争端)。,或者确认仲裁庭能够选择适用不限于投资条约的国内法和其他国际法规定。例如,美国2012年BIT范本(Article 30: Governing Law)、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Article 40: Governing Law, 但该条没有列举国内法)。就仲裁规则而言,早在美伊仲裁庭时,其争端解决宣言(Claims Settlement Declaration)第5条就规定,仲裁庭应当在考虑相关贸易习惯、合同条款以及变化的情势之基础上决定法律选择规则以及商事、国际法原则,以解决争端[8]。当前最主要的投资仲裁规则《ICSID公约》第42条第1款规定,在当事方没有约定可以适用的法律规则时,仲裁庭有权适用争端国家的国内法(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能够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参见:ICSID Convention, Article 42(1).这些规则没有详细规定规则适用的必要连接因素,仅是开放地确认仲裁庭拥有选择适用规则的权力[8]42。
国际投资法体系与国内法体系的关系从投资仲裁之始就广为争论。主权国家一开始坚持国内法体系的首要性,这使得在确定《ICSID公约》第42条第1款的内容时几经波折。该款最终作了一个开放性规定,希望仲裁庭在实践中能促成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9]。Aaron Broches在1972年的海牙研究院提到,仲裁庭应当首先适用国内法规则,然后再用国际法对此适用结果进行检验[10];其根据在于,投资发生在主权国家管辖范围内,基于投资发生的争端应当首要地受该国法律规制[10]390。受此影响,在第一个涉及此问题的ICSID案件——Klckner v. Cameroon案中,临时委员会认为《ICSID公约》第42条实际上赋予国际法附属性的双重作用,即对国内法进行补充与修正。参见:Decision on Annulment, Klckner Industrie-Anlagen GmbH and others v. United Republic of Cameroon and Société Camerounaise des Engrais, ICSID Case No. ARB/81/2, May 3, 1985, 2 ICSID Rep.90 (1990), para.69.不过,鉴于内容日益细化的投资条约能更好地解决投资争端,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地位逐渐提高。例如,在ICSID第一个根据投资条约提起的案件(AAPL v. Sri Lanka)中,仲裁庭认为国际投资法不是一个封闭(slef-contained)的体系,应当首先适用BIT,国内法与其他国际规则是补充性的法律渊源。参见:As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Limited v.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ICSID Case No. ARB/87/3, June 27, 1990, ICSID Rev.- FILJ 5(1990), p.533. 直到现在,国际投资法体系仍然是仲裁庭裁决案件的首要渊源。endprint
国际投资法体系并不排除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适用。首先,国际投资法体系作为专门规制国际投资关系的特殊法(lex specialis),以一般国际法规则(legi generali)为指导和补充。有关国际法体系中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参见:Bruno Simma, Dirk Pulkowski. Of Planets and the Universe: Selfcontained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Law[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 (17): 486.通常,仲裁庭解释投资条约时直接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则作为习惯法进行援引。其次,国际投资法体系与其他国际法子体系也相互关联。UNCTAD发布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了新一代投资政策,强调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11]。它注意到各国投资条约在保护投资的同时日益重视国内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投资保护不影响各国环境、公共健康、安全等公共利益[11]89。国际社会就人权保护、企业责任等问题也发展出越来越多的规则和指南[11]91。国际投资与国家利益、环境、人权等息息相关,投资仲裁开放的准据法规则又为这些国际规则的适用提供了可能,因此,国际投资法学体系不可能脱离国际法体系母体而存在。
国际投资法体系承认对国内法体系、其他国际法体系开放,却没有对各体系进行功能定位和秩序协调。就技术层面而言,这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冲突法的问题。判断特定性质的法律关系应当适用的规则体系,需要专门的冲突规则。这一套冲突规则并不能通过对可以适用的规则简单进行列举而完成,从而自成一个独立的体系[8]52。国内事项适用国内法规定,国际问题适用国际法规则。不同法律体系构筑于特定的适用范围,在不同层面共同解决国际投资争端。
三、国际投资法体系碎片化结构的优势
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碎片化结构是其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源在于主权国家不同的投资政策以及国际投资本身多元的利益追求。它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体系结构,更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碎片化结构与正当性危机
客观定性碎片化现象,为正确认识并解决国际投资法体系的正当性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国际投资法体系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遭受了严峻的正当性危机。投资条约与临时仲裁的无序扩散影响了国际投资法体系的一致性[12],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失衡损害了此体系的公正性。关于正当性危机有许多论述,参见:Ari Afilalo. Meaning, Ambiguity and Legitimacy: Judicial (Re-)Construction of NAFTA Chapter 11[J].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 2005, (25):279 - 315; CN Brower, SW Schill. Is Arbitration a Threat or a Boom to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J].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 (9): 471 - 498.然而,一致性、公正性恰好分别映射出国际投资法体系内部、外部碎片化结构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1. 内部碎片化结构与一致性问题
Susan D. Frank在其2005年的论文中最早对投资仲裁的前后不一(inconsistency)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强调确定性与一致性(determinacy and coherence)是体制正当性的必须[12]1522,1584。Frank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这种成长的结果是,对将产生经济、政治后果的公共事务的裁决由不同主体私下作出。这些主体能够也实际上就同一法律问题作出相互冲突的裁决,并且没有一个实体有能力去解决这些不一致……正当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诸如确定性、一致性等因素,而这些因素进一步与预见性、可靠性相关。相应的概念比如公正、平等、责任性、代表性、正当程序以及核查机会等也会影响正当性。” 此后,学者往往宏观地将裁决相互矛盾归咎于投资保护标准模糊(vagueness)[13],以及仲裁机制的分散与重叠(overlap)[14]等问题。然而,投资仲裁前后不一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投资法体系缺乏正当性,只要这种不一致是基于国际投资法体系内部碎片化的结构。碎片化最直接的负面作用在于各子体系的冲突、矛盾,以及国家承受相互排斥的义务、责任[5]851。东道国签订的投资条约直接转化成东道国对投资者作出的主权承诺。若其缔结的投资条约标准不一,同一管理政策可能会引致不同责任结果,并增加主权国家的负担。这种不一致只是国际投资法在满足多元主权需求时必然带来的副产品,需要协调,但不能因此否认整个体制的正当性。
事实上,将国家管理投资者的事项纳入国际法平台,只有通过双边或区域的多元化路径才现实可行。国际投资法具有公法性质关于投资法公法性质的论述,参见:Benedict Kingsbury, Nico Krisch, Richard B. Stewart.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J].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05: 15-61; Gus Van Harten, Martin Loughl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s a Species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 (17): 121-150; Stephan W. Schil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直接调整国家对其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regulatory power)。参见:Gus Van Harte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Public Law[J]. OUP Catalogue, 2007: 45-71; Stephan W. Schil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17.东道国管理其经济领域的任何行为都可能影响投资者的利益,如东道国采取的司法行为参见:Loewen Group, Inc. and Raymond L. Loewe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CSID Case No. ARB(AF)/98/3.、环境保护措施参见:Metalclad Corporation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AF)/97/1; Chemtura Corporation v. Government of Canada, UNCITRAL.以及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汇率措施参见: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 ICSIDCase No. ARB/01/8;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 ARB/01/3; Gas Natural SDG, S.A.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0; LG&E Energy Corp., LG&E Capital Corp., and LG&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等。尤其是投资仲裁庭具有宽泛的管辖权,国家通过投资条约、投资合同等方式单方面作出仲裁同意,无法控制将来可能面对的仲裁申请。Paulsson就此提出了“arbitration without privity”,以说明投资仲裁对国家的管辖特征。(参见:Jan Paulsson. Arbitration without Privity[J]. ICSID Review, 1995, (10): 232-257.)并且,条约往往给仲裁庭保留了较大裁量空间例如,《ICSID条约》第25条第1款对投资争端的定义:“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entre shall extend to any legal dispute arising directly out of an investment”,但在解释时,很难确定“dispute arising directly out of an investment”的具体含义与范围。(参见:Rudolf Dolzer, Christoph Schreuer.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30-233.),事实上赋予其控制国家行为的权力,直接影响国家公共权力的实施及国内公共利益的保护。主权国家的国情不同,企图用多边统一的标准来划定保护国际投资的责任,在政治上难以为各国接受。只有通过双边、区域性途径,才能既满足国家主权的需要,又发展其投资政策。endprint
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通过此灵活多元的路径完善其投资环境关于投资条约扩散的原因,主要有“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两种理论。Guzman教授最早指出BIT扩散的“囚徒困境”,即发展中国家全体认同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性,且明了签订投资条约会为其主权带来损害,却私下纷纷通过缔结BIT以吸引投资,以提高本国制度在投资市场的竞争力。(参见:Andrew T. Guzman. Why LDCs Sign Treaties That Hurt Them: Explaining the Popularity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J].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8, (38): 639-688.)Santiago Montt则反对Guzman教授的观点,认为投资条约扩散不是因为各国基于“囚徒博弈”不得不作出较坏的选择,而是在于投资条约本身的功能将通过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使用而增强,从而形成“网络效应”。(参见:Santiago Montt. State Liability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Global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BIT Generation[M].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9: 83-123.),在难以达成多边体制的背景下,投资条约“多元化”是国际投资法体系发展的主要方向。更多国家的投资政策被纳入国际法体系之时,国际投资法治水平就会增强,同时,国际投资法体系内部的冲突也会加剧。这是体系多元程度加强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困难,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协调,不能因此而否认国际投资法体系扩张带来的积极效果。
2. 外部碎片化结构与公正性问题
国际投资法体系面临的另一正当性质疑即是其公正性。在其发展初期,投资条约就被视作发达国家为保护海外投资者利益而对孱弱发展中国家施加的霸权[15],逐渐地,学者转而批判此体系仅保护投资者及其投资、财产,没有对主权国家的其他利益给予恰当关注。参见:Gus Van Harte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Public Law[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Naveen Gurudevan. An Evaluation of Current Legitimacy-Based Objections to NAFTAs Chapter 11 Investment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J]. San Diego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5, (6): 399 - 402.例如,认为投资条约仅赋予投资者权利[16],批判仲裁庭在适用美国征收标准时甚至比美国国内法院更为激进,完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法律环境[17]。所有批判的核心集中在以下几点:国际投资法体系偏好投资者利益,侵蚀国家主权,具有不公正性。国际投资法体系在发展初期或许的确以保护海外投资为主要目的,然而,国际投资涉及国家公共利益与投资者商业利益,其被纳入国际法平台又获得国际社会关注,这一复杂性要求国际投资法体系承载多元的功能,利益平衡不可能一蹴而就。
更进一步,国际投资法体系外部碎片化结构正好为利益平衡提供了条件,它向外部规则保持开放,有助于融合不同法律体系追求的价值。例如,将国际社会关于跨国企业行为指南的规则与投资条约结合,能够在保护投资的同时兼顾投资者责任。尤其是国际投资法体系向国内法体系开放,为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平衡提供了支持。投资条约仅为东道国管理投资者设立原则性标准,不足以规制投资项目在国内的具体运营,需要依赖各国立法与行政安排。同时,国家与投资者还时常在油气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签订投资合同以满足特定投资关系的需要。在1945年以前,这些合同通常将大片的油田等特许给投资者,主要规定权利转让问题,不为投资者附加相应义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主权”等概念的兴起,产油国纷纷要求对本国资源进行控制。相应地,投资合同发展为“利益分享协议”(profit - sharing agreements),主权国家仍然保持对资源的所有权,与投资者分享开采的收益,并且对投资者的技术转让等问题作要求。到20世纪90年代,投资不仅局限于资源开发,基础建设等领域的投资也异常活跃。由此,投资合同发展出“建设、运营、所有”(build, operate, own, BOO)与“建设、运营、转让”(build, operate, transfer, BOT)等模式。(参见:Dolzer R, Schreuer 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72-73.)投资条约代表国际社会对投资保护的基础要求,国内法体系反映主权国家国内政策与公共利益,两者共同适用将促进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的平衡,以补充投资条约未曾关注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投资条约条款主要分为绝对待遇标准与相对待遇标准,直接体现出利益的多元与平衡。公平公正待遇、保护与安全条款等绝对标准根源于习惯法中的最低标准待遇,反映了国际社会给予投资的保护;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则指向东道国既有的保护水平,以尊重东道国的国内法治环境。有关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的发展过程,可参考Montt对卡尔沃主义的论述。(参见:Santiago Montt. State Liability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Global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BIT Generation[M].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9: 31-82.)endprint
(二)碎片化结构与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发展
进一步而言,国际投资法体系目前出现的缺陷,本质上在于此体系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此时,为国际投资法体系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宽阔空间,承认碎片化结构似乎是最为现实可行的路径。投资条约与投资仲裁的真正扩散仅始于20世纪90年代,关于国际投资法理论的认识也在21世纪才有所发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国际社会无法准确定位投资法体系应当具备的功能,也无法设置精细的条款来覆盖投资问题的所有层面。此时,设立一个一体化的多边制度并不明智,甚至还可能将整个投资法体系引向错误的方向。放弃这个不完美的体系也不可能,退回到主权国家各自为阵的国际规则最小化状态,等于切断了国际投资法体系发展的可能。碎片化结构取其中庸,既不激进也不消极,它允许扩散的投资条约缔约实践和仲裁庭多元的裁决结果,提供一种有效的试错过程,有助于成熟规则经验的积累和共同价值的发掘,国际投资法体系能够在这样的试错过程中逐渐成长、丰满。
首先,碎片化结构为条款内涵明确、价值提高提供了可能。现阶段投资条约条款内容模糊,本身不能为投资争端提供确定性指引,仍然处于较原始的阶段。然而如同网络效应,以合同格式条款为例,在创设之始内涵模糊、实用性差的条款,其明确性与实用价值可以通过更多主体的适用、解释得到提高。Klausner教授以格式条款为例,发展出“网络效应”理论,认为规则可以通过不断适用而增加价值。(参见:Michae Klausner. Corporations, Corporate Law, and Network of Contracts[J]. Virginia Law Review, 1995, (81): 757.)碎片化结构允许投资条约和仲裁实践数量扩散,在3000多个投资条约中,主要条款大同小异,扩散的仲裁、条约实践已经使其内涵日益清晰,可以为投资争端提供恰当尺标[18]。尤其是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具有准先例作用,有助于国际投资法体系内的规则前后指引。
其次,碎片化结构允许国家修改并完善其条约实践。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能判断条约条款是否符合国家意图。临时仲裁庭针对特定案件解释、适用特定投资条约条款,传达不同国家政策。裁决结果公开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对不同投资政策进行理解与比较,发掘最优实践(good practice)。双边、区域的碎片化结构允许国家对条约进行灵活的修改,甚至退出。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国家时常根据仲裁裁决对投资条约范本条款的措辞进行修改,并完善其内容。
最后,碎片化结构有利于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投资问题。多元的缔约、仲裁实践提供了国家间对话与理解的机会,国内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加入丰富了国际投资问题的内涵,为投资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了丰富的思路。
(三)碎片化结构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当前,整个国际经济法体系逐渐呈现出碎片化形态,这一现象在国际投资法体系内最为突出。在投资贸易领域,美国在WTO谈判陷入僵局后转而促进TPP、TTIP谈判,以期在亚太、欧洲构建以美国政策为主导的区域秩序。这不仅分解了现有多边体制的权威,也与该区域内既有的贸易投资安排如《中日韩投资保护协议》形成冲突。在货币金融领域,在IMF投票权结构难以满足崛起的发展中国家需求时,金砖国家试图构建一个专门促进发展中国家间外汇合作的金砖银行,对全球性的多边体制提出了挑战。这似乎是一种软实力的角逐,为国际经济秩序营造了些许紧张气氛。尤其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延长其霸权地位,将其超强的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安排,因此,任何制度改革的话题都被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为美国所不能容忍。然而,国家实力此起彼伏,通过霸权维持的体系难以长久。国际法是国家外交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虽无意颠覆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也需要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确认识碎片化结构有助于缓解紧张气氛,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和谐发展。首先,碎片化结构赞赏多元性,反对垄断话语权。各子体系在碎片化的国际经济法体系中共存,相互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事实上,它们构筑于特定的法律问题之上,发展出专门的理念、规则与技术,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承认多元性,允许多种制度并存,是对每个利益集体话语权的尊重。在碎片化的经济秩序中,各国不会因为出现不同制度而剑拔弩张,新发展的国家具有更宽松的话语权。同时,碎片化结构内涵一体化的要求,有利于防止各子体系间出现分裂。一切差异且多元的子体系都不应脱离国际法整体,它是各个子体系的正当性基础和效力来源。多元能够满足更多需求,但必须避免的是将国际法整体分裂为完全独立的孤岛,各分支之间互不关联。然而,应当避免发生的是碎片化在国际法体系中制造自给自足的孤岛,与国际法体系内其他分支不相关联。(参见:Joost Pauwelyn. Bridging Fragmentation and Unity: International Law as a Universe of Inter-Connected Islands[J].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25): 904.)这实际上要求彼此对话、相互理解,主权国家之间、法律体系之间借鉴彼此好的经验,甚至通过相互合作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反对误会、对抗与彼此割裂,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和谐统一。碎片化结构并非一种体系的竞争,而是提供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碎,却不杂乱;和,而不同。
四、结论碎片化是国际法体系、子体系在发展扩张中的客观结构,以其多元化满足差异的需求,并同时要求一定程度的统一,反对分裂。在现阶段,国际经济法体系正逐渐呈现此样态,尤以国际投资法体系最为典型。国际投资法在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由3000多个投资条约、专门仲裁机制组成的独立体系,呈现出内部、外部两个层次的碎片化结构。该结构根源于国际投资法混合的性质,是其发展的必经阶段。不仅如此,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碎片化结构还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内部、外部碎片化结构,分别为重新认识国际投资法面临的一致性、公正性困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条件;结构具有开放性与灵活性,还为国际投资法规则内涵的明晰、完善与丰满提供了有效的试错机会和宽阔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国际投资法体系的碎片化结构折射出了当前国际经济法体系的发展趋势,正确认识碎片化性质,承认多元,相互尊重,彼此协调,有助于为新崛起国家的话语权提供友好环境,并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和谐发展。MLendprint
参考文献:
[1]UNCTAD.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R]. Geneva: UNCTAD, 2013:101.
[2]Pemmaraju Sreenivasa Rao. Multipl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Forums: A Reflection of the Growing Strength of International Law or Its Fragmentation?[J].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25): 929 - 962.
[3]Joost Pauwelyn. Conflict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R]. Geneva: ILC, 2006: 400.
[5]Gerhard Hafner. Pros and Cons Ensuing from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J].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25): 850.
[6]Georges Abi-Saab. Fragmentation or Unification: Some Concluding Remarks[J].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1998, (31): 925.
[7]Andres Rigo Sureda.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Judging under Uncertain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9-131.
[8]Zachary Dougla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Investment Claim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3.
[9]Andreas Kulick. Global Public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
[10]Aaron Broches.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J]. Recuil des Cours: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2, (136): 392.
[11]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R]. Geneva: UNCTAD, 2012.
[12]Susan D. Frank.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J]. Fordham Law Review, 2005, (73): 1521.
[13]Charles H. Brower II. Structure, Legitimacy and NAFTAs Investment Chapter[J]. The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003,36(1): 37.
[14]Charles N. Brower, Charles H. Brower II, Jeremy K. Sharpe. The Coming Crisis in the Global Adjudication System[J]. Arbtration International, 2003, (19): 415.
[15]B.S. Chimni.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day: An Imperial Global State in the Mak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15): 7.
[16]Olivia Chung. The Lopside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gime and Its Effect on the Future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J].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7, (47): 956-957.
[17]Vicki Been, Joel C. Beauvais. The Global Fifth Amendment? NAFTAs Investment Protections and the Misguided Quest for an International “Regulatoy Takings” Doctrine[J].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3, (78): 35-37.
[18]CN Brower, SW Schill. Is Arbitration a Threat or a Boom to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J].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 (9): 47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