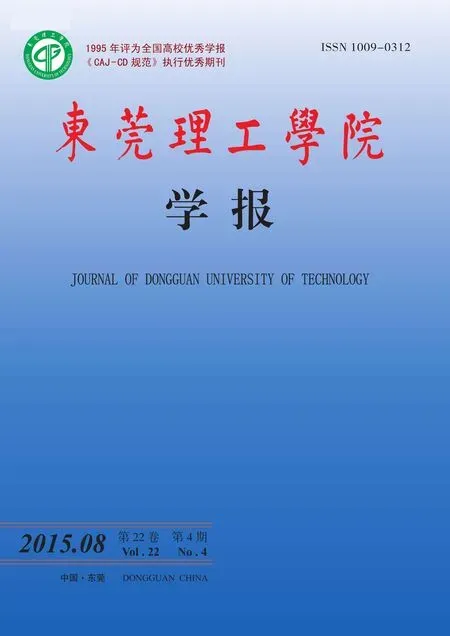论中国纪录片的伪真性
严楚晴
(广东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 510320)
论中国纪录片的伪真性
严楚晴
(广东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 510320)
中国当前部分纪录片制作者以收视需求为创作目的,为此,讲究纪录中的非痛感,讲求画面的美感,并以此为艺术性,以非常意象化的影像吸引观众,形成伪真性的纪录片。伪真性是中国纪录片在多元文化融合作用下潜移默化后形成的迎合艺术形态的表现特征,作者认为,中国纪录片应坚持创作出富有自己特色内容与形式感的作品,同时,可以吸收纪录片创始与一直坚持的客观性原则,以此追求与实现纪录片的最重要价值:历史的见证者与真实的表达者。
纪录片;伪真性;客观主义;客观性
“纪录片是创作者根据生活的本来面貌对生活事实的客观叙事,其中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是纪录片叙事的核心。”[1]创作者在遵从客观纪实的基础上,运用摄影、剪辑等手段表达对象的真实性,使影像价值达到最大化。在市场化需要,以及传统的虚美文化的影响下,我国时下纪录片呈现出“大众化”的特点,比如,制作者以收视需求为创作目的,为此,讲究纪录中的非痛感,讲求画面的美感,并以此为艺术性,以非常意象化的影像吸引观众,形成伪真性的纪录片。伪真性是中国纪录片在多元文化融合作用下潜移默化后形成的迎合观众的一种艺术形态的表现征象,笔者认为,中国纪录片应坚持创作出富有自己特色内容与形式感的作品,同时,可以吸收国外纪录片的客观性原则,以此追求与实现纪录片的最重要价值:历史的见证者与真实的表达者。
一、纪录片中的伪真性
纪录片应当是怎样的?这不论是制作者还是接受者,目前看来,还是难以获得一致的看法,有些看法甚至大相径庭。是以呈现为主呢,还是以表现为主,是客观性为主呢,还是主观性为主?这不仅涉及到纪录片本身的创作理念,甚至连何为客观性何为主观性,都存在异议。客观性就没有主观性吗?事实上,我们所谓的客观性,毕竟还是以人的描述为凭借的,而在影像作品中,呈现什么与不呈现什么,不仅摄影师可以把控,后期剪辑也可以加以取舍,于是,客观性的悖论便突显出来。而我们知道主观性备受争议,但何为主观在纪录片中又有更多的歧义。以拍摄一个人的流泪为例,远距离地拍摄被纪录对象与近距离地拍摄和特写拍摄,效果是不一样的,于是在这里,哪一个镜头是主观性的,哪一个镜头是客观性的,或者客观与主观的分界在哪里,就成了问题。更何况,还有取舍这个流泪镜头与否的可能性。
所谓的伪真性,有其特定含义。这个含义并非贬义,而是对某类纪录片的描述。真,指的是客观性,但是,它又是带有明显艺术手法的,因此,称之为“伪”。伪,是一种虚饰,是一种可以感觉得出的技法的实现,是强烈表现性的介入,是主观性的艺术性。
中国纪录片在讲究客观纪实的前提下,主张与艺术表现完美结合。典型的例子包括从20世纪80年代的《话说长江》到290年代的《再说长江》《江南》《苏园六纪》,再到时下的《舌尖上的中国》。中国纪录片提倡诗思合一的美学追求,即在写实与写意之间徘徊,如《江南》一方面利用解说词的文学性,另一方面利用镜头展现江南水乡意境美的真实,以声画合一的手段达到审美追求。然而,就是这一类以解说为主,力图通过解说引导观众,达到升华影像内涵的纪录片,带有了特定的伪真性。《江南》是伪真性的一种:
用华美或刻意的解说词来增强片子的层次。它缺乏画面表现力,单纯以解说构成叙事脉络,过分追求写意风格。虽然这样的手法能给予受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热爱感,然而,它过于单纯地指向看上去华丽或优美的过去,试图引发观众的自我赞美意识,事实上,带有强烈的导向性。细加分析,这样的导向,往往是以牺牲真实或现实为代价,追求的是让观众被动地置身于遥远的或者经过虚饰的现实的幻觉中。
二、视觉、技术与叙事的伪真性
镜头作为影像叙事的媒介,直观记录事件的同时,还表现心理的真实。中国纪录片为记录真实采用了多方式的摄像技巧,如《再说长江——水润锦官城》以特写和俯拍相交替的形式将地域文化、人物个性彰显于世,并利用近景采访和慢镜头的移动将成都古建筑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是一部令人赏心悦目的影像。它在中国称作专题片,但在范畴上属于纪录片。这无疑是一部主题先行的纪录片。它的最大主题当然是赞美成都的变化,赞美成都的人文。当然,它采取了一种巧妙的与亲和的赞美策略。“长江上游的岷江,滋润着一片平川——成都平原,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悠闲而浪漫。这是一个水与城市、生命的故事。《水润锦官城》独具匠心地展示了成都城一组古老和现代相延续的镜头:古老的蜀锦与现代的时装设计、相隔20年茶馆中的说书人、10年来经过整治日新月异的护城河、代代延续的新生命。在古今、新旧的强烈对比中,成都展示了它新的活力。时尚从来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成都的美永远不会被遗忘,因为它拥有着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历史,这里的人们始终是富于人文内涵和创造精神的,古老,便是这座城市最深的时尚。他们有精彩的记忆,他们正在书写这座城市的现在。”①《再说长江》第九集水润锦官城。http://jishi.cntv.cn/humhis/zaishuochangjiang/classpage/video/20100109/100241.shtml。
这是一座唯美的城市,一座温润的城市。这是影像带给我们的印象,也是它要营造的印象,它的叙事目的。这个目的它达到了。我们不能要求一部30分钟的片子(还是系列片中的一集而已)将成都的主要方面都囊括其中。它要传达的,就是成都的温润,成都的人文之美。于是,人物、景象、话题的选择,都趋向柔软,趋向美化。在这样的伪真性面前,观众无力抗拒,心甘情愿地沉浸其中。
再以《再说长江》中关于三峡及三峡移民的话题为例。在这部系列片中,这个部分占的比例是比较重的。本来,这部系列片重点要介绍的是长江沿岸的城市,或者说,以城市带出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生存状态。不过,一部与三峡无关的“再说长江”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我们进入《再说长江》叙事视野中的三峡。关于三峡,它辟出了几个专场:《三峡存证》《告别家园》《他乡故乡》《坝梦千秋》。这几个专场集中于这几个内容:三峡文物、三峡移民、三峡大坝。当我们先将专题片或纪录片放下,而专注于这几个名词时,它们是中性的,是一个客观的现象。但是,当我们在这些词汇后加上必要的词汇,如文物的“保护”“破坏”、移民的“高兴”“悲伤”、大坝的“利”“弊”,客观现象就会变成一个主观印象,或者说,不论是在这些现象前后加上哪个词,如“保护文物”现象或“破坏文物”现象,它们在现实中都是存在的,是真实的,但又都只是事物或事实的一面,于是就构成了伪真性。也就是说,《再说长江》这几个专场,是以“保护”“高兴”“利”等引导观众接受事实,这就成为一种叙事的策略。这里的伪真性就指的就是事实的虚饰性。事实经过虚饰并非就不是事实,只是它不再是事实的全部;而事实的全部从理论上说,又是不可能的。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双方面都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如文物,既有保护也有破坏,移民既有高兴也有悲伤,大坝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本文认为,只有这样的双面性,才能保护纪录片的“真实”特性。
以《国家地理》的系列纪录片《河流与生活系列》的《长江》为例,可以说明真实性的重要。当然,这部系列片也有其倾向,即认为人类的开放与地球的变化,正在改变河流的系列,它纪录了尼罗河、亚马逊河、长江、多瑙河和密西西比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长江》中,其镜头语言则相对客观,能让受众有代入感。场景各异的影像记录,节奏跳跃的镜头剪辑,从中国城市发展、农作物的生长、洪涝灾害的发生、三峡大坝的修建等影像出发,以古今交错的形式叙述时代的发展,贴近了观者的生活,还原了生活的原貌。“这种与观众同样处在一个未知的角度
上,共同思考问题,面对问题,取得乐趣”[2]的表现手法,在纪实客观现象的同时,调动观众的兴趣和收看欲望,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客观的视角。
甚至纪录片的声音处理,也表明了纪录片是否具有伪真性。声音是纪录片或剧情片的重要叙事手段,现在没有观众愿意回到默片时代。作为音响或解说的纪录片声音,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功能。当解说以动情或真挚的声调介入纪录片时,它要引起的是观众感情的进入,当音响特别是音乐是主观性的音乐时,它同样要引导观众的感情,或让他们激动,或让他们欣喜,或让他们悲伤。这些在《再说长江》中表现明显。反观《国家地理·河流与生活系列》,这里的音乐是单调的,是那种没有感情的无调性音乐作背景,这里的解说声调平静、不动感情,如同机器在读稿,只是在语速上略为加快。
似乎是为了讨好观众,中国纪录片关注人们的感官享受,推崇视觉艺术。从《复活的军团》讲究光影运用开始,纪录片便着重画面的构图,如光影的设计,利用人物轮廓的侧光展示秦始皇的王者气息。而音乐与镜头的配合也随文本影像的叙事跌宕起伏,给人强烈的镜头感,仰拍下手持秦弩的骑兵在高亢悲壮的音乐里诉说着厮杀的惨烈与物是人非的沧桑。然而,过度的追求视觉美,则使中国纪录片少了纪实感。《舌尖上的中国》达到色彩饱和与极高的画面质感,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特写及制作过程,把国内传统美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如在《我们的田野》里,制作者利用声画同步,在特写镜头下将细笋柔嫩的肢体与下锅后爆出的清脆油炸声形成强烈对比,而厨师用山盐在火腿上摩挲时发出的沙沙声也在固定镜头中体现美食本身的质感。
而就如《舌尖上的中国》表现一样,中国纪录片的艺术性逐渐增强甚至达到为迎合艺术形态而发展的态势,这样的情形不容乐观。制作者为提高收视率而使纪录片更显轻松化和娱乐化,而忽视当下社会的事实与真相,片面追求社会的美好,容易对观者造成观念误区,也无法解决观众的社会需求。镜头一味地展示诱人的美食,展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触碰的美好,却对现代化餐厅中色香味俱全但韵味全无的“精致”美食只字不提,不披露工业化大生产下食品的安全问题,不考究影像内制作环境的卫生状况。制作者过于主观的叙事,多具宣传功能并带有工具属性,这样便使得主题表现略显单一,难以让人信服。
随着真人秀节目活跃于电视荧屏,引发全民热潮,《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娱乐纪实电影”被定义为新型纪录片而饱受争议。这类影像受节目娱乐性影响,在明星效应和品牌效应的作用下获得较高的收视群,而引发票房攀升。相反,纯正纪录片——2013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得主《千锤百炼》却因上座率不佳导致票房惨败。
受者以自身的认知习惯和认知特点选择纪录片的叙事题材,创作者以叙事结构与受者达成共识,激发其情感。中国纪录片在纪实题材上的贫乏致使多数观众选取娱乐性较强,叙事性较弱,摆拍度较高的真人秀纪实电影,达到趣味需求。
“纪录片中存有‘纪录剧情片’,这类纪录片的‘真实’多表现为或者由演员搬演历史真实事件或由真实人物重演真实事件,用‘准真实’的‘故事化的叙述’方式,代替原先严谨的‘真实’的‘未经筹划’的画面”[3]84-85,如“BBC制作的《失落的文明》透过剧情描述与计算机合成影像,将失落的世界受到重建并且回复原本的光彩,《诺亚方舟》将圣经故事众多传说以戏剧手法的再现与现代科学家的考证结合,以影像生动准确地描绘了人类远古的宗教、文化与历史。”[3]85-86
中国纪录片在叙事上缺乏多元化,缺少国际追求,就目前现状而言,中国纪录片应多从纪实的社会题材入手,关注弱势群体、社会环境等。要摒弃虚构纪录的表现方式,如周兵的《敦煌》曾选择虚构的人物构造纪录片剧情,虽然导演想采用虚构情节展示敦煌一千多年的历史和人们的生活。但这样的表现却与纪录片的纪实性相矛盾,难以切实地深入当地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体会他们的真实情感。
三、纪实客观主义与纪实伦理
减少影像艺术的妩媚化,杜绝无限制的艺术修饰,把握事件的真实性,尽量达到客观纪实与主观表现的圆妥结合,恐怕是中国纪录片任重道远之路。梁碧波的《三节草》为此颇有特色。这部片子以女子肖淑明为叙事线索,穿插泸沽湖畔的景色风光,将肖淑明的生活与社会变迁相结合,着重纪录其生活上的戏剧冲突,并利用镜头语言融入自然美,使画面色彩不显突兀。纪录片的真实性是它的内在诉求,在真实的叙事风格中将事
件或事实呈现给观众,而不是以煽情或华而不实的文字为导向,恐怕才得以使纪录片回归其应得的尊严与身份。
客观主义的影像创作手法也许可以为纪实客观主义的说法提供佐证。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摄影艺术中,有种创作方法叫新客观主义。新客观主义强调以旁观者的姿态来呈现事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新客观主义的方法有多种,如法官式的公正观察力,它为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1876—1964)所提倡,它强调的是实证主义的精致形式,也就是将本身与对象(目标物)精密地契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对象的自然主义状态的呈现,是最好的呈现方式。如“考古学”方法,它由摄影家贝歇尔夫妇倡导,它强调“无表情外观”,事实上,他们的摄影作品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复制,仍旧有主观性选择,为此,他们还创立了杜塞尔多夫学派,旨在以“观察家”和“旁观者”的角度拍摄作品,其技术处理讲究端正的取景,不遗漏眼睛平时不容易观察到的细节,同时在诸如看与被看关系上进行客观性的呈现。当然,新客观主义在用光、布景、色彩及人物造型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与根据。与影像中新客观主义相对应的,是世界新闻理论中一直占据最重要影响的“客观主义”报道方式。哲学中的如艾茵·兰德客观主义倒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在新闻报道中,客观主义却是新闻报道的基石。当然,新闻中的客观主义理论与报道的客观性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绝对性,后者则在这个基础上并不回避选择的倾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闻的客观主义或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并不一定可以成为纪录片的不二法则。我们以一个人在某一事件中的情绪为例,他的情绪可以有激烈的时候,但也可以有平静或至少疲惫的时刻,那么,截取哪个片断,从片源上讲,都是客观,但就播出效果来说,却并不客观。这也是纪录片创作中的两难处境。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面对纪实伦理的考量。
伦理是人的一种主观选择状态。但是,当人们在选择纪实性纪录时,是选择客观主义,还是主观导向,还是客观性,或者是带有倾向的客观性,还是有很深刻的不同。这样的不同在选择过程中的取舍,当然与纪实伦理有关。纪实伦理在这里不是指如交通事故是不是要拍当事人的惨状,或者是在某类事件中是救人还是拍摄,以及是否涉及窥视等具体伦理,这里的纪实伦理指的是对纪录对象是采取何种表现手法的选择性态度及策略。
“纪录片,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有说服力的主题或观点,但它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4]当这个定义出现“感染力”这三个字时,事实上便涉及到了纪实的伦理性。纪录片的感染力,是否是纪录片应当追求的效果,同样是有争议的。因为一旦强调了感染力,我们便可以过度地使用剪辑或音响来达到目的,这便与纪录的客观性相冲突。但事实上,纪录片的内在诉求之一,还是想让人感动或引发联想。
伪真实也好,客观主义也好,客观性也好,导向性也好,无不指向纪实的伦理,或者说,纪录片的制作有自己的道德追求,有自我的价值约束规则。如果这些有着很大不同或者略有不同的伦理选择引起了我们纪录片制作、纪录片价值观、纪录片艺术的混乱,那很可能是一个叫作“纪录片”的东西本身已经无法容纳技术与伦理选择本身的多样性。
[1] 陈国钦.纪录片解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94.
[2] 孙靖.中外纪录片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9.
[3] 赵曦.影视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融合[J].现代传播,2009(2):84-87.
[4] 任选.电视纪录片新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271.
Discuss about the Bogus Documentary
YAN Chu-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510320,China)
Currently,some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makers take the audients needs as the objects so they pay attention to the non-pain recording;to the fantastic picture and to take it as artistic therefore create the bogus-documentary.Under multicultural action the bogus documentary’s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base on catering viewers and ideology.The Chinese documentary adhere to create full of own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nt and form,meantime to absorb the world documentary’s objectivity principle and to pursue and to achieve the most of important value of the documentary:the witness to history and the expresser to the real world.
the documentary;bogus;objectivism;objectivity
J952
A
1009-0312(2015)04-0079-05
2015-05-29
严楚晴(1992—),女,福建漳州人,本科生,主要从事影视编导和文学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