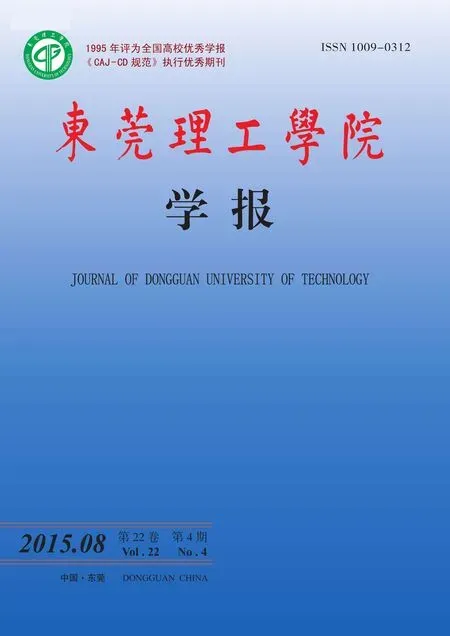多元性社会组织: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不同言说
双艳珍
(天津市委党校 校刊部,天津 300191)
多元性社会组织: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不同言说
双艳珍
(天津市委党校 校刊部,天津 300191)
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均强调多元性社会组织在市民社会构建中的作用。但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理论出发点,依凭理性的力量,忽视传统的价值,这使得其市民社会理论强调的社会组织只具有工具性价值,不可避免沦为维护个人权利的消极工具,并无法摆脱被湮没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统治范围内的命运;而保守主义重视秩序与传统的力量,更加强调社会组织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并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理性;社群;传统
自由主义是建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它强调的是个人价值的基础性意义。为此,自由主义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力的限制以及民主政府的恰当原则和程序问题。自由主义因此设计了一系列制度保障以维护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个人权利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实际成为对政府权力的边际约束。因此,对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而言,同“国家-个人”关系相比,“国家-社团”关系显得有点黯然失色。即便是探讨后者,也是为前者服务的,社会组织只是调节个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消极机制。然而,“国家-个人传统在政治分析中会掩盖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从而造成错误的结论。”[1]218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虽然也强调:保持作为制衡力量的强大中间派的存在是理性的自由概念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在自由主义的视野中,各种团体只不过是由独立的个人意志组成的集合体,其实质是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自由主义的这一观点忽视了社会组织本身所包含的共同体的概念以及关于共同的善和公共利益的内在价值,而仅仅关心个人的权利。因此,基于这种本体论个人主义而倡导的志愿性社会组织必然滋生如下问题,即集体的自治与构成这些集体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对立。因此阿伦特指出,自由主义能够代表利益,但不能培养公民;能保护个人自由,但不能维持在分享公共生活的共和意义上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这一特点在传统自由主义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沃特金斯看到了自由主义的这一不足,他指出,在西方世界,强有力的私人结社组织的发展必须与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分裂性影响互相抗衡,而自由主义的未来主要来自于此。我国学者刘小枫也认为,先验论的主体个人观是自由主义柔软的下腹部的里层,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对其进行了修正[2]102。然而,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的观点又使得自由主义的最基本前提——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似乎不再有效,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能主义的形成。自由主义的这一缺陷遭遇了来自保守主义的批判。
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与秩序、理性与传统的界分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是要以某种形式界定社会不可让渡的权利,抗拒政府的侵犯。但由于他们关注的对象不同,由此他们开出的“药方”也就不同。
自由主义建基于个人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相信人凭借理性的力量即可解决一切问题,构筑整个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因而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个人自由及其理性,人类唯一需要的就是容许个人随意施展才能的自由市场制度,而政府的活动只应局限于对这个制度的护卫上。与之相反,保守主义则更关注社会秩序的维持。在保守主义看来,自由固然重要,然而缺乏秩序的自由
只能是混乱。因此保守主义更注重寻求自由与秩序间的统一。而教会、贵族、社会风俗习惯等传统是与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的。保守主义极其强调社会自发自愿的中间性社会组织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协作组织不同于使用强制权力构造的组织,它们是维持社会秩序、防止社会原子化和国家权力膨胀的基础力量。保守主义相信社会进步的主要媒介就是这些背负传统色彩的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社会要进步,仅靠个人理性与单一的自由市场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维持各种传统的存在。传统是没有遗嘱的遗产。积极的政府行动应该尽可能扩大和加强家庭、邻里和自愿性的社会组织,维护并促进这些结社组织的成长,维护社会秩序与推动社会变化。
保守主义的鼻祖伯克是强调维护传统的第一人。在伯克看来,每个国家的环境和习惯决定其政府的形式,政府的改变并不依靠一个固定的形式,恰恰相反,是“成长的原则”维持着国家,这一原则集中体现在传统之中。伯克将英国权力机构的成长过程看作是运用了使自由社会各种不同利益成为“一致的整体”的“结构性优势”的方法,而不是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借助理性之力强加给社会一个计划,最终只能制造出一个沦为暴政工具的急匆匆的产品。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中,伯克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之处在于忽视了人类对家庭和邻居、对“小群体”的自然之爱。实际上,教会和贵族等团体是使社会团结起来的美德和社会传统不可缺少的支柱,是保障各种社会制度稳定的各种习俗和传统的监护人。他说:“教会组织提供了使他们可以不断地保持活力和得到强化的力量”[3]124,而具有正义感的贵族则是抵制王室影响和腐败的必要力量,是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必要保障。但是,法国大革命却将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一道投进了泥淖之中,遭到了一群猪一样的粗鄙之徒的践踏[3]105。针对这一点,施特劳斯指出,“伯克在边沁认为丑的地方发现了美:即苦心经营的传统秩序之美,它反映了几代人的经验和错误,及通过长期实践合法化了的成就。”[4]826
当代英国思想家奥克肖特更为明确地批判了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理性主义特征,强调了传统的社会组织的价值。他认为,西方近代政治的基本样式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病即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相信,只要得到很好运用,不受阻碍的人类理性是政治活动绝对可靠的指南,它可以用来解决所有的现实需要、问题与危机。这样,政治生活在理性主义的政治中被消解为一连串危机,每一个危机都能运用理性来克服;根本不能设想其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的政治,或者一个根本不能用理性来解决的政治问题。任何问题的理性解决本质上都是完美的解决。理性主义的这一气质使它过于依赖“理性的狡计”,从而更容易理解和从事破坏和创造,而不是接受或改良。这样的政治实际上将理性看作万能的工具,切断了与社会传统的联系,剥夺了包含在传统中的理性真理的基础。事实上,“在所有世界中,政治世界可能是最经不起理性主义的检验的——政治总是深深布满了传统、偶然和短暂的东西。”[5]3理性知识只是一种可以从书上学到的“半吊子知识”。奥克肖特批判美国早期的历史倾向于相信一个社会的合适组织和其事物的处理的基础是抽象原理,而不是以汉密尔顿说的“必须在古老的羊皮纸文稿和发霉记录中仔细检查”的传统为基础。因此,他指出,《独立宣言》是理性主义时代特有的产物。[5]27
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奥克肖特强调传统的暗示在政治中的作用:“在政治上,每件事情都是作为结果发生的事情,都是追求,但不是追求梦想或一般原则,而是追求一种暗示。”[5]49政治就是现代与传统的对话,而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论证。政治危机始终出现在一个政治活动传统中,对它的“拯救”只能来自未被削弱的传统资源本身。在他看来,政治是与一个社群传统资源的暗示分不开的,社群的传统具有调适性的活力,必须探讨和追求这些传统暗示以对现存的安排作进一步的改进。然后奥克肖特以现代国家形式说明了“暗示”的这一作用。他认为,现代国家及其宪政实际上就延续了中世纪的两种基本社会生活形态,即两种结社模式:一是君主国,另一则是社会合作团体及相关的领主管辖的封建产业。自由宪政国家继承了中世纪的“societas”这一特定的结社模式,允许人民与各种社会合作团体享有自由的地位、身份和权利;另一种结社是继承了中世纪的“universitas”,即具有多样分歧的“民间合作团体”。无论哪一种结社形式均有其成员相互结合的纽带以及形成结社的智力或管理方式。虽然受拉斯基的影响,奥克肖特将国家看成是一种结社形式的看法有其不足,但他强调中世纪传统对近代宪政国家的“暗示”作用则是至关重要的。
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社会多元主义的不同运用
受多元论的影响,保守主义重视各种中间性社会组织的存在,认为中间性组织是社会权威的主要来源之一。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同样也强调社会多元主义,允许公民在其生活世界中自由结社,形成一种权力分散的市民社会的格局。但自由主义强调的中间性社会组织在理论预设和强调的侧重点上不同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以个人对抗国家,无论国家还是社会组织,其存在的意义都是为了“个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因此,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成为必要的恶,社会组织也沦为维护个人权利的消极工具。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被强大的中央集权所吞噬的命运。
孟德斯鸠是强调中间性阶层、倡导以社会多元性制衡国家的典型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所重视的中间性阶层主要是指贵族阶层。在中古的英国,贵族的挑战和制约行为形成了对君权的掣肘。孟德斯鸠继承了中世纪的这一遗产,并试图将其纳入自由主义的宪政架构内。他首先假设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君主制政府的存在,但是由于君主制要求一个人按照法律进行统治,这就难免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如何使政府受制于法律呢?孟德斯鸠将目光转向了非政治的社会领域,力图从社会中寻找制约君主的力量。在他看来,社会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构成一个非政治的领域,而在于它构成了政治体制内的权力分立与多样化的社会基础,中介于君主和人民之间的中间权力,即贵族、教会和城市同业公会组织构成了这些基础的载体。借助这些附属性权力所拥有的特权和独立性,便能够限制君主的行为,尤其是贵族在一定方式上是君主政体的必要要素。他断言如果废除君主政体中的贵族特权,“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平民政治的国家,或是一个专制的国家。”[6]16
孟德斯鸠强调贵族的立场当然与他的贵族身份是分不开的。但他终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强调中间性社会组织是维护个人自由的有力武器的同时,又惧怕这一武器在不具有政治权力的情况下会流于形式,因此,他并不是简单地将其看作一种无力的制约力量,而是将其整合进分权制衡体系内,纳入了国家政治体制的范畴之中,并赋予贵族很大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以此使得贵族的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发挥。查尔斯·泰勒指出,在孟德斯鸠的思想中,对于中间性团体的力量,“相关之处不是它们外在于政治体制的生活,而是它们被整合到政治体制之内的方式,以及它们在其中具有的份量。”[7]195然而,孟德斯鸠的这一想法在强大的民族国家面前被击得粉碎,被纳入政治体系内的中间性团体的权力立刻变成了君主的奴仆,成为中央集权体制的一分子。
与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对抗国家主义的方式不同,保守主义对中间性社会组织的强调是在既反对个人主义又反对国家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中间性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对抗国家对社会的侵入,另一方面又是阻止个人沦落为大众人的重要壁垒。因此,在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浪潮之中,一个国家的整个中间结构应有生存的权力,就成为保守主义的主要信仰。在中世纪之时,中间性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前者,反对国家对社会的侵入,对抗国家用政治秩序代替社会秩序的努力。但是自近代以来,民主的不断发展使得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越来越合为一体,从个人的角度讲出现了大众民主的趋势;从国家的角度讲则是民主时代新型的温和专制主义的形成。于是,保守主义重拾中间性社会组织这一中世纪的遗产以反对这一趋势。
如果说孟德斯鸠还只是一个带有贵族色彩的比较忠实的自由主义者,因而他更愿意将中间性社团组织纳入自由主义体系中的话,那么托克维尔则明确地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深受孟德斯鸠影响,并因此被密尔称作“19世纪的孟德斯鸠”。与孟德斯鸠相同,托克维尔也出身于穿袍贵族家庭,贵族的地位在他的思想中是个痛苦的产物。他一方面欢呼民主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又深刻体会到优秀的贵族精神与新型民主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不适应。因此,他试图挖掘贵族制中有利于民主的成分,期待着它与民主的融合。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中看到了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者结合的可怕后果。法国大革命在打碎束缚个人的枷锁的同时,也使个人严重原子化。人们之间相互并立,彼此冷漠,失去了将彼此结合起来的联系纽带。正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最容易招致专制的侵入。在这种专制形式下,由于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存在空旷的空间,个人比较驯服和软弱,因此中央政
权就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并且成为更划一、更强大的专制形式。与此同时,暴政必将随着平等的扩大而加强。托克维尔指出,“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专制所造成的恶,也正是平等所助长的恶。专制和平等这两个东西,是以一种有害的方式相辅相成的。”[8]630面对此种情况,托克维尔乞助于前资产阶级社会机制的保护,提醒注意其中中介力量的意义。在他看来,这些中介力量在民主社会中能够在个人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之时有效防止中央权威滥用权力,从而筑起防止暴政的堤坝。托克维尔尤其强调贵族的作用。他认为,贵族是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阶级,他们拥有的伟大品德使他们养成了某种天然崇高的骄傲气质,以及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这使他们成为了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扮演了抵制行政当局的重要角色。然而法国大革命却将贵族连同封建制度一起抛进了历史的坟墓。托克维尔认为,这样做势必是使人民少了一道防卫中央专制的机制。他指出,“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9]34虽然托克维尔对中介力量的消失深感惋惜,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歇,而是要求建立新的中介力量。于是在他的理论中,各种社会组织拥有了至高的意义。他认为,抵制温和专制主义的唯一堡垒就是各类自发的社团组织,结社的艺术是维护自由与民主之间和谐的有效手段。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实际上是将中世纪的贵族精神嫁接到了民主社会的社团组织之上,以此作为牵制专制主义的力量。针对这一点,施特劳斯指出:“托克维尔把各种社团看作是过去贵族等级的人工替代物,后者以其财富和地位而起一种抗拒君主侵犯人民自由的堡垒作用。”[4]893然而,也正是因为托克维尔强调贵族团体功能的保守主义特点使他成为19世纪自由主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思想家之一。
三、中间性团体:保守主义抗衡新自由主义全能主义的屏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干预,这造成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体化以及国家权力的不断扩张。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宪政制度愈来愈丧失其限制权力的功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活动的加强不仅没有强化社会的联系纽带,反而削弱了自然形成的社群联系,那些较有活力的公共生活的社群中介形式遭到了合作经济和官僚国家权力集中的不断腐蚀,各种利益团体的作用被严重削弱,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中间性社会组织在市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自由民主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极大的动摇。西方社会愈来愈需要一种新的力量的辅济,以抗拒新自由主义的全能主义形式。保守主义将这种力量归之于社群,试图借助个人和整体社会之间的各种中介形式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这突出地表现在尼斯比特的保守主义思想中。
尼斯比特非常强调传统的作用,他尤其强调中间性社群组织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保守主义的核心是传统,尤其是中世纪的传统,这对于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作很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由社会进化而来的,不需要强制执行。它们在演化中形成了一些十分灵活的原则,同时又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以预期的。而这种传统更容易在一个团体中存在,这会使得人们能够和谐有效地一起工作,可以省去无共同惯例的团体中那些出于迫不得已而进行的有意识的、主动的协调工作[10]182-184。在中世纪的传统中,“自由”首先意味的是一个团体拥有适当自主性的权利。但是,自由主义却将这种团体的自由忽略掉,进而只强调个人的自由。因此,整个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可以看成是社会的、团体式的自由观分崩离析,进而转化为以个人为基础的自由观的历史。但是,面对这一状况,保守主义仍然一直在努力,尼斯比特指出,“在过去两个多世纪,美国及欧洲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保守主义政治学的标志一直在于对私人部门、对家庭和地方社群、对经济和私人财产,以及对相当程度上的政府分权的影响,而这种分权体现在对国家和社会中较小联合体的团体权利的尊重上。”[10]188
尼斯比特重点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全能主义。在对新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批评中,尼斯比特提出了“全能主义”概念。他认为,全能主义不仅包括德、意法西斯主义或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而且还包括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主导下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对社会过多干预的权力扩张现象。全能主义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传统社群的削弱。在他看来,国家的扩张必然导致志愿组织的功能下降,并因此而使得它们逐渐衰弱,正是不断扩张的国家权力取代了志愿团体并削弱了使
志愿团体得以产生与维持的社区精神。因此,他强调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性社团组织——包括那些小的社群,像家庭、教会、邻里、地方族群性的、类似行会的,以及自愿性联合组织[10]180——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尼斯比特认为,社群在中世纪时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像家庭、教会、兄弟会、邻里等小群体,是个人安全、道德、卓越和身份的最自然、最有效的来源。“在中世纪,‘自由’首先是一个社团群体获得其应得的自治权的权利”[10]190。然而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开始,国家开始不断侵蚀社群,中间性团体遭到致命的侵害,而现代官僚制国家更是像癌症一样消耗着中间性群体的生命力。他认为,全能主义国家剥夺公民自由的第一步就是取缔各种组织,或使之变成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从而使个人自由失去屏障,个人成为孤零零的原子,不断被异化,并丧失其个性。因此,当代国家权力扩张的主要受害者是个人权利。自由主义原本要维护其个人权利的基石,却在其自身内部培育了致使其灭亡的种子。针对这一情况,尼斯比特指出,之所以会有如此结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间性社群组织的消失,正是因为现代政治权力的扩张抽走了社群的能量,才使得个人逐渐被孤立起来,成为孤独、分离、异化和绝望的个体。为了消除孤立感和隔绝感,个人在全能式的国家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归属。但这实际上是一种错位,“现代国家的真正意义体现在它连续地渗透到个人的经济信条、宗教信仰、家庭的和地方性忠诚中,体现在它使既成的功能中心和权威中心发生根本性的错位。”[10]180面对这种情况,尼斯比特指出,20世纪,人们必须重新认识到社群是人的持久的同时也是迫切的需要,抵制全能主义国家权力扩张的途径是复兴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群组织的力量。正像威廉·杉布拉指出的,“《寻求社群》一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键性的框架,使我们能够理解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民族共同体的兴起,而且为未来的政治打下了基础,即指出中间性社团可满足人们对社群的追寻和对自由的渴望。”[10]182
保守主义的出现,反映了自由主义发展的局限性。虽然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着交集,即在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方面,双方都完全肯定由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组织来从事活动,但是双方强调的根据与侧重点却不同。前者仅仅强调社会组织的工具性价值,因而当国家强大到足以超越一切社会组织之时,社会组织就难免被吞噬的命运。而保守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能主义,恰恰是要为个人自由和国家职能重新寻找一个适当的位置,在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设置一个适当的缓冲带。保守主义强调社会组织本身包含的价值,这一价值使得“现代民主所赖以存在的社团和价值观比霍布斯的社团和价值观要更为多样。”[11]234
[1] 帕特立克·邓利维,布伦登·奥利里.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 刘小枫.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M]//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 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 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5] 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 查尔斯·泰勒.吁求市民社会[M]//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0] 马德普.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1] 罗伯特·W赫夫纳.公民社会:一种现代理想的文化前景[M]//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Multiplex Social Organizations:The Different Opinion of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SHUANC Yan-zhen
(The School Editorial Department,Party School of CPC Tianjin Municipal Committee,Tianjin 300191,China)
Liberalism takes individualism as theoretical basis,relying on the power of ration,and ignoring the value of tradition,which mak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emphasized by its civil society theory inevitably degenerate into negative tool which protect individual rights,and unable to get rid of the destiny buried by strong central regime,while Conservatism values the strength of order and tradition,more emphasizing on the valu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tself,and criticizes this opinion advocated by Liberalism.
liberalism;conservatism;ration;community;tradition
D093
A
1009-0312(2015)04-0023-06
2014-12-02
天津市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性权力制约机制研究”(TJDJ13-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双艳珍(1974—),女,山西临汾人,编辑,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