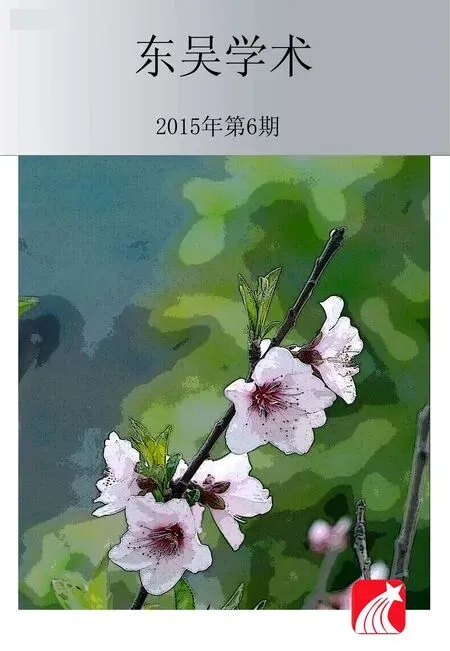金周荣的游民意识与成长小说
[韩]吴生根 著 权赫律 译
金周荣的游民意识与成长小说
[韩]吴生根 著权赫律 译
面对作家金周荣的作品世界,我们会觉得描述其为“游民作家的文学”最为贴切,这是因为什么呢?也许那理由就在于他那不停留于某一地,不断地去旅行的流浪癖;又或许是因为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大体上都带有游民性格。金周荣的游民意识不仅在《客主》,在《惊天雷声》等其他作品中也表现无遗。金周荣之所以用这种游民意识刻画到处游荡的人物,似乎就是因为作家认为人类本来就是“游荡的动物”。那么,“游荡的动物”或者“原本就是游民”类的人类观和作家的游民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呢?他的这种文学特征意味着什么呢?本文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作家的三部成长小说(《捕鱼者不毁芦苇荡》、《洪鱼》、《鳀鱼》)以及以母亲为主题的《走好,妈妈》的分析来探讨前述的相关问题。
游民意识;成长小说;小孩视角与成人视角的成功转化;成长与感悟;主题与象征意义
1.金周荣与游民意识
德国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曾在《说书人》当中指出,世上有两类说书人,其一是定居于某一处耕地的农夫型说书人,另一是划着船东游西荡的船工型说书人。①瓦尔特·本雅明:《瓦尔特·本雅明文艺理论》,第167页,潘星完译,首尔:民音社,1983。换言之,如果说有一种在某地定居且深谙当地的历史,对当地从古到今的变迁史也相当了解,并将其编成故事讲述的定居型的作家,那么,还有一种不管是喜欢旅行还是因为职业而不得已喜欢上旅行,反正乐意将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编成故事讲述的游民型作家。本雅明的这一分类法,应该算是在信息流通和交通手段未曾发达的当时,说明说书人原型的一种方法。而当今世界,现代作家大部分都很难用上述两种方法具体分类,实际上他们都兼而有之上述的两种特点。根据作品的主题和故事的性质,也许游民的观点占优势,或者是定居人的性质更为浓厚。然而,面对作家金周荣的作品世界,我们却觉得描述其为“游民作家的文学”最为贴切,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也许那理由就在于他那不停留于某一地,而不断地去旅行的流浪癖;又或许是因为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大体上都带有游民性格。金周荣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流浪癖:
从幼年时期到现在的花甲之年,我人生的外观总体上就是十足的流浪汉。先不说这是不是值得褒扬,但是,流浪汉毕竟会有自己特有的性格,那应该就是根本上拒绝停留在某一处的、像浮萍草一样的气质吧。①黄宗渊编:《解读金周荣》,第24、31页,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9。
迎来花甲之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就是这样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过去的人生概括为是流浪汉的日子,并说自己就是“像浮萍草一样的气质”的所有者。在随笔《流浪的佃农》里,他仿佛对拒绝定居于某一处的流浪佃农深表同感一样,写下了如下一段:
就像游牧民天生就是驿马星的命,他们远离家乡辗转于陌生的地方,从来不惧怕旅途遥远,一旦走进一家农户决定打短工,很快就融进那个村庄固有的风土人情中……
虽然都是陌生的面孔,但是同病相怜的命运令他们很快就变得亲热,打成一片,常常伴着嬉笑熬过一整夜。虽然他们装束家什简陋,但是内心却装着比自己的年轮还要多几倍的故事。他们辗转于忠清道,江原道,全罗道,庆尚道等地而饱受的艰难困苦,都会化成古老的故事,就像理顺了的线团一样绵延不断,那真正就是娓娓道来的天方夜谭。②金周荣:《湿漉的鞋》,第219-221页,首尔:金英社,2003。
这里提到的辗转异地的短工,不像长期定居某一大户人家包揽所有杂活儿的长工,他们在一户人家做短期帮工,只住一年半载而已。金周荣所关注的不是这类短工辛酸的日常生活,而是他们聚集在酒家嬉笑中永远也讲不完的那些故事。在小说家的眼中命运注定是流浪短工的人们装在心里的谈资话料,完全就是永远也说不完“天方夜谭”,就是山鲁佐德嘴里源源不断的故事的飨宴。
金周荣的代表作《客主》是关于朝鲜王朝末期,辗转全国各地的行商的故事。行商无疑就是一种不能定居于某处的游民,他们的人生和命运本身就是一个个故事。同时,在交通不很发达的当时,他们不仅是传递各地信息的使者,也是能够讲述各地万般趣闻轶事的故事高手。撰写《客主》的时候作家为了挖掘朝鲜王朝末期行商之间可能广为运用的口语和习俗以及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信息,“甚至自己仿佛也成了当年行商,具有了同样的生活习惯和意识,不知不觉地过着像他们一样的生活”。③黄宗渊编:《解读金周荣》,第24、31页,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9。经过作家这样将自己“行商化”和实地踏查的努力,作品中人物的口语对话显得自然、生动和丰富。小说家在《客主》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想象力,得益于将自己“行商化”之后,作家本身也具备了如同当年行商同样水准的讲述能力。作家的意图显然是通过对当年行商的商业活动和游荡生涯,完整形象地展现当时商业的发达过程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过程。
金周荣的游民意识不仅在《客主》,在《惊天雷声》也表现无遗。《惊天雷声》描绘了一个叫做申吉女的女人,从八·十五解放始到六·二十五朝鲜战争期间所经历的痛苦艰难的人生。申吉女并不是积极反抗封建家父长制度社会的女性,她在饱受屈辱和苦难当中从不埋怨自己不幸的命运,是一个在不可避免的艰难处境中努力开拓自己人生的智慧女性。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岁月里,她不仅没有挫折或者陷入绝望,反倒渐渐成长为一个坚忍不拔且宽以待人的人物。
作品《惊天雷声》里的游民意识,体现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申吉女移居和临时性的暂居,相逢和离别的情节上。小说伊始,月田里崔氏家门的年轻寡妇申吉女因婆婆的亡故面临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处境,被强暴自己的车炳祚卖到长春屋,导致了她必须脱离那种环境才可获生的绝境。主人公处在这样一种境况,从迫不得已导致离乡背井的角度而言,也许不足以与作家游民意识相提并论。但是,从主人公在日后的生活中体现出的决心和非离开不可的意志,我们可以看到与定居民完全异样的游民意识。
申吉女以种种理由坚持不定居而辗转异地,是因为她比起自己的安逸和命运,更加关注他人的生活和消息。她得知帮助和热爱自己的黄占盖被监禁,就为了拯救他而远赴安东;陪同和援助强暴过自己的货车司机池尚茂的妻子度过一段日子,见所助之人生活稳定后,才回了自己的娘家。在娘家她积极帮助处境艰难的父母,尤其为了搭救父亲表现出了积极的一面。当离开娘家去见池尚茂的路上,她后悔自己突如其来的举动,回顾“反人生常规而行的自己的模样”,读者百思不解她非要去见池尚茂的理由。不管理由如何,从她说走就走的行为习惯上,可以说她离开的动机与其说是有计划和富于理性,倒不如说是偶然和本能使然,而且全都不是为了贪图自身的安逸,而是为了帮助别人而为。
金周荣之所以用这种游民意识刻画到处游荡的人物,似乎就是因为作家认为人类本来就是“游荡的动物”。作家在一次对话中,谈及自己作品中人物充满野性的生活和作家游民意识的相关性的时候,曾提出“活在陆地上的所有的人,原本就是游民”,“投胎轮回,也是以人是游荡的动物为前提”的概念。①黄宗渊编:《解读金周荣》,第29页。那么,“游荡的动物”或者“原本就是游民”类的人类观和作家的游民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呢?他的这种文学特征意味着什么呢?本文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作家的三部成长小说(《捕鱼者不毁芦苇荡》②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9-10页,首尔:民音社,1992。、《洪鱼》③金周荣:《洪鱼》,首尔:文而堂,1998。、《鳀鱼》④金周荣:《鳀鱼》,首尔:文而堂,2002。)以及母亲为主题的《走好,妈妈》⑤金周荣:《走好,妈妈》,首尔:文学村,2012。的分析来探讨前述的相关问题。
2.《捕鱼者不毁芦苇荡》与成长小说
《捕鱼者不毁芦苇荡》所收录的四篇系列小说中的第一篇《冬天的旅行》,开始就是对金周荣幼年时代施予较大影响的集市场景的描写。
从村里去往面办公室的上坡路口,坐落着我经历穷困潦倒的那所房屋。围着篱笆的狭小院子里刚够养几只小鸡,篱笆墙外是块儿总是尘土飞扬和垃圾满地的空地,在那里每五天开一次集市。《……中略》随着太阳西斜,罢市的时间也来临,于是经历倾盆大雨和烈日炎炎的集市摊子里,众多摊主和赶集的人们渐渐离去,只有摆过粮谷摊的位置上落着吃米粒儿的黑压压的一群鸟。罢市后的空旷的地上掠过凉风的时候,我不知怎地总会感觉到郁闷,甚至因此而想哭。每五天我因罢市而感觉到的空虚,因为妈妈不在家显得更是凄惨。⑥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9-10页,首尔:民音社,1992。
这个场景一方面描绘了主人公孤独贫寒的幼年时期以及家附近每五天开启的集市,同时展现了在集市上靠着玩商标纸牌忘掉孤独和饥饿,而随着罢市渐渐逼近的主人公内心世界备感的空虚和孤独。主人公说那是“每五天来临的空虚”,而且因为赶集日也不得不在外务工的妈妈的不在,显得更加难以忍受。
我喜欢车站。为了看每天一两次经过我们村口的巴士,我经常去有一所破壳般售票处的车站……夏天巴士会被茂密翠绿的白杨树阴遮挡,我经常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傲慢地坐在那巴士靠窗的座位上,离开家乡去另外一个世界呢。⑦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26页。
主人公想象着坐在巴士靠窗座位上的自己未来的模样,实际在想着“傲慢地坐在靠窗座位上”的某个权力者,因为在主人公的眼里能够去旅行的人,就是一个享有旅行自由和权利的人。少年望着坐在巴士里的乘客,梦想着自己也有一天“离开家乡去另外一个世界”。这里传递的信息并非少年想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者,而是只求做一个能够去另外一个世界旅行的自由人。另外,通过《冬天的旅行》开头部分关于“集市”和“车站”风景的描绘,读者就可想而知幼年时期的“我”是多么喜欢集市热闹的场面,多么憧憬能够自由旅行的人生。少年之所以喜欢集市里的一切,是因为集市里没有管制自己的教师从而显得自由,同时在集市里能学到学校里所学不到的许多关于人生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集市是少年人生之路上的学校,而学校则不仅不是学习的场所反倒成了如同监狱般的存在。学校的教师常盯住学生小过错大做文章,并处以“一直到下课为止脑袋顶着椅子的严厉体罚”①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31、136、177、178、136、138、143、37-40页。或者“检查作业,检查卫生,检查体能,检查功课,检查清扫情况,甚至检查血液、牙齿和指甲”,②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31、136、177、178、136、138、143、37-40页。完全把学生当成罪犯对待。有的时候教师还像检查嫌疑犯一样检查学生个人用品,“经历过无数次检查危机的孩子们,最为恐惧的就是检查衣兜里的东西”。③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31、136、177、178、136、138、143、37-40页。这种检查令孩子们感到恐惧是因为,与其他检查不同事先毫无预兆,突然袭击式地进行。而且,教师根据检查结果把学生当作嫌疑犯、“扣帽子”,④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31、136、177、178、136、138、143、37-40页。予以审讯般的质问,此时的教师俨然就是警察或者检察官。“监视与责难多于表扬的地方就是学校”⑤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31、136、177、178、136、138、143、37-40页。的陈述,使我们联想起了福柯在《规则与惩罚》中提到的观点。教师把学生当作考试和检查的对象,如果学生落下不及格就会实施所有让学生足以感到羞耻的体罚或者谴责。
奇怪的是老师们几近病态地喜欢“短”,希望头发和指甲、算数的答案、自我辩解、裤腿、休息时间都要越短越好。他们喜欢“长”的只有自己实施的训话和跳远跳出的距离。⑥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31、136、177、178、136、138、143、37-40页。
作家通过少年的视角表现了揶揄教师的高超的讽刺技法。作家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揭露了试图凌驾被统治者之上的所有的统治者和权力者僵硬划一的思维方式,同时揭示了他们并不想聆听他人“自我辩解”的顽固心态。教师应该尊重个性,理解差异,但是《捕鱼者不毁芦苇荡》里的教师却全都以自我为中心,学生只是他们训斥的对象而已。作家通过比较“长”与“短”,敏锐地刻画了教师“作为的训斥”是多么的虚伪和伪善。主人公的眼里学校如同监狱,教师如同警察,不仅是因为教师是所有检查与体罚的执行者,同时觉得从来交不起学杂费的自己是教师特别厌恶的对象。交不起学杂费是因为少年的家境贫寒,但是,“妈妈的处境并不惨到筹措不了那点学杂费”,⑦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31、136、177、178、136、138、143、37-40页。据此可以推测妈妈是不是一个义务教育观的崇尚者。不管怎样,作为自尊心很强,是非观念很明白的妈妈,在送孩子去读书的事情上比谁都热忱,我们可以推断对孩子因为未交学杂费而遭受的侮辱和委屈,母亲很有可能是佯装不知。
《镜面上的旅行》里重要的事件是主人公第一次发现镜子的时候,所体验到的“美丽无比”的感觉。这不仅在整篇小说的发展上是重要情节,同时有必要与成长小说的主人公的内心变化联系起来考察的场面。
饥饿勒紧脖子不停地在折磨着我,在这样的幼年时代我发现了一件令我甚至忘记饥肠辘辘的东西,就是镜子。但是,实际上家里连一块能够真正映出家人脸庞的镜子也没有……我第一次发现能够充分发挥映照人脸功能的镜子,是在对面的理发馆里……我故意嫣然笑了一下,果然镜子里映出了我的笑脸。我作出愠怒的表情,镜子里也马上显现了出来。与这面镜子照面之后,弟弟和我像西方人一样,即便是说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也会故意使用夸张的手势或者身体语言。⑧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31、136、177、178、136、138、143、37-40页。
上述作品的场景标上题目应该就是“镜子的发现”。为了理解“镜子的发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拉康的“镜像阶段”⑨Dylan Evans,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Routledge,1996,pp.114-116.的概念。拉康认为镜像阶段在小孩精神发展阶段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并与身体发育阶段的欲望发生联系。换言之,从小孩的成长与成熟的视角看,与镜子里形象的遭遇令孩子对自己形象产生一种整体的认识,同时,渐渐地克服自己的缺点,虽然略显盲目,但会对自己在现实中所应承担的主体作用产生了一些感悟。拉康通过面对镜子作出不同反应的小孩和猩猩,发现了人类成长过程中“镜像阶段”的重要性。即,小孩和猩猩虽然都能够发现镜像的虚拟性,小孩却持续地表示出了关注,猩猩则不会表示更多的关注而转身离去。小孩通过镜子里的自己的影像而表现出惊喜,并不断地更换自己的姿势来观察自己。拉康所说的镜像,指的是映在镜子里的自己的躯体,那既是自己的同时又是属于他者的镜像,意味着通过小孩或者对成人的模仿可以观察自己行为的事实。重要的意义不是在于小孩通过镜像如何接近对真实状况的了解,而在于触发了小孩试图去了解真相的动机,或者寻找自己本来面目的愿望。
在理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等成长小说里主人公内心的变化与成长的时候,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显然颇有一定的启示。首先,“与这面镜子照面之后,弟弟和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陈述,即,“弟弟和我像西方人一样,即便是说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也会故意使用夸张的手势或者身体语言”,既是模仿他者的行为,同时也是自我行为的表现,是自我融进他者的结果的体现。人的欲望无疑就是模仿他者欲望的表现,人类在模仿他者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本性。主人公试图模仿他者的行为或者态度,尤其关于走路的姿势问题的情节具有特别的意义。妈妈埋怨我总是缩着脖子走路,要求我“不管是在哪儿,都要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地走路”,①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40、44、301页。显然这不仅仅是在教如何走路,而是在教导如何去做人。同样我的关于镜子的体验,也会出现类似的表现,“我”不仅被镜子所迷惑,同时因为镜子里的镜像而苦恼。
我透过主人咯吱窝缝偷窥了镜子里映出的自己的脸蛋。两行眼泪沿着腮帮子流下,正好和鼻涕合流到了一块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那么丢脸和傻呆呆的样子。那模样无情地碾碎了对自身的美好的幻想和期待。我的记忆里那些可以联成长长一段的所有美好的瞬间,也没有当时所感觉到的痛苦那么漫长。②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40、44、301页。
这段引文里的“主人”是指毫无理发经验的蹩脚理发师。上述的场面正是那个理发师用理发推子就像薅草一样胡乱给“我”理发后,经历痛苦的过程和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那般模样之后“我”对自己的几近幻灭般的感受。镜子可以把人引入幻想的境界,但是,也会令无法接受自己本来面目的人产生厌恶和幻灭感。一个成长中的小孩对镜子的双重体验,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的体验。经历这种“镜像阶段”的过程当中,小孩会发现与镜像吻合或者相反的自己,从而渐渐形成自己的主体。《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的少年主人公正是通过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欢乐与哀伤,幻想与挫折,希望与恐惧渐渐走向成熟。对他来说,成熟就意味着领悟了不能在妈妈面前撒娇的理由,反而要去理解妈妈的痛苦,甚至能够去“发现妈妈内心深处的遗憾”。③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40、44、301页。
3.《洪鱼》和《鳀鱼》,成长小说的两个类型
成长小说可以说是关于小说的主人公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变为成熟大人的过程当中经历种种精神危机和考验,并逐渐领悟自己应起到的作用和身份,从而去确立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现实关系的故事。成长小说的主题简而要之,就是如何生存的问题,主人公会通过自己或者他人的经验和阅历,领悟人生的真谛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在《洪鱼》里主人公通过妈妈和三礼学会了生存之道,而在《鳀鱼》里主人公则通过爸爸和舅舅感悟了真正的人生。两部作品作为成长小说最为明显的差别,在于主人公“我”的人生导师在《洪鱼》里清一色都是女人,而在《鳀鱼》则全都是男人。而且,如果作品《洪鱼》的题目象征着父亲的缺位,那么《鳀鱼》则并非象征着缺位的母亲,而意味着在任何艰苦的环境当中也不放弃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的自由精神。作者在《鳀鱼》“自叙”里提到“鳀鱼微不足道,然而,鳀鱼却比鲸鱼更加坚韧和勇敢”,“鳀鱼通体透明,连内脏也依稀可见,然而,它却从不显露自己产卵前的形象,是一个完美的隐遁者”,作家这一陈述,可以看做像鳀鱼一样选择一种坚韧、勇敢、正直、光明磊落之人生的作家个人意志的体现。
那么,对《洪鱼》中的“我”来说,妈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作为一个遭受丈夫冷对的妻子,五年来妈妈独守空房,承受着丈夫的背信弃义,同时还承受着一个女人的孤寂。但是,从外观上妈妈的生活似乎并不因此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或者变得多么艰难。即便是有了天大的痛苦,可妈妈好像很看不起有一点事儿就大肆张扬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显得很浅薄。①金周荣:《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第31页。
在儿子的眼里,妈妈不轻易向外张扬自己的不行和痛苦,是自尊心和忍耐力极强的女人。为了不让儿子被人损为没有父教的孩子,妈妈对孩子的过错会施以严厉的处罚。不仅如此,时时刻刻不忘克制自己,是非分明,为了家人的生计长年累月去揽做针线活,忙里偷闲还不忘为喜欢放风筝的儿子做一个风筝。看着端坐在缝纫机前忙碌的妈妈,儿子感到的不是羞愧,而是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发生摇动,是小说开头暴雪天和躲避大雪住进他们家的三礼一起生活之后。
与爸爸分开的日子越长,妈妈越是努力维护自己的形象,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奇怪也很费解。可是三礼出现之后,妈妈的那种做法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天夜里,妈妈突然出走的记忆很久没有消去……瞬间掠过我心头,令我猛然察觉到那就是背信弃义和虚脱,还有急转直下的挫折感。妈妈那年龄段的女人,只要没有犯下什么不贞的坏事儿,绝不会瞒着孩子偷偷出走。②金周荣:《洪鱼》,第81、217页。
少年主人公第一次感觉到了妈妈的背信弃义以及由此引起的挫折感,因为他怀疑妈妈有所不贞。在这里,妈妈不贞与否并不重要,少年感觉“一到深夜,妈妈就像三礼一样偷偷去密会什么人”,对他重要的事情是“如果妈妈像爸爸一样出走,那么自己就会成为被遗弃的孤儿,会经历随之而来的离别与绝望”。少年这种忧虑甚至恐惧真正变成现实威胁,是某一天突然自己多了个弟弟开始。少年目睹妈妈给陌生女人丢下的孩子喂奶的场景,感到了非同一般的冲击。
那天夜里妈妈的行为,真的难以理解和接受。不是我与妈妈,而是发现了妈妈和昊英之间的深厚的情感,给我留下的是急转直下的挫折与绝望。不是妈妈对我的,而是妈妈针对昊英的爱心,因此这对我来说毫无价值。妈妈就这样没有动用责骂与殴打,就轻而易举地让我陷入了挫败之中。实际上,我也并没有因此受了多大的伤害,但是,感觉心酸倒是真的。由此妈妈对昊英的爱心,对我来说比起残忍和无情的暴力或者彻骨的憎恶,更具威胁和杀伤力。而且,送走三礼的恰恰是妈妈的事实,更令我感到了背信弃义和内心的创伤。③金周荣:《洪鱼》,第81、217页。
少年难以接受和理解妈妈对突然出现的弟弟表示出的爱心。妈妈的那份爱心,令少年感到“急转直下的挫折与绝望”和“背信弃义”,而且这“比起残忍和无情的暴力或者彻骨的憎恶,更具威胁和杀伤力”。读者也许纳闷少年主人公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仅仅是一个陌生女人留下了小孩,妈妈也只是让小孩含了一下并无奶水的奶,为什么会引发少年主人公如此剧烈的反应?这些问题,如果一旦去读《走好,妈妈》就会迎刃而解,简言之,陌生女人留下的那个小孩恰恰就是妈妈亲生的孩子;换言之,妈妈对那个孩子的爱心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女人对小孩的母爱,而是对亲生子女的本能表现。经历了这类事件的孩子一般会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反应,但是,作品中的少年主人公却独自漫步河堤反刍孤独带来的痛苦,“开始觉得我也应该像爸爸一样远走高飞”。向往远走高飞,对远走高飞本身带有坚决意志的少年的反应实际上无助于治愈内心所受到的创伤,但是,从少年主人公的角度来说这也可以认为是靠着自身的智慧,试图超越自己所处的不幸境遇的较为成熟的思考。
少年主人公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内心的孤独和挫折,只是默默地去寻找邻居磨米间自己的秘密空间。在磨米间的机械的震动中,主人公感觉深藏自己内心的某种能量在涌动,明白了自己“也具有憎恨某个对象,并像子弹一样冲向憎恨对象的邪恶的冲力”。①金周荣:《洪鱼》,第221、231、249页。少年试图通过不断地坚定自己要离开妈妈的意志,或者将对母亲的憎恨转换成自己能动的攻击本能,努力摆脱难以忍受的困境。从这一点上,少年对母亲的憎恨与从母亲那里获得解脱是共存的一对情怀。少年并不因为对母亲的憎恨而自责,相反更加强化那种憎恨,是因为他坚决认定一切全都起因于妈妈自己。少年一方面憎恨自己的妈妈,同时将母亲当作平凡的一介女性来审视,结果少年发现之前绝没有过的一个事实,即,妈妈也是一个具有本能性欲的人。少年发现妈妈和常范妈妈一起偷窥邻居男人光着身子洗浴的场面,极其自尊且自我控制力极强的妈妈的形象那一瞬间消失得荡然无存。另外,妈妈夜半三更带着儿子为了寻找丢失的公鸡,肆无忌惮地擅闯挨家挨户的场面,令儿子认为是“我仔细观察妈妈的错误的判断和失败的机会”,②金周荣:《洪鱼》,第221、231、249页。甚而至于因此感到一丝慰藉。过去讲道理,是非分明的妈妈做出的错误判断以及因之而起的过失行为,使少年不仅嘲讽母亲,甚至让他尝到了冷笑和揶揄之后的快乐。
核实和偷窥到了深藏在妈妈称谓背面的女人的本能,令我紧张得心里咚咚直跳。这可能导致改变我命运的结果,我反倒因这样的冒险感到了颤栗。难以说清楚和极其模糊的混乱心绪,还有我感到的背信弃义已经在怂恿着我。③金周荣:《洪鱼》,第221、231、249页。
少年假想“妈妈称谓背面的女人的本能”促使妈妈跟邻居男人发生性行为的场面,陷入了“难以说清楚和极其模糊的混乱心绪”之中,但是,少年感觉到的妈妈的背信弃义并不足以否认对妈妈的另外的感情。
《洪鱼》的结尾是妈妈和少年翘首以待已久的爸爸的回归。爸爸对我和妈妈来说,是一个思念和憎恨交加的对象。妈妈得知爸爸要回来,兴奋得满脸红彤彤,忙着打扫房间准备迎接,而“习惯于独自一人的我,反倒觉得爸爸回来的消息像是一个谜团,比起兴奋和期待,更多的感觉是错乱和幻灭”。少年所说的“习惯于独自一人”,证明少年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人格主体。相对于兴奋不已的妈妈,少年认为爸爸只是虚无缥缈的存在,这一段主人公的内心描绘显得很真实和合理。照此情节发展,小说是不是“习惯于独自一人”的少年主人公,因对父亲回归的失望而离家出走为结局呢?换言之,少年主人公是不是应该因妈妈的背信弃义和对爸爸的失望,而断然去寻找自己朝思暮想的三礼姐姐呢?然而,小说的结局里出走的是妈妈,而不是少年主人公。这种结局的安排,也许是作者认为少年的离家出走过于突兀或者不合情理,又可能是作家早已构思了如《鳀鱼》这样的后续作品。少年猜测妈妈可能认清了对爸爸抱有的幻想,全都不过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这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家出走。
《鳀鱼》是关于妈妈离家出走之后,与爸爸过日子的少年的故事。《洪鱼》里“我”的名字叫作“世荣”,而《鳀鱼》里“我”的名字叫作“大燮”,两部作品从外观上似乎完全是不同的故事,但是,《洪鱼》里“世荣”年当十三岁,《鳀鱼》里的“大燮”年当十四岁这一点上看,可以认为《鳀鱼》是承继《洪鱼》的系列成长小说。《洪鱼》结尾没有说清妈妈离家出走的原因,《鳀鱼》同样也没有说清楚妈妈离家出走的动机所在。爸爸怀疑妈妈与同父异母的舅舅关系暧昧,少年只是认为舅舅的介入导致了妈妈的离家出走,而舅舅则告诉少年妈妈离家出走的原因是爸爸的外遇。于是,“我”在妈妈到底为什么离家出走这一问题上,因两个亲近的人的不同解释而陷入混乱当中。
舅舅期待妈妈回来的心情不比爸爸差,而且,看得出舅舅对妈妈的爱心依然如故。但是,舅舅的爱心,是以妈妈和爸爸恢复如常为前提……我们三个人同样都盼望着妈妈早日归来,却各自反目、怀疑,甚至仇视。另一方面,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又使我们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①金周荣:《鳀鱼》,第165、31、40、42、59、73、257页。
期待离家出走的妈妈是少年主人公、舅舅和爸爸共同的愿望,据此“我”认为这共同的愿望就是将平日里几乎反目成仇的三个人融合到一起的重要理由。爸爸虽为猎手,“但一次也没有带回什么猎物”②金周荣:《鳀鱼》,第165、31、40、42、59、73、257页。;舅舅虽然住在江边的窝棚,还经常带着鱼叉出去,却从来没有见到捕鱼或者捕获什么猎物。舅舅认为“要是想活捉家雀,不能使劲去捏拿,而要轻轻地抚摸”,③金周荣:《鳀鱼》,第165、31、40、42、59、73、257页。他像一个无所不知的大自然专家,不仅准确地说出鱼的生活规律,“对水下所有的变化和水床的地貌”④金周荣:《鳀鱼》,第165、31、40、42、59、73、257页。也有极其详尽的了解。“我”通过这样的舅舅学到了鸟类是如何根据季节移动,如何筑巢,如何交配等等。尤其“在探查乌鸦如何在三个地方假装筑巢,最终在排水管里建造用于产蛋的真正的巢穴的过程”⑤金周荣:《鳀鱼》,第165、31、40、42、59、73、257页。当中,“我”与舅舅建立了浑然一体的感情。
“我”与舅舅建立了如此亲密的感情,并不预示着“我”与爸爸就是对立的关系。“我”即便是见到了爸爸令人失望的表现,也不加以非难,反倒试图去理解爸爸。
对这样的妈妈我有所失望,但是,爸爸却没有给我留下那种失望。妈妈的确是无限怀恋的对象,但她同时留给我的还有憎恨。⑥金周荣:《鳀鱼》,第165、31、40、42、59、73、257页。
妈妈既是怀恋的对象,同时又是“我”仇视的对象,而爸爸则对“我”来说一向就是尊崇的对象。没有特别的情节或者小插曲,关于一件件小事的叙述构成的小说中,值得一提的就是末尾少年与爸爸一同去捕猎野猪的场面。少年之所以能跟着爸爸一起去捕猎野猪,是因为迫切期待舅舅一臂之力的爸爸曾经答应少年,如果成功让舅舅帮助自己就带他一起去捕猎。在这次捕猎之路上,协助赶猎物的几个人说了一些贬低爸爸的话,少年义愤填膺地与之强辩的场面也值得一提。
瞬间,我猛地窜了过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咬住了那个汉子的胳膊。妈妈不在的这两年,是我把屋里擦拭得油光铮亮,我又是毫无惧怕地点火烧了学校校长家仓库的主谋,所以,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我浑身都充溢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即便是那高大的壮汉,我也有攻击他的能力和气魄。⑦金周荣:《鳀鱼》,第165、31、40、42、59、73、257页。
这一场景与其说反映了少年具有敢于和那些大人打斗的能力,不如说是呈现了少年在妈妈出走之后如何度过了那些年月,如何渐渐走向成熟的整个过程。少年考虑妈妈随时可能回归,不忘记每天将屋子的“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不仅显示出了勤快和诚实的一面,同时展现了并没有因孤独和思念而变成懦弱的挫败者,反倒成长为一个果敢、富于冒险精神的坚忍不拔的少年。从这个意义上,《洪鱼》结尾出走的不是少年,而是妈妈这一构思,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此时重要的不是少年出走与否,而是他如何融进这个现实世界的问题。
妈妈的离家出走给少年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在这个没有妈妈的世界里如何生存下去。于是,少年通过爸爸虚妄的挫折感悟人生,通过舅舅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学会人生态度。《鳀鱼》的结尾里像舅舅一样守着窝棚过日子的少年,在潜水的时候发现一群鳀鱼华丽的舞姿,并瞬间产生与鳀鱼成为一体的感觉,这恰巧与预示自己的人生如鳀鱼的“作者序言”里的话遥相呼应。
4.《走好,妈妈》与妈妈的真貌
《鳀鱼》出版整整十年后发表的《走好,妈妈》,一开始就是四月的某天清晨乡下的弟弟给住在首尔的兄长传妈妈讣告的场景。接到消息的哥哥,回想很久以前妈妈和弟弟到首尔去自己家时的情形。妈妈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迎合城市里的生活节奏,尤其不愿因此给儿子家增添麻烦,来到首尔第三天的清晨就离开了儿子家。儿子的第二个回忆是从电话中获悉妈妈当选政府选拔并奖励的“了不起的妈妈奖”获得者的事情。当时妈妈从电话中说,孩子们小的时候因为贫穷经常让孩子们忍饥挨饿,没能按照学校要求“及时购买教材”,“因两次换了丈夫”①金周荣:《走好,妈妈》,第44、44、103-104页。的过错致使孩子们在继父膝下唯唯诺诺,这都是自己的过错,所以没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妈妈将没能及时给孩子们买教材的过去和再婚后让孩子们在继父膝下唯唯诺诺等同了起来,但是,对儿子来说致命的伤痕和挫折却来自于其中的一件事,即妈妈的再婚。
我一生中很早毫无目的地离开家乡尝尽世上的辛酸,是因为想摆脱关于妈妈和突然出现的新爸爸的记忆,还有从而引起的挫折感和羞耻心。幼年时期不离我左右,常伴随着我的是对陌生的恐惧和好奇心。所以,我,在外人看来总是不伦不类的孩子,是什么也做不好的、犹若寡断的、没有果断性的孩子,也因此经常被同龄的孩子们孤立起来。②金周荣:《走好,妈妈》,第44、44、103-104页。
主人公明确地表示自己离家出走是为了摆脱由于妈妈的再婚带来的“挫折感和羞耻心”。“妈妈的再婚”无疑就是离家出走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不可排除还有其他的因素作祟。上述的引文中,少年“在外人看来总是不伦不类的孩子”,“也因此经常被同龄的孩子们孤立起来”,他之所以这样也会有很多原因,但是自己住在连篱笆都没有的、只有两间房屋的简陋的茅屋,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是个小孩,但是我还是不喜欢那透着不吉祥和悲戚的破屋。外面和屋里隐秘的生活之间没有缓冲的余地,直接呈现出来的房屋结构,实在是令我羞愧难当……因此,我总是萎靡不振,面对一些琐事也鼓不起勇气,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孩子,遇上电闪雷鸣的天气,也会钻进壁橱里的胆小鬼……造成我各色各样的劣等感的背景,就是没有大门和篱笆墙的破屋子。③金周荣:《走好,妈妈》,第44、44、103-104页。
有想象力的哲学家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当中指出“家保护梦想,家守卫做梦的人,家可以使我们安宁地去做自己的梦”,“家是人类最初的世界”,“如同性急的形而上学者主张的那样,人类在‘被抛向世界中去’之前,会搁置在叫作‘家’的摇篮里”。④G. Bachelard,La poétique de l'espace,P.U.F.,p.26.显然,他在强调家的重要性,反思了家与人类想象力之间的关系。当然巴什拉在这里提及的家,是指有阁楼,有地下室,拥有很多间屋子,拥有宽敞庭院的家,令人遐想连篇、错落有致的洋房。在这样的房子里度过童年时代,就能够在自己的空间里陷入遐想,会把那里当作可以远离世界,保护自我的安全地带。
与之不同,“外面和屋里隐秘的生活之间没有缓冲的余地,所有的一切全都直接呈现在外的房屋结构”,令处在童年时期的主人公因自家简陋肮脏而感羞愧,甚至变成了胆小怕事儿的孩子。巴什拉认为家对人类来说是根本的栖息处和避难处,它“保护人类不受自然暴风雨和人间暴风雨之害”,⑤G. Bachelard,La poétique de l'espace,P.U.F.,p.26.但是,少年主人公却告白自己成了“遇上电闪雷鸣的天气,就会钻进壁橱里的胆小鬼”。即便是少年可以躲进壁橱里面,但毕竟壁橱不是他的房间,而且躲进壁橱还要冒着被妈妈严厉责骂的风险。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的少年谈不上属于自己的甜蜜幸福的美梦,只能天天在外面,不管是市场,山间小路,还是河边不停地游荡。这应该是探索金周荣游民作家意识形成的重要依据。《捕鱼者不毁芦苇荡》中主人公第一次发现镜子的地方不是屋子内,而是外面的事实也耐人寻味,因为自我形成过程中的“冬季阶段”里,主人公比起屋内更熟悉的旅途中的经历。《走好,妈妈》的主人公在“弟弟出生之后,我经常跑出家门,无所事事地蹲在别人家屋檐下像寒风中的树那样发抖”,①金周荣:《走好,妈妈》,第153、180、205、244、258、265页。这在证明妈妈再婚以及弟弟出生后,主人公不在屋子里陷入自己的美梦,而在外面徘徊的次数变得更加频繁。
妈妈接来新爸爸的选择成了灾难,是因为我的内心由此滋生了羞耻心。那就像脚后跟长成的茧子一样,怎么弄都没法消除痛苦的印痕。阴暗潮湿的屋子,无法缓和的矛盾,仿佛遭了抢劫一般的痛苦心境,面对两人真实的关系实在令我极其难堪,简直就是难以承受的事情。我的十岁光景,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枯萎干瘪。②金周荣:《走好,妈妈》,第153、180、205、244、258、265页。
这段引用部分,恰好说明了妈妈的再婚正是给胆小怕事的少年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的决定性事件。十岁大小的少年不仅无法理解“妈妈接来新爸爸的选择”,甚至认为“面对大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件令自己难堪,难以承受的事情。妈妈的再婚将少年的十岁阶段,弄成了缀满灾难、不幸的阴暗、悲戚的时光。少年顺其自然地要报复自己造成如此创伤的妈妈。“如何能让妈妈感觉到撕心裂肺的后悔和痛苦呢?只要能在妈妈的内心钉下一辈子都无法洗刷的耻辱的钉子,上学之类的事情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③金周荣:《走好,妈妈》,第153、180、205、244、258、265页。少年主人公能够让“妈妈感觉到撕心裂肺的后悔和痛苦”的事情,就是辍学,然后远走高飞。而且,少年的这种假想实现的迫切性在于,离家出走的确能够不再去见那憎恨自己,经常体罚自己的老师。
报复妈妈和新爸爸的办法……只有远走高飞,我唯一的报仇手段只有这样……对我来说,走向外面的世界只有停留在想象当中,因为,那伴随着恐惧。但是……我也自有胆大和无所畏惧的一面,所以,对离家出走的自信开始摇动了我原来的恐惧。④金周荣:《走好,妈妈》,第153、180、205、244、258、265页。
少年试图报仇的对象不仅是爸爸和妈妈,对自己实施无情体罚的老师和孤立自己的小伙伴都在报仇之列。但是,因为内心对离家出走的恐惧,报仇行动迟迟无法实现。经历那种恐惧和自信的矛盾之后,少年终于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了离开家到处游荡的日子”⑤金周荣:《走好,妈妈》,第153、180、205、244、258、265页。。孤独和艰难的游荡生活当中,他领悟了只能靠着谎话才能维持生计。因为不说谎,没有一个人会关注自己。
在《走好,妈妈》里主人公强调自己是十五岁那年离家出走,但并没有讲述离家出走之后所经历的磨难和痛苦。读者只有通过主人公办完妈妈的葬礼之后,与姐姐说的那句话,即,“伴着我长大的只有愤怒和酒精”,揣摩他度过了多么艰难的日子。听了弟弟这自我解嘲般的话,姐姐说出的话对理解金周荣所有的成长小说的主题和关于人生的感悟都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小时候的记忆就像刀刃一样,能割破了舌头。人们在雪地里抓捕野狼的时候,就把沾了动物血的刀刃,倒插在野狼经常出现的路口。深夜路过的野狼发现沾着血的刀刃,就一整夜在那里舔舐那血迹,等到天亮的时候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也流没了,就那么倒在那里死掉。这都是传说的,不知道是真是假,可有点道理吧。你都这么大了,还藏着那么多小时候经历过的痛苦和创伤,你看到的世界也只有痛苦创伤……你离家出走之后的那些经历,如果全都搁在肚子里不去忘掉,那留下的只有抱怨。你说的愤怒与酒精伴着你走到了现在,那等于是在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任何人。⑥金周荣:《走好,妈妈》,第153、180、205、244、258、265页。
姐姐的上述一席话,不由令人联想起前面提过的本雅明《说书人》中的一段话。本雅明认为,故事真正的本性是不管公开的和暗示的,都蕴含着有益于人生的信息,其有益成分不仅符合道德规范,而且很有实用价值。说书人也不仅仅是单纯讲故事的人,而是通过格言警句忠告和提醒听众的人。①瓦尔特·本雅明:《瓦尔特·本雅明文艺理论》,第169页,潘星完 译,首尔:民音社,1983。《走好,妈妈》正是通过姐姐的上述一段话,提醒读者爱心在人生历程中的重要性,那种爱心应该是等同于妈妈之爱的道理。同时,这又是针对金周荣自己在《洪鱼》“题记”中的固定观念,即,游牧民“甚至痛苦与憎恨也随身携带”的批判。这应该是通过妈妈的一生和去世而获得的作家自己的反省。我们无法获知姐姐的那一席话,令主人公得到了怎样的感悟,但是,“题记”中的话,即“是妈妈让我彷徨于自由市场般的世界,去诅咒它,而我却厚颜无耻地生活在那个世界,在接踵而至的恐怖中战战兢兢”,但是,“就是那些经历才是妈妈赋予我的自由的时光”,从中我们可以获知作家也只有通过妈妈的过世才能够领悟那些道理。
5.代结
金周荣在《走好,妈妈》的末尾安排了“作家自叙”,使作品中主人公和作家发生某种联系,比如作家通过“自叙”来解明作品主人公没有理解的“姐姐”的那一席话,从而作品中的人物与作家变得浑然一体。从这点上可以说,小说的叙事并没有在“作家自叙”之前结束,而是一直到“作家自叙”才得以完结,而这种结构与作家前面的三部成长小说截然不同。前面三部作品中的“作家自叙”都放在叙事开始之前,与小说内容并无直接的联系,作家和主人公是分离的,作家的话和主人公的叙述也从时间上断绝。比如在《捕鱼者不毁芦苇荡》的“作家自叙”里,“小时候看起来无限美好的东西,能够重新照原样恢复得了吗”这一句,说明作家的幼年时代和主人公是完全分离的。还有,在《洪鱼》里“甚至痛苦与憎恨也随身携带”的游民可以认为与作家等同,但是游民作家和少年主人公的立场却又是断绝的。另外,《鳀鱼》的“作家自叙”则如“鳀鱼俨然比鲸鱼更加高大,更加超脱”之句,更像是诗化了的散文,虽然有益于对小说主题象征意义的解释,但与小说情节依然不可能发生关系。但是,《走好,妈妈》里的“作家自叙”却摆设在作品的末尾,令读者不禁产生作品的情节在延续,主人公与作家相融于一体的感觉。
前面三部成长小说与《走好,妈妈》的文体、结构也完全不同。《捕鱼者不毁芦苇荡》按照作家再现童年时代美好回忆的意图,其内容与其说是少年贫穷不幸境遇的如实写照,不如说是更好地展现了孩子们纯真无邪的世界;《洪鱼》的主人公始终如一坚持小孩的视角,既细致又严谨,但是小孩理解大人们的世界上有一定的局限性;《鳀鱼》因没有具体描绘现实中三个人物的生活,因此不像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倒很像寓言小说。但是,《走好,妈妈》里小孩的视角和大人的视角结合得恰当,现实生活的叙述和回顾性叙述的连续性和紧张性相互交汇,作家从正面直视自己过去的意图通过写实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走好,妈妈》将前面三部成长小说的小孩视角成功转换成大人的视角,给读者展现了小主人公离家出走的意志终于得以实现。但是,仅此无法判断作品中主人公的离家出走与作家自身的经历吻合程度。即便如此,可以明确断定的是作品中主人公离家出走后所经历的艰辛、还有“不说谎无法生存下去”的体验与游民作家小说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根据卢卡奇和戈德曼关于小说的定义,小说是在堕落的世界里用堕落的方式追求真实的谎言,那么,金周荣作品中的主人公离家出走后不说谎无法生存下去的陈述,也就与理论家的主张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在金周荣的成长小说里最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就是“我”与“妈妈”的关系。《洪鱼》从“我”的视角细致地叙述了“我”与“妈妈”之间的爱憎关系,但是,尚没有达到真正揭示“妈妈”真面貌的阶段。小说的末尾,妈妈翘首以待的爸爸回到了家,而妈妈却离家出走,从而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走好,妈妈》不仅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疑惑,随着原本模糊的真貌也得以揭开面纱,给读者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感动。那么,这个感动究竟具体源于何处?是领悟了自己痛苦的经历和游荡的日子就是妈妈留给自己的自由时间?还是即便遭受男人的蹂躏、牺牲自己也不埋怨任何人,努力克制自己度过一生的妈妈的牺牲精神和人生态度?我们似乎没有必要急于去找其根源,因为“作家自叙”里的一段话——“我自负为离开家乡后所领悟到的爱、誓言、关怀、谦逊等耀眼的词汇和高贵的修辞,都只不过是为了遮掩谎言和缺陷的虚张声势而已。”——在不断地刺激我们去读作家的作品的欲望。“作家自叙”中体现的自我反省,体现了无论在任何时空点上也不止步的、一个游民作家的自由奔放的态度。通过作家的上述作品,我们看到了作家反省羞涩、荒芜的幼年记忆,试图超越那没有梦想的过去,鼓足勇气去面对现实的勇气。
【译者简介】权赫律,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吴生根,韩国文学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家、国立首尔大学名誉教授。一九八三年在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获得文学博士,一九七〇年获得韩国《东亚日报》新春文艺评论奖而步入文坛,著有多种文学著述以及评论集,曾获得韩国现代文学奖、大山文学奖、于湖学术奖、大韩民国学术院奖、片云文学奖、八峰文学批评奖等多个重要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