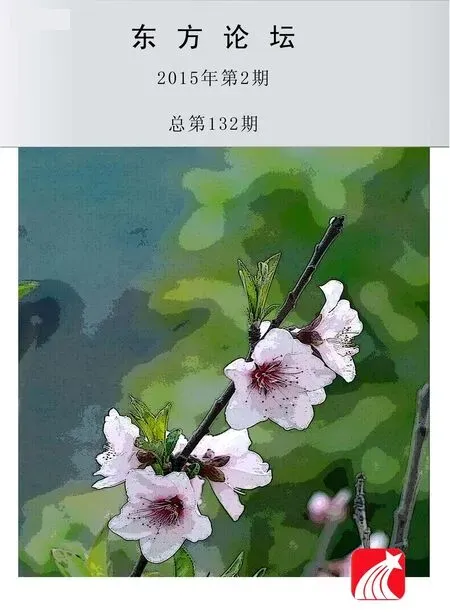弗·施勒格尔的反讽方法论
摘 要:弗·施勒格尔对浪漫主义有重要影响,反讽是他的重要概念之一。修辞学上的反讽与浪漫反讽是截然不同的,浪漫反讽具有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地位,它虽与形式逻辑相对,但却不是完全的非理性。对弗·施勒格尔来说,反讽是解决二元对立,达致统一哲学的唯一路径。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5)02-0071-04
收稿日期:2014-10-09
作者简介:王铜静(1985-),女,河南开封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
“反讽”在德国浪漫派那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甚至进而成为一种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对此风尚,思想界褒之有之,贬之亦有之。浪漫反讽的始作俑者一般认为是弗·施勒格尔,其哲学思想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费希特哲学,另一个则是苏格拉底式反讽。通过对弗·施勒格尔在《雅典娜神殿断片集》中的言语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反讽作为一种方法论几乎贯穿了他哲学论述的始终,这反映出弗·施勒格尔与传统冰冷理性的针锋相对,也预示着传承这一衣钵的哲学流派将与传统理性哲学走向不同的哲学视域。
一、反讽修辞与弗·施勒格尔的浪漫反讽观
反讽作为一种修辞,在艺术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多有运用,中国古代就有许多反讽诗,诗人在政途上不得意时,喜欢借此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懑,比如唐代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表面的冠冕堂皇与真相的委琐一相对照,嘲讽的意味显而易见。寓言中更是多用反讽修辞,比如庄子的寓言《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则显示了表面上聪明与实质上愚钝的冲突。一言以蔽之,反讽就意味着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表面意义的冲突。
这种反讽修辞手法在中西都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但在德国浪漫派那里,他们对“反讽”概念进行了改造,使其从修辞学概念扩展为一种艺术创作原则。以至于历史上将弗·施勒格尔为其代表的浪漫派的反讽称之为“浪漫反讽”。弗·施勒格尔作为德国浪漫派开山人物,非常欣赏反讽在文学作品中的奇妙作用,“有些古代诗和现代诗,在任何地方都完全无例外地散发着反讽的美妙气息”。但是哲学上的反讽是不同于修辞学的,因为浪漫反讽并非像修辞学那样建立在嘲讽的地位上。浪漫反讽不是一种简单地情绪宣泄手法,而是一种表面戏谑而实质上严肃认真的态度。哲学意义上的反讽虽然不乏丑角的演出,但在本质上是对无限的探问,“无限提升自己,超越一切有限,甚至超越自己的艺术、美德和天才” [1](P24)。
一般认为弗·施勒格尔的反讽理论有两个来源:苏格拉底式反讽与费希特哲学。苏格拉底式反讽可概括为:对话者在苏格拉底的请教和追问下暴露出其观点的自相矛盾;就苏格拉底而言,他故意自我菲薄,自称无知,却教人“认识你自己”。弗·施勒格尔对此评价到,它“是唯一完全非任意的,完全有意识的伪装”,但“反讽并不欺骗任何人”,虽然它“伪装很深”,却“严肃”“坦白公开”“肝胆相照” [1](P39)。
弗·施勒格尔等浪漫主义者对苏格拉底式反讽进行了根本改造。欧文﹒白碧德认为两者的反讽只具有表面相似性,即对他所属时代的信仰和习俗的偏离。然而,苏格拉底式反讽是有中心的,并且他的偏离是因为“比其他人膨胀的知识幻想更具有中心性”;而浪漫派的反讽是离心的,这意味着浪漫派总是借助于想象“超越了在他的时代被认为是正常和核心的东西……不仅如此,他还必须冲破他自己已经建立的任何中心”,这种无休止的超越的一个重大危险就是“它不仅冒犯某种特殊的习俗,而且还冒犯人类自身的正确判断”[2](P144-147)。
弗·施勒格尔从费希特哲学那里吸取了反讽理念中的超验性,构建了超验的诗的概念。费希特超验哲学致力于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并赋予自我进行创造性行动的可能。而这一点,正是浪漫反讽所需要的无限提升自己、超越一切有限的本体论基础。对于这种改造黑格尔并不认同,他认为弗·施勒格尔的反讽完全失掉了客观性“反讽善于把任何客观的内在的内容,变成为无价值的和空虚的东西” [3](P76),由于它以任意性和偶然性对待定义,最终落入了空幻。这种评价当然是源于黑格尔对客观精神的追求,但也正显示出了浪漫反讽对主体性的强调和重视。
批评弗·施勒格尔的反讽“离心”“失掉客观性”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弗·施勒格尔的思想正是基于对分析的、机械的哲学思维方式(特别是自笛卡儿以来)的不满。他正确地指出,“反讽是悖理事物的形式”,“反讽的东西是跟被看作不矛盾的东西的理性相对立的”。他并没有完全否认逻辑推理,而是认为世界从整体上来看,总是“诡论式”的,因此,他有理由认为“反讽”作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当“哲学成为语文学,语文学成为哲学,科学成为艺术,而艺术成为科学”,弗·施勒格尔设想这时最合适的认识方法只能是浪漫反讽。反讽在他那里意味着“逻辑事物范围里的美”,“非系统地思考哲理的特定方法”。 [3](P57-58)
二、弗·施勒格尔的反讽与逻辑的关系
弗·施勒格尔的浪漫反讽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而是与一种超验本体论密切相关。浪漫反讽与想象密切联系,它追求以自由的想象来取代枯燥的逻辑推理,特别是用来解答那些总是困扰着人类的哲学问题,比如,宇宙的界限、上帝的存在、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等等问题。
弗·施勒格尔认为可以把反讽定义为“逻辑事物范围里的美”,并且通过比较认为,形式逻辑是一种“稀薄的和空泛的”理性,而反讽是一种“稠密的、浓烈的”理性。在有限事物、经验世界那里,弗·施勒格尔并不反对形式逻辑,但是对宇宙整体的考虑,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思考,只能借助反讽。反讽不同于形式逻辑之处,在于它不但承认存在的现实矛盾,并且力图沟通有限与无限。
反讽又是一种日常生活逻辑。弗·施勒格尔许多时候用“机智”一词表示此种逻辑,但它们有些用法上的不同,浪漫反讽着重指一种表达手法,强调对语言、各种符号的借助,以达到对无限的关注;而机智的含义要丰富灵活得多,甚至包含着反讽手段在内,它侧重指一种思考品性,如当弗·施勒格尔说康德缺乏机智时,是认为康德太古板、太遵从机械的形式,酷爱界开一切。虽然有这种区别,这两个概念实在有着根本上的共同,特别是对于弗·施勒格尔来说。这两个词在许多场合下表达同样的意思,即:反讽或机智作为一种日常生活逻辑,必须容纳现实中的矛盾。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智慧,为了躲避冗长枯燥的推理,反讽进入了一种“自由的形式”——长篇小说,“长篇小说(Roman)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苏格拉底式的对话。”[1](P19)
弗·施勒格尔将精神分为三个阶段,机械的理性、化学的机智、有机的天才。反讽是“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经常交替” [1](P59), 包含着“无休止的冲突的感觉”,是“化学逻辑” [1](P40)。于是反讽具有化学的特征,混乱的冲突、对立面的分解与结合,还伴随着自由想象的碰撞与火花。“对永恒的灵活性和无限充实的混乱的清醒认识” [1](P165),这就是反讽。这恰是浪漫主义的理性,它抛弃形式理性,用想象重新置身于美的迷茫、混乱中。
三、弗·施勒格尔的反讽方法论
虽说浪漫反讽是浪漫主义的理性,但弗·施勒格尔并不一般地反对形式逻辑,他说“逻辑学既不是装饰,也不是工具、表格,也不是哲学的插曲,而是一门与诗和伦理学相对立的、与他们地位相当的实用科学,产生于对积极的真理的要求和一个体系之所以能成立的前提。” [1](P68)但他更加强调对形式逻辑和实证精神进行限制,“因为四则运算和精神的实验物理学的精彩之处,只能在形式和材料的对比中。” [1](P64)不管是数学还是实验科学,都是在一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对这些前提的追溯很快就会达到一种止步不前的境地,因为在那里遭遇到了无限。无限在形式逻辑那里无法思考,并遭遇到各种悖论。
对于这种困难,康德的处理方式是限制理性的运用,将有些问题交给信仰去处理。弗·施勒格尔则继承了古希腊的机智,他确实看到了古人的一些高妙之处,因此,他十分推崇苏格拉底式反讽在哲学思考中的作用。针对有些人认为哲学局限在逻辑形式中,弗·施勒格尔反问道“逻辑的宪法完稿之前,临时性的哲学不可能存在吗?直到宪法获得通过而生效之前,全部哲学不都是临时性的吗?” [1](P102)他对古希腊神话和历史的重视也说明了他无意限制人的理性,也不赞成在理性、情感、意志之间作泾渭分明的区分。反讽作为一条路径,朝向一种理念,“理念是一种通过自己的完整性达到反讽的概念” [3](P62)。“反讽的”作为一个形容词,意味着“绝对的对立的绝对综合,两个冲突着的思想自行产生着经常的交替” [1](P75),可以称之为反讽辩证法。
哲学主要探讨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而方法论则关注怎样来获得这看法和观点。方法论的一个特色,特别是笛卡儿以来,就是从怀疑和分析入手,以自然科学、数学知识为基准,借助形式逻辑的工具,辅以适当的想象,展开哲学的求索。如上所述,弗·施勒格尔并不一般地反对形式逻辑与经验主义,他也不是完全地反对分析与怀疑,他认为如果“把任何分析都视为破坏享受” [1](P27),那么“胡说八道大概堪称对最崇高的作品的最优秀的艺术判断了” [1](P22)。但是他对独断论与彻底的怀疑主义都有批评,对于前者,他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喜欢而且能够道出一切,毫无保留,把他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这样的作家是不足道的”;对于后者,他说“根本不存在一种名副其实的怀疑论”,因为“它自身内部的逻辑将把彻底的毁灭引向自身” [1](P131)。面对诸多思想家要以数学为典范重建一切理性的要求,他也不以为然,“对数学的崇拜,呼吁健全的人类理智,乃是不完整的、不真实的怀疑论的病相。” [1](P131)这一点也显示出浪漫派与理性派的不同,前者以诗为典范,后者以数学为典范。
为了能够言说这个世界,特别是在形而上的道路上,弗·施勒格尔从古希腊哲学与戏剧中找到了反讽,重新加以阐释,并认为相对于分析性的形式逻辑来说,具有综合性质的浪漫反讽技高一筹,“可以把反讽定义为逻辑事物范围里的美:因为凡是用口谈或笔谈都不能完全系统地沉浸于哲学的地方,就应当创造反讽,也需要反讽。” [3](P57)浪漫派要求在逻辑推理无能为力的某些哲学领域里,反讽应有很大作为,在这种意义上,反讽正是为浪漫派所借助的根本方法。
有人认为弗·施勒格尔的反讽,“将什么都不能干涉想象的自由游戏这一法则推向了极端” [2](P143)。其实,浪漫反讽虽很重视自由想象,但并不意味着毫无原则。弗·施勒格尔说“无论何处,人们若不自我限制,世界就限制人,于是人就沦为奴隶。” [1](P22)反讽方法中所不可或缺的“自我冲突”也不意味着绝对的任性,因为那将导致不自由的产生,从而“自我限制将沦为自我毁灭”。反讽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所要求的是“首先要给自我创造、虚构和热情提供活动场所,直至自我限制完成。”这正像理性方法论对怀疑精神和逻辑分析的要求。
反讽方法论反感空洞和乏味,“如果理想不具有古代神祗对于艺术家所具有的那样众多的个性,那么所有涉及观念的活动,就不外乎是用空洞的公式,玩无聊乏味又伤精费神的掷色子的游戏。” [1](P39)这种掷色子的游戏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纠葛和实际上的单调,正是严格理性生活的反映。反讽方法论的思维方式对此不满,它要求丰富性,进而要求哲学、科学、艺术的相互转化,它要求将人类文化的众多领域纳入思考或想象中,特别是在它们的隔阂之处。
反讽方法论还反对各种二元对立。当时,牛顿力学体系居于理性的主导地位,但其完整严谨的外表掩盖着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经验科学的实证典范背后又弥漫着神学影子,这可以说是逻辑理性与经验理性不完善的一个明证。浪漫反讽希望将理想与现实的分裂结合起来,“它产生于生活艺术感与科学精神的结合,产生于完善的自然哲学与完善的艺术哲学的融聚” [1]。在关于诗的论述中,这种要求表现得更加强烈,“有一种诗,它的唯一和全部的内涵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它作为讽刺,从理想和现实的截然不同入手” [1](P95),超验诗借助反讽,它本身又必须是反讽,在这里哲学与艺术,理想与现实得到了融合,分裂也以绝对同一的面目出现,并且以蕴涵着现实的非理智的矛盾为前提。
综上所述,传统理性派非常注重形式理性的地位,并将之上升到独一无二的高位,而早期浪漫主义者弗·施勒格尔却不满意形式理性所导致的局限性,他重新解读了反讽,并对之非常重视。修辞学上的反讽或者说是嘲讽与浪漫反讽是有根本不同的,前者只是文学上的小伎俩,而后者却预示着对世界的一种方法论态度。浪漫反讽与逻辑虽然看似相悖,但却也不是截然反对,毋宁说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互补。弗·施勒格尔将浪漫反讽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思考方式,甚至比形式理性具有更根本的地位。对弗·施勒格尔而言,反讽与机智、想象、艺术以及特别被看重的“诗”(超越诗及其他)等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弗·施勒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批评和对反讽的推崇,其实是要求以截然不同于理性派的方式解释无限、世界和人生,并籍此反对二元分裂,追求一种综合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