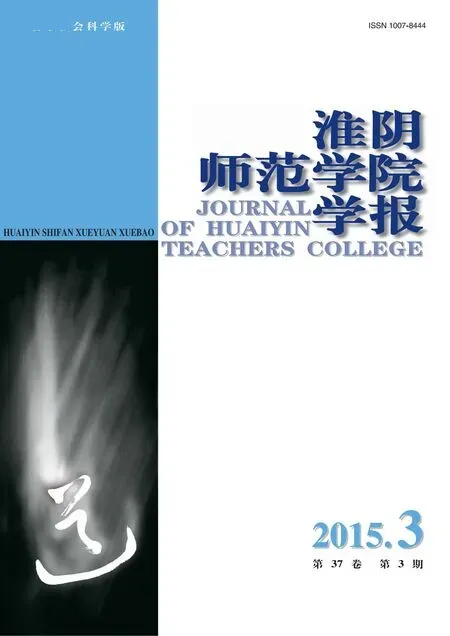生态批评视野下关于《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模仿
蒋永影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一、生态批评视野下的悲剧性模仿
在西方文明史中,人类是由上帝创造,上帝在七日之内完成了创世纪的工作,并安排人类负责管理自然中的一切。人和自然的关系由此被注定成为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自此开始了。到了中世纪时期,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教会神学变得异常强大,上帝中心论的思想贯穿了整个漫长的中世纪。紧接着,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对人的重新发现使得人文主义思想光芒万丈,理性的人类再一次成为万物的中心。由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革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当人类为自己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时,殊不知一种反中心论的思想已经悄然而起。由此可见,无论西方文明处于哪个时期和阶段,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由某种中心论思想支配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已经侵入生命的各个领域,科技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本是属于自由领域的伦理审美活动也变得异常僵化和教条,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受到了文明的戕害。此时,法国的卢梭成为反文明的先驱,其后一大批文学家也提倡回归自然,崇尚原始主义。
在文学领域也是同样的情形,在现代主义文学出现之前,以往的任何文学形式都是围绕着某种中心主义的思想而进行创作。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以“神、人、半神半人的英雄”为中心,呈现的文学形式是神话、悲剧或史诗。在中世纪,以神和上帝为中心的教会文学盛极一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使得人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主体性,歌颂人自身的文学占据了主导。工业革命之后,浪漫主义文学向自然和生态转向,拒绝再以人类为中心,而是带着一种反文明的倾向。于是,文学领域内的生态文学、文学批评中的生态批评由此而萌发。
18世纪开始兴起的生态批评主张用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主导的文学研究范式代替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的文学研究范式,从而将文学与自然联结,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生态批评要求文学创作必须具有生态学的视野,认为文学批评家必须建构一个完满的生态诗学体系,并且无论以何种语言定义这样的生态诗学体系,它都意味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次超越,批评家们试图亲近生态。在提出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时,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已经有了自己清晰的建构意向,他试图将生态学视野引入文学研究,让文学与自然生态重新联姻,寻找人类和自然的原始联系,赋予文学批评以抵抗生态危机的力量。
在诗学领域,西方关于文学的主流看法是模仿论,由于人类长期处于宇宙的中心,所以模仿的对象主要是人。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他认为悲剧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1]。在这里虽然模仿的是行动,但行动的主体都是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看法和他的美学思想是契合的,他贯彻着美的有机统一性原则,其核心范畴便是遵从中心化和秩序化的统一。他的诗学思想影响深远,以后文学创作中的“模仿说”都可以在此追根溯源。在黑格尔那里,他认为悲剧中冲突的双方都在坚守着各自立场的正当性,他们毫不妥协的情势只能最终导致双方毁灭的结果,只有双方调解和包容,才能有永恒正义的诞生和存在。在这里,悲剧模仿的中心仍然是冲突中的双方,即人。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几乎被认为是关于悲剧的理论,其地位不可撼动,很少有人敢对此作出挑战。而西方生态批评学家米克则持如下观点:
悲剧展现了人的潜在力量和伟大,而喜剧则揭示人的凡俗品格。悲剧观念只有在人果真超越其自然环境和动物起源时才是正确的,但这个假定在我们的时代里受到强烈质疑。尼采以降的哲学呈现了人道主义理念论的贫困,进化论生物学发现了人的动物性,现代心理学则表明人被许多比伟大观念更强大的力量所驱使。当下的环境危机就是由于人太看高自己而产生的。悲剧性视角实际上指向一种对人的力量和未来的自以为是的乐观主义,这已经导致文化的和生物学的灾难。现在,为了使自己和其他物种幸存下去,我们应该寻找可以替代悲剧观念的东西。[2]
米克的观点似乎已经对传统悲剧模仿的中心主义模式提出了挑战,但传统的悲剧性模仿却仍被后世的悲剧或多或少继承,从古希腊开始,直至现代主义文学出现,其间当然包括《哈姆雷特》,但莎士比亚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生态观的写作被凸显出来。
二、《哈姆雷特》中复杂的生态观
《哈姆雷特》是对悲剧性模仿的中心主义观念的继承,尽管这种观念在19世纪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已经消亡了。《哈姆雷特》剧中的生态观呈现出某种复杂性,有着关于生态观的种种转向趋势,下面分别从自然与文明、自然与人类、自然与女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自然与文明——疯癫与理性的交汇呈现。这与尼采关于疯癫的审美人生态度有些不谋而合。事件的开始是丹麦宫廷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老国王突然驾崩,国王的弟弟克劳狄斯夺取王位,并娶了寡嫂,作为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在寻见老国王的灵魂时,得知了一切真相。他一下子陷入了家国的不幸之中,理想的破灭让哈姆雷特看清了人生的悲剧本质,就算人生是一场悲剧,他也要有声有色地演下去,并且不回避人生的痛苦。他认为“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很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3]335。之后,他便决心替父报仇,这一强大的意念在他的头脑中盘旋,时刻控制着他的思想。这一理性的动机在那么一个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宫廷之中,很难真正实现行动上的复归。为此,哈姆雷特试图用一种近乎疯癫的态度和冲动来拯救人生,他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交织着痛苦和狂喜的酒神状态,在癫狂中暂时忘却现实的苦恼,获得了与本体的沟通。如果说理性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那这就意味着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而代表着酒神精神的疯癫在尼采那里则是一种陶然忘我之境,破除了中心主义的模式,提倡一种更高的审美境界的复归。从这个角度说,这也是剧中生态观值得商榷之处,因为真的理性和假的疯癫在哈姆雷特那里处于一种交汇的状态。主人公的话语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甚至连对手克劳狄斯听了之后都对他是否真的疯癫表示怀疑,并且数次想试探他。这种理性与疯癫的交汇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态观的写作转向在出现之初,还不能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和自觉的形态,它总是与旧有的人类中心主义模式时有交融。但当人类试图以文明征服自然,以自身的意志力征服自然成为一种强迫症时,不得不说这又是人类自身的另一重悲剧。生态学的关联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被引入剧中,人类中心论实际上是一种悲剧性的弱点,在这里莎士比亚试图重建人与世界之间的原始联系。即使哈姆雷特有强大的理性,他也无权将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所以暂时选择在“醉”的状态下与自然达成了本体的沟通。
其次,自然与人类——忧郁与意志力的对决。作为人文主义时期的丹麦青年王子,哈姆雷特有着这样过人的形象:“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3]332按照莎士比亚如此的描述,哈姆雷特应该是一个具有强大意志力的光辉人性典范,对凡事都有绝对的控制力,一切以自我的行动和判断为中心,秉承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光辉,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性格忧郁和犹豫的王子,而不是一个意志力强大的悲剧主人公,他的行动力和判断力都够不上果断,常常以外在的因素和导向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在剧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内心独白活动,哈姆雷特的内心独白居然达六次之多,其中最典型的一段是,当克劳狄斯在祈祷之时,哈姆雷特犹豫是否在此时动手报仇,思前想后,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行动,此时主人公的意志力已经不再能够战胜种种局外因素,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逐渐被驱逐到边缘,外界因素的制约反而占据了上风。莎士比亚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他有时身怀人文主义的光辉理想,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推到极致,将人类视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有时又对人类自身的角色产生种种怀疑和不确定,并借哈姆雷特之口发出了悲叹:“可怜的我,却要承担起扭转乾坤的重任”,“可怜”二字生发出对自身角色的悲悯,也是对人类处于宇宙中心地位的质疑。“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生存和毁灭是对人类存在意义作出的探寻和质问。此时的莎士比亚已经对悲剧性模仿产生了种种困惑,这也是他生态观写作开始发生转向的标识。
第三,自然与女性——第三性的悬置。本真的奥菲莉亚崇尚自然和美好,她在剧中的出场都伴随着自然、河流、花草和泥土等一切美好事物,代表着自然的纯真和感性,她单纯,但是脆弱。这么一个天真柔弱的女性寄托了莎士比亚的某种生态学写作的理想。然而,对奥菲莉亚来说,生活的不幸马上接踵而来,心爱的人发疯使她心力交瘁,父亲被爱人误杀使她一蹶不振,最终变得彻底疯癫,并落水而亡,连最后的安葬也草草了事。美好的事物被莎士比亚安排了这样一个结局,从中不难看出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在生态观创作上的矛盾之处,他的自然理想与现实困境有着一定的不可调和性。美好而感性的事物都是脆弱的,他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了“女人啊,你的名字叫脆弱”这一想法。从传统的人文批评角度讲,虽然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但更确切地说是男性中心主义,柔弱的女性奥菲莉亚只能处于男性的摆布控制下,哈姆雷特对她前后不一的态度,父亲波洛涅斯对她终身大事的干预,甚至在死后,连两个掘墓人也对她的死冷嘲热讽。如果说自然以人类为中心,人类以男性为中心,女性以男性为中心,那么奥菲莉亚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便是介于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第三性,她更接近于自然,和自然有着类似的被统治和压迫的命运,自然被人类统治,女性被男性统治。但她因为人类的身份,还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和自然隔了一层。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得先向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进行挑战,但莎士比亚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关于此类思想还并不明晰,这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他为何安排奥菲莉亚落水的命运。
三、关于莎士比亚后期写作的生态观转向
悲剧性模仿认为人比其他事物都要高级,人处于万物的顶端,违反了生态文学观。生态主义的光芒将这一幻想彻底击碎,特别是19世纪达尔文的物种进化学说,让人类意识到自身并不比其他物种更高贵。因此,为了整个世界生态系统的和谐,人类必须接受自身物种平凡性的事实,接受自身不再是宇宙中心的事实,所以,放弃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成为一种必然,需要放弃悲剧性的模仿,转向更为谦卑温和的模仿,而带有喜剧性或正剧性因素的模仿则是其中之一。莎士比亚晚年的创作是一种不自觉的尝试,暗合了这一趋势。他晚年的传奇剧写作实际上是悲喜剧因素混杂在一起,“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4],这是莎士比亚悲剧的特点之一。在他晚年的传奇剧中似乎传递着一种快乐而温和的情绪,与悲剧时期的沉重迥然而异,虽然其中也不乏对黑暗现实的讽刺、批判和揭露,但明显温和冲淡了许多,因为在这些传奇剧中,他的宗旨是宣扬教义、爱、和解和宽恕。为了解决这一情境,他常常借助一些偶然性事件,或者是超自然的神力来使得剧中冲突的双方达成和解,这是一种适应和调和的艺术,力图在不摧毁参与者的前提下解决冲突,这正和生态的喜剧因素模仿不谋而合。
莎士比亚此时的转向还得要从《哈姆雷特》说起,该剧写于1601年,正是莎士比亚前期向后期转向的时期,在这一年,莎士比亚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动向,这直接使得莎士比亚在生态写作观上也有一个彻底的回转,由前期对人文主义的无上推崇,后期逐渐向低调处落笔,认为人本身并没有值得炫示之处。倘若想让万物处于和谐、完满和自然的状态,就必须让人从狂妄的状态转向谦逊,这样才会超越现实的种种限制,最终通向自由和完满。上述分析的《哈姆雷特》中关于生态观思想的种种张力和断裂,都表明了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思想矛盾和转变的趋势。
喜剧因素从生态主义的观点出场,它是一种喜剧精神,倡导着众生平等的原则,遵循和平、调解和适应的良性生态。而悲剧主义与此恰恰相反,悲剧精神倡导着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有着等级体系,动辄有冲突和征服的情境。这种悲喜剧二分的模式和方法为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开辟了重要的思想道路。继《哈姆雷特》之后,悲剧性模仿逐渐衰落,悲剧文学的高尚地位不复存在。不必为此而哀叹和悲悼,因为这是进化论式的选择,没有任何事物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包括人类自身。莎士比亚的后期创作转向了传奇剧,放弃悲剧性模仿在他那里成为一种可能。
[1] 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59.
[2] 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M].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167.
[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M].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4] 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