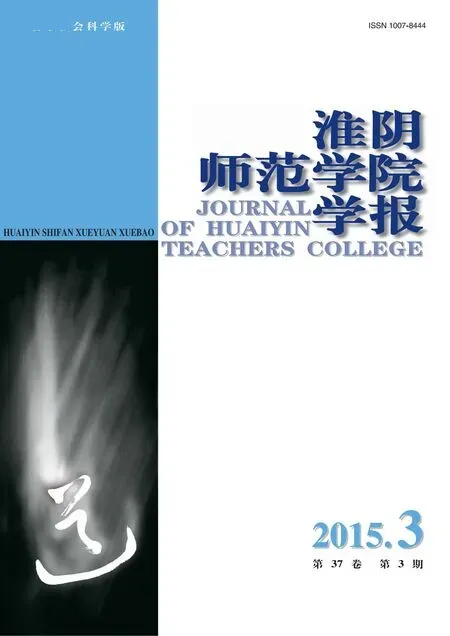《丁卯集笺证》商榷
周金标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中国古代诗歌注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长期的注释实践中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学术体系和规范,为今人有关古诗的注释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学术遗产。但如何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却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近日因为研究之需,粗粗翻阅罗时进先生《丁卯集笺证》(以下简称《笺证》)一过,深觉有必要重视这一问题。《丁卯集》是晚唐诗人许浑所著,元代和清代分别有祝德子《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集》、许培荣《丁卯集笺注》两部注本,但皆较简略。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丁卯集笺证》在此基础上作了较多开拓,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校勘,注者搜集了有关该集的各种版本,对重出互见诗以及佚诗进行考订,并对异文详尽比勘;二是集评,关于许诗的各种评论搜罗丰富,这个工作十分辛苦,但很有价值;三是考证,对许诗所涉之历史、人物、地理、名物等作出了较为认真的考证。
但该著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几乎触目皆是。笔者仅以前100页为例,列举较为重要的几大问题。
一、编排
别集注本历来以编年为佳,如《四库总目》即曰:“注本之善不在字句之细琐,而在于考核出处时事。任注《内集》,史注《外集》,其大纲皆系于目录每条之下。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1]编年体注本的主要功能,是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可以全面了解作者的生平遭际,反过来也可以通过背景知识,更深地理解作品。正因如此,清代对前代诗人的别集注本基本采用编年体。许浑的生平研究至今已较为成熟,罗先生亦有《许浑年谱稿》[2],应该将最新研究成果采纳其中,据此对许诗按年份或时段编排,并在解题中对时事背景等作出介绍。即使有一些诗篇暂时不能考定创作时间,亦可采取先编考定之作、另编未定之作的方式处理。但《笺证》完全按照旧版分体编排的方式,解题也基本满足于一般的人名、地名考证和文字校勘,对史实等材料付之阙如。这是本著的一个重大缺陷。
二、条目
注释条目的编列体现了著者对诗歌解读的深度,也是体现著作质量的重要指标。其中滥注和失注是值得重视的两个问题。
滥注是滥列条目,将简单易懂的知识点也作为注释的条目。古籍整理和注释重在专业性而非普及性,如果不加选择,势必造成篇幅臃肿,浅俗厌观。例如:《笺证》第2页“画舸”“回雪”“猿声”,3页“玉人”,7页“银河”,12页“诗僧”“雁门”,16页“素琴”,19页“寄世”“修身”“二毛”,21页“宫莎”,22页“袅袅”“三湘”,25页“断肠”,29页“素手”“玉壶”,33页“露华”,37页“烟波”,40页“袈裟”“别怨”,49页“陶彭泽”,54页“素衣”“穷巷”,55页“京洛”“断蓬”“易水”“白云”,57页“叠嶂”,58页“荆江”,62页“兰堂”,70页“武陵”,80页“函谷”“薜萝”,84页“坐禅”“天台”,87页“漏未残”,94页“五岭”,95页“翠娥”,96页“藤杖”,97页“蒲团”等,还有不少属于两可之列,皆专业学者甚至普通读者耳熟能详的词汇,大可不必列为条目。诚然《丁卯集》较为浅显,用典较少,但不能因此而硬凑条目,滥竽充数的结果必然导致水准降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余箫客《文选音义》注释的八条弊端,其中一条是“抄撮习见,徒溷简牍”,曰:“世有不知汉武帝、曹子建而读《文选》者乎?”[3]这对当代古籍整理者应有所启发。
与之对应的是失注,失注是注者不知有典而失察。如15页《晨起二首》其二“因知北窗客,日与世情乖”,“北窗客”明显用陶渊明“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的典故。20页《广陵道中》“山暝牛羊少”,暗用《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22页《洞灵观冬青》“露重蝉鸣急,风多鸟宿难”套用骆宾王《在狱咏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句式(49页《晨至南亭呈裴明府》“露重萤依草,风高蝶委兰”、95页《江楼夜别》“蕙兰秋露重,芦苇夜风多”亦然)。24页《送友人自荆襄归江东》“剑愁龙失伴,琴怨鹤离群”,后句失注,其实用“鹤琴”之典,古有《别鹤操》之曲,是抒发离情的琴曲。杨炯《幽兰赋》“鹤琴未罢,龙剑将分”正与许诗两句相合。按许培荣《笺注》曰“琴怨断弦。《琴谱》有《别鹤引》”[4]。《笺证》当引。27页《孤雁》“霄汉力犹怯,稻粱心已违”,其实套用谢灵运《登池上楼》“薄霄愧云浮”“退耕力不任”两句。29页《寓怀》“争忍嫁狂夫”,“狂夫”乃无知妄为之人,用《诗·齐风·东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41页《发灵溪馆》“千岩万壑中”,乃用《世说新语》顾恺之“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语。45页《送李定言南游》“重惜芳尊宴,满城无旧游”,袭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意。51页《题张司马霸东郊原》“更欲寻芝术,商山便寄家”,注者对“芝术”“商山”分别注释,其实“商山芝”乃古诗文习见之典,两句不可分割。55页《送从兄归隐蓝溪二首》其二“京洛多高盖,怜兄剧断蓬”二句,化用杜甫《梦李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75页《献白尹》“褐宽乌帽斜”,用孟嘉落帽之典。86页《留赠偃师主人》“晓灯回壁暗”,化用何逊《临行与故游夜别》“晓灯暗离室”。93页《津亭送张崔二侍御散北归》“津亭堕泪频”,用羊祜死后百姓见碑而落泪之典。97页《霅上》末句“云树满陵阳”,暗用“云树之思”之典。99页《下第别杨至之》“逢君话心曲,一醉霸陵间”,暗用李广醉霸陵的熟典,表达怀才不遇之情,而作者虽注释“霸陵”,却仅作为地理名词。类似的暗用、化用当还有不少,不及细检。造成失注的原因多样,但作为古籍整理,应当抱持谨小慎微的态度。
三、穿凿
穿凿之弊,历代多有,《笺证》亦不能幸免。如第7页《早秋三首》其一“迢递白云期”,注引陶弘景《山中》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云云,其实用《庄子·天地》:“乘彼白云,游于帝乡”之“白云乡”之典。13页《寄契盈上人》末句“汤师不可问,江上碧云深”,两句皆平常之语,至多如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结语有味而已,但注者却引汤惠休《怨诗行》“妾心依天末,思与浮云长”,又引江淹《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更是治丝而棼,多歧亡羊。其实“汤师”只是比拟契盈,注者徒以“碧云”字眼而引二人之诗。20页《广陵道中》“城势已坡陀,城边东逝波”,写景之语,亦寓今昔沧桑之感,但注释“逝波”却引《论语》“子在川上曰”云云。其实后世用《论语》此典,多为珍惜时间之意,与此凿枘不合。30页《洛中游眺贻同志》“桥势排高凤”,注曰:“指洛阳天津桥。《寰宇通志》卷八五《河南府上》:天津桥在府城外西南,架洛水,隋炀帝建云云。”但从诗中丝毫看不出此桥即天津桥的暗示。33页《长安旅夜》“掩瑟独凝思”句,注引阮籍《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且不论两者感情不类,前者表示客愁,后者表示苦闷,单就“掩瑟”和“弹琴”而言,字面、意义亦皆无可比之处。39页《汤处士返初后卜居曲江》“黄槿四时花”,注曰:“木槿花朝开夕凋。李颀《别梁锽》:‘莫言富贵长可托,木槿朝看暮还落。’”但黄槿与木槿并非一物;且上句“绿琪千岁叶”与本句“四时花”,皆表示祝福之意,所以引李颀诗十分不妥。42页《留题杜居士》“应知此来客,身世两无情”,注“身世”曰:“身,佛教所谓身持戒行。《涅槃经》第二十八:‘身戒心慧,不动如山。’世,世事俗法。”按句意谓俗客至此,全忘身世烦扰,“身世”指本身和身外,亦无深意。而注者徒以题中“居士”字面,竭力挖掘“身世”的佛教意涵,但“居士”并不一定就是佛徒,隐士、道士乃至雅士皆可。57页《思归》“山寒谢守窗”,注“谢守”为谢朓。按“谢守”当为谢灵运,《登池上楼》“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写其久病登楼,临窗眺望远山。64页《送李暝秀才西行》“停车山店雨,挂席海门涛”,注“海门”曰:“在井口。《嘉定镇江志》卷六云云,又卷二一云云。”按“海门”指通海之处,与上句“山店”一样,皆属泛指而非实地。77页《茅山赠梁尊师》“云尾何年客,青山白日长”,注“云尾”曰:
王士性《广志绎》卷二:“《金陵志》:‘茅山与蜀岷、峨相首尾,蒋山实其脉之尽者。’固然,然茅山不得与岷、峨首尾也。为岷、峨尾者,乃天目耳。句曲亦从天目发龙。”书棚本、祝德子订正本作“云屋”。云,蜀刻本校“一作雪”。
此条注文长达百余字,注者据题中“茅山”字眼,试图从《广志绎》中寻找有关茅山的材料。且不论以明人地理书来注释唐代作品,已经稍觉不妥,况且所引文字并没有厘清“云尾”。其实很简单,“云尾”乃“云屋”之误,校勘已经指出,“云屋”乃隐者之居,但注者生拉硬扯,还是不得要领。又本诗“上象壶中阔,平生梦里长”,注“上象”曰:“犹言世界。《易·系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按“上象”或不词,或为校勘问题,但定与所引《易·系辞》毫无瓜葛。
四、体例
中国古代诗歌的注释规范,大部分针对注文,因为注文是注释的核心和主体。引什么,如何引,在注释实践的历史上有不少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理应为今人所吸取,但从《笺注》看来,完全没有做到。下面略作分析。
(一)最先的问题。引文应该追踪原始,正本清源,古代学者早有共识。如李善在《文选注》中就强调“举先以明后”,清初著名学者朱鹤龄在《辑注杜工部集凡例》更明确地说:“凡征引故实,仿李善注《文选》体,必核所出之书,书则以最先为据。”[5]之所以强调文献引用的“最先”原则,主要是因为典故的原创性,它与后世的引用是源与流的关系,因此这个原则被历代注家奉为圭臬。唯有引用最先文献,才有助于读者准确理解诗文之意,有助于把握作者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借鉴和创新,其意义不可小觑。但《笺证》在引文方面较为随意。例如:第2页“画舸”引岑参诗,“日华”引苏頲诗,3页“鸟迹”引杜甫诗,4页“玉人”引《世说新语》,5页“笻杖”引唐人李中诗,“无机”引中唐耿湋诗,10页“禅床”引《旧唐书·王维传》,但引文中仅有“绳床”而无“禅床”字眼,二者并非一物;16页“素琴”引《晋书·陶潜传》,19页“寄世”引寒山诗,“二毛”引庾信赋,22页“翠帱”引宋玉赋,23页“石坛”引中唐皇甫冉诗。24页“商洛”引《资治通鉴》胡注,而胡注又引《隋志》。为何不直接引用呢?25页“断肠”引曹操诗,27页“扃”字引《庄子》成玄英疏,28页“稻粱心”引杜甫诗,29页“玉壶”引鲍照诗,31页“河洛”引《史记》,32页“白玉盘”引杜甫诗,33页“良夜”引《后汉书》,36页“柏城”引白居易诗,37页“烟波”引孟浩然诗,37页“秋风摇落”引曹丕诗,40页“绿琪”引孙绰赋和李绅之文,“黄槿”引李颀诗,“别怨”引柳宗元诗,41页“丝桐”引王粲诗,42页“石床”引卢纶诗,“心猿意马”引敦煌变文。51页“三径”,注文先概述蒋诩院中辟三径,唯与知己过从。接着曰:“参《文选》卷四五陶渊明《归去来辞》‘三径就荒’句注。后人本陶文之意,以三径喻隐士所居。”须知“三径”出自东汉赵歧《三辅决录》,陶文亦是引用,后世更非“本陶文之意”而用“三径”之典。72页“王粲”引李善注,“吕虔”引《蒙求》注,等等。如此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这些条目,笔者虽未一一查询,但基本可以断定所引文献不是最先。有时《笺证》干脆引用类书或辞典,而非以此为线索查找源头,如19页“曹溪”,注末云“见《祖庭事苑》卷一《曹溪》”,《祖庭事苑》乃北宋人编辑的佛学辞典。《笺证》所引材料八成乃至九成是乱引,皆非“最先”文献。注者唯一顾忌的,好像是所引文字仅在作者之前而已。
(二)滥引的问题。引多少,也是一个学问,其原则是贴切诗意。古代注家多采取节引的方法,也就是节取与诗意有关的部分材料,否则极易汗漫无当。《笺证》即犯有此弊。如第8页“生公”,晋代高僧竺道生,注文所引“石点头”的故事,却与诗意毫无关联。22页“三湘”,泛指洞庭湖、湘江一带,但注文引明人王士性《广志绎》,长达140字之多,实为赘冗。28页“榆塞”,注文虽长,却更令人糊涂,其实“榆塞”仅指边塞,与上句“芦洲”皆泛指。49页“陶彭泽”即陶渊明,无需大费周章,但注文亦达百余字。其余如53页“鲁肃”,55页“易水”,65页“海门”,67页“解题”之“马镇西”,69页“解题”之“郁林”,76页“乌帽”,84页“心法”“无住”,94页“素车”“珠履”“五岭”,97页“解题”之“新安”,98页“陵阳”,等等,皆不顾诗意,大段转引,漫无节制,徒费笔墨。
(三)顺序的问题。注释古诗,应首先标明典故的原始出处,但《笺证》相反,却在注末以“事见某书”的方式标明,例如6页“华表”,注末云:“事见《搜神记》”;8页“生公”,注末云“事见晋佚名《莲社高贤传·道生法师》”;19页“曹溪”,注末云:“见《祖庭事苑》卷一《曹溪》”等。14页注释“婚嫁乖前志,功名异夙心”二句,注曰:
浑有《酬殷尧藩》云:“相知愧许询,寥落向溪滨。竹马儿犹小,荆钗妇惯贫。独愁忧过日,多病不如人。莫怪青袍选,长安隐旧春。”本诗言“婚嫁乖前志”,用东汉人向子平料理儿女婚嫁既毕,遂肆意出游五岳名山之典故,谓不得遂其超尘之愿也。向平事见《后汉书·逸民列传·向长传》。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引用《后汉书》解释“婚嫁”之典,再解释二句诗意,最后再引用《酬殷尧藩》,但《笺证》完全相反,令人不知所谓。不仅最重要的“婚嫁”之典,无一字文献引证;且引许浑《酬殷尧藩》诗,揆之本意,是想说明作者早有儿女婚嫁即归隐之心,但从引诗中却难以看清。内容错误,逻辑混乱,徒增烦扰。
(四)语言的问题。《笺证》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典故和诗意,有两个问题,一是表达欠妥,二是过于直白。欠妥的问题,如23页“翠帱”,注曰“翠色床帐”,按“翠”当为“绿色”;27页《山鸡》“月圆疑望镜”,注曰:“山鸡甚自爱羽毛,常照水而舞”,但与所引《异苑》照镜而舞的文字却不合。42页“石床”,注曰:“平坦之石,可偃可卧,谓之石床。”按当解为“石制坐卧具”;44页“龙气”,注曰:“传说龙能兴云雨,故称水气曰龙气。”按当为“云雾”而非“水气”;47页“终童”,注曰:“终军少即出众,世称终童。”按称之“终童”,是因为终军死时仅二十余,而非其“少即出众”;57页“平芜”,注曰“平旷的草地”,按当为“平旷之原野”;65页“缊袍”,注曰:“以新绵合旧絮为袍”,按当为“乱麻为絮之袍,贫者所服”,等等。其二是直白的问题。《笺证》多处以白话注释,如9页“咏贫”,注曰:“陶渊明有《咏贫士》七首,刻画了历代典型的贫士形象,表现出贫士的心理与气节。”不仅累赘,而且刺目。现代学者注释古诗,当尽量用浅近文言。
(五)来源不明。虽然注者对词语作了注释,或者也知道其有典故,但却不交代文献来源。如36页“金蚕”“玉燕”,前者注曰“殉葬之具,以铜铸为蚕形,饰以金银”,而无来源交代,后者注曰“钗名”,引《洞冥记》白燕飞天事。按“金蚕”“玉燕”皆葬品,典故源自任昉《述异记》卷上:“阖闾夫人墓中……漆灯照烂,如日月焉。尤异者,金蚕、玉燕各千余双,皆殉葬之秘器也。”之所以以之为葬,当取其蜕化之意。同页“随龙驭”,注者虽注“龙驭”为“天子驾崩”,但对“龙驭”来源却无引用,按此典用《史记·封禅书》黄帝于鼎湖乘龙升天事。44页“龙气”,当引《易·乾》:“云从龙。”65页“缊袍”,当引《论语·子罕》:“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79页“倒接篱”,注曰“参《陪王尚书泛莲池舟》‘客散山公醉’句注”,但2页“山公醉”条,却无“倒接篱”的佐证。94页“爱树”,注引《诗经·甘棠》,却无“爱树”字眼,按当引《左传·定公九年》:“《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五、赘言
古人曰“注书难”,早在宋代,洪迈就感慨“著书难,注书至难”[6]。到了清代,这种感慨反而更多,如乾隆时学者杭世骏为王琦《李太白集辑注》作序曰:
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证佐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7]。的确,注释不仅需要详尽考察作者的生平时事,而且须仔细涵咏诗文,对每一词语和诗句考定其内涵意旨,“核其指归”“还其根据”,还必须编列年谱,确定作品创作时地等,“必有什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所以说“注书难”洵非虚言。除了这些功夫,注者尚需熟悉古代注释体例,所以即使著名学者,笺注却非必是其所长。古代诗文注本过万,但佳作寥寥,原因就在于此。
古代注家有“不愧古人,不负来者”之说,意思是注家的注释应该知人论世,无愧于作者;开物启智,有益于后人。对待古人诗集,当代注者应抱持敬畏之心,对古人敬,对后人畏,唯有所执,方有所成。前者拜读高克勤《莫把“贡禹”改“禹贡”》一文,高先生针对《王荆公诗集补笺》存在的各种错误,指出古籍整理者须有“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而绝不能草率从事、急于求成”[8],确实颇中肯綮。清代《钱注杜诗》耗费钱谦益大半生精力,甚至临终还指示钱曾“杜诗某章某句,尚有疑义”,“口占析之”,嘱咐钱曾记录[9],其情其景,令人动容。今人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亦费时二十余载,与编辑同仁几经往复,方付剞劂。我想,如果注者和编辑都能有如此精神,我们何愁不能奉献更多古籍整理的佳作呢!
[1] 纪昀,等.山谷内外别集注提要[M]//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2067.
[2] 罗时进.许浑年谱稿[M]//唐诗演进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214-273.
[3] 纪昀,等.文选音义提要[M]//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2669.
[4] 许培荣.丁卯集笺注[M]//续修四库全书:13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13.
[5] 朱鹤龄.凡例[M]//杜工部诗集辑注:卷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6] 洪迈.注书难[M]//容斋续笔: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杭世骏.跋[M]//李太白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1683.
[8] 高克勤.莫把“贡禹”改“禹贡”[J].文艺研究,2008(8):134-138.
[9] 季振宜.序[M]//钱注杜诗: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