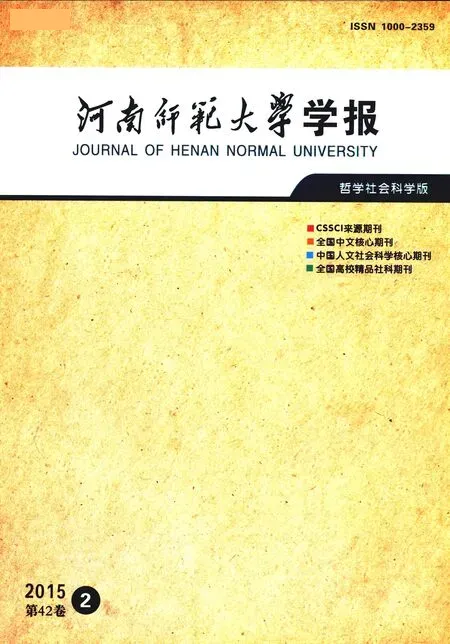唐代试判制度考述
陈勤娜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唐代“试判”主要用于铨选,过去在“科举与文学”语境下的相关研究,往往并不涉及;但从更宽广的“取士”概念上说,铨选亦在其中,故试判也是“取士文学”的重要文体。理论上说,唐人凡参与铨选者皆有过判文的制作,而所有参加“关试”者也须试判,其总量之大可想而知;现存的判文也为数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像唐代试判制度这样的基本问题,也由于诸多原因,现在还不甚详明。本文根据相关文献材料,就此作一简要梳理和探讨。
一
《通典·选举典》云:“其选授之法,亦同循前代。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视品及流外官,皆判补之。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供奉官,若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1]359唐代六品以下文官(开元四年后员外郎、御史、起居等官除外)选授由吏部主管,谓之“铨选”。铨选有一系列活动与标准,试判即为其一。
唐代取士试判之制有其渊源。常衮《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云:“开元十年,举文藻宏丽……与孙逖同入第二等,擢鄠县尉。秩满,判入第三等。自周隋已来,选部率以书判取士,海内之所称服者,二百年间,数人而已,(常无名)又居其最焉。”[2]4956此处既称周隋已来以书判取士,又有二百年之约限,则知北周隋朝应有试判之制。又刘肃《大唐新语》云:“国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选,主者将视其人,核之吏事。始取州、县、府、寺疑狱,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此判之始焉。”[3]可见唐代试判之制借鉴于周隋。
唐代以试判选官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唐初兵革方息,“士不求禄,官不充员。吏曹乃移牒州府,课人应集,至则授官,无所退遣。”[1]362后来,求仕者众,才渐行沙汰。唐代以试判沙汰选人,最初实行于显庆初年,用于杂色出身人(按:《通典·选举典》的“杂色解文”,具体包括“三卫、内外行署、内外番官、亲事、帐内、品子任杂掌、伎术、直司、书手、兵部品子、兵部散官、勋官、记室及功曹、参军、检校官、屯副、驿长、校尉、牧长”等等。见《通典》卷一七《选举》五,第403页。)入流的简择。《通典·选举典》云:“高宗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以选举渐弊,陈奏。其一曰:吏部比来取人,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是伤多;不简杂色人即注官,是伤滥。经学时务等比杂色,三分不居其一。且官人非材者,本因用人之源滥;滥源之所起,复由入流人失于简择。今行署等劳满,唯曹司试判,不简善恶,雷同注官。”[1]403
唐制,官阶在九品以内者为流内,“入流”即进入流内居官。唐代入流者通常可概括为贡举出身人(明经进士等)和杂色出身人两大类,刘祥道此疏陈奏吏部取人之弊为“多且滥”。然贡举出身人奏第即付选,刘祥道犹嫌其占入流数比重少,更毋论再行沙汰。因此刘祥道所言“多且滥”实际皆就杂色人入流而言。而杂色人居内外行署的流外官,原本官不充员时,可能“劳满”后即“入流”,此时因选人渐多,始以试判加以简择。故杜佑称“此则试判之所起”者:就时间而言,起于显庆初,就情状而言,起于杂色人入流。
需要补充的是,杂色入流试判之制虽延续下去,然其“不简善恶,雷同注官”流于形式的情形,直至唐中期仍无明显改观。赵匡《举选议》曰:“诸色身名都不涉学,昧于廉耻,何以居官?其简试之时,虽云试经及判,其事苟且,与不试同。”[1]423究其原因,主要是杂色入流人多是勋戚子弟,而“勋戚子进取无他门”[4]4047,所以大量的杂色出身人不作严格简择便注官入流。
二
由于“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1]361,选人多而官阙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以试判简择选人的做法得以扩大化:不仅适用于杂色入流,也用于贡举出身人的“入流”(即“关试”),而且用于官满罢秩、守选期满的前资官常规选调。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进士科故实”条云:“关试,吏部试也。进士放榜敕下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部守选。”[5]这里云进士放榜后,礼部将及第举子的姓名、科目等材料“关”(告知)吏部,吏部组织“关试”试判后,“始属吏部守选”,及第举子才算“入流”进入选门。实际上,不止进士科,其他礼部科目及第后皆需关试。《唐会要·选部下·冬集》载:“大历十一年五月敕:礼部送进士、明经、明法、宏文生及崇贤生、道举等,准式,据书判资荫,量定冬集授散。其春秋、公羊、谷梁、周礼、仪礼业人,比缘习者校少,开元中,敕一例冬集,其礼业每年授散。自今以后,礼人及道举明法等,有试书判稍优,并荫高及身是勋官三卫者,准往例注冬集,余并授散。”[6]1626
由此可见,礼部进士、明经、明法、宏文生、崇贤生、道举、春秋、公羊、谷梁、周礼、仪礼等科目得第人皆需关试。关试的简择作用表现在,其所试书判优劣直接关系到是“冬集”还是“授散”,甚至一些惯例上“授散”的礼业等人若能“试书判稍优”,亦准许“冬集”。
然则,试判真正发挥其铨择官吏的作用,是在常选活动中。《通典·选举典》载其制曰:“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可取,则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其六品以降,计资量劳而拟其官;五品以上,不试,列名上中书、门下,听制敕处分。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1]360唐代常选择人虽称“四事”,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7],“彼身、言及书,岂可同为铨序哉!”[1]427可见试判在常选中之地位及其重要性。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凡参选者皆需试判,亦即:就吏部官方而言,铨择六品以下旨授文官皆需试判;就个人而言,自入流居官,直至升至五品以上出选门,每官满罢秩守选期满,参加选调时皆需试判。可见其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
试判推广至常选择人非常迅速。《通典·选举典》云:“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寖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1]361-362《新唐书·选举志》:“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牓……铨总之法密矣。然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4]1175结合两段材料可知,自显庆三年(658)唐代实行试判起至总章二年(669),短短十余年,试判已经明显分作三个阶段,则常选当在杂色以试判简择入流人后不久即行引用。
常选以试判择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择优,其二为黜劣,其三为达标。《通典》云:“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1]361-362《新唐书·选举志》亦云:“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4]1169实指常选试判的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佳者—入等—升”,一种是“甚拙者—蓝缕—降”。然则二者之间,还应有一种不好不坏的情况,即参选者试判水平既达不到“入等”的高度,也不至于拙劣至“蓝缕”的程度。因此,常选试判的结果便有三种情况:一是“入等”者“升”,可理解为择优;二是“及格”者“过”,可理解为达标;三是“蓝缕”者“降”,可理解为黜劣。试一一论之。
常选试判有考定等第之制。其具体等级及其标准不得而知,然赵匡《举选议》建言或可作为参考:“其有既依律文,又约经义,文理弘雅,超然出群,为第一等;其断以法理,参以经史,无所亏失,粲然可观,为第二等;判断依法,颇有文彩,为第三等;颇约法式,直书可否,言虽不文,其理无失,为第四等。”[1]425赵匡从“文”与“理”两个方面权衡试判成绩,分为四等。虽然只是其拟议之言,但应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凡试判达到某种水平论以“等第”,便称“入等”,或具体为“判入第某等”。其等第较高者,称“判入高等”或“判入殊等”。《旧唐书·韦贯之传》:“贞元初,登贤良科,授校书郎。秩满,从调判入等,再转长安县丞。”[8]4173《旧唐书·文苑传》:“初则天时,敕吏部糊名考选人判,以求才彦,(刘)宪与王适、司马锽、梁载言相次判入第二等。”[8]5017颜真卿《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云:“(宋璟)长寿三年,从调,判入高等,有司特闻,天后亲问所欲。”[9]皆为常选试判入等之例。
常选试判定等第之所起难以确指,然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公名震,字元振。十六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同业。十八擢进士第,其年判入高等。”[2]5111徐松《登科记考》“以开元元年卒、年五十八推之”将其进士及第、试判之年系于咸亨四年(673)[10],则至少此时已有其事。
常选试判定等第之举长久稳定施行,“入等”便逐渐具备登第“科目”的性质,独孤及《唐故朝议大夫高平郡别驾权公神道碑铭并序》载:“初,选部旧制,每岁孟冬以书判选多士,至开元十八年,乃择公廉无私工于文者,考校甲乙丙丁科,以辨论其品。是岁,公受诏与徐安贞、王敬从、吴巩、裴朏、李宙、张烜等十学士参焉。凡所升奖,皆当时才彦。考判之目,由此始也。”[11]试判考定等第早有其事,而称“考判之目由此始也”,应指开元十八年考定试判等第(即“入等”)开始成为“科目”。故《通典》称“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1]361-362,言“入等”即试判佳者登于“科第”。
常选试判“佳”者“入等”而“升”屡见记载,其“拙”者“蓝缕”而“降”亦有文献可征,如《唐会要·选部》云:“大足元年正月十五日敕:选人应留,不须要论考第。若诸事相似,即先书上考;如书判寥落。又无善状者。虽带上考。亦宜量放。”[6]1611即便选人带“上考”符合正常留人授官的条件,若是书判寥落,也不予授官。书判的优劣,在铨选授官过程中,具有“一票否决”的关键作用。
然而,铨选试判“及格”者“过”的情况,很少见到明确的文献记载,因此常为人们所忽略。其实从数量统计上,我们就可以印证这一点。《新唐书·苗晋卿传》载:“方时承平,选常万人……天宝二年,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4]4638唐代每年参选人数和入官人数不等,但现有资料显示,每年留人数多在千人以上,而判入等者六十四人,其余选人得留者均为试判“及格”的情况。
试判在常选中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可谓择人之要,然在唐代中后期选官取士中,其作用进一步扩大化。
三
吏部的常规铨选,对选人资格有一定的要求。高宗总章二年,裴行俭设立“长名姓历榜”,玄宗开元年间裴光庭创作“循资格”,对各级官吏的守选年限作出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守选达到一定年限的人方能参加铨选授官。此举对于规范铨选制度、缓解京城交通食宿压力等方面有积极意义,然而,未免有失才之嫌,或称之“虽小有常规,而抡材之方失矣”[1]361,或“上言废循资格”[4]4425。因此,朝廷对贤才选拔之制作了一些补充,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唐会要》载:“(太和三年)其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内外常参官改转。伏以建官莅事,曰贤与能,古之王者,用以致理,不闻其积日以取贵,践年而迁秩者也。况常人自有常选,停年限考,式是旧规。然犹虑拘条格,或失茂异,遂于其中设博学宏词、书判拔萃、三礼、三传、三史等科目以待之,令不限选数听集。其实限年考者,非择贤能之术也。”
由此可知:“常人”“常选”的“旧规”须“停年限考”,亦即有一定的“年”和“考”的限制。但是考虑到这些限制可能不利于“非常”优异人才的脱颖而出,于是设立了非常规的科目以待不合格限的选人,惯例谓之“吏部科目选”,其一即为“书判拔萃科”。
最早设置的科目选为博学宏词科。裴光庭开元十八年作“循资格”,开元十九年朝廷置博学宏词科。《唐语林》载:“开元十九年置宏词,始于郑昕。”[12]《旧唐书·萧昕传》:“萧昕,河南人。少补崇文进士。开元十九年,首举博学宏辞,授阳武县主簿。”[8]3961及第人名虽有差异,然首置时间一致。
实际上,书判拔萃科亦当首现于同时。前言之,吏部一向以书判择人,且惯有考定等第之制,选人参选无资格限制时皆参加常选,“试判两道”[13],佳者则为“入等”;实行“循资格”后,符合格限的选人参加常选,格限未至的选人,加试一道判文(即试判三道),且成绩特别突出者(高于“佳者”)为“书判拔萃”。故《通典》云:“(常选试判)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1]362
然则书判拔萃科也有一个渐趋规范的过程。《唐会要》载天宝十一载十二月二日诏:“文部选人调集者,宜审定格限,令集铨日,各量官资、书判、状迹、功优,据阙合留,对众集便定。其宏词博学,或书判特优、超绝流辈者,不须定以选数,听集。”[6]1613将实为博学宏词科与书判拔萃科的情况,分别称作“宏词博学”者和“书判特优、超绝流辈者”,并以下诏的形式重申其“不须定以选数听集”的规定,亦可从侧面证明当时书判拔萃科未成定制。至大历时赵匡言:“宏词、拔萃,以甄逸才;进士、明经,以长学业,并请依常年例。”[1]426则已形成惯例。
正因常选试判入等与书判拔萃科在试项(判)、标准(优秀)、结果(从优授官)上的相似性,人们常将二者混淆,如徐松《登科记考》将试判入等皆系“拔萃科”下。实际上,书判拔萃科是常选试判的进一步深化:其一,常选的选人参选需要满足年考资格限制,书判拔萃科则不限选数听集;常选试判入等从优授职,书判拔萃科“得不拘限而授职”,其待遇应更为优厚;其二,唯其参选资格宽严不同,而结果处置高低有差,试判的实施与录取的标准必有差别:二者虽试项皆为判,但常选试判两道,书判拔萃科试判三道;书判拔萃科之谓“超绝”,定然要比常选入等的“佳者”更胜一筹;其三,常选需要综合选人的出身、资历、身言书判等多方面表现铨授官职,虽试判“入等”可从优授职,然表现平平亦可照常决定留放。书判拔萃科则唯据试判优劣勘定登科与否。由此可知,较之常选,试判在书判拔萃科中的作用大大提高。
[1]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3]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2.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8.
[6]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马端临.文献通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54.
[8]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颜真卿.颜鲁公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1.
[10]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58.
[11]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973.
[12]王谠,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713.
[13]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