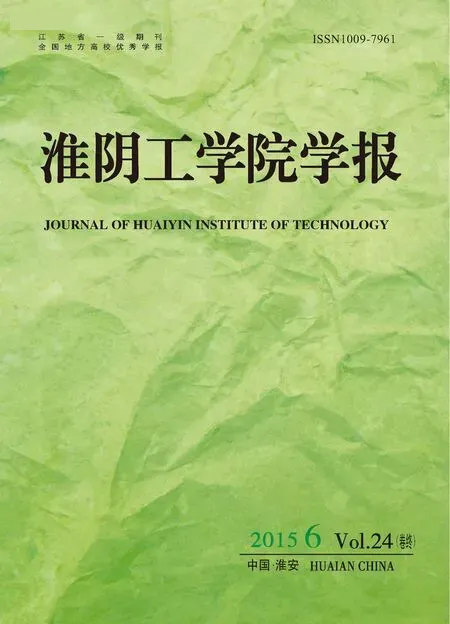略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散文特质及其溯源
孙高顺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略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散文特质及其溯源
孙高顺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中国的女性散文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源于外部环境的宽松和女性作家们在创作上的提高。女性作家们改变了宏大叙事观念的写作,更多地关注起自己的内心情感体悟,女性的身体、女性的内心及女性的感觉成为叙写的中心。
女性散文;内心体验;女性感觉
自20世纪初以来,虽说女性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社会、家庭和自我的因素依然束缚着女性文学的发展,女性文学在这种备受挤压的环境下艰难地成长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骤然轻松起来,当社会、家庭都不再是一种主要的束缚因素后,女性文学获得了真正地长足发展,尤其是作为感性文学的女性散文创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女性的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庞大,其数量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更为可喜的是,其散文创作成绩亦是异常突出,甚至可与男性散文创作并驾齐驱。不同的女性作家甚至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创作风格。可以说,在这段黄金发展时期内,中国女性散文的思想观念、哲学意识、文化水准、审美境界、文学艺术品味及其语言表达功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从宏大叙事到内心体悟,女性散文的方向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和21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的推进,女性散文的创作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当然和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有着极大的关联,不少作家开始摆脱创作的严肃性与重大性原则,他们脱离了国家、社会与人的固定创作模式,而将整个目光转到了自然万物、自我情感、身边琐事上来,而女性作家们,因为这样的转变,她们的散文创作成了熟稔的叙写与体验。惯常的日常关心与体悟一旦成为创作母题,其蕴含的创作能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有人写自然现象,有人写身边的动物,有人写身边或家中的植物,有人写自己的收藏,有人写旅途见闻,有人写爱情的风花雪月,甚至于有人写自己的十月怀胎。总之,她们惯常的体验与感悟全部付诸了文字。“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日渐增强,更多的女性作家开始关注女性自身问题。”[1]一句话,女性散文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宏大题材,其创作题材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的这种创作,不仅仅是将世界万物作为一种纯客观来叙写,更多的是,她们结合自身的敏感和多情,将“外物”与“内心”交融起来,其笔下的世界万物有了更多的“物性”,这是一种以天地自然之心来体验自然之物的心怀。一朵花,不仅仅是花,而是自我的内心;一片云,不仅仅是云,而是自我的思想境界。她们的文章有了水乳交融的气质,有了气定神闲的品质,有了“物人一心”的和谐,自此,女性散文的创作面目有了全新的改变。在这些女性作家的笔下,物不再是客观的物,而是有了情感的生命。它们有思想、有情感、有和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比如唐敏在1984年写的《心中的大自然》一文,就体现了自然世界的万事万物具有的生命体验。她笔下的虎不是一只仅仅伤害生命的野兽,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人类的敌人,而是具有独特生命感悟的可爱生灵。“因之,唐敏的散文创作获得了她所期待的精神高度:以心灵的倾吐表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引出最普通、最真切的人生体验,唤起读者在人生经验上的共鸣。”[2]这样的叙写让我们认识到“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女性作家。”[3]作家周晓枫对动物、植物以及器物也有着非常细致的内心体悟,她能脱离人类通常的观念,用一颗精微的自然之心去体察大自然的一切。这种从自然万物的角度思考问题的确新颖、有深度。“其散文风格显示出沉郁稳健、凌厉而不僵滞的智性面孔。”[4]
与这些具有文化反省或价值观反省的文章不同,还有一类文章主要是谈物性体悟的,作者力求通过对物的感悟,达到人和物的内心感应,这类文章充分体现了女性作家的心思细腻之处,也将她们善于观察、善于体悟的长处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家张抗抗写过一篇《瞬息与永恒的舞蹈》,作者从昙花开放之初写到昙花开放,再写到昙花凋谢,语言极尽冼练清新,有一种通透之感,而其中的主题也将人与物的本质表现了出来。 “她的散文体现出了更多的理性色彩与深度追求。”[5]读这样的作品就像看天女散花或唐代的公孙大娘舞剑,给人以超凡脱俗的精神享受。另外,作家马莉、周佩红、郑云云等人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文章。正如散文作者楚楚所说:“真正的好散文不是用来读的,而是让人穿过眼帘,用心感受的。”[6]其实,1980年代之前的女性作家们也有过这样的创作,比如冰心的“爱意”散文、张爱玲的感悟性散文、丁玲的生活化散文都有过这样的表现,在她们的散文里,天地物性也有过很好的表现,但她们的散文还只是零星地流露,只是最初的一个萌芽,而形成一种群体的创作态势,以及变成一种积极主观的创作意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形成的。
2 女性感觉提升为散文的核心主题
与男性散文作家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散文有着和男性的价值观不一样的特质,而其中最主要的特质就是她们对自身性别意识的加强,多数女性作家的散文所关心的所熟悉的所擅长的还是表现与她们相关的内容,即她们的生理、心理、理想和感觉世界,如果更集中起来,那就是家庭、爱情、婚姻。在这一点上,她们依然有着历史的继承,从李清照到张爱玲,写的最多的也是家庭、爱情与婚姻。但与以往的女性作家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家们思想明显更加开放,尺度更加大胆,表达更加随性,她们对前辈们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自我身体的展示上。女性的身体本就是柔美莫测的地方,充满着迷惑与探求欲望,而这些女性作家通过对自身身体的展示尤其是女性特有的怀孕与分娩的描写,展示了女性作家们特有的散文魅力。如作家海男和叶梦就曾对自己的怀孕过程及心理感受作了细致而动情地勾画。在《女人的梦》一书中,作者的关注从社会文化环境转向女人自身的自然生理,“叶梦用散文形式表现一个女人丰富独有的生命季节,在海内外的华文作品中无疑别具特色和魅力。”[7]在她的散文里,她永远追求那种难以言说的人之美,“叶梦的生命选择过程就是她对人性之谜的探索过程。”[8]
与探讨女性的身体、生理相比,这一时期的女性散文更多的是书写心灵世界的幽微、内蕴、恬美。女性的世界是怎样的?这在卓文君、李清照、张爱玲、丁玲、庐隐、冰心、萧红、林徽音等以前女性的作品里都有所体现,但那种展示只是零星的流露,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及21世纪以后,女作家们可以自由地、畅快地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充分流露自己的爱或恨,快乐或痛苦,悲伤或喜悦,坚韧或脆弱,满足或绝望,甚至是一些无法言说的内心的潜意识。她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多样的情感流露了出来,多数情况下,她们展现出来的主要是痛苦、焦虑、彷徨及无奈。她们展现的“是创作主体内在主观世界的情感显现而不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单纯描摹。”[9]但在这些情愫的表达中,有些内心的感觉则是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甚至于自己也不知道要表达什么,只知道内心里有那样的一种苦闷,这往往让这些女性作家们更加感到无奈,这些情愫仿佛就在自己身边,但当自己睁眼寻找时,却也不见踪影。如艾云的《细读蘩漪》就试图以心灵贴近的方式打开蘩漪的内心世界,但解读到后来,连她自己也充满了困惑。
这种多义性的写作往往带来了这些女性散文特有的一些内质,比如隐晦化、诗意化、虚构化、象征化。如楚楚的《箫》表面看是写对箫这种乐器的感觉,但却是阐述了另一类人生哲理:爱的东西,不能放得太近。可贵的是,这些女性作家在表达此类情愫的时候并没有完全陷入个人情感郁闷、彷徨、困惑的小圈子里,她们不断地从这种感性中走出去,从社会,从人性上,从实实在在的尘世生活中找到了更新的创作素材,在突破的同时,也让自己的文风有了清新、健康地发展,如作家毕淑敏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也有一些作家一步步地将自己封闭了起来,从此沉沦于个人情感的苦闷心结中,不断复制着日日相似的内心纠结,在小感觉、小经验、小情调中不断地表现,她们在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的心理作了深刻开掘的同时,也无形中对自我进行了封闭,这或许是一种另类的成功,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失败。
3 女性文化散文的开拓、挥洒与迷失
20世纪80年代末的文化散文热,除了将众多的男性作家拉入到这种文化诉求语境当中外,也将众多的女性作家从精美的情感叙述散文里拉了出来,众多的女性作家不再局限在自己的情感圈子里,而是将描写的目光伸向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当中,在浩瀚的文化世界里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较有代表性的有马丽华的西藏文化散文、素素的东北文化散文、冯秋子的蒙古文化散文、王英琦的灵魂拷问散文和韩春旭的与文化大师对话散文等,她们的写作与努力,也慢慢地形成了气候,成为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奇军。“新时期的女性散文呈现出极高的精神向度。 ”[10]
在女性大文化散文的创作母题上,众多的女性作家们突破了以往情、景、理、趣、事的创作格局,将笔触伸向了地域、历史、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范畴里,于是,众多的文化语境在作家的笔下成为笔墨驰骋的天地,这样的选题自由性带来的结果就是文章的知识容量非常大,时间和空间的幅度也会拉得非常大,带来了整个文章的感觉就是张力特别大,而且整个文章具有了恢弘的气势和深厚的内蕴。另外,在文化精神层面上,她们的文章往往根植于民族的土壤,对一个地域的民族历史或者人类历史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以此感受生命、灵魂、文化及哲学上的问题。男性作家们在创作这类散文时往往带有宏大、广阔的命题,而且笔下的物、事及书写也往往具有粗犷性与概括性,如周涛的《巩乃斯的马》就明显具有男性作家的剽悍性。与男性的这类大文化散文不同,女性作家在这方面则带有了很多的细腻、柔美及敏锐性。就像男性作家们更多地从构架、骨骼、肌肉上去书写,女性作家们则更多地从皮肤、呼吸、心跳等一些细微处体现真实而有质地的东西。男性作家们多是从广度、深度上去作文,而女性作家们则是从密度上去作文,她们的文章甚至可以听到血液流动的声音。“在总体倾向上表现出对主体间性的理论自觉,表明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已经走向一个独立和完整的主体性女人。”[11]创作的时候,她们也意识到顺境下藏着礁石和陷阱,作家们一旦执着于此就会迷恋沉落其间而难以自拔。因为,广阔浩瀚的文化语境及深沉历史学识对于女性作家们本就是偏门,她们的优势本是以感性、感情、体悟为主的情感类表达,抛掉了以往的特长而专攻自己的弱项,其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就像男性作家中的李存葆一直迷恋于大文化散文的广阔与无垠,其散文已渐渐失去了散文本真的味道,通篇就在大、广上做文章。而女性作家们也在这条路上迷失过,作家艾云说:“思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好像是与她们快乐感觉的天性相悖谬的。”[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大文化散文的最大风险莫过于文化价值选择上的迷失。文化的内涵有很多,可选择的角度也很丰富,可表现的内容涵盖非常广阔,在这样多的文化视点上,如何选择一个角度进行切入是非常重要的,这同样也是值得女性作家们去思考的,比如马丽华的“超越苦难”式的文化价值取向就是健康积极的,这也秉承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萧红的散文精神,只是在知识容量上更为丰富。但马丽华还有一些散文则突出了“渴望苦难”的文化价值取向,某种程度上则是体现出了矫情与虚假,我们每个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可以不言放弃,寻求超越,但我们也不至于为了超越而故意寻求苦难,这体现了做作的为苦难而写作的思想。这样,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女性主体意识的极端强化又会导致女性主体性再度迷失。”[13]
众多的女性作家们虽然在这条路上进行了开拓,而且通过自身的努力也创造了令人敬仰的成就,她们挥洒着自己的才情,也挥洒着对文学、对文化的执着之爱,但也有一部分作家迷恋于此,越陷越深,最终在这种大文化散文的模式里走向了刻意,走向了做作,走向了迷失,散文最本真的真善美已然失去。
4 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散文是非常丰富而辉煌的,它秉承了以往女性作家的创作精神及内心体验,但同时也实现了对以往女性作家在文艺、题材、思想方面的超越。当然,对于女性文学的这些成就,有评论认为她们的作品仅仅是从自身的体验入手,写的也多是身边事,虽然一些具有物性的散文也很有美感和通透感,但从整体上来看,这类文章过“小”,缺乏宏观性、重大性、深刻性,仅是一些风花雪月的美文而已。还有评论认为,这些女性的散文,甚或是大文化散文也大多是停留在自然现象的把握上,大多数文章只是一些事物表层的探讨,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作深刻、全景式的剖析。“如果说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散文体悟天地自然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容易停留在现象上,而难以上升到理论上作形而上的思考。”[14]但笔者以为,这些评论显然有太过苛刻之处,什么事都要往一个高度上去拔,这有违常理,也显得有一种做作的挑剔,为挑而挑。女性的生活、女性的气质、女性的视野、女性的感触本来就和男性不同,或者是与那些思想家、社会学家不同,为何要强加给她们这些责任、这些包袱? “她们已经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已是最好的表现。”[15]
作为文学成就而言,女性作家的创作显然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就让她们在自己擅长的文学区域里尽情地挥洒。笔者以为,女性作家就应该表现出女性作品的特色及优势,就应该在她们所擅长的领域多思考、多创作,一味地靠近男性作家的创作是没有自己特色和前途的。另外,在大文化散文的创作选择上,女性作家们也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选对创作的坐标,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行文化的开掘,但不能沉迷于此,而且应该少一些空洞、抽象的文化说教,多一些智慧的因素,只有这样,女性散文的创作才会真正有所突破。
[1] 黄艳.女性心情的自由挥洒——由《女孩子的花》谈唐敏散文的女性意识[J].安徽文学,2011(8):42-44.
[2] 周艳华.挥洒心灵花瓣的安琪儿——唐敏散文的审美追求[J].写作,2007(3):10-12.
[3] 孙绍振.散文领域的一颗希望之星——论唐敏的散文[J].当代作家评论,1988(1):65-67.
[4] 刘云春.论周晓枫散文的审美特质[J].当代文坛,2013(5):139-140.
[5] 邓利.理性色彩与深度追求——张抗抗散文论[J].当代文坛,2002(2):63-64.
[6] 楚楚.我的散文观[J].散文,1995(7):56-57.
[7] 叶梦.月亮·生命·创造[J].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8.
[8] 马识途,曹丰.论叶梦散文的生命意识[J].求索,2010(7):214-215.
[9] 李虹.女性自我的复归与生长——新时期女性散文创作的流变[J].文学评论,1990(6):103-105.
[10] 胡颖峰.论新时期女性散文的精神向度[J].江西社会科学,2002(9):66-68.
[11] 刘思谦.生命与语言的自觉—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中的主体性问题[J].厦门大学学报,2007(4):90-92.
[12] 艾云.女人——为深刻所累[M]//当代中国作家随笔精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5.
[13] 余曲.女性散文主体意识的悖谬现象[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6):61-63.
[14] 王兆胜.超越与局限——论8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散文[J].文学评论,2002(6):87-88.
[15] 郭海鹰.世纪之交中国散文的一道绚丽风景——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散文”[J].中山大学学报,2000(4):43-44.
(责任编辑:郑孝芬)
On Chinese Feminine Prose Peculiarity and Historical Tracing Since the New Period
SUN Gao-shun
(Collgeg of Liberal Art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n'an Jiangsu 223300,China)
China's feminine prose creation has obtained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80's, which stem from the loos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creation improvement of feminine writers.In the creation, the feminine writers changed great narrative writing,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innermost feelings realied from experience. Moreover, the feminine body, the feminine innermost heart, the feminine feeling become writing prominence. In the big cultural prose creation, the feminine achievement is also extremely prominent.
feminine prose;innermost feelings experience;feminine feeling
2015-06-01
孙高顺(1973-),男,江苏淮安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H052
A
1009-7961(2015)06-00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