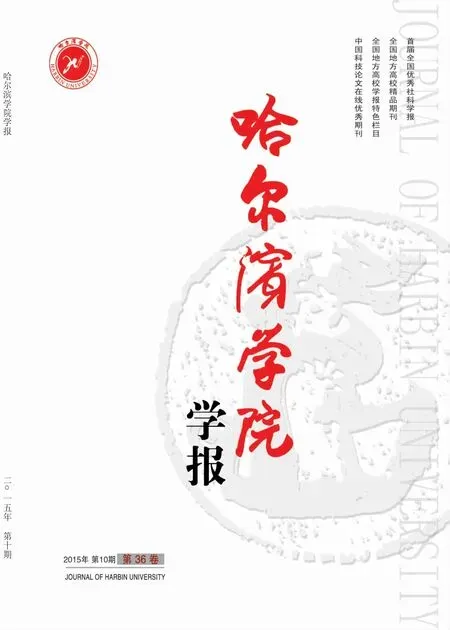黑龙江方言的多元文化内涵探析
周晓燕,张 宇
(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 50086)
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1](P139)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致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局部。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游汝杰指出,“方言是灿烂多姿的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载体之一。”[2]方言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共性,也有自己的地域个性。刘中树指出,从现有行政区域上看,“东北地区”包含着黑、吉、辽三个行政省,从文化上讲都归属于“东北文化区域”。但从实际情况看,受不同自然空间、历史传统、民族结构、外来文化及行政区域划分的影响,在“大东北文化”的涵盖下又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小文化圈。[3]自然的陶冶和历史的熔铸使黑龙江方言逐步形成了独特而又多元的文化特色,使之成为中华语言文化花园中的一支奇葩。
一、自然的陶冶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也都留下了自然环境的印迹。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域特色会形成不同的人文景观,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黑土地文化孕育了简洁、生动、形象、昂扬、富于节奏感的黑龙江方言,这与黑龙江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是一致的。
(一)寒冷低温,冬长夏短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而寒冷,北部甚至长冬无夏。旧时东北农村,最常见的是土壁草顶的房子,称土坯草房,它就地取材,工序简单、盖造方便且冬暖夏凉。窗户不但开得小,冬天还要在外面糊上窗户纸以防止热量散失达到保暖效果,屋内用土坯砌成土炕、搭成炉子,烧柴取暖,因此“炕”“烟筒”“糊”“窗户纸”等词语就成了特色的黑龙江方言。黑龙江地区一年要有半年的时间不能耕种土地,人们只能在家“猫冬”,曾有人形容东北人的生活是“三个月过年,三个月赌钱,三个月种田,三个月干闲”,虽然有些夸张,却体现了过去东北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习惯。大家都“猫”在家里难免寂寞,街坊邻居互相走动就是难免的了,因此农闲在家的多数男女都养成了抽烟的习惯,他们自己种烟草,而且是烈性的烟草。“草皮房子篱笆寨,狗皮帽子头上戴,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烟袋”所描述的正是这种寒冷冬季里的农村生活。
(二)地广人稀,物产丰富
深山老林常有野兽出没,因此在黑龙江方言中常以具体的动物做比,并赋予其各种不同的含义。如东北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人爱东北虎,所以话中“虎”也多,如“这人真虎”,一个“虎”字,使勇敢而又鲁莽的本性展露无遗。人们也常用“驴脸大褂”“耗子眼”“鸭子嘴”“猪腰子”等形容人的长相,用“猴精”来形容一个人机灵精明。此外,用“崽子”“犊子”“蹄子”作为詈骂词语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动物词语出现的高频率体现了动物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三)良田沃土,农业繁荣
黑龙江省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土地条件居全国之首,总耕地和人均耕地面积均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广袤的平原、肥沃的土壤孕育了悠久灿烂的农耕文化,农业生产的俗语和谚语应运而生。例如,苞米是黑龙江地区盛产的粮食作物,由此也产生了很多关于苞米的词语,秋收时把苞米穗子外面包裹的皮去掉叫“扒苞米”,扒苞米的过程需要把苞米叶连拉带扯一层一层地剥去,因此用“掰扯”来形容说理争辩,扒出来没有果实或者不饱满的空棒子叫“瞎苞米”,因此形容毫无根据地说称为“扒瞎”,用“黑瞎子掰苞米”比喻做事只贪求进度和数量,而不求质量和实际效果。劳动创造了文明,人们也在劳动中创造了很多方言词语,例如,耙子是从事农业生产时常用的工具,因此用“撂下耙子就是扫帚”来描述不停歇地干活,用“摔耙子”表示丢下应当负责的工作,用“菜耙子”表示吃饭时特别能吃菜的人,用“无齿耙子”指代人的双手。黑龙江地区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河流、无垠的草原为各族人民提供了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生命之源。除汉族外,满族、朝鲜族以农耕为主,赫哲族以捕鱼为生,鄂伦春族以狩猎为生,蒙古族、达斡尔族以牧业为主,农耕、渔猎、游牧这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使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主观地与外界切断了联系,也决定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乡土化。“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对这种知足常乐、悠闲自在、自娱自乐的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无论是农耕、渔猎、还是游牧,老派黑龙江人多数从事初级生产劳动,因此性格粗犷、淳朴、率直,说话开门见山、直来直去,总是将自己的想法毫不保留地宣泄出来,以达到强烈火爆的言语效果,故而经常运用夸张比喻的表述方式,如“肺管子”“腮帮子”“笑掉大牙”“脚打后脑勺”,等等。这种既热辣形象,又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体现了黑龙江方言农民式的幽默和乐观的文化品质,也提升了方言的亲和力和表现力。白山黑水孕育了黑龙江地区的肥田沃土和丰富的物产,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鲜活的黑龙江方言,它生动细腻、逼真形象,夸张而不脱离实际;风趣幽默、活泼俏皮,质朴而不乏灵气。
二、历史的熔铸
(一)黑龙江方言记录民族融合
黑龙江是一个汉、满、蒙、回、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朝鲜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三百多年的互相融合使龙江方言别具特色,方言词语展现了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清代以前,这里主要居住着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满族人口比例占多数,汉族人口几乎没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满族不断涵容着周边诸多部族。元、明之际汉族人口大批进入东北,此后,满汉两族交往频繁密切,各民族长期的接触,带来语言上的交流和相互吸收。满族人在向汉族人学习汉语的同时,汉族人也把一些满语词语吸收到汉语中,并在东北大地广泛地传播和使用,黑龙江方言就是在吸收以满语为主的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黑龙江方言中满语借词具有淳朴、直观、生动、逼真的特征,对黑龙江方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词语长期以来沉淀于东北方言的底层,活跃在东北方言的日常口语里,并以小品、二人转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于中华大地。
如今,满语在老派黑龙江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如用“喇忽”(办事不认真,疏忽,又不履行诺言)、“勒特”(衣履不整洁,不利落)、“虎势”(比喻人健壮、强壮,有勇劲)形容人的品性;用“嘞嘞”(没完没了地说)、“扎孤”(看病)、“撒摸”(搜寻地看)、“攮搡”(斥责、挖苦)、“胳肢”(挠痒痒使人发笑)来描述人的行为动作;用“兀突”(水不热也不凉)、“哈拉”(肉或油日久腐烂发出的气味)、“埋汰”(不干净)来描绘事物的性质。民以食为天,黑龙江地区的饮食更是具有明显的满族特色,腌酸菜、白肉血肠、坛肉、馇子粥、饭包儿、年糕、粘豆包、发糕、烀肘子、炸丸子、大酱等都是满族习俗的遗留。
满语中的人名和地名蕴藏着丰富的满族文化内涵,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清太祖努尔哈赤家族人名为例,“努尔哈赤”是满语词汇的音译,意思是“野猪皮”,寓意像森林里的野猪一样勇猛无敌,像猪皮一样坚韧;努尔哈赤的三弟名为“舒尔哈齐”,意思是“小野猪”;四弟名为“雅尔哈齐”,意思是“豹皮”。[4]黑龙江地区的直接音译自满语的地名比比皆是,如牡丹江,满语中称“牡丹乌拉”为弯曲的江的意思;吉林,又叫“吉林乌拉”,是满语江沿的意思;勃利,语义为“豌豆”;海林,语义为“榆树”。除满语外,蒙古语、锡伯语等对黑龙江方言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乌兰浩特”“呼和浩特”“二连浩特”“查干浩特”里的“浩特”来自蒙古语,指城寨、村寨;“昌图县”源自蒙古语“常突额尔克”,“常突”则是绿色草原的意思;“卡伦湖”来自锡伯语,为“边防哨卡”之义;“齐齐哈尔”来源于达斡尔语,是“落雁”的意思。
(二)黑龙江方言记录移民文化
关内的汉人出关到东北谋生,俗称“闯关东”,“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事”,[5](P85)1644 - 1667 年,清政府实行了鼓励移民政策,期间山东移民东北者居多。康熙七年,清廷下令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却并没能阻止闯关的流民。1860年(咸丰十年)清政府正式废除封禁政策,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人民,出关人数日难数计。及至清末,“闯关东”浪潮已蔚为大观。中华民国成立后,这种移民的势头有增无减,据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委员会统计,1923-1930年,华北移赴东北者约500余万人。[6]直到解放后,仍然还有许多人迁移到东北各地。“闯关东”的人群蜂拥而至,占据大批土地的同时与本地人聚居在一起促进了方言的融合,这种不同寻常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使移民者带来的旧地方言在黑龙江地区大面积保存下来并与本地方言融合在一起,丰富了黑龙江方言的词汇系统,因此东北以南的京、津、冀、鲁、豫等地的方言与黑龙江方言有很多共有的词汇。如:(1)山东方言:丢人现眼(丢人)、五积六受(指难受而不安分)、爆仗(鞭炮)、歪歪(说话做事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瞎(白白地、浪费)、叫驴(公驴)、倒灶(倒霉、倒闭);(2)河南方言:硌(因下垫硬物而感不适)、卷子(花卷)、花大姐(瓢虫)、叫唤(哭的蔑称)、仰百叉(仰面朝上摔倒在地上);(3)河北方言:电棒(手电筒)、起头(开始,最初)、晌午(中午)、滴溜(提起,提着)、使性子(耍脾气);(4)北京方言:撒丫子(放开脚步跑)、开瓢儿(指人或动物的头部受到重创)、背兴(倒霉、背时)、老疙瘩(最小的孩子);(5)淮北方言:见好(情况好转)、早起(早晨)、腆脸(厚着脸皮,不知羞耻)、打圈(母猪发情)、恣儿(舒心,舒服,自得)、老娘(外婆或外祖母;姥姥)。
黑龙江方言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忠实地记录和折射着本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黑龙江方言作为北方官话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方言在词汇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这与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移民风暴有直接关系。除此以外,清代大批满人“随龙入关”,作为统治阶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东北方言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东北方言的影响力,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以黑龙江方言为代表的东北方言代表了清代北方官话的语言面貌。如图穆热通过对《红楼梦》中活跃在东北官话中的方言词汇的研究,指出《红楼梦》与东北方言颇有渊源,证明了现代东北方言是清初北京方言的“活化石”。[7]
(三)黑龙江方言记录中外交往
东北地区有着绵长的边境线,北接蒙古、俄罗斯,东与日本、朝鲜、韩国毗邻,在长期的文化接触和贸易往来中,东北人吸收了许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但成为东北方言的补充成分,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果说东北文化是土著满族文化和中原地区汉族移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那么外来俄罗斯文化使黑龙江文化有别于其他的东北文化。[8]黑龙江方言中有一些独具特色的俄语外来词,折射出了以俄式文化为代表的异域文化在当地的影响。例如,用“巴篱子”指“监狱”,“蹲巴篱子”就成了进监狱的意思,至今已使用百年之久,是哈尔滨和黑龙江省铁路沿线地区妇孺皆知的口语。再如,“八杂”是俄语“集市”的译音,“八杂市”特指露天菜市场,现在的哈尔滨新一百商厦和道里菜市场一带,过去就叫“道里八杂市儿”。除了道里区,过去南岗和马家沟一带也有这样的“八杂市儿”。“里道斯”指的是哈尔滨市秋林公司卖的一种俄式香肠,至于喂德罗(铁皮桶)、布拉吉(连衣裙)、大列巴(大面包)等词语,直到现在仍在沿用。
日本对中国东北曾经实施的殖民统治是不堪回首的历史,但这期间发生的语言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东北方言。如:便所(厕所、卫生间)、果子(点心、糕点、糖果)、满员(名额已满,满座)、榻榻密(床垫、蒲苇草垫)、瓦斯(东北煤气、天然气)。近年来,韩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从食品到服饰,从音乐到影视剧,东北方言中有许多从韩语意译过来的词,如:拌饭(把米饭、煎蛋、蔬菜等按照一定的工序制作的韩国料理)、辣白菜(用白菜、精盐、辣椒和白梨等腌制的咸菜)、紫菜包饭(用紫菜把米饭、胡罗卜、海鲜等卷起的一种韩国特色小吃)。除意译外,以音译方式引进的韩语外来词也很多,如阿里郎(歌名)、金达莱(花名)、唧个啷(争辩、吵嘴)等。
通过研究与学习,我们发现正是这些广泛存在于平民阶层的、老派的、纯粹的、流利的土语才形成了黑龙江浓郁而独特的“大碴子味儿”方言。这种“土”和“俗”与高雅和时尚似乎背道而驰,殊不知,这种语言状况正是民族迁徙、民族交往、民族融合的鉴证,是自然和历史留下来的无价财富。挖掘方言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意义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乡土和民俗文化,在年轻一代中广泛传播方言土语对于培养其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美好情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英〕帕默尔(L.R.Pamer).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游汝杰.略谈普通话和方言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N].语言文字周报,2006-12-06.
[3]刘中树.关于开展东北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考[J].学习与探索,2012,(2).
[4]李学成.满族姓名初探[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1).
[5]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6]范立君.“闯关东”与东北区域语言文字的变迁[J].北方文物,2007,(3).
[7]图穆热.《红楼梦》与东北方言[J].社会科学战线,2000,(3).
[8]哈尔滨文化:渊源与定位[N].黑龙江日报,1999-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