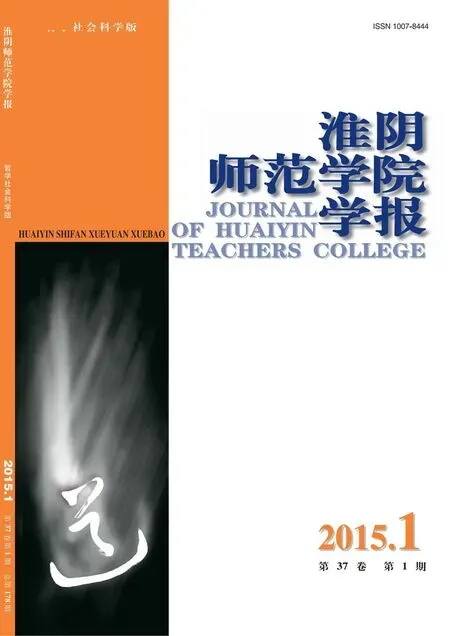《旧五代史》史臣对十国史的研究
陈晓莹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旧五代史》的研究以辑补、考订居多,亦有讨论其史料价值及史学思想的,但对其如何看待十国,对十国史料如何取舍及评价,却未曾深究。其实,《旧五代史》史臣对五代与十国的不同态度及史料取舍,正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其所显示出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旧五代史》成书于开宝七年(972)闰十月,是由宋太祖诏令编修的官修史书。全书150卷,绝大部分是关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史事,这从其原名《梁唐晋汉周书》便可看出端倪。而描写在五代十国的舞台上占据着很大份额的十国史事的,却仅有五卷。其中钱镠、马殷、高季兴、李茂贞、李仁福、韩逊、高万兴入《承袭列传》,杨行密、李昪、王审知、王建、孟知祥、刘守光、刘陟与刘崇入《僭伪列传》。划分的标准主要是依据其是否臣服于五代中原王朝而定。就目前可见《旧五代史》的史料,关于十国史的记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十国史的极度漠视。
《旧五代史》共150卷的篇幅,关于十国部分却只有短短5卷,内容多是对十国君主生平的简单记述,群臣则只对宋齐丘、梁震、王保义等极少数人作了简略介绍,分量显然是相当不足的,对十国历史的了解也有不少欠缺与讹误之处。《旧五代史》撰修时,十国多已入宋,未入宋者除北汉外,基本上也已臣服。如吴、蜀、南唐等国设有史馆,重视修史,也不乏私家修史者。因此,编修《旧五代史》时,史臣可以搜集到的十国史料当不致太过零落。但《旧五代史》却最终给了十国以极少的卷帙。这其中,除了十国材料较少,且以十国为伪的原因之外,恐怕还与宋朝君臣对十国史的极度忽视有关。
纵观五代十国的历史,十国几乎从没能对五代造成太大威胁,《旧五代史》撰修时,十国更是已入穷途末路,只余苟延残喘之力。除北汉还在苦苦支撑外,其余或已入宋,或已臣服于宋。对宋朝而言,来自于外部政权的威胁已经基本上解除,但政权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仅以开宝五年与六年为例:开宝五年,霖雨不止,黄河、汴水决口,天下大饥;岭南乐范、周思琼等人各聚众负海为乱,崖州牙校陆昌图作乱,烧劫牙署。海门监盐户庞崇等叛,北汉倚仗契丹的支持,频频袭扰北宋边境。开宝六年正月,韶州静江军士一百余人鼓噪城中以应外贼,渠州李仙众万人劫掠军界,殿直傅廷翰为棣州兵马监押,欲谋叛北走契丹。三月,融州修河卒叛,杀长吏。时人无法判断,宋朝会不会像五代诸朝一般,转瞬即逝。宋廷官吏大多承五代而来,多以吏道见称,读书却少,只能根据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感受与领悟寻找治理,缺乏对历史大势的了解与体悟。更何况忠义之风淡薄,像冯道这样历事多朝的人才是为官的榜样。隐患尚存的北宋,要如何避免五代的短命命运,是压在赵匡胤心上的大石。这就决定了《旧五代史》的修撰目的是为了给宋廷提供治国的经验教训,防止宋朝成为继梁、唐、晋、汉、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因此,与宋朝政治制度、军事架构、价值体系、文化背景皆十分相似的梁、唐、晋、汉、周便成为《旧五代史》的关注重点。《旧五代史》定名《梁唐晋汉周书》,大约就是这个道理。
在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中,两宋向来注重五代史而忽视十国史。雍熙四年(987)九月,右补阙直史馆胡旦曾欲修国史,上言:“诸伪国并无文字可修,今许州行军司马李晖尝为河东伪宰相,其人年高不任步履,望遣直馆一人,就本州与晖同共修纂,太常博士分司西京萧催旧事伪广为左仆射,亦请留在馆,与直馆同修本国事迹。又伪蜀实录及《江南录》皆纪述非实,荆南、湖南、夏州各无文字,莫知事实,今请于朝臣中各选知彼处事迹者,与直馆同编录。”[1]拾遗卷下·国史:314太宗敕旨依奏。但不久胡旦即罢史职,修史一事也不了了之。其时距北宋完全平定十国已有8年,如《晋阳见闻录》、《刘氏兴亡录》等当已问世。但收录于史馆中的十国文字居然还是如此之少,可见北宋政府对十国史的漠视。
第二,对十国贬多褒少。
《旧五代史》非但给了十国史以极少的卷帙,而且对十国的历史贬多褒少。比之后世的《新五代史》与《资治通鉴》,它流于人物传记式的简单描述,对列国的治国方略、政治架构、军事体制等所谈不多,对其治绩也很少涉及。这基本上奠定了十国史研究的基调。
以南平(荆南)为例。据他书记载,南平高季兴于唐末五代荆州兵火之余,招抚流亡,“赖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2]卷二百七十五:8980;延揽人才,重用梁震、孙光宪,“南平起家仆隶,而能折节下贤。震以谋略进,光宪以文章显,卒之保有荆土,善始善终。区区一隅,历事五主,夫亦得士力哉!”[3]卷一百二:1464,甚至“游士缁流至者无不倾怀结纳,诗僧贯休、齐己,皆在所延揽”[3]卷一百:1438,其子高从诲“性明达,亲礼贤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从善如流,采取“事大”原则,修复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南平君臣还曾得到司马光的赞扬:“孙光宪见微而能谏,高从诲闻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2]卷二百七十九:9135因此,南平虽然有诸多不足道之处,但能在荆南盘踞数十年,也是有其原因的。但《旧五代史》却突出了高季兴的跋扈不臣,对其善政则所记甚少。高季兴的起家,只有“招葺离散,流民归复”一条记载较为可观,其余则是“厚敛于民,招聚亡命,自后僭臣于吴、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后唐庄宗灭梁后,高季兴前往朝见,认为庄宗骄矜过甚,迟早必败,便增加防御,引诱后梁旧将佐,“由是兵众渐多,跋扈之志坚矣”。庄宗死后,其子李继岌平蜀时所选的宝货皆为高季兴所邀取。明宗即位,高季兴又提出诸多过分请求,“不臣之状既形”,引起明宗的讨伐。其子高从诲虽然于高季兴反叛后唐时“常泣谏之”,并于高季兴死后累表谢罪,复修职贡。在襄州安从进叛乱时,也曾馈赠军食助朝廷征讨。但史臣也揭露了他在晋、汉之际欲趁中原大乱捞取政治好处,向后汉高祖求取郢州为属郡,遭拒后与后汉反目,攻打郢州,不修朝贡的不臣之举。高从诲还向诸国称臣,“从诲东通于吴,西通于蜀,皆利其供军财货而已”。南平所倚任的将领王保义(即刘去非),也是粗暴无行。颇有才识的谋臣梁震则耻于做高氏政权的僚属,“不受辟署,终身止称前进士”[4]卷一百三十二:4105。因此,在目前可见的《旧五代史》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跋扈不臣、无善政可纪的南平政权。
南唐政权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南唐在十国中号为强盛富庶,“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也”[5]卷二:234。先主李昪励精图治,倾心下士,深受后世史家所赞誉。嗣主李景虽然不能将李昪之业发扬光大,却也为政宽厚,礼遇士人。但《旧五代史》对二人政绩却只字未提,只在李景一条提及“属中原多事,北土乱离,雄据一方,行余一纪。其地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又尝遣使私赂北戎,俾为中国之患,自固偷安之计”[4]卷一百三十四:4170,将南唐的强盛归因于拣了中原乱离的便宜,加之疆土广袤,才导致强盛的现状。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旧五代史》还指责南唐与契丹交通,为中原之患,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不止是对荆南与南唐,《旧五代史》对楚、北汉等其他政权也存在着贬多褒少的问题。
第三,具有浓厚的正统意识,政治意识形态强烈。
《旧五代史》修撰时,北宋尚未统一,政治、军事环境皆不安定。因此,对堪称为其近现代史的十国史,官方记载的意识形态色彩较为强烈。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历史及人物,《旧五代史》较为温和,所持评价体系较为宽容,这与后世的《新五代史》呈现出强烈的反差。但是,对于十国,它的总体态度却相当严厉,并依据各国对中央政权的恭顺程度,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呈现出浓厚的正统意识。
在《旧五代史》中,承袭诸国的地位要高于僭伪诸国。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僭伪诸国与承袭诸国实在没有太大区别。各国都在自己的割据范围内自成一个独立王国,实在找不出一个自始至终恪尽臣节者。《旧五代史》在承袭诸国中,按照对中央王朝的恭谨程度,将吴越、马楚、南平排了一个等次:对南平与马楚的历任统治者及其朝政皆多贬辞,对他们表面称藩、私下僭越不臣之举多所揭露,比如南平的不臣之状、马楚的“穷极奢侈,贡奉朝廷不过茶数万斤而已”[4]卷一百三十二:4074。而对吴越的“事大勤王之节”较为赞赏,认为“与荆楚、湖湘不侔”,对其历任统治者及政治、经济状况也多赞许之辞。据《旧五代史》记载,吴越受封吴越国王之后,“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寮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4]卷一百三十二:4038-4039。实际上,据林仁志《王氏启运图》、余公绰《闽王事迹》、阎自若《唐末泛闻录》等书记载,吴越曾经私自改元。但《旧五代史》史臣或许是未见到这些材料,或许是未予采信。吴越地位在马楚、南平之上,固然与吴越国运盛于马楚与南平有关,但也与《旧五代史》史臣的态度有关。
在《僭伪列传》中,《旧五代史》史臣并不完全抹黑诸国。史臣称赞王审知在治理闽地期间,“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4]卷一百三十四:4179。因为杨吴政权占据淮南,他不得不每年从海路向中原王朝朝贡,使者因之漂溺者有十之四五。史臣因此将其比作秦末汉初的名臣吴芮。其余如吴政权的杨行密“高材捷足”,南唐于“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后蜀孟知祥“虽无英武之略,然行己恭俭,待士勤至,自赵季良、李仁罕、张业而下,皆优以官爵贵之,厚以财货富之,由是人人各尽其死力”[4]卷一百三十五:4229,各有其优点。但对他们的僭窃之举,《旧五代史》并不宽容。闽王审知死后,长子王延翰嗣位,不久为其弟王延钧所杀。王延钧袭位后,自称皇帝,国号大闽。其后,王氏子弟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最终亡于后唐。《旧五代史》史臣评论闽“始则可方于吴芮,终则窃效于尉佗,与夫穴蜂井蛙,亦何相远哉!五纪之亡,盖其幸也”。江南积吴杨行密与南唐李昪的多年苦心经营,境内繁华富庶,人民生活安定,统治者也很有治绩,但史臣所述甚少,且斥二者是“以伪易伪”[4]卷一百三十四:4197。对“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虽刑罚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颇安之”[6]卷下:62、“治蜀有恩”[7]卷一:7、“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8]卷一:220的后蜀主孟昶,《旧五代史》也未录其政绩,反而有周世宗显德二年(955)五月,“秦、凤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4]卷一百十五:3561的记载。
对于北宋的死敌北汉,《旧五代史》最不留情。一般而言,对十国的首任统治者或其治绩,史臣会有较为正面的描写,唯独对于北汉没有一句褒辞,处处凸显北汉主刘崇的愚愎昏庸。在十国史中惜墨如金的史臣,却不惜笔墨细致描绘了高平之战后刘崇狼狈逃窜的丑态,这在《旧五代史》的十国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旧五代史》将北汉与“恶之极”且“愚之甚”的刘守光,及苛虐残暴的南汉列在一起,痛斥“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今元恶虽毙,遗孽尚存,势蹙民残,不亡何待!”[4]卷一百三十五:4269如果对比后世欧阳修对北汉“其立虽未必是,而义当不屈于周,此其可以异乎九国矣”[9]卷七十一:882的同情、朱熹“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10]卷一百五:2636的言论,则可以看到《旧五代史》极为鲜明的正统意识色彩。
出于政治偏见,《旧五代史》对十国政权及其人物未免持论严厉甚至有失偏颇。对南唐孙晟的描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孙晟,又名孙凤、孙忌,山东人,南唐烈祖李昪与元宗李景时期的重要谋臣,南唐党争中孙党的代表人物。他本为朱守殷的幕僚,后投奔南唐,显德三年(956)出使后周时,因不肯吐露南唐虚实,为世宗所杀,深为南唐人所敬重。但在《旧五代史》里,孙晟却是一个奸诈阴贼之人,几乎通篇为贬词。据《旧五代史》记载,孙晟,“性阴贼,好奸谋。少为道士,工诗”。曾在庐山简寂观,因为喜欢唐朝诗人贾岛的诗,便将贾岛像挂在屋里,以礼事之,被简寂观观主视为妖妄,拿着棍子打了出来,“大为时辈所嗤”。孙晟于是改易儒服,谒唐庄宗于镇州,得授官职。天成中,朱守殷谋叛,孙晟为其幕宾,“实赞成其事。是时,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数骑自随,巡行于市,多所屠害,汴人为之切齿”。朱守殷被诛后,孙晟弃其妻子,亡命江南,因“微有词翰”,曾起草过尊吴王杨溥为让皇的册文,颇受重用。孙晟生活奢侈,“财货邸第,颇适其意。晟以家妓甚众,每食不设食几,令众妓各执一食器,周侍于其侧,谓之肉台盘,其自养称惬也如是”。显德三年(956),后周征伐南唐,孙晟奉命出使后周。世宗对其“礼遇殊优”,屡次问以江南虚实,孙晟却只言“吴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为求,保无二也”,守口如瓶。当时,后周将领张永德与李重进不合,南唐李景知之,秘密令人送蜡书与李重进,密谋拉拢。李重进将蜡书进呈世宗。世宗“怒晟前言失实”,遂将孙晟下狱,与其侍从百余人一并诛杀。及将下狱,世宗令近臣再问孙晟“江南可取之状”,他仍然默然不对。临刑之际,孙晟整理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道:“臣惟以死谢。”
虽然《旧五代史》史臣也承认孙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报之”[4]卷一百三十一:4031,对其从容就死与忠心为主,字里行间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肯定。但是,《旧五代史》是将孙晟列在《周书》传里的,也就是说,把孙晟定位为一个从中原王朝出逃的叛徒。孙晟违反世宗的命令,在被周军围困的寿州城下,劝南唐守将刘仁赡死守城池、以尽臣节一事,是他下狱被杀的导火索,但此事在现存《旧五代史》中却没有记载。众所周知,原《旧五代史》已经佚失,现存版本是辑本,那么,这一事迹有可能在原书中是存在的。但是,观《新五代史》也未取此事,仅在《刘仁赡传》中有一句“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孙晟等至城下示之”[9]卷三十二:352的含糊记载。《新五代史》材料多本《旧五代史》,加以删削,兼采笔记、小说而成,且《新五代史》极重臣节,本应对此事大书特书。由此推断,《旧五代史》很可能也没有这一记录。《旧五代史》主要在《五代通录》及五代实录的基础上删削而成,而现存《周世宗实录》对此事并无记载,但其史料缺失较多,因而不排除有两种可能:一是实录中并未记载此事,史臣在实录基础上加以简单删减,未及注意此事;二是实录中原有此事,却被史臣遗漏。因史料所限,已无法确知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史臣给孙晟树立的形象并不高大。原因大约是吴—南唐乃中原王朝的重要对手,至《旧五代史》撰修时,南唐虽已奉中原正朔,但仍是貌合神离,心怀异志。因此,对孙晟的死,《旧五代史》以“议者以晟昔构祸于梁民,今伏法于梁狱,报应之道,岂徒然哉!”[4]卷一百三十一:4030作为结论,只在最后以寥寥数语,言其以死报江南之恩,足见其对敌国之臣的态度。
与宋初官方对孙晟的描写不同,在民间私史尤其是南唐遗民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孙晟,一个忠诚耿直、有文辞、有才干的南唐忠臣。
具有较强遗民色彩的《钓矶立谈》对孙晟的评价相当之高,“宋子嵩初佐烈祖,招徕俊杰,布在班行,如孙晟、韩熙载等,皆有特操,议论可听”。他曾当面数落深受宠信的冯延巳:“上置君于亲贤门,下期以道义相辅,不可以误国朝大计也。”作者赞扬孙晟“可谓有先知之明,世之议者,乃指以为由忮心而发,岂其然耶!”宋齐丘晚年惑于小人,孙晟与韩熙载力劝宋齐丘,宋齐丘皆不听,后来果然贻误国政,退居九华山。一天,宋齐丘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感叹说:“吾貌有惭色,应愧孙无忌、韩叔言”。后周伐南唐,孙晟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北上,面见世宗,自知不免,私下对副使王崇质说:“吾思之熟矣,终不忍永陵一抔土,余非所知也。”最终“不顾身首异处,违诏而致其区区之忠”,被世宗诛杀。作者高度赞扬孙晟与刘仁赡,“为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与古烈士比”,指责周世宗“曾不标异以奖薄俗,而俱从显戮,文武之师,固如是乎!”[11]223其爱憎一望可知。陈彭年《江南别录》也突出记载了孙晟呼劝刘仁赡死守城池,从容被诛之事。《江南余载》虽成书较晚,但却是以南唐遗民郑文宝的《江表志》为稿本撰成。它认为孙晟于明宗年间跟随秦王李从荣,李从荣败死后,孙晟才亡命江南。渡江之前,“追骑奄至,晟不顾,坐淮岸,扪敝衣啮虱,追者舍去。乃渡淮”,表现了他的机智与沉着,并称“江南文臣,烈祖时唯称杨彦伯、高弼、孙晟、李匡明、龚凛、萧俨、成幼文、贾泽”[12]卷上:238,对孙晟也多褒辞。
在《江南野史》笔下,孙晟家贫好学,中后梁进士,后来说服朱守殷谋叛乱。叛乱失败后,孙晟落发为僧,逃往江南,“才宏口辨,词说泛滥”,常为宋齐丘所忌惮,也为嗣主李景素所“畏重”。为相期间,“颇有志于重熙富庶,燮育疲民”,并辛辣讽刺冯延巳“玉巵象瓯,盛内狗秽;鸡树凤池,栖集枭翟”。《江南野史》还突出记载了孙晟临死的事迹。“仁赡坚守不下。世宗怒江南失约,遂引忌责之。及话江南事实,忌对以兵甲尚强,宋齐邱良相也。乃致忌于楼车,令呼仁赡趣降,忌知终无生还之理,不忍负国家恩顾,至城下,乃反辞大呼曰:‘刘仁赡,汝好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即至。我遇强暴,死在旦夕,汝可效死立忠,无为降虏,使我羞于泉下。’左右交击其口,忌颜色自若”[13]卷五:186,世宗大怒,加之左右中伤孙忌,以劝朱守殷谋反事,世宗遂杀孙晟。临刑前,孙晟望南而拜,从容就刑。
如此可见,孙晟在南唐遗民的著述中是以忠臣面目出现的,“可以与古烈士比”。这与《旧五代史》的描写全然不同。对孙晟的死,《旧五代史》冠之以“报应”,只在最后以寥寥数语,言其以死报江南之恩,足见其对敌国之臣的态度。这与民间私著尤其是遗民笔下的十国史明显不同。两种文本的相互对照,使五代十国的历史呈现出耐人寻味的不同面貌。
对投奔敌国者,史臣的态度颇为严厉。卢文进曾背叛后唐投靠契丹。明宗继位后,他又率众归附。后晋高祖称帝后,与契丹约为父子,卢文进惧不自安,于天福元年(936)冬投奔南唐后主李昪。李金全任安远军节度使期间,政事皆委于亲吏胡汉筠,胡汉筠贪诈残忍,所为多不法,晋高祖因此命贾仁绍代其职,准备召回胡汉筠。胡汉筠却鸩杀贾仁绍,并教李金全将自己留下。天福五年(940)夏,高祖命马全节代替李金全为安州节度使,胡汉筠惶惶不安,遂骗李金全说朝廷将治其罪。李金全大惧之下,投奔南唐。对此,史臣斥责“文进惧强敌之威,金全为舆台所卖,事虽弗类,叛则攸同,咸附岛夷,皆可丑也”[4]卷九十七:3002。
即使是自始至终忠于敌国之人,《旧五代史》也有所保留。刘仁赡是五代十国威震南北的名将,对南唐可谓忠贞不贰。后周讨伐南唐期间,他死守寿州,甚至不惜杀掉劝自己投降的亲生儿子,后周军队屡攻而不能克。后来,刘仁赡病重不能视事,副使孙羽等开城降周,而非刘仁赡之意。对此,南唐遗民作品《钓矶立谈》等皆有明论,《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也都有考证。《旧五代史》却独持降周乃刘仁赡之意。这样的偏见无疑会影响《旧五代史》的客观公正性。
第四,突出显示北宋王朝的皇恩与天威。
如前所述,《旧五代史》对僭伪诸国有一些正面的描写,如吴杨行密的“高材捷足”,闽的“一境晏然”,南唐的“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后蜀孟知祥的“人人各尽其死力”,但这些描写却是为了突出北宋的皇恩与天威。比如,江南虽然积吴杨行密、南唐李昪等数十年辛苦经营,是近代最为强盛的“僭窃”之地,但在后周与北宋的讨伐之下,简直不堪一击,“洎有周兴薄伐之师,皇上示怀柔之德,而乃走梯航而入贡,奉正朔以来庭,如是则长江之险,又何足以恃哉!”[4]卷一百三十四:4197闽更是“与夫穴蜂井蛙,亦何相远哉!”南汉政权地处偏远,趁中原大乱时据有岭南,长达五十余年,“刘晟据南极以称雄,属中原之多事,洎乎奕世,遇我昌朝,力惫而亡,不泯其嗣,亦其幸也”[4]卷一百三十六:4269。蜀地险峻,易守难攻,相继存在前、后蜀两个政权。前蜀为王建所建,传至其子王衍,亡于后唐。后蜀为孟知祥所建,传至其子孟昶,亡于北宋。《旧五代史》史臣特引《剑阁铭》中“惟蜀之门,作固作镇,世浊则逆,道清斯顺”之句,加以对比:前蜀亡国后,后唐庄宗昏庸无道,不久被弑,奉命在蜀地主持军政事务的孟知祥逐渐割据此地,并于后唐应顺元年(934),趁潞王从珂与闵帝争夺皇位的混乱之机在成都称帝,史称后蜀。因此,史臣称前蜀亡国后,“兵力虽胜,帝道犹昏,故数年间得之复失”。后蜀孟知祥称帝仅六个月即发病去世,其子孟昶继位,史称后主,在位三十余年,亡于北宋。尽管平蜀的过程中,宋将王全斌等人纵容士兵“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14]卷二百三:754,渗透了蜀地民众的血泪,而孟昶亦在到达汴京、受封秦国公仅七日后便死去,史臣仍然盛赞“及皇上之平蜀也,煦之以尧日,和之以舜风,故比户之民,悦而从化”[4]卷一百三十五:4232;并以前蜀王衍被族诛,后蜀孟昶则受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的例子,来凸显北宋的真主圣君、皇恩浩荡。
综而观之,《旧五代史》对于十国历史不但不加经意,且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具有浓厚的正统意识。这虽然背离了史书当求客观的准则,但亦显示出在战事纷繁的年代,《旧五代史》这部官方史书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以及鲜明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
[1] 程俱.麟台故事校证[M].张富祥,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 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 陆游.南唐书[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
[6] 张唐英.蜀梼杌[M]//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八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7]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9] 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佚名:钓矶立谈[M]//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2] 佚名.江南余载[M]//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二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3] 龙衮.江南野史[M]//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三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4] 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兼论《新编五代史平话》为元编、元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