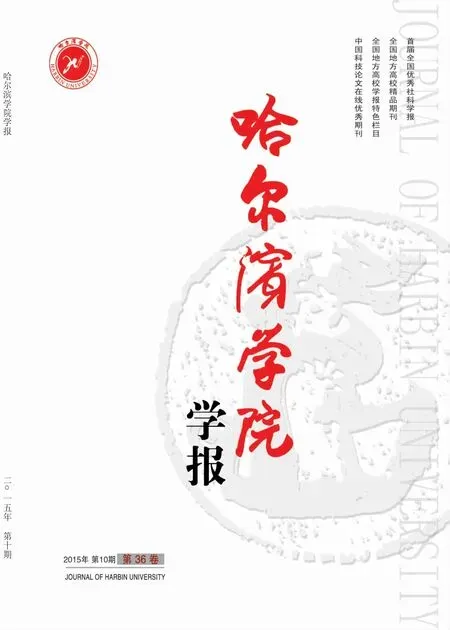唐代法律中家庭直系亲属身份关系刍议
郭武轲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郑州 4 50002)
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尤以贞观至开元为盛。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民族关系改善。从法律的视角来看,被誉为“法典之王”的《唐律疏议》也诞生于这一时期。盛世同样影响了婚姻家庭关系,因此唐代的婚姻家庭关系既有和前代相似的方面,同时又不乏特色,堪称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家庭关系的范本。本文旨在讨论家庭中的身份关系。欲展开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区分两个概念,即家族和家庭。家族是由西周的宗法制度演化而来的。宗法制度中,宗子掌有祭祀权、财产权以及管理宗族中大事如婚丧嫁娶等事务的权力。宗法组织消失之后,家族取而代之,家族是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结合,而家庭是家族中基本的单位。家族中有一人充当族长,掌管祭祀、处断族内纠纷等职权。比宗子的权力弱化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族长本身不掌有财产权,因为族内每个家庭是各自分居的,家内事务多由家长负责,族长是不干预的。家庭作为同居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范围较家族为小,包括父家长型的家,即直系亲的同居共财,以及复合型的家,即旁系亲的同居共财。[1](P119)前者的身份关系包括祖父母与孙子女的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后者则比前者增加了兄弟关系、叔侄关系。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直系亲属之间的身份关系。
一、男性与其他直系亲属之间的身份关系
(一)夫妻关系①
男女结合才能衍生后代,因此夫妻关系是婚姻家庭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男权社会,在婚姻家庭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妻子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作为丈夫的附庸而存在,这种关系通过卷帙浩繁的文献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表现出来,如《韩非子·忠孝》云:“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唐代的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唐律中多次出现“夫为妇天,尚无再醮”,[2]“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3]“夫者,妻之天也”。[4]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在法律上主要通过对夫妻相犯行为所规定的法律后果的不同表现出来,唐律对夫妻相犯处罚的总原则是夫犯妻从轻,妻犯夫从重。夫妻斗殴,同一罪刑,妻殴夫加重其刑,夫殴妻则减其刑。“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过失杀伤者,各减二等。”[5]“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过失杀者,各勿论。”[5]由此可见,妻子的地位明显低于丈夫,而仅仅相当于丈夫的卑幼。丈夫对妻子拥有绝对的权利,主要包括为:
第一,夫得典卖其妻。唐律是禁止夫典卖其妻的,在“和娶人妻条”中明文规定:“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两年;妾,减二等,各离之。即夫自嫁者亦同,仍两离之。”然而晚唐时期民间由于灾荒、战乱所迫,典卖妻子是一直不能为法律所禁绝的。《通鉴》载唐代乾符元年:“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费。”
第二,夫得单方出妻。唐代的离婚形式有三种,分别是七出、义绝与和离。其中七出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只要丈夫有单方的意思表示便得以休妻。七出包括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和恶疾。以常理看来,七出之中至少无子和恶疾并不能仅由妻子来承担过错,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的出现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七出在唐代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只有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家庭和谐稳定,社会才能够长治久安。七出的创制在家庭伦理、宗庙祭祀、家庭财产共有等方面无一不是为家庭利益所考虑。
(二)父子关系
虽然家庭的范围有大有小,但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个统治的首脑,他对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卑幼行使权力。《说文解字》中解释“父”字时云:“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从杖”,由此可见,父字的本身即含有权力和统治之义。中国古代亦有“夫者妻之天”的观念,所以夫妻实为一体,法律中所规定的有父母共同形式的权利就其本质而言是父权。主要包括:
第一,父母对子女的惩戒权。唐律中严格规定子女对父母言听计从,否则便是子孙违反教令,便要面临两年的牢狱之灾。[6]一旦子女违反教令,父母可以对其进行惩戒,但必须有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擅自将子女处死,便会有公权力干涉。唐律不问理由如何,杀死子孙皆处徒罪,子孙违反教令而杀之,也只能较故杀罪减一等,殴杀徒一年半,刃杀徒两年。[5]但是这一规定和普通人犯杀人罪的处罚相比,显然是轻多了。
第二,父母对家庭共有财产的支配权。子女不得在父母在世的时候与父母分家析产,否则不仅有亏侍养之道,而且大伤慈悲之心,因此法律将父母在别籍异财列为不孝罪之一,置于律首,如有违犯,处三年徒刑。[7]子女也不得擅自处分家中的财产,但是许多富家子弟受到教唆挑拨瞒着家长卖掉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法律设立了保护家长的规定,即如果家长否认的话,交易视为无效,责令返还标的物,处罚卑幼、对方以及中间人的制度。如唐律中规定: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7]
第三,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决定权。中国古代的婚姻的目的是合两姓之好,因此几乎是由直系尊亲属尤其是男性直系尊亲属全权掌控的,男女结合若顾及双方的感情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唐律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3]就主婚权的顺序而言,直系尊亲属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顺序的主婚人,嫁娶违律的婚姻由主婚者负法律责任,嫁娶者无罪。[3]这是因为祖父母、父母有绝对的主婚权,子孙不能违背,所以法律上的责任由主婚者负全责。父母的意志不仅是子女婚姻成立的条件,同时也可以左右子女婚姻的撤销。最为典型的为七出中“不事舅姑”的规定,与其说是客观行为,不如说是姑舅的主观态度。此外,三不去中曾持舅姑之丧为不得离婚的要件,不在七出之限,可知父母在子女婚姻上的重要性远重于子女本人。
在此处还有必要讨论家庭中的拟制血缘关系,即养父母同养子的关系。如果一个家庭之中没有男性继承人,为了使祖先的血脉得以绵延,就需要立嗣,即在宗族中收养一个男性卑亲属作为继承人。除了早幺的男婴外,所有的没有男性继承人的男子都可以立嗣,立嗣可以在他生前进行,也可以在他死后进行,养子实质上最主要的功能是祭祀。作为祭祀的物品,如果不是由得到与祖先相同的血的后辈所贡献的话,则被认为祖灵就不能享受这些祭品。[1](P28)所以唐律规定: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在这里立嫡违法主要指违反了先后顺序,即应以嫡妻之子为嫡子,疏议中明确规定了立嫡的先后顺序,如果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则可以立庶子为嫡,众多庶子中必须先立年长的,违者徒一年。如果嫡子有病或者犯罪,就立嫡孙,如果没有嫡孙,就立嫡子的同母弟,没有同母弟,就立庶子。[7]养子同养父母的关系和亲生父母子女的关系别无二致。由于养子的身份牵涉到家族血缘的纯洁性,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收养外姓养子为法律所不容,但是唐代法律网开一面,准许在一定的条件下收养异性子女。唐律规定:“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7]但是异性养子不能立为嗣子,不能继承宗祧。唐代的收养制度和前代相比有其合理之处,允许收养三岁以下的弃儿体现了立法者一定的人道主义,但是三岁这一期限也不尽合理,因为即使是十几岁的儿童独立生活仍要面临不小的挑战。
(三)祖父母同孙子女的关系
虽然服制上为父服斩衰,为母仅服齐衰,为祖父母服齐衰,但在法律上,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的关系可以比照父母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绝对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如:法律同样处罚祖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的犯罪行为,殴詈祖父母、告祖父母同殴詈父母、告父母同罪。
由此可见,唐代男性在家庭中占据着支配地位,除了不能擅自剥夺卑幼(包括妻子和子女)的生命外,他们可以任意惩戒卑幼,而卑幼只能对丈夫或父亲唯命是从,否则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然而唐代男性的支配地位随着女性地位的上升而受到一些挑战,下文将从女性同其他家庭成员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这一变化。
二、妇女与其他直系亲属之间的身份关系
唐代女性的地位较之前代有所提高,甚至出现了临朝称制的女皇帝武则天。究其原因,首先,意识形态方面,唐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儒释道尽展风流。佛教主张众生平等,道教宣讲个性的张扬,这对于解脱儒教对妇女的束缚大有裨益。其次,政治方面,唐代是处于门阀世族制度逐渐衰落和解体的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是选官制度的变化,出身于庶族的官吏得以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体恤民间疾苦,因此唐代的统治呈现出开放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唐代女性才有可能大胆地追求个性解放。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唐代受胡俗的浸染,因而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地位。隋唐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唐代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唐世祖妻独孤氏,高祖李渊妻窦氏,太宗之皇后长孙氏就都是汉化的胡人。胡人为受礼教制约的汉民族注入了活力,唐代社会风俗受胡风影响显著,如妇女的服饰出现了效仿少数民族而为礼教视为有伤风化的袒胸窄袖服。这一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妇女地位的提高成为可能。
(一)从女性的角度看夫妻关系
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提高,但是在作为指导思想的礼教的束缚之下,妇女在家庭中的人身地位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放。妻子对于丈夫主要还是以义务为本位。妻子对丈夫的义务主要包括贞操义务和同居义务。唐律中分别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8]和“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3]便是对这两种义务最好的注脚。在宽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妻子的地位又有所提高,主要表现在:
第一,妻子有部分离婚的决定权。如前所述,唐代离婚的主要形式是七出,但是由于唐代的婚姻制度受胡俗影响较大,和离即今天所谓的协议离婚一度盛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妇女的离婚权受到法律保护。如唐律中规定可以要求离婚的条件为丈夫殴打妻家亲属,丈夫杀害妻家亲属,丈夫强奸妻家女眷,丈夫卖妻为婢。还规定“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3]当时有不少离婚是由妻子提出的,如初唐的刘寂,其妻夏侯氏因娘家父亲失明,便坚决要求同刘寂离婚,回家侍候父亲;中唐的杨志坚好学而家贫,妻子王氏坚决要求同他离婚,时任地方长官的颜真卿虽然认为此举有伤风化,但还是判了他们离婚。[9](P1126)妇女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婚姻而单方提出离婚要求,这在受三从四德钳制的中国古代社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这种现象在唐代的出现足以看出当时妇女地位的提高。
第二,寡妇有再婚的权利。由于唐代贞操观念相对淡漠,所以寡妇改嫁的现象极其普遍,只要丈夫死后过了服丧期,妻子便能够再嫁。以公主为例,唐代共有211位公主,明确记载的出嫁的有123位,其中再嫁的有24位,其中还有三次嫁人的。[9](P1124)上层社会尚且如此,民间也不会把“从一而终”视为圭臬。唐初统治者颁布诏书,鼓励寡妇改嫁,贞观元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在诏书中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制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妇合。”[10]统治者之所以如此规定,一方面是宽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增加税收的考虑。唐代的税制实行租调庸制,朝廷规定一部分人免除赋税劳役,寡妻妾也在其中,因此鼓励寡妻妾再嫁也是增加税收的一种策略。唐代法律同时也尊重寡妇的自由选择权,如果妻子想要为亡夫守志,那么除了至亲尊长,其他人是无权干涉的。唐律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3]南宋大儒朱熹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11]唐以后,宋代教育更强调身体的禁锢,男性内心的处女情结在这一时期逐渐得到强化,为了取悦男性,缠足等毁坏身体的陋习也在这时得以发端。[12]这从反面再次说明,唐代妇女地位之高,为历代巅峰。
(二)子妇同舅姑的关系
子妇对舅姑,犹如子女事父母,悉心服侍,惟命是从。如前所言,不事舅姑作为离婚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子妇唯有恭敬勤勉,如履薄冰。子妇如果殴詈舅姑是当然的加重量刑的情形。唐律规定“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须舅姑告,乃坐。);殴者,绞;伤者,皆斩;过失杀者,徒三年;伤者,徒二年半。”[5]
(三)寡母同子女的关系
由于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导致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所改善。唐代母亲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高宗上元元年,武则天上表“请子父在为母服三年”,[13]此前,父在,子仅为母服丧一年;父死,为母服丧三年。此后,父母在丧服方面享有形式上的平等。母亲对儿女的权利主要发生在父亲死后,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夫妻关系实为“夫妻一体主义”,由父亲代表父母二人承担对儿女的教育权、惩戒权等权利。如果父亲先于母亲死亡,这些权利自然而然地落入寡母手中。寡母对子女的权利主要涵盖:
第一,寡母对子女的教育权和惩戒权。寡母对子女的教育权在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是一以贯之的,最为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孟母三迁”。唐代科举考试盛行,学而优则仕是各社会阶层登堂入室的重要手段,因此重视教育的风气大盛,这种教育不仅包括知识的传授,也有人格的养成。父亲死后,这一重任就由寡母来承担。在新旧唐书《列女传》中,记载寡母对子女进行教养的事例可谓是汗牛充栋。如泗州长史董昌龄的父亲早逝,“受训于母”。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不发丧,举兵反叛,此时董昌龄是吴元济的手下,董母杨氏教育董昌龄“逆顺之理,成败可知,汝宜图之。”董昌龄没有下定决心,吴元济又任命董昌龄为郾城令。杨氏再一次告诫他说:“逆党欺天,天所不福。汝当速降,无以前败为虑,无以老母为念。汝为忠臣,吾虽殁无恨矣!”浓浓的舐犊之情感化了董昌龄,他献出郾城迎接朝廷军队的到来。宪宗召见董昌龄并为他升官加爵,董昌龄感激涕零地说:“此皆老母之训。”[14]寡母不仅有教育子女的权利,在极端的条件下,寡母还能够惩戒子女,若寡母以不孝罪为名要求官府将子女处死,官府是不会拒绝的。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唐时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对寡妇说:“汝寡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说:“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悔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最后官府按照她的要求处死了儿子。②从这一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寡母对于子女的权利是很大的。
第二,寡母对家庭经济的管理权。唐律规定法定继承要在父母死亡后的特定的时间开始,因此父亲死亡而母亲还健在的情况下,卑幼是不能得到应属于他的那部分财产的。此时财产由寡母代管,她实质上充当着父亲和儿孙之间中介的角色,对于这部分财产,她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唐律中规定的父亲当家时对子女的经济权利对于寡母当家同样适用。寡母的家产管理权也可以通过文献得以佐证,如韩愈的《唐代鄎国夫人(何氏)墓志铭》中有:“元和二年,李公(栾)为户部尚书,薨。夫人遂专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养嫁娶如一。……御憧仆,治居第生产,皆有条序。居卑尊间,无不顺适。”③可见在这位寡母的管理下,家庭井然有序。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无论寡母对子女享有多大的权利,这些权利究其本质而言是父权的自然延伸,即“谁是家长谁就是父权的行使者”。[15](P157)
综上所述,唐代家庭中直系亲属的身份关系仍然没有摆脱以父权为主导的窠臼,但是由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相应的有所改善,这些都得益于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和统治者较为宽松的统治方式。即便如此,家庭生活中男性和女性的地位仍然不可同日而语,在男尊女卑的环境中,真正的男女平等只能是一种奢谈。
注释:
①唐代的夫妻关系形式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因此本文中的夫妻关系如果没有特指的话都是指丈夫和正妻的关系。
②张鷟,朝野佥载:卷上,转引自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9月第一版,第12页。
③转引自段丽塔,《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1]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中)[M].
[3]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下)[M].
[4]唐律疏议:卷一·名例[M].
[5]唐律疏议:卷二十二·斗讼(二)[M].
[6]唐律疏议:卷二十四·斗讼(四)[M].
[7]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M].
[8]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上)[M].
[9]白寿彝,史念海.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全唐文:“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M].
[11]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历代类[M].
[12]王雪.宋代女性身体束缚与摧残[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4).
[13]旧唐书:卷二十七·礼仪志[M].
[1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三·列女传[M].
[15]徐连达.唐朝文化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