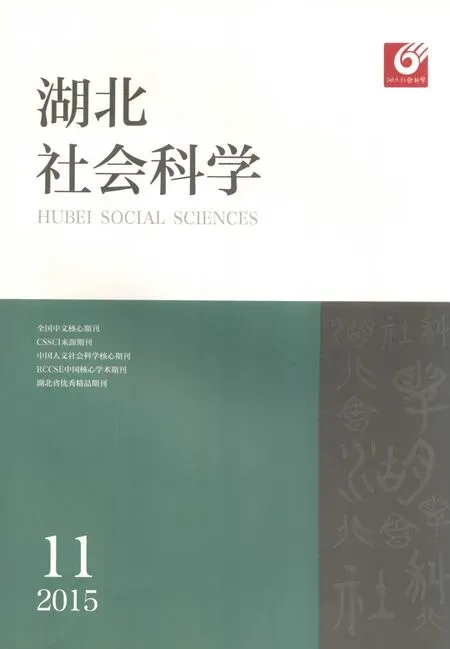试论安旗李白研究的贯通观
——以《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为例
张淑华
(1.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2.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陕西西安 710072)
试论安旗李白研究的贯通观
——以《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为例
张淑华1,2
(1.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2.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陕西西安 710072)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对李白现存诗文大部分进行编年,以梳理李白一生经历命运、思想脉络及诗歌创作特点为主旨,并围绕此主旨从校勘、注释、编年等各个方面将这一主旨贯通起来。校勘方面采取按断校,避免了不必要的异文之争;注释方面力求简洁,并注意把词语还原到诗歌语境中去理解其准确意思,注中有评,通过评的方式点明诗歌写作主旨及技巧;编年方面注意结合李白其他诗文和同期交游诗人的诗文,善于利用诗歌中的情绪导向并结合诗人经历,联系当时历史事件与社会环境寻找编年的线索和依据。
安旗;李白研究;贯通观
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谈及整理史料的三种方法时,特别在校勘与训诂之外强调了贯通的重要性。胡适认为校勘是本子上的整理,训诂是字义上的整理,而贯通是指融会贯穿一书的内容要旨,旨在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否则就会流于支离碎琐。[1](p21)古代文学的研究面对的是古籍和史料,如何在校勘与训诂的基础上,将散乱的文献贯通起来成一家之说,是每个研究者都要面临的难题。
安旗先生是李白研究的大家,在李白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后出版了《李白纵横探》、《李白传》、《李白年谱》、《李白诗新笺》、《李诗咀华》、《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太白别传》等十数部李白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些研究贯通了李白的生平经历、诗歌特色和作品内涵,形成了安氏对李白其人其诗的总体认识,亦形成了鲜明的安氏李白研究特色,使得安旗先生的李白研究在当代李白研究者中独树一帜。其中安旗及其弟子薛天纬、阎琦、房日晰共同完成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版)更是集中体现了安旗先生的李白研究成果,是其李白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书将刻画李白一生行踪、思想发展、作品内涵、创作规律作为主旨,通过诗歌编年展现了出来,很好地体现了安旗李白研究的贯通观。
编年本比起其他分类本或分体本的优势便是可以知人论世,形成一个对诗人一生经历和情感变化的全面认识,但是编年的基础是校勘和注释,不然不足以正确认识诗人作品的真实文本、深刻寓意及艺术特色。因此,有效统筹校勘、注释、编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将编年的目标很好地体现出来。安旗这本《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通过注释李白诗歌,将李白一生生活和创作经历的目标贯通在校勘、注释、编年等具体方面,在诗集编年注本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
一、校勘方面——定是非,做判断
校勘是整理古籍的基础,是获得准确文本的第一步,因此大多数注书者都注意校勘并于此用力甚多。然而,由于安本的主要目的在于编年,再则其所选底本已是清代大家王琦精校精刻的本子,且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以下简称瞿朱本)已经在校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故本书比较信任地使用了前人的校勘成果,自己于校勘不下更大的功夫,而是将校勘放在注释中,看成注释的一部分,是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这从该书凡例中所申明的校勘原则即可看出。这些原则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两点:一是凡底本与校本有异文者,不一一出校。出校原则为:(1)底本误。(2)异文可致歧解者。(3)异文文字差异较大者。(4)底本或校本注云:“某,一本作某”,虽然所谓一本今不详何本,仅出校记而不改动原文。二是凡底本明显有误而校本不误者,则据校本改正。[2](凡例)
校勘的目的无非在尽量恢复文本原貌,为准确理解原文奠定基础。安本对于校勘的态度显然是择善而从、加以取舍、唯求其是,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李白诗歌。根据凡例原则,一类是出校但保留底本原文者。比如:瞿朱本《金陵酒肆留别》共出校异文四条,分别是“风吹”、“满”“唤”、“试问”,[3](p928)然安本仅出校“风吹”一条,校记云:“风吹,两宋本、缪本俱作‘白门’。”[2](p72)究其原因,可能是因此条异文属于“异文文字差异较大且异文可致歧解者”。又如《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瞿朱本出校记十条,[3](p610-614)安本仅出校记两条,具体是“阴阳乃骄蹇”句中的“阴”字与“乃”字。校记云:“阳,萧本作‘霾’;乃,两宋本、缪本、咸本作‘仍’”。[2](p120-124)依旧符合凡例所云“异文差异大”及“可致歧解者”。
另一类为安本认为底本明显有误者,就直接根据校本改正了。如:《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瞿朱本出校十条,[3](p924-926)安本仅出注“云旗”一条,校记云:“云旗,王本作云骑,据两宋本、缪本、咸本改。”[2](p1643-1646)查其诗歌原文为:云旗绕彭城,显然“云骑”文意不通。又如,瞿朱本《梁甫吟》共出注十四条,[3](p211-212)而安本仅出注一条“广张三千六百钓”之“钓”。校记云:钓,王本作钩,据咸本改。[2](p213)因为“三千六百钓”指姜太公八十钓于渭十年间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钓,故曰三千六百钓,非钩也。以上两类对待异文的例子在全书多处可见,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安本对于能从文意上明确判断正误的异文所采取的这种“定是非”的态度,近于清段玉裁考证一派之主张。因为“顾自唐以来积误之甚者,宋本亦多沿旧,无以胜今本,……胸中未有真古本汉本,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4](p2)因为诗歌文本由于篇幅短小,在传播之时多为互相传抄,辗转传抄过程中就难以避免产生各种异文,因此,校勘过程中不必完全拘泥于古本、宋本,应根据上下文作出合乎诗意的判断与取舍。这种“按断校”方式,是抱着“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4](p332)的态度,其所强调的是义理推断的重要性而弱化对版本的依赖。抛弃清代考据学“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5]的做法。将不影响诗意表达的部分校勘内容忽略不计,避免繁称杂引,一切为扫清读者阅读障碍而服务,把梳理李白一生的生活与创作情况作为注本的核心目标。
二、注释方面——将词句注释还原到诗歌中把握
按照中国传统注释学的观点来看,注释就是发现和揭示作者寄托于作品中之原意的过程,因此注者必须尽一切可能想方设法还原诗文本意。这就要求注家本人的学力必须深厚,才能了解诗文出处、典故,才能正确理解作者原意。同时,传统注释学还倾向于认为一切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都存在着互文性。因此,繁复地、不厌其烦地罗列可能与注释文本有互文关系的其他文本,成为了很多注本的特点。然而,安本对于注释采用的是较为简洁的注释方法。一般只注重点或难点,从不字字句句皆注。因此,我们看到安本的注释基本只引一条,说明情况即可,因为目的在于扫清阅读障碍,便于读者理解诗意。
1.疏通文意,方便理解。
诗中涉及之名物典故经常是后人阅读典籍的障碍,所以,安本于这些词汇的注释非常注意,比如:安本《襄阳歌》中注释了“接”、“舒州杓”、“力士铛”,[2](p270-275《)天马歌》中注释了“兰筋”、“权奇”、“寒风子”“逸景孙”,[2](p1570-1575《)梁甫吟》中注释了“朝歌屠叟”、“高阳酒徒”、“投壶”,[2](p1570-1575)因为不解释这些词语无法理解诗歌本意,但是又摒弃了
有的注本甚至连“轩辕”、“经籍书”、“落魄”、“仗剑”、“天伦”都注释、都引出处的繁琐注释风格。始终将是否必要看成是出注的重要取舍标准。
因此,注释不能只强调对名物典故本身的注释,还应该注意它在文中的意思,方能作出更精准的注释。比如:瞿朱本对《天马歌》中“尾如流星首渴乌”之“渴乌”注云:“《后汉书》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漉南北郊路。章怀太子注: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3](p234-238)安本注云:“渴乌,古代漏刻计时之部件,铜为之,其状如曲颈之鸟。”并引《初学记》《刻漏法》中“以铜为渴乌”句证之。[2](p1570-1575)比较两者注释可发现:两书引用注释材料不同,皆可证之。但惟安本注释了渴乌的形状,方便读者理解诗中“尾如流星首渴乌”的意思。又如,安本在注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之“蓬瀛”后,云:“二句谓其欲建言而不能,遂有出世之志。”注释完“公卿奴犬羊,中谠醢与葅”中之“谠”、“醢葅”后,安本还引《通鉴·唐纪》至德元载杀害劫掠京城公卿的残酷记载来坐实这句诗意。
2.在具体诗句中注释词语的细微差别。
对于同一词语多次出现在不同诗作中时,安本的处理方法是采用“互见”法,即直接表明此词语见某注中。但是,有时候同一个词语会以不同面貌出现在不同诗歌中,对于这种现象,安本都是将词语放在具体诗歌语境下,根据诗歌内容作出更贴切的注释。
如“青鸟”一词多次出现在李白诗中,安本对其采取的注释方法也不尽相同。对《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安本中“青鸟明丹心”之“青鸟”,安本引《艺文类聚》所引《汉武故事》中的青鸟为西王母使者的典故。注云:“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鸟,侠侍王母旁。后因称信使为青鸟。”;[2](p1476-1487)对《题元丹丘颍阳山居》中“益愿狎青鸟”中之“青鸟”注云:“传说中之神鸟,喻元丹丘。《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西王母之山……有三青鸟。又“有元丹之山……青鸟。”[2](p206-207)对《寄远十二首》中“三鸟别王母”之“青鸟”注云:“三鸟,即三青鸟。《山海经·西山经》:“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郭璞注:“三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者。”后人言使者多借用之。”[2](p225)同样是“青鸟”这个词语,出现在不同的诗句中用意不同,安本正是没有简单地看待这些词语的意思,而是将词语还原到具体诗歌中去把握其最准确的意思。
3.注中有评,点透写作用意。
安本在注释中时时将注与诗歌分析结合起来,通过对重点诗句的分析,将整个诗歌的写作特点凸显出来,帮助读者理解李白诗歌的写作技巧及深意。
比如:《蜀道难》中注“西当太白有鸟道”之句时,对“尔来四万八千岁”以下六句的写作用意做了注释,认为“写自古以来秦蜀二地隔绝之状。”注释“地崩山摧壮士死”句典故后,认为“二句乃化用二事写古蜀道之开辟。”“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注云:“二句乃旅人扪心自问之辞。古代诗词中不乏此例,如陶潜“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又如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诸句中“君”皆自谓。以上写蜀道北段之艰险。“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注云:“亦旅人扪心自问之辞,写蜀道中段之艰险。”“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注云:“以上写蜀道南段之艰险。”[2](p175-188)
又如:《玉真仙人词》“少室”注释完后,云:二句以王母喻玉真,以少室喻其修炼之处。“蟏蛸结思幽”注释完后,云:“见蜘蛛结网而兴深远之思。”“蟋蟀伤褊浅”注释完后,云:“句谓闻蟋蟀夜鸣而有失志之感。”“一斛荐槟榔”注释完后,云:“以上四句以刘穆之自喻,暗刺张垍。”[2](p118)再如:安本注释《清平调词三首》中“云想衣裳花想容”之“想”意为“如也”,并指出其为比喻之词;“露华浓”之“露华”为露珠,并指出此句承上句之喻,花上着露,形容杨妃之容光艳发。[2](p455-461)
再如:注释“巫山云雨”时引宋玉《高唐赋》序、《神女赋》序说明李白此诗总《高唐》、《神女》二赋之意,谓巫山神女惟梦中得见,不可果致,故曰“枉断肠”,以反衬君王今日之有杨妃在侧之欢。[2](p455-461)
三、编年方面——强调李白诗作风格特点和人格形成与发展
安旗曾经借其《李白诗秘要》表达过对诗歌诠释的看法:“知人论世、尚友古人遂成为诠释诗章必要之途。”[6](前言)又说:“任何作者、任何作品皆是
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势须从其所属之环境与背景考察之。……总当顾忌作品的全体,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及精神状态。”[6](前言)由此诗歌诠释观念可见,安本在为李白作品编年时,目的正是要通过对李白诗文的梳理,结合当时李白生活之时代背景及其经历,把握李白一生创作风格之形成轨迹、人格命运之发展变化轨迹。因此,安本在编年方面注意从与李白相交游之同时人、李白其他诗文,李白诗作情绪,李白的经历以及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等多方面方面考察,寻找编年依据。
1.根据李白诗作或同期他人诗作,发现系年线索。
对于某些重要生平经历,诗人可能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诗文中有所记载,安本熟悉诗人的每一首作品,将其中涉及某些重要时间点或事件的诗文联系起来比较,发现了其中蛛丝马迹的联系。如《初月》、《雨后望月》、《对雨》、《晓晴》、《望夫石》五首诗安本将其皆系于开元三年,李白十五岁之时,首先是基于王琦曾对录自《文苑英华》的这五首诗做过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些诗可能就是《唐诗纪事》引《彰明逸事》中所说年少时写的那些颇类“宫中行乐词”的诗作。安本又认为:“杨天惠所著《彰明逸事》访之邑人,当非无稽之谈”,应该所记为实;又“李白诗文中屡称‘十五观奇书’、‘十五学神仙’、‘十五学剑术’,因此,十五岁应该是李白大量学习诗歌写作的重要年龄,他在其他诗文中多次提到,再加上这些记载来自可信之书,故将这几首诗作系于李白十五岁之时,即开元三年[2](p5)是站得住脚的。
又如,安本将《庐山东林寺夜怀》系于天宝九载之原因是李白天宝九载《留别金陵诸公》诗中有云:“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寻庐峰顶,先绕汉水行。”说明李白是年五月游庐山。[2](p923)便将此次庐山之行与初出蜀时第一次登庐山区别开来。
对于此前诸家将《宿巫山下》系于乾元二年的说法,安本根据李诗中“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句判断,李白当日系自奉节登舟启程,必无夜宿巫山一事。故而认定此诗当为初出夔门之作。[2](p31)
对于《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的系年问题,安本引用了储光羲诗中涉及信安王北征一事的诗句。储光羲《贻鼓吹李丞时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者也》一诗有句云:“出车发西洛,营军临北平。”可知信安王北征系从洛阳出发,则此诗当系本年正月作于洛阳。[2](p236)
再如,关于李白是否曾经三入长安,一直是李白研究者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三入长安之说支持者甚少,但是,安旗先生是三入长安的坚定支持者,那么,李白天宝十二载是否有长安之行,安本除已在《经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抒怀赠韦太守良宰》、《述德兼陈情上哥叔大夫》等诗中一再陈述三入长安之事,还在《下途归石门旧居》诗后加按语补正了李白当年确有长安之行。那何以诗中无一字提及安史之乱?安本先质疑本诗情绪感伤,所别何人?然后指出已有研究否定荐白入朝为吴筠,然后引任华《杂言寄李白》诗句“中间闻道在长安,及余戾止,君已江东访元丹”说明李白曾经于某次离京之后赴江东寻访元丹丘,但是考察已经确知的李白两出长安之路线,发现这两次出京均未至江东,于是判断任华所言“中间闻道在长安”,当指天宝十二载李白入京一事。[2](p1127)此诗所别者正是元丹丘,因元曾荐白入朝,如今又失败出京,故此别格外感伤。
2.从诗歌情绪出发结合李白经历,作出编年判断。
言为心声,诗作必然带有诗人写作时的情绪与境况,何况李白这样的主观性诗人。安本非常重视李白诗作的这种特点,利用诗文中的情绪色彩结合李白当时经历,为一些诗作的系年找到了编年依据。比如,对于李白一生三赴金陵的系年问题,安本的编年根据主要是从这些与金陵有关的诗歌写作内容和情绪来判断的。李白初次入金陵,是辞家出蜀之后的游历地之一,此次来金陵并无亲密朋友,途中结识的也只是一些年轻人,再者也未经过仕途失败的打击,故心情较轻松。因此将《金陵望汉江》、《金陵酒肆留别》等情绪昂扬的诗歌系年于开元十三年第一次入金陵。对于系年有争议的《金陵酒肆留别》一诗,安本又从本诗表达主旨及情绪出发对本诗的系年作出了解释。安本指出本诗主旨仍为“颂扬开元之治,唯末二句微露惆怅之情,盖有憾于当此治世而无所作为。”[2](p72)认为李白当时似在江东干谒无成,方有此感慨。驳斥了瞿朱本将其定于安史之乱之后的说法。
于是,安本将《金陵三首》、《登金陵冶城西北
谢安墩》、《金陵白杨十字巷》等诗作系于第二次入金陵。并在《金陵三首》题解处表达了对系于天宝六载的原因:“此及以下金陵诗七题,与早期金陵诗作相较,写景咏物,俱着苍凉之色;抒怀寄慨,亦多深悲之情。因俱系于本年春游金陵时。”[2](p792)
又如,安本不同意王本将《玉壶吟》系于去朝以后,而是将此诗系于天宝二年,其理由有三:一者,诗中有“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之句,应是以东方朔之隐于朝廷类比自己在朝行为;二者,诗中又有“凤凰初下紫泥诏”之句,可见是言供奉翰林情景,不乏自矜之感;三者,“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可知谗谤虽已盛,而君恩未衰。如在去朝之后,则李白对君王亦多怨词矣。[2](p559)
再如,詹锳将《江上吟》一诗系年于开元二十二年,并认为是李白出蜀之后的作品。安本却将此诗系于上元元年,其主要原因是安本认为李白早年不应有如此强烈蔑视求仙隐逸及功名富贵之情绪,而志在删述、希图以诗文传之不朽之思想,亦应在晚年方有。同时征引李白本年流连江夏时所作诗歌,发现其遣词用语多有与此诗相同者,如《江夏赠韦南陵冰》也表达了此种意在归隐的想法。
3.结合诗歌内容和所涉史实,辅助编年。
诗歌文本有所谓叙事性文本与象喻性文本,叙事性文本多写实,记录生活本身,故诗中记录多有与史实相合处。安本有效利用了李白诗歌中叙事性的文本,将诗歌内容与史实结合起来,找到了编年的线索。
比如,安旗反对王琦、郭沫若、詹锳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一诗系于上元二年。就是结合诗中所涉及到的历史事实来辅助编年。安本首先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及有关史籍,发现上元二年并无李光弼乃至唐官军出征东南、或在东南某地与安史叛军作战之记录;然后反驳王琦有关东南的理由。王琦认为李光弼此时坐镇临淮,地在长安东南。安本反驳云:临淮唐时属河南道,在中原,仍不得言“东南征”;其次,从诗歌内容“太尉杖旄钺,云旗绕彭城”出发,考证李光弼移军徐州在宝应年间,又引诗中“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为李白与金陵群官告别西行,往依当涂宰李阳冰之事。同时又比较此诗与《献从叔当涂宰李阳冰》诗中时令、地望、情绪接近。[2](p1643)故将此诗系于宝应元年,可以说是以史证诗的典范。
又如,安本将《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系于天宝九载,原因是《旧唐书》记载过天宝六载和天宝九载两次京师之旱。又此诗中有“炎赫五月中”,知天宝九载的干旱始于三月,而天宝六载的干旱始于五月,因此,溧阳尉李济充任泛舟之役当在天宝九载这次。[2](p916)故将此诗系于天宝九载。
再如,《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一诗的系年问题,安本先引诗句:“自吴瞻秦,日见喜气。上当攫玉弩,摧狼狐,洗清天地,雷雨必作。”(诗歌大意是:从此地望向长安,每天皆可见喜悦之气,上皇即将御驾亲征、剿灭叛军、恢复大唐江山,到时必然大赦天下,你也将会盼来好消息。)安本加按语曰:上年(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玄宗有亲征之制,《序》文当谓此,作时应在本年。[2](p1995)查《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7](p6940)安本正是根据史书记载,结合诗歌内容将此诗系年于至德元年春所作。
通过以上具体编年方法,安本将李白诗文的85%进行了编年,循着这些编年后的诗歌,可以看到:安旗先生将自己对李白一生追求用世,矢志报国,鞠躬尽瘁的看法表达了出来。如安本将《别匡山》系于李白出蜀之前,从本篇揭示出少年李白即胸怀成就一番政治事业的雄心壮志;将《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系于开元二十七年秋,李白一入长安失败后,虽受打击,然不能时刻忘却建功立业;将《赠何七判官昌浩》系于天宝十载,此期李白正与元丹丘棲于叶县石门山,地近沮溺隐居之所,故反用长沮、桀溺其事以明志,何判官时在幽州军中,白欲往幽州一探究竟。将《公无渡河》与幽州之行联系而观,认为本篇为本年冬在幽州目睹安禄山反迹后作,是自喻其幽州之行之作;将《远别离》系于天宝十二载,指出其表达了李白三入长安进谏失败后内心的苦闷和失望之情;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
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系于宝应元年,李白以衰病之身尚欲报效祖国的一片忠心;将《临路歌》系于广德元年,表达李白于垂死之际,对自己才未尽用、中天摧折的叹息。
对李白诗歌艺术特色及风格形成过程的评论,安本经常通过按语方式表达的。如在《望鹦鹉洲怀祢衡》诗后按语中指出:“严、沈二说大误,高说近之,然亦有未妥处。首二句,非言正平轻魏武,乃言魏武轻正平,然意在讥魏武之不能容物。才高、寡识云云,亦是此意,皆反话正说,借古讽今。”[2](p1441)在《巴女词》诗后加按语指出:巴地民歌,源远流长,……白在巴渝一带盘桓数月,想亦常闻之矣,故有此作。其后行至荆州则有《荆州歌》、行至越中则有《越女词》,行至襄中则有《襄阳曲》。同时拟古乐府之作,如《白纻辞》、《杨叛儿》等,亦日益增多。[2](p29)
《李白诗歌编年注释》一书正是通过编年方式,辅之以对李白诗歌诗意的注释与阐发,考证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与李白个人际遇、情感变化之关系,将注者对形成李白全面立体看法的观念贯通至全书的角角落落,最终帮助读者了解了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光芒,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爱国诗人、政治诗人李白。我们不妨借用安旗先生本人的原话来表达我们的看法:通过研读这部著作,“李白其人及其诗,在很大程度上,以我们前所末窥的新面目呈现出来。这位与世纪同龄、与盛唐同步的诗人,他的凌云壮志,豪情逸兴;他的坎坷道路,血泪人生,不能不使我们感慨唏嘘:原来他是这样的人!”[6](前言)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1990.
[3]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段玉裁.经韵楼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姚鼎.赠钱献之序[A].惜抱轩文集[M].四部丛刊本.
[6]安旗.李白诗秘要[M].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1.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责任编辑 邓年
I206.2
A
1003-8477(2015)11-0136-06
张淑华(1972—),女,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
陕西省社科基金“当代三家李白全集校注本比较研究”(12J181),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项目(3102014RW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