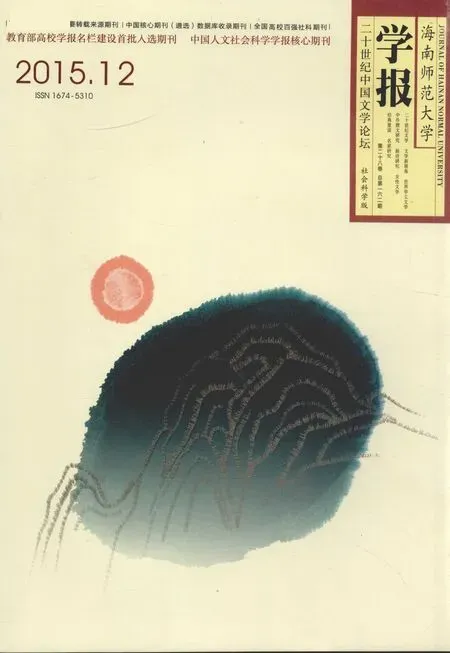譬喻论诗——论叶燮《原诗》的说诗方式
邹 欣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原诗》是叶燮诗学批评的重要论著,其说理之系统严密,论证之方式多端,使其不惟在清代诗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论者将其看作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另一部体大思精的说诗论著。其论诗持通变的观点,对明代复古派论诗独尊盛唐的观点予以驳击。他提出“理”、“事”、“情”,“才”、“学”、“识”、“力”等观点,为后世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此外,《原诗》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其批评方法亦有着相当的关系。《四库提要》评价《原诗》:“其大旨在排斥有明七子之摹拟,及纠弹近人之剽窃。其言皆深中症结,而词胜于意,虽极纵横博辨之致,是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也。”[1]四库馆臣所拈出的“纵横博辨”“词胜于意”,所表征的正是《原诗》论诗的思维路径和话语风格。“作论之体”反映出建立在对话体基础上的申说极具论辩色彩。以上馆臣的评价都是就《原诗》的批评方式和特点而谈,案之于《原诗》,《提要》的评价颇能切中窾要。而这种批评特色之形成,与叶燮多方取譬以论诗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对叶燮《原诗》的研究中似未受到足够的重视①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要的批评方法,今人对此有深入研究。钱钟书、张伯伟、吴承学、周裕锴等人都有相关的论述。近来,古风以及闫月珍等也对这一问题有深入讨论。但是,具体到对《原诗》譬喻说诗的研究,尚较少论及。,本文将对此作出阐发。
一
以取譬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悠久传统。大量的文学批评著作通过譬喻论说诗文。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2]513,“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2]650,以人之骨气,神明、肌肤比喻诗文文辞,情志。《文赋》:“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二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难众辞之有余,必待兹而效绩”[3],用以策击马来比喻片言佳句在文章中的警动作用。颜之推《颜氏家书》:“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4]249,“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4]250。杜牧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5],以主、辅、兵卫喻文章之意、气与辞章三者之间的关系。严羽《沧浪诗话》:“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6],通过兵法来喻诗法,说明李杜诗之不同,杜甫诗可学而李白诗难学。由以上简要的梳理,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采取象喻说诗论文,为历代的评论家普遍所采用,形成了文学批评的传统。从这一层面而言,《原诗》在采取比喻论诗,当然是对批评传统的承继。这一点甚为显明,无需赘述。但是更重要的,《原诗》对传统的承继基础上,更有新创。很少有一部批评著作像叶燮《原诗》这样,大量采取比喻的批评方式,并且,叶燮的取譬范围之广,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关系之微妙,似都较前代的批评著作更胜一筹。
《原诗》多方取譬的批评语言和言说方式,在当时就已经被注意到。沈珩为《原诗》作序曰:“非以诗言诗也”,“凡天地间日月云物山川类族之所以动荡,虬龙杳幻,鼯鼪悲啸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圣贤节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爱恶好毁之所以彰其机,莫不条引夫端倪,摹画夫毫芒,而以之权衡乎诗之正变与诸家持论之得失,语语如震霆之破睡,可谓精矣神矣。”①以下凡引《原诗》内容,皆出自《原诗》,(清)叶燮著,蒋寅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这里就指出叶燮论诗,善于多方取譬,举凡天地间的山川动植,皇帝圣贤,都被叶燮用来作为说诗的材料,其论诗能够“语语如震霆之破睡,可谓精矣神矣”,这种言说效果的取得,一方面自然与其所持之重变等诗学观所带来的诗学思想上的冲击力密不可分,另外,与其所采取譬喻论诗这种言说方式亦有关联。
二
正如沈珩在为《原诗》作序时所说,叶燮论诗文取譬多端。不论是山川草木等自然物象,还是建筑、饮食等人事现象,叶燮都将其纳入到批评话语之中,一方面造就了其诗文批评明晓易懂,同时,其批评本身也具有着诗意言说的意味。下面按照象喻类别对《原诗》中涉及的比喻进行辨析。
(一)草木之喻
有人从“温柔敦厚”的诗教的角度,认为汉魏诗歌去古未远,古意犹存,是诗歌之典范,后世之诗因此不足观。对于此种持复古主张的诗学观,叶燮通过“草木之喻”予以辩驳。
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尝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曰:若者得天地
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者哉!
作者首先从体用的角度,认为“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汉魏之诗,唐宋之诗,皆是用。这正如阳光照耀万物一样。万物生长,虽各具形态,但无不是得天地阳春以发生。那么,同理,怎么能说汉魏以后的诗就没有“温柔敦厚”的诗教呢?这个比喻的巧妙之处在于汉魏唐宋诗歌分属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历时性的存在。由于年代的跨度,人们不易体认到不同时期诗歌皆受到“温柔敦厚”诗教之浸润。而阳光普照万物是共时性的现象,叶燮将较难把握的历时性的诗教传统,转变为共时性的万物接受阳光普照这种自然现象来认识,更为清晰地揭发出汉魏唐宋各代诗歌,应该都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观点,从而有力地反驳了厚古薄今的复古论调。
叶燮认为诗文所表现的对象无外乎“理”、“事”、“情”。而“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则是“气”。在论述气与“理”、“事”、“情”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叶燮再次运用了草木的比喻。
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苟无气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纤叶微柯以万计,同时而发,无有丝毫异同,是气之为也。苟断其根,则气尽而立萎。此时理、事、情俱无从施矣。
草木可以生长出来,这是“理”。生长出来了,就是“事”。长成之后,情状万千,这是“情”。叶燮首先是将“理”、“事”、“情”比作草木生长的各个阶段。然后又说合抱之木,枝叶繁茂,但是如果斩断其根,则树木立萎。原因在于树木之气已竭。因此,没有“气”,则“理”、“事”、“情”俱无所依托,“气”统摄了“理”、“事”、“情”。“气”、“理”、“情”是具有浓厚形而上意味的哲学话语,其间的关系更是不易把握。而根断则树木立萎则是人们熟知的常识,通过这个比喻,“气”与“理”、“事”、“情”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清晰地呈现出来。
叶燮论诗,持“盛衰”、“正变”的观点。在他看来,一部诗史就是盛极必至于衰,又自衰而复盛的循环过程。因之,权衡诗歌高下,就必须破除“在前者必居于盛,后者必居于衰”的陋识。叶燮此种诗学观念无疑是否定了明代格调派学汉魏盛唐的诗学观。但是,具有强烈针对性的驳论自然有其适用的限度。当此种论点遭遇学诗“置汉魏盛唐诗勿即寓目”“于唐以后之诗而从事焉,可否”这样顺其自然推导出的诘问时,便陷入了困境。叶燮当然不是主张应学唐以后之诗,甚至他根本上就是抛开师法对象如何选择的问题,取法于唐还是取法于宋,并非最紧要的问题。“相似而伪,无宁相异而真”,叶燮认为何必纠缠于宗唐还是宗宋,如果作诗者能自出手眼,自然就可以写出好诗来。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汉魏之诗还是唐宋之诗都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环节,历代诗歌的发展是相承相继的,这就在诗史的层面上消解了师法对象选择的诘问。他用树木生长来比喻历代诗歌之间的关系:
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其节次虽层层积累,变换而出;而必不能不从根柢而生者也。故无根,则蘖何由生?无由蘖,则拱把何由长?不由拱把,则何自而有枝叶垂荫、而花开花谢乎?若曰:审如是,则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发,不必问也。又有由蘖及拱把,成其为本,斯足矣;其枝叶与花,不必问也。则根特蟠于地而具其体耳,由蘖萌芽仅见其形质耳,拱把仅生长而上达耳;而枝叶垂荫,花开花谢,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叶与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由是言之:诗自三百篇以至于今,此中终始相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岂可以臆划而妄断者哉!
树木生长是一个生命过程,生根至萌芽,进而生枝长叶开花,相续相生。诗歌的发展亦是如此。采用这个比喻,一方面阐明了诗歌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踵事增华的过程,同时又将历代诗歌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出来。另外,有论者指出,叶燮的这个比喻还为后来诗论家所采用①参见詹福瑞《王尧衢〈古唐诗合解〉的宗唐倾向及其选诗标准》,《文学遗产》2001 年第1 期。,王尧衢在《古唐诗合解》的凡例中云:“譬之于木,《三百篇》根也,苏、李发萌芽,建安成拱把,六朝生枝叶,至唐而枝叶垂阴,始花始实也。”[7]可以看出完全是袭用叶燮以树比诗的论诗手法。有趣的是,叶燮认为“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而王尧衢则认为“至唐而枝叶垂阴,始花始实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透露出了两人论诗的歧异,不同于叶燮的不废宋诗,王尧衢论诗还是以唐诗为旨归的。
(二)筑屋之喻
诗是可学还是不可学?通过对前代之诗的学习,是否自己就能写出流传后世的诗篇?对此叶燮一方面认为,诗歌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写出工而可传之诗,则并非通过多读古人之诗便可达到。在叶燮看来,好诗之诞生关乎诗人的胸襟,对诗歌材料的择取,结构上的经营安排,乃至文辞的修饰整饬等诸多方面。他通过筑屋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
今有人焉,拥数万金而谋起一大宅,门堂楼庑,将无一不极轮奂之美。是宅也,必非凭空结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云气。以为楼台,将必有所托基焉……乃作室者,既有其基矣,必将取材。而材非培塿之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阛阓村市之间而能胜也。当不惮远且劳,求荆湘之楩楠,江汉之豫章……既有材矣,将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后可。得工师大匠指挥之,材乃不枉……宅成,不可无丹雘赭垩之功;一经俗工绚染,徒为有识所嗤……其道在于善变化。变化岂易语哉!终不可易曲房于堂之前,易中堂于楼之后,入门即见厨,而联宾坐于闺闼也。惟数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于天然位置,终无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谓变化。
作诗好比筑屋,房屋须建在稳定可靠的地基之上,这样才能有所依托。诗人之胸襟就是诗歌之地基,有胸襟,诗人才能于其上发挥性情智慧。房屋地基已牢,就要考虑取材,取材须择良木。写诗也要对诗骚以至唐宋诸大家诗歌之神理指归,默会于心。既有良木,还需善用。写诗亦然,先要痛除自己本来面目,以古人之学识神理充之,然后再去除古人面目,自己之匠心乃能发扬。宅成,不可无丹雘赭垩之功,诗歌之语词也需藻饰。叶燮通过筑屋复杂的过程来比喻诗歌写作需要的各种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叶燮所指出的奠基、取材、粉染等过程都是筑屋过程中至为关键的环节。那么,以之比诗,人们自然会认识到胸襟等也是作诗至为关键的要素。同样采取筑屋之喻,在《原诗》中还有另外一处:
又汉魏诗,如初架屋,栋梁柱础,门户已具;而窗棂楹槛等项,犹未能一一全备,但树栋宇之形制而已。六朝诗始有牕楹槛、屏蔽开阖。唐诗则于屋中设帐帏床榻器用诸物,而加丹垩雕刻之工。宋诗则制度益精,室中陈设,种种玩好,无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虽未备物,而规模弘敞,大则宫殿,小亦厅堂也。递次而降,虽无制不全,无物不具,然规模或如曲房奥室,极足赏心;而冠冕阔大,逊于广厦矣。夫岂前后人之必相远哉!运会世变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也。
叶燮将汉魏以至唐宋各代之诗比作筑屋不同阶段所具有的形态。叶燮此喻一方面表明,诗歌的发展是踵事增华的过程,唐宋诗较之汉魏诗更为精巧。另一方面,叶燮此喻更强调的是后代之诗虽能极足赏心,但是论到冠冕阔大,则就逊于汉魏之诗了。因之,对诗歌的理解,诗歌技巧之高下与诗歌艺术水平之高下并不能等量齐观。
(三)探宝之喻与射箭之喻
前已论及,叶燮论诗持“源流正变”的观点,他认为“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因此,他是肯定变的,认为苏轼之诗就是“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他将宋人对诗艺之探求比作石中寻宝:
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余蕴,非故好为穿凿也;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且未穿未凿以前,人人皆作模棱皮相之语,何如穿之凿之之实有得也。
石中寻宝这一比喻甚为巧妙,从凿石的动机而言,显然是为了获得宝贝,而不是无谓的穿凿。显然这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或者说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叶燮以此喻诗,这里面实际暗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即他认为宋人作诗求变,乃是出于对完美诗艺之追求,较之抱守成规,只能做模棱皮相之语之人,“实有得也”。
叶燮认为诗歌写作,主要是表现客观世界中的“理”、“事”、“情”,而要表现“理”、“事”、“情”,作诗者应具有“才”、“胆”、“识”、“力”。其中,叶燮尤为强调“识”的重要。“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不随古人脚跟。”他以射箭为喻:
譬之学射者,尽其目力臂力,审而后发;苟能百发百中,即不必学古人,而古有后羿、养由基其人者,自然来合我矣。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欤?古人合我欤?
射箭的好坏,以射中与否为标准,而诗歌之好坏,并没有一定之标准。叶燮用射箭喻诗,实际上就消解了诗歌好坏标准的不确定性。换言之,诗之好坏的标准也是唯一的,在叶燮看来这个标准就是作诗者需要有“识”。有“识”,则所作之诗能自出手眼,脱尽粘滞,进而就可超越“学谁”、“合谁”这种评判体系。
(四)云之喻与花之喻
诗文写作有法无法问题,历来为诗论家所关注。叶燮论诗亦谈及此一问题。他说:“法者,虚名也,非所论于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论于无也。”又说:“法有死法,有活法。”活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在他看来好的诗歌应该是顺其自然,并没有一定之法。他用泰山之云来说明这一抽象的问题:
天地之大文,风云雨雷是也。风云雨雷变化不测,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即至文也。试以一端论:泰山之云,起于肤寸,不崇朝而徧天下。吾尝居泰山之下者半载,熟悉云之情状:或起于肤寸,弥沦六合;或诸峰竞出,升顶即灭,或连阴数月;或食时即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鹏翼;或乱如散鬊;或块然垂天,后无继者;或连绵纤微,相续不绝;又忽而黑云兴,土人以法占之,曰:“将雨”,竟不雨;又晴云出,法占者曰:“将晴”,乃竟雨。云之态以万计,无一同也。以至云之色相,云之性情,无一同也。云或有时归,或有时竟一去不归;或有时全归,或有时半归:无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若以法绳天地之文,则泰山将出云也,必先聚云族而谋之曰:吾将出云而为天地之文矣。先之以某云,继之以某云,以某云为起,以某云为伏;以某云为照应、为波澜,以某云为逆入,以某云为空翻,以某云为开,以某云为阖,以某云为掉尾。如是以出之,如是以归之,一一使无爽,而天地之文成焉。无乃天地之劳于有泰山,泰山且劳于有是云,而出云且无日矣!
之所以用泰山之云来比喻诗文,叶燮找出了它们之间的共通点。风雨雷电是天地大文,诗文属于人文,两者都是属于文的层面。这无疑是受到《文心雕龙·原道》的影响。在叶燮看来,变幻莫测的泰山之云乃是至文,也就说是文的最高境界。泰山之云是无思维的自然物象,其表现形态,诸如聚散起伏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诗文写作则是人的智慧心思的思维成果,类比泰山之云,则其最高境界也应是自然而然之随在自得。此喻同时又是一个寓言,“则泰山将出云也,必先聚云族而谋之曰”一段,皆为人人共知的荒谬之辞,那么,以法来论诗文其实和它一样的道理,由这个比喻,叶燮不仅可以表明好文应该是随有所得的,同时也提示了以法来论诗文之不可取。
明人论诗多尊盛唐,晚唐诗歌不受他们的重视。叶燮论诗则不废晚唐,认为晚唐诗歌与盛唐诗歌各为一时之秀,虽两者存有风格上之差异,但并不能简单地以优劣论之。他以春气、秋气、春花、秋花来说明盛唐诗与晚唐诗之关系:
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飒。气之候不同,非气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秋气也,衰飒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萄,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夫一字之褒贬以定其评,固当详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辞加人,又从而为之贬乎!则执盛与晚之见者,即其论以剖明之,当亦无烦辞说之纷纷也已。
叶燮用春、秋来喻盛、晚唐诗,表明盛、晚唐诗在诗歌史的层面,是相赓续的过程。四季之发生,是天地运行之自然结果。春日万物滋生,秋天百草枯零,我们并不能因此来判定春优秋劣。春花如桃李牡丹,具秾华妍艳之姿,秋花如芙蓉丛菊,亦有幽艳晚香之韵,都能极一时之隽。因此,并不能以生长时节之不同,作为品评花之美丑的标准。叶燮以花喻诗歌本身,而以春、秋喻盛、晚唐,就将诗歌与时代剥离开来,表明其论诗着眼于诗歌艺术本身,而不是局限于时代。
此外,《原诗》中还有很多比喻,诸如请客之喻、行路之喻等等,都能将诗学理论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分析。
三
《原诗》多方取譬的论诗方式,并非是凭空而出的。一方面它受到古代传统诗文评批评的浸染,是其影响下的产物,因之,《原诗》以喻论诗有其理论和材料资源。另外,《原诗》采用对话体的阐述方式,使得比喻的运用更为有效地表达其诗学理论主张。
第一,古代传统诗文评对《原诗》的影响。由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以喻论诗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叶燮身处其中,自然不能不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进行文学批评时采取取譬的这种方式,这可以说是批评方法上的影响。另一层面,叶燮说诗所采用的喻体,均非独造,这些喻体在前此的文学批评中并不鲜见,这一影响可以说是取象系统层面的。如以筑室之喻进行批评,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何谓附会?……若筑室之需基构,裁衣之需缉缝也。”[2]650王骥德《曲律·章法》:“作曲,由造宫室者然。工室之作室也,必先定归式,自前门而厅、而堂、而楼,或三进、或五进、或七进,又自两厢而及轩寮,以至廪、庾、疱、湢、藩、垣、苑、榭之类,前后、左右、高低、远近,尺寸无不了然胸中,而后可施斤斫。”[8]如石中探宝之喻,黄宗羲《论文管见》:“昌黎‘陈言之务去’。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犹如玉在璞中,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认璞为玉也。”[9]这些比喻,在前代批评论著中皆有运用。
第二,《原诗》的诗话性质决定了其用譬喻说诗的可能性。《原诗》作为叶燮诗歌理论系统表达的著作,并且其写作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即反驳明代的复古主张诗学观,因此他采取问答的方式,来展开其论述。关于这种对话是真实的存在,还是叶燮所采取的论述策略,并不能给予明确的认定。但是,这种对话体的论述,正如蒋寅先生所说:“它明显的优势在于可以自如的引出各种议题,特别是集中探讨诗学的基本观念,基本概念,诗歌史原理的基础问题”[10]13。同时还可以“通过设问和论辩揭示问题的实质,也有效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见解”[10]13。正是因为有对话者的存在,所以,叶燮在论诗时,必然要考虑到听者的接受。而取譬的方式,正可以将抽象不易解的诗学问题形象化。所谓“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11],“穷理析义,须资象喻”[12]。在《原诗》中,叶燮明确地解释了其采用取譬论诗的原因也正是因此,“我今与子以诗言诗,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晓然矣”。当然,上面的分析主要基于《原诗》的对话体论述方式,实际上,即使没有采用此种明显的对话体论述方式,从诗话的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而言,诗话的这种隐性的对话也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一部诗学论著,叶燮在写作时也必然会考虑到它的传播接受情况,会考虑到它的可能性的阅读对象,因此,易接受性仍然是叶燮需要考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采用取譬的方式也是可以得到有效解释的。
[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806.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45.
[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唐)杜牧.答庄充书[M]∥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4.
[6](宋)严羽.沧浪诗话[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56.
[7](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M].单小青,詹福瑞,笺注.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1.
[8](明)王骥德.曲律[M].陈多,等,注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22-123.
[9](清)黄宗羲.论文管见[M]∥王运熙,顾易生,主编.清代文论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96-97.
[10](清)叶燮.原诗[M].蒋寅,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清)沈德潜.说诗晬语[M].王宏林,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5.
[12]钱钟书.周礼正义·乾[M]∥管锥编(一):上.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