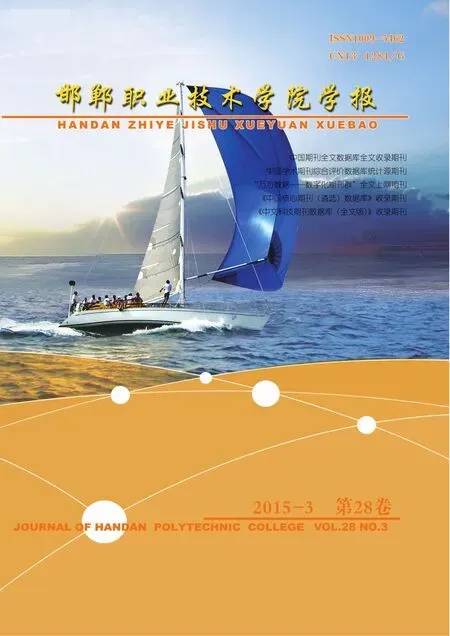从《列子》与《列子注》的不同看魏晋玄学的发展
闫现霞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列子》是道教经典,又被称为《冲虚真经》,相传为战国列御寇所著,历来以其“贵虚”的思想、精彩的寓言故事和简练的叙事风格而备受推崇,有着重要的文学与思想价值。《汉书·艺文志》曾记录《列子》共有八篇,已亡佚。今存《列子》一书据学者考证为魏晋时玄学家伪作,东晋张湛收集整理,编为八篇,并为之作注。
作为《列子》的注解,张湛的《列子注》与《列子》在思想上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本文主要通过比较《列子》与《列子注》的不同,来突出张湛的思想,并进一步探寻魏晋玄学的嬗递轨迹。
张湛在其《列子序》中这样概括《列子》一书:“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1]279但是果真如序言所说,张湛的《列子注》是为了阐明《列子》的要旨吗?事实上,仔细比较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列子注》是东晋儒道交融、玄佛互释这一时代特征在张湛思想上的折射,是张湛个人哲学理念的表现。《列子注》与《列子》不仅在字词句理解上有许多矛盾之处,在思想理论方面也有明显的不同。
一、修正原书内容
对于《列子》原书的遣词、用字、事迹如有所怀疑,张湛则一一挑出,进行校正,本文仅举几例试以说明。
(一)校订错字
《天瑞篇》:“道终乎本无始,进乎本无久。”
张湛注:“久”当为“有”。[1]19
《天瑞篇》:“终进乎?不知也。”
张湛注:“进”当为“尽”。此书“尽”字例多作“进”也。[1]18
《黄帝篇》:“黄帝乃喟然讃曰”
张湛注:“讃”当作“叹”。[1]40
这些字多为同音假借,或后人传抄文本时出现的讹误,张湛一一列出,再用同音之字进行校正。
(二)质诸原文
《杨朱篇》:“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
张湛注:庄子云杨子居,子居或杨朱之字,又不与老子同时。此皆寓言也。[1]80
《杨朱篇》:“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
张湛注:此传云子产诛邓析,左传云驷歂杀邓析二用其竹刑,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也。[1]202
这是故事中人事不符的现象,张湛对其人或其事产生怀疑,并根据史传资料对不合史实的地方进行更正和标注。
(三)引用文献
《天瑞篇》:“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张湛注:老子有此一章。[1]4-5
《天瑞篇》:“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张湛注:此一章全是周易乾凿度也。[1]8
《黄帝篇》:“今东方介氏之国,其国人数数解六畜之语者,盖偏知之所得。”
张湛注:春秋左氏传曰:介庐闻牛鸣,曰,是生四子,尽为牺矣。[1]85
《天瑞篇》:“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张湛注:庄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自生耳。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自化耳。[1]4
张湛在解注《列子》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借鉴前人的著述成果,引用了大量的典籍资料和他注。据学者严灵峰的考据,《列子注》引用的古籍多达25 种[2],为《列子》篇章内容作了充分的印证和补充。最值得一提的是,张湛保留了郭象、向秀《庄子注》中的部分内容,在向注佚失的今天,为我们研究郭象和向秀《庄子注》的区别与联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四)不闻存疑
《仲尼篇》:“孤犊未尝有母,非孤犊也。”
张湛注:此语近于鄙,不可解。[1]142
《天瑞篇》:“黄帝书曰:谷神不死”
张湛注:古有此书,今已不存。[1]4
对于自己不认得的字,不理解的词,张湛自称“不知”、“不祥”、“不可解”;对于没有听过的书篇或人物,张湛则坦言未闻。
从张湛对《列子》做出的种种修正和补充,我们可以看出张湛作注时的态度之谨慎。张湛在注解《列子》文本,理顺《列子》思想的同时,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理论。
二、思想异同之处
张湛既是为《列子》作注,那么注文与《列子》应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但是经过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注文中所传达的思想与《列子》原文的思想有很多存在出入甚至相抵牾的地方。
(一)关于“创生本原”的分歧
《天瑞篇》:“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张湛注:皆自尔耳,岂有尸而为之者哉?若有心于生化形色,则岂能官天地而府万物,瞻群生而不遗乎?[1]2-5
《天瑞篇》集中体现了《列子》的宇宙生成论。《天瑞篇》开篇便以生物者化物作为言论的中心,把“不生不化”作为“有生有化’的本体,而这个本体却是“自生自化”的,同时可以产生“有生有化”的万物,即生化万物的主体是自生的,可以相互转化并化尽无穷,不存在一个更高的本原来生成“生生者”“化化者”。对这一段话,张湛的注解却具有了两层意思。一方面,他认为万物自生,并不存在一个更高的本原,另一方面又认为作为万物主宰的“至虚”是无心于生化形色的,否则就不能官天地俯万物,成为万物的本原了,前后的矛盾很明显,这是因为在《列子》原书中,本原是自生的,一切具体事物都由本原生化而来,但在张湛看来,具体事物是“忽尔而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即是自生自足的,这和《列子》原书具有明显的出入。
所处时代的不同造成了《列子》和张湛对“自生”概念的认识不一。《列子》是魏晋人的伪作已被学界基本认定,其成书大致在西晋玄学的过渡阶段,《列子》的创生理论并没有采用道家“道”的概念,而是提出了一个“不生不化”的虚无作为万物的本原,其自生独化理论尚未成为体系。而张湛生活于距离《列子》成书大抵百年后的东晋,当时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贵无论和崇有论先后陷入理论泥潭,难以自拔,郭象的万物自生独化论独当一面,张湛不免受其影响,因此《列子注》也烙上了时代的烙印。
(二)关于“有无之辩”的差异
《天瑞篇》:“夫有形者生于无形。”
张湛注:“谓之生者,则不无,无者,则不生。故有无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则有何由而生?忽尔而自生。忽尔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以生,生则本同于无。本同于无,而非无也。”[1]6
有无之辩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历代玄学家在本体论上努力调和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矛盾,为传统名教找寻形而上的依据。《列子》原文明确地指出“有形生于无形”,也就是说“无”与“有”两者是形成与被形成的关系。张湛却认为“无”不能生“有”,“无”可以是生成的原由和凭据,但并不是“有”的直接生成者,“则有何由而生?”“忽尔自生”,这里的“自生”不是自己产生自己,而是非孤立性的事物本身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与其他事物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种彼此间的联系构成了事物生成的因由。显然张湛的理解已不同于《列子》的原意,他在注解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理论见地,用“无形以相形”替换了《列子》“有形生于无形”的命题。
(三)圣贤观上的区别
《仲尼篇》:“孔丘能废心而用形。”
张湛注:此颜回之辞。夫圣人既无所废,亦无所用。废用之称,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万机,对接事务,皆形迹之事耳。冥绝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动矣。”[1]117
《杨朱篇》:“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天下不失,享柞百年。”
张湛注:伪实之迹因事而生,致伪者由尧舜之迹,而圣人无伪也。[1]218
圣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理想人物的描摹。起始于先秦时期的圣人观,具有浓厚的社会政治伦理色彩,道家老子以无为而无不为作为圣人的行为规范,庄子虽然也以无为锻造圣人,但他的圣人是彻底的从无为到无为。到了魏晋时期,圣人观有了更大的发展,王弼主张圣人有情论,郭象则提出了冥内游外的新观点,到了张湛这里,他开始努力弥合儒道两家的圣人观。[3]
通过把注文与《列子》原文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张湛认为《列子》言语多为“诬贤负实之言”。他延用了郭象分“圣人之迹”与“所以圣”的讲法,认为普通人认识的圣人是行迹上的圣,不是“所以圣”。这样,张湛的圣人观既具备了道家圣人关注自身内在锤炼的色彩,又拥有了儒家圣人关切社会政治的色彩,在郭象“冥内游外”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圣外王,冥通内外”的圣人观。在张湛的评价体系里,“圣人”更多情况下成为“至人”。他在《黄帝篇注》中言“至人之心豁然洞虚,应物无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终日不言,而无玄默之称;终日用知,而无役虑之名。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据此,他提出“圣人为伪”的命题,提议要认真辨别“圣”与“圣之迹”,这个思想在《列子》中是没有的。[4]24
(四)对待名教的态度不同
《仲尼篇》:“诗书、礼乐之无救于治乱。”
张湛注:唯弃礼乐之失,不弃礼乐之用,礼乐故不可弃。[1]116
《仲尼篇》:“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矣?”
张湛注:治世之术实须仁义。世既治矣,则所用之术宜废。{1}115
两汉以来的政治统治思想一直以名教为核心,但是在实践中,名教却遭遇了困难。于是,魏晋玄学家发起一场自然与名教之辩。名教是一种维护社会条理秩序的道德标准;自然是统治世界变化的和谐的自然规律。儒家重视纲常秩序之名教,道家则任由个体本性之自然。玄学家们在这场争论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王弼主张对待名教和自然要“崇本以息末”[5],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一说;竹林时期,嵇康阮籍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讲仁义礼制的假名教,并对其进行了猛烈地抨击;郭象则另辟蹊径,提出“名教即自然”[6]的观点。虽然理论不同,但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在对待名教的问题上,张湛与《列子》的态度截然相反。《列子》认为诗书礼乐无以救乱世,从根本上否定儒家礼制存在的必要性。张湛则不同,他反对将名教与自然对立,提出了“任自然而顺名教”的观点。首先张湛肯定了名教治世救弊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伪善名教给社会造成的损害。这一关键在于在讨论名教与自然的问题前,张湛先区别了名教的真与伪。他认为,真正的名教是人们不为名利而行善,而虚假的名教是打着名教的幌子,私底下谋取个人利益。张湛既任情自然又揄扬名教,将自然与名教进行了融合。对比之后,我们发现对待名教,张湛的态度更为理智,他的这种把道、儒融合的观点也就更具有合理性和说服性。
(五)生死观上的差异
《杨朱篇》:“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张湛注:夫不谋于前,不虑其后,无恋当今者,德之至也。[1]221
魏晋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知识分子生死难测、朝不保夕,因此对现实生死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们开始研究宇宙的产生,讨论人类的生死自然,对人生进行深刻的思考。《列子》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生死无常,依据现实,对自然生死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列子》认为人生短暂,必有一死,且终究要转为虚无,“故当生之所乐,厚味、美服、好色、音乐而已耳”[1]216,以此四者来满足人们的欲望,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恋世情怀。关于世人乐生厌死的现状,张湛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以生以劳为行,以死以息为归。他认为生存就像人在旅途,要不断地向前行走;而死亡是家,是归途。真正有德之人是不会留恋人世的,那些留恋人世而惧畏死亡的人实则是迷途的人。张湛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认识到生生之理不在于外在的情欲之事,而是在于内在对人生的思考。因此,他要求人们不要执着于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有所舍弃,从而不为物役,给那些因执着于生死而烦恼的人指明了方向,这与《列子》的观点有些许出入。
(六)对“名”“实”的关注点不同
《杨朱篇》:“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
张湛注:为善不以为名,名自生者,实名也。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伪名也。伪名则得利者也。[1]218
西晋灭亡以后,东晋政权偏安江左,出于辅佐之功,东晋士人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他们身居高位,一方面追求精神上的高雅风流,另一方面又致力于稳定江东政权,有重振朝纲的雄心壮志。[7]立名、立言、立功、立德,进而扬名于后世,成为了当时一个重要的价值标准。针对这种现象,《列子》反其道而行之,充分肯定了现实人生的价值,重视个体的自由与真实,主张抛弃虚名,不要为名所累。例如伯夷、叔齐因为国家灭亡,不肯食嗟来之食而饿死在首阳山,在世人看来他们是为名而死,是忠义之士;在《列子》看来,他们仅仅是“名”的牺牲品。对于名和实,张湛的关注点却不同,他暂且将《列子》的名实之辩放在一边,把焦点放在了“名”上,把“名”划分成为善之“实名”和为利之“伪名”。为善之实名不仅是自生,还可以流芳百世,而为利之伪名则为人不齿。对此我们应严格区分,做到去伪存真。
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列子》与《列子注》在文字理解与思想理念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对待《列子》一书,张湛总体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基本同意《列子》神形兼有的意识观、轻名重实的价值观、人性为本的道德观、齐一生死的生死观以及持后全身的处世观。但是由于所处年代的不同,张湛作注时无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他在《列子》思想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这些见解大量地存在于注文中,因此,区分张湛的注解十分重要,是我们准确剖析张湛思想的先决条件。
三、结语
《列子》一书至今读来仍不失其理论意义和文学价值,堪称文学殿堂的瑰宝,它的人生哲学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东晋玄学家张湛的《列子注》,不仅重现了《列子》文本,同时阐述了张湛自己的理论思想,展现了东晋时期儒、道、佛相互融合的情况,为我们研究魏晋时代的思想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材料。通过对《列子》与《列子注》作比较,我们发现张湛的《列子注》吸收了前期玄学家的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外来佛教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至虚”本体论、二元的宇宙观、“顺应天理”的人生观和“道儒互补”的政治观。《列子注》是玄学与佛学碰撞的花火,是异域文明相结合的典范。
[1]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3
[3]许抗生.魏晋玄学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邹金霞.东晋张湛之思想探微[D].山东大学,2006
[5]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郭象.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王弼名教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