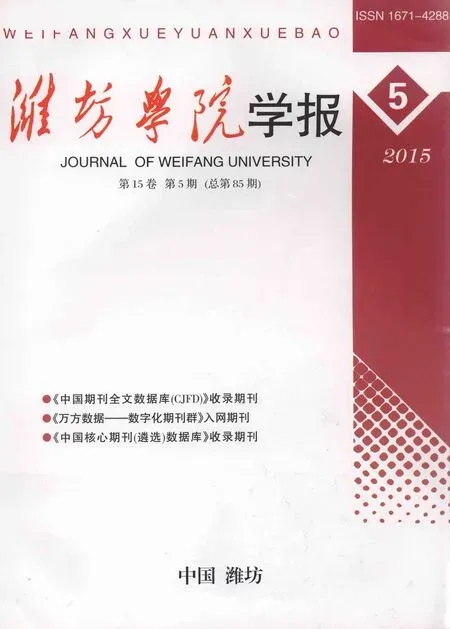为失败者书写历史——司马迁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杨淑明
(中共潍坊市委党校,山东 潍坊 262406)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此话反映出叙述历史、书写历史的一个“话语权”问题:唯有胜利者才有资格评判历史、解说历史、书写历史;而失败者只能被动的接收评判,他被排斥在评说历史这个过程之外——此种现象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在中国封建社会,“胜者为王,败者为囚”,当一场真实的历史大戏谢幕后,胜利者一定是站在审判席上,而失败者则站在被告席上。因此“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的历史,往往是“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然而历史话语权掌控在胜利方的历史能是真正的历史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原因显而易见,这样书写的历史缺少了上演历史大戏的另一方:失败者的参与。因此这样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是不真实的。
众所周知,中国史学一贯标榜“鉴往知来”、“察古知今”,治史旨在“资治”,但面对这样只有胜利者参与、掌控下书写的历史,能否完成上述目的则是大有疑问的。但遗憾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几乎“清一色”的都是“由胜利者为胜利者自己书写的历史”。
尽管如此,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过对历史申说的“不同声音”的,有过“对失败者书写历史”的先例的,这就是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司马迁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奇迹”,当然也是一个“另类”(班固就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他的《史记》不仅写胜利者,亦写失败者,而且是公正地写,实事求是地写,“不虚美、不隐恶”地写。比如《史记》就写了《项羽本纪》,为项羽这个失败的悲剧英雄记录其历史。而且“规格”甚高,享以“纪”的殊荣。不仅为项羽,而且他还为另一个“弱势阶层”出身的失败者陈涉书写历史,且以“世家”载述之,其“规格”也是相当高的。
司马迁“为失败者书写历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的煌煌一章,意义重大。
首先,它使“书写的历史”(纸上的历史)更加全面、客观、生动、具体、鲜活,较好地实现了对真实历史的“复写”和“再现”。众所周知,胜利者之所以成为胜利者,当然自有其某些方面的“过人之处”,然而他们在载述历史时却不免平庸、短见。他们为把自己的胜利说成是“有德之至”、“顺天应人”、“君权神授”的必然结果,往往不惜美化自己,贬抑、丑化、妖魔化对方。这样的史学载述虽则部分的起到了胜利者所希冀的其胜利“合法性”、“必然性”的欺骗作用,但同时对自己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有意拔高自己,使自己向“天意”、“神旨”靠拢,有时反而使自己“人的能力”方面趋于“暗淡”;同时丑化、歪曲、贬抑失败者,也必然弱化自己的胜利得来的艰难与不易。所有这些都是胜利者所始料未及的:他们越想美化自己,却越透出自己的低能。此种现象几乎成为封建社会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带规律性的现象。而《史记》则是一个例外,即以“楚汉相争”这段历史为例,由于司马迁公正、客观地为项羽这个失败者书写了历史,从而把胜利者的刘邦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艰难环境中:他所面对的项羽英勇无敌,攻必取,战必胜,敢打硬仗、恶仗,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项羽光明磊落,不恃权谋,信必守,言必行,称得上是伟丈夫。但他的弱点也是致命的:勇有余而智不足,刚愎自用,性格暴烈,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与建议。刘邦正是在同这样一位与其势均力敌、短长互见的强大对手的斗智斗勇中成为胜利者的。这样的历史载记更能体现出刘邦作为政治家的不凡,而失败者的项羽也不失为一个“失败了的英雄”。我们读《史记》,项羽的“灭秦之功”在史籍中得以凸显,“灭秦”这一“不世之功”不因其为失败者而被淹没、尘封,项羽作为一位悲剧英雄已经矗立在历史人物的长廊中;作为胜利者的刘邦恃智谋,善用人,能变通,不计小节,趋利避害,虽然不乏流氓无赖相,但他的素质具备了在传统政治场中得高分的能力,因之他成了最后的赢家。这样的客观书写使得胜、败双方“各得其所”,各得其“中的之评”,同时“胜利者未必崇高,失败者未必充满瑕疵”的历史复杂性也在《史记》中得以体现。比如我们尽管看到刘邦胜利了,但却不感到他是多么的“崇高”;而项羽虽然失败了,也使读者不感到他是多么的令人不堪。倒是使人对他有一种惋惜的情感在。为何有这种感受?就是因为司马迁对这胜、败二方都是“秉笔直书”、“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刘邦的“得民心”,得力于他的“约法三章”,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的实质在于“钓买民心”,他的内心还是“好财货美女”。但通过这样的叙述竖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权谋”者的刘邦,而不是一个“道德圣贤”的刘邦,而这正是历史的事实。因此司马迁“为失败者书写历史”丰富了历史的真实内容,使历史更加全面、客观、生动、鲜活。试想如果少缺了对项羽、陈涉这些失败者的真实书写,或者像以后史家那样对失败者皆冠以“贼”、“寇”般的妖魔化、扭曲化的书写,那么“楚汉相争”的历史也就不可能那般丰满。这样的书写不仅项羽等失败者的历史作用不能得到公正评判,就是胜利者的刘邦的政治家形象也难以“立”得起来。
其次,司马迁“为失败者书写历史”的另一重大意义就是,他为历史研究所要达到的“鉴古知今”、“察往知来”目的提供了可能。我们知道,少缺了失败者参与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妖魔化、扭曲化了的失败者的历史则是编造了的历史。后人面对这样的不完整的历史与“掺假历史”,那是不可能真正吸取经验,接受教训的。而司马迁的《史记》既写胜利者,也写失败者,还写弱势阶层、日卜星象,各色人等,这样的历史书写体现了历史的“群体性”推动的特点,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之它更全面、更客观。这样的史著当然有可能达到“鉴古知今”、“察往知来”,亦即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史目的。
“为失败者书写历史”溯其渊源则是中国史学“秉笔直书”这一优良传统。在司马迁之前“秉笔直书”这一史学传统即已屡遭困境,但却一直不绝如缕,得以延续。晋之董狐,齐之太史,不畏强权,以生命、人格对这一传统予以捍卫。至司马迁更是不遗余力,并将其发展到敢“为失败者书写历史”的程度。但伴随着西汉中期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秉笔直书”这一传统日益式微,而作为这一传统的极致“为失败者书写历史”更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一代杰出史家的司马迁曾为捍卫这一传统付出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戳害,但它无力回天。自此之后“秉笔直书”愈益艰难,司马迁所首创的“为失败者书写历史”就此绝嗣。与此相映照,歌功颂德,美化、神化胜利者,贬抑、歪曲、妖魔化失败者的“为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史学大兴。一部二十四史,除司马迁的《史记》包含了“为失败者书写历史”(真实地书写,而不是冠以“贼”、“寇”般的污蔑)外,其他史著几乎都是“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研究从来不缺对胜利者的歌功颂德,缺的是对失败者历史的真实书写。而缺失了对失败者真实历史的书写,那么胜利者的历史的真实性也就令人大为怀疑了。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