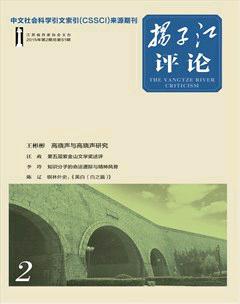在西北边地体验安琪诗歌
金春平+牛学智
集中阅读完安琪近期出版的两部诗集《极地之境:2003——2012,北京。短诗选。》与《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漳州-北京﹒长诗选》后,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也似乎深深地陷入在了诗歌认同的迷惘之中。当然,这个被格外突出出来、甚至于有点硌着我的困惑、迷惘,绝不是安琪这两部诗集的不好,情况正好相反,她如此凶猛的语言修辞,如此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语境转换,如此直击现场并且直接把现场视作诗歌思想生成唯一源头的原创性,着实给我当头一闷棍。要清晰地解释这种冲击,知识接受层面说,或许会牵扯出一大堆关于诗歌评价、诗歌思潮变迁的话题,因为唯有它——诗歌知识规定性、诗歌流派规定性和种种诗歌意识形态规定性等,才有理由强化或者屏蔽个体的诗歌体验方向。然而深一步追究,准确地说,当把安琪的诗歌背景,诸如漳州、北京,还有在路上的所有空间进行连接,最后再回到我所在的西北边地,社会学语境的支持便越来越清晰了。
在漳州,在北京,在别的什么地方,和在西北边地,于是有了某种共识。恰好在这里,安琪诗歌世界里的一些强悍价值信息,才有了必须由理论突出的亮度。而要呈现这种价值亮度,我只能先退回到属于我和我们共同体的现实感知语境上来。
一
沉淀一段时间后反过来再想这个我没弄明白的问题,其实与某种给我诗歌阅读以定势的诗歌世界有关。正好身边有本青海格尔木诗人曹有云的诗集《边缘的 琴:2009-2012诗选》 (作家出版社2013),他的后记说出了我的大多数感受。这感受就是他所谓的“边缘”。一则地理意义上的边缘:“我出生在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四十余栽春秋,已年届不惑,可谓地道的‘青藏高原人了。青藏高原是世界的‘屋脊,也是世界的边缘。青藏高原,距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遥远。”二则文化生态意义上的边缘。“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和东部,西部文化虽然多元繁富,特色鲜明,但就整体而言,其价值观和影响力尚无无力撼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和东部的文化中心地位,在很长时期内将无法改变自己的边缘文化身份,这既是历史,更是现实。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新城格尔木,就更复是边缘之边缘了。”三则文学生态意义上的边缘。“随着市场经济的凶猛发展,文学也在被凶猛地边缘化,而在精神意义上处在文学塔尖之上的诗歌,则比其它任何文体更加迅速更加有力更加彻底地被边缘化了。回顾中国文学史,诗歌一直处在几乎‘霸权地位的中心地带,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中国诗歌史。而世事沧桑,风水流转,如今,诗歌已处在了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尴尬的边缘境地了。勿论其他,仅看各大文学期刊‘施舍给诗歌栏目的页码,你就能心领神会而恍然大悟。”
只要把曹有云的“青藏高原”、“格尔木”换成“西海固”、“石嘴山”或“银川”,就完全是我的。这既是基层西北文学共同体基本的遭遇,同时更是基层西北文学人共有的生存环境。毋庸讳言,在这样一个客观环境之下,我经常被这样一种或几种诗歌所围追、敲打和洗礼,我被它们的世界观彻底建构了。其一,他们或者像曹有云那样,在昌耀的“自传性”(耿占春)西北体认中,顽强地与自然、与风吹来又复弹回去的主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对抗,诗写得凌厉、孤绝和富有西北漠风的肆意、荒凉,然后反过来以后者的坚硬重构思想主体性意识,诗人这个独特的主体性,便成了人们反复加码的诗学审美符号,社会语境于是退居第二位。其二,他们或者像近年来的沈苇那样,为各自所在西北地域风情立传,自洽自在的地方知识合成了另一西部诗歌结构,使你更有理由相信,诗意就在其词语的自明中,仿佛另一路诗人的对抗、批判显得有些幼稚、不知好歹,西北遂成为“文化寻根”者的归宿地,诗人主体性在此悄悄淡出了。其三,他们或者像邱新荣、杨梓那样,以历史资源为源头,或纯粹把西夏、戎狄等曾经被“正史”有意遮掩的经纬,重新纳入诗歌命意,为无意义感可挖掘的当下注入价值活力、在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黄页中找寻原始诗意,经过几度变异的诗人主体性,重新复活。其四,他们或者像高凯、王怀凌那样,为“村落终结”的乡土精神再唱一回挽歌,重新仪式化,重构后现代的“乡愁”,复活的诗人主体性陷入文化现代性诉说的迷茫之地。其五,他们或者像北上广、中东部“80后”那样,用别人玩腻了的口语灌口,试着描摹正如火如荼城镇化、现代化的西北城市生活,结果,借来的衣冠装饰,小市民趣味的身体美学、小中产阶级的心态美学等,不胫而走,于是西北真好像有了自己的城市文化、并且也好像已经到了“反现代性”的时候了,诗歌留下了微妙修辞和精致结构,但诗人主体性的意义大厦似乎坍塌了。
暂不论目前正在运行的西北诗歌的价值意义,仅就它们的词语、结构、象征体系所形成的诗意世界而言,我个人的确长时间沉陷其中,并没有多少清醒的反观意识。生活共同体、地域共同体,乃至方言共同体的缘故,读他们的诗歌,多数时候,我是认领,而非拒绝。时间长了,我被告知,西北的人文环境正像曹有云指出的那样,可以退而求其次,在“边缘”中发掘自己的特色,那或许还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正能量”呢;西北的社会现实,乃至文化现代性,像多数西北诗人描述的那样,可以仍旧保持在“前现代”、甚至原住民的形态中而不被“污染”,大家都高高兴兴地、乐呵呵地庆幸幸亏没生在南国、北上广,没有那么多焦虑、迷茫;西北的政治经济话语,似乎也没有其他地域那么深入,人们好像完全不用担心——也当然没必要担忧个体被规划、被异化、被扭曲的情况,生在西北,目前为止,至少西北诗歌告诉我们的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自己最大的障碍物,是自然,而非其他。
事实果真如此吗?老实说,在系统阅读安琪诗歌以前,我的以上忧虑,只限于我在我的理论文章中压缩性地、修辞性地委婉表达,因为总感觉我的表达仅为个人私密经验、另类“异说”,登不了言说西北的大雅之堂,更遑论跑到前沿向诗人们叫板——诗及诗人,在我眼里,始终是、一直是某种具有鲜明先觉品质的存在。
可是现在,当我慢慢从安琪的语境中回过神来,从即便西北省际之间一坐就是几个乃至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单调而乏味的汽车或火车汽笛声中醒来之时,对于我所置身的环境及其里面内容,就算最敏感的诗歌表达,介入焦虑、痛感、无助感、不确定性的程度着实是低了、浅了、近了,而不是高了、深了、远了。这意味着它们所呈现的语境、问题、遭遇,并非像给予它们的论评那样是及物的、现场的。而及物的、现场的,乃至于由此而生成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感知体验,正是安琪诗歌给我的首要冲击。
二
相对而言,对于安琪诗作的论评频率是相当高的,但我发现,论评文章中,立意在诗歌及思想文化思潮的,和范围规定在诗学本身的,远比在目前社会——也是安琪诗歌具体语境,来正面谈她批判性经验的多得多。后者正是我在西北边地,最迫切需要的一种价值充实,或者,也是我对我的共同体内部的诗歌,最感乏力的一个原因。
在安琪诗歌论评文章中,有两篇值得在这里再讨论一遍。一篇是燎原的《世纪初一代诗人的联动:论中间代》 (本文原发于《中间代诗全集》及《诗歌月刊·下半月》,2006年10/11合刊中间代理论特大号),另一篇是赵思运的《中间代诗人:生长在“上本身”与“下本身”的夹缝中》 (原载:丑石诗歌网)。这两文都学养深厚、才气沛然,尤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堪称关于“后朦胧诗派”以来的中国诗歌断代史。“中间代”的来龙去脉清楚了,安琪的诗歌史坐标也就清楚了;另外,只要“中间代”出场的文化思想语境充分,安琪诗歌世界里的个人经验,也就有了切实的土壤墒情支持。不过,对照安琪诗歌,两文在给了安琪准确时代文化位置的同时,好像又推远了安琪诗歌真正进入该时代文化中心的焦距。因此,安琪诗歌经验,便多少显得远了点、淡了点。也就是安琪诗歌是什么有了,为什么是这个的问题似乎仍悬而未决。
比如燎原认为,安琪的写作“具有一种混乱的才气和罕见的速度”。她的诗歌资源入口呈现着完全敞开的广阔,当这些资源进入她的写作成为遍地碎片,甚至这些碎片又在意念中再度分解,以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时,她却凭借着灵动的诗思和莽撞的才力,在主题意念的统摄中使之强行粘合。所以,他从个人天性气质上,把安琪诗作描述为 “任性”(《任性》)、“奔跑”(《奔跑的栅栏》)、“未完成”。又说这种气质类型似乎像海子,在自己内心无穷诗思的任性纵驰中急促地抵达峰巅;在一次次急促的抵达中,留下了诸多粗糙状的“未完成”。但她没有海子那种野蛮的强度,她的速度是“奔跑”,而海子则是“冲刺”。但无论如何,这类诗人都证明着“诗歌是一种快”现象和原理。燎原的这个结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他所谓“民间诗人”的“快乐原则”,“从而以直接简单的言说,保持当下生存场景中那一生机勃勃的现场感和粗浊感,并在其语义效果的终端,凸现快乐至上的原则。而快乐,则代表着人类的游戏精神中,心灵的撒欢状态。如果考虑到我们的人民大众从苦大仇深、义愤填膺、庄重深沉等一幅幅时代表情中,切换至今天的铁杆球迷式的起哄和狂欢,便自然会明了快乐原则的时代生成基础”。一个是庞德,安琪不但写过庞德,而且也几乎把庞德诗歌视为现代诗的楷模,比如她的诗作《庞德,或诗的肋骨》便是。他把庞德诗歌中,将众多的庞然大物拆解打碎成意象的碎片,然后对其精华做巨无霸式地整合的做法,比附于安琪,“安琪由此为自己的‘任性获得了振奋的根据,并进而将这种手段发挥到她能力的极限。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形态上大都是中型规模,诗行转入碎片填塞中容纳一至两个短句的沓杂长行。而这些碎片,一是来自当下生活场景,其二是来自文化经典和新闻事件”。
同样,赵思运也在“中间代”的社会文化坐标,获得了对安琪长诗——史诗的解释灵感。上个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中间代诗人从众声喧哗转型为个体言说,于是诗人成为个体思考者,而不再是时代的“运动员”。他们是一个松散的个体集结,摒弃了派别专政,呼吁一个诗歌共同体时代的到来——诗歌共产主义。他们摒弃了大而无当的宣言,不善于做“圈地运动”。80年代的民刊多为圈子集结,90年代中间代诗人的民刊之间则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交叉、融合现象。他们每个人作为独特的个体存在,不是组合成圈子,而是不同的“点”渲染出一个流动的活跃的“诗歌场”。“在他们的作品中,少了第三代诗人的软性调侃,少了70后欲望狂欢的肉感,而是充满了于沉沦之狱中的隐忍与决绝抗争”, 安琪的《西藏》《张家界》 《轮回碑》 《灵魂碑》等以“天”、“地”、“神”、“人”等母题构建其史诗体系的长诗,或者将任命书、邀请函、访谈、戏剧、儿歌等各种文体融入进来的开放性文本,变得“形散神也散”,是以散点透视,无中心,拼盘、杂烩,将“其支离破碎的精神之痛与支离破碎的结构的统一,不是证明安琪的‘无能,恰恰证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状况——破碎感”。
三
罗列这些,我想说的是,诸如此类诗歌断代史上的安琪诗歌特点,其实不单是迄今为止的诗歌写作流程不得不有的形式感。与其说是形式的时代反映,毋宁说这形式承载的内容、主题和思想,本身是诗人置身现实的直觉体验。言之凿凿的诗歌理论有理由打捞个体经验的诗学意义,但生活在西北边地基层的诗读者,始终在乎的是诗歌与“我”的关系。如果安琪的长诗只具有被某种理论征用的价值,而与迟滞的诗歌言说,索性说与我感知到的社会学认知无关,那么就此可以断定,所谓特异的个体经验,还不是成熟的诗歌经验。成熟的诗歌经验,只能是、而且必须以基层现实感知为经验来源。
在这个角度,我倒认为,正是《西藏》 《张家界》 《轮回碑》 《灵魂碑》,还包括《任性》 《出场》 《失语》 《风不止》 《神经碑》 《泉州记》 《工具论》 《灵魂的底线》等,就我的体验而言,实际上安琪的写作,是建立在清晰的对个人史诗写作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批判精神凸显,而非有意识的史诗构思。
相对而言,她的诗直觉来源于主流社会学的一个漏洞,或者是对主导性政治经济学话语下的日常生活方式、个体心灵秩序的庄重观照。她的长诗大多数写于漳州,有些直接草就于从漳州出发的路上,这意味着她的写作,根本没有成熟的范本可依凭。创造性转化现实生活,其主要目的在于思想表达,而非精巧整饬的文体结构。只不过,当安琪如此想时,已经前有“启蒙”话语、中有“朦胧诗”,后有日常生活话语、身体话语,而且这些类型写作,基本都有它们成熟的经验模式。安琪只有镶嵌生活现象,再把现象编排进既有的美学程序,然后,再用它来检验该程序的无效,于是,她的修辞既确保了经验的个体性,同时也获得了普遍性的语境支持。比如《灵魂的底线》,看上去,“灵魂的底线”是写通常的个人道德伦理问题,实则指向了长期以来打造如此合法性道德伦理的美学原则。就此而论,我甚至觉得,安琪是中国当代用诗语有效承续福柯以来知识话语权力理论,或鲍德里亚消费主义社会学批判理论的一个最成功的诗人。她以诗的形式,包括语境跳跃、政治经济话语借用和对既有审美方式的调遣,颠覆了“反现代性”的幼稚和“审美现代性”的天真,以及“总体性”的错位。书写的结果是,民生问题不单是一个社会学政治经济学问题,本质上它是一个时代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心灵秩序如何不被遗漏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层面,她诗的“尖锐性”和才华的“混乱”,才在深层结构上取得了对“五四”启蒙话语、“朦胧诗”话语和日常生活、身体话语的价值矫正。抽象的人性诉求、高蹈的人道主义和空洞的身体、个体期许,在她这里,统统化合成一幅幅具体的现实图景。目前个体何以自处,价值何以有效,规划何以生成的问题,才有了切实而微观的阅读体验,不同主体间认同上的隔阂,因感知共鸣而趋于共识,读者从此被唤醒。
所以,我个人认为,诗歌理论所说的她的“拼盘”、“大杂烩”或“未完成”,恐怕是各种理论范式本身的危机问题,不能作为对安琪诗歌的价值定论来看。“农民们推着香蕉为被克扣的磅底无能为力/城市的发展以乡村的停滞为代价/当初是谁供应了一个崭新黎明?是谁创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东方?/你早已因司空见惯而拒绝怀疑/选择的附件,每条道路都有直觉在起作用,但路在哪里?”……“梦想与橱窗不断更替/一切都被系统地设计过,灵魂成为典型消费/物质粉碎时看起来比完整更令人心动/你坚守自己的底线,知其然而不为,因为坚守/文字没能成为事实/简单像佛一样降临,社会以及人们的灾难组合成腐烂/的气息,一种美学原则的摧毁/它甚至直到今天都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延伸/精密的仪器在寻找爆炸现场/你探寻传统,讨论关于远离的努力。”
底层视角就是底层书写,底层书写理所当然就应该具有人文精神的优先权、豁免权,等等,如此形成的文学评价机制,我以为是个伪命题,或者至少是一个需要重新检验的价值立意。安琪的诗歌书写,就反过来颠覆了这种价值体系的正当性。刚才说过,她的长诗大多写于漳州、或从漳州出发的路上,并且从写作日期上看,又是如此之密集,我的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的直觉主要来源于空间,而不是时间。在空间的快速变换中,近三十多年、二十多年、十多年来的时间,被压缩、整合,然后又徐徐展开、扩大、延伸,最终形成了一个诗歌意义上的平面,这正好得益于她跳出底层、在穿行于底层的不同时空差中的把握,成功地甩开了情感共同体、方言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所强塞给她的文化羁绊。也就是说,她是在似乎一以贯之、据说连续性并未打断的社会运行机制中,求证式地、对应式地用逆推的方式来呈现眼前景象。本该拒绝,但“早已因司空见惯而拒绝怀疑”,因而打开“选择的附件”,看起来似乎很丰富,其实这些“附件”已经删除了个体直觉。没有直觉参与的选择,很难说是自主性谋划而来的——但这恰恰是被“梦想”赋予了合理性的集体性期许。这个时候,关于“当初是谁供应了一个崭新黎明?是谁创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东方?”式的“路在哪里”的追问,因是在压缩时间叙事后的空间体察,大片大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未被省会城市、一线城市视野收融的“同一性”日常生活,或者按照鲍曼“赘疣说”来解释,他们其实都是被甩出现代化快车轨道的“新穷人”,是“美丽图景上的污点”和“丑陋而贪婪的杂草”,“不但没有为花园增添和谐的美,反而吸收了许多植物的养分”(《工作、消费、新穷人》)。他们承受着日复一日的麻木,“已厌倦抒情”。“这一切行为归结起来持续到一颗浆果萎缩/留下鸟之的线条/犀利却不含敌意/怀念已呈现不出深度,刻在碑上的铭文/每读一遍就会产生落寞/人们沥青一样衰老/抽象和具象的尘埃,语词堆砌的胆/虚假的繁荣提出辞职申请。”(《神经碑》)
经过时间的空间化处理,我相信,安琪的这些经验,不只是遍布于东南的漳州、西南的滇池(比如雷平阳的诗歌),西北的“甘南”、“格尔木”、“西海固”、“陇西”更是如此,只不过,后者的诗写作,诚如上文所说,是对某种“安全”的诗学理论的照应,大概接近于安琪所谓“因司空见惯而拒绝怀疑”,进而反写想要寻找的路。
这就涉及到诗歌如何处理、消化时代噪音的问题了。即在诗学所指引的方向,特别是“文化寻根”所需要的方向前行,还是直面噪音、杂质,回收并主题化它们的问题?
四
把直觉形式化,和把现实感知提炼成诗的修辞方式,作为一体两面的方法,在安琪诗歌里,主要集中在她对底层世界的体悟上。这里面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尊重个体经验而又不限于个人经验的问题,同时,同样难的是,跳出写作对象后怎样获得其他读者的认同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安琪选择了空间而不是时间,也倾心于快速的观察、大胆聚焦,而不是相对静止的结构,比如人、神、天、地的内部观照(尽管她的个别长诗像有论者说的有这类痕迹)。由此可见,她的这类题材写作,看起来庞杂、繁复,究其实质却是相对单纯和简约的,这完全归功于她自觉的写实主义取向。在写实中,才能准确转化语境,以至于沟通东西南北;关注现象,才能巧妙地凝聚主流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话语所遗漏的地方。那么,飞快变化着的诗歌风格,才会被有效沉淀。尤为重要的是,当“破碎感”作为后现代文化指涉,反过来作用于诗歌写作理念而产生某种趋同的单纯形式之时,安琪的诗歌努力,将其进行了主题性升华,把它变成了价值论本身,这大大扭转了自“后朦胧诗时代”以来诗主体一路低迷、自卑、不自信,乃至于匍匐、平行、低于对象的狭小视野,推进了诗歌重返时代思想前沿的节奏。
这样的诗选择,当她的观照视域越来越大,从“边缘”的漳州进入“中心”的北京之时,或者说,从远距离的观察者置换成零距离的对话者时,她如何处理蜂拥而至的噪音和无处不在的杂质呢?
我想先举几个例子,比如大多数论者不约而同提到的《任性》。有这样的诗句:“那时柯在车上喊:‘看,多好。此时白雾蒸腾于山梁间/沈摇头晃脑‘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做)爱吧。安迅速接上去,同时的尖叫/哄然而出……”;再比如《梨花结》其中的一节:“梨花,梨花,三月的倒春寒,沙尘暴,操心操命的疲惫/疲惫,半夜惊心探讨的事务,事务。猛然间翻身而起的/搜寻,电脑,电脑,屏幕上变化不定的梨花,梨花/暗中超现实的白,你浑身烟火,无一丝文气/你令人爱恨交加的温存,与恐吓,与紧锁的/双眉,梨花!”;还比如《宁夏》,通篇由“某某某说”构成,许多“某某某”其实就是宁夏本土诗人,他们说了什么,说得怎样(其中包括对诗人姓名的拆解),安琪并不予以价值判断。
燎原曾认为,安琪庞德一样地使用着对于汉字的折解手段“是有晃岩被称为日光岩/风像语录那样掀动”——这其中的“晃”之于“日光”。在这些作品中,安琪力图以对这些缤纷碎片的整合,传递出当下生存场景中包罗万象的精神文化信息。因此,这些诗歌在整体形态上,就像当下生存场景本身一样模糊混乱,而在局部和细节上,却有着凸显性的清晰。尤其是她诗歌中大量的这种神来之句:“一个国家的军火在另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个国家流离失所”;“接吻就是以牙还牙”等等,几乎具有一种灵光突至、人力难为的奇幻。
这里面,所谓“当下生存场景中包罗万象的精神文化信息”与解读个别诗句的“灵光突至、人力难为的奇幻”,显然是不对称的。包罗万象与点睛之笔,在逻辑上似乎是成立的,它们的确构成了清晰的因果关系。但我却认为,安琪类似这样的诗歌,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最终推出所谓诗眼而成立,因为它们与前一类诗歌有着完全不同的面向。这一类诗歌的重心仍然在对包罗万象的文化信息的处理上,就犹如酒肆或茶坊,置身嘈杂无度、杂质甚嚣尘上的环境,为了听者听得清楚,你只能以更高分贝的声音来压制一切一样。安琪有意编排市声的杂乱、卧室的工作化,以及只有拆字游戏似乎才吻合情景的场面,是以俗的方式处理俗物、以噪杂消化杂质,并且达到沉淀生活现实的目的。相对应的是,如果躲避噪音和杂质,诗只留下过滤后的清静和安逸,不消说,要么只能滑向本质主义,要么变成异常亢奋的道德主义。问题是,高速旋转的都市生活和无限物化的现代化计时程式,是否允许一个安静的心灵最终把自己打造成经济主义价值观所鼓励的“成功”?
我知道,这或许不是一个严格的诗学问题,但它一定反过来解构整饬精巧的诗学。
五
最近在《文艺报》 (2014-5-12)读到诗人欧阳江河的一篇对话《欧阳江河:诗歌应对时代做更复杂的观照》,其中有一个标题颇为引人注目,叫“从反抒情到反消费”。他所谓“反抒情”,指的是那种迎合消费主义文化口味,把语言“变得很‘甜,到处被引用为格言、广告语”的诗歌修辞,达到事实上的被消费目的;而所谓“反消费”,指反而给读者设置各种各样的阅读障碍、理解障碍,当这种诗歌触及现实生活中的丑陋一面时,便成功避免了处理上因惯性、风格化,导致痛感消失、尖锐性消失,以至于歪打正着异化成仅仅是文化消费品的“消费政治”意识形态,那样的话,艺术的自由之境就彻底被解构了。
安琪是否有此意识,不得而知,但阅读她这一路诗歌,直感告诉我们,她的语词编码所造成的修辞效果,实际上故意回避了“声音文本”应有体验——未必有实指意思,但却能够深深感染听者;也有意拒绝了反复、排比的习见修辞,以干巴巴、赤条条、硬梆梆的词语组装,表达毫无质感可言的冷酷与机械;或者以汤汤水水、荤素混杂、自以为是、自我作古、自我消费的拖沓冗长、毫无节制,揭示人文世界的无聊与狎邪。
自“语言转向”以来,向语言索求意义感,差不多成了当今一切文学文本的根本目的,我们的确从词的华丽流转中和句的温婉动听中,享受了文学的静美。但当有一天我们用来描绘我们生活、刻写我们生命过程的词汇,如同安琪诗歌所示那样,仅止于几个单调名词、动词,或者当我们的语言能力只剩那么一点借用古诗、征用段子,以及凭拆字诉诸文化的能耐之时,我们恐怕就真的不是一个强者、富者和成功者了。从这个隐喻意义上说,安琪对城市人文景观的发现,已经令人吃惊而颤栗。
这一角度来看,安琪诗歌,究其价值诉求而言,无疑是对“五四”启蒙思想话语、“后朦胧诗”的隐喻形式感,和日常生活诗歌写作流的全面诗语转化和整饬。尤其进入北京,把北京作为住地来观照的诗集《极地之境:2003——2012,北京。短诗选。》,放大了看,实际是对“中心”整体人文状况的批判和揭示。思想渊源上,她是在消费主义语境对“五四”思想余绪的诗性凝聚;诗歌形式感上,她是在重新象征化的理念下,对后朦胧诗派中核心审美元素的复活;介入现实的程度上,她是对泛化的日常生活写作趣味的整体性改写,诗被深深地植入了有所指的批判锋芒。如此等等,读她的诗,总感觉虽流派风格显明却不隔;虽带有地方的和个人的体验标记,但能深入到主流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话语缝隙、并能把这个漏洞上升到普遍性人文观照的一个原因。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我所谓西北边地,仅仅是检验安琪诗歌思想价值的一个视角,而决非确指的空间。